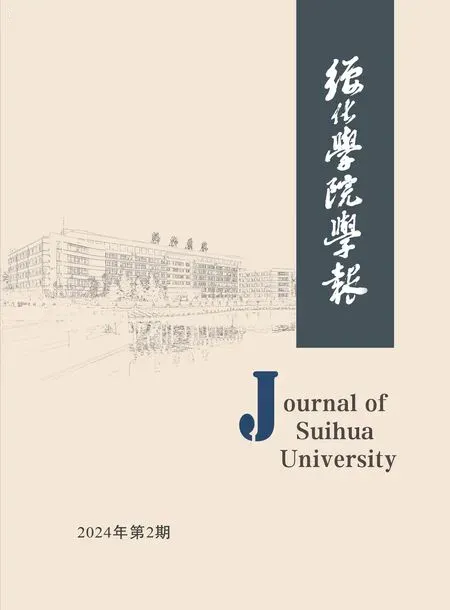鄉村到城市的歷史更迭:文學桂軍生態傳遞的家園情結
沈 明 裴 蓓 祁守仁
(1.廣西農業職業技術大學;2.廣西民族大學 廣西南寧 530000)
文學桂軍作家群體在文本創作中顯現出歷史的承續之關聯,而作為壯族作家的陸地和楊映川,在創作承續關系外,顯現出對于生態美學意義上人的存在狀態的關注。20世紀50年代生存生態的交接姿態和歷史質素,左右了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價值,《美麗的南方》作為表現新中國土改運動風云的文學桂軍第一部長篇小說,其地域和民族意義之外的生態美學表征,值得置放在當代眼光下加以注視。
一、“孤立”對話:土改零余者與石城小怪人
土改小說在20 世紀50 年代并非新鮮之作,而陸地著重取寫土改歷史之初衷,恐怕更多的是一種對于和諧生態的追尋和人的成長意義的重視。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小說文本,實際上是一種時間上的書寫,即以時代背景為刻畫,以宏大和主旋律為意味鋪陳。而改革開放后的小說創作,一方面立足于經濟社會的結構價值嬗變,一方面取材于與以往生活大相徑庭的新新人類生存生態,兩種新中國歷史的社會現實,在《美麗的南方》和《藍百陽的石頭城》中以耦合的方式呈現。
土改革命小說中所謂的零余者,是一種因為政治身份孤立于新中國鄉村場域的精神理想式的孤獨患者,杜為人、傅全昭、馮辛柏和韋廷忠等類型化的土改革命干部形象,是一種真抓實干的土改踐行者和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姿態,其對于鄉土中國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和等級觀念的破除和改良存在著一種對立的孤獨狀態。
《藍百陽的石頭城》主角藍百陽同樣以其厭惡世俗的童性本真成了村民口中的小怪人,這種對于和諧、中和理想的生態回歸,極其貼合地形成了一種跨越式歷史性對話,即生存家園和精神家園的詩性互文,而其互文性鋪伸,顯露出精神家園的孤獨痛感。
可以說,任何一部作品都會成為其他作品的鏡子,同一作家群體,享受同一民族集體無意識文化的作家創作的作品亦要與自身進行歷史對話。藍百陽和杜為人等孤獨者的形象是移植了作者男性革命理想和女性童話意識的人,一個欲望超克的符號。《美麗的南方》里拒絕鄉土權力誘惑堅持革命理想的杜為人等人與《藍百陽的石頭城》里拒絕成為百萬富翁誓死保衛石頭城的藍百陽,在歷史的必然中展開了超越現實的對話,回歸家鄉,回歸內心,找尋個人記憶中至純記憶,堅持純粹的欲望平衡和自然本性,懸擱誘惑并致力和諧,構成了兩部相隔數十年的作品的互文性。因此,土改零余者與石城小怪人所在的空間場所形成了生態美學向度理想之場域的對話。
透過兩個不同的文本我們不難發現,兩個主角都是當時社會的遺世獨立的“不普通的人”。杜為人、馮辛柏等革命青年作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本應順從內心的狹隘而追尋自我的愛情和享受,但這些知識分子多番拒絕思想的動搖,直面地主、土匪、間諜的威逼利誘,將革命事業作為自身最重要的質素,在體驗美麗的南方這片風景大好的地域性符號中追尋真理和價值,顯現出這些知識分子對于居住地、逗留地的感念和對于精神家園的追索,讓他們在追尋精神家園的完滿的同時,生發了與舊惡勢力抗戰到底的決心。
當代生態美學主張人與自然、社會及自身和諧共處,統合西方環境美學的“人類中心主義”“環境中心主義”與中國古代傳統哲學的“萬物齊一”“道法自然”,主張以生態存在論為本,力求達到一種動態平衡與和諧一致的生態審美狀態。藍百陽的生存狀態正是如此。如果說杜為人等革命知識分子的孤獨是一種脫離鄉民社會的認知不清的孤獨,那么藍百陽的孤獨就是一種融入自然的孤獨,但杜為人等人的孤獨是一種自我反思而希求回歸精神家園的自知,藍百陽則是以自然生態作為精神家園的支柱。
石頭是紅水河的產物,此間的石頭似乎以萬物有靈的個性變現出對藍百陽的天然親近。藍百陽從水底拾起來的石頭件件都是價值不菲的寶貝,藍百陽把自己當成他偶然構建的石頭城一份子,一個守護人:“石頭之間看似沒有交流,內在氣息不斷流通、交融,石頭城越來越和諧”[2](P143),在精神交流和自然接觸中,他與石頭城之間形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沒有紅水河就沒有這些寶貝,沒有藍百陽也就不會有人發現這些寶貝的價值,藍百陽如果不想構建一個和諧共生的精神家園,就不會搭建這么一座承載自己至純精神原鄉與生態存在家園的石頭城。但尊重自然與和諧共生恰恰是導致他成為石城小怪人的根本原因。
藍百陽從紅水河里撿到的每一塊石頭都是“金子”,這些“金子”引起了全村甚至村外人的注意,金錢欲望的驅使使所有人化作利益的傀儡,他們不顧藍百陽的勸阻大肆捕撈石頭以獲利,其朋友阿發對他贈給自己的石頭毫無感覺,只是問了一句“我可以賣了它嗎,能賣多少錢?”而全村的人都將這位發現石頭的孩子選擇性遺忘,并認為他不是正常人。母親改嫁后,藍百陽構建的石頭城被城市老板相中,要以百萬元價格購回,他頭也不回地拒絕了,爺爺奶奶和村支書都罵他神經病,不理解其拒絕百萬富翁的出價而寧愿石頭變為無用的物件。
藍百陽因此成了守護石頭城的小怪人,這與杜為人對于革命理想的堅守形成了可感知的互文性對話,而兩種人的“奇怪”皆是現代社會城市與鄉村中不被人理解的童話性固執。
“木棉樹”“農民協會”“大學生身份”和“土改運動”無不指向20 世紀50 年代現實符號記憶,而“紅水河”“圩場”“石頭壘的豬圈”和“石頭城”則明指貧瘠鄉村的原鄉自然復魅。時隔數十年的時代與現實,處在鏡中的精神超克與自然意象記憶,是組構兩部作品的精神助力,純凈天真的情愛關系與自然和諧的生態關系暗指了造夢者必將孤獨的形而上之宿命,即精神家園的純粹與殘忍,而革命理想和斗爭必要的遞歸關系明指知識分子要在精神生態上追尋和諧和生存生態上回歸自然的審美旨歸。
二、欲望懸擱:壯鄉與石城的家園復歸
美麗的南方壯鄉是陸地的精神家園和原鄉家園,也是其塑造的文本形象杜為人等人的精神化身。知識分子身份的一干人等,有的人領了國家任務卻不做實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做聲,有的編辮子,有的剪指甲,有的大口打呵欠,有的掏耳朵,黃懷白教授含著煙斗,好像他不是在參加會議而是在沒有人的客廳里沉思。”[1](P121)有的人每天燉排骨蘿卜湯,宣揚享受論,而全昭和馮辛柏這樣的北大青年,則“整夜睡不著覺,全昭為老祖母所敘述的故事,腦子里留下了舊社會殘酷黑暗的魔影,不覺燃起如焚的憤怒。”[1](P186)因此,陸地在文本中提出,知識分子想要更好地完成土改任務,必須在和鄉民同吃、同住、同勞作的“三同”及以壯鄉為家園的自我認同中改造升華。
而楊映川文本中的家園意象,需要通過其多部作品來考量。對《逃跑的鞋子》而言,城市是其內在本質,城市與人的關系是貫穿整個文本而被凸顯的城市環境論調,主角賀蘭珊的原鄉家園想象和回憶,則是斂聚童年記憶與現實存在的一種回溯情結。反觀《藍百陽的石頭城》,則是以遙遠的城市想象為敘述外殼,本質則指向了貧困鄉村中身處原鄉家園的一群孩子和現實的糾葛程式,這兩種想象姿態與存在姿態皆指向寫作者其對于現代性的反叛,而最終實現形態則是一種拋棄物質居所朝著原鄉家園逆向行進的尺度。
“所有的家園都是個性化的,凝聚了祖輩的勞績與自己的印記,有著自己特有的親情、友情及記憶。”[3](P303)如果說,陶淵明的家園是“園田”,魯迅的家園是“百草園”,那么旅居新加坡的楊映川的家園則是紅水河畔奇異野性的“壯鄉”。在其城市小說中,楊映川已經不止一次筆鋒直轉從城市寫回自己的原鄉家園,那種童年的意識駐地。在《逃跑的鞋子》中主角受挫后對于自己做小女孩時候的想象,自己悠蕩的雙腿以及一本連環畫的宿命指引,特別是路上加在生育自己的鄉村里以斷指為誓將自己的一部分還給原鄉,展示了楊映川不自覺的原鄉回溯,同時,對于分別代表著物質欲望、精神欲望和想象欲望的胖子、于中與路上加的多重誘惑,賀蘭珊選擇以城市的對立者的形象遺世獨立,拒絕城市里不確定性極強的愛情、房子和金錢,展現了她城市逆行的審美選擇,而這選擇無疑是一種對于精神與原鄉家園的逆向主動回歸。楊映川的反現代性傾向無疑在向浪漫主義復歸和對于原鄉家園之追索中顯現,當然,依此來看并不能透徹地讀解其作品的童話性互文及家園情結,因現代社會的另一個側面就在于對于現代的背叛。
純粹不交叉的小說文本就如純粹的理論本文幾無可能一樣,《藍百陽的石頭城》盡管將大量筆墨放置在了紅水河畔一個貧瘠的鄉村中,其植被之不適生長的自然環境并不能指向整個文本的鄉土再現,實際上,城市背景則像堅硬的外殼一般左右著整個文本的走向。
其一,城市幽靈促成了弄里村生存原鄉的嬗變。如若沒有城市里的有錢人的慧眼識珠,也就不會有弄里村挖石頭、賣石頭的后續,在這種敘述中城里人作為一種金錢掌控者的局外人一般左右著弄里村村民的欲望,按照常理而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應該順理成章地成為物質的奴隸,名牌包包、汽車、豪宅,這些城市獨有的名詞像是理所應當一般附著在城市男男女女的身上,而鄉村作為城市的大背景,一個縮小了的無人問津的家園,一個城市人曾經的故土,自然難以脫離城市的影響。藍百陽在欲望如蓋的現實選擇向度則和其他村民不同。
弄里村的村民賣了石頭后開始發家致富,有的買了新球鞋,有的買了新手表,還有新摩托車、新電視機,這些作為城市次級化的城鎮符號像是理所應當一般嫁接到了開始以賣石頭為生的弄里村,欲望吞噬了村民的天性,貪婪則一步步追逐著村民的背影。藍百陽則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他的觀念里,石頭屬于紅水河,他懼怕拿了紅水河的東西以后會加倍地還回去,這種割裂了自然與人和諧狀態的貪婪最終導致了藍百陽父親的死,作為將欲望懸擱的自然人,藍百陽仍然擁有那一座價值不菲的石頭城,但他卻永遠失去了父親,一個為村民的欲望買單的老實人。和村民相比,藍百陽的行為是逆城市化的,用村民的話說,是傻子,是怪人,一個不想賺錢改變自己生活的人,怎么會是個聰明人呢?然而聰明反被聰明誤,父親的死,更加加強了藍百陽這一角色的反現代性和對于原鄉家園的逆向回望,即對于紅水河與紅土地的和諧平衡的尊重,不愿打破這種平衡便是最好的力證。
其二,物質都市牢籠囚禁原鄉靈魂。藍百陽在小學升入初中后,遇到一次南寧春游的機會。作者沒有選擇自己的家鄉百色市,亦沒有選擇濱海城市與桂林文化城,而是選擇了一個擁有700多萬人口的廣西唯一的大城市——南寧,這種選擇并非無指向意義的選取。南寧,作為一個多民族融合的新興城市,其建立的群眾基礎是由四面八方的鄉村原住民和外來人口構成的,而作為眾多鄉民中的一員,作者對這座欲望城市又愛又恨,因此,她特意將砸死藍百陽父親的重達數百斤的石頭,極其意外地置放在南寧買家丁西順的私有財產的門外,一尊囚禁了紅水河原住鄉民的靈魂的石頭,無法左右自己命運地落在了南湖路42號“金石齋”的門前。
金石齋,一個欲望和家園合二為一的意義指稱,像是一種昭示了村民命運的究極宿命符號。村民為了金子(錢)而選擇涉險挖石,用命換來的石頭裝飾了石齋,確實得到了金子(錢),這種輪回分明將欲望和代價指向了藍百陽生活的家園,死去的父親(作為人的審美主體)與紅水河之巨石(生態客體)的永恒共生,是以靈魂附貼為代價,以供城市人賞玩為表征的宿命歸一。
其三,人性呼喚割裂石城生態的人與人和諧。藍百陽并不是個貪財之人,盡管他的周身環繞著太多見利忘義的貪財鄉民,但他始終是一個逆行少年。這在他到南寧春游,見了丁西順卻只是摸了摸砸死他阿爸的石頭時表現的淋漓盡致,沒有吵鬧和爭執,藍百陽也沒有跟丁希順討回公道,只是流著淚感受著石頭的溫度,感受著死去的阿爸的靈魂和氣息,臨走時,留下了“石頭是最好的記錄者,每一顆石頭都有一個專屬的故事”的奇妙的讖言,他像一個石頭的代言人或是先知一般,淡淡地留下了自己純粹而單純的讀解,而最終破壞了他自己所造之石城生態的人又恰恰是他自己,就像他自己說的,每一顆石頭都有一個專屬的故事,而他也和石頭一樣,有著自己的故事。
而他的故事,則是從人性底部發出的呼喚,即母親的隱忍和弟弟的疾病。改嫁的母親沒臉見自己原生家庭的一雙兒女,藍百陽費勁心思找到了母親,卻得知自己擁有一個剛出生不久便確診為嚴重疾病的弟弟,為了給弟弟做手術,他毅然決然地打破了石頭城原本的生態平衡,決定以拍賣的方式將這價值百萬的石城托于他人之手。最終,那個曾經購買了附著父親氣息的石頭的丁希順以100萬的價格,將石城帶離弄里村,進而塵落大城市。
盡管藍百陽破壞了石城與自己的生態平衡,但卻換來了弟弟的得救,從而演進為人與人之間的平衡,而為了打破這種生態與人的偏移,他把弟弟治病剩下的幾十萬全部捐給了鄉政府,用來修繕因洪水河災沖破的大橋。大橋落成之后,藍百陽給這座橋起名為“石頭橋”,塵歸塵土歸土,這些錢從紅水河而來,最終送回紅水河去,不顧阿公的“這些錢能在城里買兩套房子”的勸阻,也不問村民們是否感謝自己,他所關心的是一種家園的和諧,自己和弟弟、母親、繼父之間的和諧,自己和紅水河、石頭城、原鄉的紅土之間的和諧。
藍百陽和杜為人等人異路同向,分別以懸擱欲望指向了原鄉家園的回歸,正如藍百陽的心里話“從這河里得到的,我都還回去了,紅水河,你應該歡喜吧!”[2](P195)說的那樣,揚眉在南方壯鄉所失卻了自己原有的小資情緒和猶豫性格,她以沉痛的代價收獲了成長,收獲了忠于自己精神家園的寶貝,一種榮譽和赴朝鮮作戰的愛人的肯定;藍百陽則收獲了一種灑脫,一種歡愉,一種難得的少年成長之經歷。面對欲望,陸地與楊映川的土改小說與兒童小說的主角都以極其純粹的生態理想,和諧地處于世界的平衡中,無一偏移。
三、詩化家園:回歸純粹的生態性
欲望意象的中止和家園意象的獲得,是陸地與楊映川小說創作回歸純粹的生態質素。楊映川的家園是一種毫無疑問的詩意的童話家園,而其塑造的類型化的女性角色與兒童文學形象,成為了其詩化家園的耕地者和代言人。而陸地的家園是一種革命意味極強和生存意義極盛的人性家園,這片家園里的鄉民同生活在這里的大城市知識分子們在意象堆疊的美麗的南方共同營造了一種詩意。
《美麗的南方》中,陸地著重通過排骨湯、卷煙、旗袍、牛肉罐頭等意象暗指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的游移不定,在土改問題中,這群知識分子一開始表現出自身的徘徊、猶豫和不成熟,而文本中的整個場域以不和諧到和諧指稱。地主覃俊三破壞了韋廷忠童年的和諧,家庭的和諧,和人生的和諧。生存環境被剝奪、異化,妻子和唯一的骨肉被覃俊三伙同梁正、婦女主任趙佩珍殺害,盡管面對著如詩如畫的南國壯鄉,知識分子們和廷忠等被迫害鄉民沒有一天感受到南國和諧的氛圍,而這種氛圍,嚴重違背了詩意棲居的審美期待。
這種異化通過深入群眾、查找問題逐漸淡化,最終,覃俊三和何其多被繩之于法,他們謀害良民、打擊土改、強迫少女、殺害戰士的惡行,通過土改隊員的努力和鄉民的配合終于有了解決,因此,便出現了“大地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改換了新裝,村邊和房屋的枇杷樹,在闊大濃綠的葉子下伸出了迷人的果實;豐碩的荔枝掛滿了枝頭;木棉棉桃開始吐著飛絮,春風把它的籽送到別處;玉米已開始結穗;扁豆蔓兒爭先恐后地攀到棚架上,接受雨露和陽光”[1](P306)至此,精神的蛻變影響了戰斗的效果,土改的生力生發了鄉民的自由和和諧,詩意的棲居落到實處。
《藍百陽的石頭城》所描寫的改革開放后的城市權力控制下的鄉村,有必要和楊映川其他城市小說進行對比,以期探求作者對于生命和諧追尋的耦合之姿態。《逃跑的鞋子》是一部富有哲思意義的城市小說,男女角色的二元對立承擔了女性角色純愛理念的不可靠性。在文本中,賀蘭珊對于酒吧、高樓、奔馳車等城市意象的輕視,反常規地為讀者宣告了一個城市零余者的不現實理想,但逃跑這種富有現代性哲思的方式正是撕破城市欲望面具的有效手段。楊映川小說中的女性角色都在逃跑,她們從不屈服于金錢或是權力,任何“農民企業家”和“暴發戶”都是例證女主角追索純粹愛情的工具,而書中的男性也成為了維持城市社會中人與人動態平衡的籌碼。
賀蘭珊利用這些籌碼生存,不想自己也被這些籌碼所利用。而平衡一但打破,置換的必定是慘痛的代價,但楊映川筆下的女主角從不畏懼這種代價,《只愛陌生人》里白蘭心苦苦等待卻不覺乏味的“研究生男友”秦山,《愛情侏羅紀》里拒絕現實追求幻覺之愛的小嬋,所有主角都有一個共性,她們拒絕與現實妥協,反而追尋柏拉圖式的幻覺。而賀蘭珊對于放棄豪宅、金錢、名利的選擇無異于是對于自己戲弄城市玩偶的懲罰,她知道這種平衡一旦打破,自己將會墜入無盡的深淵,因此,她拒絕于中的豪宅,拒絕唱片公司的邀約,為了自己純粹的愛情將肉體置之度外,這無疑是一種精神家園的依皈,而孩子只是賀蘭珊詩性童話的結晶,以至于孩子的父親是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對于純愛的堅持。
藍百陽則與土改隊員們展開對話。一個少年與一群革命理想熏染的知識分子,在不同的年代做出了同樣的抉擇,即放棄淪為權力的奴隸,馬不停蹄地追尋自己詩意的棲居。
相比于《美麗的南方》里革命意象的鋪陳,《藍百陽的石頭城》則以原鄉意象對前者形成錯位性的互文對話。從紅水河原鄉的飲食意象茶油、艾粑、玉米酒,到原鄉地理意象紅土、白巖壁、溶洞穴,再到原鄉人文意象阿公、藍姓、祭祖,作者把自己童年的記憶原封不動地搬到了文本中,以獨特的人文、地理和飲食疊加的紅水河區域意象吊足了讀者的胃口,讓讀者在感知這些詩意家園的詩化意象同時,忘卻了城市的喧囂與聒噪,是一種強制換位的意義指向。
不論是賀蘭珊還是杜為人、楊梅、韋廷忠,這些角色都適應了各自存在的動態循環,即對于精神家園和原鄉家園的歸返,意象作為鋪墊和反襯,折射出陸地和楊映川對于純粹的家園的理想與現實努力,展現了二人詩化意象的審美追求和純粹人性的審美生態。
兩個作者在創作兩篇小說的時候并沒有任何的問題勾連意圖,通過讀解,那種對于純粹人性之情感的追尋使其創作較好地循環于文學桂軍兩位作家所構建的生態文本世界中,兩部跨越數十年之久的不同形式、不同主角的小說文本,宿命般地形成了一種互文性的對話與互動,自覺地完成了人、物與家園的生態平衡。或許,土改零余者和石城小怪人才是我們這個社會所缺少的“真正的人”,遺忘了自己精神家園和原鄉家園的所謂的“城市人”是無法實現自身自由棲居的生存夢境的,但文本中的主角們,是真正活出了自己,進入了“詩意棲居于家園”的純粹世界,以知識分子自我革新和鄉村少年自身成長之故事生力,在兩位壯族作者純粹的審美理想中升華,完成了對自身的超越,實現了人與人、人與家園的和諧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