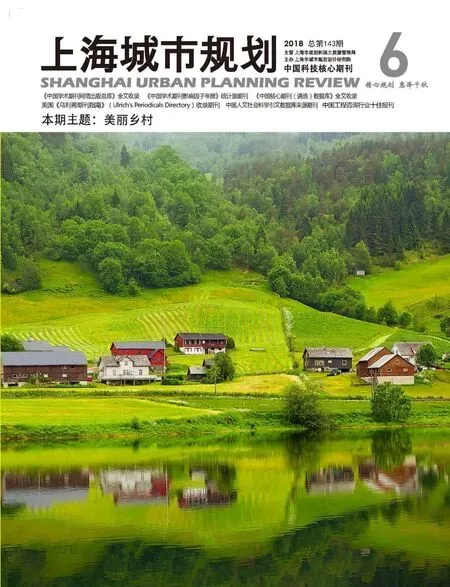文化定樁:鄉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間營造*
——浙江黃巖嶼頭鄉沙灘村實踐探索
楊貴慶 肖穎禾
0 引言
我國廣袤的土地上散布著大量的鄉村聚落,它們承載著千百年來積累的優秀傳統文化。由于我國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建筑風貌以及鄉土民俗有著較大差別,在不同的歷史和地域環境下形成的鄉村文化也因此具有多樣性和地方性特征。隨著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轉變,鄉村聚落普遍呈現出傳統社會結構瓦解和空間衰敗的現象,尤其是在傳統鄉村聚落中曾經承擔核心功能、具有重要社會內涵和文化價值的核心公共空間,由于其難以適應新時代鄉村社會的新功能需求而逐漸荒廢。反觀一些地區的鄉村規劃建設,千篇一律問題較為嚴重。缺失地方風貌特色和文化特質的鄉村規劃建設較為普遍,甚至出現了由于理論認識水平有限、規劃對策不當而導致的“建設性破壞”,令人十分痛心。我國鄉村人居環境蘊含的地方文化多樣性正在急速變化的社會經濟空間進程中快速消失。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靈魂。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 2022年)》中也提出要繁榮發展鄉村文化。近年來全國多地開展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從2013年起每年開展歷史文化傳統村落保護利用工作,截至目前已有7批共304個重點村、1 484個一般村的保護利用項目。通過保護和利用,傳承了鄉村聚落的優秀傳統文化。總體上看,理論研究亟待深入,實踐范式亟待總結。那么,如何認識鄉村聚落的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三者的關系?如何看待鄉村聚落的文化性、社會性的演進特征?又如何以文化振興為靈魂、通過鄉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間的規劃營造來實現鄉村振興呢?本文將從理論層面對上述問題展開研究,并結合浙江黃巖鄉村振興的實踐,探討“文化定樁”這一工作方法的實踐成果。希望本研究對同類規劃實踐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1 概念解析
“文化定樁”指通過對地方各類型文化資源進行挖掘、整理和提煉,確定鄉村物質空間和精神內涵的主題,以統領鄉村產業經濟、社會文化和空間環境的各項實踐。“鄉村聚落”是指在傳統農業社會背景和手工生產條件下,人類為了定居而形成的相對集中并具有一定規模的住宅建筑及其空間環境[1],是以農村人口為主且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居環境類型。“核心公共空間”指集中反映鄉村聚落社會關系主要特征、承載鄉村社會文化認同的公共活動場所。
2 鄉村聚落的文化特質及當代意義
2.1 鄉村聚落歷史演進的文化特質
鄉村聚落的形成和演進受到不同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軍事防御等諸多因素影響。在生產力水平較為落后的時期,以生存繁衍為基本目的的定居多選址在易于耕種、收成和避災的地區,先民的耕作活動逐漸發展形成鄉村聚落。農作物收成主要依靠自然條件,而災害的打擊讓人無所適從。因此,“靠天吃飯”反映出對自然的依賴,也伴隨著對自然災害的恐懼。由此產生對自然力的敬畏和崇拜,將一切吉兇禍福歸于神的力量,敬神祈福成為原始民眾的精神支柱[2]。各地鄉村聚落信奉的神靈不同,常見的有供奉土地神求風調雨順,東南沿海地區信奉媽祖求出海平安,藏族地區信仰山神求豐收和安康等。自然崇拜逐漸成為鄉村聚落文化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抵抗自然災害威脅、外族侵略和兵災威脅,鄉村聚落的發展要求家族成員緊密團結并以聚居方式相互支撐。隨著封建社會宗法制度的推行以及宗族制度的倡導,鄉村以血緣和親緣關系聚族而居的現象普遍存在。宗族制度講究依照血緣等級的原則維護家族秩序[3],強調家族整體優先于個人,一切以家族的團結、延續為宗旨。為增強家族凝聚力和認同感,通過建造祠堂、編制族譜等方式傳承秩序觀念,祭祀先祖,表達對先祖的尊崇并祈求保佑,如劉軍[4]研究的廣東謳坑村中的盧氏家族通過大規模拜山活動祭祀先祖表達敬意、祈求財富和安全;通過制定家規家訓宣揚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義等品德,紀念品行杰出的族人以宣揚家族精神;講究“學而優則仕”,以做官光宗耀祖、衣錦還鄉為榮。這樣的鄉村聚落集體認同感和向心力最強,一方面由于家族嚴密的血緣網絡的資源調配,另一方面來自內心對祖先的極度尊崇和族眾的友善[5]。
如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鄉關系二元結構徹底打破了傳統農耕社會高穩定的鄉村社會一元結構。鄉村聚落大量的勞動力等資源要素外流至城鎮,鄉村總人口特別是青壯年人口急速減少,“空心村”現象非常普遍。由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導致村民對自然力量崇拜意識的減弱;同時,生產關系的變化導致傳統大家庭結構瓦解,代之以核心家庭主體結構,導致宗族觀念降低,村民的集體感與歸屬感減弱。傳統的農業社會和耕作經濟下形成的鄉村社會結構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下逐步瓦解,鄉村聚落的傳統文化特質也隨之流失。
2.2 鄉村聚落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
鄉村聚落傳統文化具有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以保全生存、繁衍發展為目標的鄉村聚落,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包括家族文化、鄉土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及物質文化等。傳統家族文化中提倡的長幼有序、孝敬長輩等觀念仍可促進當代鄉村聚落的鄉風文明建設,對具有優秀品行的人或事跡的傳頌紀念也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種方式。鄉村聚落的傳統民俗文化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文化本底。它極大地豐富了鄉村日常生活內容。民俗活動的舉辦有助于鄉村社區活力的提升以及鄰里關系的鞏固,是現代鄉村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重要來源。因此,這些文化內涵在當今依然有其積極意義和實用價值,其社會價值對當代鄉村聚落社會結構的活力仍可發揮借鑒作用。
鄉村聚落中的鄉土信仰文化發源于對自然、祖先和優秀人物的崇拜,給村民以精神慰藉并進行道德教化,也是鄉村聚落重要的共同價值構建基礎及社會凝聚力量之一。鄉土信仰文化能影響村民價值觀念并維系社會關系,郎維偉等[6]認為沈村的兩種宗教文化不僅在精神領域對村民行為制定了規范準則,而且通過貼近村民生活的宗教儀式來滿足村民心理需求,兩種宗教文化共同成為村落社會維系的精神要素。龔成紅等[7]認為宗教文化始終是打拉池人歷史接續和社會維系的主線,宗教是社會整合的重要機制之一。
鄉村聚落演變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特質具有多樣性和地域性,并對正在轉型的鄉村社會關系的重構有重要的社會意義。鄉村振興中提出文化振興是靈魂,深入挖掘鄉村文化,通過豐富文化的表現形式、提供多樣的物質及活動載體等方式,發揮文化的引領作用,促進城鄉文化融合,在保護傳承的基礎上賦予時代內涵。因此,對鄉村聚落的文化特質進行具有當代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使命。
3 鄉村聚落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的有機對應
3.1 鄉村聚落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的相互關系
鄉村聚落的文化特質不是孤立存在的。根據對鄉村聚落的文化觀念、社會結構以及空間形態的研究發現,鄉村聚落的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具有有機的對應關系(圖1)。鄉村聚落從生存繁衍的本底向宗族發展壯大的目標行進,正是三者有機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建構的過程。鄉村社會結構的變化影響村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和生活方式也會作用于文化觀念的形成,文化觀念反過來也會改變社會的結構。而文化和社會的關系正是通過物質空間加以呈現,物質空間同時也鞏固了鄉村聚落的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

圖1 鄉村聚落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的有機對應關系

圖2 南海霍氏合爨圖
鄉村聚落的村落空間結構形態以及建筑內部功能空間的布局一般是由家族社會結構關系決定的,而社會結構與空間結構的對應關系也是社會文化和建筑文化形成的基礎。鄉村聚落的家族文化中,宗族觀念的空間承載即為聚落中的祠堂以及民居中的祖堂等,是祭祖、家族議會以及舉辦家族活動的場所。聚族而居的方式決定了民居建筑群的規模尺度。祠堂、組屋在聚落中的布局方式以及中軸對稱的民居內部布局反映了家族的等級觀念,如南海霍氏合爨圖即為封建社會累世同居的民居典型(圖2),充分展示出霍氏家族的等級秩序。家族文化中宣揚的禮制思想可通過牌坊體現,鄉村聚落中的牌坊包括忠烈坊、功名坊、功德坊、節孝坊、義行坊等,以紀念在不同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族人。例如,安徽歙縣棠樾村的村口按忠孝禮義列有7座排坊。聚落中的文昌閣、文峰塔等信仰建筑,以及書院、文廟、文館等都是“學而優則仕”思想的產物[2],展示了對文化教育的倡導。而這些反映社會結構關系和公共價值觀念的場所,通常都是村落或家族院落中重要的核心公共空間。
鄉村聚落的鄉土信仰文化可由寺廟、鐘樓以及佛堂等物質空間展現。鐘樓、祭壇、土地廟等是崇敬自然的象征,關公廟、觀音廟等是祈求所供奉的神話人物的保佑,還有一些雜祀的廟殿,供奉當地具有一定神化色彩的先賢。鄉土信仰場所通過承載信仰活動來體現鄉土信仰文化,主要是在日常和節慶期間為祭拜祈禱和集體信仰儀式活動提供空間載體。鄉土信仰建筑的空間類型及分布與其功能及服務范圍有關,如規模較大的院落式或獨殿式信仰場所通常供奉護佑范圍較廣的神靈,也多位于護佑范圍的中心位置;規模較小的自由式信仰場所則多供奉護佑范圍小的神靈,可能是一間小屋子或僅由建筑圍墻外龕壇構成,與居民的生活場所較近[8]。這些鄉土信仰場所也是鄉村聚落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俗文化通常是由家族文化和鄉土信仰文化為基礎衍生而來,空間呈現為以承載民俗活動的公共空間為主。鄉村聚落中,建筑文化一方面由普通民居形式體現,另一方面通過聚落中反映核心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的公共建筑或構筑物來展現。由上可見,鄉村聚落中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精神相互依存,共同存放于物質空間,并以公共空間為主要載體(圖3-圖4)。

圖3 鄉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間的文化彰顯

圖4 沙灘村核心公共空間
3.2 鄉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間的文化性和社會性的演進特征
鄉村聚落的公共空間反映了社會政治關系,也蘊涵了深層次的文化含義[9]。核心公共空間集中反映社會關系主要特征,體現社會核心公共精神,承載重要文化內涵,是鄉村聚落社會性和文化性在物質空間層面主要的載體。
3.2.1 核心公共空間的物質呈現
核心公共空間是鄉村聚落整體空間結構中重要的內容,通常位于鄉村聚落空間的重要位置,如鄉村聚落的幾何中心位置附近,或聚落邊緣但海拔較高處。核心公共空間的建筑通常體量較普通民居大,或建筑高度較高,或具有較大的廣場空間,空間識別性強。同時,作為聚落布局中心或村民公共活動中心,核心公共空間的可達性較高。云南傣族村寨中的核心公共空間是佛寺及其周邊場地,部分傣族村寨地處山區,佛寺建于村寨邊緣(圖5),或處在山坡最高處(圖6),是全村寨的制高點,或建于村口,便于在遠處識別。侗族村寨中鼓樓及其周邊場地即為全村的核心公共空間,普通民居圍繞鼓樓而建,鼓樓多位于村寨中心位置(圖7),且高度明顯高于周邊普通民居。核心公共空間在位置、空間體量和布局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空間上呈現明顯的中心性和統領地位。

圖5 云南西雙版納橄欖壩曼聽寨平面圖

圖6 云南景洪傣族村寨鳥瞰圖

圖7 貴州叢江侗族村寨鳥瞰圖

圖8 福建南靖書洋鄉田螺坑村平面圖

圖9 四川犍為縣羅城鎮核心公共空間
3.2.2 核心公共空間的文化性和社會性
核心公共空間的空間布局特殊性與其在領域中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主導和控制作用相對應。鄉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間的標識性表達了社會控制的核心價值[1],是聚落社會結構、公共價值和公共精神的集中體現。核心公共空間通常是以宗祠、廟宇、鼓樓等具有社會意義的建筑為主體,周邊配以廣場、戲臺等,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心理認知場所。
以宗祠為主體的核心公共空間反映了該鄉村聚落是以血緣、親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社會,注重家族集體的力量和榮譽。土樓或圍屋是歷史上一些戰爭移民定居后建造的以防御為目的的居住建筑,通常一個土樓或圍屋即為一個家族的聚居組團。從村落的整體布局來看,并無明顯的中心性空間,但各土樓或圍屋自身圍合的中心公共場所是該聚落族人進行信息交流、公共活動的核心公共空間,此處多為家族祠堂所在地,反映了族人重視凝聚家族力量,共同抵抗外界侵犯以確保家族得以生存繁衍(圖8)。
在鄉土信仰文化興盛的地區,廟宇、鼓樓等信仰場所作為鄉村聚落的核心公共空間,是鄉村聚落傳統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穴位”。傣族是信奉南傳佛教的民族,佛寺是全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其在空間布局上的顯著性,也正印證了佛教在傣族村民精神層面上的突出地位。侗族村寨中的鼓樓多為同一地區或族姓共同集資興建的供集體使用的公共建筑,用于通報重大事件,結合周邊曬坪成為村民踩堂、祭祖、集會、議事、娛樂的重要場所[2]。鼓樓還具有宣揚禮教思想的功能,如貴州黎平肇興大寨的5座鼓樓分別按仁、義、禮、智、信命名,以表達對儒家思想的尊崇,并以此為道德準則構建和諧社會關系。可見鼓樓在鄉村聚落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統領地位,與其在村寨空間的中心位置也是有機對應的。
在一些家族觀念或鄉土信仰文化相對較弱的地區,聚落的核心公共空間多適應于村民在產業或生活中的實際功能需求。如四川樂山市犍為縣商貿村鎮羅城古鎮的核心公共空間為船形主街,因居民多為廣東移民,家族文化或宗教文化的氣息并不濃厚,但船形主街“同舟共濟”、“船首望鄉”的寓意卻間接體現了思鄉文化[2]。主街為商業街,中央為戲臺、牌坊及階梯狀觀劇空間,可見該聚落核心公共空間的功能以商業和休閑娛樂為主,側重實用性。主街盡端的靈官廟地勢相對較高,但中心性不強,反映出宗教文化在該聚落中并非統領地位(圖9)。
因此,鄉村聚落的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有機對應,文化特質的傳承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結構和空間形態。而空間形態中,核心公共空間是主要社會結構和核心精神文化的物質空間載體,鄉村文化振興應以核心公共空間為觸媒進行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3.3 鄉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間重塑的辨證觀
核心公共空間的文化性和社會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發展不斷改變,相互適應。例如,在長期農耕文明時代,核心公共空間多為象征家族精神或鄉土信仰文化的場所,而在20世紀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則為供銷社、曬場等集體生產勞動場所。在改革開放后,鄉村聚落的傳統核心公共空間的中心性弱化,代之以新功能的行政文化場所,而如今主要呈現由商業、娛樂活動廣場為核心公共空間的形態特征。不同時期的核心公共空間適應了當時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反映了特定時期的文化性和社會性。
時代發展要求我們應當辨證地看待不同時期核心公共空間的文化價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其中適應當代發展的文化加以保護、傳承和更新。如今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已然改變,核心公共空間的重塑要適應新的生產關系、社會背景和發展前景,而不是對各歷史時期核心公共空間的簡單的修復重建。應尊重當地鄉村聚落文化發展類型的多樣性,同時,采取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方式予以傳承并發展。例如,同濟大學常青等開展杭州來氏聚落再生設計就充分考慮了長河古鎮3個發展階段中3種不同的文明。不同文化以不同形式的建筑體現:農耕文明遺產的清代和民國傳統建筑、20世紀50至70年代初期工業文明改造下的“革命現代式”建筑、近年來受后工業文明影響的聚落新建筑。在上述3種文明依次作用下,來氏聚落的文脈在延續中逐漸演變。他主張再生設計的“首要目標就是在保持不同文明形態可識別性的前提下,對聚落新舊空間要素進行整合,從而維持風土環境的文脈延續性,并使之融入現代都市生活演化的進程”[10]。因此,鄉村聚落的文化特質隨著歷史演變也在發生變化,文化的傳承應適應當代鄉村生活,衍生出具有時代特征的鄉村文化。
4 以核心公共空間為“穴位”的鄉村振興文化定樁
在當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各地正在開展鄉村振興的探索。浙江黃巖的鄉村振興實踐已經取得一些成效,歸納其中的經驗得到“鄉村振興工作法”[11],其中位于首位的即為“文化定樁”。文化定樁落實在空間上即為鄉村聚落中的核心公共空間的營造。

圖10 沙灘村現狀用地及公共設施分布圖

圖11 沙灘村規劃用地及公共設施分布
4.1 文化定樁工作法
黃巖區嶼頭鄉沙灘村是浙江省級歷史文化村落,文化底蘊深厚,是擁有太尉殿為代表的道教文化、柔川書院的儒家文化、農耕文化、中醫養生文化以及近現代建筑文化的美麗鄉村試點村,文化要素豐富多樣。但文化振興不是對文化要素的簡單挖掘和保護,而是要在生產力生產關系變化、城鄉要素流動的背景下,對文化要素進行保護性利用,適應現代鄉村的居民生活需求和旅游服務需求。由于鄉村聚落的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密不可分,文化定樁要與產業、社會、空間等有機結合,產生“造血”機能。
文化振興應在區域宏觀背景下進行,充分考慮鄉域、村域、村莊之間的關系聯動。村莊是否進行振興以及如何振興要根據整體的村莊體系結構來確定,而后對其進行系統性的規劃。沙灘村在老村東側進行了新村和集鎮建設,新建鄉政府、商業設施等均分布在新村,而老村的建筑、街巷空間因不能適應新的功能需求而逐漸衰退(圖10)。對此,在宏觀層面將沙灘老村放在集鎮中考慮,基于其豐富的文化要素而將其作為集鎮總體規劃中的文化功能板塊。
在定位明確后,采用一系列方法來進行文化定樁,主要包括:(1)尋找到村民的文化認同點,如祖廟、祠堂、風俗、手藝等;(2)修復、重建或新建當地村民認同的文化傳承點;(3)結合當地風情習俗,規劃建設不同層次的文化設施;(4)建設文化禮堂,導入新時代先進文化與道德風尚。沙灘村中存在太尉殿和柔川書院兩大文化建筑以及人民公社時期的鄉公所、獸醫站、衛生院、糧站等公共建筑(圖10),均為不同時期村民的文化認同點。但現狀大多已荒廢,仍然發揮公共服務功能的建筑數量很少,并不能滿足村民需求。針對公共服務設施供需之間的矛盾,對歷史上的文化認同點進行修復和改造。最終實現對老村中具有文化內涵的建筑的保護和重建,并結合村民活動及鄉村旅游的需求進行適應性功能改造(圖11),從而延續老村的文脈,恢復沙灘村的文化氣息。如柔川書院恢復成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基地,同時兼有鄉村振興學院的功能;人民公社時期的建筑根據其位置布局和室內空間,適應性地改造為信息服務中心、文化禮堂、民宿等功能。
4.2 鄉村聚落核心公共空間的營造實踐
文化定樁首先針對鄉村聚落中衰敗的建筑和空間環境,尤其是具有文化內涵的核心公共空間。核心公共空間一般具有較好的物質空間基礎,是聚落傳統文化特質的主要載體、村民的文化認同點,因此也是文化振興重要且首要的“穴位”。聚焦于核心公共空間進行文化定樁,便于在有限的資金條件下落實,從而帶動鄉村聚落文化的全面振興。文化定樁結合點穴啟動的方式,適用于資金條件受限的鄉村逐步推進文化振興,可操作性較強。
沙灘村的規劃建設起源于對鄉村獨有文化內涵的挖掘,最終定位于太尉殿南側,營造新的社戲廣場。太尉殿建于南宋年間,距今已有800多年歷史,元貞乙未(1295年)修建時有石刻碑文記載,其建造緣起是紀念因撲火救人而犧牲的沙灘村村民黃希旦,受到御賜“太尉殿”和“忠應廟”,后人將他奉為先祖。至今,太尉殿香火旺盛,每逢農歷十月初一,村民依然通過舉辦社戲活動來表達對先祖的崇敬。“崇尚英雄”和“養我德行”是沙灘村的文化之根,也是沙灘村文化振興的基石,太尉殿即為沙灘村村民的文化認同點。在充分挖掘沙灘村的文化之后,對核心公共空間進行規劃設計。原先的太尉殿建筑破損,殿前空間雜亂荒廢。為適應村民供奉活動需求、弘揚沙灘村文化,規劃設計沙灘村社戲廣場,整理太尉殿前分散雜亂的茅廁、垃圾,配置干凈整潔實用的公共廁所,修建戲臺和亭廊,形成以太尉殿為主,由戲臺、社戲廣場以及配套設施共同組成的核心公共空間,重塑村民的文化傳承點(圖12-圖15)。

圖12 沙灘老村核心區現狀平面圖

圖13 沙灘老村核心區規劃平面圖

圖14 沙灘村核心公共空間平面圖

圖15 沙灘老村核心區模型效果圖

圖16 沙灘村廣場舞

圖17 沙灘村太極拳表演

圖18 沙灘村社戲表演

圖19 沙灘村黃氏園譜慶典大會
空間通過功能使用產生意義。沙灘村的核心公共空間是以太尉殿為主體的鄉土信仰空間,也是村內家族活動的舉辦場所,同時還能滿足現代村民休憩交流、體育健身的空間需求(圖16-圖19)。核心公共空間的建成帶動了周邊其他公共活動場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修復的柔川學堂兼有鄉村振興學院的功能,人民公社時期建成的多處集體設施也適應性地改造為信息服務中心、文化禮堂和民宿等功能。以核心公共空間為中心的沙灘老村修復改造,在尊崇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沙灘村核心公共空間的營造,為沙灘村的黃氏村民祭祖活動和鄉土信仰活動提供了場所,不僅有助于傳統的家族文化和鄉土信仰文化的傳承,增強村民的文化認同和自豪感,而且也滿足了當下村民的健身旅游活動需求,有助于構建新型的鄉村社會結構,提升村民的歸屬感和凝聚力。此外,在城鄉要素流動的背景下,核心公共空間也是游客和村民之間的互動交流場所,促進鄉村融入新型的城鄉關系。
5 結論
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不斷變遷,我國鄉村聚落的社會結構也在變化,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鄉村聚落的文化特質,尤以家族文化和鄉土信仰文化為主。這些傳統文化正在不斷流失,但其在當代鄉村聚落中依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應當被傳承。
文化并非獨立存在,它與社會結構和空間具有有機對應關系。不同地域不同聚落的社會結構、文化觀念以及空間形態各不相同,但三者之間有機的對應關系卻有相似性。因此,鄉村振興中的文化振興要充分考慮社會關系和精神文化的變遷,并規劃營造適合的空間來承載。
鄉村聚落的公共空間是村落社會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核心公共空間集中呈現了鄉村聚落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中的主要部分,因而選擇其作為觸媒進行文化定樁。深入挖掘鄉村聚落文化根源,識別鄉村核心公共空間。
核心公共空間作為村落舊的物質空間,需要重新定義新功能和新的社會結構,才能使村落物質空間環境獲得新的發展內涵和動力[13]。因而充分認識當代鄉村聚落文化性、社會性和空間性的有機對應關系,以此指導核心公共空間的營造,既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弘揚,又是新時代鄉村文化和鄉土文明的空間體現。
在適應新的時代和社會需求的背景下,以文化振興為靈魂,對核心公共空間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最終實現鄉村振興。“文化定樁”的理論認識和工作方法學習對歷史文化傳統村落的保護利用具有普遍的指導性意義,但各地還應根據其自身條件因地制宜地進行文化振興,尊重并保護鄉村文化多樣性和地方性特征。
(沙灘村美麗鄉村規劃和鄉村振興建設得益于多方支持,在此向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和嶼頭鄉地方政府的參與者,以及各階段參與的同濟大學團隊師生表示誠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