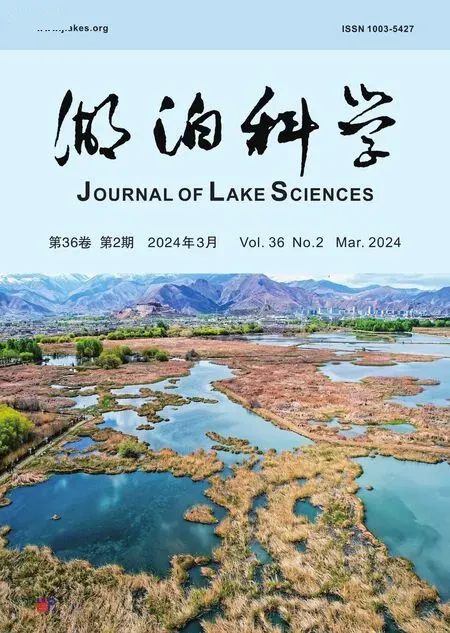風場對鄱陽湖豐水期表層藍藻密度的影響*
楊 平,劉聚濤**,胡 芳,溫春云,文 慧,吳 槳,付莎莎,戴國飛
(1:江西省水利科學院,南昌 330029)(2:江西省鄱陽湖流域生態水利技術創新中心,南昌 330029)
作為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已處于輕度富營養狀態[1-2],營養鹽濃度的增加促進了浮游植物的生長,浮游植物生物量隨之上升,藍藻占浮游植物群落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3-6],豐水期水華藍藻在多個湖區有分布,主要在內灣及尾閭區生長積累[7],局部形成的肉眼可見水華群體主要集中在都昌縣城以南的約20 km2水域[4],部分碟形湖枯水期藍藻水華程度也較為嚴重[8]。
在闡明藍藻生長和水華暴發的驅動因子方面,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水體營養鹽、氣象和水文與藍藻的相互關系等[9-13],其中,氣象和水文條件對藍藻水華暴發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風場是影響藍藻水華暴發的重要因素之一[14-20]。風產生的風浪和湖流改變了藍藻的位置,使其積聚形成水華,風浪擾動會促使大量的營養鹽從底泥中釋放,導致湖泊水體重新分層與混合,增加了藻類可利用的營養鹽[21],風力因素可以通過影響湖泊擾動、流速、光照條件、懸浮物濃度、透明度、底泥營養鹽釋放等因子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藍藻濃度及其分布[22]。目前,國內關于風場對藍藻的影響研究主要針對太湖、滇池、巢湖等淺水湖泊[20,23-25],針對鄱陽湖的研究則多集中于藻類群落特征及其與營養鹽之間的關系[4-7]。
由于鄱陽湖通江湖泊的特性,水體交換時間僅為10 d左右[26],遠低于太湖(192 d)[27]和滇池(981 d)[28],鄱陽湖水體流速(平均流速0.17~0.55 m/s)[29]也要明顯大于太湖(流速小于0.1 m/s的時間占90%)[30-31]和滇池(平均流速0.002~0.04 m/s)[16, 32]。因此,作為長江流域重要的通江湖泊,風場如何影響鄱陽湖表層藍藻密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對2019-2021年鄱陽湖水質、藻類、風場及流場情況進行調查和分析,探討了風場對鄱陽湖豐水期表層藍藻密度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鄱陽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長江中游南岸,南北長173 km,東西平均寬16.9 km,水面面積在28~3700 km2之間,流域面積16.2萬km2,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陽湖是典型的通江湖泊,具有過水性、吞吐性、季節性特征,承納了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等河流來水,經調蓄后由湖口注入長江。鄱陽湖水位受本流域來水及長江干流水位的雙重影響,呈現出豐枯變化顯著的水文特征。鄱陽湖水文特征表現為“高水是湖、低水似河”的特點,平水期及枯水期以河相為主,水域面積低,水體呈現為河流特征;豐水期以湖相為主,水域面積廣闊,水體呈現為湖泊特征[29]。近幾年的鄱陽湖水生態監測結果顯示,2019-2021年鄱陽湖豐水期氮磷比在0.4~38.2之間,均值為10.2,氮磷比小于29的比例在95.3%~100%之間,平均為97.2%,鄱陽湖豐水期低氮磷比有利于藍藻在浮游植物種群組成中占據優勢[24]。
1.2 采樣點布設
根據鄱陽湖地形特點,將鄱陽湖分為入江水道、主湖區和東部湖區3個區域,于2019-2021年平水期(4月)、豐水期(8-9月)、枯水期(12月),根據鄱陽湖平豐枯水位變化情況布設13~49個采樣點進行樣品采集(圖1),其中鄱陽湖入江水道點位6個(1#~6#)、主湖區36個(7#~42#)、東部湖區7個(43#~49#),因鄱陽湖各個時期采樣實時水位有所變化,部分點位因水位太低導致監測船只無法到達,故各個時期實際監測點位數量有所差異,具體監測時期、點位數量和指標情況見表1。

表1 鄱陽湖監測點位和時期情況Tab.1 Sampling sites and time of Lake Poyang

圖1 鄱陽湖采樣監測點位布設Fig.1 The sampling stations of Lake Poyang
1.3 樣品采集分析方法
監測指標包括水質、藻類(密度、生物量)、風場(風速、風向)和流場(流速、流向),其中水質指標包括pH、溫度、溶解氧、氧化還原電位、電導率、總氮、總磷、氨氮、硝氮、正磷酸鹽、葉綠素。使用YSI多參數水質儀(YSI EXO, YSI Company, USA)現場測定水體表層pH、水溫、溶解氧等指標。按照《水質采樣技術指導》(HJ 494-2009)規范采集表層水體水質樣品,參照《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第四版)[33]對總氮、總磷等水質數據進行測定。使用便攜式手持風速儀現場采集風速風向指標。使用流速流向儀(HH.ZSX-6型,濰坊河海水文科技有限公司)現場實時測定水體表層流速、流向。使用25#浮游生物網現場采集藻類定性樣品;現場采集1 L表層水帶回實驗室,加入魯哥試劑固定并沉淀48 h后濃縮富集至約30 mL得到藻類定量樣品,鑒定計數參考《中國淡水藻類:系統、分類及生態》[34]等進行。
1.4 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
使用Excel 2016進行數據整理和預分析,使用Canoco 4.5軟件對鄱陽湖水質、風速與藍藻密度等之間的關系進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RDA),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19.0軟件進行Spearman相關性分析。使用Arcmap 10.2軟件制作鄱陽湖監測點位圖和藍藻空間分布圖,采用Origin Pro 2021軟件繪制風場流場玫瑰圖及其他圖形。
2 結果與分析
2.1 表層藍藻密度的變化
為了闡明藻類和藍藻變化趨勢,將2017-2018年藻類調查數據也納入分析,采樣時期為2017年5、8、12月,2018年5、8、12月,2017-2021年鄱陽湖表層藻類密度監測結果如圖2所示。

圖2 鄱陽湖2017-2021年藻類(a)和藍藻(b)密度分布情況Fig.2 Changes in algae(a) and cyanobacteria(b) density in Lake Poyang from 2017 to 2021
1)藻類密度變化趨勢。觀測期內,2017-2021年鄱陽湖表層藻類密度變化范圍在3.9×103~4.05×107cells/L之間,均值分別為9.17×104、2.19×105、1.25×106、5.79×106、1.79×107cells/L,各年度藻類密度變化規律均表現為豐水期最高,平水期次之,枯水期最低。
2)藍藻密度年際變化趨勢。觀測期內,2017-2021年鄱陽湖表層藍藻密度變化范圍在0~3.2×107cells/L之間,均值分別為6.33×104、1.66×105、8.16×105、3.27×106、1.45×107cells/L。
3)不同水位期藍藻密度變化趨勢。觀測期內,2017~2020年鄱陽湖平水期表層藍藻密度變化范圍在0~2.2×106cells/L之間,均值分別為0.58×103、1.52×103、1.99×105、4.9×105cells/L,藍藻出現頻率分別占12.5%、37.5%、46.1%、88.2%;2017-2021年豐水期表層藍藻密度變化范圍在0~3.02×107cells/L之間,均值分別為1.15×105、3.27×105、1.28×106、4.58×106、1.45×107cells/L,藍藻出現頻率分別為64.1%、66.7%、65.9%、100%、100%;2017-2020年枯水期表層藍藻密度變化范圍在0~1.59×106cells/L之間,均值分別為0.32×103、0.92×103、1.1×103、4.03×105cells/L,藍藻出現頻率分別占6.2%、12.5%、11.8%、100%。觀測期內,2017-2020年內藍藻密度特征均表現為豐水期遠大于平水期和枯水期(P<0.01),豐水期藍藻出現頻率最高,平均為79.3%,平水期和枯水期平均分別為36.9%、26.1%。
2.2 風場的變化
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現場調查風場特征如表2和附圖I所示,由圖表可知,風速方面,從年際變化趨勢來看,觀測期內,2019-2021年鄱陽湖豐水期全湖風速均值在1.8~4.4 m/s之間,年際變化規律為2021年>2020年>2019年;2019-2020年豐水期各個區域風速均值變化規律均為入江水道>主湖區>東部湖區,2021年為東部湖區>入江水道>主湖區。風向方面,2019-2021年豐水期全湖主導風向分別為N、W、SSW,2019及2021年各個區域主導風向不一致,2020年各個區域主導風向以NE風向為主。已有研究表明,鄱陽湖全年主導風向以NE向為主,6-8月風向以SSW向為主[35],湖區多年平均風速為3.8 m/s[36]。

表2 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現場調查各區域風場特征Tab.2 On-site wind field data of Lake Poyang during the flood period from 2019 to 2021
2.3 流場的變化
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流場特征如表3和附圖Ⅱ所示,由圖表可知,流向方面,觀測期內鄱陽湖入江水道主要流向朝北偏東方向,與入江水道天然流向一致。主湖區流向較為分散,但總體流向朝北、北偏西及西方向,即入江水道方向;東部湖區主要流向朝南偏西方向,與東部湖區所處位置有關,湖流僅能從南偏西方向進入主湖區。流速方面,觀測期內鄱陽湖2019-2021年全湖流速均值分別為0.16、0.05、0.14 m/s,流速大于0.1 m/s的頻率占比為89.2%。全湖、入江水道、主湖區平均流速規律為2019年>2021年>2020年,東部湖區平均流速最高的年份為2021年,其次為2019年和2020年。分區域來看,2019-2020年豐水期流速均值表現為入江水道>主湖區>東部湖區的特征,2021年豐水期流速均值表現為入江水道=東部湖區>主湖區。

表3 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現場調查各區域流場特征Tab.3 On-site flow field data of Lake Poyang in flood period of 2019-2021
2019年8月鄱陽湖星子站水位從16.3 m下降至15.57 m,水位下降快,湖流以吞吐流為主,流速最大;受流域超歷史大洪水及長江頂托影響,2020年8月湖區水位從19.00 m上升至19.11 m,處于長江頂托的低流速時期,2020年9月水位從18.56下降至18.20 m,水位下降緩慢,流速較小;2021年8月水位從16.26 m下降到15.08 m,水位下降快,流速較快。
3 討論
3.1 風速對豐水期表層藍藻密度的影響
對鄱陽湖豐水期水質(pH、溫度、溶解氧、氧化還原電位、透明度、懸浮物、總氮、硝態氮、氨氮、總磷、磷酸鹽、高錳酸鹽指數)、風速、流速與藻類密度及生物量的關系進行冗余分析(RDA),同時為了明確藍藻各個屬對風場的響應情況,將鄱陽湖優勢藍藻屬納入了分析,鄱陽湖豐水期優勢水華藍藻屬為微囊藻屬、長孢藻屬、平裂藻屬、色球藻屬、假魚腥藻屬,出現頻率分別為33.9%、39.3%、26.3%、29.5%、46.9%,分析結果見圖3。

圖3 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藻類密度(a)、生物量(b)與環境因子等的RDA二維排序Fig.3 Two-dimensional RDA ranking of algae density(a) and biomass(b)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Lake Poyang from 2019 to 2021
由圖3a可知,鄱陽湖豐水期藍藻及水華藍藻密度與風速、氧化還原電位、總磷、氨氮呈正相關,與流速、硝氮、高錳酸鹽指數、正磷酸鹽、總氮等因子呈負相關;微囊藻屬、平裂藻屬、色球藻屬等球狀藍藻密度與風速、氧化還原電位、總磷呈正相關,與總氮、氮磷比呈負相關,與流速不呈顯著相關(P>0.05)。由圖3b可知,鄱陽湖豐水期藍藻及水華藍藻生物量與風速、總磷、氨氮、氧化還原電位呈正相關性,與總氮和氮磷比呈負相關;微囊藻屬、平裂藻屬、色球藻屬等球狀藍藻與風速、氧化還原電位、總磷呈正相關。
對鄱陽湖豐水期水質、風速、流速與藻類密度進行Spearman相關性分析,結果見附表I,可知鄱陽湖豐水期風速與藻類總密度、藍藻密度、硅藻密度、水華藍藻密度、微囊藻屬密度、平裂藻屬密度、色球藻屬密度、假魚腥藻密度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與色球藻屬密度呈顯著正相關(P<0.05)。流速與綠藻密度、長孢藻屬密度呈極顯著負相關(P<0.01),與顫藻屬呈顯著負相關(P<0.05),與其他藻類不呈顯著相關。
對不同風速范圍鄱陽湖豐水期藍藻密度占比情況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見表4。當風速在1~5 m/s區間時,各風速區間藻類和藍藻密度超過1×107cells/L的點位占比逐漸增大,超過5 m/s后逐漸減小。風速在4~5 m/s區間時,藻類和藍藻密度超過1×107cells/L的點位占比最大,其次為5~6 m/s、3~4 m/s區間。

表4 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不同風速范圍藻類與藍藻密度分布情況Tab.4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algae and cyanobacteria in Lake Poyang in different wind speed ranges during flood period from 2019 to 2021
RDA分析和Spearman相關分析結果表明,風速與鄱陽湖豐水期表層藍藻及主要水華藍藻密度呈顯著正相關性,風速越大表層藍藻密度越高。對不同風速范圍藻類與藍藻密度分布情況的統計結果也表明,風速在一定范圍內升高,藍藻密度超過1×107cells/L的點位數占比也逐漸增高。李春華等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太湖湖濱帶春夏季風速與藻密度均呈顯著正相關[37]。其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豐水期水體溫度和營養鹽濃度等水環境因子均適宜藍藻生長,風場對水體施加剪切力造成水體上下混合、擾動增大,低至中等強度的水體上下擾動可以改善藻類所處水環境中的位置和光能的均勻分布,引起光照輻射的改變,有利于藻類光合作用和能量代謝[38-39]。
另一方面,風場通過驅動湖泊表層水體形成風生流[40],引起水體表層流速變化對藻類生長產生影響。7月中旬至9月底的“湖相”期,在長江頂托作用下,鄱陽湖吞吐流變緩,開闊湖面有利于風生流的形成,流速流向受風的影響相對明顯,明顯環流區面積可達600 km2,其中風生環流比較明顯的區域為主湖區和東部湖區。姚靜等對鄱陽湖風場影響水動力的模擬研究結果表明,無論哪種風向,3.03 m/s的定常風模擬下,在湖區中部湖灣及中部西岸,風生流速最大增幅為2.0~2.5 cm/s,其它大部分湖區流速變幅均在±0.5 cm/s以內[35]。彭兆亮等對洪澤湖風生流的模擬研究表明,湖面風速為1 m/s時,湖區表層水體平均流速為0.48 cm/s,4 m/s時上升到6.55 cm/s,6 m/s時上升到約16 cm/s,13 m/s時到76.4 cm/s[40]。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平均風速范圍在1.9~4.4 m/s之間,最大風速8.8 m/s,僅考慮風場產生的風生流速,水體表層流速應在7 cm/s左右,最大不超過50 cm/s。實際觀測中,鄱陽湖豐水期全湖流速均值在0.05~0.16 m/s之間,最大值為0.51 m/s,王婧等的研究也表明鄱陽湖豐水期時,入江水道平均流速在0.17~0.36 m/s之間,主湖區平均流速在0.17~0.25 m/s之間[29]。因此,鄱陽湖豐水期風場引起的風生流對鄱陽湖水體,尤其是主湖區和東部湖區水體,表層流速的貢獻較大。
張海涵等的研究表明流速低的水體適宜藍藻和綠藻生長,而硅藻適應流速高的水體[39]。張毅敏等的室內模擬實驗中,當水體流速為0.3 m/s時藻類的密度達到最高,超過該流速后藍藻密度逐漸下降[41]。藻類生長存在臨界流速,當流速低于臨界流速時藻類密度隨流速增大而升高,超過臨界流速時藻類生長受到抑制,銅綠微囊藻臨界流速為0.25~0.3 m/s之間,絲狀藻Lyngbyawollei完全覆蓋水面的流速小于0.1 m/s[39],項圈藻暴發水華的臨界流速為0.05 m/s[42]。綜合以上分析,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大部分區域流速低于藍藻生長臨界流速,此時風場產生的風生流對藍藻生長具有促進作用。
3.2 風向對豐水期表層藍藻密度的影響
鄱陽湖豐水期風向對表層藍藻密度的影響分析結果見圖4~6。由圖4可知,鄱陽湖2019年豐水期(8月)藍藻密度最高的區域在東部湖區東岸,其次為主湖區中部。分區域來看,入江水道藍藻密度分布較為均勻,主湖區中部藍藻受主導風向N、NE、SW、S影響在中部集中,東部湖區藍藻受SSW、W主導風向影響在東岸堆積。

圖4 鄱陽湖2019年豐水期(8月)藍藻密度空間分布分布與風場對應情況Fig.4 Cyanobacteria dens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wind field correspondence in Lake Poyang in August 2019
由圖5可知,鄱陽湖2020年豐水期(8月)入江水道、主湖區南部藍藻密度最高,其次為主湖區中部。分區域來看,入江水道藍藻密度由南向北逐漸降低,至長江口處密度升高,藍藻密度受NE、E主導風向影響下呈現西高東低的特征;主湖區藍藻密度在主導風向N、NW的下風向堆積,但考慮主湖區由南向北的水流驅動力要大于風速,此時藍藻分布受風速的影響可能較小;東部湖區藍藻密度分布特征為東高西低,受風速影響不明顯。

圖5 鄱陽湖2020年豐水期(8月)藍藻密度分布與風場對應情況Fig.5 Cyanobacteria dens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wind field correspondence in Lake Poyang in August 2020
由圖6可知,鄱陽湖2021年豐水期(8月)主湖區西南區域、東部湖區東部區域藍藻密度最高,分區域來看,入江水道藍藻密度空間分布特征為南高北低,主湖區藍藻密度呈現西南區域高、其他區域低的特點,與主導風向SSW、S、SE下風向區域堆積的規律不一致。

圖6 鄱陽湖2021年豐水期(8月)藍藻密度空間分布與風場情況Fig.6 Cyanobacteria dens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wind field correspondence in Lake Poyang in August 2021
鄱陽湖2019-2021年豐水期表層藍藻空間分布分析結果表明,湖區表層藍藻密度的空間分布與風向作用并不完全一致,也即藍藻并不總是在主導風向的下風向聚集。具體來看,2019年東部湖區藍藻空間分布與風場具有一致性,在主導風向的下風向東岸聚集,可能與2019年豐水期流速低、風速較低有關,2019年東部湖區平均風速為1.6 m/s。而太湖的研究表明,當風速低于臨界風速(3~4 m/s)時,水體表面藻類順著風向迅速向迎風岸邊漂移,形成藻類大量堆積。當風速超過臨界風速時,藍藻受強烈的紊流作用而難以上浮、已經上浮的受到擾動混合而在垂向較為均勻分布[23, 43],因此該時期風速有利于藍藻在流速較緩的東部湖區沿主導風向的下風向聚集,導致表層藍藻密度較高。2020年豐水期入江水道和主湖區表層藍藻密度與風場的一致性較好,入江水道和主湖區表層藍藻由南向北依次從高到低分布,在主導風向的下風向聚集。但經過進一步分析發現,2020年南昌市贛江和撫河發生嚴重的藍藻水華,實地觀測和現場采集的藻類數據表明,入江水道南部贛江主支入湖口處水柱中藍藻顆粒肉眼可見,表層藍藻密度達到1.37×107cells/L;主湖區西南部贛江南支、撫河入湖口處表層藍藻密度分別為1.96×107、2.18×107cells/L。同時,2020年鄱陽湖豐水期入江水道與主湖區風速均值分別為4.7、3.0 m/s,超過藍藻隨風向遷移堆積的臨界風速,藍藻趨向于在水柱中垂向均勻混合。因此,2020年鄱陽湖豐水期入江水道和主湖區表層藍藻密度分布主要是受流場影響,沿由南向北流向依次由高向低分布,受風向的影響較小。2021年豐水期表層藍藻密度與風向的一致性不強,此時期流速均值在0.09~0.28 m/s,風速均值在4.1~5.7 m/s,在該風速范圍內表層藍藻密度在水柱中垂向均勻混合,并沿著流場方向向下游由高到低分布。
綜合本小節分析可以發現,在流速較高的區域,無論風速高于還是低于臨界風速(3~4 m/s),鄱陽湖表層藍藻密度的空間分布受流場的影響更大;在流速較低的區域,風速在臨界風速以下時,鄱陽湖表層藍藻密度的空間分布受風場影響更大。
3.3 風場對豐水期藍藻水華的影響
余茂蕾等的研究結果表明,風場對太湖表層水體藍藻水華的空間分布具有決定性影響,較高的風速能夠引起藍藻水華在空間上較高的一致性[44],當風速低于臨界風速(3~4 m/s)時,易發生藍藻水華,當風速超過臨界風速時,藍藻水華現象消失[23, 43],Wu等的研究則表明太湖藍藻水華消失的臨界風速(流速)為6 m/s(0.057 m/s),此時上層和下層葉綠素濃度比值接近1,水體藍藻充分混合[45]。風速是滇池藍藻水華暴發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46],在具備藍藻水華發生所需營養鹽條件下,滇池藍藻水華發生頻率高低與風速關系最為密切[24]。對巢湖而言,在營養鹽充足且溫度較為適宜的季節,風速和風向是巢湖藍藻水華預警的重要因子[25]。胡旻琪等對2016年巢湖藍藻水華的研究結果表明,當風速高于3 m/s時,風浪作用使得水體發生擾動,藻類在湖中的水平及垂直分布趨于均一,不再出現藻類聚積現象,從而抑制了水華的形成[47]。
本文盡管未對觀測期內的藍藻水華分布區域和面積作詳細調查,但結合野外實地觀測和文獻結果,鄱陽湖豐水期藍藻水華主要集中在流速較小的內灣、尾閭區、部分碟形湖及都昌附近水域[4,7-8]。鄱陽湖2019年豐水期風速均值較低,處于有利于藍藻形成水華的風速范圍內,但現場調研僅在局部庫灣發現有藍藻堆積,主要原因可能是2019年豐水期表層流速范圍在0.02~0.36 m/s之間,均值為0.16 m/s,大部分區域流速均超過藍藻水華消失的流速臨界值(0.057 m/s),因此,在全湖藍藻密度達到水華級別且風速處在適宜形成水華的區間內,并未發生大面積的藍藻水華。2020年鄱陽湖豐水期因長江頂托全湖流速處于較低水平,流速范圍在0~0.28 m/s之間,均值為0.05 m/s,東部湖區小于0.05 m/s,但風速均值在2.6~4 m/s之間,接近藍藻水華消失的臨界風速,故也未發生較大面積的藍藻水華。2021年鄱陽湖豐水期流速和風速均處于高位,流速均值在0.09~0.28 m/s之間,均值為0.14 m/s,風速均值在4.1~5.7 m/s之間,均值為4.4 m/s,兩者均已超過藍藻水華暴發的臨界值,因此在全湖藍藻密度達到水華級別的背景下也未發生大面積的藍藻水華。上述分析結果提示,當鄱陽湖豐水期水體處于長江頂托的低流速且微風條件下時,鄱陽湖發生大面積藍藻水華的概率可能明顯上升。
4 結論
1)2019-2021年鄱陽湖豐水期風速與表層藍藻密度呈顯著正相關,風速越大表層藍藻密度越高,風速在1~5 m/s之間時,藍藻密度超過1×107cells/L的點位占比隨風速的增大而逐漸升高,風場對水體的充分混合及驅動水體形成的風生流是促進藍藻生長的原因之一。由于野外實際觀測條件限制,本研究觀測期內獲取的鄱陽湖最大風速為8.8 m/s,缺乏大風速(>8.8 m/s)條件下鄱陽湖表層藍藻密度的原位監測數據,因此大風速條件下風場對表層藍藻密度的影響情況尚有待進一步闡明。
2)2019-2021年鄱陽湖豐水期流速較高(>0.05 m/s)的區域,無論風速高于還是低于臨界風速(3~4 m/s),鄱陽湖表層藍藻密度的空間分布受流場的影響更大;流速較低(<0.05 m/s)的區域,風速低于臨界風速以下時鄱陽湖表層藍藻密度的空間分布受風場影響更大。
3)2019-2021年鄱陽湖豐水期藍藻密度超過水華暴發的閾值,但在高風速高流速的共同作用下未能發生大面積的藍藻水華,僅能在風速適宜(<3~4 m/s)、流速較低(<0.05 m/s)的內灣、尾閭區等區域發生小面積的藍藻水華。鄱陽湖豐水期水體處于長江頂托的低流速且微風條件下時,發生大面積藍藻水華的概率可能明顯上升。
5 附錄
附圖Ⅰ、Ⅱ和附表Ⅰ見電子版(DOI: 10.18307/2024.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