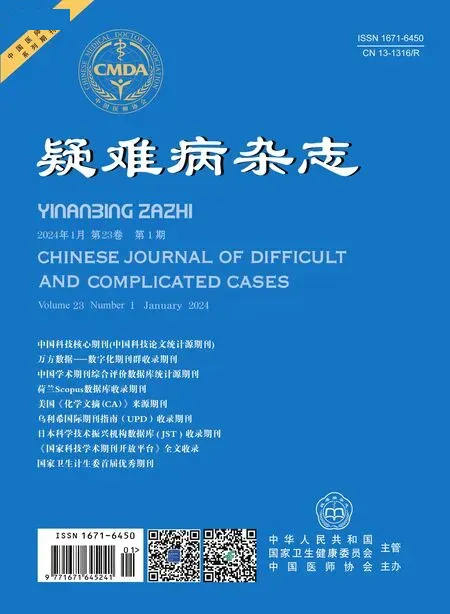歐洲心律協會(EHRA)關于虛弱綜合征心律失常管理的專家共識解讀
浦介麟,周曉茜,蔡英
作者單位: 200120 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
虛弱和虛弱綜合征是全人類的問題,也是老年醫學和全科醫學面臨的挑戰。虛弱前期狀態(pre-frail state)和虛弱綜合征(frailty syndrome)的發生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成倍增加,并且與更高的疾病發病率、殘疾、住院、死亡和醫療資源消耗有關。心律失常在患者年齡增長、慢性疾病和身體虛弱時很常見。然而,目前還沒有專門針對老年人和虛弱人群心律失常管理的系統性研究或推薦。此次歐洲心律協會(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EHRA)的專家共識重點關注虛弱的生物學特性、常見的合并癥和評估方法。在心律失常和傳導性疾病的具體問題上,為虛弱綜合征患者提供基于臨床證據的管理建議。
共識中闡述了虛弱的生物學特性、常見合并癥、評估方法和各類心律失常的具體問題,對老年和虛弱患者的心律失常管理提供建議,適用于參與治療老年虛弱前期和虛弱患者心律失常、傳導疾病和心臟植入電子設備的初級和二級預防的醫護人員。
共識聲明是基于證據和共識的強度,分別為:具有治療或操作有益的和有效的科學證據,或得到了作者共識的強烈支持(should do this);普遍同意和/或科學證據支持治療或操作的有用性/有效性(may do this);科學證據或普遍同意不使用或推薦的治療或操作(do not do this)。
1 定義、流行病學及虛弱相關的內容
1.1 定義和流行病學 虛弱被定義為一種綜合征,其特征是高生物脆弱性、生理儲備減少和抵抗應激的能力降低。據估計,社區中虛弱的患病率為12%(10%~15%),在非社區人群中上升到45%(27%~63%),女性的患病率較高,85歲及以上的人群中最高。多種合并癥與虛弱患病率增加相關(高達63%~81%)。
關于虛弱有2種不同概念性模型。Fried等提出的模型,認為級聯事件從分子氧化應激到DNA損傷均可加速細胞衰老,使得內分泌和免疫系統失調,導致患者出現虛弱的表現,包括肌肉力量、體質量和步速的下降,并可導致疲勞感增加或無法完成高要求的活動。Mitnitski等的另一種模型描述了累積缺陷模型,它不是將虛弱定義為一種特定的綜合征,而是定義為一種與年齡相關的醫療和功能問題疊加的狀態。盡管這兩種模型在理論上存在差異,但也有很多共同之處,均能夠識別出發生事件風險較高的老年人。
1.2 虛弱前期狀態 虛弱前期狀態的概念還不夠完善,也沒有完善的流行病學和臨床數據的支持,定義也很模糊。如果基于Fried模型的5個標準中的1個或2個,或者是基于虛弱指數(FI)的累積缺陷的數量來定義虛弱前期狀態或中等程度的虛弱,虛弱前期通常被認為是虛弱前的臨床沉默階段或易導致虛弱的一種狀況。虛弱前期狀態是介于強壯和虛弱之間的過渡狀態,其臨床重要性在于通過有效的康復干預措施可以逆轉虛弱狀態。
1.3 虛弱與臨床復雜性 衰老與生物穩態及功能儲備的逐漸喪失有關,雖然健康和功能狀況的下降部分直接歸因于疾病,但在某些特定的個體中,損害的積累是非常普遍和多系統的,包括多種合并癥、行動能力喪失、殘疾、認知障礙,并最終嚴重到影響日常生活,因此,臨床醫生和科研人員將其定義為虛弱。
虛弱和臨床復雜性有時被認為意義相同,但“復雜性”一詞應該用來表示多種共病的存在及其復雜的藥物治療。在這方面,復雜性可能是虛弱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更有可能導致虛弱,但并非等同于虛弱。
1.4 與虛弱相關的主要臨床情況
1.4.1 厭食和營養不良:厭食癥(食欲不振或不能進食)在老年人中多見,可引起營養不良、肌肉松弛或萎縮,最終導致殘疾和更高的發病率、病死率。約20%的老年人存在厭食癥,住院的老年人(23%~62%)和長期居住養老院的老年人(高達85%)中更多見。
共識聲明:對厭食癥和營養不良者進行常規評估,對所有高危老年人或其他高危人群都應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
1.4.2 肌肉萎縮癥:肌肉萎縮癥是指隨著年齡的增長,患者肌肉的數量、力量和功能逐步喪失,與虛弱和不良的健康結局相關。70歲以后,平均每10年肌肉損失達15%。在社區中,肌肉萎縮癥的患病率為1%~29%,在需要長期護理的人群中發病率上升至14%~33%。
可實施預防性和治療性干預措施(如優化營養、消除維生素D缺乏癥和體育鍛煉),旨在扭轉身體虛弱,減緩或阻止向殘疾和依賴性發展。
1.4.3 心力衰竭:虛弱在心力衰竭中尤其常見,在一項薈萃分析中,心力衰竭患者的虛弱患病率為47.4%。心力衰竭患者的虛弱患病率與年齡無關,這表明2種綜合征之間存在更復雜的相互作用。虛弱與心力衰竭相關的機制是多因素的,炎性標志物、線粒體功能障礙導致的骨骼肌功能受損、毛細血管密度降低和脂肪組織浸潤等都可能參與其中。相反,衰老、虛弱、合并癥和住院導致的不活動都可能會加重心力衰竭并加速其進展,從而增加了心力衰竭的發病率和死亡風險。
共識聲明:(1)對虛弱的評估應納入心力衰竭患者的常規臨床管理。(2)采取早期干預措施,改變患者虛弱的部分狀態,對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預后、提高生活質量十分重要。
1.4.4 癌癥:虛弱的管理對癌癥患者特別重要,超過50%的癌癥病例中可以發現虛弱前期或虛弱狀態。注冊數據顯示,癌癥預后與虛弱的狀況相關,如體質量減輕、步速減慢、重度抑郁和養老院住院。
共識聲明:對虛弱的早期評估、及時識別虛弱前狀態,就可能采取干預措施,阻止虛弱的發展,并保持生活質量,特別是在可治療和非侵襲性的癌癥患者中。
1.4.5 跌倒:身體虛弱的老年人很可能會出現反復跌倒的情況。對102 130例65歲及以上的社區居民進行薈萃分析發現,虛弱患者跌倒的風險增加了2.5倍,而處于虛弱前期狀態的老年人跌倒的風險比健康老年人增加了1.5倍。
有疑似心律失常的虛弱患者應評估跌倒風險。除環境因素(松動的地毯、臺階等)外,可改變的跌倒風險因素包括步態和平衡障礙、認知障礙、抑郁癥、多藥治療、精神藥物、心血管藥物、視力異常、直立性低血壓、低血壓、心律失常(最常見的為緩慢性心律失常)、尿失禁、既往跌倒和對跌倒的恐懼。所有已確定的危險因素都應進行改善。
跌倒可分為意外的跌倒(即滑倒、絆倒)和非意外的跌倒。后者更有可能歸因于心血管異常,特別是低血壓疾病或心律失常。在實踐中,除非有目擊者和/或老年人對事件有清晰的回憶,否則這兩者很難區別。
跌倒與心律失常直接相關,最常見的是緩慢性心律失常、心臟停搏以及快—慢型心房顫動(房顫)。抗心律失常藥物可能增加直立不耐受、心動過緩的風險,導致跌倒的其他危險因素包括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礙、電解質紊亂或視力障礙。
共識聲明:(1)評估跌倒的風險因素對所有虛弱的患者都是有益的。(2)對于不明原因的非意外跌倒,應根據2018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SC)關于暈厥的診斷和管理指南,當作暈厥事件進行調查。(3)對于有直立性不耐受的患者,應準確問詢藥物治療的細節,包括非心臟藥物。(4)對有低血壓和/或直立不耐受/直立性低血壓的患者,應謹慎使用降壓藥物,或應評估停藥對患者可能帶來的益處。(5)給患者處方抗心律失常藥物時,應監測患者跌倒的風險。(6)首選對血壓影響最小的抗心律失常藥物。
1.4.6 神經系統疾病(包括認知功能障礙和老年癡呆癥):虛弱和跌倒在與年齡相關的神經系統疾病中更為常見,如腦卒中、帕金森病、癡呆癥或癲癇。即使在耳鳴和頭痛等神經疾病可能性最小的患者,“跌倒者”的比例也更高。
預防跌倒是治療的主要目標,近期隨機試驗的薈萃分析顯示,運動聯合認知訓練改善了輕度認知障礙患者的平衡性,而體育鍛煉對預防存在認知障礙的老年人跌倒有明顯效果。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虛弱患者對跌倒的恐懼。最近的研究表明,虛弱與跌倒恐懼有獨立的聯系,而認知行為療法可能會改善對跌倒的恐懼。
共識聲明:(1)接受精神藥物治療的患者應進行跌倒監測。(2)運動和認知訓練可以改善早期認知障礙患者的平衡能力并防止虛弱的進展。
1.4.7 多種合并癥和多種藥物治療:心血管健康研究表明,虛弱與一些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和糖尿病有很大的關聯,33%的虛弱者有3~4種慢性疾病,27%有2種,8%有多于5種伴隨疾病。虛弱者的多種合并癥不僅可能加重虛弱的表現,而且可能導致多種藥物治療的風險增加,這已多次被證明是不良臨床結果的標志。法國一項對年齡大于70歲人群的隊列研究顯示,處方藥物的平均數量隨著虛弱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虛弱和藥物治療種類大于10種是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兩者結合使2.6年的死亡風險增加6.30倍。心力衰竭、腎衰竭、房顫、癡呆和癌癥是與虛弱相關的最常見的合并癥。
1.4.8 電解質紊亂、腎臟損害、代謝問題:慢性低鈉血癥是老年人最常見的電解質紊亂,雖然通常是輕微和無癥狀的,但加重了虛弱的表現,導致認知障礙和步態障礙,并促使骨質疏松癥引起骨質脆弱,從而使患者容易跌倒和發生髖部骨折。
慢性腎臟疾病(CKD)在老齡化中很常見。肌肉疏松癥隨著腎功能的損害而逐漸進展,在血液透析患者中,虛弱與2.6倍的病死率和1.4倍的住院風險相關,與性別、年齡、合并癥和殘疾無關。
在代謝問題中,胰島素抵抗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顯著增加,并被認為是許多年齡相關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
2 虛弱評估和虛弱評分
最常用的標準根據心血管健康研究數據制定。根據以下標準來定義:體質量下降、疲憊感、肌肉無力、行走緩慢和低活動量,通過自我報告和客觀測量(表1)相結合來確定。符合3個或3個以上指標應該被認為是“虛弱”,而符合其中2個指標應該被認為是“虛弱前期”。這些評判標準對不同結果預測的有效性,已經在國內外發表的數百篇老年醫學文獻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證實。

表1 虛弱診斷標準(Fried 標準)
第二種方法是FI,計算方法是檢測到的缺陷數量與考慮到的缺陷總數之間的比率,這些缺陷是可變的,包括疾病、身體和認知障礙、社會心理風險因素,以及老年綜合征,如跌倒、譫妄和尿失禁(表2)。FI是不良健康結局的一個強有力的預測因子,可以進行強有力的臨床推斷。FI將老年人分為若干等級,從“強健”到“嚴重虛弱”。由于FI幾乎可以從任何一組與健康相關的變量中生成,因此該工具高度靈活,可以適應大量不同的情況,并在不同的研究項目和臨床中心之間進行協調。

表2 虛弱指數(FI)簡表
虛弱最有效的臨床應用是對患者進行分層,以驗證哪些醫療干預措施對這一特殊人群有益,或是否應考慮替代干預措施。虛弱的老年人不應被預先排除在任何類型的治療之外,而應采用基于科學證據的個體化治療。具體來說,不同類型心律失常的治療對虛弱和非虛弱的老年人是否有相同的有益效果,目前尚不清楚。
3 虛弱相關生物學變化的病理生理概述
虛弱是一種綜合征,其特征是儲備減少和抗壓能力下降,易導致發病率增加、反復住院、自主能力喪失和死亡等不良后果。虛弱可導致一個或多個生理系統的衰退。總體上,可以將虛弱分為4個主要領域:(1)身體方面,主要與肌肉質量和功能的喪失,以及身體行為的下降有關。(2)認知方面,由認知能力下降和/或癡呆引起。(3)心理方面,主要與抑郁的表現有關。(4)社會活動,與孤立和缺乏社會活動有關。
3.1 虛弱和與年齡相關的心血管系統心電和結構的變化 心血管老化是由于以下結構和功能發生改變的結果:(1)動脈。內皮功能障礙,內膜厚度,動脈壁鈣化,細胞外基質的改變。(2)心臟。室壁肥厚和纖維化,心腔擴張,瓣膜鈣化和變性,心肌細胞收縮力改變。這些改變的急性和慢性表現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見,如收縮期高血壓、缺血性心臟病、心律失常、瓣膜性心臟病、腦卒中及急性、慢性心力衰竭。
3.2 心血管系統老化與虛弱之間的相互作用 虛弱和虛弱前期已被證明與各種類型的心血管疾病相關,與強壯的個體相比,其HR分別為1.70(95%CI1.18~2.45)和1.23(95%CI1.07~1.36)。
衰老、虛弱和心血管疾病通過多種機制聯系在一起,有一些共同的生物標志物,包括炎性反應和氧化應激生物標志物、利鈉肽、肌鈣蛋白,以及CKD的標志物。一些心血管危險因素,如肥胖是導致虛弱的重要的長期危險因素(在臨床心血管疾病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特別是在年輕人中。
對于相同程度的心功能障礙,虛弱人群將比強壯人群有更明顯的臨床影響。在心力衰竭患者中經常可以觀察到虛弱、肌肉萎縮癥與心臟病的后果有相互協同作用,加重臨床癥狀,如疲勞、呼吸困難和惡病質等。此外,虛弱的存在將增加藥物相關不良反應的風險。臨床研究表明,虛弱的嚴重程度會改變心血管內科和外科治療的效益/風險比。
共識聲明:(1)評估患有心血管疾病老年人的虛弱程度很重要,以便評估功能衰退、喪失自理能力和死亡的風險。(2)基于虛弱評估,可以更好地確定治療策略的風險/效益平衡。(3)在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整體管理框架內,特別是有多種合并癥和多藥治療的患者,虛弱評估是必要的。(4)應避免將年齡作為評判為老年人提供保健和社會保健服務的主要標準。
4 臨床藥理學
正常衰老會產生生理變化,影響抗心律失常藥物(AADs)的藥代動力學(吸收、分布、代謝和排泄)和藥效學(表3、4)。

表3 與年齡有關的藥代動力學變化

表4 與年齡有關的藥效學變化

年齡相關的腎血流、腎小球濾過率和腎小管分泌減少降低了腎臟清除藥物(地高辛、伊布利特、索他洛爾和多非利特)的清除率和半衰期。其他AADs經過肝臟和腎臟消除(多非利特、普魯卡因酰胺和二苯丙吡胺)。因此,對于直接腎臟清除或其活性代謝物被腎臟清除的AAD,需要調整劑量。大多數AADs會與其他廣泛使用的藥物相互作用。奎尼丁、胺碘酮和卓尼達隆會抑制地高辛經腎臟排泄所需的P-糖蛋白,從而增加地高辛的血漿水平。胺碘酮可抑制CYP3A4、CYP2C9和P-糖蛋白,可增加老年人群中廣泛使用的藥物(氟卡胺、Ⅱ類和Ⅳ類AADs、抗凝藥)的血漿水平。
4.2 不良反應 虛弱患者更容易發生AADs的不良反應,包括心動過緩和房室傳導阻滯(Ⅱ類、Ⅳ類AADs或地高辛)、室內傳導阻滯(Ⅰ類AADs)、HF(二苯丙吡胺、索他洛爾和Ⅳ類AADs)、直立性低血壓、跌倒以及尿潴留(ⅠA類)。相反,老年患者對β-受體阻滯劑的敏感性降低。Beers標準建議避免: (1)胺碘酮作為房顫的一線治療,除非患者有心力衰竭或顯著的左心室肥厚;(2)二苯丙吡胺,因其具有抗膽堿能的特性;(3)地高辛作為房顫或心力衰竭的一線治療,或對于任何適應證,地高辛的劑量<0.125 mg/d。
此外,由于合并癥的存在(心力衰竭、高血壓、冠狀動脈疾病),AAD的治療變得復雜。合并癥可以影響AADs的藥效學/藥代動力學,多種藥物治療增加了藥物的不良反應和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使用的一些延長QT間期的非心血管藥物,會增加致心律失常的風險,應避免使用。
處方者應仔細評估年齡對AADs的藥效學/藥代動力學的影響,并評估AADs藥物可能與有合并癥的老年患者廣泛使用的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應根據肝腎功能以低于建議的劑量開始治療,并逐漸滴定,直至達到所需劑量,同時評估不良反應,主要評估致心律失常的不良反應。
5 慢性心律失常
慢性心律失常的發病率會隨年齡增大和合并癥增多而增加,因此,隨著虛弱程度的增加,預計會出現更多的慢性心律失常。由衰老引起的竇房結的特發性退行性變可能是竇房結功能障礙(SND)最常見的原因。隨著年齡的增長,房室傳導阻滯更為普遍。
5.1 藥物引起的心動過緩 虛弱患者更容易被處方減慢心率的藥物,如鈣通道阻滯劑、β-受體阻滯劑和抗心律失常藥物,用于治療高血壓、HF和房顫。由于首次通過代謝降低、肌肉質量減少和腎功能惡化導致標準劑量下發生不良反應,即使是同一類藥物也可能有所不同。在CIBIS老年患者研究中,心力衰竭患者隨機采用比索洛爾或卡維地洛有相似的不良反應發生率(24%~25%)。然而,比索洛爾能更大程度地降低心率和有更多的劑量限制性心動過緩(比索洛爾16%,卡維地洛11%),而卡維地洛與呼吸急促相關(比索洛爾4%,卡維地洛10%)。
據估計,只有15%的房室傳導阻滯真正是由藥物引起的。雖然據報道,當停用降低心率的藥物時,41%的患者房室傳導阻滯得到緩解,但在沒有治療的情況下,超過一半的患者房室傳導阻滯會復發。接受膽堿酯酶抑制劑治療癡呆的患者更有可能因暈厥(HR1.76)或癥狀性心動過緩(HR1.69)而住院,并接受起搏器植入(HR1.49)。
5.2 室內傳導異常 束支傳導阻滯(BBB)的發病率和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在855例50歲的男性中,BBB的患病率在30年內從1%上升到17%。孤立的右BBB比左BBB更常見(0.18% vs. 0.1%),隨著年齡的增長,從45~54歲的0.4%增加到>64歲的1.3%。同時存在性別差異:在60歲以上的男性中11%存在BBB,而女性中只有5%。對于伴有暈厥和雙束阻滯的虛弱患者,可經驗性植入起搏器,無需進行電生理檢查。
5.3 起搏:適應證、模式選擇、程控、隨訪、遠程監測 現有的指南不建議改變虛弱患者的起搏器治療,但在考慮心臟再同步化治療(CRT)時建議使用CRT-心臟起搏器(CRT-P)而不是CRT-除顫器(CRT-D),強調需要全面審查風險—效益比,包括攜帶設備一起生活的影響和患者的偏好。診斷出顯著的虛弱且合并其他危險因素,如高齡、活動受限和限制預期壽命的合并疾病,可能更傾向于決定植入單腔起搏器。一般來說,年輕和老年患者植入起搏器的風險相似,但氣胸、導線脫位和由于消瘦引起的囊袋破損在老年人中更常見。因此,考慮到虛弱患者起搏的潛在益處,在遵循標準起搏適應證的基礎上,即使考慮到并發癥的風險和手術費用的增加,也建議對虛弱患者進行起搏治療。
模式的選擇取決于起搏的指征。UK-PACE試驗將2 021例年齡>70歲的高度房室傳導阻滯患者隨機分為單腔或雙腔起搏器組,發現2組在病死率或心血管事件方面沒有差異。高齡和/或非常虛弱的患者,如果不經常出現心室停搏,且身體功能受限和/或預期壽命較短,使用DDD (R)起搏模式和VVIR起搏模式相比,臨床獲益有限或沒有獲益。同時,在選擇起搏器模式時應考慮到植入第二根導線(心房導線)會使得相關并發癥的風險增加。相反,SND患者保持房室同步可減少因房顫、起搏器綜合征和心力衰竭的住院率。對于懷疑有功能缺陷的患者,在植入起搏器和選擇起搏模式之前,應使用已批準的方法正式評估其虛弱情況。
虛弱的患者參加隨訪可能很困難,遠程監測是有優勢的。
5.3.1 未記錄的心動過緩的起搏:跌倒是虛弱綜合征的共同特征之一。老年患者可能有多因素的跌倒原因,難以區分機械性跌倒和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跌倒,如緩慢性心律失常。認知障礙和健忘癥往往會妨礙鑒別診斷。在這種情況下,業內已認可的是傳統的暈厥檢查后可以采用植入式循環記錄儀(ILR),而不是經驗性起搏器植入。
5.3.2 無導線起搏:無導線起搏器可以預防一些與植入相關的并發癥,包括胸前血腫、破潰、囊袋感染、氣胸、心包填塞和電極脫位。在老年虛弱患者中,由于使用較大的導管鞘和心包填塞(約1%)而引起的血管并發癥是顯著的風險,因此在植入無導線起搏器前需要加以考慮。
從長期來看,心臟起搏導線通常被認為是起搏系統中最薄弱的環節,存在絕緣層破裂或導線斷裂和感染的風險。這些并發癥的發生率增加往往與存在伴隨的疾病和年齡大有關。無導線起搏降低了導線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兼容磁共振成像。這些特點使無導線心臟起搏器成為需要心臟起搏器的老年和虛弱患者的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
這些設備的長期狀態尚不清楚,特別是內皮化和纖維化的風險,可能會阻礙無導線起搏器的取出,并導致放棄無導線起搏,但對老年患者而言并不重要。目前,高達25%的患者采用VVIR模式,特別適用于老年和虛弱患者,這樣設備需要更換的可能性很小。
共識聲明:(1)虛弱在慢性心律失常患者中很常見,通常不是植入起搏器的禁忌證。(2)對于有輕微缺陷的患者,需要進行虛弱評估,因為它可能決定起搏模式和隨訪方式的選擇。
6 室性心律失常
6.1 室性早搏和室性心動過速 室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率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老年人動態心電圖室性早搏(VPB)的患病率高達70%~80%。頻繁的VPB可能具有潛在的心電、結構異常或心肌缺血。室性心律失常發生具有不同的機制,如折返與心肌梗死后瘢痕有關、慢性缺血組織中存在自律性升高、與獲得性QT間期延長相關的后去極化、由地高辛引發的觸發激動、并與新發心肌病或現有疾病惡化風險增加相關。
單形性VPBs最常見的是右心室或左心室流出道的起源,無結構性心臟病,無不良預后,通常不需要特定的AAD治療。
在頻發室性早搏合并心臟病理性改變的虛弱患者中,AAD治療的風險/效益比不佳,室性早博消融的數據有限,因此對這一人群的管理具有挑戰性。
老年患者的心源性猝死(SCD)常與惡性室性心律失常有關。主要原因是心肌缺血,生存率<5%。老年或虛弱患者的SCD也可能與機電分離或停搏有關,病死率接近100%。老年幸存者往往表現出認知或情緒障礙,凸顯了年齡對心臟驟停生還患者的影響。
6.2 VPB和室性心動過速(VT)的藥理學管理 VT的急性治療包括靜脈注射β-受體阻滯劑、胺碘酮(150~300 mg)、利多卡因和美西律,可以防止VT的立即復發和心室顫動(VF)的發生。胺碘酮仍然是唯一可以用于虛弱的危重患者的AAD。
6.2.1 β-受體阻滯劑和非二氫吡啶鈣拮抗劑:如前所述,β-受體阻滯劑通常被列為有癥狀的高負荷心室異位搏動患者的一線治療,但其療效有限。在某些情況下,非二氫吡啶鈣拮抗劑(維拉帕米)可用于特定的患者和維拉帕米敏感的心室異位搏動,也適用于非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NSVT)。頻繁發作特發性NSVT的患者應評估遺傳性心臟病的可能。
6.2.2 美西律和利多卡因:美西律和利多卡因可有效抑制異位心室自動除極和延遲后除極引起的觸發激動;在部分去極化心肌發生缺血時,美西律和利多卡因可將單向阻滯轉化為雙向阻滯,來干擾心律失常的折返機制。有小型研究對美西律的單藥治療療效進行了評估,在電生理程序刺激時,可抑制20%~30%室性心動過速的誘發,減少75%NSVT的發作次數。
美西律和利多卡因致心律失常或其他嚴重不良反應并不常見。在老年虛弱的SND患者中,如果曾經記錄到竇性心動過緩和竇性停搏,需要對受損的有竇房結和/或房室結功能進行監測。美西律和利多卡因主要由肝臟代謝,在心力衰竭和其他導致肝功能不全的原因中,藥物的清除可能會延遲。
6.2.3 D,L-索他洛爾:第三類藥(HERG通道介導的快速鉀電流阻滯劑)D,L-索他洛爾,通常避免用于有多種并發癥、多藥治療和經常電解質紊亂的虛弱患者,但可用于特定的患者,多為室性心律失常,但需要監測QT間期,且患者沒有明顯的左心室肥厚。索他洛爾還具有一種非選擇性競爭性β1-腎上腺素受體拮抗作用(主要局限于左旋異構體L-索他洛爾),它能有效抑制復雜的心室異位搏動,在穩定的冠狀動脈患者中效果優于β-受體阻滯劑,但不適合高血壓性心臟病、左心室肥厚和明顯左心室收縮下降的心力衰竭患者。索他洛爾160~640 mg/d能減少心室異位搏動,對于復雜的室性心律失常(多形性和多發室性早搏、成對室早或反復的NSVT)作用最明顯;這種作用在輕度左心室功能不良的情況下能夠維持2~6年。
6.2.4 胺碘酮:當單獨使用β-受體阻滯劑無效時,目前的證據表明胺碘酮通常對射血分數降低型心力衰竭(HFrEF)和高VPB患者有益,同時也考慮到其對心臟的安全性。
6.2.5 其他抗心律失常藥物:盡管ⅠC類(氟卡尼和普羅帕酮)藥物治療有效,并在無明顯的結構性心臟病個體患者中廣泛使用,但由于藥物的負性肌力作用和致室性心律失常的風險,目前的證據并不表明ⅠA類(二苯丙吡胺)和ⅠC類(氟卡尼和普羅帕酮)藥物在有潛在心臟疾病和/或心力衰竭的虛弱的個體中適用。純Ⅲ類藥多非利特(Dofetilide)在世界范圍內都沒有使用,包括許多歐洲國家,而多通道離子阻滯劑決奈達龍(Dronedarone)的使用僅限于房顫(AF),在歐洲也沒有廣泛使用。
6.2.6 何時啟動治療:對于VPB的頻次,目前還沒有確定的啟動治療的分界點。高度頻發的VPB患者(在24 h監測期間>總搏動的10%)可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左心室功能障礙或發展為心律失常性心肌病。在24 h內室早負荷>24%或>2萬個室早,與心肌病的發展有很強的相關性。但是,VPB有意義的分界點差異很大,在左心室收縮功能受損和心力衰竭的患者中分界點的閾值可能顯著降低,有報道顯示,VPB負荷低至4%就可與心肌病和心力衰竭惡化相關。
其他VPB特性如QRS波寬度作為心室不同步的標志,早搏指數[早搏指數(PI)=RR'/QT,其中RR’代表室早的聯律間期,QT為前次心搏的QT間期值。PI值<0.85時,提示該室早容易引起室速或室顫],多形性VBP,運動時VBP發作增多,室早二聯律/三聯律、插入性室早、心外膜起源和頻發VBPs持續的時間可能與心肌病發生和HF加重有關,應當進一步完善影像檢查,如心臟MR 和密切的隨訪,以評估VBPs的頻率和左心室收縮功能(如果MR檢查沒有發現任何潛在情況,可行超聲心動圖檢查)。
6.3 藥物性引起的室性心律失常 獲得性長QT可能導致多形性和尖端扭轉性室速,是最主要的藥物誘導的心律失常。大多數AAD可能有致心律失常作用,特別是在電解質異常和藥物相互作用等誘發因素的情況下。虛弱患者易出現電解質紊亂和多種藥物治療的情況,尖端扭轉型室速被認為是重要的關注點,主要原因是醫源性QT延長,但它也可能繼發于竇性心動過緩或房室傳導阻滯。
致心律失常(proarrhythmias)的治療:有效的治療需要準確識別心律失常和確認誘發心律失常的藥物,并及時停用相關藥物。同樣重要的是識別可能與心律失常發病或惡化相關的危險因素(如女性、高齡、腎臟或肝臟功能障礙、基礎結構性心臟病、低鉀血癥、低鎂血癥、藥物過量/濃度高、快速靜脈給藥、心動過緩、QT延長和已存在的離子通道病變)。
停止使用引起心律失常的藥物,無論血清鎂水平如何,都應靜脈注射硫酸鎂(如2 000 mg,彈丸式注射1~2次,如果致心律失常作用持續存在,則可持續靜脈輸注)。心動過緩和心臟停搏可能會觸發尖端扭轉性室速,通過>70 次/min起搏或靜脈注射異丙腎上腺素逆轉。應糾正低鉀血癥,將血清鉀補充至正常較高的范圍(即4.5~5.0 mmol/L)。
β-受體阻滯劑可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在較輕的病例中,由于洋地黃毒性引起的心律失常可以通過停藥、補鉀和觀察來控制。對于洋地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以往已經提出了幾種AADs,如苯妥英、利多卡因和β受體阻滯劑。近年來,洋地黃特異性抗體已被證明通過快速結合并迅速降低血清洋地黃濃度,被證明可有效逆轉洋地黃毒性。當出現由于傳導異常引起的癥狀性緩慢心律失常時,異丙腎上腺素靜脈注射或心臟起搏通常有效。
6.4 室性心律失常的射頻消融 在室性早搏高負荷和心律失常誘性心肌病惡化心力衰竭的患者中,射頻消融可能是首選治療方案,據報道消融可導致持續減少室性早搏負荷和心力衰竭住院、心臟死亡或心臟移植的風險。然而,這種干預措施尚未在前瞻性研究中進行探索,在虛弱綜合征患者中應用也有限。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70歲結構性心臟病患者(但未進行系統正式的虛弱評估)接受VT消融術,年齡較大的老年患者更容易發生圍手術期并發癥,院內病死率(4.4% vs. 2.3%,P=0.01)和1年病死率(15% vs. 11%,P=0.002)也更高,而1年VT復發率(26% vs. 25%)和VT復發時間(280 d vs. 289 d)與年齡較輕的患者相似。隨訪期間無VT復發與≥70歲患者生存率的提高密切相關。應該承認的是,這些數據涉及的是老年人,但不一定是虛弱的人群,這些數據不能推斷虛弱的患者。另一方面,這些患者可能會從手術中獲益匪淺,因為它可能會消除用藥物進行節律控制的長期風險。雖然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前瞻性試驗具有挑戰性,但收集虛弱患者室速消融的數據應成為國家消融注冊內容的一部分,或應啟動國際性登記注冊。
共識聲明:(1)如果患者有VPBs的癥狀和/或發展為左心室收縮功能惡化的證據,應立即開始適當的治療。(2)非常頻繁的VPBs(每24小時>20%)發生心肌病風險增加,患者應立即開始適當的治療,以改善預后和防止心肌病的發生 。(3)新診斷為頻繁VPB(>500次/24 h)的患者即使無癥狀,也應轉診進行專家評估,包括心臟影像(超聲心動圖、心臟MR、運動負荷試驗等),以排除任何潛在的心電和/或心臟結構異常。(4)在進行電生理檢查、開始治療之前,應仔細評估患者是否存在虛弱狀態;即便是細微的問題也最好在干預之前予以糾正。(5)最佳的藥物治療也應該針對基礎的心臟病。(6)室早的射頻消融治療可能導致左心室收縮功能障礙,因此治療前對患者進行風險—效益比的徹底評估,許多虛弱綜合征患者不適合進行消融治療。
6.5 ICD:適應證、選擇和結果 當預期壽命>1年時,植入式心臟轉復除顫器(ICD)治療有利于老年患者SCD的一級預防。關于ICD對老年患者的益處,隨機研究報道的結果不盡相同。在精心選定的心律失常死亡高風險和共病因素很少的老年患者中,ICD干預可將病死率降低到接近相應年齡的預期壽命。
應該承認的是,以上人群是高度選擇的,但由于競爭性死亡因素(通常是非心臟性原因),非缺血性人群中ICD一級預防的適應證不足以支持在老年和虛弱患者中常規進行ICD植入。因此,在最近對80多歲患者的ICD一級預防的研究中,3/4的患者沒有合并癥,最終適當和不適當ICD放電治療的比例和年輕患者相當,在19個月隨訪期間死亡的患者中(死亡患者占35%,死亡患者中38%死于非心血管原因),1/3接受了至少一次適當的ICD治療。
查爾森共病指數(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的預測有效性已經在老年(平均年齡 78歲)植入ICD患者中進行了探索。在ICD植入后的5年隨訪中,CCI評分為0~1、2~3和≥4分患者的生存率分別為78%、57%和29%,而非虛弱對照組的生存率為72%。 適當治療后的中位潛在生存期增加分別為>5、4.7和1.4年,CCI評分分別為0~1、2~3和≥4分。CCI評分在臨床實踐中使用困難,且CCI評分并非在老年人群中建立,虛弱和癡呆癥等情況可能對評分結果有很大的影響,以上這些CCI的局限性并沒有予以適當的考慮或重視。
因此,多變量評分(而不是按照年齡排列)和個體化考慮,關注共病、預計預期值、并發癥的終身風險、ICD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包括心理健康和患者偏好,應有助于ICD選擇及其生存效益的決策。
ICD對老年整體人群的干預可能成本效益較低,但老年患者預估壽命較長,如大于5~7年,植入ICD的成本效益是可以預期的。
然而,在所有這些研究中,大部分信息來自于精心挑選的伴有少量共病的老年個體、低級別衰弱,或使用不同定義衰弱的混合人群,因為以上這些因素不是這些研究的主要終點。衰弱的存在通常是RCTs甚至觀察性研究的排除標準。因此,關于ICD治療的風險—效益的數據非常有限。
可穿戴式心律轉復除顫器可能是一些患者的一種替代方案。然而,這些設備需要高度的依從性,良好的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以及一定的體力。因此,這些設備在預防虛弱患者SCD方面的作用有限。
6.6 針對身體虛弱老年患者的ICD程控 最近的ICD研究集中于新的程控策略,針對具有很少或沒有排除標準的患者,以減少不適當治療的發生率,并在持續室性心律失常的情況下提供不那么激進的治療。這些現代策略在老年患者中是否安全有效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快速室速設置較長時間的檢測區域、提高VF頻率設置,可以減少不恰當的治療次數,減少超速抑制和電擊的次數。這些程控參數設置在科學協會目前的共識文件中被提出,可以安全地應用于老年或虛弱患者。
6.7 皮下ICD(S-ICD) S-ICD正在成為一種預防SCD的療法,避免與經靜脈導線相關的并發癥可能對相對年輕和活躍的患者更相關。然而,在血管通路有限或持續感染的情況下,這可能是老年或體弱患者的一種選擇。基礎體質量低或存在進行性體質量和肌肉損失的風險,可能是虛弱評分較高的患者植入S-ICD的限制。
6.8 電極故障管理 在老年和虛弱患者中,電極拔除工具、對廢棄和召回電極的管理、感染的預防和治療以及電極拔除的危險分層方面的證據很難收集,因為即使在大的研究中心,這類患者的數量也太少,無法創建可靠的統計數據。在超高齡而預期壽命有限的虛弱患者中,導線(以及脈沖發生器,如果治療終止)通常會被棄用。
共識聲明:(1)一些心律失常死亡風險高的患者盡管年齡較大,但幾乎沒有共病因素,ICD一級預防可降低病死率。(2)進行程控設置,以提供最佳的ICD治療,旨在減少持續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放電,可適用于老年虛弱的患者。
7 心力衰竭和心臟再同步化治療(CRT)
7.1 心力衰竭患者中虛弱的定義和評估 在所有心血管疾病中,心力衰竭與虛弱的聯系最強,高達79%的心力衰竭患者被確定為虛弱。這2種情況有幾個共同的病理生理機制,主要是心肌和代謝功能不全,同樣被確定為虛弱的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死率和住院率最高。
對虛弱的評估在老年心力衰竭患者的管理中至關重要,因為實際年齡并不能自動識別健康狀況。心力衰竭協會(HFA)提出了心力衰竭患者虛弱的定義為一種多維動態和部分可逆的狀態,獨立于年齡。雖然一些衰弱評估工具已用于心力衰竭患者,但沒有一種在心力衰竭中得到驗證。HFA呼吁開發一種特異性的評分來識別心力衰竭的虛弱。
7.2 CRT:適應證、優化、隨訪 有或無除顫功能的CRT是NYHAⅡ~Ⅳ級心力衰竭、寬QRS波(主要是LBBB)、左心室射血分數<35%的患者廣泛使用的非藥物治療方法,在緩解癥狀、改善運動能力和生活質量、心力衰竭住院和病死率方面已被證實有效。使用CRT治療的患者的虛弱患病率尚未得到系統評估,但一些使用虛弱評估工具的小型研究報道稱,在接受首次植入的患者中,衰弱率可能高達81%,在接受系統升級的患者中,衰弱率可能高達68%。
由于多種共病,包括較高的房顫患病率,預計CRT對虛弱患者的益處較低,盡管初步報道表明,CRT可阻止虛弱相關癥狀的進展,如認知障礙。
虛弱評分G8評分<14分與CRT反應較差及無反應的比例較高相關。病死率和住院率也顯著高于非虛弱患者,大部分死亡源于心力衰竭而不是心律失常。這強調了對接受CRT治療的高危患者進行系統篩查的必要性,以及最佳藥物治療和運動訓練的重要性,以逆轉或阻止與虛弱相關的活動能力下降、營養和認知障礙。
共識聲明:(1)以力量、平衡和步態訓練為重點的有針對性的康復計劃可能有助于延緩虛弱的進展,并可能部分逆轉與衰弱相關的癥狀和改善生活質量。(2)對于選擇或接受CRT/CRT-D治療的患者,篩查虛弱可能有助于評估CRT預后和及時采取措施來抵消活動能力、營養和認知功能缺陷帶來的影響。
8 設備更換、升級/降級和在壽命終止時關閉
ICD在老年人群中的臨床療效可能由于“健康候選者”而出現偏倚。虛弱的患者有巨大的死亡和殘疾風險,不太適合進行CRT升級、 ICD植入和/或更換。雖然沒有前瞻性試驗證明ICD更換或CRT升級在虛弱患者中缺乏益處,但相當比例的虛弱患者對CRT的反應性低,且具有更大的心力衰竭失代償的風險和心血管器械植入后并發癥、再入院和死亡的風險。
在更換ICD之前,電池壽命耗竭時,應該重新評估虛弱,而且,無論是否給予了“適當的”抗心動過速治療,放棄ICD更換甚至考慮關閉ICD都是合理的。同樣地,對于那些考慮進行CRT升級的患者,基于虛弱的嚴重程度和潛在的共病,放棄CRT升級是合理的。
ICD植入者需要宣教,與醫生交流如何以系統的方式管理設備。瑞典一項針對80歲及非老年ICD植入患者的調查顯示,約34%的患者與醫生討論了他們的疾病進程,少數患者(13%)與醫生討論了關閉電擊涉及的問題,只有7%的患者告訴了他們的家人希望未來可能停用電擊。大約1/4的80~90歲患者對ICD在倫理、功能以及停止ICD治療的后果方面缺乏了解。重要的是,大多數參與者都表達了他們想要更換電池的愿望,即使他們已經年屆高齡(69%),或者患有危及生命的重病(55%)。
共識聲明:在所有個案中,醫生、虛弱患者和護理人員間應該進行一次涉及法律和倫理問題的實質性討論,包括最終需要停用設備。
9 室上性心律失常
房性心動過速在一般人群中不常見,年齡越大,大折返性房性心動過速的比例越高。房性心動過速通常具有耐藥性,而消融術可能因顯著的心房重構而無效。
房室結折返性心動過速可在晚年出現,這是由于衰老和共存的心血管疾病的觸發因素增加所致。年齡相關的房室結電生理改變可能導致慢徑的心房不應期延長。目前有限的房室結改良的系列報道成功率高達98%。
10 房顫
房顫是成人中最常見的持續性心律失常,不考慮年齡、性別和合并疾病,住院的合并房顫患者被歸類為虛弱的幾率是非房顫患者的4倍。
房顫患者的虛弱患病率為4.4%~75.4%,而虛弱人群的房顫患病率為48.2%~75.4%。在房顫患者中,虛弱與住院時間延長、癥狀加重、卒中發生率和全因死亡率顯著相關。
由于虛弱患者中認知損害、跌倒傾向、多種藥物使用和心血管疾病或其他合并癥的發生率較高,管理AF具有挑戰性。整合的ABC房顫管理路徑提供了AF患者的管理方法,也適用于虛弱的AF患者。
10.1 頻率和節律管理 頻率控制:將心室率減慢到生理上合適的水平。其優勢包括簡單易行、避免了AAD的潛在毒性或與房顫復發的電復律或左心房消融相關的風險和不適。
節律控制:恢復和長期維持竇性心律,主要使用AAD(離子通道阻滯劑),但偶爾會自主恢復節律,如使用β受體阻滯劑。
即便治療的主要策略是節律控制,心率控制仍然是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 心率控制的目標:(1)嚴格的心率控制,靜息心室率<80次/min,中等運動時<110 次/min。(2)寬松的心率控制,允許靜息心室率<110次/min。
通常單一藥物治療、寬松目標心率控制適用于永久性且無癥狀的房顫,且合并癥少的老年虛弱患者。β受體阻滯劑是心率控制的一線選擇,尤其是在HF患者中。地高辛(62.5~250 μg/d)具有抗腎上腺素能作用,可延長房室結不應期,抑制鈉—鉀腺苷三磷酸酶泵,從而改善心室收縮力,也可用作對β受體阻滯劑不耐受的永久性房顫患者的一線心率控制藥物,尤其是老年、久坐患者。地高辛作為二線治療對β受體或鈣通道阻滯劑反應不佳的患者是有益的。
10.2 卒中預防
10.2.1 一般原則:房顫相關卒中或全身血栓栓塞的最佳預防包括三個關鍵步驟(表5)。對于卒中低風險患者(即CHA2DS2-VASc評分為0的男性和評分為1的女性),不需要任何抗血栓藥物治療,而所有其他AF患者均需要使用口服抗凝劑預防卒中。非VKA口服抗凝藥(NOAC)優于維生素K拮抗劑(VKA)主要是因為其安全性更好,特別是在出血性卒中和其他顱內出血方面,并且與VKA相比,長期使用更方便。

表5 房顫更好監護(ABC)路徑
需要對出血風險進行跟蹤評估,控制可改變的風險因素,識別具有不可改變的風險因素的患者,這些患者需要頻繁的臨床隨訪評價。腦卒中和出血風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需要在臨床隨訪期間重新評估。
10.2.2 老年虛弱患者的抗栓治療:對6項研究進行的薈萃分析表明,虛弱房顫患者的OAC處方模式受到多種因素復雜的相互作用的影響,包括血栓栓塞和出血風險、虛弱狀態和房顫管理設置(如社區、醫院或護理機構),反映伴隨而來的競爭風險、預期壽命、醫生在房顫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病例評估的完整性。
可能影響OAC處方不足或中斷的因素,包括高齡、多種并發癥、認知功能受損、依從性差和出血風險增加,在普通房顫人群中常見。在高齡患者中,與阿司匹林相比,華法林在≥75歲的房顫患者中獲益[卒中或全身性栓塞的絕對風險降低2%,而大出血率兩者相當(1.4% vs. 1.6%)],與≥90歲的未治療或者抗血小板治療的患者相比,華法林同樣獲益。
在對包括27 000例老年人的關鍵的NOAC房顫試驗的薈萃分析中,NOAC的總體療效和安全性在所有年齡組是一致的。但在使用達比加群的≥80歲的患者中,年齡和顱外大出血發生率之間存在顯著的影響(與華法林相比,達比加群110 mg劑量的事件發生率相似,而達比加群150 mg劑量的事件發生率顯著增高)。利伐沙班、阿哌沙班、艾多沙班沒有觀察到這種交互作用。使用阿司匹林對預防腦卒中基本無效,且極度虛弱增加了阿司匹林相關的出血風險。
在老年房顫患者中,使用VKA較使用阿司匹林具有更好的認知功能。同樣,使用NOAC較使用華法林具有更好的認知功能。
跌倒在虛弱的房顫患者中是不良事件風險增加的標志,但不是OAC相關出血的獨立預測因素,在這些患者中,OAC的凈臨床獲益超過了嚴重出血的風險。
在為虛弱的房顫患者選擇OAC藥物/劑量時,其他考慮因素包括低體質量(阿哌沙班和艾多沙班劑量減少的標準)、多藥聯用(藥物—藥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增加)和共病(即慢性腎臟病、惡性腫瘤、癲癇等)。在EHRA關于房顫患者使用NOAC的實用指南中進行了詳細討論。
但在符合條件的房顫患者中使用OAC(最好是NOAC),虛弱并不應該作為排除條件。在急性住院的虛弱老年房顫患者中,未使用OAC與使用OAC相比,缺血性腦卒中或出血的綜合結局的比率顯著升高(HR4.54,95%CI1.83~11.25),且在使用OAC的老年房顫患者的社區隊列中,腦卒中發生率仍然高于大出血(1.73/100人年 vs. 0.9/100人年)。
ELDERCARE-AF試驗是一項安慰劑對照試驗,在被認為不適合標準OAC治療的日本老年房顫患者中,使用非常小劑量的艾多沙班(15 mg/d),使腦卒中的絕對風險每年降低了4.4%,大出血的絕對風險增加了1.5%,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重要的是,使用OAC的房顫虛弱患者需要對他們的基線風險概況、個人價值觀和偏好進行詳細地評估,并進行頻繁的臨床隨訪。
10.2.3 左心耳封堵:一般來說,左心房封堵(LAA)優于全身性OAC的最常見理由是高出血風險(如由于跌倒、肝腎功能障礙、多藥聯用和藥物相互作用)或全身性OAC的絕對禁忌證,其中虛弱的患者尤其脆弱。由于缺乏LAA封堵器和NOAC比較以及植入后抗血栓治療的必要性,缺乏高質量的前瞻性數據,以及缺乏對虛弱患者進行此類干預的經驗。
最近對Medicare數據庫的分析表明,從長遠來看,經皮左心耳封堵可能會使虛弱的患者受益。研究中包括21 787例65歲及以上接受左心耳封堵手術的患者,其中10 740例 (49.3%)根據醫院虛弱風險評分(HFRS)被認為虛弱(>5);33.5%被認為是中度(HFRS 5~15),15.8%被認為是高危(HFRS>15)。與HFRS <5相比,HFRS >15使長期住院(>10 d)的風險增加8.3倍,30 d再入院和30 d病死率分別增加1.8倍和近5.7倍。高風險組的1年病死率增加了2.8倍。虛弱患者的1年病死率(8.2%)幾乎是PROTECT-AF(2.5%)和PREVAIL(3.0%)試驗報道的3~4倍。
共識聲明:(1)在所有具有非性別相關CHA2DS2-VASc卒中風險因素的AF患者中,OAC治療是有益的,無論其虛弱狀態如何。(2)虛弱的房顫患者需要詳細評估他們的基線卒中和出血風險概況,并考慮他們在房顫治療方面的個人價值觀和偏好。(3)虛弱、認知能力下降和跌倒風險通常不是不給患者抗凝的原因。(4)服用OAC的虛弱AF患者需要頻繁、定期的臨床隨訪,以監測治療效果并重新評估卒中和出血風險。(5)在虛弱和非虛弱AF患者中,NOAC相對于VKA的優勢可能一致,但由于虛弱AF患者血栓栓塞事件的絕對風險較高,可能從NOAC中獲得更大的絕對獲益。(6)在LAA封堵前,對患者進行正式的虛弱性評估,可能會提供關于治療結果的重要補充信息,以及需要糾正的確定的缺陷和更徹底的隨訪。(7)阿司匹林不應用于虛弱的房顫患者的卒中預防,因為它本質上是無效的,且與NOAC或VKA的出血風險相似。
10.3 消融適應證和結果 虛弱狀態也可能對治療方法的臨床決策產生負面影響。年齡本身是老年患者消融后房顫復發的重要危險因素。在消融成功的所有患者中,腦卒中的長期發生率相對較低。與年輕患者相比,對80歲以上患者進行導管消融也是安全有效的,1年內無心律失常的存活率為78%,而年輕患者的存活率為75%。在另一項研究中,隨訪(18±6)個月,68%的80歲以上患者無房顫,小于80歲的患者中71%無房顫。老年組的嚴重并發癥并未增加。其他研究針對較年輕的人群(75歲及以上),結果顯示1年有效率為86%,3~5年有效率為52%~59%。然而,老年患者更有可能出現非陣發性房顫和非肺靜脈觸發的房顫,需要更廣泛的左心房消融和/或重復手術。
回顧性報道中有限的證據表明,接受AF消融術的患者中,一定程度的虛弱可能并不罕見,并且與消融術后較高的病死率和不良結局相關。在接受導管消融治療的5 070例住院患者中,38.6%被定義為虛弱患者(HFRS>5),其中包括8.3%的高危患者(HFRS>15)。虛弱與住院時間、術后30 d病死率和30 d再住院率獨立相關。長期病死率(長達630 d)在低危組為5.8%,中危組(HFRS 5~15)為23.4%,高危組為42.2%。相對于非虛弱患者,虛弱患者在因HF住院或卒中方面并未從消融中受益。
一些患者,尤其是患有多種內科疾病的患者,不愿意手術,而強烈傾向于藥物治療。共同決策對這些患者至關重要。
10.4 無癥狀性心律失常與房顫的篩查 通常高達40%的房顫患者可能沒有癥狀,或者癥狀不典型(約25%的病例)。與有癥狀的房顫相比,無癥狀的永久性房顫在老年人中的患病率更高,臨床情況也更加復雜,這種情況導致了更高的血栓栓塞、腦卒中風險,以及心血管和全因病死率。
機會性篩查的目的是檢測無癥狀性房顫和治療不足的已知AF,有40%~50%未識別AF因而沒有接受適當的治療。
CIED檢測到的房性高頻事件(AHRE)通常是在植入設備隨訪中發現,將在特定時間段內AF發作的總時間定義為“AF負荷”;CIED在無AF臨床病史或臨床癥狀的患者中檢測到的持續時間在5 min~24 h的房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發作定義為“亞臨床AF”。
AHREs和房顫負荷的發生率不同,這取決于基礎心臟病、觀察事件,尤其是包括AF在內的臨床上有明顯房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既往病史。持續時間為5~6 min的AHREs在植入CIED的患者中的發生率高達10%~68%。
CIED檢測到的AHRES與腦卒中或全身性血栓形成之間的關系,已經通過幾項研究進行了評估,這些研究總共收集了超過22 000例患者,持續≥5~6 min的AHRE負荷與卒中或全身血栓栓塞癥的風險增加顯著相關,風險比在2~9。然而,亞臨床房顫的卒中風險約為2.4倍,低于傳統報道的臨床性房顫(4.8倍)。隨機對照LOOP研究表明,在70歲及以上有卒中風險因素的個體中,使用ILR設備進行篩查,可能使房顫檢出率增加3倍,同時啟動OAC治療,但這一策略與腦卒中或全身性栓塞發生率的顯著降低無關。
目前的證據表明,在決定對AHRE患者進行抗凝治療時,個體化決策是有益的,特別是在虛弱的患者中。這種方法包括持續隨訪,采用CIED遠程監測房顫的發展、AHRE或AF負荷的演變,特別是超過24 h的AHRE變化,HF發作或惡化,或可能提示臨床狀況變化的任何其他征象。
共識聲明:(1)偶爾檢測到并持續30 s以上的無癥狀房顫不是良性疾病,需要進行與癥狀性房顫相同的臨床評估,包括卒中危險分層和抗血栓栓塞預防處方(基于CHA2DS2-VASc評分)。(2)篩查發現的房顫,無論是心電圖篩查到的,或者是脈搏觸診、血壓測量、智能手機或手表上的應用程序發現后經過心電圖證實的,不是一種良性的病情,在適當的臨床評估和卒中危險分層后,考慮采用抗血栓栓塞劑預防是合理的。(3)在植入了CIED并檢測到AHRE的患者中,需要進行完整的心臟評估,包括12導聯ECG、臨床一般狀況和血栓栓塞的臨床危險分層的評估。(4)在CIED檢測到AHRE的患者中,建議繼續進行患者隨訪(包括遠程監測),以檢測臨床AF的發展,監測AHRE或AF負荷的演變,特別是持續超過24 h的AHRE轉變,HF發作或惡化,或可能提示臨床狀況的任何變化,作為制定口服抗凝藥的個體化策略的基礎。
11 在高齡老年人中,腦卒中作為一個虛弱的成分及其具體特征
11.1 缺血性與出血性卒中風險 因為虛弱患者有很高的血管危險因素,治療中臨床醫生不愿使用抗血栓藥物,因此,虛弱患者面臨更高的腦卒中風險。腦卒中會加重虛弱,虛弱又會使腦卒中患者的預后更差。即使在最初是出血性腦卒中或高負荷的腦微出血的情況下,房顫患者的大多數腦卒中仍是缺血性的。
11.2 急診處理和慢性抗凝的意義 盡管在輕微的心源性腦卒中后急性抗凝似乎相對安全,但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在心源性腦卒中后的前14 d內抗凝能凈獲益。對于大多數心源性腦卒中,合理的方法是在第14天內開始抗凝。但如果有大面積梗死、神經影像學上轉化為出血或者未控制的高血壓,則抗凝推遲到14 d后進行。對虛弱患者而言,沒有證據支持其他更好的方法。
關于慢性抗凝治療對房顫血栓栓塞的預防,很少有專門針對虛弱患者的可靠數據。年齡的增長與血栓栓塞的相關性比出血更強,抗凝的臨床凈益處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即使在頻繁跌倒的老年患者中,抗凝也能帶來益處。即使是虛弱的患者使用現有的抗凝藥,出血風險也與阿司匹林類似。這些因素支持在虛弱的患者中使用抗凝治療。
共識聲明:在進一步的數據可用之前,虛弱的房顫患者應該像非虛弱的患者那樣接受抗凝治療。
12 直立性低血壓和暈厥綜合征
12.1 頸動脈竇高敏綜合征 頸動脈竇綜合征(CSS)是一種以心動過緩和低血壓為特征的反射性暈厥。該綜合征幾乎只在老年(男性)患者中診斷,40歲以前很少見。建議50歲以上出現不明原因跌倒或暈厥的患者應進行頸動脈竇按摩(CSM),對神經系統事件發生風險的患者按摩過程中需特別注意。診斷需要再現心臟停搏和/或血管抑制的癥狀。
在一個大型隨機社區隊列研究中,平均年齡75歲人群CSM反應的第95百分位數為心臟停搏7.3 s,收縮壓下降77 mmHg,提示了診斷和干預的臨界值。
12.2 直立不耐受綜合征 直立不耐受綜合征的特點是收縮壓和舒張壓異常、進行性和持續下降≥20 mmHg和≥10 mmHg,或收縮壓下降至<90 mmHg,見表6,根據血壓異常的發生時間,可分為速發型、經典型和延遲型低血壓。

表6 直立不耐受的癥狀
12.3 研究和管理 ESC暈厥指南提出的診斷標準也被用于老年患者,使無法解釋的暈厥比例減少到10%左右。初步評估依賴于臨床病史、體格檢查、主動站立試驗和12導聯心電圖。醫生應評估全身性疾病、身體虛弱和運動障礙的情況,記錄認知狀態、社會環境、受傷情況、暈厥對基礎的/器械輔助下的日常活動影響的細節。由于老年或虛弱患者可能存在逆行性失憶,應對可能的目擊證人進行詢問。必須仔細觀察患者的步態和站立平衡情況以評估跌倒的風險。鑒于老年人CSS高發,可以先進行CSM檢查。對以前有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或腦卒中病史,或當頸動脈狹窄>70%時,謹慎進行CSM檢查。臨床病史對心臟和神經系統病因的鑒別診斷價值有限。因此,傾斜試驗(TT)和CSM是必不可少的診斷步驟。
TT在老年受試者中的使用得到了驗證,且耐受性良好,即使在最年長的老年人中也是如此。TT可以檢測到低血壓的易感性、速發型和延遲型直立性低血壓,并指導暈厥和其他引起不明原因跌倒之間的鑒別診斷。ILR可能有助于區分暈厥、不明原因的跌倒和癲癇發作。
對于血管抑制型反射性暈厥的老年患者,可以通過停止/減少血管活性藥物來減少暈厥/暈厥前兆的復發,以減少不良事件,建議老年和體弱的成年人平均收縮壓控制在140 mmHg左右,或不小于130 mmHg。
兼顧臥位高血壓治療直立性低血壓的藥物包括:米多君、屈昔多巴、氟氫可的松和吡多斯的明。另外,等距物理抗壓動作、彈力襪、腹部束帶以減少靜脈淤積,可預防復發。
根據目前的ESC指南,對于由反射性心臟停搏引起的暈厥患者,應考慮心臟雙腔起搏。在直立傾斜誘發的血管迷走性暈厥患者以及CSS患者中,當心臟抑制性反射占主導地位時,也推薦雙腔起搏。然而,起搏器植入應限于≥40歲的患者,在替代治療失敗或不可行,且暈厥對患者的社會和自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下考慮。
13 改善患者預后:特殊思考
13.1 生活質量 虛弱會導致身體、情緒和社會功能的下降,從而顯著影響生活質量。對于大多數虛弱的患者,他們期望的治療目標是改善功能狀態和生活質量,而不是延長生命,在制訂治療決策過程中應考慮這些因素。目前,針對心律失常患者虛弱對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較少。虛弱對治療選擇有顯著影響,虛弱的心律失常患者接受積極治療的可能性較小,如虛弱的房顫患者不太可能接受口服抗凝治療,主要是因為醫生擔心與虛弱相關的特征(跌倒和認知障礙的風險)、相關的出血,也不太可能接受心律控制策略。由于體弱患者非心臟性死亡的風險增加,可能會降低ICD的益處,因此在體弱患者中使用ICD也存在爭議。
13.2 護理模式 護理模式側重于逆轉可改變的虛弱因素,特別是解決導致和/或促成虛弱的潛在醫療條件,并優化管理和審查藥物,以延緩潛在的疾病過程。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需要認識到虛弱,因為他們往往關注特定的疾病/共病,這些可能掩蓋了虛弱。需要對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進行教育,以明確虛弱的組成部分,認識到虛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并演示如何優化這一虛弱患者群體的管理。使用適當的工具識別虛弱是第一步,如果確定,應該進行進一步的全面評估(由老年醫學醫生評估)。虛弱的概念需要更全面的定義,而不是以疾病為基礎的醫療方法,應將健康和社會護理結合起來,并考慮到對患者及其家人/護理人員的重要性。因此,這種方法需要多學科干預以及多學科團隊的支持和投入。
13.3 發展一支專家團隊和后續護理 最近EP Wire的受訪者更傾向于由電生理學家、臨床心臟病學家、老年醫學家、內科醫生、護士和家庭成員/護理人員組成的“心律失常團隊”來管理虛弱患者。此外,專家團隊還應包括專科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運動生理學家、全科醫生、藥劑師和社會工作者。團隊的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患者的個人需求,最好有合適的各方面的專家加入。對患有心律失常的虛弱患者的持續護理最好由社區中的專科護士主導,并根據需要適當隨訪和轉診到多學科心律失常團隊。
13.4 數字技術與電子健康 需要長期護理并經常評估健康狀況的虛弱患者可能受益于數字健康(遠程健康、移動健康和可穿戴設備,如心率、活動跟蹤和生物傳感器)。這些技術能夠檢測和監測虛弱綜合征的組成部分,如體力活動、步態速度、姿勢變化和跌倒、心率和健康狀況、心律失常,并有助于及早識別亞臨床健康惡化。認知、視覺或感覺障礙可以通過遠程健康或移動健康設備進行評估。遠程醫療可以為越來越多的虛弱患者提供高質量和低成本的護理。
參考文獻229條(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