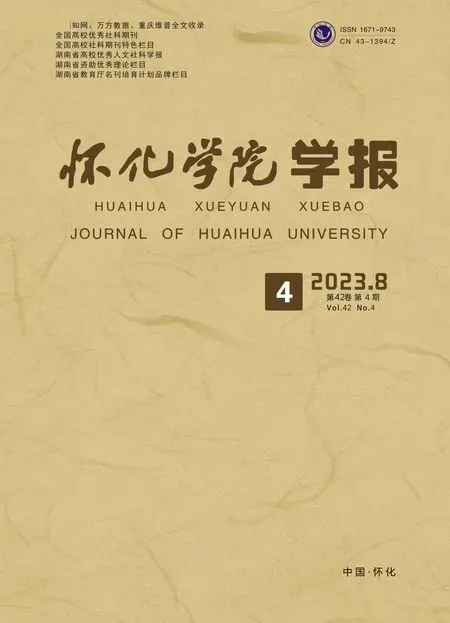窗戶·三棱鏡·漸近線·畫框:電影與現實的四種形態關系
譚志勇
(懷化學院,湖南 懷化 418008)
電影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是經典電影理論家研究的重點內容,在這一問題上,經典電影理論家于果·明斯特伯格和寫實主義理論大師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都提出了電影是“窗戶”的觀點;魯道夫·愛因漢姆則認為電影是現實折射的“三棱鏡”;安德烈·巴贊在物質本體論基礎上提出電影與現實“漸近線”關系;讓·米特里強調畫面關注點的自由選擇,進而提出了“畫框論”。這些論說引起了美國電影理論家達德利·安德魯的關注,他分析了經典電影理論家對電影與現實形態關系理解的異同。在達德利·安德魯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將以“窗戶”“三棱鏡”“漸近線”和“畫框”四個形態論說為基礎,分析論說形成的理論基礎和心理機制,歸納和對比不同論說之間的關系,從而探究電影與現實的關系,揭示電影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一、“窗戶”論:心智素材和物質現實的復制
在探索電影真實藝術本質上,傳統形式主義大師明斯特伯格和寫實主義大師克拉考爾都提出了“窗戶論”,但是視點各有不同:一個是從形而上的角度詮釋電影是照進觀眾心理“窗戶”的審美藝術,是心智的素材,而非機械復制的工具;一個從現實主義筆觸審視電影映照屬性,即物質現實復原的“窗戶”。兩者在辨析電影與現實的形態關系時,存在統一的論說,卻有著不同的視點,從而形成了形態論說一致,但是觀點內核悖反的關系。
(一)心智素材“窗戶”論的理論依據
明斯特伯格在《電影:一次心理學研究》一書中肯定了電影作為一種心理動機藝術,即“電影是對人心理機制的模擬,是信息的加工過程”[1],并運用威廉·馮特的結構主義解析電影在觀眾心理的過程:縱深感和運動、注意力、記憶和想象、情感,即人通過對光影縱深、運動的感知,以及注意力的改變,獲得二維畫面的三維真實感,再通過大腦的記憶和想象,產生意義、沖突和個人旨趣,最后,這些內容通過“情感”在主體心理得以呈現。電影的審美過程成為明斯特伯格認為的不同層次的心理活動,電影通過人類的心智素材的重組、沖突而產生意義,是純粹的心理活動。他著重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強調人的心理活動中智力、經驗感知的主動性參與,指出電影以無生命的虛幻畫面喚起觀眾生活中感知的具體物像,這些心智素材的組合是一種非現實、意識流和光影的游戲,觀眾透過電影銀幕這扇“窗”了解人的精神活動。他指出“電影不存在于銀幕,只存在于觀眾的頭腦里”[2],并提出電影是展現人類心靈“窗戶”的論說。
(二)“物質復制”與“心智素材”的辯證關系
克拉考爾和巴贊一樣享有“現實主義”的標簽,在《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世界的復原》中,他十分強調攝影在電影中的核心地位,認為電影的真實性與攝影密切相關、不可分割,這種近親性必須受到尊重,并把對現實的復原作為首要任務和核心。克拉考爾認為觀眾看電影就像透過一扇窗,觀看窗外隨機的、客觀的視覺真實的世界。
和明斯特伯格一樣,克拉考爾也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沿用了格式塔心理學中對物象心理感知的觀點,他的電影“窗戶論”類似康德的“先驗”即對映照的現實進行整體感知的觀點、韋特海默主張的直接經驗的觀點、胡塞爾現象學中如實描述再本質認知的觀點、契合考夫卡關于“環境場”“心理場”“行為場”等“場”論的觀點,以及馬赫的物象可以獨立于物質屬性被個體經驗感知的觀點。
區別于明斯特伯格純粹心理感知的“窗戶論”,克拉考爾強調“窗戶”映照現實物質外部表征的特點,認為電影作為“窗戶”具有復制物質外在形象的屬性,觀眾對“窗戶”內的外在物質產生經驗感知,經驗感知是建立在自然物象和事件產生大量的“心理—物理”的基礎上。[3]為此他對電影作為“窗”在洞察外在物質的形態時提出了具有心理感知效應的要求,即物質現實應具備偶然性、不確定性、多義性和模糊性的感知特點才能夠被觀眾感知到經驗的真實,并尊重觀眾“窗戶”內關注點的自由選擇。在創作主體層面,他指出創作者對物質存在的心理頓悟,可以通過攝影復制展現出來,觀眾在開放、經驗式的想象中發掘超越素材本身的意義。
總體上,雙方側重的視點不一樣,明斯特伯格“窗戶論”重點在作為心智素材層面;克拉考爾的“窗戶論”則把電影“窗戶”作為媒介,重點關注媒介內物像映照后的心理感知。不同的側重點,使得電影作為“窗戶”的觀點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延伸。
二、“三棱鏡”論:折射藝術和“局部幻想”
愛因漢姆是深受明斯特伯格和格式塔心理學影響的電影理論家,他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明斯特伯格形而上的心理學研究,并開始專注于視知覺、審美藝術和經驗心理、審美知覺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他把電影當作“三棱鏡”,重點指出了電影作為“三棱鏡”具有的“形象偏離”折射性和局部幻想性特征。
(一)延續:視知覺認知心理和藝術獨立性
魯道夫·愛因漢姆認為視知覺具有和思維一樣的功能,他主要從格式塔心理學的“張力”“場”“異質同構”等理論來研究視知覺在直覺基礎上的審美情感,認為意象是視知覺在物質表象上抽象的結構,是視知覺整體本質結構上的感知,而非完全復制。[4]愛因漢姆認為電影是人類視知覺感性認知基礎上的理性活動,視知覺可以通過抽象的邏輯判斷達成對事物本質的理性認知。
愛因漢姆延續了明斯特伯格強調的藝術表現形式與現實之間的區別,認為藝術不是對現實簡單的模仿,電影是一門獨立的藝術,是現實的抽象和剝離,要求電影區別于戲劇,與現實保持距離,從而保持電影的本真和藝術的獨立性。為強調電影與現實之間的區別,愛因漢姆提出電影區別于現實的“六因素”:平面上的投影、縱深減弱、無色彩和人工光、畫框限制、時空不連續、視知覺外其他感覺失去作用。他堅定有聲電影給電影帶來的破壞,認為技術應該為藝術服務,主張承認差別,反對寫實,倡導電影作為獨立的藝術化,反對電影是現實的復制觀點,認為電影是技術性的視域產物而非人類真正的視覺,以及電影具有畫框限制的重大“缺陷”。
(二)區別:強調“形象偏離”和“折射”的藝術
相對于明斯特伯格的心靈映照的“窗戶論”和克拉考爾外在物質形象復制的“窗戶論”,愛因漢姆關注于存在人與“窗戶”之間的“折射”現象,他形象地把主觀性的折射比喻為“三棱鏡”,即通過技術轉換、主觀性創造,使現實“改頭換面”成為新的藝術形式,他強調了電影與現實“形象的偏離”,以及對現實的主觀“折射”性,并指出:與其說電影是“窗戶”,不如說是“三棱鏡”更恰當。
愛因漢姆的觀點中強調的物象映照,并不是鏡子直接的鏡像,不是對現實“直線”的復制,因為他發現電影與現實之間存在“鴻溝”,比如演員夸張、程式化的表演,這些區別于現實的形態呈現更加容易刺激觀眾感應,從而形成電影獨有的區別于現實的心理效應,以及觀眾對電影約定俗成的理解方式。在對電影動作的認知中,他指出電影動作是對自然動作的簡單模仿,這種“仿造”的進一步演進,使得電影動作更加區別于現實動作而存在,電影進一步“儀式化”“電影化”“獨立化”。在這些區別基礎上,他堅持認為對象和事件作為電影的心理素材,需要透過“三棱鏡”脫離現實才能成為一種創造性的藝術,這也成就了他著名的電影“三棱鏡論”。
(三)延伸:電影是現實的“局部幻想”
愛因漢姆在格式塔心理學主張的“心理的結構能力說”的基礎上提出“局部幻想論”。[5]觀眾通過局部的物質形象,想象并結構成一個整體,從而獲得一個高度集中的、具有強烈藝術性的完整印象。[6]
“局部幻想論”認為只要電影出現與現實相符的關鍵部分,觀眾就能建構一個整體形象,產生幻想印象,而無需對現實進行完整地再現。“局部幻想論”是愛因漢姆“三棱鏡”論的進一步發展。“三棱鏡論”側重于折射和“形象偏離”,“局部幻想論”極力要求承認電影與現實之間存在的不完整對稱,并認為電影的“殘缺”反而成為創造藝術的可能。愛因漢姆指出“只有在現實與表現手段不一致時,藝術家才有發揮創造力的余地”,于是,他極力維護“無聲電影”的合理性,反對技術的運用,指出蒙太奇在對時空割裂的同時,間接創造了更多可能。“局部幻想論”強調了畫框的限制產生藝術的創作可能性,這與米特里的“畫框論”有一定的聯系。但是區別于“窗戶論”,愛因漢姆的“局部幻想”觀點把電影與現實的關系描繪得更像是半掩蓋的“窗戶”,觀眾只看到窗戶內的一部分再通過幻想獲取完整的形象。這種“半邊窗”局部幻想觀點,在后來間接得到豐富,現代電影創作者力求突破畫框的限制而創造更大范圍的空間,往往主觀的“局部殘缺”化,局部的畫面外存放看不見的“殘缺”內容,觀眾通過想象拓展畫面內部空間,產生延伸效果,形成獨有的電影空間藝術。愛因漢姆的“局部幻想”觀點,使得電影作為“窗戶”的觀點得到新的延伸。
總體上,愛因漢姆延續了明斯特伯格的“心靈窗戶”論,但是否定電影僅僅是純粹的心理、視覺認知,更加重視電影形式技巧表達和藝術功能,強調了電影與現實之間“三棱鏡”折射關系,以及電影與現實非完整復制的“局部幻想”特征,承認了電影與現實的區別,將電影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所以,如果電影是明斯特伯格和克拉考爾所說的“窗戶”,那么愛因漢姆則認為電影是被窗戶上的玻璃折射到外面的光扭曲現實的景而成的藝術。同時,他進一步強調這種折射的不對稱性,即電影和現實之間存在局部限制性,觀眾通過局部想象補充完整,完成對電影與現實之間的高度“仿真”效應。愛因漢姆在《電影的藝術》中開始探索從意識層面發展到形式藝術層面,從關注電影的意識內容,到關注電影作為藝術本身具有的特征,并主張利用形式和技巧的變化拓展電影藝術的張力。“三棱鏡”和“局部幻想”論成為愛因漢姆看待電影與現實關系的重要觀點。
三、“漸近線”論:無限靠近,永不相交
巴贊認為:影像是“光的模型”(A mould in light),它捕捉物體的“印象”(Impression)。它不是真實的物體,而是真實的、可追尋的“痕跡”(Tracing),電影素材就是事物留在膠片上的痕跡,影像高度接近實物,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Asymptote of reality)[7]。
(一)“漸近線”論的形態特征
第一,同一性的“漸近線”。巴贊深受薩特的存在主義、梅洛·龐蒂現象哲學、柏格森直覺主義等思想的影響,“電影的存在先于本質”“攝影本體論”源于薩特的“存在早于本質”的觀點。[8]在存在主義的影響下,巴贊首先強調了“影像本體”的論斷,攝影機“照相”屬性和物質現實的復原屬性是攝影的本質屬性,攝影機存在意義和價值符合人類的“木乃伊”情節中“長生不老”心理,人類保存“像”的完整性和延續性心理欲望是先于攝影機存在的,這是攝影機復制“像”功能存在的價值和電影心理動機的基礎,觀眾通過攝影機復制的“像”完成移情、共情和自我認識。其次,巴贊極力尊重“像”和現實之間復制同一的關系,認為蒙太奇組接方式主觀地將時間、空間割斷,違背現實時空該具備的連續性,長鏡頭則彌補了缺陷并尊重了現實的客觀性。他贊揚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并不屈從“心智素材”“視知覺經驗”“先驗”等形而上觀點,而從物質外在純表象去推斷存在的含義。所以,巴贊一直強調電影的紀實性、客觀性和攝影機的“冷眼旁觀”視角,并進一步認為現實主義電影需要放棄戲劇性、邏輯性、劇情結構和對人物的心理表現,關注現實本身,保持現實的多義性、模糊性和偶然性。[8]這種偶然性、多義性進一步強調了對現實素材攫取的非主觀性原則,力求做到極致的客觀創作,多義性則強調尊重觀眾對現實素材復制的“像”的自由理解。巴贊前期的觀點著重于電影和現實同一關系,如同兩條“漸近線”,在物質外在形象真實上高度一致。但是巴贊同樣認可電影不可能實現對客觀現實的完整摹寫,尤其是攝影復制不能挖掘物質外在形象的內心真實,這讓巴贊在后期更加重視對精神維度真實的探討。
第二,精神真實的“漸近線”。在巴贊后期的電影研究中,他發現了更多自我矛盾的地方,現實真實具有攝影無法描摹的復雜性,比如攝影機無法解讀演員臉部復雜的情緒以及物象之間存在微妙的規律和關系。與愛因漢姆的固執己見不同,巴贊果斷地跳出唯實主義,提出真實也是觀眾心理感知的真實,電影的感覺真實是建立在攝影機所展現的真實空間基礎上的。與把費里尼當作新現實主義的“叛徒”不同,巴贊認可費里尼和安東尼奧尼所傳達的從“現實真實”到“精神真實”的觀念,接受了費里尼“在想象和現實之間,我看不到明確的界限”的觀點,認為這是現實主義電影的革新和延伸,提出了“人之新現實”(Neo-realism of the person)的概念[9]。這些觀點使得“漸近線”理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延伸,并使得現實主義電影走向“形而上的現實”即精神層面的真實,探尋透過物象背后的內容、規律和潛在意義,尋找精神緯度的真實,開始了客觀真實向內心真實的深入。此外,巴贊賦予了現實主義電影人文情懷、人道主義視角的表達,這在一定層面上與他前期強調的偶然性復制互相矛盾。于是,巴贊在“總體現實主義”基礎上,開始豐富對“漸近線”的理解,并指出電影與現實之間是無限靠近,永不相交的“漸近線”關系,即電影真實和現實真實無限靠近,但是永不相同。
(二)從形式主義到寫實主義演變
相對于明斯特伯格的“窗戶”和愛因漢姆“三棱鏡”論形而上研究,巴贊的“漸近線”論從傳統的形式主義轉到寫實主義研究,這與克拉考爾的“窗戶論”保持一致。同樣作為寫實主義的電影理論家,巴贊肯定和繼承了克拉考爾的大部分觀點,否定了作為電影剪輯的蒙太奇對時空的破壞作用,提出尊重攝影機的復制屬性,現實是電影的基本素材,強化表現的真實、時空的真實和敘事結構的真實。反對形而上的論說,反對非理性、純視覺的敘事方式,強調電影與現實的一種對應關系,認為電影的本性是紀實性的再現。巴贊不同于克拉考爾的是克拉考爾強調的現實是哲學基礎上的、大自然的、存在的、物理屬性的“物質現實復制”,是排斥內心、幻想等精神層面的絕對的物質真實,而巴贊表達的是攝影機對現實完整的“臨摹”,是指一種“完整的真實”,包括精神層面存在的真實。與巴贊相比,克拉考爾的“現實觀”顯得規定性更強,在他那里“現實”只等同于“物質現實”,而絕對排斥“精神世界”真實觀主觀真實與客觀真實。[10]
區別于傳統的形式主義理論,巴贊從單個空間的映照,發展到形而上層面的真實性面貌,基于精神世界對現實的真實反饋,而不是重新的組合、反應,是一種透過外在現象看本質的藝術思考。“漸近真實”的提出使得巴贊區別于傳統形式主義形而上的理解而又進一步,他的美學思想和電影評論對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創辦的《電影手冊》成為法國新浪潮電影宣傳的陣地,長鏡頭理論被熱捧至今。隨著3D、4D 等新技術的出現,電影與現實之間愈加無限接近,但是電影虛幻、畫框限制等特征的存在使得電影同樣無法等同于現實,因而無法相交。巴贊的“漸近線”理論將在長時間內被奉為電影與現實之間關系的圭臬。
四、“畫框”論:畫框限制
“畫框論”是建立在蒙太奇理論之上,愛森斯坦把鏡頭取景形容為“對象與人們觀察它的角度和從周圍事物中截取它的畫框之間的相遇”。[11]基于西方電影理論中的“摹仿論”,愛因漢姆、明斯特伯格、愛森斯坦和巴贊等電影理論家把電影作為畫框討論過,重點在電影畫面與繪畫之間形態關系的類似,米特里則針對“畫框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強調畫框的存在
米特里贊同巴贊的“漸近線論”,但是著重探索“漸近線”的原因,即為什么現實和影像無法交織。他認為電影影像不同于心像,影像是對現實的復制,心像是建立在觀眾經驗上的映照,但同時,電影影像與現實的區別是不能反映原物的在場。此外,電影影像是窗戶還是畫框,米特里認為兩者皆是。當影像只是反映被紀錄的現實事物時,就如同窗戶;當影片影像作為再現形式承擔起表意功能時,則構成了表意系統的一部分,如同畫框那樣,成為構圖的一部分。[12]
米特里強調了畫框的存在,并指出了畫框存在的限制性,這是區別現實的重要特點。熒幕上有框現實卻沒有,人們只能通過想象邊框外的世界的存在以達到真實的體驗。繪畫也是在有框的基礎上產生更寬廣的想象,才具備了更大的藝術魅力。因此,米特里從畫框限制出發,指出電影更像是“畫框”。同時,米特里也指出電影和繪畫一樣,觀眾承認畫框外的世界是存在的,并相信畫框外的世界也是真實的,這是觀眾審美認同的一種約定和訴求,也是觀眾的一種經驗“預設”,并通過現實中的邏輯結構畫框內和畫框外的世界,使之產生整體意義。
(二)“類似物”:“中庸”路線產物
米特里綜合愛因漢姆和巴贊的理論,走出一條“中庸”路線,以闡述影像是寫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綜合。電影被他認為是攝影機創造出來的“類似物”,電影只是與現實具備同質的視覺形式,這一特征如同繪畫一樣,同樣是“類似物”的視覺形式,也同樣有畫框限制。畫框限制是米特里認為巴贊的“漸近線”永不相交的重要原因,“畫框”論成為米特里區別于形式主義和寫實主義的重要論點。與明斯特伯格和愛因漢姆相同的是,米特里同樣受到格式塔心理學的影響,并試圖從心理學的視角去解讀電影的景深、運動、色彩、音樂等元素,他充滿著辯證精神,試圖調和蒙太奇和長鏡頭之間的矛盾,證明兩者能夠和諧共存。他并沒有嚴格區分自己的理論派系,而是兼容并包、博采眾長,并認為這才是現代電影理論的研究方法。
“窗戶”論、“三棱鏡”論、“漸近線”論和“畫框”論是經典電影理論家對電影與現實關系的比喻體,經典電影理論家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滲透、借鑒、補充和討論,或有共同的理論基礎,比如一定程度上受到格式塔心理學和西方理論中的“游戲說”“摹仿說”的影響,巴贊的“完整現實神話”就涉及畫框和窗戶形態論說,米特里探討過其他三個觀點,這些論說的觀點并非劃清界限,更多的是理論基礎和視點的不同。隨著電影理論的發展,在探究電影與現實本質關系上,作為開端的經典電影理論側重電影與現實之間關系的探討,現代電影理論中出現的“鏡像”“符號”“媒介”等論點側重研究電影與觀眾的關系,后現代認知符號學理論側重于跨學科符號研究人類意義的生成。總體來說,經典電影理論的不同形態論說,像打開了一扇“窗”,推動電影理論不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