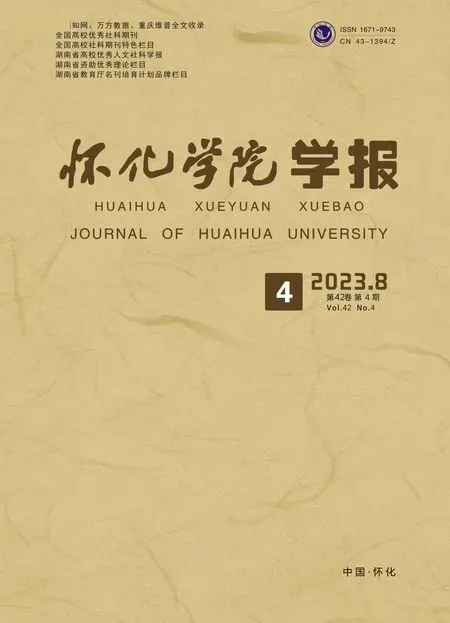論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的學(xué)術(shù)淵源與基本理論
蔣 瑜, 黎千駒
(1.成都文理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401; 2.湖北師范大學(xué),湖北 黃石 435002)
韓非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術(shù)勢(shì)思想,其法術(shù)勢(shì)思想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性惡論是其理論基礎(chǔ),老子、墨子、荀子及以往的法家學(xué)說(shuō)是其學(xué)術(shù)淵源,韓非子對(duì)法術(shù)勢(shì)的界說(shuō)、功用及其關(guān)系的闡釋構(gòu)成了其基本理論,刑名之學(xué)是其御臣之道,君主專(zhuān)制和極權(quán)是其政治內(nèi)容,重農(nóng)耕而除五蠹是其經(jīng)濟(jì)內(nèi)容,實(shí)現(xiàn)帝王之業(yè)是其終極目標(biāo)。限于篇幅,本文僅探討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的學(xué)術(shù)淵源和基本理論,而另撰文探討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的政治、經(jīng)濟(jì)內(nèi)容與終極目標(biāo)等。
一、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的學(xué)術(shù)淵源
韓非子繼承并改造了老子的道家學(xué)說(shuō)以及墨子主張統(tǒng)一的思想和主張權(quán)威的學(xué)說(shuō),拋棄了荀子的隆禮思想而繼承和發(fā)展了其重法思想,同時(shí)又吸取了以往的法家學(xué)說(shuō),特別是商鞅的法治思想、申不害的術(shù)治思想和慎子的勢(shì)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一)繼承并改造老子的道家學(xué)說(shuō)
韓非子大量繼承并改造了老子的道家學(xué)說(shuō),其《解老》與《喻老》兩篇,首次對(duì)老子思想進(jìn)行了集中的闡釋?zhuān)⑶以谄渌S多文章中,也對(duì)老子思想進(jìn)行了闡釋。例如:老子哲學(xué)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韓非子則認(rèn)為,制定法律應(yīng)當(dāng)“因道全法,君子樂(lè)而大奸止;澹然閑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wú)離法之罪,魚(yú)無(wú)失水之禍。”[2]這無(wú)疑繼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認(rèn)為“魚(yú)不可脫于淵,國(guó)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韓非子解釋道:“勢(shì)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失勢(shì)重于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fù)得也。簡(jiǎn)公失之于田成,晉公失之于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yú)不可脫于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jiàn)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jiàn)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jiàn)賞而人臣用其勢(shì),人君見(jiàn)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4]這無(wú)疑繼承了老子的辯證法思想,并將其改造為重“勢(shì)”的理論依據(jù)。老子倡導(dǎo)“無(wú)為而治”,曰:“是以圣人處無(wú)為之事,行不言之教。”[5]韓非子則倡導(dǎo)“明主治吏不治民”[6],應(yīng)如“日月所照,四時(shí)所行,云布風(fēng)動(dòng);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自己;治亂于法術(shù),托是非于賞罰,屬輕重于權(quán)衡”[7]。這無(wú)疑繼承了老子“無(wú)為而治”的思想,并將其改造為以法術(shù)勢(shì)和賞罰為中心的“無(wú)為而治”。因此,司馬遷曰:韓非子“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xué),而其歸本于黃老”[8],“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皆原于道德之意”[9]。
(二)繼承并改造墨子主張統(tǒng)一的思想和主張權(quán)威的學(xué)說(shuō)
墨子認(rèn)為,治理國(guó)家最重要的一種方法是“尚同”。所謂尚同,就是人們的思想應(yīng)當(dāng)統(tǒng)一于上級(jí),進(jìn)而統(tǒng)一于諸侯,諸侯統(tǒng)一于天子,天子統(tǒng)一于上天。“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10]尚同的宗旨是主張統(tǒng)一思想和主張權(quán)威。然而墨子認(rèn)為,尚同是具有前提條件的,這就是“尊天”與“事鬼”和“賢人政治與好人政府”。尚同不能以天子為止境,因?yàn)樘熳又线€有上天和鬼神存在,只有上天和鬼神是最公正無(wú)私而可以效法,因此墨子認(rèn)為尚同的最高境界是要尚同于天。天子并非可以為所欲為,他上面還有上天和鬼神管著。尚同的政治基礎(chǔ)是賢人政治與好人政府。實(shí)施尚同就必須實(shí)施“尚賢”,因?yàn)橹挥羞x拔出賢人,才能形成賢人政治,從而組成好人政府。韓非子部分采用了墨子尚同的政治主張,他贊同墨子的“下同乎上”,但墨子所說(shuō)的“上”,是以上天和鬼神為最高價(jià)值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于天。”[11]韓非子則拋棄了墨子尚同的前提“尊天”與“事鬼”,而以君主為最高價(jià)值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韓非子拋棄“尊天”與“事鬼”的宗教外衣之后,則由墨子的權(quán)威主義政治主張而走向君主專(zhuān)制和極權(quán)的政治主張,君主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不受上天與鬼神的約束,完全以君權(quán)取代了神權(quán);也拋棄了墨子尚同的前提“賢人政治與好人政府”,而只倡導(dǎo)權(quán)術(shù)勢(shì)。
(三)繼承荀子儒家思想中的重法思想
荀子主張“隆禮”與“重法”并用來(lái)治理天下。荀子曰:“故人無(wú)禮則不生,事無(wú)禮則不成,國(guó)家無(wú)禮則不寧。”[12]“法者,治之端也。”[13]“其耕者樂(lè)田,其戰(zhàn)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diào)議,是治國(guó)已。”[14]“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ài)民而霸。”[15]韓非子作為荀子的弟子,拋棄了荀子的“隆禮”主張而繼承了荀子的重法思想。
(四)吸取以往的法家學(xué)說(shuō)
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除了繼承并改造老子的道家學(xué)說(shuō)、墨子主張統(tǒng)一的思想和主張權(quán)威的學(xué)說(shuō),以及繼承荀子儒家思想中的重法思想之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來(lái)源是以往的法家學(xué)說(shuō),諸如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shù)治和慎到的勢(shì)治。
商鞅主張廢除禮治,實(shí)行法治,認(rèn)為法治是治國(guó)之本、強(qiáng)國(guó)之路。商鞅曰:“今有主而無(wú)法,其害與無(wú)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無(wú)法同。”[16]“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為治而去法令,猶欲無(wú)饑而去食也,欲無(wú)寒而去衣也,欲東而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17]“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tīng)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故國(guó)治而地廣,兵強(qiáng)而主尊。此治之至也。”[18]商鞅于公元前356 年被秦孝公任命為左庶長(zhǎng),實(shí)行第一次變法,并獲得極大的成功。公元前352 年,商鞅升遷為大良造。公元前350年,商鞅開(kāi)始第二次變法。兩次變法為秦國(guó)富國(guó)強(qiáng)兵乃至今后的統(tǒng)一六國(guó)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公元前351 年,韓昭侯破格拜申不害為相,于是申不害開(kāi)始變法改革。他推行法治,限制貴族特權(quán),加強(qiáng)君主專(zhuān)制,從而穩(wěn)定了政局,使國(guó)力逐漸強(qiáng)盛;他又實(shí)行術(shù)治,對(duì)官吏加強(qiáng)考核監(jiān)督,最終使韓國(guó)成為戰(zhàn)國(guó)七雄之一。司馬遷云:“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xué)術(shù)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nèi)修政教,外應(yīng)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guó)治兵強(qiáng),無(wú)侵韓者。申子之學(xué)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shū)二篇,號(hào)曰《申子》。”[19]
司馬遷云:“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huán)淵,楚人。皆學(xué)黃老道德之術(shù),因發(fā)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huán)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20]慎子在齊國(guó)稷下學(xué)宮講學(xué)多年,司馬遷云:“宣王喜文學(xué)游說(shuō)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huán)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xué)士復(fù)盛,且數(shù)百千人。”[21]慎到重“勢(shì)”。慎到曰:“故騰蛇游霧,飛龍乘云,云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于不肖者,權(quán)輕也;不肖而服于賢者,位尊也。堯?yàn)槠シ颍荒苁蛊溧徏遥恢聊厦娑酰瑒t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shì)位足以屈賢矣。”[22]慎到認(rèn)為,君主和權(quán)勢(shì)就像飛龍和云霧,飛龍憑借云霧而高飛,如果云霧散去,飛龍則不能騰飛,與地上的蚯蚓相同。即使是堯那樣圣明的人,他為匹夫時(shí),不能使喚其鄰家;他南面稱(chēng)王時(shí),則可令行禁止。由此可見(jiàn),對(duì)于君主來(lái)說(shuō),權(quán)勢(shì)是最為重要的。
商鞅在秦國(guó)實(shí)行變法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申不害在韓國(guó)實(shí)行術(shù)治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以及慎到的勢(shì)治學(xué)說(shuō)在齊國(guó)稷下學(xué)宮所擁有的巨大聲望,這些無(wú)疑對(duì)韓非子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韓非子博采眾家之長(zhǎng),尤其是將法、術(shù)、勢(shì)融為一爐而最終成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
二、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的基本理論
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的基本理論主要包含對(duì)法術(shù)勢(shì)的界說(shuō)、功用及其關(guān)系的闡釋等方面的內(nèi)容。
(一)法、術(shù)、勢(shì)的界說(shuō)及其功用
韓非子分別對(duì)法、術(shù)、勢(shì)作了界說(shuō),并分別闡述了其功用。
第一,關(guān)于法的界說(shuō)及其功用。韓非子曰: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shè)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23]
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24]
韓非子認(rèn)為,法就是編著成書(shū)而放置在公府里,并且向百姓公布的法令。法是治國(guó)的依據(jù)和綱領(lǐng)性文獻(xiàn)。因此,法制定之后,就應(yīng)該“布之于百姓”,教民學(xué)法懂法,“故明主之國(guó),無(wú)書(shū)簡(jiǎn)之文,以法為教;無(wú)先王之語(yǔ),以吏為師”[25],并用法來(lái)規(guī)范百姓的言行,“一民之軌,莫如法”[26],從而讓人們都學(xué)法、知法與守法;法制定之后,就必須保持相對(duì)穩(wěn)定性而不能屢次改變法令,“治大國(guó)而數(shù)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guó)者若烹小鮮。’”[27]“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wú)赦。譽(yù)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28]從而避免朝令夕改而民無(wú)所措手足的局面;法制定之后,就必須“以法為本”[29]。“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nèi),動(dòng)無(wú)非法。”[30]“故以法治國(guó),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zhēng)。刑過(guò)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31]從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防止有法不依的局面。法的重要內(nèi)容是“賞罰”,應(yīng)實(shí)行厚賞重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yù)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32];應(yīng)實(shí)行“信賞必罰”[33]。如此,就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法治體系。
韓非子認(rèn)為,法具有巨大的功用,國(guó)家是否強(qiáng)大,關(guān)鍵在于是否奉法。韓非子曰:
國(guó)無(wú)常強(qiáng),無(wú)常弱。奉法者強(qiáng)則國(guó)強(qiáng),奉法者弱則國(guó)弱。[34]
明法者強(qiáng),慢法者弱。[35]
君主是否尊貴,關(guān)鍵在于是否任法。韓非子曰:
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qiáng),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36]
夫凡國(guó)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yán)以重之。夫國(guó)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shí)。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shí)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wú)法也。[37]
即使是平庸的君主,只要實(shí)施法治,就能維持其統(tǒng)治。韓非子曰: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反)是(非)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以為言勢(shì)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shì)則治,背法去勢(shì)則亂。[38]
韓非子認(rèn)為,像堯舜和桀紂這樣的圣王和暴君,千世才出現(xiàn)一次;絕大多數(shù)的君主是上不及堯舜的圣明而下不及桀紂的殘暴。盡管如此,只要“抱法處勢(shì)則治”,否則“背法去勢(shì)則亂”。
第二,關(guān)于術(shù)的界說(shuō)及其功用。韓非子曰:
術(shù)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zé)實(shí),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zhí)也。[39]
故國(guó)者,君之車(chē)也;勢(shì)者,君之馬也。無(wú)術(shù)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shù)以御之,身處佚樂(lè)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40]
韓非子認(rèn)為,術(shù)是根據(jù)能力而授予官職,根據(jù)臣下所說(shuō)的能夠承當(dāng)某事而責(zé)求其實(shí)效,掌握生殺大權(quán),考核群臣能力的策略。術(shù)是君主任免、考核、賞罰官吏和駕馭群臣的深藏不露的策略,也是推行法治的手段。如果君主有勢(shì)而無(wú)術(shù),即使身體勞累,也難免遭受亂;如果有術(shù)來(lái)駕馭群臣,則既可使身體處于逸樂(lè)的境地,又可以獲得帝王之功業(yè)。由此可見(jiàn),術(shù)之功用大矣!韓非子認(rèn)為,術(shù)與法的運(yùn)用方式恰好相反。韓非子曰:
故法莫如顯,而術(shù)不欲見(jiàn)。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nèi)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dú)滿于堂;用術(shù),則親愛(ài)近習(xí)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于室,滿室;言于堂,滿堂。”非法術(shù)之言也。[41]
凡治之極,下不能得。[42]
術(shù)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43]
明主,其務(wù)在周密。是以喜見(jiàn)則德償,怒見(jiàn)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jiàn)。[44]
韓非子認(rèn)為,法律要顯明而使群臣吏民皆知之,術(shù)則深藏于胸中而不能外露,以參驗(yàn)各種現(xiàn)象,暗地里駕馭群臣;即使是所親愛(ài)的人和近臣都不能聞知。君主治理群臣的最高手段,就在于使臣子不能測(cè)知其心意。因此,明主的要?jiǎng)?wù)在于周密。君主現(xiàn)其喜于某人,則臣下以君此喜而施德于其人,其人則感此臣之恩德。君主現(xiàn)其怒于某人,則臣下以君此怒而逞威于其人,其人則畏懼此臣之威。因此,明主之言應(yīng)該阻塞于胸,并周密而不外露,應(yīng)該“去好去惡,群臣見(jiàn)素。群臣見(jiàn)素,則大君不蔽矣”[45]。
第三,關(guān)于勢(shì)的界說(shuō)及其功用。韓非子曰:
君執(zhí)柄以處勢(shì),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shì)者,勝眾之資也。[46]
夫有材而無(wú)勢(shì),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zhǎng)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shì)重也;堯?yàn)槠シ颍荒苷遥遣恍ひ玻槐耙病47]
夫勢(shì)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shū)》曰:“毋為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勢(shì),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tái)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shì)者,養(yǎng)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shì)之于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yǔ)專(zhuān)言勢(shì)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48]。……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shì)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shì)亂也。故曰:“勢(shì)治者,則不可亂;而勢(shì)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shì)也,非人之所得設(shè)也。[49]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nèi),海內(nèi)說(shuō)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guó),境內(nèi)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勢(shì),誠(chéng)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shì)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勢(shì)則哀公臣仲尼。[50]
韓非子認(rèn)為,勢(shì)就是君主的權(quán)勢(shì),就是政權(quán)。君主具有權(quán)勢(shì),掌握政權(quán),就能令行禁止,就掌握了對(duì)其臣民殺戮與慶賞的權(quán)力,勢(shì)是凌駕于眾人之上的憑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這并非他具有才能,而是其權(quán)勢(shì)重;堯?yàn)槠シ颍荒苷遥@并非他沒(méi)有才能,而是其地位卑賤。如果桀紂掌握了權(quán)勢(shì),即使有十位堯舜這樣的賢才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如果桀紂喪失了權(quán)勢(shì)而成為匹夫,即使有十個(gè)桀紂這樣的殘暴之人也不能亂天下;不但不能亂天下,他們還沒(méi)有開(kāi)始實(shí)施暴亂就已遭受刑戮了。孔子之賢遠(yuǎn)甚于魯哀公,然而魯哀公掌握了君主的權(quán)勢(shì),因此境內(nèi)之民莫敢不臣服于魯哀公,孔子也不能不臣服于魯哀公。魯國(guó)之民與孔子都是臣服于魯哀公的權(quán)勢(shì)。由此可見(jiàn),無(wú)論是暴君還是明君,有了權(quán)勢(shì),就能制服其臣民;而臣民就不得不臣服于其君主。因此,韓非子強(qiáng)調(diào):“凡明主之治國(guó)也,任其勢(shì)。勢(shì)不可害,則雖強(qiáng)天下無(wú)奈何也。”[51]“善任勢(shì)者國(guó)安,不知因其勢(shì)者國(guó)危。”[52]
(二)法、術(shù)、勢(shì)之間的關(guān)系
韓非子分別對(duì)法與術(shù)、法與勢(shì)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闡釋。
第一,關(guān)于法與術(shù)的關(guān)系。韓非子曰:
問(wèn)者曰:“徒術(shù)而無(wú)法,徒法而無(wú)術(shù),其不可何哉?”對(duì)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guó)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shù),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托萬(wàn)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雖用術(shù)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shè)告坐而責(zé)其實(shí),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guó)富而兵強(qiáng)。然而無(wú)術(shù)以知奸,則以其富強(qiáng)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yīng)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lái),諸用秦者,皆應(yīng)、穰之類(lèi)也。故戰(zhàn)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wú)術(shù)以知奸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qiáng)秦之資,數(shù)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雖勤飾于官,主無(wú)術(shù)于上之患也。”[53]
問(wèn)者曰:“主用申子之術(shù),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duì)曰:“申子未盡于術(shù),商君未盡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雖知弗言’。治不逾官,謂之守職也;知而弗言,是不謂過(guò)也。人主以一國(guó)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guó)耳聽(tīng),故聽(tīng)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dāng)匾皇渍呔粢患?jí),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jí),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chēng)也。今有法曰:‘?dāng)厥渍吡顬獒t(y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y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dāng)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yī)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術(shù),皆未盡善也。”[54]
韓非子認(rèn)為,“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shù)也”[55]。然而申不害“徒術(shù)而無(wú)法”,“故托萬(wàn)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雖用術(shù)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56]。公孫鞅則“徒法而無(wú)術(shù)”,“公孫鞅之治秦也,設(shè)告相坐而責(zé)其實(shí),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guó)富而兵強(qiáng);然而無(wú)術(shù)以知奸,則以其富強(qiáng)也資人臣而已矣”[57]。由此可見(jiàn),“君無(wú)術(shù)則弊于上,臣無(wú)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wú),皆帝王之具也”[58]。韓非子認(rèn)為,法必須公之于眾,術(shù)則應(yīng)深藏不露。術(shù)與法可謂“一顯一藏”而形成治國(guó)之道。
第二,關(guān)于法與勢(shì)的關(guān)系。韓非子曰:
抱法處勢(shì)則治,背法去勢(shì)則亂。今廢勢(shì)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shì)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59]
夫國(guó)之所以強(qiáng)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quán)也。故明君有權(quán)有政,亂君亦有權(quán)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quán)而上重,一政而國(guó)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ài)之自也。[60]
韓非子認(rèn)為,像堯舜那樣的圣君和桀紂那樣的暴君,千世才出現(xiàn)一次,絕大多數(shù)的君主則是“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的中等之君,這就需要憑借法和勢(shì)來(lái)治理天下。國(guó)家之所以強(qiáng)大,是憑借對(duì)政事的治理。這種治理主要體現(xiàn)在法治方面,即韓非子所謂“故治民無(wú)常,唯治為法。法與時(shí)轉(zhuǎn)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61]。人君之所以尊貴,是憑借權(quán)勢(shì)。無(wú)論是明君還是亂君,皆有權(quán)有政,然而明君聚權(quán)勢(shì)于己身,亂君則散權(quán)勢(shì)于臣下。這是明君與亂君的區(qū)別所在,即“積而不同”。明君治政以法治,亂君治政以心治。這是明君與亂君的區(qū)別所在,即“其所以立異也”。因此,明君掌握權(quán)勢(shì)則貴重,統(tǒng)一法令則國(guó)治。因此說(shuō),法是王者之本,而刑是愛(ài)人之始。
綜上所述,雖然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對(duì)韓非子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韓非子認(rèn)為他們的思想皆有偏頗之處: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皆偏執(zhí)于一端,而沒(méi)有將法、術(shù)、勢(shì)三者密切結(jié)合起來(lái)。韓非子認(rèn)為,法是治國(guó)的綱領(lǐng),是強(qiáng)國(guó)之本;術(shù)是君主任免、考核、賞罰官吏和駕馭群臣的深藏不露的策略,是推行法治的手段;“勢(shì)”是君主的權(quán)勢(shì)和政權(quán),是推行法治和術(shù)治的憑借。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就形成了韓非子將法、術(shù)、勢(shì)融為一爐的法家理論,從而使得法家理論臻于完善,并且達(dá)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法術(shù)勢(shì)”就成了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即他所主張的一種治國(guó)之道:君主依據(jù)法令、使用權(quán)術(shù)、憑借權(quán)勢(shì)來(lái)治理國(guó)家。
韓非子提出法術(shù)勢(shì)思想,是想為君主治理國(guó)家提供一種御臣之道,為君王統(tǒng)一天下提供理論指導(dǎo)。事實(shí)也是如此: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為秦王嬴政統(tǒng)一六國(guó)提供了理論指導(dǎo)。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最終沒(méi)有選擇儒家所倡導(dǎo)的以仁義治天下的王道,而是選擇了法家韓非子所倡導(dǎo)的憑借武力、法術(shù)勢(shì)等進(jìn)行統(tǒng)治的霸道,秦王嬴政完成了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當(dāng)然,韓非子法術(shù)勢(shì)思想亦有其巨大的弊端,這就是不施仁義而專(zhuān)任嚴(yán)刑峻法。這既是秦王嬴政得天下的重要原因,也是秦王朝失天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