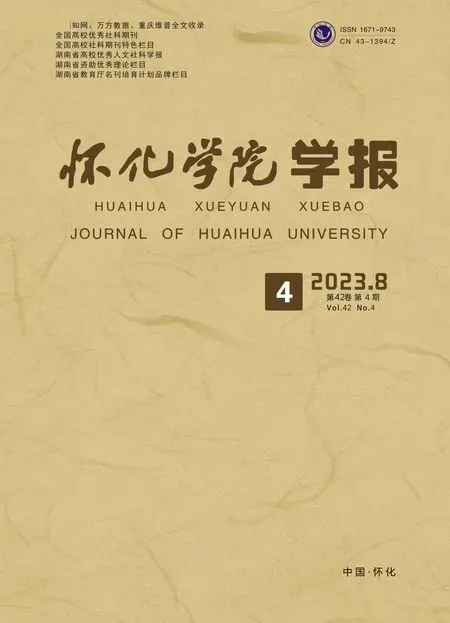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初探
辛時代, 丁祉涵
(渤海大學,遼寧 錦州 121000)
唐朝中央事務機構主要由三省、九寺和五監組成。渤海國在仿照唐朝中央事務機構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中央事務機構。①關于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研究,著名歷史學家金毓黻將其置于渤海國通史的視野中進行探討,通過對照唐代文獻,推理出渤海國統治機構的設置和職掌。此后的研究基本是在金氏提出的分析框架下進行展開與闡述。[1]如果將相關研究持續深入下去,可以發現渤海國在借鑒唐朝中央事務機構的過程中相關建制級別的變化,中央事務機構長官地位的變化等等,這些問題中外學者措意甚少,沒有進行過系統地闡述。
本文以唐朝制度為參照,對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加以梳理,揭示唐朝與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演變的內在紋理,深化對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的有關認識。
一、中央事務機構的概況
《新唐書·渤海傳》記載了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的大致情況:
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2]
據此,可將唐朝與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對照:
三省:
文籍院—秘書省;巷伯局—內侍省;
殿中寺—殿中省;
九寺:
太常寺—太常寺;司膳寺—光祿寺;
宗屬寺—宗正寺;司賓寺—鴻臚寺;
大農寺—司農寺;司藏寺—太府寺;
—衛尉寺;—太仆寺;
—大理寺;
五監:
胄子監—國子監;—少府監;
—將作監;—軍器監;
—都水監;
上述比對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誤解: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并不像唐朝中央事務機構那樣職能完備、功能齊全。有些學者據此認為,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只有一院、一局、一監、七寺。然而,這只是《新唐書·渤海傳》給我們造成的刻板印象。實際上,我們根據《南唐書》的記載,可以訂正《新唐書·渤海傳》的不足。
《南唐書》載,烈祖昇元二年(938)六月,遼太宗耶律德光使梅里捺盧古、“東丹王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3]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東丹國采用的是渤海國舊制,兵器寺是沿用渤海國時期的事務機構。這個例子也說明,《新唐書·渤海傳》所載的中央事務機構并不完整。
綜合來看,唐朝中央事務機構中的“三省”都能在渤海國找到對應的機構,“九寺”能在渤海國找到七個對應的機構,基本上能夠落實,“五監”中除了胄子監,其余機構語焉不詳,這很有可能是由文獻闕載造成的,按說應當還有如“兵器寺”等其他的事務機構存在。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完全有可能沿用了唐朝以三省、九寺和五監為核心的中央事務機構的框架設置。
唐朝中央事務機構中的“三省”下設“局”:
第一,秘書省下轄著作局和太史局。其中,著作局設有郎二人,佐郎四人,太史局設令二人,丞二人;
第二,內侍省下轄內謁者、掖庭局、宮闈局、奚官局、內仆局和內府局。其中,內謁者設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掖庭局設令二人,丞三人,宮闈、奚官、內仆、內府四局各設令二人,丞二人;
第三,殿中省下轄尚食局、尚藥局、尚主局、尚舍局、尚乘局和尚輦局。各局設有奉御二人,直長四人。
從官署名號看,渤海國在借鑒唐朝制度的過程中,繼續沿用唐朝中央事務機中的“寺”“監”,而不使用“省”。究其原因,省寺是中國古代中央官署泛稱,不過也有“官司之別”。[4]清代學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解釋道:“省者,察也。察者,覈也。漢禁中謂之省中。師古曰:‘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漢書》注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廣韻》:‘寺者,司也,官之所止有九寺。’”[5]也就是說,“寺”為國家官方機構,“省”是皇家機構,事關皇權的威嚴。渤海國作為唐朝的羈縻府州,其中央事務機構不再沿用“省”號,是為了杜絕逾制之嫌,于是設置文籍院,以比唐朝秘書省;設置巷伯局,以比唐朝內侍省;又設置殿中寺,以比唐朝殿中省。與唐朝制度橫向比較,可以發現文籍院長官仍然是卿,下設有述作局,較唐朝秘書省的建制級別沒有變化;巷伯局建制級別相當于唐朝內侍省下設機構——局,地位明顯下降;殿中寺較唐朝殿中省,機構性質和服務對象都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唐朝中央事務機構諸寺的長貳官為卿、少卿,太常卿官為正三品,地位最高,其余諸卿為從三品;“寺”下設“署”,署的正副職為令、丞。比如:太府寺下設兩京諸市署、平準署、左藏署、右藏署、常平署。其中,兩京諸市署各置有令一人,丞二人;平準署置有令二人,丞四人;左藏署置有令三人,丞五人;右藏署置有令二人,丞三人;常平署置有令一人,丞二人。再比如,鴻臚寺下設典客署和司儀署,其中,典客署置有令一人,丞二人;司儀署置有令一人,丞一人。
另外,渤海國諸寺長貳官有“卿—少卿”、“大令—少令”和“令—丞”三種模式,三種模式又有地位高低之分。從名稱上分析,可以確定“大令—少令”的地位高于“令—丞”。結合上文所舉唐代太府寺和鴻臚寺的例子,渤海國“大令”很可能相當于唐代諸寺一令署的正職,“少令”相當于唐代諸寺一令署的副職;“令”相當于唐代諸寺多令署的正職,“丞”相當于唐代諸寺多令署的副職。“卿—少卿”的地位高于“大令—少令”。以司賓寺為例,其長官為卿,次官為少卿,司賓署作為其下設機構,正職為司賓大令,副職為司賓少令。魏國忠將司賓卿等同于司賓大令、司賓少卿等同于司賓少令[6],這種說法有待進一步商榷。從唐朝鴻臚寺看,卿—少卿是主管機構的長貳官,令—丞是從屬機構的正副職。由此可以推導出,在渤海國司賓寺中“卿”與“大令”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可以推出渤海國諸寺分為三個層次:長貳官為“卿—少卿”的太常寺、司賓寺與大農寺為第一層次,長貳官為“大令—少令”的兵器寺、殿中寺與宗屬寺為第二層次,長貳官為“令—丞”的司藏寺與司膳寺為第三層次。與唐朝制度橫向比較,可以大致確定第一層次與唐朝諸寺相當,說明其職能部門在渤海國比較受重視,在諸寺內部地位比較高;第二層次與唐朝諸寺下設機構——一令署相當;第三層次與唐朝諸寺下設機構——多令署相當,在諸寺內部地位比較低。
二、中央事務機構的職能
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我們以唐朝中央事務機構為參照,對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的設置與職掌加以考察。
(一)一院、一局和一寺
渤海國出于遵奉禮制的考慮,借鑒唐朝中央事務機構的“三省”,設置了文籍院、巷伯局和殿中寺。
文籍院:相當于唐朝的秘書省,主管“經籍圖書之事”。渤海國雖然改“省”為“院”,但是長官的稱呼并沒有變。文籍院長官為監,相當于唐朝秘書監;次官為少監,相當于唐朝秘書少監。
唐朝秘書省下轄兩個機構,一是分管“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的著作局,著作局正職為著作郎;一是分管“觀察天文,稽定歷數”的太史局。太史局正職為令,還設有司歷、天文生等。
見于文獻記載的渤海國文籍院屬官有少監裴颋、王龜謀和裴璆,《日本三代實錄》卷四十三陽成天皇元慶七年五月三日條載:日本陽成天皇“授(渤海國)大使、文籍院少監、正四品、賜紫金魚袋裴颋從三位”[7]。《本朝文粹》卷十二收錄的《贈渤海國中臺省牒》中有“(渤海國)入覲使、文籍院少監王龜謀”[8]。《日本紀略》后篇日本醍醐天皇延喜八年四月八日條載:醍醐天皇延喜八年(908),“存問渤海領客使、大內記藤原博文等,問(渤海國)入覲使、文籍院少監裴璆”[9]。又有文籍院述作郎李承英的記載,如《類聚國史》載,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十一月,渤海國“遣文籍院、述作郎李承英賚啟入覲,兼令申謝”[10]。述作郎相當于唐朝著作局的著作郎。通過《貞惠公主墓志》與《貞孝公主墓志》比較,可以發現兩個墓志銘有大量的用語完全相同,說明這兩個墓志并非出自個人手筆,而是按照官方規定的墓志程式套出來的,而主管官方墓志修撰之事當為述作局。
另外,在渤海國對日朝聘活動中活躍著天文生的身影。比如,日本清和天皇貞觀十四年(872)五月,日本國“授(渤海國)大使楊成規從三位,副使李興晟從四位下,……品官以下并首領等授位各有等級。及天文生以上,隨位階各賜朝服”[11]。《延喜式·主稅上》載:“凡渤海客食法,大使、副使日稻各五束,判官、錄事各四束,史生、譯語、天文生各三束五把,首領、梢工各二束五把。”[12]天文生在使團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他們主要負責占候天象,為使團出海提供備選信息。清和天皇貞觀元年(859),“渤海國大使烏孝慎新貢《長慶宣明歷經》言:是大唐新用經也。真野麻呂試加覆勘,……請停舊用新。”[13]從“新貢”的用詞看,進獻《長慶宣明歷經》是渤海國官方的行為,之前,其無疑已在渤海國印發、頒行。與此相應的是,《長慶宣明歷經》的印發、頒行以及后期的稽測星度、勘驗昝影,都需要專門的機構和專業人員去執行。由此可以推測,文籍院之下也應存在著分管“觀察天文,稽定歷數”,類似于唐朝太史局的機構。由于文獻有限,這個機構名稱無法考證。
巷伯局:承擔了唐朝內侍省的主要職能,主管“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制令”[14]。“巷伯”一詞,典出《詩經·巷伯篇》:“陳曰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寺人被宮刑者,蓋因讒而被刑也。”[15]巷伯局長官為常侍,建制級別與唐朝內侍省下設機構——局相當。
殿中寺:承擔了唐朝殿中省的主要職能,主管國家“乘輿服御之政令”[16],殿中寺長官為大令,次官為少令。
(二)七寺
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同樣沿用唐朝“九寺”的框架,目前文獻可考的有太常寺、大農寺、司賓寺、宗屬寺、兵器寺、司藏寺和司膳寺。
太常寺:與唐朝太常寺的同名機構。主管“禮樂、郊廟、社稷之事”[17]。太常寺長官為卿,相當于唐朝太常卿。
大農寺:相當于唐朝的司農寺,主管“倉儲委積之事”[18]。大農寺長官為卿,相當于唐朝司農卿。
司賓寺:相當于唐朝的鴻臚寺,主管“賓客”“兇儀”之事[19]。司賓寺長官為卿,相當于唐朝鴻臚卿;次官為少卿,相當于唐朝鴻臚少卿。
唐朝的鴻臚寺下轄兩個機構:一是分管“賓客”之事的典客署,典客署正職為令,副職為丞。一是分管“兇儀”之事的司儀署,司儀署正職為令,副職為丞,正九品下。[20]
渤海國的司賓寺,文獻記載其屬官有司賓卿賀守謙,《張建章墓志》載:“渤海國王大彝震遣司賓卿賀守謙來聘。”[21]又有司賓少令史都蒙、張仙壽,《續日本紀》載:光仁天皇寶龜八年(777),日本“授渤海大使、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正三位”[22]。又載:光仁天皇寶龜十年(779),“天皇御太極殿,受朝。渤海國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張仙壽等朝賀,其儀如常”[23]。
聘日使節中史都蒙官居“司賓少令”,魏國忠由此推定司賓卿又稱司賓大令,司賓少卿又稱司賓少令。[24]對此觀點筆者不能茍同,由司賓少令可以推導出其正職為司賓大令,既然司賓寺的長官為司賓卿,那么司賓大令、司賓少令就不是司賓寺的長官、次官,而是司賓寺的下屬機構——司賓署的正職、副職。如果推測能成立,司賓少令便相當于唐朝典客署中的典客丞。從史都蒙、張仙壽銜命出使看,司賓署分管的是司賓寺所掌的“賓客”之事。“兇儀”之事當由司賓寺的另外一個下轄機構分管,《貞孝公主墓志》載:“喪事之儀,命官備矣”[25]也證明分管“兇儀”的官方機構在渤海國歷史上確實存在。由于文獻有限,這個機構名稱無法確證。
宗屬寺:承擔了唐朝宗正寺的主要職能,主管“皇九族、六親屬籍”之事[26],宗屬寺長官為大令,次官為少令。
兵器寺:相當于唐朝的衛尉寺,主管“器械、文物之政令”[27]。兵器寺長官當為大令,次官為少令。
又有“兵署”的名稱,《續日本紀》記載,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758),“渤海大使、輔國大將軍兼將軍、行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開國公楊承慶已下廿三人,隨田守來朝,便于越前國安置”[28]。
唐朝的衛尉寺下轄3 個機構:一是分管“藏兵械”的武庫;一是分管“在外戎器”的武器署;一是分管“供帳之屬”的守宮署。[29]日本學者鳥山喜一考證,兵署是渤海國兵器寺的下設機構之一,相當于唐朝衛尉寺中的武器署。[30]由兵署少正可以推導出其正職為兵署正。
司藏寺:承擔了唐朝太府寺的主要職能,主管“財貨、廩藏、貿易”之事[31]。韓國學者金東佑認為,渤海國司藏寺相當于唐朝尚書省二十四之一的太府司[32]。金氏可能將尚書省戶部的倉司和中央事務機構的太府寺混淆。司藏寺的長官為令,次官為丞,建制級別與唐朝太府寺下設機構——多令署相當。
司膳寺:承擔了唐朝光祿寺的主要職能,主管“酒醴膳羞之事”[33]。司膳寺長官為令,次官為丞,建制級別與唐朝光祿寺下設機構——多令署相當。王成國認為,司膳寺主管王室后宮用膳之事,但沒有指出與唐朝的對應機構[34]。這種理解很可能是立足于“司膳寺”的字面意思。司膳寺的職掌范圍恐怕比王成國的理解更大,所提供的膳食未必局限于王室與后宮人員。根據《唐六典》與《新唐書·百官志》載,唐朝光祿寺下轄太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具體涉及“供祠宴朝會膳食”“供祭祀、朝會、賓舍之庶羞”“供(祭祀)五齊、三酒”“供醢醯之物”[35]。所以,光祿寺的職掌可能與渤海國司膳寺更為接近。
(三)一監
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也沿用了唐朝“五監”的框架,目前可考的僅有胄子監。
胄子監:相當于唐朝的國子監,主管“儒學訓導之政”[36]。“胄子”一詞,典出《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顏師古注:‘胄子即國子也。’”[37]胄子監長官為監長,相當于唐朝國子監祭酒,次官為少監,相當于唐朝國子監司業。清代張賁的《東京記》載:“土人掘地得斷碑,有‘下瞰臺城儒生盛于東觀’十字,皆漢字,字畫莊楷,蓋國學碑也。”[38]從斷碑的文字可以想見渤海國文學之盛。
三、渤海國與唐朝政治制度的淵源
對渤海國與唐朝的政治制度淵源,中外學界常引的史料是“大抵憲象中國制度”[39]。那么,渤海國政治制度多大程度上借鑒了唐朝政治制度呢?朝鮮學者張國鐘認為,渤海國地處原來高句麗的版圖,而且又是由高句麗遺民建立的國家,所以其政治制度也必然繼承高句麗的政治制度,而不是過多地效仿唐朝。[40]這種觀點顯然經不起推敲。
以中央事務機構為例,渤海國大體上沿用了唐朝中央事務機構“三省、九寺和五監”的框架,但是在一些細節上有所調整。
從機構名稱上看,渤海國根據唐朝制度和職能重新對中央事務機構進行命名,但是命名原則有跡可循,基本采用與唐朝中央事務機構名稱相同、相近或相關的詞語。通過比照,很容易找到兩者之間的對應關系。
從官署名號上看,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有“寺”“監”,一如唐朝制度。同時,渤海國以“院”“局”和“寺”對應唐朝中央事務機構的“三省”,反映了遵守中原禮制的精神。不過,“院”“局”并非渤海國的制度創新,而是來自于唐朝中央事務機構的、“三省”的下設機構。
根據長貳官模式,渤海國諸寺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長貳官為“卿—少卿”的諸寺為第一層次,在諸寺中地位最高;長貳官為“大令—少令”的諸寺為第二層次;長貳官為“令—丞”的諸寺為第三層次,在諸寺中地位最低。與唐朝制度橫向比較,第一層次相當于唐朝諸寺,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分別相當于唐朝諸寺下設機構的一令署和多令署。
渤海國以唐朝制度為藍本,建立起自己的中央事務機構,經過不斷地調整,逐漸走向規范。這種制度調整,基本都在唐朝制度的框架中進行,根據渤海國的統治需要和中原禮制展開,而與高句麗政治制度沒有什么瓜葛。
縱觀整個渤海國的歷史,日本學者鳥山喜一用月亮反射太陽的光輝,來比喻渤海與唐的制度淵源[41]。渤海國正是向唐朝制度不斷學習、推行唐朝制度來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和困境,由此開啟了“海東盛國”的輝煌。由于缺乏自身再生的文化基礎,渤海國政治制度變革缺少內在動力,始終沒有擺脫唐朝制度的歷史慣性。隨著唐朝的衰亡,渤海國末期的發展失去了制度參照系,社會危機、與外族交侵疊加成國家崩潰之前的斜陽晚照。
注釋:
①結合唐朝制度來審視,渤海國中央事務機構與政堂省六部十二司應該在職能上也有交叉,但是側重點各不相同。前者是具體辦理所屬的事務,后者從制令角度統領全國行政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