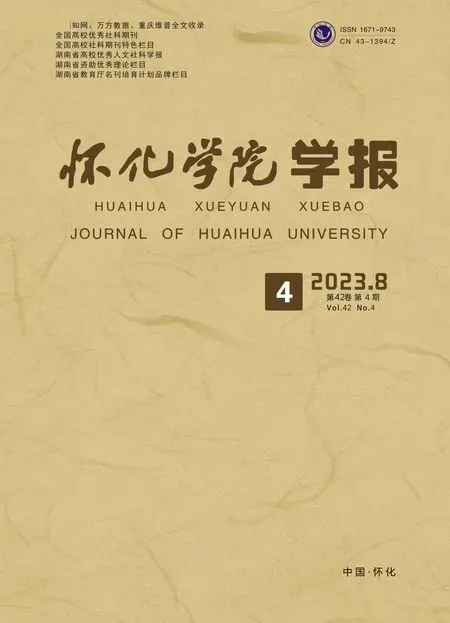本土生態知識的內涵與價值探析
農仁富, 楊庭碩
(1.南寧市博物館,廣西 南寧 530219; 2.吉首大學,湖南 吉首 416000)
本土性知識是20 世紀后期學界才提出并普遍接納的學術性概念,其內涵極為豐富。在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的今天,本土性知識中必然包含著的生態知識日益引起學界同仁的關注,并展開了熱烈了探討,成果豐碩,逐步形成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但為何要深入探討傳統的本土生態知識,時至今日人們還存在著諸多認識上的分歧和差異,并直接影響到這一術語的準確運用。為此,本文圍繞這一概念的內涵展開進一步的探討和澄清,希望對當代的生態文明建設發揮促進作用。
一、本土生態知識的內涵
20 世紀后半葉的西方國家學術界出現了一個具有很大影響的社會文化思潮,即后現代主義思潮,這一思潮給傳統的學術觀念構成了重大沖擊。“地方性知識”正是這種學術觀念變革的派生產物和重要方面。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的觀念雖然早在古希臘哲人的思想中就已經被多次提及過,但明確提出這一概念并展開系統論證的代表人物,則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他贊同馬克斯·韋伯提出的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的觀點,于是,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1]。因此,文化概念實質上是一個符號學概念。“文化模式是歷史地創立的有意義的系統,據此我們將形式、秩序、意義、方向賦予我們的生活。”[2]在不同民族和地區中客觀上存在著不容忽視的文化差異,這是因為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對其所處世界的不同理解的產物,文化的各種符號之間的關系取決于該文化中行為者的行為組織方式。因而文化模式并非普遍性規則,而是具有多樣性的特殊意義系統,并由此構成了所謂的地方性知識,一種具有地域文化特質的知識形態及構成方式即一種具有地域文化特質,并具有特定時空場域的知識形態及構成方式[3]。
地方性知識這一學術概念與普同性知識相對應。“廣義地講,地方性知識是一定地域的人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體力和腦力勞動創造并不斷積淀、發展和升華的物質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和成就,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反映了當地的經濟水平、科技成就、價值觀念、宗教信仰、文化修養、藝術水平、社會風俗、生活方式、社會行為準則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狹義的地方性知識專指地方的精神文化。作為一種經過長期創造、積淀和傳承的寶貴精神財富,地方性知識有其鮮明的地域特色、獨特的價值體系和豐富的內涵,生存其間的每一個個體總是天然地與本地域的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4]
王鑒和安富海認為“地方性知識最初只是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學術概念而存在,但目前它的重要性已遠遠超出了文化人類學的范疇。在許多學者看來,‘地方’是以祖先領地和共同文化為核心內涵的,這就把地方性知識的概念植入了‘地方’復雜的歷史和文化多樣性背景之中,以至于難以做出簡單的界定”[5]。陳來認為“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文化乃是人們適應環境的產物,不同的地域共同體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下造就了自己的文化,從而造成了文化的地域性差異。地方性知識意味著一地方所獨享的知識文化體系,是此地人民在自己長期的生活和發展過程中所自主生產、享用和傳遞的知識體系,與此地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及其歷史密不可分”[6]。
目前,“學術界主要從肯定地方性知識的實踐價值出發,力圖在政治層面上去理解和把握地方性知識的內涵。然而,這種理解方式不可避免地淡化了地方性知識的權力維度,掩蓋了地方性知識的歷史負荷”[5]。在生態人類學界,為了避免這一提法隱含著的歧視意味,楊庭碩將其定義為“本土知識”,即“特定民族針對特定地區的自然與社會背景,通過世代積累而建構起來的知識體系。這樣的知識體系服務于特定的民族和地區,具有明顯的民族歸屬性和地緣性”[7]。而作為本土知識一部分的本土生態知識,則是“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社群對所處自然與生態系統做出文化適應的知識總匯,是相關民族和社群在世代積累上健全起來的知識體系。這樣的知識體系總是間接或直接地與該民族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系統相關聯,擔負著引導該民族成員生態行為的重任,使他們在正確利用自然與生物資源的同時,又能精心維護所處生態系統安全”[8]。這樣的研究取向與我們今天正在從事的生態文明建設,明顯存在著認識和理解上的高度一致和實踐應用價值。
“本土知識”強調的就是所有知識的平等與特性,反對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歐洲文化中心主義。本土生態知識認為任何一種地方性知識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和優勢,對人類自身發展的認識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也許很難被異種文化的人們所理解和接受,但它卻有自身存在的價值和含義。作為知識觀念和認知模式的地方性知識而言,它決不僅僅只是一種批判性的知識觀念和話語武器,其實踐性與建設性才是它最有價值的特性所在[9]。作為一個人類學者,想要研究某一民族或地區的地方性知識,必須秉持寬容、接納、適應的文化相對主義的原則,因為這是決定其能否承認并客觀研究地方性知識的基本條件。
由此可見,“地方性知識的確對于傳統的一元化知識觀和科學觀具有潛在的解構和顛覆作用。過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證明的‘公理’,現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強加在豐富多樣的地方性現實之上,就難免有‘虛妄’的嫌疑了”[10]。地方性知識的存在是多元化的,是與特定民族所處的自然生境和社會生境相對應的,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用簡單的因果模式去處理。這樣看來格爾茲對本土知識的理解可拓展到我們跨文化的研究當中。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是多樣性的統一體,只強調本文化的優越,或者為保持本文化的純潔而拒絕與他文化進行交流,就可能發展成為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孤立主義。符合當前時代潮流的本土生態知識觀,才可望得以徹底的澄清,并在這樣的觀念轉型中能夠對那些從表面上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議的、形形色色的各民族、各地區的本土生態知識,保有進一步認知的激情,從而才有望公平理性地去認識和接納他們,并為此展開深入的研究。客觀存在著的本土生態知識在當代的傳承弘揚和高效創新利用,也才能落到實處。
二、本土生態知識的價值
鑒于本土生態知識是眾多經驗、技術、技能的復合存在,其中還不缺乏理性總結出來的生態哲理和生態智慧,內部構成極其錯綜復雜,因而在當代傳承弘揚和創新利用時,不僅僅需要系統的把握具體的操作方法,還需要輔以當代科學知識和理論的驗證,更需要向世人揭示本土生態知識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為此對本土生態知識的當代價值就其實踐應用而言,展開分門別類的討論,實屬必不可少。
(一)生態維護價值
一切本土生態知識都是特定民族文化在世代調適與積累中發育起來的生態智慧與生態技能,都系統地包容在特定族群的文化之中,本土性生態知識的本質在于對生態環境的高效利用與精心維護[11]。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土生態知識必然與所在地區的生態系統互為依存,互為補充,相互滲透。相比之下,普同性知識則不可能具備如此精準的針對性。“若能憑借生態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系統發掘和利用相關地區的地方性知識,一定可以找到對付生態環境惡化的最佳辦法。如果忽視或者在無意中丟失任何一種本土性知識,都意味著損失一大筆不可替代的精神財富。”[12]發掘和利用一種地方性知識,去維護所處地區的生態環境,是所有維護辦法中成本最低廉的手段,因為本土知識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與當地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當事的個人在其日常活動中,幾乎是在下意識的狀況中貫徹了地方性知識的行為準則,地方性知識中的生態智慧與技能在付諸應用的過程中,不必借助任何外力推動,就能持續地發揮作用。”[13]
我國少數民族多具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生態平衡的觀念與認知,在生態制衡上有許多有效的鄉土措施。如居住在滇南地區的彝族撒尼人,每年農歷十一月都要隆重舉行為期七天的“祭密枝”儀式,又叫密枝節。“祭密枝”儀式的祭祀對象為密枝林,幾乎每個撒尼村寨都有自己的密枝林,撒尼人認為密枝林里住著“密枝神”密枝斯瑪,是撒尼村寨的守護神。因此“密枝林”在撒尼人心中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密枝林中進行破壞活動,并且每年還要舉辦盛大的祭祀儀式,以獲得密枝斯瑪的保佑。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生態理念和行為規則,只要是在撒尼人的生息區,一定能夠看到屬于他們的茂盛的密枝林,這幾乎是在傳統文化的延伸中建構起了與當代生態保護區功能與效用完全重合的生態維護行動。而使密枝林發揮生態保護區功能時,相關部門乃至社會組織,根本無需投入任何意義上的人力、物力、財力代價。這一切都可以在撒尼人傳統文化的正常運行中,做得十全十美。由此看來,本土生態知識用于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和維護,顯然是一種最經濟、最節約的路徑和手段,而且實施的成效比當下由國家和地方政府經管的自然保護區,其保護成效更為理想。
在羌族地區的自然宗教信仰中,杉樹、白石與柏枝都是他們心目中的圣物,當地人不僅對這三種自然物的崇拜和保護有加,而且在生產和生活中都嚴密地監控這三種自然物的樣態,確保它們不受任何人類活動的干擾,以期它們能夠按照原樣超長期的穩定存在[14]。這樣的崇拜同樣事出有因,杉樹、白石與柏枝是其生息地帶自然生態災變的警示標志。羌族的生息地,位于青藏高原的東緣,海拔都在3000 米上下。加之,這里是地質結構極不穩定的地震帶,海拔的相對差又極大,高山峽谷所在皆是。即令沒有受到人類的干預,冰川、地震與地表徑流都可能造成大面積的滑坡和山崩。在如此嚴酷的生存背景下,山體植被的超長期穩定,關系著羌族人們的日常生活。以至于在他們的心目中,這三種自然物的穩定存在和匹配,是他們得以安居樂業的基本保障。正是因為羌族民眾將生息地自然結構的穩定視為人類社會得以穩定延續的首要前提,于是在他們對這些自然物崇拜之余,不僅其自身不敢輕易觸動這些脆弱性的自然物,而且也會阻止其他民族民眾的接近。這樣的保護活動持之以恒,就必然可以坐收穩定當地脆弱地質結構的保護成果。在這個問題上,看似不合理的自然崇拜,卻在無意中避免了當地自然環境脆弱環節的失效。即使到了今天,這樣的自然崇拜對提醒生態保護的專家和執行者,意識到當地自然生態保護的要害就在于確保地表的穩定,還可以發揮直接的警示作用。
在唐代,南方少數民族曾利用蟻來除蛀養柑[15]。具體做法是,他們一旦發現黑螞蟻蛀食柑橘樹,就會起用相關的防治技術,做出有效的控制。這是因為柑橘樹被黑螞蟻蛀食后,在柑橘樹的樹干上都會留下蛀洞,洞口還會留下它們的排泄物,柑橘樹的樹葉漸漸地也會變黃。只需要找準黑螞蟻出洞飲水留下的痕跡,那就可以在野外尋找黃螞蟻的洞穴,找到后將蟻巢搬運到受害柑橘樹的附近,黑螞蟻出洞必經之路旁,讓黃螞蟻在這里安家落戶,那么黃螞蟻就會主動地攻擊黑螞蟻。黑螞蟻群受到這樣的入侵干擾后,就會自然地遷往他處,否則將會導致整個蟻群全軍覆沒。
各族鄉民之所以能夠找到這些本土生態知識的獨特技術和技能,顯然是通過長期觀察后,不斷試錯,最終總結出來的經驗和可行的防蟲除害的特種知識。這樣的知識雖然看上去不起眼,卻符合當代生態學和植物保護技術的科學原理。而且其技術操作簡便,一看便會,收效明顯且穩定,經得起當代科學意義上的反復驗證,并不缺乏科學性、合理性與實用性。
(二)農業經濟價值
本土生態知識是當地人思想觀念和實踐的復合體,它通過經驗代代相傳,在發展的過程中并不封閉自守,也會發展和吸納新的知識、技術和技能。我們不能把本土生態知識簡單地看成普同性知識的對立面,它實際上不僅包括文化,也包括當地的政治、科技和社會實踐的生產和生活,特別是與當地的農林牧各業的生產息息相關[16]。因此相關部門在規劃農業生產發展時,特別是在選定產業項目時,啟動時就應對本土生態知識和技術給予更多的關注。
眾所周知,馬鈴薯和玉米都是原產于拉丁美洲的農作物品種,但這兩種農作物在川西彝族地區引種的效果卻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玉米為高稈作物,植被郁閉度較低,而馬鈴薯匍匐生長,植被郁閉度較高,因此種植馬鈴薯不會像玉米那樣容易引起水土流失;其二,馬鈴薯比玉米更耐寒,生長季更短,與彝族的傳統農作物圓根和芋頭具有很好的兼容能力,套用傳統的糞種技術,種植馬鈴薯,容易獲得高產和穩產。在這一馴化種植馬鈴薯的歷史過程中,不管是國家還是地方官員,都僅僅是一般性的建議或倡導,各族鄉民可以試種馬鈴薯。反倒是鄉民套用傳統的圓根和芋頭的種植方法,種馬鈴薯意外地取得了成功。國家農業部門最終認定四川省涼山州的布拖縣和鹽源縣產出的馬鈴薯是最好的繁殖用種薯,不僅組織有關部門在這兩個縣建立種薯基地,而且組織力量批量出售種薯。這使涼山地區的馬鈴薯生產不僅提高了其經濟效益,還使得其他溫暖潮濕地區的馬鈴薯種植也獲得了豐收。
在川滇黔毗鄰地帶的彝族地區調查時,我們發現,當地的彝族鄉民會把畜圈中混入牲畜糞便的草料廄肥定時翻出來,放在自己的家門口,在陽光下暴曬。不少農學家對這樣的操作辦法頗有微詞,認為這樣做以后,廄肥中的氮肥會被無效浪費掉,從而極大地降低了施肥的效果。而當地的彝族鄉民卻反詰到,如果不用這樣曬干的廄肥墊在種植的農作物馬鈴薯下,馬鈴薯就很難及時發芽,而且結出的馬鈴薯塊也會很小,單位面積的產量反而大大下降。凡是在彝族地區長期做過田野調查工作的民族學工作者,最終都會接受鄉民的做法,這樣的種植方法恰好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本土生態知識,而且可以當地彝族種植圓根、芋頭為例,證明這樣的本土性技術操作,恰好適應了當地獨特的自然與生態環境。經過自然地理學的驗證,這些民族學家的判斷是正確的認識和理解。其原因在于,這些彝族生息的地區海拔偏高,其地表下都存在著長期的凍土層,整個地表的土溫即使到了夏天也會明顯的低于10℃。如此偏低的土溫,對于大多數植物的根系發育而言,肯定是禁區。因而,如何避免氣溫偏低地層土壤的干擾,自然成了種植塊根類作物最難以攻克的挑戰。而彝族鄉民們的做法,是將脫水后尚未完全腐爛的廄肥墊在土中,將馬鈴薯種子放置在廄肥上,再用地表的土掩埋種子,就完成了播種工作。如此一來,種子有了廄肥的保護,馬鈴薯的根系就能在廄肥中生根,等到氣溫回暖后,再進入土壤中生長。以這樣的方式種植馬鈴薯,出芽、生根都可以提前半個月。這乃是本土生態知識的運用使四川省布拖、鹽源縣的馬鈴薯種薯得以行銷全國的原因。此項本土生態知識的科學性、合理性毋庸置疑。
除了用糞種法種植馬鈴薯外,當地彝族種植圓根、芋頭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延續了同一套本土生態知識。他們會在夏季高山放牧時,晚上收牧后將羊群、牛群集中到柵欄中,通常要在這樣的輪牧點留駐一個星期左右,等到轉換牧點時,地表留下的厚厚的牛羊糞便,在太陽的暴曬下,早就脫水干燥,而且糞團與糞團之間也留下了很多空隙。他們會把圓根的種子撒在這些干糞層上,就再也不予理會。到了冬天,牲畜群下山后,播下的圓根種子不需要翻耕、除草、除蟲,也會長出高大的植株,結出肥大的塊根來。來年,牲畜上山前,肯定可以獲得豐收。通常每一畝地可以收獲三千到四千斤鮮圓根。這些圓根,既可以作為牛羊的飼料,也可以曬干后作為人們的糧食。當地彝族諺語言:“有了圓根,就不怕挨餓。”由此可見,圓根在他們文化中的重要價值。從表面上看,這樣的種植方式似乎與馬鈴薯有些差距,但其實其原理均是一樣的,都是利用糞便脫水后發揮絕熱作用,避免底層的低溫干擾農作物的根系發育,從而可以用最小的勞力投入獲得最大的生產效益。此前的研究者之所以會誤讀這樣的本土知識,其原因也不復雜,那是因為他們習慣于用固定農耕的思維定式去理解高海拔山區的自然和地理環境。在漢族的農耕區,地下根本不存在永凍層,入春后解凍時間較早,一般的農作物都會正常生長。而《齊民要術》所提到的糞種法,僅是為了提供土壤的肥料。問題的癥結在于,在涼山地區,施肥僅是其效用的有限構成部分,最大的目的在于使種子根系發育免受低溫的傷害,以等待氣溫的回升后能夠正常生長。故而,保暖才是這里使用糞便法的關鍵所在。如果不這樣去作出解釋,不同學科為此肯定是爭議不休。
在涼山州,當地各民族還有一項獨特的本土知識和技術,那就是馬鈴薯與蕎子、燕麥實施間作輪種。此前的研究對這樣的做法往往持有不同的認識,認為這樣的種植方式,由于成熟期參差不齊,收獲時很難實現規模化的效益,也不便于現代農耕機械的推廣。植物保護要耗費的人力、物力會很高。但在當代的田野調查中卻發現,這些疑惑其實是多余的。原因在于在彝族的傳統農業生產中,耕地和牧場用地要實施規律性的輪回使用,農作物收獲后都要開放做牧場使用。一旦要復耕時,牲畜排放在地上的糞便只需翻耕就可以成為肥料使用。投工投勞都不多,但土地的肥力卻有充分的保障,不會退變。更重要的還在于,在這樣的農耕體制下,農作物的秸稈乃至地里長出的雜草,都是牲畜最好的飼料來源。收獲時雖然投工較大,但在固定農耕區的眾多農事操作中,中耕、除草、防蟲,對秸稈的再處理,都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這里卻可避免以上的各種農事操作。因而從綜合的整體操作著眼,其投工投勞的總量,比種植單一作物還要節省得多。單項作物每畝的平均產量雖然不高,但多種間作作物,收獲量的總和卻比種植單一作物高出一倍多。而且參與間作的作物,還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做出靈活的調控和匹配,并可坐收貨幣化的市場收入。此前的研究往往是沿用固定農耕區的測量手段,只計算其中某一種作物的產量作為評判依據,這樣的結論不言而喻乃是偏離了事實的真相,不可偏信。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川西高原的各民族中,他們的生息環境海拔高,災害性天氣頻發,地表容易遭逢流水的沖刷,地下還有永凍層造成的地溫偏低的制約。如果大面積地種植一種作物,即令獲得高產但經受不住災害性天氣的打擊,要穩產通常都不大可能。此前的研究者往往是根據某一年的產量提升就匆忙下結論。但這里的實情恰好相反,生產的瓶頸不在于某種作物的產量可以提升,而在于能否成功地應對災害性天氣的打擊。這樣一來,當地各族鄉民實施多作物復合間作,恰好可以成功地規避各種氣候災害的風險。比如冰雹的襲擊,在這里經常發生。但間作的各種作物,生長季長短不齊,即令其中某一種作物受到冰雹的襲擊,其他作物還可以填補留下的空缺,綜合產量不會因此而下降。再如,倒春寒和早霜,在這樣的地區也會頻繁發生,也會影響到作物的生長和收獲。但受害的對象,由于作物的生長季參差不齊,僅是其中的某一種作物受害明顯而已,也不會影響產出量大勢。應當看到各族鄉民的這些傳統生態知識,本身就是適應自然災害頻發的智慧之舉,這也是本土知識和技術精華所在。套用其他地區的普世性規范做出的得失評議本身就偏離了事實真相。而生態人類學倡導的文化適應理論更具有參考和借鑒價值。此前的“唯產量”論恰好在這一問題上,無意中犯下了錯誤,理應盡快得到匡正才是。
(三)恢復受損生態系統價值
地質史上形成的純自然性生態系統,本身就是一個可以獨立運行的生命實體總成。它有其存在和運行規律,根本無需人類插手加以維護。受損后也可以完全憑借生物的本能實現自我恢復。但人類來到這個地球后就不一樣了。人類得憑借自己建構的文化將人的單個個體,凝聚成一個穩定的群體,形成強大的社會合力,對早已存在的純自然生態系統實施加工、改造和利用,以滿足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但絕不是為了純自然生態系統的需要。于是在這樣的兩個系統并存的大背景下,相關的民族和社會一旦所實施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偏離了純自然生態系統的穩定延續機制,相關的生態系統就會因為人類的干預而發生退變,甚至釀成難以挽回的生態災變。
有幸之處僅在于,任何意義上的民族文化都具有能動認知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稟賦,一旦對人類不利的生態災變發生,相關民族都會啟動相應的補救措施,助推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而與此相關的本土知識、技術、技能,任何一個民族文化中均有相應的儲備,可以做出有效的應對,確保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洪澇災害頻發地帶的民族,其文化中肯定有防洪排澇的本土知識和技術于其中,即使遭逢災害,也可以做到應對有方。生息在雷擊頻發地帶的各民族,不僅在宗教祭祀中有祭雷神的傳統,村寨選址也會做到避開雷擊區。面對獸害頻發的民族,其文化中肯定儲備有應對獸害的本土知識和技術、技能,可以確保人畜兩安。事實上,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因為單一的自然災害而趨于滅亡。反而是在外人看來極具挑戰性風險性的地帶,生息的民族對當地的自然災害,會從容應對,防范有力,其生存與穩定延續都不會成問題。生態人類學家正是憑借這樣的認識和理解,做出認定越是生息在惡劣環境中的民族,局外人看來無法掌控的自然生態風險,他們的文化建構中肯定有正確應對的本土知識和技術,即令生態退變,也能做到恢復有方。
我國西南部的中山、低山喀斯特地貌出露帶,是石漠化災變的重災區。連片分布的石漠化災變帶遍及湖南、湖北、四川、重慶、貴州、廣西、云南等省市,連片分布面積廣達十多萬平方公里。不僅在我國,甚至在世界范圍內都表現得十分明顯。歐洲的克羅地亞,亞洲的印尼的蘇門答臘島都有嚴重的石漠化災變帶,但連片分布的范圍,都比我國中南、西南地區小得多,災變程度雖然很高,相關的國家通過生態移民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我國石漠化災變區則分布著上億的人口,災變程度雖然參差不齊,但牽涉到的各級行政機構卻數量不小,要達到協調綜合治災,組織管理上挑戰不小。不同學科的學者,雖然都做出了相應的努力,國家相關部門也能做到盡職盡責,并收到了一定的治災成效,但就總體而論,至今還無法令人滿意。據此有人公開宣揚石漠化災變是治不好的土地“癌癥”。這樣的論斷盡管是出于無奈,但容易造成誤導。因為我國的石漠化災變區生息著苗族、土家族、壯族、瑤族、彝族等10 多個少數民族,在他們的傳統文化中,一直保留著應對石漠化災變,有助于生態恢復的本土知識和技術技能。僅僅是因為此前的治理行動,往往是按照不同學科各行其是,不同行政單位分別規劃治理方案,從而在無意中造成相互之間難以協調,治理的方略難以統一,具體的治理操作往往各行其是,這才是治理成效達不到預期目標的關鍵原因所在。
事實上石漠化災變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成災的原因僅一個,那就是地表植被的生物多樣性水平遭到了人類不合適利用方式的干擾,從而派生的負效應。俗話說“解鈴還須系鈴人”,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一直到20 世紀中期,我們今天看到的石漠化災變表現得并不明顯。相關各民族的社會經濟,一直保持相對穩定,還能產出諸多的名特優產品足以供應國內外大市場的需求。石漠化災變的蔓延,其實是以大規模推廣種植單一糧食作物而派生的負效應,這樣的做法恰好是當地各民族傳統資源利用方式的對立面。只有正確認識到各民族本土生態知識和技術技能對環境的實用性價值,在行政管理層面,在科研的層面上都達成共識,那么憑這些民族傳統文化的再起用,憑借文化的常態化運行,石漠化災變才可以做到在常態化生產的同時實現自然恢復,而且巨額的投資和人力、物力的消耗,都可以大大節約,也能實現對原有藤喬叢林生態系統的恢復。
所謂藤喬叢林是一個特殊的生態類型,主要分布在石灰巖、白云巖大面積出露的中低海拔山區,越是溫暖濕潤的地帶,這樣的生態系統分布面越廣,生物多樣性水平越高,生命物質和生物能,單位面積產量越高。這是因為在溫暖濕潤的大氣環境下,出露地表的石灰巖和白云巖,溶蝕作用發展會極為迅速。地表崎嶇不平,地下伏流、溶洞密布。原先地表的珍貴土壤資源,都會順著溶洞和巖縫開口被流水攜帶入溶洞中去,從而導致地表的土壤資源稀缺。以至于原有的植被,一經人類擾動,生物多樣性水平有所下降,就會演化為牽連性的災變后果。隨著生物多樣性水平的降低,生物物種間的相互依存就會喪失,生態系統對地表的覆蓋度就會降低。流水的沖刷作用和地下的溶蝕作用就會加快,從而生態系統自身就會走上萎縮的道路。如果人類利用的方式不改變,石漠化災變也就不可避免了。正確的災變救治方法,就是需要各地區各民族統一認識、統一行動,啟用各民族本土知識和技術技能。按照傳統的生產方式去利用,哪怕是最重的災變帶,也實施有效的利用,才是正確的做法。具體的操作包括如下五個方面。
第一,以各民族此前種植農作物的經驗記憶為依據,去找尋和發現地下含有土壤的溶蝕坑和巖縫的開口,但不能用于種植常規的農作物,而只能種那些地下帶有塊根的藤蔓植物,或者是有經濟價值的低矮灌叢。目的是讓這些作物長大后,其藤蔓和葉片能夠最大限度將裸露的巖石和礫石遮蓋起來,以此抑制當地可貴水資源的無效蒸發。
第二,同樣是借助當地各民族傳統本土知識,收集動物的糞便或者苔蘚類、蕨類植物的孢子,撒播在已經被藤蔓植物所覆蓋的巖石上,進行引種。這些低等植物只要不直接暴露在陽光下,即使沒有土也可以旺盛地生長,將整個裸露的基巖覆蓋起來,并且能夠發揮截留大氣降水的功能,緩解缺少水土的缺陷。
第三,及時的引進當地已有的低等動物以及相對耐旱的低矮植物,以此恢復相關地區的生物多樣性水平,靠動物的糞便在地表提供更多的有機質,以緩解水土垂直流失的趨勢。
第四,也是按照當地各民族的經驗,引進有經濟價值的草本或者灌木類、藤本類的農作物,如中藥材、纖維植物、香料植物、油料植物等,以期更多層次的覆蓋裸露的基巖和礫石,確保看不見巖石,只看得見綠色植物。
第五,定植有重大經濟價值和可持續發揮經濟價值的木本作物。如可以因地制宜考慮種植桄榔木,桄榔木全身都是寶,其桄榔子的藥用價值很高,桄榔粉則是藥食同源的食品,廣西龍州縣的桄榔粉已經成為地理標志產品,桄榔木的樹干部分可以拿來做家具、筷子、筆筒等物品。
以上五個操作,必須嚴格按照以上順序推進,但需要整個石漠化災變區各民族協同推進,切忌各自為陣、各行其是。具體的操作,只需要激勵各族鄉民按上述次序推進即可。因為相關的種植知識、技術和技能,各族鄉民均已具備。只要鼓勵他們做,他們會做得很好。接下來只要不再擾動這樣的生態格局,那么即使持續產出,也不會妨礙整個原有的藤喬叢林生態系統得到完全恢復。
綜上所述,本土生態知識是不同民族的經驗積淀,所包含的生態智慧與技能可以幫助我們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雙重限制,憑借最小的投入獲得現代自然科學難以獲得的古代生態資料,抵御自然風險,規避學科分野的干擾。本土生態知識也是省錢省力的生態建設的經驗總結,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和針對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價值與經濟價值。在大力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今天,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當然需要大力推廣運用,但在這樣的過程中,千萬不要忽略各民族本土生態知識和技術技能的特殊價值。因為他們是落實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抓手和路徑。在地性強,可操作性大,普及面廣,因而只要對這樣的本土知識和技術技能,在現有的學術水平上,做出其科學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驗證,并上升到政策層面,加以統一規劃,協同推進,那么不管是生態維護、經濟發展、生態恢復都可以合為一體,協同推進,將生態文明建設熔鑄于常態化的文化運行和生產生活中去。相關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就可以實現事半功倍,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