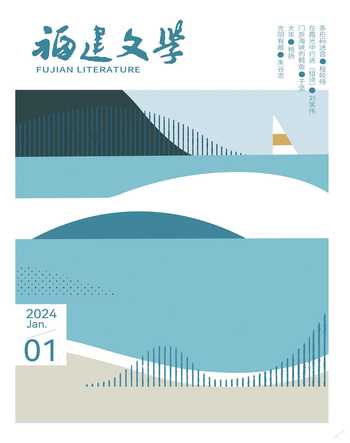屋頂的枇杷樹
楊文蓉
1
家門前的這條老巷子,在閩南最是尋常不過的。巷子兩邊一些出租的店鋪,總被人們不斷地隨性折騰翻新,所以這小巷子,總像是一個剛剛新做了發型的老人,新潮得有些讓人不適應,或許只有深愛著它的人,才能體會到它那老樹發新芽的美。水泥的路面年年修補,東一塊西一塊新舊補丁的重疊,越發使地面坑坑洼洼,細看隱約能看到年代的痕跡。走起路來,需仔細著腳下深淺,否則就會崴進小水坑里。
巷子里,時常響起載客三輪車“丁零零”的清脆鈴聲,喚醒巷子里的煙火氣息。晴天時,早晨陽光在右邊,下午又移到了左邊,地上總有一條明顯的陰陽界線,這讓人聯想到許多時事的變遷和古老的光陰故事。雨天時,悠長的巷子就會披上一層縹緲的薄紗,霧氣朦朧,詩意煥然,仿佛能看見一個丁香花般的姑娘撐著油紙傘,正從巷子深處施施然地走遠,幽幽的小巷襯著細腰窈窕,如夢如幻。
有時候,要尋得一個能清心的環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喜歡讀書,尤喜在清靜的環境里看書,去書里遇見美好,在字里行間領略難得的簡單與干凈。就在這個深秋的午夜里,我正蜷縮在沙發的角落里讀著詩集,窗外忽然滴滴答答下起急促的秋雨。一陣秋雨一陣涼,干燥沉悶的空氣明顯比昨夜更滋潤清涼了一些,蒼老的屋檐也有了些許的活力,似乎能感覺到那縫隙中潛伏的青苔也紛紛在伸展著腰身,它們交頭接耳、互相碰撞,像車廂里擁擠沸騰的人潮。
“滴滴答答……”,逐漸密集的雨水滴落聲在耳邊環繞,使困意頻頻向我襲來,漸漸地,我進入了夢鄉。然而,那棵曾令我牽腸掛肚的枇杷樹,再次強行闖入了我的夢中,此刻的它,正在風雨中努力地張開細長的枝丫,仰頭暢快地狂飲來之不易的甘露。忽然,一聲悶雷震得我神經一緊,把我從夢中拽回了現實,迷迷糊糊中才記起,那棵枇杷樹,已壽終正寢多時,但它仍然不時常在我的夢中重現。
那是一棵生長在鄰居家屋頂的枇杷樹,在一個干燥悶熱的初秋,它徹底地枯萎了。我不知道它是在哪一年生長出來的,但我卻見證了它生命走向枯萎的過程。一個在逆境中的生命終結,也許是一種最好的解脫。
在幾年前一個春光明媚的午后,巷子里靜悄悄的,只有那個目測有九十來歲的老阿婆,悠哉地靠在自家廊下的藤椅里,她的旁邊小幾上,擱著一把暗褐色的小茶壺和一包香煙。這是一個身量嬌小的老太太,喜歡身著淺色寬松唐裝,有些稀疏的銀灰色長發,在腦后簡單盤繞成鬢,看著十分休閑精致。她嗍一口紫砂壺里泡著的老樹茶,再深深吸一口香煙,瞇起眼睛吞云吐霧,不知她在思考著什么,又好像對什么都無動于衷,我猜想,她應是在想念曾經把巷子鬧翻天的那些頑童吧。一直以來,我總感覺這條小巷兩旁黑黝黝的門縫里、窗戶里,有許多雙神秘的眼睛偷偷地在窺視著巷子里的一切,每次經過時,我都不敢東張西望,躡手躡腳地想悄無聲息快速地溜過巷子,生怕驚擾了黑洞里的那些精靈,更不敢滋擾到那個似乎已入禪的老神仙。
但總會有事出偶然。就在一次匆忙趕路的不經意間,抬頭看了天空一眼,我發現了那棵矗立在屋頂的枇杷樹,它就靜靜地高站在那里,它空洞的俯視讓我有些壓迫感。小巷兩邊,灰黑色的水泥板屋檐,把天空切出一條長方形的藍色長條,枇杷樹貿然突顯的幾條纖細枝干,向四面八方伸出,各長各的,互不挨邊,又在枝丫的尾端掛著幾片寬厚的葉子,在風中搖頭晃腦。我愣愣地,有些想不明白,為什么那么羸弱細小的枝干會長出又寬又長的葉子呢?有些詭異的感覺。因為是逆光仰望,枇杷樹的枝丫模糊得有些看不清它的真實顏色,但站定細看之下,能發現樹干上有幾處正在吐綠的新芽。春日的陽光從那枇杷樹的枝丫縫隙中投射了下來,我伸出雙手,想掬一捧溫暖,但觸摸卻還有些許冷冽,光從我的指縫中漏了下去。
這是一座老舊的兩層水泥構造小樓,灰色的水泥外墻裂紋交錯,屋檐下,一只蜘蛛在忙著修補破了一邊的網,木門的朱漆已片片剝落,像失了鱗片的魚,半張大紅的春聯在風中顫顫地抖動著。我喜歡老舊有古典美的物件,但這樣破落的老屋卻讓我有些懼怕,這種貌似即將坍塌的老屋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雙布滿紅血絲的渾濁老眼在審視一個新鮮的世界,讓人渾身不自在。由于常年沒有人修整打理,老屋蕭條破落,但不要真以為它會即刻倒塌,那墻角結實的石條奠基告訴我,它離崩潰還早著呢,這情形倒是跟屋頂那棵奇怪的枇杷樹很有同框的契合感,似乎靈魂都上了天堂,肉身卻還掛在人間。
在深藍色天空的襯托下,那棵枇杷樹顯得頭大身小,有些滑稽可笑,又有那么一種讓人極不舒服的凄涼感,仿佛風再大一些,就能把它吹成灰燼。那一刻,我定住了腳步,心中竟然萌生了一絲莫名的興奮與激動。
2
從此以后,每次經過巷子時,我總會習慣性地仰頭看向那棵枇杷樹,甚至駐足觀望。這樣的時間久了,我便自認為和它已經成為朋友了,我開始嘗試把我的思想穿越到它的領地,去觸摸它孤獨的世界。這樣的接觸讓我有驚喜也有震動,但感受更多的卻是濃重的寂寥和安靜,濃到讓我的時間凝固,靜到讓我心無波瀾。剛開始,我是抗拒這種感覺的,但慢慢地,我接受了,也接受了它略帶荒涼的況味,最終,我沉迷于它獨處的清歡。
我的舉動,終于引起了鄰居的注意,有一天,那個夏天總在巷口搖著蒲扇納涼、略帶富態的嬸子,操著濃濃的九峰腔喊住了散步回來的我。夏天的巷口風總是令人清爽無比,老嬸子神情悠哉,斜靠在一張老舊得包漿的藤椅上,慢慢搖著扇子,微笑著朝旁邊的矮凳子努努嘴,示意我坐下,我也趁機坐了下來,舒展一下走得有些發脹的雙腿。
這好奇心還真的是不分老少,嬸子笑瞇瞇地問我每次從巷子經過時,為什么總是站定仰頭觀望,是在看什么稀奇。于是,我告訴她,我是對屋頂那棵枇杷樹好奇,我好奇它怎么來的,現在又怎么被棄在那兒,令人感到不是滋味。老嬸子篤定地問我:你是老師吧?我說,我是畫畫的。嬸子呵呵大笑幾聲:是畫畫的老師吧?難怪這么多心思,一棵水果樹而已,就能讓你擔憂到睡不著覺。可能在她的認知里,只有為人師者,才會有這樣的多愁善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吧。在這一個多鐘頭的閑聊中,我解了她的疑惑,她也讓我了解了那棵枇杷樹的由來。這時我心想,我可不能把我的想法跟她透露太多了,不然她會覺得我腦子有問題,畢竟,她是不會覺得樹木花草會有知覺的,也不能理解我這有些莫名其妙的慈悲情懷。
原來,那老屋原住著一對七十來歲的老夫妻,唯一的兒子常年在外極少回來。他們家屋里有個樓梯可通往屋頂,老兩口還健朗時,在屋前和屋頂用大大小小的花盆種滿了花草,雖不名貴,但卻常年花紅葉綠。每天老兩口除了早晚出雙入對去散步,余下時間就是養花種菜,日子過得十分悠閑自在。前些年,男主人忽然病倒,并很快離開人世。驟然被丟下的老婆婆,時常坐在門口的石凳上發呆,整日精神恍惚,別說照顧那些花草,連自己三餐都照顧不好。她兒子不放心,就把老母親接走,再沒回來,老屋就逐漸荒廢了。
經過幾年風吹雨打,屋前、屋頂盆盆罐罐里的花草都枯爛成泥,大家卻忽然發現,那屋頂不知何時冒出了一棵瘦弱的枇杷樹,誰也不清楚是老屋主人離開之前種的,還是后來它自己長出來的。這棵生長在屋頂的枇杷樹,它的主人摒棄了老屋,屋外沒有登上屋頂的樓梯,把通往它的路都給封鎖了。故事說到這里,老嬸子手中輕搖的蒲扇,慢慢地放緩了節奏,她的神情也似乎若有所思。我在她的一聲嘆息中,結束了此次交談。
性格與工作環境使然,我對外界所有的一切感受力都格外深刻,尤其是別離的傷痛。記得之前我曾讀過的心理學理論:人在極端痛苦艱難的時候,就會分泌出快樂的物質來平衡痛苦,所以,當痛苦源忽然結束,人就會被一種極大的幸福感所包圍。我想,同樣有生命力的動物、花草、樹木的感受大概也應該是如此吧。
3
常年被晾在屋頂,除了面對炎熱與寒冽,還得歷經狂風暴雨摧殘,這棵枇杷樹,顯然已經接受了現有的生存條件,更加珍惜陽光和雨露,用瘦削的身軀,反反復復地在每個春天里描繪那一抹鵝黃色的美麗。它站在那屋頂,默默地俯視著巷子里每個低頭趕路的人,看著他們頂著烏黑的或灰白的腦袋,像魚兒從它的眼前游過,不留痕跡。這世間的繁華與衰敗,都已讓它無動于衷,它應該知道,這世上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救世主,它的淡定,是一種最直接的人間清醒。
炙熱的大夏天,空氣像著了火,讓人連呼吸都凝固,隔壁屋頂的那個老鄰居,它一定非常饑渴,我能深切地感覺到,它通過空氣流動的電波在向我求救,那微弱的喘息呼救聲,在干燥的空氣中斷斷續續地向我“嘀嘀”傳來,令我坐立難安。曾經好幾次,我提著噴水壺,在老屋的周圍繞來繞去地尋找,希望可以找到攀爬的樓梯或者藤索,可是很快,我在烈日狂浪的追逐下,落荒而逃。
閩南的氣候大多時候是溫暖而濕潤的,雨量還算充沛,但光照也十分充足。在那個寸草難生的水泥屋頂,僅需幾個干旱的夏日,就足以把這棵枇杷樹曬成標本。我站在狹小的巷子里,仰望那十幾米高的屋頂,束手無策。看著它枯葉飄零,我憂心忡忡,它的困境和我的焦慮好像已經被捆綁在一起,就像兩個每天必須出勤的工人。有一天清晨,天空飄著小雨,我站在臨街的窗臺,遠遠地與它對視,它渾身濕透卻精神抖擻,我嘆了口氣,低頭開始燒水泡茶,一杯敬它,一杯溫暖自己。
在逆境中成長的生命,它們衍生出特殊的生存技能,會產生一種魔力,讓我為之著迷,浮想聯翩。頑強不屈的生命,它們抖擻的樣子最能觸動我脆弱的命門,我佩服它們的生存能力,覺得它們都值得擁有自己的紀念碑。現實中,并不是每一粒種子都能落在芳草連天的沃土里,生命的發端,往往不可自主地選擇生在哪里、落在何處。有些種子偏偏就落在鋼筋水泥森林里、落到臺階下或者石縫里,它們從夾縫里探出頭來,似乎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它們生長。它們自信樂觀,已經不在意有沒有人去評價它們的美丑,對它們來說,只管活著即可。開花與結果也許就一次,所以絕對不容錯過,這些頑強的生命總能活出另一副精氣神來。
就在前年枇杷成熟的季節,我發現樹梢上居然掛了幾顆拇指大小的青綠果實,瘦小結實。我反復確認,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幾乎每天都會去看它一眼,它是什么時候開的花?!我沒問,它也沒有告訴我。可見,它開的花朵是弱小到我看不見的。開花與結果,本就是植物自然成長的規律,卻成了屋頂這棵枇杷樹一生的夙愿似的。
也許是上年結果子而拼了全力,耗盡了所有的養分,去年,枇杷樹不見開花,也不見果實,幾場春雨過后,它才遲遲冒出了幾葉細細的嫩芽,在冷風中搖擺著幾片老葉子,似乎在告訴左鄰右舍:瞧見沒?我還活著。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它還活著!但也嘆了一口氣,接下來,又是艱難的一年了,或許會比往年更加難熬了。
對這個老鄰居過多的關注,有時會使我產生一絲偷窺隱私的不安與偷歡,腦子里時常出現一幅灰蒙蒙的動態畫面:那棵在屋頂飄搖的枇杷樹,長得丑陋不堪,它偷偷地儲藏了陽光和雨水給予的養分,小丑一般地活著,但它努力使自己站成紳士的模樣,掙扎著向上挺拔,把每一次落葉都當作蛻變。它養精蓄銳,終是開過花結過果。
我和枇杷樹十多米高的距離,摸不著也看不清,但總感覺它跟我有著某種關系,這讓我覺得那高處里有些神秘莫測。在探索的過程中,枇杷樹枝頭暗淡的微光,似乎不斷地在向我暗示遙遠的未來想象,反向的影響讓我有些恍惚也有些狼狽。我諱言生死,但在這個隨時面臨枯萎的生命面前,我仿若瞬間就讀懂了生命。死亡,是生命在時間領域里的一個極限,相對于環境的嚴酷,任何堂皇的偉大都是虛幻的。
藝術是生命維度最生動的體現。但這個時候,我覺得在殘酷的生死面前,藝術是最虛幻的東西,甚至把生命的慘烈終結作為藝術來談論都有些殘忍,但是現實就在我的眼里,這棵枇杷樹此時已經是一件藝術品,正在用生命的歷程,定義生命的價值,詮釋著屬于它的獨特存在的奇妙意義。它讓我知道,生命包含的不只是鮮活的肉身載體,還包含它所有的經歷與信念。生命的終結,只是一種肉身的寂滅,它的精神價值是存在的。這棵枇杷樹,把活著當作一種信念在修行。對我來說,它是我與另一個世界的接口,包含著無數的關系和意義。
去年深秋,屋頂的枇杷樹徹底枯萎了,像露珠一樣從世間蒸發了。但它卻把濃愁與長情留在老巷深處,在每個月朗星稀或風雨搖曳的深夜,出現在我的夢境里。秋風見涼,枇杷樹枝頭的樹葉漸漸泛黃,隨著冷風搖擺,一片一片地脫落,每一片都飄落進了我的心里,堆積在我心田中最肥沃的那塊土壤里,年深月久,逐漸長出了一棵萬年常青樹。我站在老巷的一角,仰望它清減羸弱的老態。我停止了所有的思考與追問,把埋在心靈深處的隱衷,與它一同化為塵土。
時光荏苒,又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春季午后,溫度令人十分舒適。小巷的廊下,那紅地磚,依然擦洗得光滑透亮,卻不見了那個喝茶抽煙的老神仙與藤躺椅。我一如既往想要快速地穿過小巷,卻在低頭趕路的一瞥間,驚訝地發現在墻角,一棵正在成長的小小枇杷樹苗,對著我怯生生、好奇地探出了它稚嫩的臉龐。
責任編輯陳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