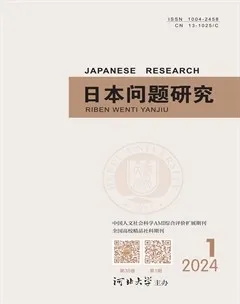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的現代性闡釋及其當代價值
摘要: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基于歷史傳統文化考察中國,指出中國是實現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關鍵。他與世界知識分子進行對談,剖析西方現代文明中的困境,從“以人為本”的維度考察中華文明中的文化底蘊。為破解西方現代文明中排他性與均質化的局限,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進行現代性闡釋,指出中華文明和平主義色彩的“普遍性”,以及價值論與存在論的統一,具有超越西方現代文明的可能。因此,池田大作對21世紀的中國充滿期待,認為中華文明將在形成真正符合人類利益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中發揮重要價值。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的現代性闡釋,為理解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提供了東西方文明比較的維度,予以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一定的啟迪和借鑒。
關鍵詞:池田大作;中華文明;西方現代性;以人為本
中圖分類號:B3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24)01-0060-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401007
20世紀70年代,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與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進行關于人類文明的對談。兩人在東西方文明比較的基礎上,得到“中國將會成為今后世界歷史的主軸”的結論[1]347。湯因比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特征秉持批判態度,與此相對應,認為“中華民族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所培養出來的世界精神”,將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池田大作也指出,在中國歷史豐富多彩的精神遺產中,“感受到了與帶有強烈侵略色彩的歐洲普遍主義完全不同的世界精神的萌芽”[1]347。池田大作何以得出這一結論?他對中華文明懷有怎樣的期待?盡管學界關于池田大作對中日友好的貢獻、池田大作外交和教育文化思想的研究頗豐①,但對池田大作中華文明觀的研究成果較為不足。此外,池田大作身為“公明黨和創價學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2],他對中國的認知深刻影響著日本公明黨與創價學會對中國的態度,值得密切關注。因此,本文嘗試通過梳理池田大作對中國歷史傳統、東方文明的諸多論述,剖析中華文明中解決西方現代文明局限的精神智慧,進而探討池田大作中華文明觀的當代價值,以期為把握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五個突出特性提供東西方文明比較的視角。
一、池田大作與中國之緣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1950年,22歲的池田大作受恩師戶田城圣的影響,為學期間被中國的氣勢恢宏的理想和豐富多彩的精神境界強烈震撼,深知中國對于日本來說,“因緣極深、恩德極大”[3]。此后,他基于對中國歷史傳統的深入思考,對中國解決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并不遺余力踐行中國與世界的和平友好事業。
在20世紀60—70年代,池田大作認為中國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1968年池田大作發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后文簡稱《倡言》),主張推動中日兩國實現正常的邦交關系,這一主張打破了當時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阻礙兩國關系的艱難局勢。當時,受美蘇兩極格局的影響,處于共產主義陣營的中國被美國視為世界和平的威脅,在政治和經濟上被世界孤立。而且,美國將中國視為共產主義陣營的后盾,為防止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興起,美國和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日本納入遠東政策之中。因此,日本輿論界受美國影響,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充滿恐懼。
但是,池田大作沒有受國際輿論的影響。在1968年發表的《倡言》中,池田大作從兩方面對“中國威脅論”進行駁斥,以論證中國是和平的國家。一方面,他從歷史和文化入手理解當時中國的對外方針政策。池田大作指出,多民族性、自然災害多發、地區經濟差別大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基本國情,受地理和社會結構的影響,歷來當權者以“鞏固邊境、專心內治”作為中央的政治方針以保障內政的安定。因此,20世紀60—70年代中國對美對蘇方針,是中國出于反抗美蘇的包圍主義而激化出來的對外防衛政策,過高估計這一方面會導致對中國的誤讀[4]240。另一方面,他結合中國的東方精神與傳統認識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駁斥日本社會普遍將毛澤東思想歪曲為侵略性、危險性的理論。池田大作指出,毛澤東非常注重人的思想變革,并不是會引起日本社會混亂的危險學說。在中日之間恢復正常邦交之后,只要日本社會內部思想健全、國情安定、人民生活富足,絕對不可能出現美國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4]243245。由此,在《倡言》中,池田大作強調,中國是“解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關鍵”[5]。
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池田大作繼續擴大在海外的和平實踐行動。他通過首腦與民眾間的溝通、對話、交流加強國家之間的共識,緩和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矛盾。一方面,池田大作主張以東方傳統的“演繹法”解決國際關系危機問題。這種演繹的方法即兩國領導人相互交談,鞏固對和平基本原則的共識,以找到解決方案[4]6792。1974年池田大作訪問中國和蘇聯,力求通過與兩國首腦對談加深中蘇之間相互了解,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蘇關系。1974年5月池田大作首次訪華。在此期間,池田大作積極與各階層中國民眾進行友好交流,與政府要員探討中國核問題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4]251。同年12月,池田大作首次訪蘇,在與蘇聯總理柯西金會談中,池田大作向柯西金傳達了在訪華期間了解到的中國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主張,以及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期待[6]。另一方面,1974—1997年池田大作十次訪華,進一步增強中日民眾間的交流與信任。在23年的時間里,池田大作與中國普通民眾和青年學生進行了廣泛直接地交流,并在大學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多次探討中國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以及中美關系的未來等問題。為加強中日兩國民眾之間的相互信任,池田大作創辦了日本最大的民間音樂團體——民主音樂協會,拓展日本與世界的藝術活動[7]。此外,池田大作還建立創價教育機構、東京富士美術館等教育和文化交流的聯絡點,鼓勵中日兩國民眾進行廣泛深入的文化交流。
綜上所述,池田大作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認知,使他在20世紀60—70年代對中國現實情況做出正確判斷,認識到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池田大作在踐行和平行動中進行有關文化、文明的交流。基于池田大作的對談集、回憶錄以及在大學發表的演講,可以縷析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的認知。
二、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的考察維度
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的考察是立足于全球視域的西方現代性危機背景之下進行的,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是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或東方文明)頗為感興趣的起點。
首先,在池田大作與莫斯科大學校長沙德維尼茲的對談中,兩人探討了何為“現代化”的問題。沙德維尼茲認為,“近代化”與“現代化”意思等同。現代主義在一百年前先后在藝術、建筑領域被使用,是歐洲藝術新潮流的體現。進入20世紀后,現代化被用于宗教界堅持的世界觀,在20世紀中葉之后常與科技畫等號,現在用作以西方傳統價值觀為基礎的世界“全球化”的含義。對此池田大作認為,現代化的內涵是多樣的、分歧的,但其共性在于“與封建性訣別”“脫胎換骨”[8]184185。
其次,池田大作指出西方現代化的主要特征。在對談中,池田大作借湯因比博士的《世界與西歐》(The"World"and"the"West)一書中的觀點為依據,提出主導數百年來現代化潮流的是歐美,尤其是西歐湯因比在《世界與西歐》(The"World"and"the"West)一書中認為:“直至今日,連續四五百年來世界與西歐的交涉,借此得到某種價值經驗的,不是西歐,而是世界。并非西歐受到世界的沖擊,而是世界因西歐受到了重大沖擊。”。俄羅斯、印度、遠東等地區都需要面對來自西歐的現代文明,這種現代化呈現出“無法競爭的同質性且普遍性的世界化性向”,迫使其他文明只能接受[8]174。池田大作認為,“傳統與現代化搭橋”的問題是所有國家在各自立場、在時代的波濤中都無法避免的問題——無論是竭力推進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民主主義、市場經濟、科學技術等方面達到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需要考慮的都是如何在不拋棄傳統的前提下,繼承發展現代化的成果,這是未來后現代文明發展的方向[8]172。換言之,由于此前其他文明在競爭中難以超越西歐文明,因此西歐文明在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逐漸走向均質的世界化傾向。
再次,池田大作闡明了造成“同質性且普遍性的世界化性向”的因素——現代化科技。他指出,由于科技帶來極大的方便與效率,因此沖破了地域性、民族性、傳統性的差異,在帶來物質繁榮的同時卻造成了私欲的無限膨脹[8]175。進而,池田大作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文明主導的現代化在世界形成的秩序與規范感是抽象的——真正的世界秩序應該是從國家、民族或文明的歷史及傳統中產生。為論證這一點,他對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視為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勝利”、認為資本主義由此可以獲得全球化時代“世界標準”地位的觀點予以駁斥,指出世界各國都接受自由競爭原理的市場經濟,進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的樂觀論調的不切實際性[8]177。
最后,在池田大作與德國思想家狄爾鮑拉夫的對談中,池田大作論述了西方主導的現代化文明為何排斥其他國家的文明和歷史傳統的原因。池田大作對歐洲人與日本、中國等非歐洲人士在處理現代化與傳統問題的做法進行了區分。他指出:由于現代化從歐洲興起,因此不存在非歐洲地區現代化中存在的“與封建性訣別”的問題,而與之相對,歐洲的現代化具有“不能與歐洲傳統文化的土壤相割裂的一面”。因此,歐洲關于“傳統”的含義有了另一種詮釋——即“自己動手批判自己開展的現代化、并探索現代化過程中應該持有的態度”,例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對近代合理主義的尖銳批判正是這一例證。[9]36換言之,對現代性進行批判與反思是歐洲的傳統,由此,西歐對待傳統的態度本身就具有一種批判的色彩。池田大作認為,西歐不僅以批判的態度對待自身傳統,對非歐洲,尤其是對東方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往往是排斥。池田大作借用卡爾·古斯塔夫·瓊格的觀點,指出歐洲知識分子在接觸東方傳統文化時的態度,或全盤拋棄歐洲的傳統,或完全拒絕東方傳統文化,兩者必居其一。對于歐洲評判東方傳統文化的這一態度,池田大作認為,隨著現代化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對待西歐與東方的傳統文化應該秉持相互繼承、拋棄弊端,創造可稱之為“人類普遍的思想”[9]42。
因此,為解決西方現代文明呈現“均質化”、排他性的局限,池田大作將文明的期盼由西方轉向了東方。他對中國歷史傳統以及東方文明展開諸多論述,系統考察中華文明中以“人”為中心的文化底蘊。
池田大作認為,“以人為本”理念涉及中國歷史傳統的各個領域,這一點從未動搖。日本人山田慶兒是熟知中國思想的青年研究者,他認為,中國哲學是關于人的學問,對此池田大作也深為贊同。池田大作指出,不只是中國哲學,中國的宗教、科學、政治等與人類行為有關的所有學問,其基調都是以人為出發點[10]82。池田大作認為,中國“無論在形而上的領域,還是在形而下的領域”[11]110都以人為基軸,探討人類如何生活是中國歷史傳統中的經典思考模式。
池田大作主要從兩方面探討中國歷史傳統中的“以人為本”理念:其一,注重人對“自身”的自律和修養;其二,注重以人的維度實行和驗證一切。池田大作曾多次探討中庸思想,認為中庸思想是中國“以人為本”理念的典型。1992年池田大作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題為《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的演講,對中庸思想展開論述:“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11]110池田大作認為,“中”是指“表現在喜怒哀樂之前的不偏不倚的心中的中正、心的平正”,這種情感上的不偏不倚使人的思想和行動避免受不正的情念影響。而“和”是“達到合乎事物節度的狀態”,是一種“節度感覺”,這種感覺能讓人回到真正的人。[11]110因此,中庸思想是一種自律與自我修養。中庸并不是世俗上所理解的政治立場的折中、妥協,或者是保持圓滑人際關系的表面行為,它反映出來一種人格主義。此外,在演講中池田大作還提到,由于中庸思想以人的內部變革為第一要義,因此其中蘊含以人的維度實行和驗證一切的革新性。[11]111總之,從池田大作對中庸思想的探討,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考察是以“人”為中心展開的。中國傳統中的“以人為本”理念,一方面注重人的自律和修養,通過倫理、道德等規范對自我進行約束以實現自身的揚棄,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柔軟智慧。另一方面,這種自我約束并沒有就此停止于人內心,而是通過實踐來進行——即用人的維度去驗證規范的正確與否,并在此基礎上不斷革新自身。
在池田大作看來,中國傳統的“以人為本”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1992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中,池田大作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爭與蘇聯解體的世界大動蕩,并強調以“人”為中心、通過人的實踐去驗證一切思想意識正確與否的重要性。他以中國儒學經典著作《論語》中的“博文約禮”作為例子,指出“禮”的實行正是中國人文傳統中注重自我修養、自我規范的表現。“廣學博識,但不以博識為滿足,還應該注重禮,即實行來檢束知識。”[11]110此外,池田大作認為,中國歷史傳統中“以人為本”的思想智慧是中國留給人類未來的珍貴遺產。在池田大作與狄爾鮑拉夫的對談集序言中他提到,中國傳統哲學的中庸思想是21世紀重要的精神遺產,其原因在于中庸使人“感受到植根于每個人心靈深處的返璞歸真的‘人本主義’的躍動。”[12]2
三、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的現代性闡釋
池田大作以“人”為切入點,探討中華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從池田大作對比東西方文明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中華文明從以下兩方面對西方文明中的局限進行了補足。
第一,西方文明中的“均質化”與排他性問題。池田大作看來,西方現代文明的均質化與排他性實質上是充滿暴力與征服色彩的“偽普遍性”,而中華文明以和平主義的“普遍性”克服這種局限。池田大作曾提到,“中國文明究竟帶給人們什么樣的人生觀、世界觀呢?我不揣學淺,將其歸結為‘透過個別看普遍’這樣一句話。”[13]71池田大作認為,由于西方文明歷史主軸是“神”,因此,西方在“看待人或自然時,免不了用神的棱鏡去看待”。“這種‘神’的棱鏡對他們來說是普遍的,但想要原封不動地運用于歷史與傳統迥然不同的其他民族,就只能采用強迫的手段。因此,其結果就是侵略的、排斥的殖民主義披著神的外衣在橫行霸道。”[13]7273也就是說,西方文明自視自己是“普遍性”,但其實反而是一種“特殊性”。因此,當西歐國家伴隨資本的擴張,需要向外推行自己的文化與文明,遇到與西方不同的殖民地的傳統文明時,只能采用殖民主義的強迫手段使其他民族接受。西方國家將自己暴力和野蠻的征服視為是文明的行為,這看似是一種悖論,卻以事實的形式在殖民地殘酷地發生著。而與之相反,中華文明“不是通過某種棱鏡去看事物,而是注目于現實本身,從現實中尋求普遍性的法則。”[13]74池田大作指出,通過辨別個別案例的是非善惡探討現實的普遍原則是中國的歷史傳統。由于這種普遍性是從現實中的人出發,更容易為其他民族所接受,由此中華文明才會在最為繁榮的盛唐時期包容其他異族文明、實現和平主義色彩的和諧共生,從而規避了西方文明因文明的沖突走向暴力與戰爭的可能。
第二,西方文明欠缺價值層面的生命倫理的探討,而中華文明中以現實中人的實踐為思考范式,實現了價值論與存在論的統一,具有西方文明所沒有的優越性。池田大作認為,盡管西方文明以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沖破“神”的束縛,為人類社會帶來了生產力上巨大的變革,但人卻成為原子化的個人,由此產生利己主義與個人主義,科學理論也因過于強調實證和規律而離現實的人越來越遠。1994年池田大作在深圳大學發表的演講中指出,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的激烈震蕩,后冷戰時期的世界并沒有走向和平,依然面臨接連不斷的民族和宗教問題,力量薄弱的聯合國對此只能袖手旁觀。此外,現代社會里泛濫著人種、毒品、暴力、教育荒廢等各種危機,自由民主主義產生出一批由“欲望”和“理性”構成的利己私欲者[14]124125。在池田大作與狄爾鮑拉夫的對談中,狄爾鮑拉夫也提到,在重新探討西方“人與自然關系”的話題時,會發現基督教中缺乏有關生命倫理的探索。“西方的人道主義的基本態度是以人為核心,把人以外對自然的關心當成發展科學技術或訂立計劃時的攻關點,而在道德上不承擔任何約束。我認為這是令人惋惜的缺陷。然而,即使彌補了這一缺陷,也會有夾雜在促進美德的集體道德和個人道德之間的距離。”[9]109也就是說,西方文明注重對理性和自我意識的存在論的探索,卻造成對價值論的欠缺。對于這一問題,池田大作在中華文明中探尋到了解決之方。他認為,宋儒理學“有機的人類觀”實現了價值論與存在論的統一。由于宋儒理學認為世界上的森羅萬象都與人息息相關,因此對任何事物的探討都要扣到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根本問題上。其探討的科學、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內容多以現實中的人為出發點,采取“恰如其分”的思考范式,“驗證一切現象的意義、善惡、過和不足”[14]127。在此,探討與人有關的一切事物是否“恰如其分”,正是人的存在性的體現。
此外,池田大作指出,一般人們認為孔孟等古代儒家在價值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豐饒的,但在存在論上的探討有所欠缺,而在他看來,孔孟學說也體現了價值論與存在論的統一。池田大作談到,孔子在“正名論”中所說的“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都是在探討“名”與“實”的關系[15]118。也就是說,天道人倫等秩序并不只是“名”的價值層面表達,在實踐中自省、踐行倫理秩序是實現人的存在的方法。由此,個人通過踐行道德、倫理等規范,在實踐中驗證所得認知是否正確,使作為存在的“實”與“名”相符,以實現價值論與存在論相統一的“名副其實”。因此,池田大作指出:“名副其實的宗教或哲學都擁有兩個側面,即人應當如何生活的‘價值論’側面,和世界是怎樣構成的‘存在論’側面,是一種總括性的世界觀。”[15]118
在池田大作看來,中華文明中所體現出來的和平主義色彩的“普遍性”以及價值論與存在論的統一,使中國有望引領世界通向實現人類利益的世界新秩序。1991年池田大作在澳門大學作的《通往新世界秩序之道》演講中談到,在意識形態對抗終結之后,世界開始形成新的國際秩序。池田大作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中“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學說具有現代意義。由五常學說,即“仁”中的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義”中的克服利己主義謀求人類利益的人間大義、“禮”中尊重異域文明的和平傾向、“智”中對僵化思想的突破與革新、“信”中的對世界各國敞開心扉,[16]101105為基礎建構起來的世界新秩序真正代表了人類利益,是21世紀人類未來的趨向。由此,池田大作對21世紀的中國充滿期待。
四、池田大作中華文明觀的當代價值
21世紀進入一個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價值理念沖突不斷升級的新時代。為應對全球文明面臨的危機與挑戰,深入研究和探討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五個突出特性的內在價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成為學界的重要議題2023年6月2日,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人民日報》6月3日頭版對此進行了詳細報道,闡釋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五個突出特性,并明確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時代任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隨后發表系列文章,引起學界熱烈回應。。如何從東西方文明比較的視野理解這一重要論述?池田大作的中華文明觀為解答這一時代課題提供了一種異域思考。
第一,中華文明中的連續性。在池田大作看來,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曾經歷過盛衰榮枯,但中華文明經過悠久的歲月長河卻從未中斷,具有一以貫之的連續性。中國作為擁有遼闊版圖和眾多人口的一大文明古國,其精神文明經歷數千年“從未斷絕、生生不息”[12]96。與之相對,池田大作認為,西方文明中的人文精神并不是一直延續的。從5-15世紀漫長的中世紀時期,西方文明都是以神為中心,而不是以人為中心。池田大作曾提到,盡管古希臘的人文精神為世人稱道,但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思想“在現代希臘社會中,沒有被源源不息地承繼下來”,“現在只是將這些思想作為文明的、知識的遺產保存起來而已”[12]96。池田大作指出,在歐洲中世紀社會,“神”是歷史的主軸,“當時的社會活動,看起來是人的活動,事實上卻是以神為目的的哲學,以神為目的的宗教、科學和政治”[10]83。進入近代,歐洲社會中科技的信仰、“進步”的觀念、“理性的自我運動”開始逐漸取代了對“神”的崇拜[10]83。直至19世紀末之后,馬克思和尼采才宣布了“神的死亡”,西方歷史才開始以人為中心展開。[13]73
第二,中華文明中的創新性。池田大作對中華文明創新性的探討集中在兩方面。其一,中華文明的創新性體現在追求自律的自我變革之中。池田大作曾引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杜巴里教授在紀念錢穆的演講中關于中國儒學的論述,證明中華文明中的革新性。杜巴里教授指出,中國儒學中蘊含著“不介于外在因素”的“變革能力”[11]111。對此,池田大作深表贊同,他認為,中華文明的革新性體現在不介于外在的規范、遵循回歸自我,為實現自我的內在自由、不斷獲取新知以追求進步的行動之中。這種對自我的內在要求使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區別開來。[11]111此外,池田大作曾對中國傳統中的“自”與西方文明中的“個”(individual)的概念進行區分,他指出中國傳統中的“自”含有自律、自強的含義,“帶有自在的深度和廣度”[14]126,而歐洲文化中的“個”具有根深蒂固的孤立色彩,這種孤立性在近代之后演變為獨斷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他還特別強調,中國關于“自我”的概念是一種以自身認知、自身感受為第一要義的內部自省,例如中華文明中的“為己之學”其含義在于,追求學問的道路上并沒有受外界的強制,而是“貫穿著極其內向的、內省的基調”[16]102。其二,中華文明中的創新性體現在改造現實的實踐之中。池田大作指出,中國傳統中強調用倫理、道德等規范對自身進行約束,都是以實踐為基礎的,歸根到底要去驗證這些規范的正確性。例如,即使是在認識“天”時,中國古人也沒有將“天”視為規范的存在,而是認為“天”在人的經驗生活中與人相連。[10]103也就是說,中國古人是自發地思考關于“天”的問題,以人的維度通過現實世界來認識“天”,進而基于這種認識不斷實踐以改造現實。
此外,中華文明中的創新性也表現在教育之中。池田大作曾談到,主張以人為中心的啟發式教學是中國教育的傳統,例如《論語》中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12]95。而且,教育思想中也體現出自我約束的倫理性與驗證事實的實踐性。他指出,《大學》的“八條目”,一方面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為倫理規范陶冶人性,另一方面將其對自我的約束轉移到與人有關的經世濟民的實踐中,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12]95。
第三,中華文明中的統一性。池田大作認為,中華文明將人和與人相關聯的一切事物看做一個統一體,即從人與人到人與自然、人與宇宙,所有的事物都與人有密切的關系,而且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池田大作以宋代朱子學來論證這一點:宋代朱子學是一種“有機的人類觀”——“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系,形成一個有機體,而且這種聯系不限于人的世界,還擴展到自然界和宇宙,構成萬物渾然一體的有機整體。”“對人和自然的觀念,與對人類和事物的個別觀相比,更重視關聯性和相互依存性。”[14]126也就是說,在池田大作看來,由于森羅萬象的一切事物都與人類息息相關,因此中國古人注重以人為中心探討人與世界、自然界和宇宙的關系。此外,池田大作關于東西方社會中的“人”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做過對比分析。一方面,他指出,中國社會中的“人”具有自律、自強的含義,且注重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支撐,而西方中的人是孤立的個體[14]126。另一方面,中國歷史傳統強調對自我的約束,并將這種“克己”的概念以“禮”的形式轉到其他人身上,從對自己的規范衍生出對整個社會的規范,由此促使社會形成一種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普遍秩序。池田大作曾談到,盡管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中笛卡爾式cogito(我思)對人的探討也強調對自身徹底的自律,與中國的“克己”有一定相似性,但卻沒有出現“他者”,即沒有實現對他人的約束。[16]102
第四,中華文明中的包容性。中華文明注重與人相關的一切事物的調和共生。池田大作指出,東亞地區貫通一種“共生的ethos(道德氣質)”,即“取調和而舍對立、取結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共同支持、共同生存、一起繁榮”[15]115。池田大作認為,這種調和共生是儒家文化影響之下的結果。儒家文化追求以人的倫理和道德為中心的秩序,體現出一種人道主義色彩的普遍性。在池田大作看來,中國在處理人與他人、本民族與異民族關系時,常常以道德和文明作為交往的標尺。例如,他與金庸的對談中曾提到,“在中國只要有‘義’便是朋友”。在處理與異民族的關系時,“比起‘出身’,更重視‘文明程度’”。正是因為以人的道德和文明作為前提與“他者”進行交往,因此池田大作認為中國是對其他民族“寬容而開放的社會”[17]211。
第五,中華文明中的和平性。由于中華文明中追求倫理、道德等規范秩序,因此具有控制人和國家自身的本能和獸性的意志力和約束力,彰顯出和平主義色彩的文明力量。池田大作指出,用文化、文明中“文”的力量去抑制軍備“武”的力量是中國的歷史傳統,即便是在中國位于世界之冠、文明最繁盛的隋唐時期,在外交上依然采取“只要宗主權,并不試圖征服”“未從中獲得好處”的朝貢貿易。中國傳統認為“對外征服是非道、不德的行為”,因此主張以文明、文化使鄰國信服。例如,隋唐時期中國頻繁派遣隋唐使與日本展開關于文明與文化的交流[10]81。池田大作曾提到,“以訴諸武力為下策,不以擅動兵伐為常用手段,而以損害最少、以謀取勝為上策”,這種中國傳統優秀的政治外交,“應該說是從健全而又深奧的‘人本主義’傳統所產生的吧”[18]。總之,中國在外交中注重以人為本,避免用征伐解決問題。
與之相對,西方文明在包容性以及和平性上有所欠缺。在池田大作與湯因比的文明對談中,池田大作提到,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對異教徒極其不寬容,常因對以神為中心的不同教義解釋產生沖突,而且為了宣揚自身教義的正確性,會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性的戰爭之中。這種對戰爭的肯定一直延續至資產階級擴張時期,宗教信仰與文化傳統成為國家政治行為的理由[1]451。也就是說,西方國家以自身的文化和文明為正確,試圖在“不文明”的地區建立殖民地并展開征服戰爭,其文明實質并沒有以“人”為中心,而是以“文明”為口實構建出虛偽的、暴力性的殖民主義體制。此外,池田大作還提到,日本雖然也受東方文明的影響,但與中國的文明傳統有些許不同。日本在處理異族關系時,由于過于強調“以血統來統一”,導致民族排外主義盛行[17]211,在受西方征戰思維的影響下走向法西斯主義道路。總之,由于中華文明強調通過以人為中心的道德倫理與“他者”進行交往,更容易被廣泛地理解和接受,因此呈現出包容性與和平性,不會出現大的分裂與沖突。
綜上所述,池田大作以“人”為切入點,從東西方文明比較視野考察中華文明。從池田大作對于中國歷史傳統、東方文明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五大特征,在彌補了西方現代性不足的同時,彰顯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獨特智慧。
結語
進入21世紀,國際形勢的復雜性和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人類前途與命運成為世人無法回避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站在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的現代價值,已經不是文化的歷史回望,而是現實的關照、前路的思考;已經不是中華民族的自我價值判斷,而是事關人類繼續生存、持續發展的整體利益關切。池田大作從人類視野出發,通過中西文明比較闡明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價值,對于我們深入理解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價值,進而踐行新時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具有一定的啟迪和借鑒。一方面,池田大作與世界知識分子對談尋求突破西方現代性困境的解決之方,從“以人為本”的文化底蘊來考察中國歷史傳統,探討中華文明超越西方現代文明中排他性與均質化局限的可能,對中華文明“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學說在未來形成符合人類利益的世界新秩序中發揮重要價值充滿期待,反映出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進步的文明真正符合世界與時代潮流,構建和平性、發展性的國際人類文明新秩序是世界人民的期許與心愿。另一方面,池田大作將中華文明視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精神遺產,為理解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提供了一種東西方文明比較的維度。未來的中國將繼續堅持以實現人類利益的共同繁榮為目標,繼續推進世界各國之間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鑒,譜寫文化傳承的新篇章,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參考文獻]
[1]池田大作,湯因比.選擇生命——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M].馮峰,雋雪艷,孫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2]陳祥.公明黨的“中道”政治與保守輔弼[J].日本問題研究,2023(6):1-11.
[3]池田大作.新·人間革命:第13卷[M].創價學會,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51-52.
[4]池田大作.日中國交正常化提言(1968年12月)[G]//中國の人間革命.東京:毎日新聞社,1974.
[5]池田大作.中國問題正是實現世界和平的關鍵[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3-5.
[6]ウラジミール·トローピン·出逢いの二十年[M].東京:潮出版社,1995:66-84.
[7]崔學森.簡論二戰后日本創價學會的復興[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5(6):104.
[8]池田大作,沙德維尼茲·新人類、新世界——暢談教育與社會[M].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池田大作研究中心,2006.
[9]池田大作,狄爾鮑拉夫.走向21世紀的人與哲學——尋求新的人性[M].汪淳波,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10]池田大作.走向和平之康莊大道[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1]池田大作.中國的人本主義傳統[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2]池田大作.教育之道,文化之橋[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3]池田大作.尋求新的民眾形象[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4]池田大作.“人本主義”大地萬里無垠[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5]池田大作.21世紀與東亞文明[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6]池田大作.通往新世界秩序之道[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7]池田大作.抓住全世界華人心的大文豪——金庸先生[M]//我的中國觀.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18]池田大作,金庸.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與池田大作對話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6.
[責任編輯孫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