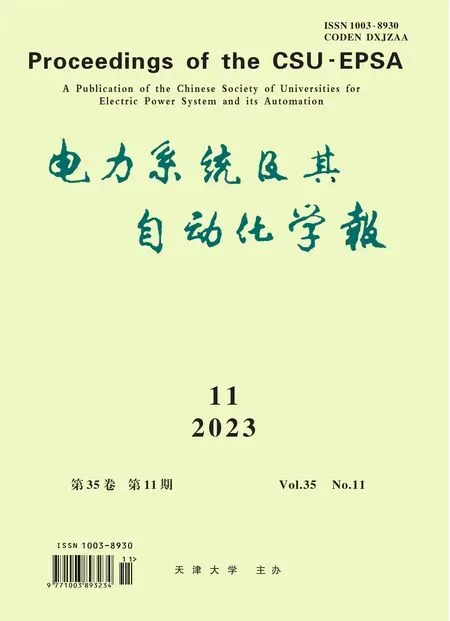發電聯盟參與電-碳-綠證市場的協同優化策略
詹博淳,馮昌森,尚 楠,盧治霖,梁梓楊,文福拴
(1.浙江大學電氣工程學院,杭州 310027;2.浙江工業大學信息工程學院,杭州 310023;3.南方電網能源發展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廣州 510663)
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能源局發布的《關于促進新時代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方案》(國辦函〔2022〕39號)[1]要求推廣綠色電力證書交易,加快研究建立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強制考核辦法,完善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權重制度。在此背景下,發電主體有必要統籌規劃,通過參與電力市場、碳市場和綠證市場,在完成消納責任的同時獲得最大收益[2-3]。
學術界針對發電主體參與電-碳-綠證市場已有廣泛研究。文獻[4]建立了基于局部均衡理論的化石能源發電主體電-碳交易的發電決策模型;文獻[5]建立了基于時間序列分析的風電主體在電-綠證市場長期風險投資決策模型;文獻[6]建立了基于多場景模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電-綠證交易決策模型,有效考慮可再生能源日內出清的不確定性。上述研究并未考慮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和化石能源發電主體同時參與電-碳-綠證交易。進一步地,文獻[7]建立了基于多方動態博弈的多時間尺度電-碳市場均衡模型;文獻[8]提出了基于逆向歸納法的多類型發電主體參與電-綠證市場競價策略。上述模型將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和化石能源發電主體在電-綠證交易時的關系刻畫為完全競爭型關系,未考慮到二者合作參與電-綠證市場交易可獲得合作剩余。
學術界對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和化石能源發電主體的合作博弈問題已有部分研究。文獻[9]建立了基于條件風險價值理論和隨機整數優化的風火機組參與電力現貨市場聯合競價模型,并未考慮風火機組聯盟參與碳市場和綠證市場;文獻[10]建立了考慮調峰補償和配額收益的自備電廠和風電廠發電權日前交易模型;文獻[11]建立了新能源與火電機組聯合參與多時間尺度電-綠證市場的決策模型。上述研究構建了發電聯盟參與多市場的決策模型,簡化了多市場的交易出清。基于此,本文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發電聯盟電-碳-綠證交易雙層優化模型,在上層發電聯盟決策模型中引入信息間隙決策理論量化現貨價格的不確定性,在下層建立了電-碳-綠證市場的交易出清模型,確定了電-碳-綠證市場的交易價格。
基于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方法有Shapley 值法、穩定集、談判集、核仁法等。文獻[12]提出了基于聯盟成員投入資源成本價值權重的改進Shapley值法,但并未考慮聯盟成員在不同聯盟活動中可能存在議價能力;文獻[13]提出了基于Shapley值等價分解的多權重Shapley 值模型,以反映成員在多項聯盟活動中的不同權重;Shapley 值法計算較為簡便,但對于非凸博弈存在組合爆炸的問題[14];文獻[15]提出了基于軟模糊匹配的穩定集收益分配方法,考慮了表征聯盟成員加入先后對收益分配的影響;文獻[16]構建了基于討價還價談判集的分布式能源收益分配策略,有效表征了聯盟個體的用電效用和風險厭惡程度;穩定集和談判集法能充分保證聯盟個體利益[17];文獻[18]提出了基于核仁法的直購電交易中電力網絡固定成本的分攤方法,核仁法計算復雜度會隨聯盟成員增加呈指數增加,不利于博弈模型的擴展。本文采用雙邊Shapley 值法將聯盟取得的總收益在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和可再生能源機組子聯盟間分配,采用改進的核仁法[19]在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和可再生能源機組子聯盟內進行收益分配。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針對屬于不同集團的化石能源發電主體和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建立了其聯合參與電-碳-綠證市場的交易決策和收益分配模型。具體地,建立了中長期-日前兩階段聯合優化的雙層模型,上層模型為考慮現貨價格不確定性的發電聯盟參與電-碳-綠證市場決策模型,下層模型為電-碳-綠證市場的交易出清模型,通過KKT條件將雙層模型整合為一個單層混合整數線性規劃問題。同時,還建立了基于Shapley 值法和改進核仁法的發電聯盟收益分配模型。本文提出的基于合作博弈的新型發電聯盟參與電-碳-綠證市場決策模型可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減少電力市場出清偏差,使可再生能源機組和化石能源機組實現雙贏。
1 發電聯盟電-碳-綠證交易決策優化模型
1.1 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發電主體的合作博弈模型
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制背景下,發電主體可參與電力中長期交易、電力現貨交易、碳排放權交易和綠證交易,各市場時間尺度如圖1所示。
圖1 中,電力中長期交易周期為Tz,發電主體可簽訂中長期合約鎖定部分收益。電力現貨市場的交易周期為Δt,各發電主體需提供競價曲線。本文設定中長期合約電量按電力現貨市場的交易周期簽訂,電力現貨市場的交易周期為2 h。
碳配額考核和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考核周期為T,碳市場和綠證市場交易周期為Tn,化石能源發電主體間可交易碳排放配額,化石能源發電主體和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間可交易綠證。碳配額余量和可再生能源消納完成情況會影響化石能源發電主體在電力現貨市場的競價。本文旨在研究碳市場和綠證市場交易對發電主體在電力市場競價決策的影響,將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考核周期T、綠證和碳配額的交易周期Tn設定為1 日,可再生能源消納量和碳配額在考核周期的劃分決策不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由于光伏和風電等出力具有隨機波動性,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的實際出力通常會與現貨市場出清電量存在偏差而被考核[20]。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在與化石能源發電主體組成發電聯盟后,依據現貨市場的出清結果優先調度,發電量超過出清電量的部分可替代部分化石能源電力,若存在負偏差電量由化石能源機組補發,可有效減少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的考核成本。發電聯盟結成后,化石能源發電主體需要為可再生能源出力的不確定性提供兜底服務,在可再生能源機組多發的情況下可能會減少出力,但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提供的綠證可減少其為滿足消納責任要求而購買綠證的成本,從而使其在合作中獲益。
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發電聯盟的交易過程本質為一個兩階段決策過程,其架構如圖2所示。在中長期決策階段,以預測的現貨市場價格簽訂中長期合約,并決策各時段簽約電量,通過簽訂電力中長期合約鎖定部分收益。在日前決策階段,各時段合約電量已定,發電聯盟需要決策現貨市場競價以及綠證和碳配額交易量;在現貨市場出清階段,發電聯盟可參與碳-綠證交易達到考核要求并獲取收益。

圖2 發電聯盟參與電-碳-綠證市場交易優化決策模型Fig.2 Optimal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generation alliance participating in electricity-carbon-green certificate markets
(1)綠證交易:在現貨出清階段,智能電表記錄發電聯盟可再生能源實際上網電量,按上網電量核發綠證,擁有綠證的發電聯盟進入綠證交易市場進行交易,通過出售綠證獲得經濟利益,以獲得綠電補貼,有消納責任需求的發電主體通過購買綠證獲得相應綠證,完成消納責任權重指標要求。
(2)碳交易:在現貨出清階段,智能電表記錄發電聯盟化石能源機組出力的實際碳排放量,若在本輪市場中實際碳排放量小于擁有的碳排放權余額,則可持有多余的碳排放權作為碳排放權交易的賣方進入市場;若本輪市場中實際的碳排放量大于企業持有的碳排放權余額,則作為碳排放權交易的買方進入市場,購買碳配額滿足碳排放配額考核要求。
1.2 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機組優化決策模型
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機組發電聯盟優化目標為在一個考核周期T內電-碳-綠證市場總收益最大,即
式中:fm為發電聯盟m的電-碳-綠證市場總收益;和分別為時段t發電聯盟m的中長期合約收益和電力現貨市場收益;和分別為時段t發電聯盟m的總發電成本和偏差考核成本;Fm,tgc和Cm,car分別為發電聯盟m該考核周期出售綠證的收益和購買碳配額的成本。
(1)電力中長期合約售電收益表示為
(2)電力現貨市場售電收益表示為
(3)總發電成本表示為
式中:K和Q分別為化石能源機組和可再生能源機組總臺數;δk,fe、δk,on-off和δq,re分別為第k臺化石能源機組的度電成本、機組啟停成本和第q臺可再生能源機組的度電成本;為時段t第k臺化石能源機組的狀態,開啟和停運狀態分別取0 和1;和分別為時段t第k臺化石能源機組和第q臺可再生能源機組的出力。
(4)偏差考核成本表示為
(5)出售綠證收益表示為
式中,Qm,tgc和αtgc分別為本考核周期發電聯盟m出售綠證的數量和綠證市場的交易價格。
(6)購買碳配額成本表示為
式中,Qm,car和αcar分別為本考核周期發電聯盟m購買碳配額的數量和碳排放權市場的交易價格。
約束條件如下。
(1)功率平衡約束表示為
式中,τ為中長期合約電量最低比例。
(2)碳配額平衡約束表示為
式中:χ為基于基準線法的單位電量碳排放分配系數[22];χk,fe為第k臺化石能源機組的碳排放系數;
(3)綠證平衡約束表示為
式中:εq,re為第q臺可再生能源機組單位電量對應的核發綠證數量,與可再生能源發電機組的類型有關[22];ηk,fe為第k臺化石能源機組的可再生能源責任消納權重,與機組的裝機容量等因素有關[22]。
(4)機組出力約束表示為
1.3 考慮現貨預測價格不確定性的魯棒優化模型
第1.2 節建立的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機組決策模型本質為一個兩階段決策模型:第1階段為中長期合約決策階段,發電聯盟通過與用戶簽訂中長期合約可提前鎖定一部分收益,但決策中長期簽約電量時需要考慮合約價格中電力現貨價格的不確定性;第2 階段為現貨市場競價決策階段,發電聯盟依據電力現貨市場、碳市場和綠證市場的交易出清規則,決策在電力現貨市場的競價以及在綠證市場和碳市場的交易量。
采用基于IGDT 的魯棒模型來量化第1 階段電力現貨預測價格的不確定性。基于IGDT的電力價格不確定模型數學表達式為
式中:X為電力價格的不確定參數;ξ為不確定參數的波動幅度;U(ξ,)為不確定參數X偏離其預測值的范圍不大于ξ。
考慮預測價格具有不確定性,風險回避的發電聯盟會要求保證最低收益,即滿足總收益不小于某一預期收益fm,ex的前提下,追求能抵抗預測偏差最大化的交易策略(即上層發電聯盟決策模型決策變量)。基于IGDT 風險決策理論可建立如下投標策略的魯棒優化模型表示為
式中:σ為發電聯盟可接受的收益偏差范圍;κ為上層發電聯盟決策變量集合;f( )X,κ為發電聯盟在策略κ下的收益;κ( )σ為偏差范圍σ下的決策變量解;X為上層發電聯盟決策目標函數中的參數集合;fm0為波動系數ξ=0 時發電聯盟收益。
具體來說,基于IGDT 的發電聯盟決策模型求解步驟如下。
步驟1不考慮在中長期決策時電力現貨價格的不確定性,即ξ=0,以求解式(1)發電聯盟收益最大化為目標,并考慮約束條件式(9)~式(15)的優化問題,獲得ξ=0 時的發電聯盟收益fm0。
步驟2考慮中長期合約中電力現貨預測價格的不確定性,基于發電聯盟可接受的收益偏差范圍σ,求解式(18)~式(21)的魯棒優化模型,獲得考慮現貨價格不確定性的交易策略及相應的魯棒區域。
2 電-碳-綠證市場交易出清模型
2.1 電力現貨市場出清模型
電力現貨市場的出清與地理位置、網絡約束等條件有關[23-24],電力現貨市場的出清出清目標是社會福利最大化,即
式中:v和o別為參與電力現貨市場的發電主體和負荷數量;αi,bid和αn,bid分別為第i個發電主體和第n個負荷的競價;和分別為時段t第i個發電聯盟和第n個負荷的出清功率;和分別為第i個發電主體的出清功率的上限和下限;和分別為第n個負荷出清功率的上限和下限;ρi,l和ρn,l分別為第i個發電主體和第n個負荷對線路l的功率傳輸分布系數,采用直流潮流模型計算;Fl,max為線路l的傳輸功率上限;?ν、?o和?l分別為發電聯盟集合、負荷集合和線路集合。
2.2 碳排放權市場交易模型
碳排放權市場交易模型采用階梯式碳交易機制[25]。與普通的碳交易機制不同,式(27)碳交易機制劃分多個碳排放量區間,當Qm,car為正時表示發電主體本考核周期實際碳排放量少于分配的額度,可以出售盈余的碳排放權獲得經濟補貼。當Qm,car為負時表示發電主體本考核周期實際碳排放量超過分配的額度,需要購買碳排放權達到考核要求。為促進發電側碳減排,購買或銷售的碳排放量越多相應的交易價格越高。階梯式碳配額交易價格為
2.3 綠證市場交易模型
綠證市場交易模型采用基于數量競爭的古諾模型。在古諾模型中,逆需求函數用來表征綠證市場的交易價格與市場綠證存量的關系,有
式中:a0和b0分別為綠證市場的逆需求函數中兩個正值參數;Qtgc,s和Qtgc,b分別為綠證市場掛牌出售量和掛牌購買量;αtgc為綠證交易價格;為綠證交易基礎價格;為基于歷史數據算出的綠證交易價格比率系數[22]。
2.4 模型的轉換與求解
在雙層模型的下層,求得的電力現貨市場、綠證市場和碳排放權市場的交易出清結果需反饋至上層發電聯盟魯棒優化模型。其中,由于綠證市場和碳排放權市場的交易出清模型不存在優化問題,可直接將其作為約束條件整合到上層模型。對于電力現貨市場出清模型,其KKT條件為其最優解的充分必要條件,根據式(22)~式(26)構造電力現貨市場出清模型的拉格朗日函數為
其KKT條件如下。
(1)拉格朗日函數為
(2)等式與不等式約束為
(3)互補松弛條件為
式(38)~(43)所示的互補松弛條件涉及兩個決策變量相乘,可通過Fortuny-Amat-McCarl法將其轉化為線性約束。以式(38)為例,可做下述變換:
式中:M為一個充分大的正數;為引入的布爾變量。
基于上述KKT條件,可將下層電力現貨市場出清模型以約束條件的形式納入由式(18)~式(21)所描述的上層發電聯盟魯棒優化模型中,這樣就把雙層優化模型轉化為單層優化問題,采用第1.3 節描述的魯棒優化模型求解流程即可。
3 發電聯盟的收益分配
基于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方法有核仁法、穩定談判集、Shapley 值法等。考慮到Shapley 值法可有效合理地將聯盟收益在各成員間分配,且計算較為簡便,因此本文首先采用Shapley 值法將聯盟取得的總收益在化石能源機組和可再生能源機組間分配,但在可再生能源機組內部和化石能源機組內部進行收益分配時,可能存在某兩臺機組各時段出力呈現正相關,不滿足Shapley 值法報酬遞增的凸博弈條件[14,26]。考慮到核仁法計算合作博弈的分配最優解必定存在且唯一,因此,本文對于可再生能源機組內部和化石能源機組內部進行收益分配時采用核仁法。
3.1 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間的收益分配
基于Shapley 值法,將總收益在多個子聯盟之間分配的一般形式表示為
式中:φi(v)為合作博弈大聯盟N中個體i的收益;W為合作博弈大聯盟中的可組合的子聯盟個數;|s|和n為子聯盟S和大聯盟N的個體數目;v(s) 和v(s-{i} )分別為個體i加入子聯盟前和加入子聯盟后的子聯盟收益。
對于可再生能源機組子聯盟和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間的雙邊Shapley值分配方案,可表示為
式中:φfe(v)和φre(v)分別為發電聯盟中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φfe和可再生能源機組子聯盟φre的分配收益;vfe和vre分別為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和可再生能源機組子聯盟單獨參與電-碳-綠證市場的收益,通過分別去除上層決策模型中有關可再生能源機組和化石能源機組目標函數部分和相應的約束條件后優化得到;vfr為化石能源機組-可再生能源機組發電聯盟參與電-碳-綠證市場的收益。
3.2 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內部收益分配
為減少計算復雜度,采用改進的核仁法[19]在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機組子聯盟內部進行收益分配,其目標函數f為收益偏差ε最小,即
式中:xi為滿足核仁解的個體i分配的收益,為決策變量;P'為化石能源機組或可再生能源機組子聯盟P內部的任意子聯盟;vP'為子聯盟P'單獨參與電-碳-綠證市場的收益;P(v)為化石能源機組或可再生能源機組子聯盟P的收益;vi為個體i單獨參與電-碳-綠證市場的收益。
4 算例與結果
4.1 參數設置
采用IEEE 14 節點系統進行算例分析,如圖3所示。假設參與電-綠證交易的市場主體有5個,分別位于節點2、4、8、11、14,節點2、11、14 為化石能源發電主體,節點8為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節點4為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發電聯盟,發電聯盟的收益偏差允許范圍σ=0.1。每個化石能源發電主體均配備2臺火電機組,基本參數取自文獻[23];每個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均配備1臺光伏機組和1臺風電機組,出力曲線取自文獻[7]。負荷數據和線路容量數據采用IEEE 14 節點系統的數據,碳配額和綠證歷史價格數據取自文獻[6]。

圖3 IEEE 14 節點系統拓撲結構Fig.3 Topology of IEEE 14-node power system
4.2 發電聯盟交易策略分析
圖4 為發電聯盟在現貨市場的競價曲線,其中:Pmix為調度化石能源機組的臨界出力,Pmix以下的競價對應只調度可再生能源機組發電,Pmix以上的競價對應同時調度可再生機組和化石能源機組發電,通過引入消納責任考核和碳-綠證市場交易,發電聯盟在400 kW 以下出力段的競價有所降低,這是因為引入綠證交易后,發電聯盟可通過出售綠證和碳配額獲取收益,因此降低了在現貨市場的競價以爭取更多的出清電量;Pcar為從碳排放權市場購買碳配額的臨界出力,出力大于Pcar時發電聯盟需要額外從碳排放權市場購買碳配額,購買碳配額成本導致發電聯盟在400~500 kW段的競價高于僅考慮電能交易時的競價;Ptgc為從綠證市場購買綠證的臨界出力,出力大于Ptgc時由于化石機組出力過多,發電聯盟需要同時購買碳配額和綠證達到消納責任考核要求,因此競價進一步提高。

圖4 發電聯盟競價曲線Fig.4 Bidding curve for generation alliance
圖5 為不同日出清電量下發電聯盟的碳-綠證交易量。可以看出,發電聯盟的度電收益隨著日出清電量先增加后減少。當日出清電量從0 開始增加至1 500 kW·h 時,可再生能源機組被優先調度,隨著可再生能源機組出力增加,出售綠證的數量也在增加,而因化石機組出力比例較低碳配額出售量幾乎不變,發電聯盟的度電收益不斷增加;當日出清電量從1 500 kW·h 增加至3 500 kW·h 的過程中,由于化石能源機組發電比例增大,發電聯盟的綠證收益下降,碳配額成本增加,但發電聯盟從電力市場獲得了更多的售電收益,因此度電收益依然緩慢增加;當日出清電量從3 500 kW·h 繼續增加時,雖然售電收益有所增加,在階梯式碳交易機制下發電聯盟碳配額成本大幅上升,且綠證收益進一步下降,因此發電聯盟的度電收益反而下降。

圖5 發電聯盟參與碳-綠證市場交易量Fig.5 Trading quantities in carbon-green certificate markets for generation alliance
圖6 為各時段發電聯盟實際出清電量和機組調度結果。可以看出,在00:00—06:00 的負荷低谷期,由于發電聯盟現貨出清電量較少,優先調度可再生能源機組出力,化石能源機組該時段出力較少;在08:00—14:00時段,雖然發電聯盟出清電量有所增加,但該時段為可再生能源發電機組發電量高峰期,因此化石能源機組出力增幅不明顯;在16:00—22:00 的負荷高峰期時段,發電聯盟出清電量達到一天中的最大值,同時該時段為可再生能源機組出力低谷期,因此化石能源機組出力明顯增加。

圖6 發電聯盟電能交易和機組調度結果Fig.6 Electricity trading and unit scheduling results of generation alliance
4.3 交易策略的魯棒性分析
圖7為收益偏差因子σ=0.1時的出清電價預測值波動范圍,可以看出,預測價格上下限波動趨勢和實際出清價格波動基本趨勢一致。在18:00—20:00時段出清電價較高,此時段預測價格波動范圍較大,為達到發電聯盟最低收益要求,魯棒優化模型會為風險較高的高價時段制定更寬的價格波動范圍。

圖7 σ=0.1 時出清電價波動范圍Fig.7 Fluctuation range of electricity clearing price when σ=0.1
發電聯盟在不同的最低預期收益目標下,其電價預測值波動系數ξ隨收益偏差因子σ的變化曲線如圖8 所示。以碳配額系數0.2、消納責任權重0.15 為例,分析收益偏差范圍對交易策略的影響。可以看出,在一定范圍內,預測價格的波動系數隨收益偏差因子σ的增加而增加,當發電聯盟可接受的預期收益越低,交易策略的魯棒性越好,越能承受越大范圍的預測價格波動。

圖8 波動系數ξ 隨收益偏差因子σ 變化情況Fig.8 Variation of fluctuation coefficient ξ with return deviation factor σ
當收益偏差因子增加到0.28時,電價預測值波動系數取到最大值0.184,表明即使現貨電價比預測值低18.4%,發電聯盟在魯棒策略下的收益依然可保證總收益不低于預期收益的72%。當收益偏差范圍繼續增加時,與不確定量有關的約束條件式(18)不再是有效的約束邊界,碳配額約束和消納責任權重約束限制了電價波動范圍的進一步增加,這意味著在σ≥0.28 時發電聯盟無法繼續通過降低預期總收益來獲得具有更強魯棒性的交易策略。因此,發電聯盟在電-碳-綠證交易決策時,應將預期總收益偏差設置為σ<0.28。
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和碳配額系數對交易策略的魯棒性亦有影響。在保證相同最低預期收益的情況下,隨著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比例的提高和碳配額系數的降低,所能承受的預測價格波動范圍越小,交易策略的魯棒性越差。
4.4 發電聯盟收益分配分析
發電聯盟可再生能源消納量如圖9 所示。當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單獨參與電力交易時,因競價優勢可出清06:00—14:00和18:00—20:00時段全部預測電量。然而可再生能源發電機組實際出力具有波動性,在16:00—18:00 時段實際最大出力為97.8 kW,低于預測最大出力115.4 kW,此時段該發電主體簽訂的現貨出清電量共計104.9 kW,因而偏差的7.1 kW 電量將會被考核;在06:00—14:00時段可再生能源機組的實際最大出力均高于預測最大出力,但其簽訂的中長期合約電量和現貨電量總計為預測最大出力,這導致了可再生能源的浪費,也使得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利益受損。

圖9 發電聯盟在某個典型日的可再生能源消納量Fig.9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by generation alliance on one typical day
當可再生能源發電主體與化石能源發電主體組成發電聯盟后,在16:00—18:00時段化石能源機組為可再生能源機組提供發電兜底服務,聯盟免于偏差考核;在06:00—14:00 時段化石能源發電機組減少出力,使聯盟內可再生能源機組滿發,消納了全部可再生能源電力,同時聯盟總發電成本降低。
表1 為不同聯盟情況下的收益對比,表2 為基于Shapley-改進核仁法的收益分配方案。可以看出,對于化石能源發電機組而言,由于可穩定出力,單獨參與或組成化石能源發電子聯盟參與的電-碳-綠證市場收益無差異;若和可再生能源發電子聯盟組成大聯盟,則可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機組的綠證完成部分綠電消納責任要求,化石能源子聯盟總收益提高了5.8%。

表1 三種聯盟下收益對比Tab.1 Comparison of income among three alliances 元

表2 基于Shapley-改進核仁法的收益分配方案Tab.2 Income allocation scheme based on Shapley value method and improved nucleolus method 元
對于可再生能源發電機組而言,由于出力具有波動性,組成子聯盟的2臺可再生能源機組可通過互補出力,減少部分差價合約考核成本,使收益提升2.8%;可再生能源發電子聯盟與化石能源發電子聯盟組成大聯盟,通過化石能源機組提供兜底供電,使可再生能源機組滿發且免于差價合約考核,可再生能源子聯盟收益提升了5.2%。
5 結 語
本文建立了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發電聯盟參與電-碳-綠證市場的雙層優化模型,經過算例仿真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可再生能源機組和化石能源機組聯合參與電-碳-綠證市場可促進可再生能源消納,減少電力現貨市場出清偏差。
(2)基于IGDT 的發電聯盟交易決策模型可有效量化現貨市場出清價格波動的風險,求解的交易策略魯棒性強,可保證發電聯盟的最低預期收益。
(3)基于雙邊Shapley 值和改進核仁法的收益分配模型可將發電聯盟收益進行公平分配,實現可再生能源機組和化石能源機組盈利的共同提升。
在后續研究中,擬考慮多發電主體之間的博弈問題以及發電主體提供輔助服務的補償與收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