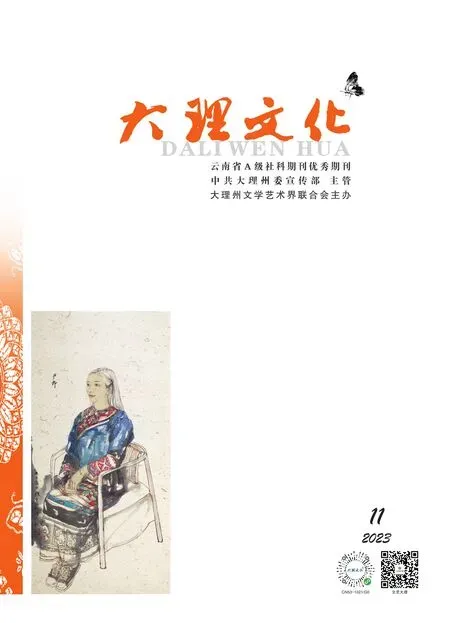春秋有語誰曾解,風雨無情總是詩
——楊建軍《祥云地方文學史稿》管窺
●楊無住
挑燈閱古卷,對月著文章。祥云自古地靈人杰,出過不少英才,其中不乏在文學上卓有建樹者。祥云80 后學者楊建軍遍尋史籍,在歷史文化研究方面獨領風騷,使地方文史研究生機勃發,如曠野中吹拂過的一縷清風。《祥云地方文學史稿》便是楊建軍的重要研究成果,填補了大理州內縣級無文學史專著的空白。
獨辟蹊徑
眾所周知,文學史成為學科只是近百年之事。中國最早的文學史是由日本人于清末光緒時編寫的《支那文學史》。光緒三十年,20 歲的林傳甲為講授中國文學編寫了《中國文學史講義》被認為是國人最早編寫的文學史,也有說謝無量編寫的《中國大文學史》或黃人編的《中國文學史》為最初。2010 年,《北京文學史》出版,屬地方文學史研究。同年江蘇常熟的《常熟文學史》被認為是中國首部縣級文學史。而在大理,相關的文學史較早的是由張文勛先生主編的《白族文學史》,1959 年出版,1983 年再版。2014 年,李纘緒編著《白族文學史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有徐嘉瑞著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和《大理古代文化史》。楊建軍所著《祥云地方文學史稿》彌補了大理州地方文學史研究的不足,可謂獨辟蹊徑,別有洞天。

治學嚴謹
楊建軍對各種史料中涉及文學的部分收集整理、條分縷析,做到“筆筆有出處,字字有來歷”,絕不以個人的主觀臆斷大膽下結論,對有出處的加以引用解析,對無出處的也不輕易填充“注水”,當詳者詳,當略者略。書名也謹慎地使用“史稿”二字。所謂“史稿”者,即不是完全成熟的史書,也不是官方集體編撰的史冊,而只是代表了個人的研究成果,還有提升的空間。作者提出,“一是本次研究是否有一個文學的空間,描繪出祥云歷代先賢的文學本相,哪怕是輪廓,并用史學的方法加以整理;二是能否在文學史中對祥云的地方文學做出應有的定位……”
特色鮮明
對戰國至宋元時期的祥云文學,因為涉及到的人物較少,缺少史料佐證,有些只是流于傳說,便在概述中寥寥數筆帶過。比如司馬遷到大理講學,司馬相如到大理還留下詩句,這些沒有可信的史料。而《蠻書》中記載的祥云段子英家庭,或與大理段思平立國有關。宋代,水目山的《淵公碑》的文學價值和文學特色,徐嘉瑞先生曾在《大理古代文化史》中提及。元代大理王室段福《春日次白崖道中》被認為是最早寫祥云風光的古詩。至于明代、清代、民國時期的文學,因為已擁有眾多的作家群,所以便以專章研究。另外,將方志編修、民間諜譜、民間故事整理、水目山文學、家族文學研究、革命文學研究皆以專章列入,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其中尤以水目山文學、家族文學和革命文學特色凸顯,具有祥云的辨識度。水目山是云南開創最早的佛教圣地之一,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南詔諸臣請建此剎,普濟慶光禪師以錫杖鑿地,有清泉涌出,因名水目,這便是“錫杖涌泉”的典故。水目山歷代高僧輩出,如凈妙澄禪師、無住禪師,“詩書畫三絕”的擔當和尚也在此剃度,法名“普荷”。水目山留下的古代詩文,目前少有人研究,有空間可以拓展。家族文學研究以王氏家族文學為主,有家族詩文集《荷池吟草》《春秋有語誰曾解》等傳世,研究相對容易。另一家族青海營雷氏作品已散佚,不贅述。“革命文學”以革命烈士王德三的白話文創作為重點,以另兩名中共黨員吳少默和王孝蕃的舊體詩文為補充,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特別是革命烈士王德三的白話文創作,開辟了祥云現代文學的先河。王德三幼承家訓,古文功底扎實。他寫白話文,為使勞苦大眾讀懂。此外,以胡適、魯迅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應當也對王德三有影響。
視野開闊
楊建軍寫地方文學史,并不拘泥于年代、作家、作品、價值判斷,而是拓寬眼界,將文學史放在地方史的視野下研究。如此,便有了《云南縣建置考》《方志編修》《民間諜譜提要》三個部分的加入。《云南縣建置考》是清代知縣謝圣倫撰文,出自《滇黔志略》,以此代序。《方志編修》涉及到《康熙云南縣志》《乾隆云南縣志》《道光云南縣志》《光緒云南縣志》《民國祥云縣志》《民國祥云地方志資料》及《華陽國志》《嘉靖大理府志》《萬歷趙州志》《滇黔志略》等,以此為根本,從中查閱“藝文志”,以此為線索,展開文學史的調查研究,使得祥云歷代作家作品有典可依,有據可查。在此基礎上向民間史料延伸,收集、整理、歸納、分類,并作出價值判斷,以如此廣闊的視野來展開地方文學史研究,應當遺漏較少。
邏輯嚴密
楊建軍認為,地方文學史作為中國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技術性的分析、研究與考證當是地方文學史的任務。在編寫上注重文學史料的收集、辨識與歸類,這是材料的方面;注重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與研究的趨勢、現狀,這是理論的方面。這兩個問題相互兼顧的核心問題又最終聚焦到文學史料這個前提上。楊建軍認為,祥云舊時代的文學具有傳世作品稀少、著述豐富但刻印少的特點。整理時發現明清兩代的著述書目僅有65種,作家個人傳記相當缺乏。從題材上看,主要的特點是詩歌存世較多,其余文體較少。楊建軍寫《祥云文學史稿》,更多注重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而不拘泥于純粹的作家作品。有了這樣的出發點,楊建軍著作便緊扣主題,在地方史的支撐下研究文學史。既有縱向的朝代劃分,也有橫向的聯系,構成了邏輯嚴密的經緯網。其中對前人記述的不準確之處,作者也進行充分考證,糾正前人之失,這需要有膽氣和耐心,也是楊建軍的可貴之處。此外,作者別出心裁地用了表格法,列出了《明代著述總目表》《清代著述總目表》《民國年間祥云一中<紀念刊>文藝目錄》《云南民間文學集成祥云篇目表》《祥云白族民間故事目錄表》《部分水目山詩文篇目表》《王氏家族著述篇目總表》《明清文武進士及文武舉人表》。由此可見,楊建軍的確是在考據考證上下了苦功夫,可謂“磨穿鐵硯”。
金無足赤,書無完書。《祥云地方文學史稿》仍存在提升的空間。一是有些作家作品仍有交叉重復之處,比如王氏家族作家作品已有專章研究,那么在之前的章目中就可以略寫。涉及到清朝詩人楊向春的篇目中已全篇引用了《野崖先生傳》,已將其軼事寫得清楚無遺,則無須對楊向春的軼聞奇事細述。二是對現代白話文研究頗有缺失。王德三烈士的白話文作品情真意切,雅俗共賞,已為祥云現代文學創作開了好頭,此后有大量的現當代作家的詩文發表傳世,筆者認為,應當有選擇性地增加白話文作家作品。三是在語言表述上,仍有提升空間,雖是史學研究,但亦應當使語言雅化與純化。當然,這對史學研究者是個苛求。
最后,以李元陽《寄楊野崖》詩作結,表達筆者對楊建軍先生的敬佩之情:
苦憶野崖楊博士,孤標落落似長松。
未論囊貯千年藥,只羨山居九鼎峰。
深閉白云無客到,盤堆香芋共僧餐。
欲聞邵子先天學,何日聯床坐曉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