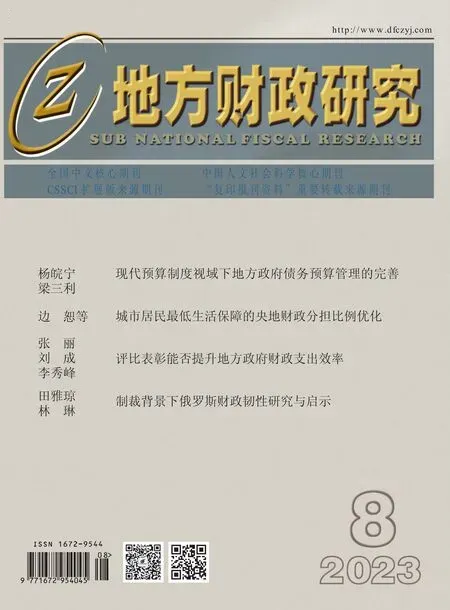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央地財政分擔比例優化
邊 恕 畢研菲 張 瑞
(遼寧大學,沈陽 110136)
內容提要:合理的財政支付是城市低保制度平穩運行的重要保障。城市低保投入強度先升后降的支付層級、以中央財政為主導的支付責任、城市低保標準上升而覆蓋人口下降的支付悖論是當前我國城市低保財政支付的現實特征。我國多級財政體制下,城市低保財政支付存在責任劃分不均衡、執行不規范和保障不得當等問題,確保轉移支付力度在各個地區達到合適水平是調整財政負擔的關鍵。由此,本文采用央地財政分擔模型測算省域間的中央轉移支付水平,進而提出優化城市低保財政支付及央地合理分擔的對策,即堅持以中央財政為主導的支付方式,合理劃分地方財政的支付責任,促進財政支付的執行規范化,完善城市低保財政支付的保障機制。
一、引言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促公平、兜底線、維護社會和諧、重視人民群眾生存權的一項基本民生保障制度,為城市居民建立起了紓困解難的最后一道“防線”,有助于消除社會不安定因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涉及各級財政主體的權責分配問題,合理的財政分擔機制是低保制度健康運行的重要保障。我國城市低保制度經歷了以“由點到面”(張永春和黃曉夏,2018)為基本特征的政策擴散過程,財政支付隨之表現出由“地方政府主責”到“中央政府主責”的演變邏輯,城市低保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國內學者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財政支付的探討主要集中于公平效應、責任劃分與面臨困境三個層面。一是公平效應。城市低保作為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保持籌資公平以實現城市低保均等化(龍異和孟天廣,2015)。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體系中,中央財政作為主要貢獻者,發揮著重要的“拉平效應”(顧昕等,2007)。二是責任劃分。為了夯實兜底保障地位,應建立中央主責的低保制度(楊立雄,2021)。三是面臨困境。低保標準與貧困線是否銜接、低保群體與城市貧困群體是否吻合等問題是影響低保制度發展的重要因素(解安和王立偉,2022);城市低保存在漏保偏誤突出(王卓和秦浩,2023)、低保對象“能進不能出、易進難出”現象(林叢,2019);城市低保可能出現制度功能異化、福利依賴、尋租和腐敗行為、福利資源損耗等問題(謝勇才,2020)。另外,“福利污名”亦會降低低保財政支付的效能(王惠,2021)。
綜上,學界對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財政支付的研究多是理論敘述,缺乏運用科學、明確的理論模型以合理測算中央轉移支付在各省域具體表現的研究。科學的估算模型能夠合理測算財政轉移支付的適度水平,幫助完善城市低保轉移支付制度,盡力避免資金的不足或過剩,更好發揮城市低保制度保障民生的作用。鑒于此,本文在分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財政支付的現狀與問題前提下,嘗試采用財政負擔模型具體測算各省域央地財政的支出責任比例,進而提出明確城市低保央地財政責任及優化分擔比例的對策。
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財政支付的現實考量
2022 年《關于進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民發〔2022〕83 號)明確提出,加大低保擴圍增效工作力度。為實現這一目標,應摸清當前城市低保財政支付的現實特征,找準財政支付的短板。當前城市低保財政支付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支付層級:城市低保投入強度先升后降
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界定為各級財政的城市低保支出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程杰,2021),可以通過觀察城市低保投入強度來了解城市低保的發展情況。2000 年-2021 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累計支出9533.8 億元,其中2021 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484.1 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0.04%,占當年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為0.20%,其投入強度較小,約為2011 年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的三分之一。圖1 顯示,從空間維度看,2000 年-2021 年社會救助投入強度與城鄉、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發展趨勢基本一致,呈現“上升-平穩-下降”態勢,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的發展趨勢更為穩定。從時間維度看,“十五”時期(2001 年-2005 年)要求盡快把所有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口納入低保保障范圍,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由2001 年的0.03%逐步提高到2005 年的0.10%,提升幅度最快。“十一五”時期(2006 年-2010 年),提出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標準,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由2006 年的0.10%逐步提高到2010 年的0.13%,2009 年達到峰值,為0.14%。“十二五”時期(2011 年-2015 年),城市低保覆蓋人數逐漸下降,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由2011 年的0.14%逐步下降到2015 年的0.10%。“十三五”時期(2016 年-2020 年),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由2016 年的0.09%逐步下降到2020 年的0.05%,城市低保投入強度的下降表明城市低保財政投入增長幅度小于經濟增長幅度,主要原因為:(1)打贏脫貧攻堅戰,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城市低保覆蓋人數逐漸減少;(2)目前解決相對貧困的機制尚未成熟,預算條件約束下低保對象瞄準機制嚴格化導致“漏保”現象突出。

圖1 城市居民低保投入強度的變動趨勢(2000 年-2021 年)
(二)支付責任:以中央財政為主導的分擔方式
在城市低保的起步階段,其籌資責任完全由地方政府自有財力承擔(黃玉君等,2015)。1994 年實行分稅制后,地方財政收入下降,中央轉移支付水平逐漸提高。圖2 顯示,2004 年-2007 年,我國城市低保中央轉移支付比例始終保持在50%-60%之間,整體上保持平穩;2007 年之后,中央轉移支付水平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支付比例保持在65%以上;從2004 年-2017 年,中央財政對城市低保的轉移支付累計達到5774.18 億元。這表明中央政府承擔了城市低保的主要支出責任,中央財政持續發揮低保救助的兜底功能,形成“地方掌勺,中央埋單”(楊立雄,2021)的低保救助模式。2014 年,國務院頒布《社會救助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安排的社會救助資金和社會救助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促進低保支出責任由“地方政府主責”到“中央政府主責”的變遷過程。“中央財政為主,地方財政為輔”的責任分擔方式既能夠彌補經濟欠發達地區財力匱乏、救助任務繁重等客觀的現實不足,又能夠提升全國范圍內低保救助的均等化水平,保障地方政府的救助責任落實。

圖2 2004 年-2017 年中央及地方低保支出預算比重
(三)支付悖論:城市低保標準上升而覆蓋人口下降
中國從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逐步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演進歷程呈現出“擴張—穩定—收縮”的階段性趨勢(程中培,2022),無論是城市低保財政投入還是覆蓋人數,都體現出這一特征。1999 年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標對象是人均收入低于最低標準的貧困家庭,從而2000 年-2003 年低保人數出現急漲情況,城市低保人口規模從402.6 萬人快速上升至2246.8 萬人(見圖3),增長幅度為458.07%。相比之下,2004 年-2009 年,城市低保覆蓋人口規模從2205 萬人上升至2345.6 萬人,增長幅度僅為6.37%。2009 年之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開始下降,2021 年減少至737.8 萬人,覆蓋人數減少意味著貧困人口逐步脫貧,而城市低保對象的快速減少可能會增加漏保風險(關信平,2019)。近年來,國家強調擴大低保覆蓋范圍,但城市低保卻表現出“標提圍擴量減悖論”(王強,2020)。

圖3 1996 年-2021 年城市居民低保財政投入與覆蓋人數的變動趨勢
當前我國城市低保出現了標準上升而覆蓋人口下降的支付悖論,這就需要結合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低保標準的動態變化來綜合判斷。2004 年-2021 年隨著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我國城市低保標準穩定上漲,但城市低保平均標準的上升速度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不適配。一方面,2004 年-2021 年,城市低保平均標準逐年遞增。2004 年城市低保平均標準為152 元/人·月,2021 年的平均標準為711.4 元/人·月,增長幅度為368.03%。這主要是因為“十一五”規劃至“十三五”規劃期間,始終將合理提高低保標準看作是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構成環節,逐步健全低保標準動態調整機制,采用基本生活費支出法、恩格爾系數法或消費支出比例法等制定城鄉低保標準,并依據當地居民生活必需品價格變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定期調整,使得低保標準逐漸科學規范。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遞增。2004 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421.6 元,2021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1.9 元,增長幅度為403.23%。可以看出,城市低保平均標準上升速度慢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肖萌等,2017)。
三、各省份央地財政分擔的分布特征與模式
城市低保中央轉移支付與低保標準存在相關關系。一般來說,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地方財力越充裕,低保標準越高,中央轉移支付水平越低,即央地支出比例的“替代效應”;或者說,在控制地方自有財力條件下,中央轉移支付水平越高,提高當地低保標準的可能性越大,即低保救助的“收入效應”。現實中省域間中央財政負擔與低保標準形成了不同的組合關系,對此可以通過四象限法觀察各省份央地財政負擔的區域分布特征。
圖4 中,橫軸是城市低保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縱軸是低保標準(元/人·月),將兩者的平均值作為橫縱軸交叉點,從而劃分成四個不同的發展模式。其中,2017 年我國31 個省份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的平均值為51.72%①由于《中國民政統計年鑒》城市低保關于中央、省級詳細支出預算數據更新至2017 年,因此本文涉及到相關內容的歷史數據都以2017 年為例。,低保標準的平均值為560.82 元/人·月。由此,根據各省的具體表現可將31 個省份劃分成四個象限:第一象限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和低保標準均高于平均值的“標準型”模式;第二象限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低但低保標準高的“發展型”模式;第三象限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和低保標準均低的“基本型”模式;第四象限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高但低保標準低的“保障型”模式。以下為中央財政負擔與低保標準分布特征的具體情況。

圖4 2017 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城市低保標準的四象限
(一)第一象限:央地財政分擔的“標準型”模式
城市低保央地財政負擔劃分的理想模式為中央財政承擔主要責任,同時保障標準較高,這一條件符合“標準型”模式。位于第一象限的省份有4 個,分別為西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湖北省。在這一區域,中央財政很好地發揮了轉移支付功能,中央低保支出比例保持在50%以上,為促進社會公平貢獻了力量。與此同時,城市低保標準較高,能夠在滿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同時,注重城市低保人群的生活質量。
(二)第二象限:央地財政分擔的“發展型”模式
“發展型”模式的分布特征表現為地方政府承擔主要的低保支出責任,同時低保標準較高。位于第二象限的省份有7 個,分別為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江蘇省、廣東省、福建省。其中,福建省(51.18,589.80) 靠近橫縱坐標的交叉點(51.72,560.82),基本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其余省份為發達、較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財力富裕,具有很強的財政自給能力,能夠負擔當地低保救助責任,中央轉移支付水平較低;地區經濟富裕同樣帶動保障標準領先全國平均水平,體現為典型的“發展型”特征。
(三)第三象限:央地財政分擔的“基本型”模式
“基本型”模式的分布特征表現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水平較低,且低保標準同樣較低。這一區域內,省級財政應發揮“保基本”效能,保障城市低保群體的基本生活。位于第三象限的省份有6 個,分別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河南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安徽省、山東省。除山東省外,其余省份分屬中西部地區,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約,從橫向看,低保標準相對較低;從縱向看,城市低保中央轉移支付較低。
(四)第四象限:央地財政分擔的“保障型”模式
“保障型”模式的分布特征表現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水平較高,而低保標準較低。位于第四象限的省份有14 個,分別為重慶市、山西省、海南省、青海省、陜西省、吉林省、河北省、貴州省、湖南省、甘肅省、四川省、江西省、黑龍江省、云南省,省份數量占全國的45.16%。其中,除海南省、河北省外,其余省份分屬中西部、東北地區。在這一模式下,中央轉移支出責任高,能夠減輕地方財政的城市低保支付壓力。同時,中西部、東北地區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城市低保標準相對較低。
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央地財政分擔的現實問題
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基礎之上,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財政支付結構性問題,如何確保轉移支付力度在各個地區達到適度水平是調整支付問題的關鍵。具體來看,城市低保財政支付分擔主要面臨以下現實問題:
(一)財政支付責任劃分不均衡,城市低保省級預算亟需提高
我國中央與地方行政性分權體制下,央地事權范圍模糊與地方政府的事權、支出責任不對稱成為阻礙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問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減少而事權、支出責任增加,無疑會增加地方政府的財稅負擔,逐漸弱化地方政府的財政功能。作為社會救助的主要項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劃分不均衡的現象。表1 顯示,2004 年-2017 年,我國省級城市低保支出比重均在15%以下,2015 年-2017 年省級財政支出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市級城市低保財政負擔比重整體最低,且呈下降趨勢,2016 年僅為2.46%;2015 年以前,縣級及以下城市低保支出比重均超過省級、市級支出比重,其平均值為19.64%。①由于《中國民政統計年鑒》城市低保關于中央、省級、市級詳細支出預算數據更新至2017 年,因此本文涉及到相關內容的歷史數據都以2017 年為例。由此可見,中央財政承擔城市低保的主要支出責任,市級支出比重最小,省級與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政責任此消彼長。就省級及以下各級政府財政支出能力而言,能力最高者理論上是省級地方政府,但實踐中省級的城市低保財政負擔比重較小。

表1 2004 年-2017 年我國各級政府城市低保支出預算情況 單位:億元、%
(二)財政支付執行不規范,城市低保工作機制亟待健全
一是城市低保支出責任過度轉嫁可能引致區域待遇差距擴大。城市低保支出責任執行過程中存在救助悖論,低保救助區域差異較大。經濟發達地區,救助人數少,財政收入富裕,救助水平高;經濟欠發達地區,救助人數多,財政收入薄弱,救助水平有限。城市低保支出責任過度下放會加重欠發達地區財政支出壓力,導致救助水平持續下降,使省域間待遇差距擴大,加劇“馬太效應”;省級支出責任過度轉接會損害市、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財政的救助能力,減弱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財政支出水平,不利于低保救助均等化及可持續發展。二是城市低保支出的責任主體層級分化可能導致行政管理效率低下。我國城市低保支出責任劃分為中央、省級、市級、縣級及以下行政層級,對應我國自上而下的行政架構。支出責任層層劃分不利于信息傳遞的及時性,同時資金層層下撥可能會形成額外的資金配套管理成本與運行成本,導致低保資金被“擠出”“占有”,阻礙行政管理效率的發揮。三是城市低保內部制度間銜接不暢可能致使支出責任執行效能不高。城市低保屬于民政部的管轄范圍,管理責任由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承擔。一方面,由于民政部門協作能力的局限性,無論是民政部與其他政府部門間的橫向協調,還是中央到基層的縱向權責,各職能部門之間系統、有效的銜接機制尚不成熟,從而制約財政支付功能的發揮。另一方面,目前尚未形成高效、科學的低保“動態準入與退出”機制與低保制度相配合。由于準入程序繁雜,城市低保捆綁較多的福利項目,易出現低保資格的“福利捆綁”,經濟利益驅動低保對象不會輕易“退出”低保福利,產生嚴重的“福利依賴”思想,加劇“福利懸崖”,不符合“應退盡退”的公平原則,這與低保的制度本意相悖。
(三)財政支付保障不得當,城市低保法治格局有待形成
城市低保財政支付的保障主要體現于支出責任劃分的明確性與責任承擔的強制性。一方面,中央、省級、市級、縣級及以下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劃分不夠明晰。現有政策沒有關于支出責任劃分的具體界定,缺乏明確的硬性制度規定。從全國層面看(以2017年為例,見表2),各省級地方政府城市低保財政責任各有側重,屬地管理的補助程度不統一,但縣級及以下政府均承擔支出責任,呈現明顯的地方性救助特點。按照央地所擔責任比重,可以大致劃分為以下幾個類型:第一類為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負有全部支出責任,代表省份有北京市、天津市;第二類為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負絕對責任,代表省份為上海市,中央轉移支付僅為5.44%;第三類為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支出責任為主,市級政府支出責任為輔,代表省份有安徽省、河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第四類為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支出責任為主,其他各級政府給予補助,代表省份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浙江省、江蘇省;第五類為省級政府負主要責任,其他各級政府承擔補充責任,代表省份有寧夏回族自治區、廣東省;第六類為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為主,其他各級政府給予補助,代表省份有重慶市、西藏自治區、海南省、山西省、青海省、陜西省、吉林省、遼寧省、河北省、貴州省、湖南省、內蒙古自治區、江西省、黑龍江省、甘肅省、四川省、湖北省、云南省、福建省、山東省。由此可見,城市低保支出責任分擔比例具有很大的自主性,省級政府可以通過轉嫁、下放等方式,將支出責任下移至基層政府,造成基層政府的財政壓力較大,亟需通過政策法規的出臺以規范支出責任合理劃分。

表2 2017 年我國各省各級政府城市低保支出預算情況 單位:億元、%

表3 2021 年全國城市低保中央財政分擔測算
另一方面,城市低保支出責任劃分的法律法規效力亟需提高。基層政府具有屬地管理的財政權,財政的自由裁量權涉及范圍廣、幅度大,且存在一定的彈性空間,地區差異明顯;資金預算分配力度軟化,缺乏相關法律依據加以規范和執行。2016 年《國務院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為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主要內容指明了方向,但未表明相應的詳細操作;2018年《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明確規范了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的支出責任分擔方式,主要實行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擔,但未指出地方各級財政分擔比例。另外,各級地方政策文件同樣很少提及城市低保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分擔比例,應盡快將這一部分上升至正式的法律層面以保障低保制度平穩運行。
五、城市低保央地財政支付分擔模型及測算
財政支付比重是否合理首先取決于央地支出責任劃分是否科學明晰,可以采用財政負擔模型測算各省域中央轉移支付的適當比例。同樣,省級轉移支付水平也面臨財政支付不清晰、不合理的問題,也可采用這一模型測算省級財政負擔比例問題。
因素法是城市低保央地財政負擔劃分所依據的方法,能夠根據各省經濟發展、財力狀況、物價水平等因素進行財政資源的合理分配,實現低保資金的均衡發展。為規范中央對地方財政的資金補助行為,2015 年財政部、民政部下發《中央財政困難群眾基本生活救助補助資金管理辦法》,明確規定采用因素法分配低保救助資金,由地方在補助資金總額度內統籌調劑使用。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補貼標準主要參考城鄉困難群眾數量、地方財政困難程度、地方財政努力程度、績效評價結果等因素,資金向貧困程度深、保障任務重、工作效績好的地區傾斜。采用因素法分配央地低保財政負擔,可以將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地方財力、受助低保人數的非均衡性內化為低保救助的公平性標準,減輕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財政壓力,避免因人情牽涉出“關系保”。由此,合意的央地財政負擔模型應參考因素法進行設定,體現央地財政關系的激勵相容。
(一)央地財政分擔的合意模型
《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明確規定,堅持差別化分擔。具體要求為充分考慮我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務成本和財力差異較大的國情,中央承擔的支出責任要有所區別,體現向困難地區傾斜,并逐步規范、適當簡化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共同財政事權支出責任的分擔方式。由此,城市低保中央轉移支付程度主要取決于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依據因素法與央地財政關系激勵相容思路,借鑒邊恕(2015)的央地財政負擔劃分方式,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Ti為城市低保制度中i 省得到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k 為財力基準比值,δ1為低保財力因子,rmax和ri分別為31 個省份中人均財政收入的最大值和i 省的人均財政收入,δ2為低保人口因子,zi和zmin分別為i 省的低保受助率和31 個省份中最低的低保受助率,Di為i 省的城市低保金支出額①公式(1)中,城市低保金支出額的系數為1/2,主要原因為: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城市低保支出責任,當k [δ1×(rmax-ri)/rmax+δ2×(zizmin)/zi]大于1 時,表明i 省城市低保中央轉移支付比例超過50%。。具體指標如下:
1.計算財力基準比值
財力基準比值等于中央財政按省級行政區劃數量所計算的平均值與各省地方財政的對比。將財力基準比值納入模型,能夠科學地反映地方財政困難程度。財力基準比值越大,表明各省地方自有財力水平越低,地方財政越困難,出于公平視角,中央轉移支付水平理應更高。經測算,西藏財力基準比值最大,為13.68(以2021 年為例進行測算,下文同),說明地方財力遠低于中央財政的平均水平,中央財政應成為其低保救助的主力。
2.計算低保財力因子、低保人口因子
從財力角度看,低保財力因子等于按照當地財力所能滿足的低保目標值的百分比,反映該地財力所負擔的低保支出責任的實際程度;從人口角度看,低保人口因子等于按照當前低保給付總額按照人均目標水平所能滿足的人數與原低保人數的比值,反映該地低保覆蓋能力。經測算,北京市、天津市低保財力因子分別為1.01、1.15,說明當地財力所負擔的低保支出責任的實際程度較大。廣西壯族自治區低保財力因子最低,為0.46,說明當地財力所負擔的低保支出責任的實際程度較小。
3.計算(rmax-ri)/rmax、(zi-zmin)/zi
人均財政收入能夠反映地方政府財政能力對城市低保標準的支付程度。一般來說,i 省人均財政收入越高,人均財政收入最大值與i 省人均財政收入的差額占人均財政收入最大值的比值越小,反映地方財政能力越大。(rmax-ri)/rmax的系數為低保財力因子,可以通過兩者相乘以調整中央轉移支付的水平。在財政預算約束條件下,需要救助的人口規模影響地方財政能力的救助水平,即低保人口越多,地方財政投入越多,這可能會讓地方政府感受到增加低保人數時成本亦會增加,減弱地方政府擴大覆蓋面的積極性。具體來看,i 省低保受助率越大,i 省的低保受助率與所有省份中低保的最低受助率的差額占i 省的低保受助率的比值越大,反映低保財政的投入越大,據此需要提高中央轉移支付水平以減輕地方政府財政壓力。(zi-zmin)/zi的系數為低保人口因子,同樣可以通過兩者相乘來調整中央轉移支付的水平。
4.計算i 省城市低保金支出額
i 省城市低保金支出額Di可以通過歷年《中國民政統計年鑒》與《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得知。Ti>Di,說明中央財政可以承擔i 省的城市低保支出責任,中央財政責任為Di。Ti<Di,說明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共同承擔城市低保支出責任,中央財政責任為Ti,地方財政責任為Di-Ti。
(二)央地財政合意的分擔測算結果
通過央地財政負擔模型,可以測算2019 年-2021 年全國城市低保的中央財政合意的分擔規模。2019 年-2021 年全國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測算結果分別為69.37%、71.33%、66.40%,符合“中央埋單”的支付模式。2021 年,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地方財政實力、低保覆蓋率等因素影響,天津市、吉林省、黑龍江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區、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9 個省份的低保支出責任可由中央財政承擔,有利于均衡全國財政負擔水平,體現公平原則;而廣東省、浙江省、江蘇省、山東省、上海市、北京市共6 個省份的低保支出責任可以由地方財政主要承擔,提高地方財政資金利用效率。地方人均財政收入越高,城市低保救助支出水平越高,低保救助的“收入效應”越明顯;城市低保受助率越低,地方財政支付壓力越小。具體來看,2021 年上海市的人均財政收入最高,浙江省的低保受助率最低,上海市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為15.70%,浙江省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為9.46%,說明以因素法與央地財政關系激勵相容思路為基礎的央地財政負擔模型是合意的,能夠促進低保救助均等化水平。
六、城市低保財政支付及央地合理分擔的對策建議
(一)堅持以中央財政為主導的支付方式,夯實城市低保救助的財力基礎
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兩者相互補充,共同承擔城市低保的支出責任,有助于財力支持的可持續。從全國整體角度看,經過現實考量與央地財政合意負擔測算,在現階段應將中央轉移支付比例整體繼續保持在50%甚至60%以上,堅持以中央財政為主導的支付方式,適當提高城市低保投入強度。從省域差異角度看,對于經濟發達地區來說,應保持“發展型”的央地財政分擔模式,強化地方政府履行低保救助的主體責任;并且強化“以獎代補”的方式激勵地方政府主動承擔應有責任,保障低保救助的內部差異性與外部公平性。具體而言,可以由中央政府統籌劃撥固定的低保獎勵經費,運用預算績效評價制度分配獎勵資金,從而推動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助力城市低保在救助深度和精度層面的提質增效。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而言,依據各地區財政實力、覆蓋人數等特征通過測算模型與低保標準,形成“標準型”“保障型”的央地財政分擔模式,在這些地區要堅持以中央支出責任為主導的支付方式,使中央轉移支付比例保持在60%以上,發揮拉平效應,增強低保救助的均等化水平。另外,設立低保資金監督機制以規避道德風險,避免地方財政產生“缺位”預警與地方政府出現“等靠要”行為,同時也要提高中央轉移支付的支撐與運作能力。對于“基本型”的央地財政分擔模式,應充分發揮“保基本”效能,實現“應保盡保”,同時克服由于低保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屬性所可能導致的“錯保”行為。
(二)合理劃分地方財政的支付責任,加強省級財政的預算統籌能力
如前文所述,省級城市低保財政支出與其財力水平不相協調,出現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高于省級的現象。省級財政支付責任缺位容易導致基層政府財政負擔過重,擠占其他公共服務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使用空間,可能引發舉債風險,不利于基層政府公共服務的合理、有序運轉。由此,可以根據各省域的實際財力,提高省級財政的預算統籌能力,緩解市級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責任分擔機制下,應加強省級財政支出力度,確立省級財政的主體責任,使其發揮全面統籌本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可將城市低保的省級財政負擔比例保持在20%以上,從而將基層政府的財政負擔由支出責任轉變為管理、監督責任,形成各級財政實力與低保工作責任相適應的應有局面。
(三)促進財政支付執行的規范化,健全城市低保救助的工作機制
在城市低保財政支付執行過程中,規范化管理程度越高,低保資金運行效率越高,低保救助運行成效就越好。首先,完善城市低保轉移支付制度,使中央轉移支付水平充分反映地方經濟實力、財力水平、覆蓋人數、低保標準等因素,合理測算各省域的中央轉移支付適度水平以適應地區實際情況。其次,在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框架體系下,為不斷縮小區域間待遇差距,應完善省級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在充分考慮基層政府的救助難度、人才需求、管理復雜程度等因素的基礎上,合理、公平支配省級財政的救助資金,使低保救助實現區域均衡,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再次,重視信息化平臺建設。減少因財政支出層級較多導致的管理成本增加、資金截留挪用問題;通過信息化平臺將低保救助均等化水平納入績效考核范圍內,增進各級民政部門、相關部門之間的配合、協作效果;通過低保戶誠信評估體系的建設,實現“動態準入與退出”機制,避免制度的“碎片化”。最后,完善責任追究制度,以確保上級政府不會因為利己原則出現博弈、推諉、轉嫁、攤派等不履行支出責任的行為,杜絕“人情保、關系保”,構建有力有效的監督格局。
(四)完善城市低保財政支付的保障機制,實現財政支出責任劃分的法定化
首先,我國城市低保關于財政支付方面的立法層次不高,支出責任劃分尚不清晰,由此,應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要以法律形式明確城市低保在央地之間、省級及以下政府之間的支出責任分擔比例,使各級財政各司其職,規避財政主體的隨意性,提升區域間的均等化水平。其次,在財政支出責任配置的法定化過程中,要避免“一刀切”性質的財政轉移支付,保障城市低保制度健康運行。最后,為充分發揮城市低保財政支付保障機制的作用,各級財政應嚴格遵守法律或政策規定,將執行標準落實到位,避免出現非理性的過度保障或福利趕超,實現橫向公平的應然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