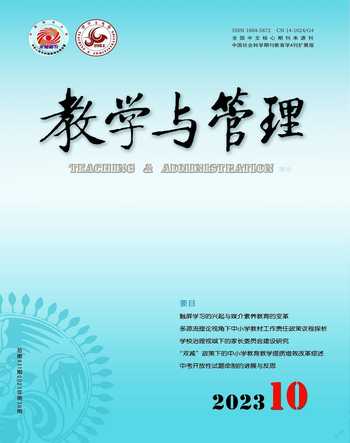“受教育者”與“學(xué)習(xí)者”之辨
摘? ? ? 要? 教育產(chǎn)生至今,有諸多對(duì)教育對(duì)象的稱呼。“諸生”“弟子”橫跨歷史,“學(xué)生”更是直到現(xiàn)在仍在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以來(lái),以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的《教育學(xué)》作為我國(guó)教育要素研究的開端,掀起了學(xué)界關(guān)于教育要素的討論。受時(shí)代趨勢(shì)影響,新的要素論接連被提出,教育對(duì)象的名稱存在“受教育者”和“學(xué)習(xí)者”兩種提法。“受教育者”背后有詞源學(xué)、心理學(xué)和邏輯學(xué)依據(jù)支持其存在,“學(xué)習(xí)者”背后的時(shí)代要求與社會(huì)需求也支持其存在。想要把握教育對(duì)象,需要從兩者的爭(zhēng)論中尋找對(duì)教育對(duì)象的普適性追求,最終落腳于對(duì)“人”的追求,即全面發(fā)展,終身學(xué)習(xí)和成為人本身。
關(guān) 鍵 詞? 受教育者? 學(xué)習(xí)者? 主體性? 人性假設(shè)
引用格式? 趙文藝.“受教育者”與“學(xué)習(xí)者”之辨[J].教學(xué)與管理,2023(30):7-12.
我國(guó)教育發(fā)展過(guò)程中,教育概念在不同時(shí)期有其時(shí)代特點(diǎn),對(duì)教育要素的看法也有時(shí)代印記。其中教育對(duì)象的界定從弟子到受教育者到人再到學(xué)習(xí)者,最后各種提法都共同存在。在教育要素論的發(fā)展中,最明顯且最關(guān)鍵的不同在于教育對(duì)象是“受教育者”還是“學(xué)習(xí)者”。不論是“受教育者”還是“學(xué)習(xí)者”,都是對(duì)教育對(duì)象的界定和描述,其變化有時(shí)代性,兩種提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性。通過(guò)對(duì)教育要素中“第二要素”的歷史梳理,分析“受教育者”與“學(xué)習(xí)者”的合理性,尋求教育對(duì)象的理想角色,厘清“受教育者”與“學(xué)習(xí)者”之間的關(guān)系,消解兩者之間的爭(zhēng)論。
一、教育對(duì)象的歷史演變
楊賢江曾說(shuō):自有人生,便有教育。探討教育對(duì)象的演變必須向前追溯到原始社會(huì),沿著歷史的軌道一路往下,直至今日,從歷史的演變中窺探教育對(duì)象的變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時(shí),在縱向?qū)徱暤倪^(guò)程中,不僅需要關(guān)注時(shí)代的主流需求,也需要關(guān)注教育對(duì)象內(nèi)涵的其他規(guī)定和主張,豐富教育對(duì)象的內(nèi)涵。
1.以“生”和“子”為指代:從重視到輕視的迭代過(gu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前的漫長(zhǎng)歷史時(shí)期,教育對(duì)象大多以“弟子,諸生,門生,學(xué)生”等為稱呼,對(duì)教育對(duì)象自主性和主動(dòng)性的認(rèn)知呈現(xiàn)由重視到輕視的迭代過(guò)程。在原始社會(huì)時(shí)期,教育產(chǎn)生于生產(chǎn)勞動(dòng)和社會(huì)生活之中,沒有文字和專門教育場(chǎng)所,教育者主要是婦女和老人,教育對(duì)象是年幼孩童,以勞動(dòng)經(jīng)驗(yàn)和生活經(jīng)驗(yàn)作為教育內(nèi)容[1]。教育對(duì)象受到社會(huì)的重視,其創(chuàng)造力也是社會(huì)所需要的重要財(cái)富。夏商時(shí)期,教育對(duì)象的范圍被縮小,聚焦于統(tǒng)治階級(jí)子弟。教育內(nèi)容也從生活經(jīng)驗(yàn)變?yōu)榱朔?wù)于政權(quán)統(tǒng)治的政治、軍事和倫理道德教育,教育對(duì)象受到教育目的的約束,并未被期望發(fā)展其他能力。這一時(shí)期教育對(duì)象范圍雖縮小,但教育者及社會(huì)對(duì)教育對(duì)象主體性和自主性并未比過(guò)去重視,甚至更為輕視。秦漢時(shí)期,法學(xué)、儒學(xué)思想輪流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三綱五常”的倫理制度賦予教育以時(shí)代標(biāo)簽。明清時(shí)期,教育氛圍被嚴(yán)重破壞,朝廷實(shí)行思想控制,屢興文字獄,對(duì)教育對(duì)象的禁錮達(dá)到頂峰。老師就是學(xué)生知識(shí)獲取的唯一渠道,儒學(xué)等官方知識(shí)對(duì)學(xué)生而言天生就是一種生疏的狀態(tài),而老師自然是以一種高姿態(tài)的狀態(tài)面向?qū)W生。此時(shí),教育對(duì)象的自主性被極大地壓制,話語(yǔ)權(quán)也被極大地剝奪。有不少學(xué)者批判傳統(tǒng)教育對(duì)教育對(duì)象主動(dòng)性的束縛: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是對(duì)弟子們自主性的肯定;顏元主張“習(xí)行”教學(xué)法,讓學(xué)生親自實(shí)踐來(lái)習(xí)得知識(shí),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生的主動(dòng)性和實(shí)踐性[5]。鴉片戰(zhàn)爭(zhēng)之后到新中國(guó)成立期間,思想涌現(xiàn),學(xué)者們各成一派,批判傳統(tǒng)教育的弊端,學(xué)生的力量被重視,學(xué)生的自主被關(guān)注。
2.“受教育者”主導(dǎo):從側(cè)重命名語(yǔ)義到追求多角度解釋
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不同學(xué)者在不同時(shí)期對(duì)“受教育者”的含義賦予不同意義。建國(guó)初期,我國(guó)各方面都向蘇聯(lián)學(xué)習(xí),教育上也如此,對(duì)“受教育者”的含義并沒有賦予新的意義。凱洛夫《教育學(xué)》未經(jīng)討論商定,就被作為當(dāng)時(shí)的教育學(xué)教材,書中對(duì)教育沒有明確定義,只將教育當(dāng)作反對(duì)剝削者斗爭(zhēng)的有力武器和建設(shè)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武器。1949年,加里寧提出:“教育是對(duì)于受教育者心理上所施行的一種確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統(tǒng)的感化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的心身上養(yǎng)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質(zhì)。”[3]這是我國(guó)最早接觸到的教育定義,首次將教育對(duì)象界定為“受教育者”。此時(shí)的“受教育者”只是作為與教育者邏輯對(duì)應(yīng)的對(duì)象,尚未被賦予更多的含義和意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之后,學(xué)者們重新活躍起來(lái),“受教育者”被增添了新的意味。第一種是在“受教育者”概念中加入主動(dòng)性色彩。有學(xué)者提出“三體論”,從教育認(rèn)識(shí)現(xiàn)象學(xué)的角度分析受教育者的地位,提出教育過(guò)程是受教育者的認(rèn)識(shí)過(guò)程,看到了受教育者的能動(dòng)作用即努力學(xué)習(xí)與善于接受教育者對(duì)自己施加的有利的影響,這其中已經(jīng)蘊(yùn)含了之后“學(xué)習(xí)者”所追求的意味[4]。特別是在新一輪基礎(chǔ)教育改革進(jìn)程下,學(xué)生主體性的發(fā)揮被作為改革目標(biāo),學(xué)者們都試圖挖掘受教育者的主動(dòng)性。鄭金洲《教育通論》和馮建軍第一版《現(xiàn)代教育學(xué)基礎(chǔ)》都對(duì)“受教育者”的內(nèi)涵做了進(jìn)一步揭示:受教育者看似處于被動(dòng)地位,但其積極主動(dòng)地參與才使教育活動(dòng)得以展開。第二種是在社會(huì)歷史背景和個(gè)體發(fā)展視野下看“受教育者”。1984年,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系出版的《教育學(xué)》中提出:“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會(huì)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計(jì)劃、有組織的影響,以使受教育者發(fā)生預(yù)期變化的活動(dòng)。”[5]書中指出,受教育者之所以作為教育實(shí)踐活動(dòng)的對(duì)象,是因?yàn)槿祟惿鐣?huì)發(fā)展規(guī)律和人的身心特性——受教性。
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系出版的《教育學(xué)》首次提出教育要素論——教育影響說(shuō),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與教育影響。之后,又出現(xiàn)了“二要素論”和“三要素論”,后者所討論的差異在于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外的第三種要素。在多要素論中,葉瀾、李德顯和李海芳等學(xué)者也將受教育者作為教育要素之一。其中,受教育者與教育者天然存在的成熟差被關(guān)注,兩者之間雙向建構(gòu)的關(guān)系被明晰,受教育者不再被一味放大其理想狀態(tài)的主動(dòng)性和自主性,而是將其放在真實(shí)情景中表達(dá)受教育者與教育者之間存在的雙向建構(gòu)關(guān)系[6]。既強(qiáng)調(diào)受教育者的受教性和受控性,也強(qiáng)調(diào)受教育者在教育過(guò)程中的主動(dòng)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育的主體[7]。有學(xué)者認(rèn)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為教育的基本要素。同時(shí),并不否認(rèn)學(xué)習(xí)者的存在,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視作社會(huì)的學(xué)習(xí)者,成為場(chǎng)景式學(xué)習(xí)的主體[8]。在這些重要的要素論中,受教育者因其獨(dú)特性和合理性而一直存在,受教育者在教育要素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3.“學(xué)習(xí)者”的出現(xiàn):從追求雙方抗衡到尋求進(jìn)階超越
1981年,《學(xué)生既是教育的客體,又是教育的主體》一文引起了教育界關(guān)于誰(shuí)是教育主體的爭(zhēng)論[9]。進(jìn)入21世紀(jì),有學(xué)者提出“泛教育理論”,認(rèn)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再絕對(duì),兩者都屬于教育主體。教育客體變成了一種中介而存在。教材和語(yǔ)言等被視作工具性教育客體,其指稱的是對(duì)象性教育客體即人的發(fā)展資源[10]。有學(xué)者提出重構(gòu)教育要素,提出新的三大要素包括教育主體、教育內(nèi)容和教育觀念,其中教育主體是指教育活動(dòng)中關(guān)于人的因素,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并將受教育者等同于學(xué)習(xí)者,是指以學(xué)習(xí)為主要任務(wù),在教育者的指導(dǎo)和影響下不斷發(fā)展和完善自我的人[11]。此處的“學(xué)習(xí)者”與“受教育者”尚且處于同等地位。
之后,學(xué)界中出現(xiàn)新的教育要素論,將“學(xué)習(xí)者”代替“受教育者”,顛覆了以往對(duì)教育要素的認(rèn)識(shí)。有學(xué)者認(rèn)為只有學(xué)習(xí)者在教育過(guò)程中起關(guān)鍵作用,而受教育者則難以發(fā)揮主動(dòng)性[12]。有學(xué)者從矛盾分析方法入手,指出教育活動(dòng)的根本矛盾即學(xué)習(xí)者與教育目的的矛盾,教育者是學(xué)習(xí)者與教育目的矛盾運(yùn)動(dòng)的產(chǎn)物[13]。把“受教育者”和“學(xué)習(xí)者”完全對(duì)立,認(rèn)為“受教育者”是完全的被動(dòng)存在,只有“學(xué)習(xí)者”這一概念才能彰顯和表示教育對(duì)象的主動(dòng)性。這一說(shuō)法將學(xué)習(xí)者地位大大提高,甚至超過(guò)教育者。對(duì)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從“受教育者”轉(zhuǎn)向“學(xué)習(xí)者”,是教育認(rèn)識(shí)深化的必然飛躍,并對(duì)轉(zhuǎn)向的原因進(jìn)行分析:第一,終身教育思潮的興起;第二,建構(gòu)主義對(duì)學(xué)習(xí)的全新詮釋;第三,社會(huì)開放環(huán)境下個(gè)體價(jià)值得到尊重[14]。在這一背景之下,馮建軍在第三版《現(xiàn)代教育學(xué)基礎(chǔ)》中對(duì)教育概念進(jìn)行了修改:“教育指根據(jù)一定社會(huì)要求,有目的有計(jì)劃有組織地影響人的身心發(fā)展,促使個(gè)體社會(huì)化和社會(huì)個(gè)性化的社會(huì)實(shí)踐活動(dòng)。”[15]此版中沒有明確提及“受教育者”,而是以“人”來(lái)替代,以此減少因“學(xué)習(xí)者”盛行而帶來(lái)的誤會(huì)。2014年,十二所重點(diǎn)師范大學(xué)聯(lián)合編寫的《教育學(xué)基礎(chǔ)》中明確提出將受教育者變?yōu)閷W(xué)習(xí)者,目的在于將教育對(duì)象看作主動(dòng)的存在,而非被迫接受教育者教育的人[16]。該書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當(dāng)時(shí)大多數(shù)學(xué)者的看法以及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認(rèn)同。“學(xué)習(xí)者”逐漸從大教育學(xué)領(lǐng)域進(jìn)入到教育學(xué)分支領(lǐng)域之中。有學(xué)者從教育技術(shù)領(lǐng)域和教育傳播領(lǐng)域都將學(xué)習(xí)者作為與教育者相對(duì)的教育要素,認(rèn)可學(xué)習(xí)者在教育領(lǐng)域中的必要地位[17,18]。無(wú)論是新的要素論和重要書籍的出版,還是“學(xué)習(xí)者”對(duì)教育領(lǐng)域越發(fā)細(xì)致的占領(lǐng),都表明“受教育者”的地位正在受到“學(xué)習(xí)者”的挑戰(zhàn)和威脅。
二、“受教育者”的存在依據(jù)
在“學(xué)習(xí)者”的進(jìn)攻下,仍然有學(xué)者堅(jiān)決捍衛(wèi)“受教育者”的地位。“受教育者”存在的長(zhǎng)期性和穩(wěn)固性讓其在“學(xué)習(xí)者”潮流中仍然保持強(qiáng)有力的地位,其背后必然有豐富的理論支撐與依據(jù),通過(guò)上述對(duì)“受教育者”的歷史梳理,可從詞源學(xué),心理學(xué)和邏輯學(xué)出發(fā),分析“受教育者”存在的合理性,為其提供理論依據(jù)。
1.詞源學(xué)中“受”的雙向過(guò)程
“教”在文字產(chǎn)生之初便蘊(yùn)含了教的對(duì)象——兒童,教的內(nèi)容——占卜,以及教育者。從最原始的含義中,可以明顯看到教育者與兒童之間是一種傳授的關(guān)系,兒童接過(guò)教育者所傳授的知識(shí)技能,此時(shí)的受是一種“接受”,但此處容易出現(xiàn)分歧,即接受的過(guò)程是否有兒童主動(dòng)性的參與。不摻雜后來(lái)學(xué)者的看法,單單從詞本身來(lái)看,“受”字看起來(lái)像兩只手傳遞東西,既然是傳遞東西,自然有給的一方和收的一方,若收的一方不伸出手拿,這個(gè)傳遞的過(guò)程便無(wú)法完成。只有教育者的引導(dǎo)和兒童主動(dòng)性的參與共同發(fā)揮作用才能使“受”的過(guò)程完整,也說(shuō)明了“受”也需要兒童發(fā)揮其主動(dòng)性。“學(xué)習(xí)者”的維護(hù)者對(duì)“受教育者”的批判主要是針對(duì)學(xué)生的主動(dòng)性缺失而提出,而對(duì)“受教育者”進(jìn)行詞源學(xué)分析可以看到其含義里并不否認(rèn)主動(dòng)性,只是部分人只看到給的一方,而忽視收的一方。如同《教育通論》中所指出的一樣:“受教育者居于第一位,沒有受教育者的存在,教育者也無(wú)用武之地。”[19]
2.心理學(xué)中“受”的主動(dòng)傾向
對(duì)“學(xué)習(xí)者”和“受教育者”的分歧主要在學(xué)生主動(dòng)性問題上,而學(xué)生是否主動(dòng),不同心理學(xué)流派對(duì)此都有不同的看法。接下來(lái)將會(huì)從不同流派分析“受教育者”所蘊(yùn)含的主動(dòng)性意味。
奧蘇貝爾的“意義接受理論”或許能夠?yàn)椤笆芙逃摺钡恼峁├碚撘罁?jù)。奧蘇貝爾將學(xué)習(xí)分為接受學(xué)習(xí)和發(fā)現(xiàn)學(xué)習(xí),機(jī)械學(xué)習(xí)和有意義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是否有意義,在于學(xué)習(xí)者是否有將新學(xué)的內(nèi)容與自己已有知識(shí)之間建立聯(lián)系的傾向及能力。也就是說(shuō),只要“受教育者”能夠?qū)⒁延兄R(shí)結(jié)構(gòu)和新的知識(shí)建立聯(lián)系,就是有意義學(xué)習(xí),也就發(fā)揮了受教育者的主動(dòng)性,不會(huì)因其是“接受”而喪失主動(dòng)性,也不需要按上“學(xué)習(xí)者”的名號(hào)。建構(gòu)主義強(qiáng)調(diào)雙方的社會(huì)文化互動(dòng),有學(xué)者以建構(gòu)主義為理論基礎(chǔ),從交往視域下看教育要素,認(rèn)為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有成熟差,兩者本來(lái)就是不完全平等的關(guān)系,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精神交往帶有個(gè)人特色的情感和態(tài)度,無(wú)論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對(duì)于教育而言都是未完成的存在,教育的過(guò)程也是主體間雙向建構(gòu)的過(guò)程,即受教育者和教育者都是教育的主體[20]。羅杰斯認(rèn)為人類具有學(xué)習(xí)的潛能,教師的任務(wù)是為學(xué)生提供學(xué)習(xí)的手段和場(chǎng)所,為學(xué)生提供安全的環(huán)境,學(xué)生就能夠更好地學(xué)習(xí)。在人本主義者看來(lái),“受教育者”本身就有學(xué)習(xí)的潛能和主動(dòng)性,只需要教育者提供安全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教育的過(guò)程便會(huì)產(chǎn)生。
3.邏輯學(xué)中“受”的邏輯自洽
教育者的含義一直沒有被質(zhì)疑,因此在討論是“學(xué)習(xí)者”還是“受教育者”時(shí),可以以教育者作為分析的依據(jù)之一。第一,從文字的表面含義來(lái)看,有施有受,有展開教育的一方,也就有接受教育的一方,教育者對(duì)應(yīng)的是受教育者,這是一對(duì)邏輯上自洽的概念。若硬要將“學(xué)習(xí)者”作為與“教育者”相對(duì)的概念,難免會(huì)引起歧義。第二,從文字的深層意義來(lái)看,學(xué)習(xí)者不僅包括受教育者,還包括教育者。三人行必有我?guī)煟總€(gè)個(gè)體都是在不斷學(xué)習(xí)、不斷成長(zhǎng)和發(fā)展的過(guò)程,既能成為教育他人的人,也能成為受他人教育的人。當(dāng)今社會(huì),終身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等教育理念層出不窮,更是要求每個(gè)人都要成為學(xué)習(xí)者,脫離簡(jiǎn)單的教育者與受教育者身份,將學(xué)習(xí)延伸到生命的盡頭。若簡(jiǎn)單將教育者與學(xué)習(xí)者相對(duì),作為一組概念,就導(dǎo)致了概念的混雜和對(duì)教育者的誤解。因此,從邏輯上講,與教育者最恰當(dāng)?shù)膶?duì)應(yīng)是受教育者。
三、“學(xué)習(xí)者”的存在依據(jù)
與“受教育者”不同,“學(xué)習(xí)者”作為一個(gè)新興詞匯,能夠突破重圍,成為諸多學(xué)者支持的教育對(duì)象,一定有其獨(dú)特的時(shí)代優(yōu)勢(shì)和特殊內(nèi)涵,有“受教育者”沒有的特性和優(yōu)勢(shì)。分析這一概念一定要將其放在歷史背景和社會(huì)環(huán)境之中,堅(jiān)持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才能真正理解其實(shí)質(zhì),發(fā)現(xiàn)其在社會(huì)背景下的意義。
1.時(shí)代發(fā)展的代名詞
1968年,羅伯特·赫欽斯提出“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緊接著,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國(guó)際教育發(fā)展委員會(huì)編寫《學(xué)會(huì)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命題》一書,倡導(dǎo)終身學(xué)習(xí)和創(chuàng)建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觀念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一觀念并非空穴來(lái)風(fēng),而是解決社會(huì)問題的一次嘗試。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信息時(shí)代的來(lái)臨,讓全球都面臨勞動(dòng)者的培養(yǎng)問題。勞動(dòng)者的素質(zhì)影響整個(gè)國(guó)家的發(fā)展,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讓勞動(dòng)者能夠充分發(fā)展其能力,盡最大力量開發(fā)人力資源,終身學(xué)習(xí)的勞動(dòng)者也為國(guó)家和社會(huì)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jià)值,“學(xué)習(xí)者”的號(hào)召與存在在這樣的時(shí)代背景下顯得格外重要。為跟上國(guó)際的步伐,中國(guó)也投身于“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浪潮中。2001年,出于對(duì)中國(guó)發(fā)展現(xiàn)狀的考慮和對(duì)未來(lái)發(fā)展的把握,江澤民提出“構(gòu)筑終身教育體系,創(chuàng)建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隨后的各類關(guān)于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談話也指明了中國(guó)教育未來(lái)發(fā)展的方向,一系列行動(dòng)在教育學(xué)界引起了廣泛關(guān)注,以“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為主題的文章數(shù)量在2001年后呈現(xiàn)爆發(fā)式增加。2002年,“人才強(qiáng)國(guó)”戰(zhàn)略的提出更是讓整個(gè)國(guó)家和社會(huì)陷入對(duì)人才的渴求,終身學(xué)習(xí)、終身教育、自我學(xué)習(xí)等觀念不斷發(fā)展,整個(gè)社會(huì)被學(xué)習(xí)熱情所籠罩。與此同時(shí),“學(xué)習(xí)者”作為教育對(duì)象的觀點(diǎn)也如雨后春筍,“學(xué)習(xí)者”成為這個(gè)時(shí)代趨勢(shì)下越發(fā)火熱的存在。“學(xué)習(xí)者”的存在,是對(duì)社會(huì)熱衷于學(xué)習(xí)的證明,是這個(gè)時(shí)代發(fā)展的代名詞,也是時(shí)代發(fā)展的需要。
在這個(gè)世紀(jì)之交的時(shí)刻,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幫助國(guó)家應(yīng)對(duì)新的挑戰(zhàn),助推小康社會(huì)的到來(lái),“學(xué)習(xí)者”作為教育領(lǐng)域中的新對(duì)象,也為整個(gè)教育的發(fā)展注入了新時(shí)代的色彩。
2.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主人公
任何歷史發(fā)展階段都有被稱為“主人公”的存在,但其對(duì)象和范圍受社會(huì)制度所制約。在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的中國(guó),尤其在進(jìn)入21世紀(jì)之后,整個(gè)社會(huì)以建設(shè)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為目標(biāo),力圖讓人人都成為學(xué)習(xí)者,人人都是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主人公,不受階層的約束,每個(gè)人都有為社會(huì)創(chuàng)造巨大價(jià)值的可能,有學(xué)者認(rèn)為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是一個(gè)“以學(xué)習(xí)求發(fā)展的社會(huì)”[21]。在這個(gè)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中,單個(gè)的人和群體組織都是“學(xué)習(xí)者”,個(gè)體是尋求自我能力發(fā)展的“學(xué)習(xí)者”,組織和國(guó)家是尋求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學(xué)習(xí)者”,他們主動(dòng)學(xué)習(xí)以求得自我的發(fā)展、組織的發(fā)展和國(guó)家的發(fā)展,這是整個(gè)社會(huì)的發(fā)展。作為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主人公,“學(xué)習(xí)者”在用自己的力量充實(shí)這個(gè)社會(huì),為這個(gè)社會(huì)注入新的力量。從社會(huì)領(lǐng)域聚焦到教育領(lǐng)域,教育對(duì)象也是“學(xué)習(xí)者”,每一個(gè)“學(xué)習(xí)者”都在學(xué)習(xí)如何學(xué)習(xí)。
“學(xué)習(xí)者”的出現(xiàn)并非是要掩蓋或替代“受教育者”的存在,相反,是為了在新時(shí)代來(lái)臨之際突出“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同時(shí)強(qiáng)化教育者的學(xué)習(xí)者身份。“受教育者”是歷史發(fā)展的結(jié)局,“學(xué)習(xí)者”是時(shí)代發(fā)展的需要,兩者并非矛盾,只是不同立場(chǎng)下的觀點(diǎn)差異,或是不同背景下的真相差異,沒有對(duì)錯(cuò)之分。
四、對(duì)于教育對(duì)象本質(zhì)的多維探索
人是什么是教育的第一問題[22]。回顧過(guò)去關(guān)于教育對(duì)象是“受教育者”還是“學(xué)習(xí)者”的爭(zhēng)論,發(fā)現(xiàn)這些爭(zhēng)論都在回答“教育對(duì)象是什么”,不同的稱呼反映不同的歷史社會(huì)背景,也反映不同的教育觀念。與“學(xué)生”“弟子”等稱呼相比,“受教育者”和“學(xué)習(xí)者”是對(duì)教育主體更為平等的表述,避免了學(xué)生和弟子中天然便帶有的對(duì)教育對(duì)象的輕視,以更民主的姿態(tài)走近教育對(duì)象。與受教育者相比,學(xué)習(xí)者更貼合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的內(nèi)涵和要求,指向所有接受教育的人。同時(shí),受教育者本身就是學(xué)習(xí)的主體,在教育過(guò)程中不斷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者的學(xué)習(xí)過(guò)程也是在接受教育的過(guò)程。從這些爭(zhēng)論中不難得出有關(guān)教育對(duì)象的共識(shí):教育對(duì)象是終身學(xué)習(xí)、全面發(fā)展的人。
1.時(shí)間維度:終身學(xué)習(xí)者
21世紀(jì)的中國(guó)要建設(shè)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的每個(gè)人都是學(xué)習(xí)者,每個(gè)場(chǎng)所都是教育場(chǎng)所。終身學(xué)習(xí)者從字面上來(lái)看,包括“終身”和“學(xué)習(xí)”兩個(gè)關(guān)鍵詞。終身即從出生到死亡的整個(gè)生命全程,學(xué)習(xí)包括學(xué)會(huì)與自我相處,與他人相處以及與自然相處。一個(gè)人出生后進(jìn)入家庭場(chǎng)域,成為家庭教育的學(xué)習(xí)者。個(gè)體離開家庭場(chǎng)域,進(jìn)入學(xué)校場(chǎng)域之后,成為學(xué)校教育的學(xué)習(xí)者。個(gè)體離開學(xué)校場(chǎng)域,又進(jìn)入社會(huì)場(chǎng)域,成為專門的勞動(dòng)者,同時(shí)也是社會(huì)教育的學(xué)習(xí)者。社會(huì)教育是一種真正的實(shí)踐,是從理論的象牙塔中走出,踏入真實(shí)的世界。此時(shí),學(xué)習(xí)者深受新環(huán)境的影響,一種未知的恐懼督促學(xué)習(xí)者不斷學(xué)習(xí),增強(qiáng)自身能力,才能避免被時(shí)代拋棄。同時(shí),這三個(gè)場(chǎng)域相互聯(lián)系,共同作用。
從出生到死亡,從無(wú)知到知曉自己無(wú)知,人永遠(yuǎn)都是學(xué)習(xí)者,終其一生都在學(xué)習(xí)。雖有學(xué)者批判這種終身學(xué)習(xí)思潮,認(rèn)為這種觀念是將人束縛在不得不學(xué)習(xí)的社會(huì)潮流之中,將學(xué)習(xí)從一種權(quán)利變成了一種義務(wù)[23]。但在整個(gè)社會(huì)主流思想中,終身學(xué)習(xí)仍然是積極正向的途徑與方式。
2.內(nèi)容維度:全面發(fā)展者
馬克思從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界定人的全面發(fā)展,認(rèn)為人的全面發(fā)展是人的品質(zhì)和才能的和諧發(fā)展[24]。2021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教育法》規(guī)定:“教育必須為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服務(wù)、為人民服務(wù),必須與生產(chǎn)勞動(dòng)和社會(huì)實(shí)踐相結(jié)合,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者和接班人。”[25]官方將全面發(fā)展解釋為“德智體美勞”各方面的和諧發(fā)展。從更宏大視野出發(fā),有學(xué)者認(rèn)為,個(gè)人的全面發(fā)展是將勞動(dòng)腦力化,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自由個(gè)性”,強(qiáng)調(diào)消除勞動(dòng)分工,消除階級(jí)基礎(chǔ)[26]。除了全面發(fā)展的概念分析,全面發(fā)展的實(shí)現(xiàn)途徑也十分豐富。在教育學(xué)范疇內(nèi)看全面發(fā)展,人的全面發(fā)展更多落腳于具體個(gè)人與自己、他者和自然的關(guān)系問題。在個(gè)體與自己的關(guān)系上,有學(xué)者提出借助“五育融合”助推全面發(fā)展,五育融合是全面發(fā)展理念的實(shí)踐需要,是實(shí)現(xiàn)育人的整體化和個(gè)體發(fā)展的全面化的重要途徑[27]。除內(nèi)容的全面性,通過(guò)生產(chǎn)力的提高為勞動(dòng)者提供更多自由時(shí)間,通過(guò)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改革為勞動(dòng)者更公平地分配自由時(shí)間,激發(fā)勞動(dòng)者自身的主體性以合理安排時(shí)間,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28]。在個(gè)人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上,可借助薩特提出的“他者注視”,尋求個(gè)體自由發(fā)展。薩特認(rèn)為他者的注視會(huì)改造“我本身”,并且改變世界。而“我”也成為被注視的對(duì)象,而非主體[29]。為避免陷入這種“他者注視”之中,個(gè)體在與社會(huì)和他人的問題解決中需要以主體性的姿態(tài)展現(xiàn),以主體的方式出現(xiàn)在與他人的關(guān)系之中,才能避免將為我變成為他,避免用他者的標(biāo)準(zhǔn)評(píng)判自我,陷入他者的思維之中[30]。因此,全面發(fā)展者是具有主體性的個(gè)體,在與他人的相處中,掌握自己世界的主動(dòng)權(quán),主動(dòng)掌控這段關(guān)系的走向。正如王策三教授所言,“主體性是全面發(fā)展的人的根本特征”[31]。在個(gè)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上,個(gè)體無(wú)法與自然相抗衡,順應(yīng)自然、保護(hù)自然才是唯一選擇。同時(shí),自然為個(gè)體提供發(fā)展的場(chǎng)地和空間,允許個(gè)體能夠在不破壞自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發(fā)展。
不同于過(guò)去職業(yè)之間的相對(duì)封閉性,信息社會(huì)的發(fā)展和工業(yè)結(jié)構(gòu)的更新帶來(lái)了更多的新興職業(yè),也要求勞動(dòng)者掌握更多的技能,能夠滿足社會(huì)對(duì)多種人才要求,實(shí)現(xiàn)不同崗位之間的流動(dòng)。各國(guó)也都在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中勞動(dòng)者的培養(yǎng)和教育,通過(guò)提高勞動(dòng)者的素質(zhì),提升國(guó)民的整體素質(zhì),借此促進(jìn)國(guó)家和社會(huì)的發(fā)展。
3.中心定位:作為實(shí)踐者和主動(dòng)者的人
無(wú)論教育對(duì)象有何種外在表征和特質(zhì),探討教育對(duì)象的狀態(tài)必須回歸教育對(duì)象的根本屬性“人”,從人性的視角討論教育對(duì)象。人性觀影響教育觀的選擇,回答教育問題首先需要明確教育中的人性假設(shè)[32]。長(zhǎng)期以來(lái),教育缺乏與人的溝通,教育對(duì)象被物化,教育的社會(huì)價(jià)值遠(yuǎn)遠(yuǎn)高于個(gè)體價(jià)值,社會(huì)的人性觀和教育觀嚴(yán)重偏離人性。20世紀(jì)90年代末,學(xué)界對(duì)這種現(xiàn)狀提出了反思,有學(xué)者認(rèn)為人是實(shí)然與應(yīng)然的統(tǒng)一。一方面,人客觀的受到外在環(huán)境制約和規(guī)定,另一方面,人具有主觀性,表現(xiàn)為為自身而存在。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就在于培養(yǎng)人的應(yīng)然性,鼓勵(lì)人對(duì)現(xiàn)有狀態(tài)的擊破,達(dá)成實(shí)然與應(yīng)然的統(tǒng)一[33]。教育所面向的對(duì)象是具有兩重性的人,教育的目標(biāo)是激發(fā)人對(duì)理想的追求[34]。2010年,有學(xué)者提出實(shí)踐人的人性假設(shè)說(shuō)。無(wú)論是將人物化或者將人神化都是將人性看作不變的本性。人性具有復(fù)雜性,既有物性又有超物性,既是生命存在又具有超生命本質(zhì),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實(shí)踐性[35]。同時(shí),人是社會(huì)活動(dòng)中的主體,既有自主活動(dòng)的能力,也受歷史條件的制約,人性具有一定的社會(huì)歷史性,是一種動(dòng)態(tài)變化之物,而非一層不變的既定物,考慮人性假設(shè)時(shí)需要將其放入流動(dòng)的水中,用活水充盈人性假設(shè)。
無(wú)論是“應(yīng)然與實(shí)然”的人性假設(shè)說(shuō)還是“實(shí)踐人”的人性假設(shè)說(shuō),都在指明一個(gè)方向:教育對(duì)象所指向的是人,且是具備主動(dòng)性,實(shí)踐性的積極個(gè)體。無(wú)論外界對(duì)教育對(duì)象賦予何種期望和價(jià)值,教育對(duì)象本身就是以這樣一種形象出現(xiàn)。“受教育者”和“學(xué)習(xí)者”,歸根結(jié)底是對(duì)教育對(duì)象的一種規(guī)定性要求,因?yàn)橐暯堑牟煌玫搅藘煞N稱謂,但指向的仍然是人,只要抓住了教育對(duì)象的本質(zhì),即具有主動(dòng)性、實(shí)踐性的積極個(gè)體,何種稱謂也不影響其內(nèi)涵。
“受教育者”與“學(xué)習(xí)者”之辨,歸根到底是學(xué)者和社會(huì)對(duì)學(xué)生主體性的追求所致,對(duì)于主體性的爭(zhēng)論,輿論上曾被當(dāng)作是解決教與學(xué)矛盾的方法,但解決教與學(xué)的內(nèi)在矛盾是需要從課程選擇中尋找出路[36]。因此,我們或許應(yīng)該轉(zhuǎn)變思路,不再過(guò)多糾結(jié)于學(xué)生到底是主體還是客體,到底是被動(dòng)還是主動(dòng),因?yàn)檫@對(duì)解決目前教與學(xué)之間的矛盾無(wú)濟(jì)于事。
參考文獻(xiàn)
[1] 王凌皓主編.中國(guó)教育史綱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3.
[2] 孫培青主編.中國(guó)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292.
[3] 加里寧.論共產(chǎn)主義教育[M].莫斯科:外國(guó)文書籍出版局,1949:88.
[4] 于光遠(yuǎn).教育認(rèn)識(shí)現(xiàn)象學(xué)中的“三體問題”[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1980(03):79-95.
[5] 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系.教育學(xu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9.
[6][20] 李德顯,李海芳.論交往視域下的教育要素[J].教育學(xué),2013,29(02):1-6.
[7] 廖小琴.思想政治教育過(guò)程要素再探究[J].思想教育研究,2022(01):28-34.
[8] 陳耀華,陳琳,姜蓉.發(fā)展場(chǎng)景式學(xué)習(xí)促進(jìn)教育改革研究[J].中國(guó)電化教育,2022(03):75-80.
[9] 顧明遠(yuǎn).學(xué)生既是教育的客體,又是教育的主體[J].江南教育,1981,10(01):6-26.
[10] 項(xiàng)賢明.泛教育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32-35.
[11] 張國(guó)霖.重構(gòu)“教育要素”及其實(shí)踐意義[J].當(dāng)代教育科學(xué),2007(09):9-11.
[12] 趙儒彬.學(xué)習(xí)要素與教育要素:教育的四要素[J].太原教育學(xué)報(bào)2005(02):6-10.
[13] 馬前.教育要素的矛盾視角分析[J].西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8(06):213-217.
[14] 沈俊強(qiáng).再論“教育要素”:新一輪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背景下的重新解讀[J].上海教育科研,2006(04):17-19.
[15] 馮建軍.現(xiàn)代教育學(xué)基礎(chǔ)[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3.
[16] 全國(guó)十二所重點(diǎn)師范大學(xué)聯(lián)合編寫.教育學(xué)基礎(chǔ)[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14:6.
[17] 馬啟龍.從教育技術(shù)學(xué)的視角看教育要素[J].中小學(xué)教師培訓(xùn),2015(01):5-9.
[18] 馬啟龍.教育傳播的類型、定義及要素論析[J].文化與傳播,2018,7(02):23-28.
[19] 鄭金洲.教育通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0:10.
[21] 顧明遠(yuǎn),石中英.學(xué)習(xí)型社會(huì):以學(xué)習(xí)求發(fā)展[J].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01):13.
[22] 張楚廷.教育哲學(xué)[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2006:26.
[23] 比斯塔.教育的美麗風(fēng)險(xiǎn)[M].趙康,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8:99.
[24] 許征帆主編.馬克思主義辭典[M].長(zhǎng)春: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1987:33-34.
[25] 新華社.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關(guān)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教育法》的決定[EB/OL].(2021-04-29)[2023-04-05].http://www.gov.cn/xinwen/2021-04/29/content_5603947.htm.
[26] 余金成.馬克思“個(gè)人全面發(fā)展”理論的兩種思路及其當(dāng)代釋讀[J].當(dāng)代世界與社會(huì)主義,2021(04):74-82.
[27] 朱麗楨,段兆兵.從并舉到融合:“五育”融合之源、之難與之序[J].教育理論與實(shí)踐,2022,42(22):3-8.
[28] 孟瑞霞.馬克思的正義理論:時(shí)間正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J].理論視野,2022(02):26-31.
[29] 薩特.存在與虛無(wú)[M].陳宜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338-339.
[30] 李海春.淺析馬克思的教育觀:朝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發(fā)展”[J].人民教育,2018(09):39-43.
[31] 王策三.教育主體哲學(xué)芻議[J].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4(04):80-87.
[32] 王坤慶.關(guān)于人性與教育關(guān)系的探討[J].教育研究與實(shí)驗(yàn),2007(03):3-6.
[33] 魯潔.實(shí)然與應(yīng)然兩重性:教育學(xué)的一種人性假設(shè)[J].華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教育科學(xué)版,1998(04):1-8.
[34] 魯潔.培養(yǎng)有理想的人:世紀(jì)之交對(duì)德育的一點(diǎn)思考[J].教育研究與實(shí)驗(yàn),1999(02):1-3+72.
[35] 馮建軍.實(shí)踐人:生活德育的人性之基[J].高等教育研究,2010(04):20-27.
[36] 陳桂生.教育學(xu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教育學(xué)辨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