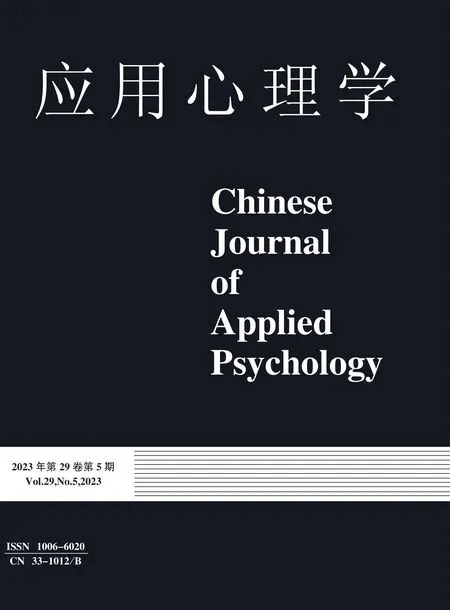朝向集體主義和保守主義:病原體對文化演化的影響*
陳維揚 謝 天
(1.西南財經大學社會發展研究院,成都 611130;2.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武漢430072)
1 引 言
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是將生物演化原則應用到文化變遷上的新興研究領域。在文化演化的理論框架中,文化被認為是人們對生態挑戰的反應(Kusano&Kemmelmeier,2018),是環境選擇的產物(Sng et al.,2018),也是對特定生態條件的適應性結果(Berry,2002)。
文化演化領域內部存在不同的理論視角。比如,生態視角是從生態環境因素出發,探究不同環境因素(如氣候、地形、種植方式等)對文化演化的影響(竇東徽等,2014)。認知視角是從個體社會學習出發,探究文化演化過程中人的認知機制(陳維揚,謝天,2020)。病原體視角的關注點是可造成人或動植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包括細菌、病毒等)、寄生蟲或其他媒介——病原體對文化的影響。當下引發新冠疫情的冠狀病毒就是一種病原體。病原體是進化史中人類發病和死亡的主因,扮演著自然選擇手段的角色(Volk&Atkinson,2013)。Diamond(1999)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也濃墨重彩地分析了病原體對文化、社會跨越千百年的劇烈影響:傳染病對于歐洲人征服美洲起到了十分顯著的作用。
由此觀之,病原體視角的文化演化研究有趣且重要,值得繼續深入探究。首先,從病原體的視角解釋文化演化,具有反常識性,顯示了病原體的“四兩撥千斤”之勢,因而有趣。同時,該視角還能幫助我們預測新冠疫情如何影響文化演化,因而重要。本文通過梳理已有研究,指出病原體影響文化演化的兩個側面——集體主義與保守主義,并在此基礎上展望這一領域的未來發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集體主義與保守主義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就區別而言,集體主義強調人的互依性、社會嵌入性以及對內群體(如家庭、家族)的義務與忠誠(Oyserman et al.,2002)。保守主義將安全置于自由之上,既通過更謹慎的行為、更強的社會管控保障人們的生存安全感(existential security),也通過維持傳統規范、強調等級秩序保障人們的認識論安全感(epistemic security),集中體現為對變革的抗拒和對權威的認同(Jost et al.,2003)。簡言之,集體主義更強調集體尤其是內群體的團結(Oyserman et al.,2002),協調一致是關鍵詞;保守主義更強調傳統和權威(Jost et al.,2003),保障安全是關鍵詞。在病原體視角下,保守主義本身強調安全、謹慎,可看作是對于病原體威脅的個體應對,而集體主義可看作是集體應對。就聯系而言,第一,持有保守主義價值觀的個體在遵循社會規范、傳統時提升了內群體的凝聚力(Altemeyer,1988),更好地區分了內外群體成員,使內群體利益最大化(Triandis,1994),因而增強了集體主義。第二,集體主義可進一步劃分為水平的(horizontal)和層級的(vertical)集體主義,前者強調群體成員間的平等關系,與保守主義的聯系較弱;而后者強調社會等級的必要性(Singelis et al.,1995)。由于等級與保守主義強調權威相呼應,因而層級的集體主義更偏保守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聯系更緊密(Terrizzi et al.,2013)。
2 病原體的界定
在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對病原體的界定可分為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客觀指標通過病原體(或傳染病)流行率測量,其理論基礎是價值觀的寄生蟲壓力理論(the parasite-stress theory of values)。該理論認為,價值觀是引導人們認知與行為的核心信念,不同時空價值觀的差異受制于當時當地的寄生蟲壓力狀況(Thornhill&Fincher,2014)。具言之,當某地寄生蟲壓力增加時,在心理層面,外群體成員會被感知為更加危險,因為他們可能是潛在的傳染源,而內群體成員的合作與支持有助于抵消寄生蟲帶來的負面影響。在行為層面,內群體成員會通過避免與新異刺激或外群體接觸來降低感染傳染病的風險,最終演化出更保守和集體主義的文化。反之,當某地寄生蟲壓力減輕時,與外群體的接觸能夠提供新觀念、新技術、更廣泛的社交網絡,為個體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利益,于是演化出更自由和個體主義的文化,如鼓勵創新、歡迎移民等。寄生蟲壓力通常用某地區歷史上和當代的傳染病流行率測量。如根據155 個國家傳染病流行率歷史數據計算出的各國傳染病歷史流行指數(historical prevalence index of infectious diseases,Murray&Schaller,2010)以及通過世衛組織官網或GIDEON①全稱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Epidemiology Network,其官方網站為www.gideononline.com。數據庫獲得(Fincher&Thornhill,2012)的傳染病流行率的具體統計數據。
主觀指標通過感知到的疾病易感性(perceived vulnerability to disease,PVD)測量,其理論基礎是行為免疫系統理論。行為免疫系統(behavioral immune system,BIS)是人們面對病原體威脅除了生理免疫系統之外的又一系統,是人們為抵御疾病而演化出的一系列心理過程,核心內容是人們會盡量遠離可能的感染源,將感染風險最小化(Schaller& Duncan,2007)。關于行為免疫系統的具體內容,不少國內外研究者都曾詳細介紹過(e.g.Schaller & Park,2011;Ackerman et al.,2018;Shook et al.,2018;吳寶沛,張雷,2011;楊盈等,2020)。病原體的主觀指標測量的是人們對病原體威脅的感知,研究中使用最廣泛的是感知到的疾病易感性量表(Duncan et al.,2009),該量表共15 個項目,分為病菌厭惡(germ aversion,GA) 和感知感染(perceived infectability,PI)兩個分量表。前者測量個體對可能存在病菌的不適感(如“我不喜歡用別人嘴咬過的鉛筆書寫”);后者測量個體自我判斷感染傳染病的可能性(如“我比周圍人更容易得傳染病”)。
3 病原體促使文化向集體主義發展
關于集體主義,本研究選取了三個方面的內容:集體主義價值觀、從眾、外群體排斥。集體主義價值觀屬于集體主義自不必說;從眾是集體主義的典型表現(Terrizzi et al.,2012);外群體排斥以及相對的內群體偏好更是集體主義的應有之義(Oyserman et al.,2002)。集體主義價值觀、從眾與外群體排斥,都是群體協調一致的表現,因此同屬集體主義。
在集體主義/ 個體主義相關研究中,區分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個體層面研究多基于自我報告或在實驗中表現的行為而開展,而社會層面的研究多基于文化產品或社會指標展開。某個層面的結論未必能推廣到另一層面,如果不加思考地推廣,容易犯生態謬誤或個體謬誤(Na et al.,2010)。
3.1 集體主義價值觀
一個地區的傳染病流行率越高,越容易演化出集體主義價值觀。其中與他人分享共同目標、相互依靠并合作、集體凝聚力是傳染病疫情中人們的重要保護因素。Nikolaev 等人(2017)將傳染病歷史流行指數(Murray&Schaller,2010)與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數據②數據來自網站geert-hofstede.com。(Hofstede et al.,1991)做匹配③該研究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測量是在Hofstede 等人(1991)框架下進行的,因而將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看作一個維度的兩端。,并做回歸分析,發現一個國家在歷史上的傳染病流行指數正向預測集體主義水平,負向預測個體主義水平。該研究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測量是在Hofstede等人(1991)框架下進行的,關注的是國家層面的集體主義,屬于社會層面的研究。下面的兩項研究是面向個體的問卷調查,屬于個體層面的研究。Germani 等人(2020)通過網絡問卷調查了2020 年3 月意大利青年對感染新冠風險的感知(病原體的主觀指標)、集體主義/個體主義價值觀①該研究以及下文Ahuja 等人(2021)的研究中,對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測量就是分別進行的,其構念的理論基礎就認為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是不同的兩個維度。,同時也測量了焦慮、壓力等心理不適應的后果變量,發現個體感知的感染風險正向預測集體主義價值觀水平,而集體主義可以負向預測心理不適應程度。Ahuja 等人(2021)通過網絡問卷調查了印度被試對新冠病毒的害怕程度、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心理幸福感,發現個體對新冠病毒的害怕程度正向預測集體主義價值觀水平,而集體主義又可以正向預測其心理幸福感水平。
除了問卷調查,還有研究者基于社交媒體數據(微博)分析了2019 年12 月1 日到2020 年2 月16 日微博文本(分成前后兩段,以2020 年1 月20 日為界)中人稱代詞、群體相關名詞、關系相關名詞的詞頻變化。發現后段相比前段:復數人稱代詞、群體相關名詞、關系相關名詞均顯著增加。而三者都是集體主義的測量指標。這說明隨著疫情的加劇,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水平顯著上升了(Han et al.,2021)。
3.2 從眾行為
從眾指的是個體與內群體規范保持一致。病原體水平越高的區域,人們會越遵守內群體規范,表現為從眾。就社會層面的研究而言,Horita 和Takezawa(2018)利用傳染病歷史流行指數(Murray & Schaller,2010) 和世界價值觀問卷(World Values Survey,WVS,1981-2008)中關于從眾的4個條目,探討不同國家或地區病原體流行率對從眾的影響。回歸分析顯示,病原體流行率可正向預測從眾水平;當將不同因素納入考量并對干擾變量施加統計控制時,與朋友相關的從眾更具跨文化穩健性。
就個體層面的研究而言,研究者還測量了加拿大被試感知到的疾病易感性以及他們自我報告的從眾水平,發現疾病易感性中僅病菌厭惡子維度能顯著正向預測從眾水平。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還通過給被試展示與病原體相關的刺激圖片啟動病原體威脅,結果證實了病原體對從眾的因果關系(Murray&Schaller,2012)。另一項面向中國被試的研究顯示,疾病易感性的兩個子維度都可以顯著預測被試的從眾水平,實驗組被試對現代藝術作品評分時比控制組被試更易受他人意見的影響(Wu&Chang,2012)。
在新冠病毒暴發期間(2020 年2 月1日—2 月20 日),研究者利用問卷星收集了我國被試感知到的新冠威脅(如“你在多大程度上害怕新冠病毒”“你覺得感染新冠的風險有多大”)、從眾消費行為(如“我最近的購物決策很大程度上受專家建議的影響”)、歸屬感、物質主義價值觀等數據,結果顯示,感知到的新冠威脅正向預測被試的從眾消費行為,歸屬感與物質主義在其中起中介作用(Song et al.,2020)。在近乎同一時間,另一組研究者利用見數(Credamo)收集數據,用感知到的新冠威脅和客觀的確診病例數同時預測從眾消費行為,顯示確診病例人數正向預測從眾消費行為,而感知到的新冠威脅在其中起中介作用(Li et al.,2021),這啟示我們病原體的客觀指標通過主觀指標對從眾行為起預測作用。
3.3 外群體排斥
病原體威脅的增加會增強外群體排斥。就個體層面的研究而言,Laakasuo 等人(2017)告訴實驗組被試某島國暴發瘟疫亟須救助,告訴對照組該島國發生饑荒、島民患癌癥等非傳染性災難,然后測量被試的道德水平及人道主義援助意愿(包括錢物支援和派本國技術人員人力支援),結果發現實驗組被試中道德水平越高的被試越傾向于錢物支援而非人力支援,在對照組中則無此差異。這反映了人們對人力支援可能會將傳染病帶到本國的擔心。接著研究者增加了感知到的疾病易感性(PVD)變量,發現病菌厭惡(GA)子維度直接預測實驗組更高的錢物支援意愿,進一步驗證了病原體環境下人們更加避免與外群體接觸的結論。在另一項社會層面的研究中,Adam-Troian 和Bagci(2021)關注新冠背景下,土耳其人所遭受病毒威脅與對移民的態度之間的關系,他們利用谷歌趨勢數據①谷歌趨勢提供了不同地理區域搜索詞的詞頻。Google Trends data)建構了疾病威脅指數和反移民態度指數,同時還搜集了各省的新冠病例數。結果發現,相比新冠病例數據,利用谷歌趨勢建構的新冠病毒威脅指數更能正向預測人們的反移民態度。
不過,也有研究發現病原體流行率的上升不一定會增加對外群體的敵意,為探索病原體威脅增加外群體排斥的邊界條件提供了線索。Zhu 等人(2021)利用最新的世界價值觀量表數據(第6 波,數據來自2010—2014 年)構建了54 個國家或地區的傳染病致死指數、內/外群體信任指數,結果發現傳染病致死指數僅能負向預測內群體信任,而不能預測外群體信任。研究者認為當傳染病來襲時,內群體比外群體更危險,因為人們更多與內群體交往,從內群體身上傳染的概率更大。此外,Zhang(2018)發現傳染病壓力指數與外群體信任呈“U”型相關,相比低/高傳染病流行率國家,中等程度傳染病壓力的國民更少信任外群體。研究者的解釋是當傳染病流行率特別高時,人們唯有不分群體界限,聯合應對才能克服挑戰。因此,如果病原體威脅已經嚴重到波及內群體本身時,病原體威脅與外群體排斥之間的正向預測關系可能就會被改變。
4 病原體促使文化向保守主義發展
關于保守主義,本研究選取了對傳統價值觀的偏好、預防性健康行為以及政治保守主義。維護傳統價值觀是保障群體認識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因此傳統價值觀偏好是保守主義的重要方面(Thornhill et al.,2009);預防性健康行為保障的是人們的生存安全感,符合保守主義對安全的重視(Jost et al.,2003);政治保守主義是保守主義在政治態度方面的表現(Terrizzi et al.,2013)。
4.1 對傳統價值觀的偏好
傳統價值觀偏好是對長期以來已存在事物或價值觀念的偏好,與創新價值觀相對。寄生蟲壓力較高區域會演化出更擁護傳統的價值觀,因為傳統意味著熟悉,熟悉帶來認識論安全感。Rosenfeld 和Tomiyama(2021) 利用網絡問卷發放平臺(Amazon Mechanical Turk)追蹤了世衛組織宣布新冠大流行前后(第一波:2020 年1 月25—26日;第二波:3 月19 日—4 月2 日),美國被試對新冠病毒的擔心、對性別刻板印象的認同。發現相比第一波,在第二波時,被試對新冠的擔心程度和對性別刻板印象的認同程度都顯著增強,說明疫情促進了人們對傳統性別角色的偏好。Bennett 和Nikolaev(2021)對傳染病歷史流行指數(Murray& Schaller,2010)、全球創新指數(Dutta et al.,2018)以及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指數(Hofstede et al.,2005)間的關系分析,發現某國歷史上的傳染病流行率越高,則創新指數越低,價值觀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此外,某地的病原體壓力也可通過建立不斷完善的衛生保健系統而降低,如盡管中國在歷史上屬于傳染病較為流行的國家(Murray&Schaller,2010),但隨著衛生事業取得的長足進步,現在的傳染病流行率已處于較低水平,創新能力也排到全球前10%,為全球貢獻了中國智慧。研究者認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這一做法(Bennett&Nikolaev,2021)。
4.2 預防性健康行為
預防性健康行為保障的是人們的生存安全感。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保持社交距離都屬于預防性健康行為。研究者們針對新冠病毒與預防性健康行為的關系展開了許多研究。Shook等人(2020)于2020 年3 月利用網絡實驗平臺(Qualtrics),收集了美國被試感知到的疾病易感性(PVD)、對新冠病毒的擔心、預防性健康行為等數據。回歸分析顯示,感知到的疾病易感性中的病菌厭惡預測了對新冠病毒更高的擔心水平、更頻繁的預防性健康行為(僅戴口罩除外)。這說明個體行為免疫系統越敏感,就越擔心新冠病毒,越傾向于采取更頻繁的預防措施。但為什么戴口罩除外呢?研究者認為在數據收集期間,疾控中心僅建議懷疑自己感染的個體佩戴口罩(戴口罩并非預防性質),而4 月3 日開始,疾控中心才推薦每人都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此時戴口罩才為預防性質)。Olivera-La Rosa 等人(2020)也于新冠大流行期間使用網絡實驗軟件(Psytoolkit),測量了哥倫比亞、秘魯等西語南美國家被試的病原體厭惡敏感性,并讓實驗組/控制組觀看戴口罩/ 未戴口罩者的圖片,最后讓他們判定對圖片人物的信賴程度并推測其健康狀況。結果顯示,高厭惡敏感性的個體會更少信任圖片人物;相比不戴口罩,戴口罩者更容易使人聯想到患病和值得信賴。患病和值得信賴似乎很難相提并論。研究者的解釋是,佩戴口罩既對自己負責也對他人負責,是新冠疫情下的新規范,所以值得信賴,但佩戴口罩與患病相連這種傳統的聯想也仍然存在,于是口罩與信賴、患病同時正相關了。
4.3 保守的政治態度
保守的政治態度被看作是抵御傳染病威脅的重要路徑,因為它主張維持舊有的規范和習俗,強調社會管控和等級秩序,有利于資源的統一調配與利用。
對病原體威脅的敏感性能正向預測保守的政治態度。Shook 等人(2017)通過問卷分析了厭惡敏感性與2012 年美國總統競選間多個政治心理變量的關聯,發現厭惡敏感性可以預測對共和黨的支持程度,兩者間的關聯被權威主義等政治態度所中介。Liuzza 等人(2018)檢驗了體臭厭惡敏感性(body odour disgust sensitivity)與權威主義政治態度的關聯。體臭是身體存在疾病或有疾病隱患的指標,因此前者代表了對病原體的敏感性。結果發現,個體體臭厭惡敏感性越高,越可能持有權威主義的政治態度。
新冠病毒對人們政治態度的影響也引發研究者的關注。Merkley 等人(2020)分析了2020 年1 月到3 月292 名加拿大國會議員的推特發文,也對2499 名加拿大公民對新冠嚴重性的認識、政治態度、預防新冠的行為進行調查,發現各黨派議員都從3月開始充分重視新冠疫情的發展,民眾對保守黨的支持力度并沒有顯著增長,這是因為保守黨和自由黨都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壓力下變得更保守,導致了跨黨派的一致性。
5 總結與展望
病原體對文化演化的影響體現了演化論背景下文化對特定生態條件的適應性改變(俞國良,謝天,2014)。病原體視角研究的優勢在于關注現實問題、研究的外部效度較高。這是通過廣泛采用縱向追蹤設計實現的。文化演化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顯現,因此縱向追蹤設計顯得尤為重要。目前心理學家開展的縱向研究設計包括最嚴格的追蹤設計、間接反映文化變遷的跨時間比較①通過比較產生于不同時間點上的數據進而揭示沿時間軸可能存在的變化及其方向。、跨代際比較②通過比較某一時點上出生于不同年代人群的心理進而揭示可能存在的時代變遷效應。和歷史重構③用非時間、非代際的差異來重構時間上的差異,如發達與落后代表社會變遷,“以空間換時間”。(蔡華儉等,2020)。病原體視角的文化演化研究者們除了關注病原體對人們心理與行為一時一地的影響,也積極開展縱向研究,追蹤不同時段病原體對人們的影響。
文化朝集體主義與保守主義演化也值得我們反思。集體主義、保守主義的確有利于抗疫,但個體正當的權利和自由也應得到保障,創新和平等的價值理念仍然值得共同追求。研究者需要思考如何在文化演化發揮正面作用的同時抑制所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如果文化演化因遲滯性而產生不良后果(疫情結束后可能仍受遺留的保守主義影響而抗拒變革、盲從權威),我們如何主動干預以盡快減弱或消除這種影響?這些反思議題為研究的持續開展開辟了更廣的空間。
在對已有研究總結與反思的基礎上,我們認為未來研究可以構建并檢驗病原體壓力解釋文化演化的路徑模型。這首先需要分析病原體影響文化演化的中介變量。Conway 等人(2020)發現不確定感在病原體對保守主義政治態度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我們推測它可能進一步對其他保守主義子維度以及集體主義都會起中介作用。
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不安全感(不確定感是其來源之一)是病原體影響集體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中介變量,因為安全感的外延更大,可包括生存安全感和認識論安全感。生存安全感是最基本的安全感。已有研究證實,當社會的安全遭受威脅時,人們的右翼獨裁主義水平會隨之上升(Mirisola et al.,2014),可見生存方面的不安全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保守主義。而認識論安全感是個體獲得認知確定性的感受,不確定感對應于其反面含義,可歸入其中。此外,有學者指出,安全感是理解人們如何合作以獲取共同目標的重要因素(Edmondson& Lei,2014),為它在集體主義路徑中的中介作用增添了研究依據。總之,病原體帶給人們的影響既可能關乎生命安全,尚未探明影響機制的病原體又涉及對認知確定性的沖擊,因此我們認為不安全感作為中介變量的解釋性更強更全面。未來研究可以在各個方面檢驗不安全感在病原體影響文化演化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要構建完整的路徑模型,還需要考慮病原體影響文化的邊界條件,這需要引入調節變量分析。目前不少地區針對新冠疫情已經實現常態化疫情防控,但防控的強度各異。面臨程度不同的病原體壓力,不同的疫情防控強度是否會對文化產生動態性影響?未來研究可以追蹤新冠疫情下變化著的病原體壓力,并探討不同強度的疫情防控策略對文化產生的各個層次的影響,以檢驗疫情防控程度的調節效應。再如生命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又是另一個可能的調節變量,個體幼年生活在資源貧乏的環境中會更多采取快速的生命史策略,這就會抑制他們在行為免疫系統方面的投入,反之則會增加投入,那么持不同生命史策略的個體在行為免疫系統的反應性和敏感性上可能也會存在顯著差異,未來研究可以就此展開進一步探究。綜上,我們構建了病原體壓力解釋文化演化的路徑模型圖(見圖1),更直觀、清晰地描述了已有研究的總體結論,也對未來研究探討中介、調節機制進行了展望。

圖1 病原體影響文化演化的理論構想
此外,未來研究還可以建構可供實證的新概念、突出研究的中國特色。有研究者提出“社會免疫系統”(social immune system) 概念以協調總體健康(population health)和個體自由(personal freedom)之間的關系(Saad&Prochaska,2021)。該概念的提出是從整體角度重新思考人類免疫以及人們應對病原體挑戰的實踐展開的。未來研究可以對其操作化、實證化。在突出研究的中國特色方面,可關注中醫學的作用,其中包含大量的預防保健內容,“治未病”的思想更是與行為免疫的目標契合。未來研究可以在研究設計中增加本土特色內容如中醫的相關思想與實踐。此外,當代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的具體實踐也可以融入相關研究中,突出研究的中國特色,為理論發展提供“中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