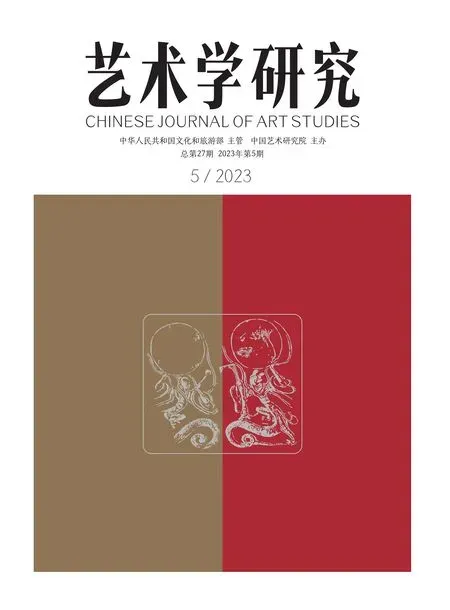版畫4.0:科技巨浪中的危機與可能
王霄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藝術院
2023 年3 月14 日,ChatGPT 的 開 發 機 構Open-AI 正式發布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多模態大模型GPT-4,隨后微軟宣布將GPT-4 接入旗下一系列辦公軟件工具,稱“人類與電腦的交互方式邁入了新階段”[1]競泰資本:《科技|GPT-4融入微軟辦公軟件,AI 2.0時代已經來臨》,https://it.sohu.com/a/657627174_121252519,2023年3月22日。。對于創作者而言,輸入幾個關鍵詞,軟件就能寫出條理清晰的文章;輸入幾個提示詞(prompt),就可生成精美的數字圖像作品。面對不斷進化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的挑戰,還在手持刻刀、孜孜不倦埋頭苦干的版畫家們,也感受到了迎面而來的危機,這一切不禁令人回想起五六百年前那個視覺圖像陡然繁華的印刷時代。
一、雕版印刷術與復制版畫的輝煌時期
印刷術的發明是中國對人類文明做出的最重大貢獻之一。美國學者托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其名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緒論”中明確指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四種偉大發明(指中國四大發明——引者按)的傳入與流播,在現代世界的誕生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形塑作用。”[1]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XIX.孫中山更于《實業計劃》中指出:“據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質原件共有五種,即食、衣、住、行及印刷也。”[2]孫中山:《建國方略》,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頁。可見,印刷術作為人類早期傳播科學思想的重要媒介,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
在中國,雕版印刷術最初被用來印刷宗教文字與圖像,這些圖文并茂的平面作品可以被視為早期的版畫。這一時期的版畫以傳播思想和復制圖像為目的,以盡可能精準地還原“母本”供更多人閱覽為核心要旨。當然,古代并沒有現代美術意義上“版畫”的概念,“版畫”的存在形式非常多元,除了大量的宗教圖像之外,還包括諸多圖文并茂的勸善經典,如《圣跡圖》《女范編》;工具類書,如《營造法式》《本草綱目》;書譜畫譜,如《宣和畫譜》《芥子園畫譜》;傳奇小說,如《三國演義》《西游記》,等等。這些文化典籍、知識手冊、通俗讀物通過雕版印刷的方式生產、傳播到不同階層的人群之中。特別是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繁榮,人們對書籍的需求大增,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各類帶有插圖版畫的戲曲、小說書籍,《西廂記》流傳至今的就有30 多個版本(圖1);一些極盡雅致的詩箋畫譜成為流傳于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高端文化商品,如《十竹齋畫譜》《蘿軒變古箋譜》;紀實和欣賞類的風景版畫開始出現,如《湖山勝概》《環翠堂園景圖》;還有大量張貼于百姓家中的年畫,日常娛樂的紙牌葉子,以及近些年開始被學界研究、作為外銷商品的姑蘇版畫,它們至今仍被保存于許多歐洲古堡的墻壁上,細致精美。這些形制多變、雅俗共賞的古代版畫,上至宮廷、下達百姓,甚至遠播歐洲,深刻地塑造了古代人的感官經驗以及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圖1 《西廂記》版畫之《窺簡》,明崇禎十三年(1640)閔齊伋制六色套印本,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藏。
同中國一樣,歐洲的版畫最初也是以滿足宗教需求為目的的印刷品,隨后廣泛地延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15 世紀,木刻版畫業已廣泛流行于歐洲各地;16 世紀,雕刻銅版畫開始流行,除了印制藝術家的原創作品,還用于復制名家壁畫和油畫,以及制作書籍插圖和畫集,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丟勒是歐洲第一位將版畫提升至藝術品地位的關鍵人物,他以極其精湛、豐富的技法,將原本簡易、粗獷的木刻版畫提升為可同壁畫、油畫相媲美的精美藝術品,“他以卓越的技巧,用這種誕生不到一世紀的印刷術,創作出能與傳統藝術相媲美的藝術作品……他把金銀匠的雕刀工,運用到木板上,用類似銅板線那樣密集的平行排線和十字交叉線的襯影來加強形體的立體感和光感……丟勒猶如一個勇敢的旗手,把版畫帶向一個新的天地,又像一個辛勤的園丁,把版畫的幼苗栽種在文藝復興的沃土上生根開花”[1]張殿宇:《西方版畫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頁。。16 世紀,工商業興起,各種商業用途的版畫開始出現,除了復制油畫和壁畫的作品,還有地圖、地方景觀圖像、肖像畫、民間版畫、“小故事書”(Chapbook)等,這些大量刊印發行的版畫成為當時人們文化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復興以后,荷蘭成為歐洲重要的印刷基地,主要是復制版畫,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優秀的原創版畫家,其中包括藝術大師倫勃朗,他將蝕刻銅版畫發展為一種不同于油畫的、獨具魅力的創作媒介,并通過這些輕盈、便于攜帶和傳播的版畫作品,使自己在有生之年即名滿歐洲[2]盛葳:《圖像的旅行:版畫、印刷與出版》,《美術》2023年第3期。。
15 至16 世紀,印刷文化在全球的興起改變了知識生產、傳播和接受的基本模式。相較于古老的、口口相傳的文化傳播模式,印刷制品的傳播更為精確,效率更高;而相較于在昂貴的羊皮紙上手抄手繪的傳播模式,印刷因能批量生產、價格相對低廉而更具有市場競爭力——它就是那個時代的“新媒體”。正因如此,今天被稱為“版畫”的印刷圖像的普及,迅速而全面地重塑了“藝術”的內與外,對整個人類社會和藝術史的早期現代轉型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舊媒介”與“新藝術”
19 世紀,歐洲人在傳統印刷術基礎上融入現代科技,發明了以機械操作為基本特征的現代印刷術,尤其是平版印刷,迅速在全球得到運用。與之相比,手工雕刻印刷版畫的人力成本高、產出率低,精細程度也遠不及機械印刷出來的工業產品。以天津為例,據天津鼓樓北的印刷作坊“毓順成”老板張芳田回憶,20 世紀伊始,石印年畫在天津逐步取代了木版年畫。1925 年天津年畫市場上,石印年畫銷量已經超過7000 萬張[3]金冶:《天津楊柳青年畫考察》,《人民美術》1950年第2期。。在現代印刷術的沖擊之下,手工雕版印刷行業迅速衰落。技術的落伍,導致“版”作為重要的復制、傳播方式的核心價值被現代印刷術所取代,版畫由新媒介淪為舊媒介。然而,歷史常常出人意料,正如攝影術發明之后,人們認為繪畫即將死亡,但繪畫至今仍然活躍。與之相似的是,在版畫的媒介價值被取代的危急時刻,歷史上幾個特殊的事件和運動,改變了版畫史的走向。
丟勒通過精研版畫技法,融合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創作出大量精美的木刻作品,并在全歐流傳,甚至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4]Morris T.Everett, “Revival of Interest in Etching,” Brush and Pencil 8,no.5 (Aug.1901): 233-246.。但在隨后的17 世紀后期至19 世紀前期的美術史中,版畫只是被主流美術脈絡所遮蔽的一條忽明忽暗的分支,除了戈雅這樣極少數的案例之外,版畫主要被用于復制經典油畫、壁畫作品,以及制作、廣告、票券等特定的商業行為。直到19 世紀中期,歐洲興起蝕刻版畫復興運動(Etching Revival)。這個由藝術家、收藏家、畫商、出版商等共同參與的運動,旨在提高版畫的藝術地位。經過長時期的努力,版畫逐漸脫離了復制圖像的局限和作為附屬性媒介的束縛,成為具有獨立美學價值的現代藝術類型。巴比松畫派的杜比尼、柯羅、米勒,印象派的畢沙羅、馬奈、德加、勞德雷克,野獸派畫家馬蒂斯,表現主義畫家蒙克、魯奧,立體主義代表人物畢加索,現實主義版畫家柯勒惠支、麥綏萊勒等都創作了許多獨具魅力的版畫杰作,成為美術史上的璀璨明珠。
與歐洲的蝕刻版畫復興運動遙相呼應,20 世紀初,創作版畫運動(Sōsaku-hanga movement)在日本興起。1904 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報《明星》7 月號刊登了山本鼎的版畫作品《漁夫》,作品介紹中第一次使用了“版畫”的概念。隨后不久,“版畫”一詞傳入中國并沿用至今。中國的現代創作版畫同樣始于20 世紀初,留日藝術家李叔同回國后曾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樂石社”指導學生進行木刻創作。20 世紀30年代初,在魯迅的引領下,中國新興木刻運動迅速由上海擴展至杭州、北京、廣州,隨后在全國蔚然成風,對中國的革命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版畫因為能夠迅速地復制,因此在各種革命運動中都承擔著宣傳的職能。延安時代畫家們根本弄不到油畫顏料和宣紙,只能用印報紙的廉價油墨和農村隨處可以得到的梨木板來創作木刻,抗戰木刻和救亡漫畫成為中國革命文藝的重要形式,更進一步把傳統木版年畫改造為宣傳革命思想的新年畫。歐洲也是一樣,從英國的荷加斯開始就用版畫來制作政治諷刺漫畫,在歷次社會革命中版畫都是重要的宣傳工具。”[1]邱志杰:《版畫是科技藝術的重要源頭》,https://mp.weixin.qq.com/s/0dTItSNI9sgJL4-Cstze_w,2023年4月20日。在革命年代,版畫數次成為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革最高效和有力的宣傳媒介之一(圖2)。20 世紀50 年代,隨著新中國現代美術學院的建立,中央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等藝術院校均成立了版畫系,開始進行專門的版畫教學和創作。至此,版畫被納入現代美術學院的純藝術系統,成為具有獨立審美和收藏價值的“精英藝術”。
三、版畫“4.0時代”
如果根據功能、形制的轉變對版畫的歷史進行粗略劃分,公元前3000 年蘇美爾人的滾印、商周時期陶罐上的刻紋、戰國時期的肖形印章,這些具有刻、印行為的“作品”,屬于版畫的雛形時代——1.0 時代;19 世紀現代印刷術發明前,主要用于復制、生產和傳播圖像的手工印刷版畫時期,則可以被視為版畫的2.0 時代;19 世紀末現代印刷術發明至今,版畫成為一種具有獨立審美功能的純藝術類型,締造了版畫的3.0時代;而近年來,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及其廣泛的社會應用,則推動著版畫進入4.0 時代。在新文科與學科交叉融合不斷深入發展的宏觀背景下,諸多既有的專業框架、知識體系不可避免地面臨新的調整,版畫技術與藝術科技的邊界已變得越來越模糊,隨之而來的是版畫系統內部開始充斥著矛盾、反思與動蕩。
從中國當代版畫創作的核心陣營——美術學院系統來看,十幾年前仍少見對“數碼版畫”的認同和實踐,而如今成長于學院系統的青年版畫家,對“數碼版畫”已懷揣著發自內心的認同,并能自由灑脫地運用數字技術創作版畫。那些自幼習慣電子屏幕、虛擬圖像的新一代年輕藝術家,或許并不認為紙質印刷品比虛擬圖像的世界更“真實”。不過,就版畫的經典定義而言,如果只是將手工制版、分版的過程轉移到電腦中,借助數碼技術將傳統版畫中的造型語言轉換為虛擬圖像,再經過打印機等輸出平臺印制完成,那么這樣的數碼版畫創作在工作流程和底層思維方面實際上并無太多新意。新技術的應用與適配不當,以及對“數碼版畫”的過度使用,反而會使作為藝術品的“版畫”概念被混淆,甚至被消融。面對洶涌的科技巨浪,作為“藝術”的版畫,如何與新科技建立對話,彼此適應、相互協調,而不是被技術反噬甚至喪失其本體?版畫藝術家、版畫從業者將何去何從?近年來,不同的版畫家給出了不同的回應。
四、升級裝備——“媒介是人的延伸”
20 世紀60 年代,媒介研究興起,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強調技術、社會和生物學的內在關系,把技術看作人類身體或感官在社會心理上的外延。他的認識至今仍然有效。20 世紀90 年代,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數字化的發展趨勢,藝術品的媒體呈現方式以及人們觀看藝術的方式日益豐富多元,藝術的展陳空間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環境的變化、技術的迭代、藝術理念的更新,對作為藝術媒介的版畫提出了新的要求。版畫技術裝備的升級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把數字技術、新媒介方法運用在創作過程中,作品的最終呈現形式仍然為平面版畫;另一種則是從創作過程到作品的最終呈現,都進行了技術和形式的更新。
學界公認的最早將數字化技術應用于美術創作領域的案例,是1950 年美國數學家、繪圖員兼藝術家本·拉波斯基(Ben Laposky)使用示波器創作的作品《電子抽象》(Electronic Abstraction),隨之引發了人們對數字化技術應用于美術創作的思考和討論。經歷了20 世紀60至80 年代數字化技術應用的起步和發展期,計算機繪畫(Drawing Computer)在一些西方國家出現并迅速發展,20 世紀90 年代中期,計算機繪畫在我國也逐步興起。對新技術頗為敏感的版畫家陳琦,從那時開始就將電腦技術源源不斷地嫁接、嵌入自己的版畫創作系統,并以此為基礎,開創了當代版畫的新局面。陳琦的水印木刻版畫作品《2012 生成與彌散》(圖3),制作技術非常復雜,作品共有240 塊印版,分7種顏色套印而成,二稿時使用計算機進行繪制、素材處理和效果預覽。他在分版過程中借助矢量軟件完成數字文件制作,在制版階段使用高精度激光雕刻機進行雕刻,從畫面語言上體現了數字化和科技化的邏輯。這件版畫作品實現了技術與手工的高度契合,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水印版畫。電腦分版、激光雕刻等數字技術的運用極大地拓展了人的手、眼所能控制和涵蓋的范圍,將版畫創作推進到實現巨大尺幅與高精密制作并舉的新階段。當這件長42 米、高4 米的水印木刻版畫于2019 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展出(參展部分長24 米)時,展場內的作品猶如一本展開的巨大經折裝書頁,步入其中仿佛置身于一片歷史的汪洋之中,同時也與威尼斯水城的文化意涵相呼應。正如陳琦所希望的,“觀眾站在這幅作品前時,可以進入另一個場域,任由自己漂浮于主觀意念的海洋,感受思之無涯,意之無垠”[1]薛浥塵:《陳琦專訪丨水光之間,無所來,亦無所去》,https://i.cafa.edu.cn/cafaresearch/resc/?s=123381,2023年1月26日。。這件鴻篇巨制正是基于技術裝備的升級,突破了版畫表現力的極限,帶給觀眾以強烈的感官震撼和浸沒式的思考空間。

圖3 陳琦,《2012生成與彌散》,第58屆威尼斯雙年展現場。
2009 年觀瀾國際版畫雙年展的大獎獲得者、波蘭藝術家馬格達萊納·杜達(Magdalena Duda)的作品《我——現在/我——未來》(Me-Now/Me-Future)(圖4),運用了照相制版和數字圖像處理技術,將現在的“我”與未來的“我”(經過數字技術虛擬的)并置在同一畫面中,帶給觀眾的不僅是視覺上的震撼,還有對歲月變遷、時光易逝的生命哲思。青年藝術家侯煒國早期經歷了版畫炫技階段,后來更關注如何把情感注入十分復雜的語言和數字技術體系中,讓情感和思考的部分凸顯出來,把語言的部分遮蔽起來。他近期的作品“夜的第三章”系列,采用了圖像切入+ 數字生成/ 選取+激光雕刻+架上材料拼貼的創作方式,最終的作品呈現為一種激光雕刻的木板與金箔交相呼應的新的視覺樣式。侯煒國認為,在藝術創作過程中新的技術、新的媒介都是認知世界的方式,他希望在更大程度上讓非版畫領域的技術與思維方式介入創作,以打破固有思維。

圖4 [波蘭]馬格達萊納·杜達,《我——現在/我——未來》,2009年,凹版,70厘米×100厘米×2厘米。
上述幾件作品借助現代技術實現了版畫創作在作品體量、制作精度、形制創新與空間轉換等多層面上的發展,同時還有效避免了觀眾對過度技術化的反感,通過作品給觀眾帶來的感官震撼與情感共鳴,引發觀者對作品中人文關懷和精神內涵的思考。
五、層級與模塊,編輯與傳播
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有不少版畫專業出身的藝術家。他們從版畫出發并以此為基礎,創作出許多突破版畫范疇的作品,開辟了全新的藝術領域。例如徐冰的《天書》和《地書》,邱志杰的《京東AI 生成地圖》,康劍飛的《版畫漂流計劃》等。他們的作品很難按照傳統方式明確歸類,然而究其創作理念,卻又無不根植于版畫的兩套底層邏輯:核心技術概念——“層級”與“模塊”,社會屬性——“編輯”與“傳播”。版畫從單版單色印刷發展至多版多色套印,產生了分版,也即形成了“層級”這一技術邏輯;套色技術中使用的組合版塊,類似于現代化生產過程中隱形的“模塊”。可以說,“層級”與“模塊”是版畫在技術和藝術兩方面的本質特征。康劍飛的《版畫漂流計劃》充分調動這種特性,邀請不同地區的參與者針對藝術家提供的一個個“版塊”進行共同創作,最終再進行圖像的聚合與展示。制作版畫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編輯、傳播知識和圖像,所以“編輯”與“傳播”也是版畫實現其社會屬性的重要方式。徐冰的《地書》,邱志杰的《京東AI 生成地圖》,運用的素材均能體現出藝術家獨到的視角,方法和媒介也與先進的技術相關聯,但其底層邏輯仍是基于版畫的編輯和傳播原理。
(一)層級與模塊
“層級”源于版畫制作過程中的分版與套色,它也是數字時代圖像軟件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譬如Photoshop、Illustrator 等軟件中的“layer”。“模塊”源于版畫中可移動、組合的“版塊”。雷德候(Lothar Ledderose)在《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模塊化生產》一書中,將“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視為中國藝術從古至今的本質性特征,這一特征不僅表現在中國古代漢字系統、青銅藝術、畫像磚石、建筑藝術中,也同樣體現在明清時期的印刷藝術和文人畫中。“模件體系并非中國所獨有,可資比較的現象也存在于其他的文化之中。然而,中國人在歷史上很早就開始借助模件體系從事工作,且將其發展到了令人驚嘆的先進水準。他們在語言、文學、哲學還有社會組織以及他們的藝術之中,都應用了模件體系。”[1][德]雷德候:《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張總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6頁。正是因為模件的應用能夠進行快速、高效的規模化生產,所以“模塊”在現代社會中亦被廣泛應用,如居民社區結構、流水生產線、集成芯片、樂高玩具、宜家家具、網絡游戲、體素藝術(Voxel Art)等。如今越來越多的智能設備所使用的核心技術之一也包括人工智能模塊。近期,美國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一份報告指出:“AI 產業飛速發展,‘技術擴散’速度超出互聯網革命,其中模塊化(Modularity)是AI 實現更快增長的關鍵。”[2]華爾街見聞:《如何投AI?全球一線VC面臨的“三大焦點問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045571818380101&wfr=spid er&for=pc,2023年5月16日。合成生物學中的“生物積木”(BioBricks)也是基于類似的原理[3]參見百度百科:“生物積木”詞條,https://baike.baidu.com/item/生物積木 / 2080907?fr=ge_ala,2023年6月3日。。因此,熟知層級、模塊工作方法的版畫家很容易介入這些新興的領域,將實體物質媒介和數字虛擬技術、人類情感進行“層級”與“模塊”的分析、歸納與融匯,實現舊媒介與新技術的嫁接與創新。
2014 年,康劍飛將一件版畫作品《林雪》分割成400 塊,與策展人姚遠東方一起,通過不同渠道征集了400 多位參與者,讓他們帶著免費領取到的“模塊”在世界各地漂流,記錄各自人生的重要時刻和具有特殊意義的目的地。2015 年7 月,其中的320 塊版畫重聚廣州風眠藝術空間,以文字、圖片和版畫實物的形式呈現300 多位普通人與藝術家在一年之中的經歷與創作。
(二)編輯與傳播
“層級”與“模塊”的分析、歸納與融匯,均源于版畫重要的社會屬性——“編輯”與“傳播”。版畫自誕生以來就與媒體的編輯、信息的傳播緊密聯結在一起。版畫家們非常了解自己創作的圖像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從創作伊始,作品未來的廣泛流傳就被作為一個前提條件納入構思之中。如今,雖然各種各樣的電子屏幕在傳播功能上取代了古代版畫,但舊媒介的運行方式總是不斷滲透在新媒介的底層邏輯中。對符號的編碼與傳播,使得版畫專業出身的藝術家可以迅速融入數字化語境的探討和實踐中,不斷創造新的藝術邏輯。藝術家徐冰早年的成名作《天書》是對傳統文字的“再編碼”,近年來的作品《地書》則是一本可讀的小說,是藝術家花數年時間搜集整理出的一套公共標識語言系統,能夠讓不同母語、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過視覺符號順暢溝通。此外,徐冰近作《蜻蜓之眼》也具有相似的邏輯,藝術家廣泛收集各種監控視頻,并將這些原本毫無關聯的內容剪輯為一部敘事性電影。這些作品在整理、歸納、呈現方式上都使用了新的技術和媒介載體,但其作品的底層邏輯依然是基于版畫編輯、傳播的媒介屬性。
邱志杰近年來創作了一系列地圖作品。從歷史上看,世界各地的早期地圖,很多都是版畫刻印完成的,從曾經紙質的地圖到如今虛擬的Google 3D 全景地圖,雖然媒介在不斷演變,但本質上都是對于地理位置及其相關的圖與詞的歸納、編輯、呈現和傳播。邱志杰將用水墨(舊媒介)繪制的地圖與人工智能(新媒介)結合,開發出一款人工智能軟件。當觀眾通過語音或文字輸入任何有效單詞時,程序會自動關聯并構建出一個個不同的地圖組合。觀眾的每一次輸入,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再編輯、再傳播的互動過程。“地圖的演變是文本語義無限增長的結果。由于在文本語義層面的無限擴展,地圖已經成長為一個具有無限可能的自主增長系統。”[1]張桂森:《邱志杰:時隔十年,從“破冰”到“寰宇全圖”的Mapper》,https://www.sohu.com/a/289868255_149159,2023年1月18日。這種舊媒介與新媒介的融合與創新,實現了藝術家、作品與觀眾的深度互動。
徐冰與邱志杰都是出身于版畫專業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早已超出某個傳統“畫種”或“藝術門類”的范疇,而開辟了各自新的語言系統。然而版畫的“層級”與“模塊”思維,以及“編輯”與“傳播”的創作方式,仍是支撐其創作的底層邏輯,他們在此邏輯上實踐出移動互聯網上的“融媒”創新。麥克盧漢曾說:“媒介作為我們感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不但各種感知會形成新的比率,而且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形成新的比率……收音機、電唱機和錄音機使我們重溫詩人的聲音,給詩歌鑒賞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1][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頁。。版畫之所以被視為重要的“媒介”藝術,正是由于其游走于“畫”“刻”“印”等多種創作方法與媒介疊合的“中間地帶”。媒介(medium)一詞的本義是“居間的(in the middle)”,版畫恰恰正是這樣一種“居間的”藝術形式。ChatGPT 時代,媒介與媒介的邊界變得更加模糊,曾經的舊媒介并沒有被完全取代和替換,而是變成了新媒介的一部分,同時對新媒介產生影響。“沒有一種媒介具有孤立的意義和存在,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與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存在。”[2][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第12頁。4.0時代的版畫,正是如此這般游走、滲透、疊合在不同藝術媒介之間,不斷幻化衍生出新的形態。
六、去技術化、低科技
在一些版畫家嘗試新科技、升級系統的同時,還有一部分版畫家反其道而行之,不斷窮盡版畫傳統技術語言表達的可能性,例如方利民,多年來一直在水印木刻領域深耕,創造了《水印寶典》。這套《水印寶典》總結了現代水印木刻創作的諸多印法,在教學中廣為流傳,正如陳琦評價的那樣,“除了操刀剞劂外,他一直著力于印法研究,在同一個版上實驗各種印痕效果,努力挖掘印刷空間資源。在他的水印版畫作品中,并置了豐富多樣的印刷痕跡,濃、淡、干、濕、輕、重、枯、潤,錯綜穿插,各得其所,有機地組合為具有現代視覺意味、動感豐富的畫面”[3]陳琦:《中國水印木刻的觀念與技術》,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頁。。《水印寶典》將古代用作繪畫教材的版畫畫譜進行了現代性的轉換與創新,這種現代性的轉換完全由手工制作實現,采用了古籍版本的裝幀方法,為現代美術學院的水印教學譜寫了新篇章。
還有藝術家使用“去技術化”的方式來挖掘版畫的當代可能性。藝術家譚平2012 年在中國美術館的個展“一畫”中最重要的作品《+40m》(圖5)是他耗時6 個小時,用刻刀在木板上一氣呵成刻制的。譚平說:創作《+40m》時,“我選擇木刻的方式完成,這和我以往從事創作的經驗有關。所有的人生經歷、對藝術的理解,都在刀和木板接觸的一瞬間體現出來”。譚平在刻板之前對畫面效果沒有預想,具體刀法完全沒有設定。這是一種摒棄既有經驗的“去技術化”創作方式。“刻刀與木板接觸的瞬間如同鋒利的刀劃開皮膚,深深地,慢慢地行走,不斷深入這塊黑色平面的內部。六個小時刻刀在木板上抑揚頓挫地行走就像將我自己沉入生命的‘時刻’,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經歷,對藝術的理解,包括我內心的掙扎,全部留在刀和木板磕絆的瞬間,只有這樣才能表達我追求的精神境界。”[1]應妮:《中國美術館主展廳首次接納抽象藝術展〈1劃〉》,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2/12-08/4393332.shtml,2023年4月20日。這種“去技術化”的版畫創作方式,強調的是手的動作在木板上的記錄,“刻”的行為與藝術家的內心世界高度融合,每一個“技術”的瞬間都灌注了藝術家的精神與感情。

圖5 譚平,《+40m》,2012年,中國美術館展覽現場。
此外,前文所述徐冰的作品《地書》是個不斷發展的項目。“2016 年《地書》發展成了立體書,基本囊括了所有立體書的表現手法,如:翻翻、轉盤、拉桿、軸桿等,標識符號與立體結構巧妙地結合反映出更強大的互動性和可讀性,使這本世人都能讀的書變得更加奇妙有趣。在紙質書籍沒落的局面下承載著原始的閱讀功能,寄托著人們對于翻動書頁的情感體驗,更成為一種綜合的藝術展現形式。在今天高科技與藝術結合的潮流中,徐冰卻反向地尋找原始的、低科技藝術表達的魅力。”[2]雕塑熱點:《解瑣文化密碼|徐冰的藝術作品和創作方法》,https://www.163.com/dy/article/GONCMTIE0534A312.html,2023年5月11日。《地書》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既運用了最新的媒介手段,又復原了手工制作帶來的情感體驗。在同一系列作品中,藝術家的創作如同彈簧,伸向完全相反的兩個方向。這或許正暗合了4.0 時代的版畫家的風格特點,基于同一個源點——“版畫藝術”所探索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路徑。
七、偶然、無序、即興
版畫創作的過程理性、嚴謹,優秀的版畫家身上常帶有如科學家和管理者一般的氣質,而藝術創作又需要感性與直覺的調動,優秀的版畫家會將二者完美協調,形成一種規則之上的自由。這種狀態類似鋼琴的即興演奏,在有限、有序的黑白鍵盤上演繹出美妙卻無法復制的音樂。在科學史上,許多發明也誕生于實驗中的偶然甚至錯誤。例如青霉素的發現源于久置的培養皿中的一塊無菌區域,微波爐的發明源于雷達技術的研究。可以說,許多創新源自偶然、無序、即興。在4.0 時代的版畫創作中,不同媒介偶然、無序與即興的混搭常常碰撞出有趣的作品,這類作品“反標準化流程”,甚至會故意“出錯”,卻具有不可思議的創新價值和啟示意義。
筆者的作品《嫦娥奔月》(圖6)將制作版畫作品所需的原始物質媒介——絹、印版、基底三部分剝離,使用視頻影像媒介記錄、干擾、解構了創作過程的原始邏輯,將作為物質實體的“版”與虛擬的數字“版”疊加、滲透、共融,編輯、建構了“錯誤”的新邏輯。最終視頻作品中的“版”有手工刻出的印板,有純粹作為象征的物質介質(以銀絲布隱喻月光),有手繪與影像結合的運動中的“版”,這些“版”實體與虛擬混雜,增強了視覺效果上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使本該理性、有序的版畫創作過程變得偶然、不可捉摸。這是一種建立在技術、規則之上的即興創作,在此過程中,“人”與“技術”體現出一種張力和博弈。這也從一個側面提示了技術與藝術的辯證關系:技術是理性、有序、歸類的,正如版畫制作的標準化流程;而藝術尤其現代藝術往往是無序的,創造性存在于常規秩序斷裂后所生成的新邏輯中,這些無法預測、即興與偶然的東西恰恰是藝術最迷人之處。在某些AI 生成并售賣作品的網站上,售價最貴的竟然是帶有偶然性、出錯的圖像,每一次傳播中的偶然性,甚至“錯誤”或許正是其獨特價值所在。
結語
20 世紀70 至80 年代,在人們還熱衷于談論后現代時,批評家和文化學者們用這個概念表達出的是他們內心深深的焦慮,這種焦慮來自新的電子和數字技術已經開始深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一個算法世界的零維空間里,一切都將無可挽回地終結在一條死胡同里。在這種論調的攻勢下,人們開始對所有具有身體性的東西進行抽象提煉[1]參見[德]西格弗里德·其林斯基:《依舊出新:從早期近代通往未來的可能——評繆曉春的文藝復興作品三部曲:〈虛擬最后審判〉〈H2O〉和〈坐井觀天〉》,黃曉晨譯,烏塔·格羅森尼克、亞歷山大·奧克斯編《繆曉春 2009——1999》,德國杜蒙出版社2010年版。。來自柏林的哲學家和人類學家迪特馬爾·坎珀(Dietmar Kamper)在1989 年接受采訪時,曾對這種世界觀予以回應:“目前,對我們而言,致命的不是癌癥,也不是艾滋病,而是我們將經歷視聽的死亡,將溺亡于圖像的洪流中,而不是自己去更多地經驗生活、以自己的身體去獲取感官體驗。”[2]Das Auge,Zur Geschichte der audiovisuellen Technologie.Narziss, Echo, Anthropodizee, Theodizee.Dietmar Kamper im Gespr?ch mit Bion Steinborn,Christine v.Eichel-Streiber,轉引自[德]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依舊出新:從早期近代通往未來的可能——評繆曉春的文藝復興作品三部曲:〈虛擬最后審判〉〈H2O〉和〈坐井觀天〉》, 黃曉晨譯,烏塔·格羅森尼克、亞歷山大·奧克斯編《繆曉春 2009——1999》。
歷史總在反復上演相同的劇本,如今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同樣的境遇。數字算法、虛擬圖像已經悄無聲息地將諸多實體藝術卷入一種更為虛幻莫測的文化交互界面。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4.0 時代的版畫藝術家將怎樣“突圍”?如果是個體版畫家的藝術創作,那么怎樣創新和革命都不為過。然而,如果我們將版畫放在美術學院、學術系統的大框架下,視其為“美的藝術(Fine Art)”的一個重要類型,勢必仍需厘清版畫的邊界、內涵與外延。在討論“數字技術”與“版畫”的關系時,我們需要保持警惕,如果不再區分數字算法生成的虛擬圖像和印刷出來的物質化形式的版畫哪個才是真正的作品,版畫必然面臨自我解構的險境。如果“印刷”的行為最終缺席,“版畫”將徹底淪為由算法控制面板與屏幕組成的虛構場。反過來,如果死守傳統版畫固有的條條框框,那么,這種歷史悠久的藝術最終必然會因為無法創新和跟上時代而成為歷史的記憶和往昔的象征。對于當代版畫家而言,無論是積極采用新科技創作,還是反過來強調非科技、反科技的身體經驗,它們都是今天這個新時代的產物,無論它們能否成功,都是4.0 時代版畫的重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