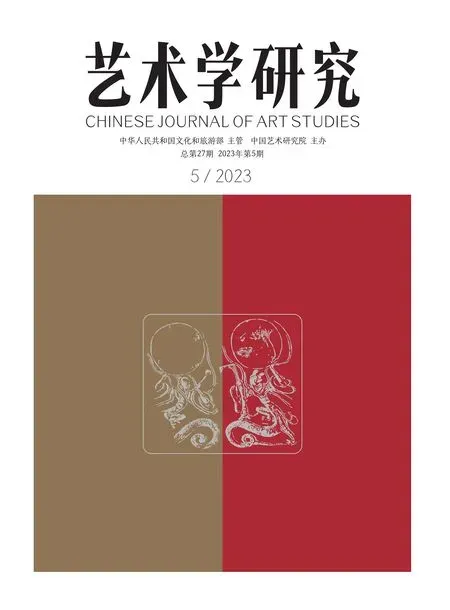論作為當代藝術材料的語言
諸葛沂
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
我們如何看待當代藝術中的文字,是閱讀它,還是觀看它?以口語形式出現在行為、表演或錄像等藝術中的語言,又產生了怎樣的效應?既然當代藝術的創作可以容納種類無盡的媒介,為什么有些藝術家還執著于用語言來創作作品?如果不從歷史、類型、體驗和社會的視角對這種創作手段進行追溯審視,就無法深切理解作為當代藝術材料的語言——它的藝術史定位、它的“物質/社會”二重性、它的批判潛力和作用機制,以及漢語作為一種語種,在全球化背景下演繹出的文化圖景和跨文化愿景。
從看到讀
顯然,語言的多種表現形式——印刷文本、繪畫標志、墻體招貼、多媒介展示、語音錄音等,已經成為當代藝術的主要元素。20 世紀60 年代以來,在諸如激浪派、波普藝術、概念藝術、錄像藝術、數字媒體藝術等標簽下,語言——不論是文字還是口語——在藝術中激增,與新興的詩歌活動、行為藝術活動以及實驗音樂有著復雜的關系,以至于對于今天的藝術家來說,用語言進行藝術創作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慣例[1]Liz Kotz, Words to Be Looked At: Language in 1960s Art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2007), 1.。
眾所周知,漢語是中國書畫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但是,中國傳統藝術講究詩、書、畫、印、意的統一,材料意義上的語言的獨立性并不彰明較著。縱觀藝術史可知,語言一直圍繞著視覺藝術,作為標題、題詞、作品說明或藝術批評而存在。在西方古典藝術中,畫面中的文字長期居于次要地位,僅起到一定的圖釋與意指作用。17 世紀以降,杜博、狄德羅、萊辛的“詩畫對觀”表面上將詩畫對立,實則將二者同置于“藝術”這一集合名詞之中,這便為語言成為具有獨立地位的藝術材料鋪墊了隱藏的理論基礎[2]張穎:《杜博的詩畫對觀與藝術理論的現代起源》,《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19 世紀末以來,文字在西方視覺藝術中的地位昭顯出來,到了20 世紀初,畢加索和喬治·勃拉克(Georges Braque)將撕裂的報紙粘貼到畫面上,創造出語言——視覺的雙關;達達主義者將文字拼貼作為“視覺政治”手段,如漢娜·霍赫(Hannah H?ch)針對魏瑪共和國的照片蒙太奇批判(圖1);在保羅·克利(Paul Klee)和雷尼·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畫作中,文字的隱喻性功能得到了進一步釋放。到了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波普藝術家借鑒廣告設計,使用文字作為圖形標志或視覺標識,在激浪派的早期行為藝術中,文字成為一種藝術創作方法指示,如在小野洋子1964 年的代表著作《葡萄柚:一本指令與圖畫書》中,稀疏的排版頁面為許多藝術品創作提供了新方案[3]參見Kim Dhillon, Counter-Texts: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Art(Reaktion Books, 2022), 7;[日]小野洋子:《葡萄柚:一本指令與圖畫書》,梁幸儀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更重要的是,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概念藝術的興起帶動了一種被稱為“基于文本的(text-based)”藝術作品的涌現,所謂“文本藝術”(Text Art)概念應運而生[4][英]戴夫·比奇:《大逆轉:論當代文本藝術》,敖露露譯,《美術觀察》2023年第1期。。同時,言語或語音也在如錄像、行為等藝術類型中出現。就本文而言,若要深入討論作為當代藝術材料的語言,就必須聚焦于“概念藝術”,在藝術史脈絡中考察它的發展和影響。

圖1 漢娜·霍赫,《廚刀裁切的達達作品,德國最后的魏瑪啤酒肚文化時期》,1919——1920年,照片拼貼,114厘米×90厘米,德國柏林新國家美術館藏。
20 世紀60 年代早期,新一代紐約藝術家擺脫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選擇語言作為材料,繞過畫廊系統并挑戰既有藝術品的地位。“概念藝術”這個詞最初由激浪派藝術家亨利·弗林特(Henry Flynt)提出:概念藝術是以“概念”為材料的藝術[1]Henry Flynt, “Concept Art,” accessed May 22, 2023, https://henryf lynt.org/aesthetics/conart.html.。既然“概念”與語言緊密相關,概念藝術就是一種以語言為材料的藝術,或是“基于文本的”藝術。此后,維克多·伯金(Victor Burgin)、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河原溫(On Kawara)、約瑟夫·科蘇斯(Joseph Kosuth)、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勞倫斯·韋納(Lawrence Weiner)等人以各自的方式進行文本藝術實驗。
當時,藝術界新銳人士的靈感來源之一,是對20 世紀10 年代馬歇爾·杜尚的現成品藝術遺產的重新挖掘。當代藝術理論家蒂埃利·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曾指出,杜尚的現成品藝術實現了從古典的審美判斷表述(“這是美的”)向現代的審美判斷表述(“這是藝術”)的轉換,也就是說,“藝術”這個詞不再是“美的藝術(beaux art)”,而成了唯名論意義上的“一般藝術(art in general)”[2]蒂埃利·德·迪弗指出,18世紀以來,古典的審美判斷表述“這是美的”,開始向現代的審美判斷表述“這是藝術”過渡。藝術成了一個容納情感判斷個案的容器;藝術成了一個專名,它的共有性源自主體借助判斷而產生的命名活動。參見[比]蒂埃利·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沈語冰、張曉劍、陶錚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49、47——62頁。。雖然杜尚在1917 年將偽裝成小便器的“一切都可以是藝術”這則“消息”放進“信箱”,但是這則消息直到20 世紀60 年代才真正抵達目的地,在它的感召下,整個西方藝術界將自身重塑為“后杜尚”的世界[3]諸葛沂:《論德·迪弗對“現代主義之爭”的甄辨與調和》,《文藝研究》2015年第5期。。杜尚的“消息”為概念藝術帶來了巨大活力,科蘇斯曾言,“(在杜尚之后),所有藝術(本質上)都是概念性的”[4]Joseph Kosuth, “Art after Philosophy I and II,” in Art after Philosophy and After: Collected Writings, 1966-1990, ed.Joseph Kosuth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1), 18.。從表面上看,杜尚現成品藝術的創作方式是將某種工業產品挑選出來,幾乎不做改變地進行展示,從而逼迫觀者作出回應,這種實踐方法允許任何預先存在的材料被裝配起來用于藝術創造,這就讓藝術家能夠處理一個巨大的“一般語言(language in general)”領域,它包含任何隨處可得的詞句——品牌名稱、廣告語、辦公室記錄、雜貨清單、日常對話、電報、匯編文件和產品說明等。這些詞句與文學作品有巨大的差異,因為后者仍然強調作者、來源、敘事、情感,而前者則趨向于機械排列、索引記錄和隨機編譯,是唾手可得的現成物。它們的便攜性、大眾性及看似中立的政治性,讓語言成為藝術的媒介。從這個意義上講,杜尚恰恰是最早的“基于文本的藝術”的制作者。據藝術史家米歇爾·薩努利特(Michel Sanouillet)對杜尚筆記的描述:這位藝術家的隨手記錄充斥著大量科學說明、數學證明和哲學概念,甚至政令、口頭語、雙關語、廣告語、粗言俚語等[5]Michel Sanouillet and Elmer Peterson ed., The Writings of Marcel Duchamp (New York: De Capo, 1973), 10.。杜尚將它們沒有參照地任意組合起來,避免所有形式的抒情,他在乎的正是現成語言的可塑性[6]Jacob Stewart-Halery, “Ian Wilson, Conceptual Art,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Language,” in Conceptualism and Materiality: Matters of Art and Politics, ed.Christian Berger (Leiden: Brill, 2019), 182.——在某種意義上,他也是現成物/藝術品的觀眾,因為大家共同參與了對作品的塑造。概言之,杜尚的現成品美學為將語言作為材料的概念藝術創作敞開了豁然的天地。
此外,概念藝術的文本藝術創作,通常將文字做一定格式的排版,繼而印刷發布,這些文字往往呈現出中性而平乏的視覺品質。彼得·奧斯本(Peter Osborne)認為,概念藝術的這類語言銘文(linguistic inscription)作品是那個時代最具批判性和生產力的書面語言應用產物,它否定了視覺形式的內在意義[1]Peter Osborne, Conceptual Art (London: Phaidon Press Ltd., 2002), 31-32.。在當時的藝術史背景下,這種否定又意味著什么呢?事實上,當時,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強調媒介自律性和形式品質的審美現代主義正成為學術界和藝術界新生力量的眾矢之的,而概念藝術家則有意識地與表現主義美學劃清界限。勒維特在1967 年《概念藝術短論》(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中說:“概念藝術家希望作品能在思想上吸引觀者,減少情感上的吸引力……對情感沖擊的期待會妨礙觀者欣賞概念藝術。”[2]Sol LeWitt, “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 Art Forum, V/10 (Summer 1967): 79-83.有論者進而認為,藝術并非一個客體(object),藝術應是一個理念(idea);觀眾的觀看是以某種方式主動參與作品的物理生成或概念創造的思想過程。由此,概念藝術家認識到,藝術理念可以通過語言而非視覺形式來實現,他們實驗性地將文本轉化為藝術,經由印刷、出版、發布,觀眾可以通過積極的閱讀過程而不是通過對任何特定視覺形式的品味來接觸作品[3]Ruth Blacksell, “From Looking to Reading: Text-Based Conceptual Art and Typographic Discourse,” Design Issues 29, no.2 (Spring 2013): 61.。
在這樣的創作指導下,排版、印刷、攝影、展示、出版發行便成為藝術創作的重要手段。盧斯·布萊克賽爾(Ruth Blacksell)認為,20 世紀60 年代特定的社會經濟氣候為藝術在出版環境中的定位提供了新的可能,新的出版環境創造了一種不同以往的藝術場所,培養了一種不同以往的觀眾——能夠接受這些印刷品(從傳單、宣傳冊到大規模發行的插圖雜志)的觀眾。概念藝術家格雷厄姆曾說:“60年代中期的文化是雜志文化,我喜歡《時尚先生》,因為它既有文章又有照片。”[4]Ibid., 63.他的印刷作品《詩,1966 年3 月》(Poem,March 1966)討論的正是作者概念的轉變:作品將遠離藝術家本身的想法,并通過一個責編對文檔在編輯和設計規范上的問題的回應,以印刷構設(typographically constructed)的方式來進行自主工作。這種對藝術家主體地位的移除,與法國結構主義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于1967 年發表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幾乎形成了一種共時性呼應。結構主義既不關心作者,也不關心內容,而只是關心作品的語法、系統和語義實踐[5]汪民安:《誰是羅蘭·巴特》,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頁。,在巴特看來,任何文本都是具有無數上下文和意義的“引用組織”,他要取消如上帝一般的作者,轉而強調閱讀和寫作之間互惠而持續的關系[6][法]羅蘭·巴特:《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299頁。。正因為所有語言都是對更多語言的探索,所以像格雷厄姆等制作的印刷文本作品,讓觀者帶著生活經驗和主觀性走進作品文本所敞開的空間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文本空間的開放性、字面意義與隱喻意義的不確定性和語境的不充分性,體現了語言作為一種藝術材料在產生和容納多重意義上的包容性。概念藝術家將物理上分散的、句法上疏離的語言移置到墻壁、印刷品等載體上,是對語言的凈化提純,對既定意義的清空。利茲·科茨(Liz Kotz)曾指出,約翰·凱奇《4 分33 秒》(4' 33'',1952)的印刷樂譜或“靜默樂譜”,對于20 世紀60 年代轉向語言的視覺藝術家和表演者而言非常重要,因為它清空了幾乎所有音樂屬性,但保留了時間容器的外部形式,從而在時間與表演之間建立起更開放的關系。此外,安迪·沃霍爾的錄音書《A:一部小說》(A:A Novel)也影響巨大,這本書的內容是沃霍爾在1965 至1967 年間與人無休止交談的錄音文稿,其中保留了所有拼寫和標點錯誤,以及從磁帶到文本轉錄所帶來的信息“噪音”,它向讀者展示了一大堆“什么都沒有發生”的東西[1]Liz Kotz, Words to Be Looked At: Language in 1960s Art, 8.。可以說,這兩件作品共同的潛在邏輯表明,隨著新的記錄和傳播媒介的出現,文字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語言將引導20 世紀60 年代藝術的轉向;凱奇的“時間的空”與沃霍爾的“滿的空”,都傾向于將語言視為一種可以被分解、隔離、隨機編譯的“透明”材料,一種存儲著定量數據的、自動運轉的可塑材料,而文本也將脫離既定規范和相應儀式,走向“不可讀”,但這種“不可讀”本身便對觀者發出了另一種“讀”的邀請。
上述這兩件對概念藝術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品也昭示著概念藝術的內部分歧和必然悖論。一類作品強調語言本身的純化、客觀和理性,強調語言本身能夠提示清晰而獨特的思想,具有邏輯實證主義風格,隱現著啟蒙傳統[2]弗朗西斯·培根、托馬斯·霍布斯和約翰·洛克都試圖通過消除語言的互文性、前現代儀式、修辭的和行話的喋喋不休來凈化語言。參見Jacob Stewart-Halery, “Ian Wilson, Conceptual Art,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Language,” 193.;另一類則像伊恩·威爾遜(Ian Wilson)和“藝術——語言”(Art-Language)小組的藝術家,通過討論和錄音[3]參見Robert Bailey, Art & Language International: Conceptual Art between Art Worlds (Durham: Duke Unversity Press, 2016).,將自然對話和口頭交流納入概念藝術的類目中,并且摒棄語言的語義和文體,把重點落在信息傳遞、循環和反饋的系統過程中。這兩類藝術實踐的共同點在于摒棄社會語言學,抗拒符號霸權。概念藝術的這兩類語言運用模型,一直延續在當代藝術創作中。
總之,從“看”到“讀”,體現了當代藝術對傳統視覺感知經驗的棄絕,對接受者而非藝術家作為藝術作品“作者”身份的確立,對思想而非物體作為藝術對象的強調,以及在抑制語言工具性與歷史性的基礎上釋放其思想傳遞性與解放性的渴望。那么,在這種創作模式變換的過程中,語言又是如何體現其材料性的呢?
非物與物
21 世紀以來,藝術史家一直試圖跟上“新唯物主義(neomaterialism)”“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materialism)”“再物質化(rematerialization)”和“物性(thingness)”的腳步[4]例如,近10年來出現的實在論唯物主義藝術(realism materialism art/RMA)強調了藝術研究(藝術史、藝術批評)在接納新實在論和唯物主義哲學時的多樣化選擇。參見Suhail Malik, Christoph Cox, Jenny Jaskey,Realism Materialism Art (Sternberg Press, 2015).,對20 世紀偶發藝術、激浪派、概念藝術至今的當代藝術中的語言,從“物性”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正是在20 世紀后現代主義藝術聲名大噪的時候,露西·R.利帕德(Lucy R.Lippard)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評述——《藝術的去物質化》(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Art),她認為概念藝術作品是思想的而非物質形式的。從去物質化/非物質性到物質性,針對當代藝術中語言的材料屬性的不同解讀,潛藏著值得一究的觀念差異和理論潛力。
對于概念藝術中語言材料的非物質性和物質性,一些藝術家和批評家各執一詞,在觀念上存在霄壤之別。
首先要提的是科蘇斯以語言取代物體作為材料來創作藝術品的意圖。1969 年,科蘇斯曾在一次訪談中描述了他不再與物體或物質材料打交道的原因,即在控制它們的含義與接受上存在困難,“在現實中,一個人自己的想法和他對材料的使用之間的分歧會越來越大,我想要消除這個鴻溝”。他認為,與物質材料相比,語言更是一種傳遞“藝術信息”的有效方式,因此,這種信息可以越來越脫離任何具體的物質條件。“只有思想才是藝術。定義中的詞語提供了藝術信息;就像一件作品的形狀和顏色可以被視為它的藝術信息。”[1]Joseph Kosuth in Arthur R.Rose, “Four Interviews with Barry, Huebler,Kosuth, Weiner,” Arts Magazine (February 1969): 23.這種對物質材料和思想之間“差距”的認識,將他引向了獨特的創作方法:展示一系列字典上對某物的定義,如《題目(藝術作為思想的思想)(水)》[Titled(Art as Idea as Idea)(Water),1966,圖2]。科茨認為,科蘇斯從一個特定物質(水)的抽象概念還原到對于抽象概念(意義:空的,虛無的)的抽象,在這種特殊的還原過程中,首先是一個基本的物質(“水”),然后是一個語言上的抽象(“意義”),它被縮減到它的“概念”,就像字典定義所表征的那樣——這種格式不可避免地(而且從根本上是不充分的)定義了它與其他單詞的關系,在一個無休止的參考循環中,照相機的拍攝就方便地裁剪、截取了這個“靜止”的互證思維。
科蘇斯通過不斷增加的抽象邏輯提出兩個問題:空間中什么樣的物質性被拋棄了,為什么要放棄它?對語言的應用是否能夠完全抹除其歷史性和社會性[2]Liz Kotz, “Language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Photography,” October 111 (Winter 2005): 10.?第一個問題揭示了通過語言材料的“非物質性”取代物體材料的“物質性”來傳達藝術理念的意圖,體現出邏輯實證主義的傾向;第二個問題則提出了提純、萃取、精煉的問題,凸顯出“物性”的維度。
所謂語言“純化”或“物化”,也就是破壞其意義效能與隱喻潛力,將其簡化為無情感、無政治化的東西,成為一種無意義的“物質材料”。概念藝術家將這種經典的極少主義策略應用于新興的信息和大眾媒體世界,創作出一系列語言作品。1967 年,羅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為杜萬畫廊舉辦的弗吉尼亞·杜萬(Virginia Dwan)的展覽題名為“要觀看的語言和/或要閱讀的東西”(Language to Be Looked At and/or Things to Be Read)。展覽上,語言文字多以雕塑形態出現,文本藝術得到了更具體的實踐。文字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物體——可以被觀看,也可以被積累、建造、移動和分解——就像物體可以被視為文字一樣,可以被閱讀或解釋為具有超越其無聲的物理外觀的意義。此外,題目模棱兩可的“和/或”故意混淆了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界限。史密森宣稱這次展覽是要顛覆“語言在字面意義和隱喻意義之間的運作”,“當所有隱喻都被抑制時,字面用法就變成了咒語。語言被建造出來”[1]Nancy Holt, ed., The Writing of Robert Smiths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4.轉引自Liz Kotz, Words to Be Looked At:Language in 1960s Art, 3.。科茨以史密森的鉛筆畫作品《一堆語言》(A Heap of Language,1966)為范例來證明上述論點。創作者在圖紙上將21 行手寫字詞排列、堆疊成金字塔形,這些詞有“語言/措辭演講/方言/ 母語,標準英語/ 方言布洛克語,方言成語俚語/多種語言的混亂,巴別塔通用語言”。這些術語可以在圖表上積累、堆積和堆疊,但它們所喚起的廣泛的意義維度并不在那里[2]Liz Kotz, Words to Be Looked At: Language in 1960s Art, 3.。可以說,在這件作品中,語言是物質而不是思想,某種程度上,單詞被當作東西,像物質一樣被對待。
與此同時,語言的物質性是非常復雜的,這導致了理論和批評上的分歧。盡管弗林特給概念藝術下的最初定義清楚地將語言視為材料,但利帕德推翻了這一論點。她在《六年》(Six Years)一書中認為,語言是“非物質化的”,就好像從語境和關聯中移除的自由浮動形式和物質形式[3]Lucy R.Lippard, Six Years (New York:Praeger, 1973), xiii-ix.。她堅持認為,“當藝術作品像文字一樣成為傳達概念的符號,它們本身就不是事物,而成了事物的符號或表征”,而某些藝術家“所堅持的學究式的、說教的或教條式的基本原則”“也許會最終導致批評的瓦解”[4][美]露西·利帕德、約翰·錢德勒:《藝術的去物質化》,宋倩譯,沈語冰、張曉劍主編《20世紀西方藝術批評文選》,河北美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頁。。有人則指責利帕德的“去物質化”論點視野狹窄,未能涵蓋當時概念藝術的全部狀況[5]Mel Bochner, “Six Years: 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the Art Object from 1966 to 1972,” Artforum X (Summer 1973): 74-75.。針對種種批評和質疑,利帕德在1997 年《六年》再版時回應道:“‘去物質化’是一個不準確的術語,一張紙或一張照片就像一噸鉛一樣是一個物體,或者說是‘材料’。”但實際上,她所關注的仍然是“藝術語境與‘概念藝術’賴以生存的那些外部條件——社會、科學和學術——之間的”關系[6]Lucy R.Lippard, Six Years, 5.。
必須指出的是,語言具有奇怪的二重性:它既是自主的,又是一種做某事的指令,通過閱讀、指示和感知,時間性和述行性的維度越來越占據語言材料本身。在概念藝術作品中,文字有形或有聲地出現在書頁上、墻壁上或存在于說話的瞬間,但同時,它也會隱喻性地召喚出一系列想法或經驗。史密森曾言:“一個詞的力量在于它所處的語境的不充分性。”他還觀察到,“一個固定的詞或一個孤立的陳述”會產生一種悖論[1]Nancy Holt, ed., The Writing of Robert Smiths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4.轉引自Liz Kotz, Words to Be Looked At:Language in 1960s Art, 3.,即盡管一個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的句子、出版物或演講中的位置來定義的,但是一個詞也不斷地超越上下文,前往他境,比如,從正常的使用環境中取出一個術語、短語或文本,并將其還原到空白頁或畫廊的墻壁上,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盡管概念藝術家堅持“純語言”“元語言”,堅持語言自反性,但是當時的語言學家正忙于擺脫這種元語義學模式,轉向“意識”理論,而像利帕德這樣的批評家也反對這種堅持,這便讓20 世紀70 年代關于語言物質性的討論陷入一種凝滯的悖論狀態。近年來,不少學者從物質性角度重新審視當代藝術中的語言,如美國概念藝術家、詩人肯尼思·戈德史密斯(Kenneth Goldsmith)曾指出:“語言物質性——流動性、可塑性和延展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要求作家的積極管理。……輸入Microsoft Word 文檔中的文本可以解析到數據庫中,在Photoshop 中進行視覺變形,在Flash中制作動畫,輸入在線文本處理引擎,向數千個電子郵件地址發送垃圾郵件,其可能性是無窮的。”[2]Kenneth Goldsmith, Uncreative Writing. Managing Language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26.“我電腦上的文本文檔未經改動地保存在一個文件夾中,保持不變,而網絡上播放的文本會發生無法形容的變化:它可以被破解、密碼保護,去除文本字符,轉換為純文本,重新混合、寫入、翻譯、刪除、根除(eradicated)、轉換為聲音、圖像或視頻,等等。”[3]Ibid., 32.戈德史密斯對增強的語言物質性的觀察,不僅與40 多年前利帕德所提出的“藝術的去物質化”觀點直接對立,還與一些當代媒介理論相左,例如弗里德里希·巴爾克(Friedrich Balke)就曾借德勒茲思想斷言:“在物理學也長期停止將實體作為物質性模型之后,不再有理由將非物質視為一種特殊實體領域的存在,這種實體領域被想象為與身體類似,并與物質性分離。”[4]Friedrich Balke, Gilles Deleuze (Frankfurt / Main, 1998), 36.可是,對于藝術而言,假如藝術家真的對藝術作品的物理演變失去了興趣,走向深度的“非物質化”,那么客體將完全被淘汰;假如不承認語言也是一種材料,一味反對把藝術變成純粹語言的嘗試,那么,這種“去物質化”就會把藝術變成“科學、歷史和哲學處理的”首選話題了[5]參見Pamela M.Lee, “Das konzeptuelle Objekt der Kunstgeschichte,”Texte zur Kunst 6, no.21 (M?rz 1996): 120-129.轉引自Sabeth Buchmann,“Language is a Change in Material: On Lawrence Weiner’s Ellipses,” in Conceptualism and Materiality: Matters of Art and Politics, ed.Christian Berger (Leiden: Brill, 2019), 163.。
“十月”藝術批評學派的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認為,格雷厄姆的文本藝術作品將文本的物質性等同于聯系著整個社會系統的物質性,而非材料的物質性。他認為,現實的物質性不再僅僅是“拾得的物品”(found objects)或日常現實中的技術現成品(如霓虹燈),而更多是指那些超越可見現實和外觀具體性的“拾得的”結構。這種結構才是現實的物質性,它憑借微妙的影響力決定著現實,它依賴于主觀行為的心理、生理動機和客觀政治實踐的社會經濟條件,從而達到一種整合效果[6][美]本雅明·布洛赫:《新前衛與文化工業:1955到1975年間歐美藝術評論集》,何衛華等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42頁。。
這種“非物”與“物”的觀念糾結,似乎正是當代藝術中語言材料的二重性帶來的自然結果。近年來,塞貝絲·布克曼(Sabeth Buchmann)借論勞倫斯·韋納的作品提出了較為新穎的觀點。她認為,韋納用油漆、帆布、鋼鐵、石頭來處理信息的呈現,如從墻壁上刮除文字區域的方法,將承載物不僅當作一個信息再呈現和信息再制作的地方,這些承載物(墻、雜志等)不再有古典意義上的物體意義,而是具有了符號的位置意義,通過格式和材料上的變化(刪除、傳輸或添加材料)呈現語言在物質性層面上轉換的條件;而韋納對作品所作的大眾媒體式的排版又意味著材料和媒體的相關參數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了一起。例如,他的書頁上的白色不僅是這首詩的物質支撐,還構成了這首詩的動態和肌理。因此,韋納的文字作品展現的不是靜態的物質性,而是在格式變化和觀者經驗過程中所形成的動態、關系性、生產性的物質性。布克曼還指出,韋納的文字作品恰如薩特對馬拉美的解讀,即詩的語言只有在同時替代和(再)生產客體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物質的地位;韋納認識到,語言有喚起一個對象而非代表對象本身的能力,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語言使自己成為被表現的對象,擁有使材料發生變化的能力,它的物性正體現在這種能力中,而不是以一個可見可觸的實體來實現[1]Sabeth Buchmann, “Language is a Change in Material: On Lawrence Weiner’s Ellipses,” in Conceptualism and Materiality: Matters of Art and Politics, ed.Christian Berger (Leiden: Brill, 2019), 159-177.。
無法否認的是,不論當代藝術作品中的語言是“非物質性”還是“物性”的,接受者都會經歷感官感知和信息接受的過程,甚至會引發聯想、情感反應或產生共鳴。德·迪弗強調,在面對概念藝術時康德古典美學仍然具有活力[2]參見Thierry de Duve, Aesthetics at Large: Volume 1: Art, Ethics, Politic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正是基于康德所提出的“情感共通性”,才得以讓基于文本的當代藝術作品,讓作為當代藝術材料的語言,具有直接的情感效應。
反文本
在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激浪派、概念藝術等流派中,語言材料被簡化為一種被孤立、被打碎、被抽離意義或對象的東西。考慮到當時西方的歷史情境,有人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在那個西方社會運動風起云涌、政治動蕩不安的年代,這些藝術家為什么要塑造這種簡化的、無表情的、非政治化的語言?
一般來講,在20 世紀60 年代的藝術語境中,語詞在圖像中的出現表現為理論說明的形式和口語錄音的形式,假如圖像對觀看者產生直接影響,那么解釋和敘述就發生在圖像之外,文本在圖像中的出現就只能是一種引用的形式,文本和聲音被從外部現實中提取并整合到藝術品中,作為現成品發揮作用。對此,鮑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ys)卻提出反對意見,他指出,這樣的觀點仍然陷于萊辛《拉奧孔》分隔語言(詩歌)和圖像(視覺藝術)的窠臼之中,實際上,相對于文學,圖像因其無言而缺乏敘事性,又因其受阻的語言沖動和被壓抑的語言欲望而不斷突破題材和媒介的限制,它通過特定的藝術策略來傳播信息、傳達想法,通過在圖像表面呈現闡釋性的語言,來表現被壓抑的交流欲望,呈現其所有的政治和詩意維度。這種藝術策略從20 世紀60 年代起一直持續至今[1]Boris Groys, “The Border between Word and Image,” Theory, Culture &Society 28, no.2 (March 2011): 94-108.。格羅伊斯的論點表明,當代藝術中的語言材料,實則是圖像被壓抑的語言欲望意圖釋放的表現方式,它本身便帶有圖像對文本的反抗性,這種反抗性以反常的情況(如基于文本的藝術)來反對理性話語秩序——按照利奧塔的話來說,拯救“圖形世界被困于文本文明的悲劇”[2][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話語,圖形》,謝晶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版,第182頁。,“打破既定的知識形式和話語形式”,以“激進的進步和解放”[3]Guy Callan and James Williams, “A Return to Jean-Francois Lyotard’ s Discourse, Figure,” Parrhesia, no.12 (2011): 48.特性帶著公共創造性能量進入既有話語秩序。簡言之,基于文本的當代藝術具有鮮明的反文本性。
在1970 年的一次采訪中,藝術家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表示,將語言材料作為物質,“是一種有意識的政治立場”[4]Jeanne Siegel, “Carl Andre: Art Worker,” Studio International 180, no.927 (November 1970): 178.。他認為,藝術的目標是恢復我們對周遭世界的現實性的直接感官體驗,而不是通過符號、表象或減少和扭曲“信息”媒介與世界建立聯系。概念藝術中那些中性、平乏、抽象的文字,強迫觀者注視并跳脫出習見的觀看與理解方式,這種語言資源的枯竭和語言豐富性的枯竭,是對敘事和抒情、辯論和政治演講、講述故事或表明觀點的能力的壓抑[5]Liz Kotz, Words to Be Looked At: Language in 1960s Art, 2.。與此同時,這種語言的“反常性”中又體現了否定性和批判性,因為散漫無章的字面性往往是激進隱喻的容器。“片斷是抵制總體性的標志。”[6]汪民安:《誰是羅蘭·巴特》,第247頁。
無論那些一直努力跟上“新唯物主義”“思辨實在論”“再物質化”和“物性”,將語言和話語轉向物質性研究的藝術史家如何邁步追趕,他們也無法否認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社會關系總是通過語言實踐而被意識形態化,語言實踐往往是意識形態活動的中介[7]Jacob Stewart-Halery, “Ian Wilson, Conceptual Art,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Language,” 179.。所以,概念藝術具有激進的意識形態批判維度。厄休拉·邁耶(Ursula Meyer)指出:“概念藝術使作品的思想前提為人所知,這與其他當代藝術形成鮮明對比,后者不關心作品的意圖,(幾乎)只關注其外觀。”[8]Ursula Meyer, Conceptual Art (New York: E.P.Dutton, 1972), xviii.邁耶的這個界定盡管比較模糊,但“思想前提”這個詞凸顯了概念藝術家帶有社會道德異識(differend)[9]“異識”即“異議的情緒”,參見[比]蒂埃利·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沈語冰、張曉劍、陶錚譯,第30頁。的潛在表達動機。上文提及的本雅明·布赫洛則評述得更為直接。他認為,概念藝術那種遠離審美性的文本作品,正是借由美學吸引力的匱乏,而對作為統治秩序裝飾品的文化商品的那種更具手工性品質的虛假妥協進行了譴責[10][美]本雅明·布洛赫:《新前衛與文化工業:1955到1975年間歐美藝術評論集》,何衛華等譯,第145頁。。顯然,布赫洛繼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對文化工業進行批判的立場,發掘了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概念藝術的激進性寓意。語言本身便具有政治潛力。回溯現代藝術史便會發現,早在達達主義藝術中,文字拼貼就具有政治性。概念藝術的興起恰逢1965 至1972 年間美國社會動蕩時期:民權運動、石墻事件、登月、黑人女性政治活動家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被列入聯邦調查局的通緝名單并接受審判,以及越南戰爭的持續。這種情勢便讓人不難理解當時的藝術家為什么越來越反感格林伯格,為什么越來越遠離耽于視覺形式審美品質的現代主義美學,所以概念藝術疏離視覺品質的文字列表式印刷作品本身便可謂是一種政治反應。
金·蒂瓏(Kim Dhillon)在新近出版的《反文本:當代藝術中的語言》(Counter Text: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Art)中批評利茲·科茨等白人英語藝術史學者對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概念藝術的記錄評述忽略了這種藝術的政治維度和民主潛力。她轉而聚焦于20 世紀80 年代以來藝術中文字材料所體現的權力與主體地位間的關系,尤其批判了藝術界潛藏的權力模式。她舉例說,2016 年在英國泰特不列顛美術館舉辦的“英國概念藝術,1964——1979”(Conceptual Art in Britain,1964-1979)展覽參展的21 位藝術家中,只包含了4 名女性藝術家,且都是白人,這種藝術語言的霸權體現在藝術史書寫、藝術展覽等活動所依賴的“一種方向性的模式,一種背后有力量的軌跡”[1]Sara Ahmed, Living a Feminist Life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17), 43.。金·蒂瓏將語言視為一個系統、一種結構,維護著社會中的壓迫性結構,包括但不限于父權制、資本主義和持續的殖民遺產,她所支持的當代藝術中的語言,是那種能夠在作為問題一部分的結構中為主體性騰出空間的語言,也就是說,通過文本來“反文本”、反霸權。金·蒂瓏在書中提及許多新鮮的藝術案例,如美國當代概念藝術家格倫·利根(Glenn Ligon)的作品《無題(黑人的陽光)》[Untitled(Negro Sunshine),2005]。利根的作品主要以語言的形式呈現,但語言的物質性已分崩離析。《無題(黑人的陽光)》題名取自作家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909 年創作的描寫黑人和混血兒的長篇小說《三個女人》(Three Lives)中的語句:“那種讓黑人陽光溫暖的光芒”。利根用暖白色的霓虹燈來表現“黑人的陽光”這個短語:燈管的正面被涂上了黑色的顏料,由此發出的“黑光”被賦予了光亮與陰影的概念。這便陌生化了霓虹燈通常表現出來的樣子,同時又強調了“negro sunshine”這個短語的社會與政治的復雜性。通過將該語句編輯為“黑人”“陽光”兩個詞,并將其摘取凸顯出來,利根“放大”了它,“打破了語言鏈條,并再次對一種虛構的整體性產生了欲說還休的渴望”。通過使斯坦因的文字變得輕盈并重新喚回它們,利根“具體化了產生身份的語言的可取消性和可變性”,“將語言本身作為結構性壓迫的工具進行質疑,從而可能會產生身份構成的新形式,揭示了歷史、語言、權利剝奪和交叉生活之間迄今為止未受質疑的聯系”[2]William Simmons, “Glenn Ligon and Gertrude Stein: Beyond Words,”Harvard Undergraduate Research Journal 6, no.1 (Spring 2013): 28-32.。所以,金·蒂瓏在《反文本:當代藝術中的語言》中論述的案例不僅打破了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概念藝術所秉持的語言中立觀,還顛覆了語言中潛藏的權力,并彰顯了這樣的事實:語言的使用在這里呈現為一種基于每個人生活經歷的世界觀所特有的關系,藝術體驗從根本上說建立在人人享有的、具有民主性的主觀經驗之上。否則,人們就無法想象芭芭拉·克魯格(Barbara Kruger)的作品——如《我購買故我在》(I Shop therefore I am)——會讓每個人有所感觸。
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以語言為材料進行創作的藝術家并不鮮見,其中以徐冰、谷文達、吳山專等為代表。吳山專將一代中國人所熟悉的日常用語、帶有時代痕跡的習見短語作為戲謔、推衍和想象的起點[1]魯明軍:《美術變革與現代中國: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根源》,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07頁。。從形式上看,其作品中的字體遠離書法傳統,紅色文字被疊加強化、過量使用,日常語句的乏味與鋪天蓋地的規模形成鮮明對比,從而產生一種異常的“幻境”[2]吳山專:《赤字的起點》(1986),轉引自艾琦思、劉建華編《吳山專:國際紅色幽默》,亞洲藝術文獻庫(香港)2005年版,第12頁。。吳山專還以無標點的凌亂手稿文本的極端“寫作”方式,企圖耗盡這些字詞的意義及其權力屬性,那些碎片相接的無邏輯文本、奇怪的圖示分析打破了完整的敘事結構,仿佛“一種語言的裝置”,一個“文字的集裝箱”[3]高士明:《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結構——吳山專、托斯朵蒂爾的物權及其他》,《新美術》2015年第2期。,通過“字詞狂歡”及其感性動能將“赤字行動”推向徹底。
當代文本藝術所具有的鮮明的反文本性,延續了彼得·比格爾(Peter Burger)所謂“歷史前衛藝術”的激進性,20 世紀60 年代以來的平權運動和文化多元主義進一步加強和助推了其批判性和介入性,從而促成了更具多樣性的當代藝術景觀。
言語社會
1988 年,時任《美術》雜志編輯的高名潞組織各地藝術家和批評家聚集黃山,為次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做準備。中國當代藝術家耿建翌在會議前親自制作了一份表格問卷,從邀請材料中獲得與會者的通信地址,向每一位與會者郵寄表格并回收。在黃山會議上,他展出了這些填好的表格,還向所有作出答復、符合他的要求并按照所提供的指示行事的人們頒發了證書。耿建翌感興趣的是收件人的反應,而不是他們的實際觀點或喜好(作品的副標題是“吃菜沒有吃肉香”,還提出了有關飲食偏好等方面的零散問題)。這件題為《表格和證書》的作品引起了爭議。不斷被要求填寫表格和出示證書,正是現代社會中普通人遭遇的習以為常的事情,也是敏感者、異見者所經歷的“煩”,不少人認為:這件作品敏銳地表達了藝術家對個人身份、個體與集體之關系的批判性思考。邱志杰認為,“關鍵是他作品里的那種緊張感,那種病態,是日常生活被觀看的社會,被整個社會關系綁架進了那種特別病態的狀態里面,特別有力量”[4]邱志杰:《不是works(作品)而是action(行動)》,高士明主編《關于——耿建翌》,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46 頁。。吳永強等則說:“我們能在他的許多作品中看到對人之‘在世’的荒誕性與悲劇性的揭示與反諷……耿建翌敏感于人與社會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并將其視為值得不斷探索的主題。”[5]吳永強、雍晴:《創傷理論視域下的藝術批評——兼論耿建翌作品〈怎一個“的”字了得!〉》,《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1期。誠然,按照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創傷理論,《表格和證書》揭橥了個人在社會、歷史、當下的各種束縛和控制中的創傷,具有隱喻的否定性,但其創作形式也意味著,語言有一種邀請并要求觀眾廣泛參與的天然能力,從而能夠在對話交流與反饋討論中構建一個語域社會。實際上,從20 世紀60 年代末開始,概念藝術的社會轉向愈加顯著,因為主觀心理行為與客觀社會條件在整體社會系統中是緊密依賴的,這種機制給當代藝術的介入性提供了前提。
在廣義上,語言包括語言系統、言語活動和言語作品。言語是人類運用語言材料和語言規則進行交際活動的過程。弗林特認為,概念藝術“是一種在社會互動儀式中發現新興概念的藝術”[1]Henry Flynt, “Concept Art,” accessed May 22, 2023, https://henryf lynt.org / aesthetics / conart.html.。在他看來,根本沒有形而上的、客觀的、變動不居的“概念”,“概念”只有在自然對話的流程中才是有效的。與傾向于純化、中立化語言的其他主流概念藝術家不同,弗林特是利用言語對話來進行藝術創作的代表,他曾寫道:“所有的藝術都是信息和交流,(做藝術)我選擇了說話而不是雕塑。我把藝術從一個特定的地方解放出來了。”[2]Philomena Mariani, ed., Global Conceptualism: Points of Origin 1950s-1980s (New York: Queens Museum of Art, 1999), 33.他還指出,因為沒有接觸過印刷文字,所以古希臘哲學家的思想大多是通過與人口語交流而生成的,今天的藝術也應該保持這種最初的狀態;口頭交流還是普遍的人類活動,之所以放棄印刷文字,是因為這種媒介的物理形象和二維限制,與難以捉摸的思想主題幾乎沒有共通之處[3]Lucy R.Lippard, “Time: A Panel Discussion,” Art International 13, no.9(November 1969): 20-23.。換言之,思想是無法以物理形式具體化的,而他找到了一種避免概念藝術依賴文獻的方法。伊恩·威爾遜曾與朋友或熟人舉行關于藝術的非正式對話,每次討論結束后,對話者都會被頒予證書以證明對話發生了,這場對話也由此被命名為作品。1970 年,在法國巴黎第18 屆IV.70 展覽會上,威爾遜組織了他最早的小組對話作品,宣布“我的計劃是將于1970 年4 月在巴黎造訪您,并在那里明確口頭交流作為藝術形式的想法”。目錄中還有這樣一句話:“伊恩·威爾遜于1970 年4 月到巴黎,談論口頭交流作為藝術形式的想法。”之后幾年,威爾遜與經銷商、批評家、收藏家和藝術家組成國際合作網絡,在歐洲和北美進行定期對話,他甚至要求經銷商預訂對話,從而將對話作品商品化(物化),以此證明,語言和所有藝術材料一樣,都是可以出售的。例如,威爾遜與藝術商人佛朗哥·托塞利(Franco Toselli)的對話,在公證人的監督下,被后者以1000 美元購買。
言語行為在以口頭交流為形式的當代藝術中具有特殊的機制與效應。就威爾遜的“口頭交流”策略而言,它似乎強調了談話的社交性,而這威脅到了概念藝術家群體中既有的語言思維方式。
首先,作為一個言語藝術作品的創作者/組織者,威爾遜是引導著參與者/聽眾關注交流者/說話者的想法或意向的,后者得到的體驗不是身體上的,而是思想上的。比如,當藝術家說出“時間”這個詞的時候,觀眾被引向他所說的“思維對象”,或言之,藝術家可以用語言來指向一個心理想法,一個由心理學家弗朗茲·克萊門斯·布倫塔諾(Franz Clemens Brentano)提出的“意向對象”(intentional object),所以,這個操作具有意向性。言語的意向性是外向性質,語言的索引性和反射性則是內向性質。
其次,當威爾遜在進行對話藝術創作的時候,新銳的語言學者正在擺脫雅各布森等學者所提出的元語言學模式,轉向“意識理論”,他們認為,在說話者通過其言語事件達成共識并進行語用工作的各種手段中,對句子意義的反思是最為生硬、精煉且外延性最強的意識實例,因為對話的參與者通常通過現有的言語類型——組織話語的傳統框架——來表明他們語言使用的各個方面,幫助他們理解自己的角色及其與他人的互動,而這些角色可能會根據前幾輪的發言者和說話內容而變化,從而允許他們的話語帶有一定程度的反諷和雙重聲音[1]Jacob Stewart-Halery, “Ian Wilson,Conceptual Art,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Language”, 200.。簡言之,在對話過程中,意識左右了意義的生成變換,言語的進行是一種充滿了猶豫、多義的動態過程。正如丹尼爾·布倫(Daniel Buren)的看法,對話的互動動力是威爾遜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威爾遜的工作就是消耗它——他傾聽、打斷、干擾、操縱、反駁,并將自己的智慧發揮到可以接受的最大能力,以參與討論[2]轉引自Jacob Stewart-Halery, “Ian Wilson,Conceptual Art,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Language”, 200.。
最后,言語行為在藝術作品中強化了參與者或觀眾對語言的社會語用功能的認識,也使藝術作品的社會意義得以彰顯。結構主義學者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認為,語言是人類相互聯系成一個關系網和一個完整的社會結構體系的基本紐帶,在某種意義上,語言的結構乃是基本社會結構的典型模式,一切結構之所以能夠形成乃在于語言結構的溝通作用,反過來說,一切社會結構歸根到底都可以還原為語言的結構[3][法]高宣揚:《結構主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頁。。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話語、手勢和其他形式的表達不僅反映了說話者、人物或動作的存在,還引發或構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身份和立場的“社會意義”,這些被藝術家納入作品的言語對話和口頭交流,這些語言、體勢或符號都帶有儀式性或象征性痕跡,帶有當下的政治經濟痕跡。在言語交流中,該痕跡被強化、改變、混合,從而在實現社會語用功能的過程中將作品的意義延伸到更廣闊、更地方性或參與性的政治或社會維度中,也更能讓觀眾理解與反思社會符號及其可塑性。
作為以語言為材料的當代藝術的一種類型,言語性作品包括演說、對談、采訪等多種形式,它憑借機動性、儀式性和民主性特點,通過種種破界策略(如視聽之界、作者與觀者之界),日益成為活躍于網絡時代的藝術類型,但其效應仍有待深入研究。
東方字陣
從20 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徐冰和谷文達一直致力于將視覺藝術漢字作為材料或媒介。如果說吳山專的《今天下午停水》拷問的是個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那么這兩位具有海外經歷的藝術家則致力于創作出在傳統與當代、東方與西方、民族與世界等層面上具有文化象征意味的作品,其創作也由此呈現出多義性和矛盾性。
漢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是國際視野中的中國符號。在跌宕起伏、風云變幻的20 世紀中國歷史上,在現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開放與堅守、變革與繼承的張力下,漢字作為一種表征,寄托了幾代人的國族理想與文化想象,它自然而然、恰切適宜地成了藝術家捕捉現實、表達思想的載體。有學者認為,徐冰和谷文達的作品體現了“中國符號的勞動競賽”[4]王南溟:《中國符號的勞動競賽》,《大藝術》2004年第1期。。
從1987 至1991 年,徐冰以漢字為型,創造了四千多個“偽漢字”,采用明代宋體字手工刻板活字印刷的方式,印制成一套四冊長達幾十米的長卷,題名為《析世鑒——天書》(后改名為《天書》)。這些“文字”乍看上去形似真的漢字,細觀則陌生如異體字,但又并非延續晚明文人創造異體字的傳統[1]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69——178頁。,而是通過表意功能的喪失而追挽漢字傳統文明,追問未來世界里漢字進化的可能性。魯明軍認為,《天書》沿用傳統技術和語言形式來擾亂漢字結構,消解漢字表意功能,實則暗合了20 世紀80 年代激進的“反傳統”思潮,但是這種“反傳統”不是拋棄傳統,而是繼續和發揚傳統,創造出過去的中國人不曾有過的、新的、現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徹底重建整體文化形象[2]魯明軍:《美術變革與現代中國: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根源》,第212頁。。
除了這種解讀之外,《天書》還呈現出一個延續到徐冰此后文字作品中的面向,即一種面向西方的東方主義想象,一種“普天同文”的烏托邦設計。在近代西方人描繪東方的圖像中,不可識讀的偽漢字屢見不鮮,如1845 年英國畫家托馬斯·阿羅姆(Thomas Allom)依據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懷特(White)中尉的素描繪制的銅版畫,畫中牌坊等建筑上銘寫著嚴謹排布、精心書成的偽漢字(圖3、圖4、圖5);在1896 年美國《馬蜂雜志》(WASP Magazine)(圖6、圖7)刊登的一幅以李鴻章出訪美國為題材而作的漫畫上,李鴻章手中所握紙上的“漢字”也是作為符號的偽漢字。這些偽漢字都營造出了一種東方的“真實感”,它是西方對中國所做的“總體性的圖像象征”[3][美]巫鴻:《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肖鐵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頁。的組成部分,既體現了一種對東方方塊字的文化想象,也暗示了薩義德所說的被“東方化”了的東方主義[4][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5——8頁。。以此為參照,《天書》恰恰呼應了中國近代早期“開眼看世界”之時西方人“另眼看東方”的目光[1]這一思路與圖證得到了正在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攻讀藝術學理論專業碩士的宋啟元先生的啟發,在此致謝。,從而為20 世紀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國重新接觸西方、接軌世界的歷史標記下更具張力的文化符號,也體現了藝術家對中西文化碰撞與對話這一問題的思考。徐冰1993 年的作品《英文方塊字書法》,將英文單詞的字母拆解,按字母順序以漢字結字方式和中國書法書寫方式重組為類似的結構。他試圖以這種表征和媒介來探究中西語言或文化的對話及文明的共處[2]魯明軍:《美術變革與現代中國: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根源》,第214頁。。約10 年后,他用從日常社交媒介中收集來的標識和符號創作出小說《地書》(2003),嘗試建立一個打破教育、民族、國別的區隔,僅靠生活經驗即可閱讀的“普天同文”的語言烏托邦[3]王寅:《他又發明了一種“世界語”?》,《南方周末》2007年6月21日第24版。。實際上,到了《地書》,徐冰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跳出了原先作品中的東方主義拘囿,接軌了20 世紀70 年代概念藝術以來強調信息傳遞和互動交流的當代藝術的社會面向。

圖3 《通往廈門城的牌坊》(Gate Way to Xiamen City),1845年,銅版畫,圖片引自[英]托馬斯·阿羅姆:《大清帝國城市印象——19世紀英國銅版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圖4 銅版畫中的偽漢字(圖3 局部)。

圖5 銅版畫中的偽漢字(圖3 局部)。

圖6 《馬蜂雜志》刊登的漫畫《李鴻章訪美可能造就一個現代的中國》。

圖7 漫畫中的李鴻章手持“我的美國見聞日志”(圖6局部)。
徐冰創設的是偽文字和異體字,谷文達則選擇了錯別字和合體字。他以錯字為材料進行創作,以此表明在文化一元主義的情境下,單字的錯形并不會從實質上影響文本信息的傳達。《谷氏簡詞》通過“合二為一”“邊旁代字”“原字為詞”等方法將成對的簡體字拼合為一體,構造成足以表義而又新異的單個漢字[4]黃專:《水墨煉金術:谷文達的實驗水墨》,嶺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頁。,實際上,這是通過對漢字造字符的重組,探討符號賦新而表義的新的可能性,從而探究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追問既有認知觀念的格式塔效果及其影響。
不論是徐冰還是谷文達,都通過使用漢字的結構特征和文化意涵,展現出某種東方式的奇觀。從某種意義上講,二者對漢字展示化效果的探索,觸摸到了漢字在中華文明初始、生成和延續中沉厚有力的脈搏。考慮到他們作為國際藝術家的特殊身份,又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在從后殖民主義到全球化再到文化沖突和地緣政治沖突的歷史背景下,他們的作品折射出的某種跨文化性的國族想象和文化共通的烏托邦理想。
當代藝術的異彩紛呈,既體現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外部情境,又展現了藝術媒介的邊界拓展。語言作為當代藝術創作的一種材料,呈現了如前文所述的種種特點,也向觀者和學者提出了不限于前文所論的眾多問題。只有結合實際藝術案例考察分析,拋卻因襲保守的傳統思路,才能跳出美學或藝術學的學科框架,從跨學科、跨文化、跨媒介的角度,加深對這種藝術現象的理解,提出具有豐富啟示意義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