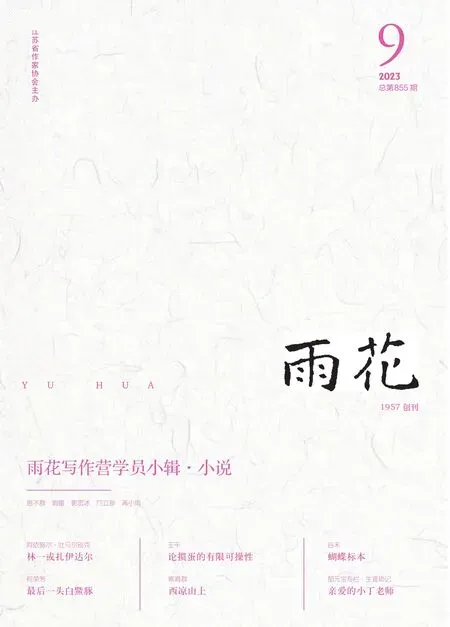月光灑滿溝渠
響 雷
在十歲左右的時候,我變得不喜歡像正常人那樣走路。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不正常,我自小乖順懂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拎得很清。我甚至有超出同齡人的成熟,跟那些上房揭瓦的小毛孩站在一堆里,我會覺得自己是個大人。因此,長輩們教育子女總拿我做榜樣,他們見了我,夸我乖、聽話、懂事,于是我越發地老實聽話,仿佛不如此便辜負了他們。這讓我有些不自在,仿佛但凡有一點點出格之舉都會自毀形象。
在走路這件小事上,我確是辜負了他們。盡管大人們一再教育我路該怎么走,不能田里一腳岸上一腳。他們說得都對,我也明白走路該有的樣子,可我就是不高興那樣做。我尤其不喜歡貫穿村子南北的那條足有四五米寬的大馬路。那時它還沒有鋪上瀝青,晴時灰塵迷眼,雨天鞋不跟腳,我不是因為它破爛而不喜歡它,我不喜歡它是因為我更喜歡在溝渠里走。
緊挨大路的兩側,路西一條排水溝,路東一條灌溉渠,溝緩而深,渠陡而淺。灌溉季,渠里有水,我便從排水溝的坡上走,蘆柴青草里被我踩出一條蛇形小道。非灌溉季,渠中干涸,我便從渠里走。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渠,渠雖陡,底卻平坦,好走。走溝渠有個好處,不用避讓汽車、拖拉機、自行車,也不用跟認識的人打招呼,直來直去,通行無阻,冬天還能擋西北風。當然,跟你說這些不是叫你學我不好好走路。
怎么又站起來了?坐啊,以后跟我說話別拘束,隨意坐。
你不愿意聽是吧?我們換個話題吧,我們來說說你爸小時候。你爸從小學到初中跟我都是同學,在一起讀書九年,很難得的。你知道吧,你爸小時候可調皮了,真的。課堂上也調皮,偷偷告訴你,他有一次在課桌上畫棋盤,被老師發現了,罰他跟同桌下課時扛著桌子到教室外示眾,哈哈,你笑了,你也覺得好笑是吧,笑就笑出來,別憋著。他還非常壯實,體育成績全班第一,爬樹掏鳥窩,下水摸魚蝦,翻墻摘桃子,沒有一樣能難住他,他算是我們那一片的孩子王。現在啊,我倒寧愿你能像你爸小時候那樣,可著勁兒地調皮,不打緊的,孩子就該調皮,天不怕地不怕,調皮就是活潑,知道不?
好,點頭說明知道了,但我希望你能大聲說出來。嘴巴不光是用來吃飯的,還可以說話、唱歌、吹口哨。吹口哨會吧?像你這么大的時候,我們都會吹口哨,能吹出一整首歌的調子。你爸還會用小麥葉子吹《上海灘》,“浪奔、浪流……”非常地清脆響亮,他常常在我們后面冷不丁一吹,嚇得人脖子一縮。當然,我可不是在你面前說你爸的壞話,我只是告訴你,像你這么大的時候他也非常調皮。我當了十多年的老師,發現每個孩子都調皮,只是有的大調皮,有的小調皮。調皮其實就是活潑,作為孩子,調皮是跟別人溝通的一種方式,你呢,應該也會調皮吧,只是你沒有表現出來,或者不敢表現出來。以后慢慢放開點,知道嗎?今天你能認真聽我說,已經比前幾天進步很多了。耐心地聽人講話也是一種溝通方式。比如在課堂上,你如果能就這樣安靜地坐著,多好呢。
好了,今天就聊到這兒,奶奶在校門口等著呢,你先回家。
再見,小吉。
師專畢業,我被分配到了縣城的實驗小學,一晃就是十多年。那是全縣城數一數二的小學,多少教師、學生想進而不得進。就在我城里的房子裝修完畢,準備從農村老家搬出的時候,教育局以均衡教育的名義把我均衡到了離城三十多公里的草集小學。雖然愛人對此諸多抱怨,我卻沒有一句廢話,因為那里是我的母校,我曾在那里度過了六年時光。草集小學離我老家三里多路,走過去也就二十分鐘,為了照顧愛人的感受,我選擇晚上住進城里的新房,無非多耗些油費。
農村的小學不及城里的熱鬧,不為別的,主要是人少,出早操的時候操場上稀稀拉拉的。班級少,每個班的學生也少,相對而言教師不缺,這樣算來有個好處,工作量沒先前那么大。我帶的是四年級的一個班,全班只有二十八人。開學第一天,學生對我很陌生,我也對學生很陌生,這不難,先作自我介紹,然后點名,對不上號的喊起來回答回答問題,根據以往的經驗半天基本能認全。可是開學第一天,在點到小吉的時候,卻沒有人喊“到”,我所說的小吉當然不是真名,原諒我不方便透露。我喊了兩遍名字,沒有回音,便跳過了。教室里確實缺了一個學生,最后一排有個座位空著,課桌上放著書包,說明人應該到校了,可能上廁所去了吧,等等再看。課講到一半,那座位依然空著,我問班長,小吉哪去了?班長說,他在外面。我說,在外面干什么?班長說,不知道,他一直就這樣。我說,你去把他喊回來。班長小聲說,我不敢。這讓我很驚訝。為了不影響其他學生正常上課,下課之后我讓班長帶我找到了小吉。
這小家伙瘦長的個兒,大大的腦袋,像根火柴,兩臂從短袖里伸出來,曬得像兩根燒火棍。我喊他時,他正伏在圍墻的柵欄上,對著外邊的馬路出神。也許受了驚嚇,他一聲怪叫頭也不回地跑了。班長趕緊落荒而逃。我在操場上老鷹捉小雞似的把小吉追到手,捏住他的臂往教室里提。他殺豬般的持續尖叫比超聲波還要刺耳,把操場上玩耍的學生統統嚇進了各自的教室,同時也把校長和老師們引了過來。校長一邊小跑一邊朝我喊,我完全聽不清他喊什么,看手勢是讓我把人放了,我手一松,小吉便兔子似的躥了。然后我在眾老師的見證之下被校長好一頓教育。你可以招惹我,但不能招惹他,校長最后這樣跟我說,他的意思很明確,你就當班上這個學生不存在。他越是這樣說,我越是想瞧瞧這是個何方神圣,連校長都退避三舍。
上課鈴響,大家散去,我接下來沒課,操場上就剩下小吉和我。我站在操場中間小型足球場的白圈里,他繞著紅色橡膠跑道閑踱。雖然操場上就兩個人,我想辦公室或者教室里一定有無數雙眼睛盯著這里,我不敢校長屁股一轉就公然違背他的命令。所以我沒有再去招惹他,我們像地球和月亮那樣遙相呼應又相安無事。
小吉的情況全校師生幾乎都知道,隨便找個人聊聊都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我剛到草集小學那陣兒,不用問也會有人興味盎然挑起話題,仿佛那是他們茶余飯后的甜點。
那是個問題兒童,老師們這么給他定性。他三年級時轉學過來,上課有時突然發神經似的怪叫,嚴重影響其他學生上課,所以經常被老師趕出課堂,次數多了,他主動不上課了,習慣于在室外閑逛,老師也懶得理他。他在學校里沒朋友,同學們也不敢跟他玩,有個高年級的學生踢球不小心碰了他,被他反手抓破了臉。學生家長們都把他當作危險分子看待,囑咐孩子離他越遠越好。由此惡性循環,他在校園里幾乎成了流浪星球,所過之處一片荒蕪。而我經觀察發現,這孩子一不調皮二不搗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主要問題在于性格孤僻,缺乏有效的溝通。
幾乎每個問題孩子背后都有一個問題家庭。不少人都這么認為,我也深以為然。治病得找根,我決定先做一次家訪。當我看了小吉的檔案資料后,我又猶豫了。他父親叫吉春,這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家庭地址確認了這個吉春就是我所認識的吉春,那個小學初中同窗九年的同學。他的境況我大體知道些,初中畢業后闖蕩社會一段時間,后來去南方打工并在那里成了家,去年離婚了又回了老家,在鎮上租了一間門面房,修理摩托車、農用車。此前我一直住在農村老家,上下班經常會從他的店門前路過,可是我從沒主動跟他打過招呼,他總是屁股朝路蹲在車旁,一身油漬。我說這些完全沒有瞧不起老同學的意思,我們上學時就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并沒有多少舊可以敘,勉強寒暄只會尷尬。經過三天的思想斗爭,我還是硬著頭皮去了他家。好吧,一切為了孩子。
可是吉春并不在家,我既松了口氣,又有些失落。吉春娘見老師來家訪很是局促,喊我坐,找杯子找水瓶,問我吃了沒,我說吃了她說再吃點,拉扯了好一陣總算安頓了下來。小吉自始至終趴在房間的書桌上看書,頭都沒抬,當我們不存在一樣。我很好奇,他怎么會這樣安靜地看書。吉春娘小聲說,不看書不行啊,他爸回來要是見他不在學習,準得脫層皮。我說,他真在學習嗎?吉春娘說,我不識字也說不上來,他爸對他管得緊,要他將來考大學,他現在成績不理想,他爸都急瘋了,還說要掙錢到城里買房,把他轉到城里去念書。
我便跟吉春娘閑聊,邊說話邊等吉春,我們談一會兒就看看時間,斷斷續續,直坐到九點,我說,吉春怎么還不回家?吉春娘說,怕是今天又不歸家了,他跟鎮上一個理發的談上了,三天兩頭往人家跑。我說我走了,吉春娘很過意不去,說下回讓吉春專門去拜訪我。我說不用了,該了解的我都了解了。是的,經過簡單閑聊,小吉的情況我已大致了解,要想改變他恐怕不太容易,所以走的時候我跟吉春娘說,以后每天推遲一刻鐘來接小吉,我得跟他聊聊。
小吉需要重返課堂,障礙在于他隨時可能發出尖叫。他的尖叫不但具有定時炸彈的不確定性,還具有核彈的輻射性,整個校園都在他的輻射半徑之內,傷害性極強。我領教過一次,并因此理解了前任班主任和校長的無奈。
小吉的尖叫并非天生,而是從他媽媽那里學來的,這僅是我的推測。據吉春娘說,吉春脾氣臭,還沒離婚的時候,經常對媳婦拳腳相向。有一次回來過年,年夜飯正吃著,吉春怪媳婦勸他少喝點,酒杯一放就打得媳婦鬼哭狼嚎,那尖叫幾里地外都聽得見。如果小吉在這種環境下長大,學他媽媽不是沒有可能。加之他性格內向,不善交流,在南方上學時,他一個外地孩子融入班級和校園也不容易。回到當地,再次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這無異于是對他適應能力的又一次考驗。很顯然,他經不起考驗,他一敗涂地。
據前任班主任描述,小吉在課堂上的第一次尖叫,是她從教以來遇到的最嚴重的一次意外事件。她是個年輕女教師,對孩子們非常和善,她僅僅是發現小吉開小差,便向他提問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小吉答不上來,她順勢教育了兩句,他便火山一樣爆發了,嚇得全班孩子像小雞一樣亂竄,她也一下子嚇得六神無主。有了第一次,她再不敢對他提問了,以為相安無事便能歲月靜好,哪知道他又一次突然發作,有了前一次的教訓,她毫不猶豫果斷出擊,沖過去把他提出教室。事后了解,可能是同桌拿了他的橡皮,捏著不還。事出雖有因,但根本問題在于小吉心理脆弱,反應過激。
為了讓小吉回到課堂,我跟他已經建立了良好的溝通,連續幾天的交流,他從最初的不理不睬到漸漸有了回應,對我講的一些故事或者道理漸漸有了認同,漸漸開口說話。他告訴我,他非常怕他爸爸,爸爸要他認真學習,就算在家也沒有半點游戲時間,除了學還是學,學不進也得把頭埋在書里。他的成績可想而知,經過我的簡單測試,他其實語文尚可,據他說,他喜歡在教室外聽同學們大聲朗讀,哪個班讀就到哪個門外偷聽,他尤其喜歡聽同學們朗誦詩,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他把《小學生必背古詩詞》背得滾瓜爛熟。其他學科就沒什么可說的了,數學基本停留在一二年級水平,英語更是白紙一張,進不了課堂又怎能學得好呢?當然,他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在學校不上課,要是知道了,他估計會被打斷腿。你愿意上課的時候坐到教室里嗎?我問他,他點頭說,想。你能保證在課堂上不發出尖叫嗎?他想了一會兒說,能。情況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盡管如此,我不確定他真能保證不再發出尖叫,但我還是想試一試。為此,我專門開了班會統一全班學生的思想,小家伙們異口同聲說愿意接受他、幫助他。可是第二天上午,校長找我談話,說我們班的不少家長找了過來,要求給孩子調班,如果不調班就調班主任。校長說,為了一個小吉,得罪整個班級,這不是明智之舉。確實是這樣,在校長警告過之后,如果我再貿然點燃引爆線,無異于引爆自己,想想還是從長計議為妙。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十月份。中秋節前夕,學校組織了一次全校性的“詩詞大會”,跟風電視節目,純屬自娛自樂,不過,在小學生看來還是挺有新鮮勁兒的。我毫不猶豫地給小吉報了名,雖然校長懷疑我有故意搗亂之嫌,最終還是接受了我的意見。其實,他內心里也很希望小吉往好的方向發展。
校長這一關好過,小吉的關卻難過。我知道,他是害怕曝光于大庭廣眾之下。好在我苦口婆心加威逼利誘,他終于從搖頭到點頭。別以為事情就此了結,更大的問題是分組,游戲規則是每個班級出三名學生,小組淘汰制。班級里選出來的學生都不愿意跟小吉一組,這不怪他們,我只好另想門路。經過我的積極爭取,以及校長的一錘定音,團體賽之外再開設一場個人賽。反過來我又去做小吉的思想工作,單槍匹馬出戰怕不怕?沒想到他這回頭點得挺快,他覺得跟其他人配合反而不自在。為把整個事情搞順,我多方奔走,既當了舌戰群儒的諸葛亮,又當了過五關斬六將的關云長。
比賽的過程我就不說了,肯定不及電視節目的萬分之一精彩。小吉最終也沒能發揮正常水平,雖然賽前我一再提醒他不要緊張,但他顯然還是緊張了。這是我的錯,我知道從心理學上講,越提醒越容易增加他的緊張,但我總是忍不住,說到底是我比他更緊張,我非常非常擔心他一緊張就發出尖叫。我不想詳細描述比賽的過程,是因為我對賽況毫未關注,把心全都落在了小吉身上,我把寶也都押在了小吉身上。我看到他的手在桌子上篩動,聽到他搶答時聲音在顫,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關進了攪拌機里,從教十余年練就的泰山崩于前而不動的定力簡直不堪一擊。我知道,同樣緊張的還有校長。現場氣氛很熱烈,老師同學們都在為自己的班級加油,而我瞥了一眼學生面前向來笑容滿面的校長,他的臉像個干癟的土豆,一動不動朝著小吉的方向。這使得我更加緊張了。因為我跟他做了一次對賭,如果小吉在活動中通過考驗,他將排除一切阻撓讓他進課堂;如果失敗了,本學期內此事免提,并且由我請他喝頓酒。喝酒的條件是我主動加的,他說他不在乎我這頓酒。對我來說,只要小吉不發出尖叫,就是這次詩詞大會最大的成功、最大的勝利,名次不名次那都不要緊。好在小吉爭氣,不但沒有尖叫,而且躋身個人賽優秀獎,排在末位(獲獎人數占參賽人數一半),雖然他自己一再嘆息沒有發揮出正常水平。站在領獎臺上,在全場的掌聲里,在照相機的閃光燈下,小吉突然用榮譽證書遮住臉,渾身顫抖蹲了下來。掌聲驟停,全場安靜,我聽到一絲壓抑的、沙啞的,仿佛從地底下傳來的聲響,繼而他慢慢站了起來,舉起火紅的榮譽證書,我看到他臉龐上淚光閃閃。
好!我大喊一聲,全場跟著嚷嚷起來。我知道,他這是多大的忍耐力啊,就算是激動的、高興的吶喊也憋著不讓自己發出聲來。
活動結束,校長走過我身邊時拍拍我的肩,面容和藹可親。我說,改天請你喝酒。他說,我來請你。
我始終認為,情況正在按照我設想的樣子變得越來越好,直到小吉走進了課堂后的一個星期。那天放學,小吉的爸爸,也就是我老同學吉春出現在我面前。一般家長接孩子,只能在校門口等,不能進校園,那天門衛給我打電話,說有個家長要找我,我同意了。
吉春見了我,叫小吉先到操場上玩會兒,他要單獨跟我說幾句話,這也沒什么,有些話確實不方便當著孩子的面說。小吉走后,他遲遲不開口。我寒暄說,好多年不見了啊。他點點頭,突然“撲通”一下跪到地上。這讓我猝不及防,趕緊扶他起來,如果說是我改造了他的兒子,也不至于以這種方式謝我。他賴了一會兒,總算起來了,我們就近坐了下來,隔著一條過道,像鄰桌的同學那樣。
我求求你。他說話時兩肘撐著課桌,把十指插在稀疏的頭發里,像在跟桌子說話。
我一頭霧水,問他什么意思。
他說,沒什么,我就這么個兒子,我不希望他將來跟我一樣沒出息。
小吉最近很好啊,詩詞大會還獲了獎。我說。
我的兒子我知道,他成績不好,但是還算用功,不像我小時候無法無天,我想,只要認真刻苦,相信他將來會好起來的。
是的,一定會好起來的。我說。
他一臉苦笑,我最近在縣城看了一套二手房,等買下來,轉了戶口,下學期就能轉學了。
好好的,干嗎要轉學呢?我愣了一下。
我求求你,放過我兒子,有事沖我來。
我怎么著你兒子了?我有些惱了。
最近,聽我娘說,上學放學的路上,他都不愿坐電瓶車,非要下車,從灌溉渠里走。
我笑說,只要他樂意,這也沒什么不妥,至少不會影響學習。
回來我問他,為什么好好的路不走要走灌溉渠,他說,他的老師小時候也走灌溉渠,然后我才知道是你當了他的老師。
你關心他的學習,連他老師是誰都不關心嗎?
不怕你笑話,從小我就怕老師,到現在還是害怕跟老師接觸。
所以當年我鐵了心想考師專,將來當老師。我半開玩笑地說。
他也笑了笑,說,過去的事是我不對,我給你賠禮道歉,你別整我兒子,讓他安心把這學期學完,我給你當牛做馬都行。
我從沒有整過你兒子,也不會吃飽了撐著要整你兒子,我們過去的事,我從沒有跟小吉提過,關于走灌溉渠的事,我僅僅是為了告訴他,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沒想到他感興趣,但這不是壞事。我說,作為老同學,我建議你不要再給他轉學了。
我只是想給他上最好的學校。他說,我只能做到這樣了。
我無奈地笑笑。小吉玩了一圈,跑到了教室門口。我們都扭過頭去看他,他又靦腆地縮到墻后。
他跟我小時候一樣,膽子小。
你膽子小?我笑說。
真的。他說,我那時仗著長得壯些,到處欺負人,就是想讓別人都怕我,其實我膽子很小,又不想讓人知道我膽小,你也知道,我從小沒有爸爸。小時候的事真的對不起,你別往心里去。
放心吧,陳年舊賬,早就銷了。我說,再說,小吉這孩子我很喜歡,我怎么會針對他呢?
他愣在那里撓頭,似乎很糾結。
我說,你先帶他回家吧。
他站起來跟我握了一下手,眼神游離不安。我坐看他們的背影消失在窗前,小時候走溝渠的那些往事像暴雨降臨前的魚一樣又一次浮出水面。
當年,村子里跟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有六個,放學都是一路玩到家。不知何時,吉春學來了一種游戲,叫作“打泥仗”,也就是六人分作兩派,一派埋伏在溝里,一派趴在渠里,隔著馬路互扔土疙瘩。這種低級的游戲我實在提不起多大興趣,于是斷然拒絕并嗤笑一聲。這樣一來,就剩下五個人,三比二有失公平,不好組隊,玩不起來。是我掃了大家的興,吉春便聯合其他四個孩子孤立我,從此以后不帶我玩了。不玩便不玩,其實我對跟他們玩一點興趣都沒有。吉春見我遲遲不向他求饒,有些惱怒,后來發展到連馬路也不許我走,我只能走溝渠。
剛開始我很難過,這太欺負人了,后來走走竟然發現,走在溝渠里還挺有意思。溝渠邊,茅刺、蛇莓、枸杞、節節草、婆婆納,那些當時都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平時沒有低頭細看,這會兒全都送到眼前,我像逛百草園一樣走走停停。這園子百逛不厭,我在里頭穿過春夏秋冬,我在里頭看過日出日落,在里頭扒過鱔魚洞、老鼠洞,總之,這里頭的樂趣是他們永遠體會不到的。
后來上了初中,比起小學來,上學時間更早,放學時間更晚,我們都開始騎自行車上學。遺憾的是,車不可以在溝渠里騎,為了跟他們保持距離,我總是落在后面慢悠悠地騎。那時以我們的身高,屁股還夠不著“二八大杠”的車座,只能跨在車杠上。他們有時賽車,我在后面看著五個屁股騰起來,在車杠上忽左忽右扭來扭去,總是忍不住想笑,這群幼稚的家伙。有一次下晚自習,他們騎得好好的突然開始比誰慢,我沒提防就趕上了他們。我懷疑他們是故意的,他們五輛車一字排著,輕而易舉把我別下了渠里。我翻下去的時候聽到他們吹著口哨揚長而去。
我慢慢爬起來,所幸冬天衣服厚,除了腳踝扭傷,其他沒什么大礙,但是車受的傷就比我嚴重多了,龍頭歪了,擋泥板折了。我想把車弄上去,試了幾次都沒能成功,渠的壁實在太陡了。那時大約晚上八點多鐘,農村的路上黑燈瞎火,已經沒有什么人走動了。我把力氣折騰盡了,想先走回去又怕車被人撿了去,那可是我家為數不多的略值點錢的資產之一。一時萬般無奈,萬念俱灰,我一頭倒在渠里,真想大哭一場。
躺著躺著,心便靜了。心靜了,便發現夜沒那么黑,月亮在上面陪著我,離我那么遙遠,卻又近在眼前,它像講臺上老師的目光,注視著每一個角落。渠邊的枯草漸漸清亮起來,我聽到霜花盛開的聲音。我幾乎就快忘記我和我的車還摔在渠里,忘記我還要回家,要不是回汗之后越來越冷,我都快睡著了,我差點以為剛剛發生的一切就是一場夢。是一陣車響驚醒了我,有人路過,我趕緊爬起來呼救。巧的是,幫我把車從灌溉渠里扛上來的正是我那身材瘦小的班主任老師,她下班回家與我同路。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那晚的月亮多么皎潔,它把老師的白色滑雪衫照得銀亮,并把她手上、袖上新沾的污漬照得清清楚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我的記憶里總是分不清哪是月亮,哪是老師白凈的臉龐。
此后,我總是在下晚自習后多看一會兒書,等老師收拾完了一起走。我們騎著自行車,有時并排而行,有時一前一后,有時忽前忽后,我再也不用心懷忌憚、小心翼翼,我可以像老師一樣勻速前行,也可以猛蹬一陣沖出老師的視線,我甚至可以慢下來,靜靜欣賞起明光高照下的鄉間田壟。那灑滿清輝的溝溝渠渠,像極了美術老師在黑板上勾勒出的粉筆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