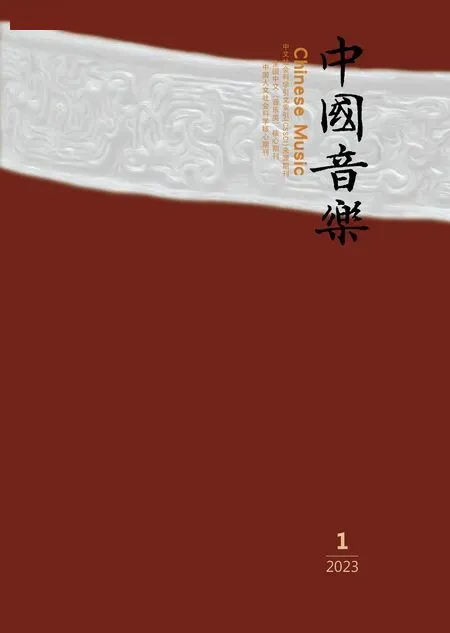紀實影像的“深描”與民間音樂的“闡釋”
——以《大河唱》個案探討音樂影像志的文化實踐
○楊宇菲 雷建軍
音樂影像志作為音樂、影像與人類學田野研究三者結合的產物,如何將融匯著文化體系的地方社會日常生活呈現為視覺化的聆聽與聽覺化的觀影?紀實影像如何“深描”民間音樂文化,而民間音樂又如何“闡釋”文化的精神氣質(ethos)與生活世界(lifeworld)?拍攝者、拍攝對象與觀影者之間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音樂影像志,究竟做什么?還可以做什么?本文試圖聚焦紀錄電影《大河唱》項目的整體創作過程,基于音樂人類學田野調查、紀錄電影田野拍攝以及觀影互動三個階段中團隊成員的田野手記與訪談資料進行反身性思考,將音樂影像志作為一種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探討音樂影像志如何在記錄歷史與當下、共享音樂影像的過程中,讓拍攝者、拍攝對象與觀影者共同完成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文化表達,將傳統民間音樂的文化資源帶回現代生活場域,更好的讓音樂影像志參與構建當下多元的文化生態。
一、音樂影像志何為
已有學者分別從影視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的視角對音樂影像志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梳理。從影視人類學的脈絡看,朱靖江指出,借鑒搶救人類學、分享人類學等理論范式,音樂影像志能夠為音樂學者的音樂調查進行文化賦值,強化社會語境,提供主位發聲的地方性知識,以象征性和聯覺性建構多元的音樂文化敘事,促進民族音樂的跨文化交流。①朱靖江:《基于影視人類學視角的音樂影像志理論與方法研究》,《民族藝術研究》,2022年,第4期,第121-128頁。從音樂人類學的視角看,音樂影像志與生態音樂學的學術關懷密切相關,蕭梅及其團隊以整體性的生態視角關注聲音/音樂、文化/社會、自然/環境之間的交互關系,在“傳統音樂資源與當代社會對話”的理念下進行音樂影像志創作,拓展傳統音樂的探討實踐空間。②蕭梅:《“生態音樂學”團隊的理念與實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第9-18頁。劉桂騰指出音樂影像志并非“音樂+影像的‘志’那么簡單”,而是基于音樂學問題意識進行學術表達的“影像文本”,強調基于事實進行摹寫、建構與復原。③劉桂騰:《鏡頭是學者的眼睛—音樂影像志范疇與方法探索》,《中國音樂》,2020年,第2期,第12-22頁;劉桂騰:《摹寫·建構·復原—音樂影像文本的生產方式與真實性》,《中國音樂》,2022年,第2期,第100-110頁。徐欣觀察到“華語音樂影像志展映”不僅呈現音樂遺產的生態,而且影像也成為一種民間音樂的遺產化與再遺產化進程,系統化以數字媒介進行傳播與保護。④徐欣:《音樂遺產及其當代性的影像敘事—記上海音樂學院首屆華語音樂影像志展映》,《中國藝術時空》,2019年,第6期,第44-49頁。可見,音樂影像志凝聚了不同學科的共同關注:(1)對傳統民間音樂的搶救記錄與學術解讀;(2)民間音樂與地域文化生態、當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聯;(3)影像書寫中學者與文化持有者之間主體性表達的平衡。而這些議題背后的核心仍是透過音樂與影像深描不同人群的文化邏輯,以期洞悉和體會不同社會文化語境下人類對生活世界的多元闡釋。
對于以上議題,2019年院線公映的紀錄電影《大河唱》均有涉及,也啟發我們持續反思整個創作過程。實際上,自2016年開啟到2019年紀錄電影《大河唱》上映,“大河唱”項目并未結束。基于西北民間音樂的田野工作,我們后續完成了以民間藝人為線索的《大河唱》分集版;出版電影書《大河唱》,讓團隊成員講述制片、田野拍攝、后期剪輯過程的所思所感⑤《大河唱》劇組編著:《大河唱》,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基于前期音樂人類學田野調查出版了《四個中國人Ⅲ》⑥蕭璇、楊宇菲、楊靜、雷建軍:《四個中國人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年。;將田野收集的花兒、說書、皮影、秦腔等傳統歌詞戲本結集出版了《在歷史的邊緣歌唱》⑦雷建軍、李瑩、彭瑾編著:《在歷史的邊緣歌唱》,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此外,導演之一的楊植淳繼續深耕皮影田野,幫助皮影藝人進行快手直播,并繼續拍攝完成影片《皮影,電影和快手》以及博士論文。紀錄電影《大河唱》更多是一種在影院環境與公眾交流的方式,相繼完成的分集版在網絡發布則補充電影版未能展開的人物故事,各個導演的后續成片亦基于不同學術視角進行深化表達,而在田野素材基礎上完成的相關書籍則容納了影像素材中視覺性不強的大量口述史、訪談及歷史脈絡。而所有這些素材都是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團隊成員基于對傳統民間音樂與土地的關系、傳統文化與當下社會碰撞的共同關注,共同在田野生活中反復思考與挖掘討論的成果。如果基于單一學科的問題意識進行田野拍攝,或許會錯失生活世界的不同觸角與多元敘事的可能。而觀影反饋的豐富維度也一定程度反映出西北民間音樂與當代都市觀眾會因共通的生活世界與情感體驗而產生共鳴,進而從自身生命經驗中完成影片的意義生產,讓傳統文化從遺產語境中被拉回到現代生活場域,獲得新的社會生命與文化意義。
因此,當我們跳出靜態的“文本”視角,將音樂影像志作為一個文化實踐的過程來看,可以看到這個過程不僅可以記錄音樂生態、介入民間音樂“遺產”保護、進行學者化表達,同時可以讓民間音樂作為文化資源介入現代性問題,拓展音樂或影像的學術議題,進行活態化傳承保護。而且,學者、影像工作者與文化持有者基于田野生活的互動而實現互主體性的文化表達,音樂影像志的實踐過程本身也助力不同文化群體的理解與互惠共生。基于此,本文將“大河唱”項目的田野過程分為三個部分—音樂人類學田野、紀錄電影拍攝田野、后期觀影互動田野,從音樂影像志的制作與意義生成的全過程進行反身性思考。探索音樂影像志的文化實踐過程,或許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討如何做音樂影像志的問題。
二、音樂田野:傳統與現實的相遇
正如《四個中國人Ⅲ》的緒言所述:“十年來清影一直將鏡頭與研究方向聚焦在當今中國語境下‘傳統’與‘現實’相遇的主題上。”⑧同注⑥,第1;315頁。清影一直關注不同行當的民間手藝人以探究人與歷史、人與社會的互動,“通過參與式觀察的方法,用鏡頭來顯微,用文字來深描,試圖用傳承機制這一框架來呈現藝術傳承、個體生活、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⑨同注⑦,第2頁。因此,當2016年得到拍攝藝術家蘇陽的機會時,我們將鏡頭對準了蘇陽及其音樂創作的文化母體——西北民間音樂。
西北傳統民間音樂與當代社會現實的相遇,不僅產生了蘇陽風格獨特的音樂,也成為紀錄電影《大河唱》的核心主題。基于蘇陽多年來的采風經驗,他推薦了四位民間藝人:花兒歌手馬風山、皮影戲班主魏宗富、秦腔團長張進來、陜北說書藝人劉世凱,由這四位民間藝人作為田野領路人帶我們深入西北民間音樂的田野。對西北民間音樂及其文化生態的理解則成為當務之急。因此,項目邀請了音樂人類學家蕭璇組織團隊展開前期音樂人類學田野調研。在蕭璇看來,這次田野調查具有更強的社會實踐意義,即以音樂人類學的知識來“開啟不同人群對不同地區音樂文化的認知,加強對音樂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并喚醒民眾對中國傳統音樂保護意識”。⑩同注⑥,第1;315頁。要喚起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對傳統音樂的意識,就需要讓這些音樂回歸到日常生活,發現音樂在生活中的意義。因此,前期田野的任務,一方面是與四位民間藝人建立田野關系,另一方面則是從每個藝人主位的視角理解傳統音樂以及自身被音樂浸潤的生活世界,同時也從客位視角對滋養這些音樂的文化意義體系、社會現實語境進行整體性的田野考察。在這個過程中,劇組為人類學者提供了輕便的攝影設備,他們可以隨時拍攝民間藝人的表演、訪談、日常生活、空間環境并留存資料,也可以讓民間藝人提前適應鏡頭的存在。
音樂田野中,還有另一層的傳統與現實相遇:學術研究的文字“傳統”與紀錄電影的拍攝“現實”。筆者之一既參與了前期田野調研,也參與了紀錄電影的田野拍攝,切身體會了兩種思維方式與實踐方式的差異。前期田野調研中,筆者在大量閱讀了地方史志、學術研究及西北相關的文學作品之后才進入西北田野。在馬風山家的田野過程中,游走于固原古戰場、參與觀察儀式活動,從討論張承志的《心靈史》聊到馬風山的生命史及家庭史,腦海中歷史的苦難與環境的蒼涼在田野生活中漸次成為切實可感的生命長卷,跌宕而堅韌。在歷史時空、民俗日常的交融情境下,跟隨馬風山坐在大山坡上望著遠山唱花兒,才真切感受到長久壓抑中的釋放與靈動,才真切體會到花兒對他的生命而言意味悠長。基于這些田野觀察寫成的田野報告,地域歷史、個人生命史、自然與文化生態占據了大量篇幅。因為在筆者看來,花兒傳唱至今勾連的正是這些歷史文化情境之下當地人的情感結構。閱讀其他前調成員的田野報告亦有相似,關注皮影戲班在鄉村的傳承脈絡、秦腔劇團在都市的發展歷程、陜北說書藝人代際間的技藝演變。然而,這些依賴語言鉤沉的歷時性時空是很難用共時性的紀實影像來呈現的。共時性的紀實影像擅長的是捕捉具體場景中人物的行為選擇、人際交往與情感狀態,從中透露出隱含的文化觀念,而這又是文字田野報告很難描述的。當筆者參與到秦腔與說書的拍攝過程時,拿著厚實的田野報告卻面臨著難以拍攝的歷史與文化闡釋,除了拍攝訪談與口述史環節,更多是將其作為“前世”背景與理解視角,需要不斷將田野報告重新解構,回到“今生”日常生活中去尋找、等待與觀察。可見,學術研究的文字“傳統”偏向在歷史或當下的生活場景中不斷結構出合理化的邏輯性敘事,而紀實電影的拍攝“現實”更多基于當下生活而不斷解構出可視化的生活場景來營造感受性的視聽空間。
同樣是秉持著人與土地的關系、傳統民間音樂與現實相遇的問題意識與觀察視角,如何處理學者在田野研究與影像工作者在現場拍攝中兩種思維和實踐方式的差異而相互配合,需要更多嘗試與磨合的經驗。就筆者經驗而言,在銜接學者觀點與拍攝安排時,導演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從田野報告中解讀出拍攝對象的處境以及可能拍攝的場景,在有預判和方向的情況下說服拍攝團隊進入現場,進行有意識的田野觀察與拍攝,考驗的是導演對紀實影像與文化理解兩方面的把握能力。此外,“大河唱”項目在后期處理上選擇了一分為二,將人類學者基于歷史縱深與田野訪談的文化理解匯集在《四個中國人Ⅲ》中,紀錄電影《大河唱》則略去歷史與訪談部分,著重以紀實段落直觀呈現民間藝人當下的生活處境與情感態度,將傳統民間音樂與現代社會的相遇分別以文字和影像各自擅長的方式抵達公眾。
三、影像田野:視覺與聽覺的互文
如何用紀實影像去“深描”看不見的民間音樂?紀實影像畢竟是在銀幕聲畫中經營生活。實現民間音樂與文化生態的視覺化呈現,一方面得益于田野中的生活情境與傳統音樂的相互交織,讓拍攝團隊通過田野的親身生活體驗而理解地域文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蘇陽結合民間傳統的現代音樂為拍攝團隊提供了情感化的感受方式。在紀實影像試圖“深描”民間音樂的田野過程中,民間音樂與地方文化也在情感層面重塑了拍攝團隊的生命體驗方式,進而實現拍攝者與拍攝對象之間互主體性的文化理解與表達。
生長于西北的攝影師張華因為從小聽姥姥講秦腔飽含情感的忠孝故事,因而希望用影像重新賦予秦腔一種情感化的溫度,打破作為藝術形式或非遺技藝的秦腔呈現:
通過秦腔,我很想賦予它一種情感的東西。我問過團里老中青三代演員,他們說其實只有舞臺上是最快樂的,因為我是將軍皇帝、才子佳人。他們是脫下了自己現實當中的一些屬性,想做一回別人好好再活一回的感覺。他有一種說不出的苦,只能轉換一個角色,在舞臺上把自己的情緒釋放出來。我得把秦腔跟人先連起來,要不然秦腔就是沒有情感的,可能只是拍了一種藝術形式,你不懂就是不懂。但畢竟幾千年下來,秦腔真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人情與道理。包括我看他們表演和生活,看懂了你也會哭也會笑,讓你在里面找到自己有共同感受的東西。?攝影師張華的采訪記錄。
可見,秦腔是演員們安頓自我的方式,這才是讓他們長年演出的情感動力,是秦腔之于今人的意義所在。因此,在完整記錄了幾場秦腔演出后,拍攝團隊聚焦于團長張進來及演員們臺上演出與臺下生活的關聯。下鄉演出的閑暇時間,他們仍會投入地聊起戲里的場面、動作神態、人物心理變化。他們認為“戲比天大”,一方面是對祖師爺傳下的秦腔藝術的尊重與較真,另一方面也因秦腔在鄉民生活中是神戲,肩負著唱給神聽求得風調雨順的重任。當我們跟拍了請神、祭蟲神、打臺等儀式之后,遙望這片干涸的黃土高坡,再聽秦腔的沖破天際的嘶吼方才理解其中的力道。這些具體的生活情境是紀實影像可以“深描”民間音樂內涵文化意義的視覺載體,而不僅將鏡頭對準傳統音樂技藝本身,正如拍攝團隊所說:
民間音樂的力量,在戲曲頻道、文藝節目里是看不到的。在沉重的生計與豐收的祈盼中,在十里八鄉趕來的凍紅了的臉上,在聚精會神望向舞臺的透亮的眼睛里,在山坡上對歌時飛揚的神采上,才能看到這些民間音樂流傳至今的火苗與動力。它讓周圍的所有人,跨越人神的、社會的、時空的距離,跨越皮囊的情感融匯在一起,從心里煥發出光彩。羨慕為內心情感找到溝通方式的人們。?楊宇菲的田野日記。
當我第一次站在黃河邊的時候,黃河沒有想象中那樣奔騰不息,反倒是很安靜,時不時從冰面上刮來點風聲。那時候腦子里會冒起很多聲音,包括蘇陽的吉他,老劉的說書,馬哥的花兒… …這個感覺一直比較深刻。所以后期在剪輯臺上,這種在場感也被化用到了剪輯中。?柯永權的采訪記錄。
視覺化的生活畫面注解著這些民間音樂對于當地人生活的意義,而將所見所感融匯于飽含情感的音樂傳唱之中,這些音樂也闡釋了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精神世界,以可視化的生活場景融入影像之中。傳統民間音樂與紀實影像的互文與通感是拍攝團隊理解與拍攝當地文化的溝通橋梁。
除了傳統民間音樂之外,蘇陽的歌成為一種內化于拍攝團隊內的情感視角。攝影師張華時常提起在拍攝劉世凱回陜北老家時,在山坡上看著他橫穿過山崗,腦海中回蕩著蘇陽的《胸膛》,不知道劉叔“冷的是身上還是胸膛”。導演楊植淳也曾提起在一天夜里,坐在老魏的三輪摩托上,聽著《喊歌》上山時莫名流淚了。在導演柯永權帶著特殊攝影組的兄弟們從黃河源頭一路走到入海口的旅程中,車里循環播放蘇陽的歌,在西北東奔西跑,見到各種各樣的人群、山川河流,“我們是真的跟這些人這些土地建立起情感了。”?柯永權的采訪記錄。或許蘇陽跟我們同是外來者,感受這片土地上傳統音樂與日常生活的觸動,進而創作出聯結傳統鄉土與現代情感的音樂。這種聯結不僅是因為蘇陽在音樂創作中借用了傳統音樂的元素,更是因為唱出了我們在西北的共通感受—對人的悲憫,無法掌控命運的無奈與倔強。這些音樂形塑了我們在田野拍攝過程中的情感體驗與觀看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拍攝對象的蘇陽對于拍攝團隊的影響可謂是潛移默化影響至深的。
討論田野中拍攝者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系時,已有人類學家指出,田野研究中感情的互動在文化溝通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因為情感是文化經驗的一部分,促進對他者文化更深的理解并深化互主體的溝通。?張小軍、木合塔爾·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類學:傳統“民族志”概念反思》,《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49-57;49頁。視覺與聽覺在田野生活之中的互文交織,音樂影像的聯覺性與象征性帶來的情感觸動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拍攝團隊對西北、對民間音樂、傳統文化甚至是對生活本身的理解。音樂影像志飽含情感的特質或許更容易在共情共感中理解彼此的文化,進而共同實現互主體性的文化表達。從這個意義上看,音樂影像志的實踐亦可拓展主張跨文化理解的“互經驗文化志”(inter-experience ethnography)?張小軍、木合塔爾·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類學:傳統“民族志”概念反思》,《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49-57;49頁。的研究。
四、觀影田野:自我與他者的共情
已有學者關注到影像民族志作者、拍攝對象及觀影者三者之間建立主體相互關系時的能動性,指出影像民族志的意義不只在于知識生產,也是“為實現跨文化分享經驗,而發現共同的經驗世界(the common world of experience)的過程”。?龐濤:《影視人類學發展的四個時期及其觀念基礎》,《民間文化論壇》,2021年,第3期,第22頁。如果將《大河唱》的觀影經驗作為音樂影像志田野的一部分,或可進一步探討作者與觀影者之間展開互主體性文化實踐的能動性。
觀影田野分兩部分,一個是團隊在剪輯過程中的反復觀影,另一個是公眾的觀影交流。整個拍攝各個拍攝組總共積累了1,700小時的素材和大量田野手記,后期把所有素材場記按五位主人公分別做了素材索引(演出、儀式、訪談、日常生活、事件、空鏡等),搭配田野手記以及整理的傳統唱詞在團隊內部共享,方便幾位導演與剪輯團隊基于相同的信息量進行溝通,促成相近的理解與風格。先后經歷了分組導演以拍攝對象為單位的粗剪,剪輯團隊基于導演初剪與素材進行重新整合,劇組內部以及小范圍觀眾的試映聽取意見后修改,反復剪輯了幾十個版本。從大量素材到成片,如何在一百分鐘里“結構生活”,又如何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在這個結構中理解他者,始終是個難題。
在剪輯過程中,最初是按田野調研的思路,試圖呈現秦腔、皮影、說書、花兒對于五位主人公的意義,勾連西北整體的文化生態(既是民眾娛樂方式,也是社會整合的方式,既與民間信仰的儀式相關,也關乎農耕社會的衣食生計),進而講述現代化浪潮碰撞中的張力。這種敘事對于一部紀錄電影似乎過于冗長沉重,因而更多保留在各個導演剪輯的人物分集版中。我們仍然選擇了一分為二,推出一個電影版、一個分集版。分集版緩解了文化表述的壓力,而電影版更專注考慮如何在影院觀影中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公眾進行跨文化溝通。
在電影版的剪輯中,德國剪輯師卡爾在并不熟悉西北文化的情況下操刀做了一版“散文式的剪輯”,以情緒感受為導向的觀看方式開啟了截然不同的剪輯思路。在反復觀影中,我們逐步意識到西北戲臺下癡迷的觀眾與蘇陽演唱會上雀躍的歌迷有著相似的興奮與投入,民間藝人面對生存困境同樣困擾著都市謀生的人們,而厚實的傳統藝術給予他們直面生活的純粹與堅韌。讓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人群基于共通生命經驗與情感體驗,理解其生成的文化土壤,或許可以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意識,讓傳統的河流淌到今天的人心里。因此,電影版嘗試提供一個共情的文本,由觀眾繼續書寫內心的河流。
在電影版公映后的互動交流中,我們發現當代紀錄電影觀眾對于紀錄影像的藝術性文化表達是有明確意識的,能清晰感知到西北民間音樂與影像的表達意圖,并不期待從中獲得某種“知識”,而更多是從內心感受出發去感知這些音樂與自我精神世界的關聯。綜觀大量的觀影反饋,大致分為兩類:(1)對民間藝術與鄉土文化的思考。如有觀影者是在閱讀《四個中國人Ⅲ》后來觀看影片的,感受到“民間藝術是老百姓的生活,是平凡單調的物質生活中人們追求愉悅、追求精神生活的‘透氣孔’,同時也是一種生存手段”?清華大學出版社組織的觀影交流,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楊陽老師分享的觀影感受。。(2)現代快節奏生活的反思。有觀影者感慨《大河唱》中蘇陽與民間藝人都專注于自己的手藝,簡單純粹地熱愛著故鄉與生活,“透著世間眾生的日常,那日常才是最偉大的存在”?豆瓣電影: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0227699/,2019年6月18日。。有觀者由他人聯想到自身:“音樂從他們身上流過,而他們本身也是在流動的河流,生老病死、喜怒哀愁,是每條人類河流都要遭遇的暗礁,都要經過的渡口。影片因為音樂走進他們的生活,但無疑記錄了更多,而也會引起觀眾有幾秒沉思:我自己這條河,現在是何模樣?”?豆瓣電影:《(大合唱):我們他們,和我們的他們的河流》,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252509/,2019年6月19日。同時亦有觀眾細心觀察到:
它成功地借助“生活”完成對觀眾的精準捕捉,喚起他們的現實經驗,從而使他們自行補滿了缺損的那部分聯系。我觀看的點映場次中,有觀眾在交流環節當場哽咽。但它的缺陷也在于此,如果刨除了經驗,可能會出現觀眾“看不懂”的情況。?豆瓣電影:《“看不懂”的電影與看哭的觀眾:大河之上望家鄉》,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250622/,2019年6月18日。
可見,不同觀影主體是透過民間音樂及藝人生活世界,分享彼此的生命體驗,共享各自與世界聯結的經驗方式(way of experience)從而達成文化溝通與共情理解,當經驗斷裂則難以生成意義。在豐富多樣的觀感中,觀者從自己的日常體驗中解讀“大河唱”的隱喻意義,解讀其中的民間藝人及其精神氣質,解讀傳統藝術與文化之于當下我們的“生命之河”有著怎樣的意義。觀感解讀也一定程度折射了當下都市文化的精神世界,這些意義生產或可成為民間音樂文化的組成部分。
正如人類學家英戈爾德(Tim Ingold)所說:“人類學的目的是與人類生命本身進行對話。這種與生命的對話不僅僅關乎世界,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對話就是世界,是一個我們都居于其中的世界。”?〔英〕蒂姆·英戈爾德:《人類學為什么重要》,周云水、陳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34頁。音樂影像志不僅是復合的文化經驗之闡釋與表征,同時也是多元感知方式與意義生成的喚起者。這些被喚起的情感體驗與意義表達或許可供人類學者重新思考音樂、影像或傳統藝術究竟在生活世界中如何存在、在生命經驗中如何生成意義,進一步闡釋交織其后的多層次的文化意義之網及其生成邏輯與動力。
結 語
基于“大河唱”項目的經驗回顧,在深入田野的基礎上,音樂與影像的互文交織出聽覺與視覺的通感,進而由感官體驗的方式達成不同文化群體的共情溝通與文化理解。影像讓民間音樂的生活情境與體驗得以具象化,民間音樂作為拍攝對象表達自我生命體驗的方式,在田野拍攝中也化為拍攝者的生命體驗而成為影像的核心靈魂,讓觀影者在視聽通感中感受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共鳴進而使民間音樂聯結自我生命而生成意義。可見,紀實影像“深描”的不僅是民間音樂人主位對傳統音樂的理解,也是民間音樂對當地人及拍攝者生活世界的形塑過程;民間音樂“闡釋”的不僅是歷史傳統與地方文化,也是當代社會的文化生態與精神世界。
因此,當我們從文化實踐的視角來看,音樂影像志是回到日常生活中去深描共享音樂的不同主體之生命經驗,而音樂影像志的制作過程是學者、民間藝人與影像工作者在田野中生命經驗交織共融的過程。音樂影像志作為互主體性的生命體驗之書寫,是基于文化土壤而生長的,其中既有民間音樂人的地域文化,也有電影人和觀眾的影視文化與都市文化。音樂影像志所承載的傳統音樂及其文化生態,在音樂與影像營造的通感體驗中形成對日常生活的共情理解,可以喚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重新關注與思考傳統文化的意義,思考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生活,進而將傳統藝術從遺產語境中帶回現代日常生活場域,在文化全球化環境中構建多元的文化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