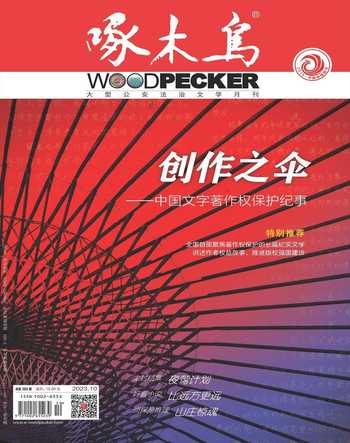在明暗中行走
李美皆
我在外面旅行已經很久了,久到我都不好意思說有多久了。行走得越久越遠,就越怕停下腳步,因為不知如何回歸和面對日常的生活,也是大多數人在過的生活。旅行是飛翔在日常之上的,脫離了現實的地面,偶爾我會茫然或不安,但還是喜歡。自由并不總是令人心安理得的,失重的漂浮感在所難免。必須承認,我身上有著自己創造的人物,比如梅小胭、梅小脂們身上的毛病,我寫她們,既內省又旁觀。
我很高興終于寫出了一部好看的小說。《胭脂灰》是一部愛情懸疑小說,在貫穿自己愛情理念的同時,我盡力把它寫得好看。其中女一號蘇墨的愛情,是一個東方《廊橋遺夢》式的故事,這是我對當下愛情的隨機和無所謂風習的一個有意的反撥。我想證明,愛情就是獨一無二、非他(她)不可的;同時,愛情也是千姿百態的。每個人都配得愛情。
人到中年,能放下的都放下了,就像脫掉多余的衣服。我的生活變得簡單,主要由兩大塊兒組成:寫小說、旅行,文學評論間雜其中。火車即將到達云南個舊站時,我在微信上看到了新一期《啄木鳥》的封面,我親愛的小說就在上面,那么鮮明,那么醒目,我心頭一亮。寫作者的明暗就是如此,等待回報的時間就像蟬爬行在黑暗的地道里,出土的一瞬,世界才豁然開朗,感覺一切值得。歷史的明暗或許也是如此。我在行走中穿越了許多歷史,感慨到不想再感慨,它們最好就像鹽一樣化到我的小說里去吧。這是一個寫作者所有感慨的最好歸宿。我還有點兒虛無地發現,無論怎樣的歷史,最后都是游客們拍照的一個背景。同樣,所有的寫作,或許都是外部和內心生活的投射,是一切“存在”后面的拖影。無論如何,在墮入虛無之前,它們存在過,這就夠了。
我喜歡“個舊”這個名字,火車正準備停靠站臺,我感覺它是通往美好的專列,此刻抵達。寫長篇大部分時間是在打井,一年能出一次油就不錯了。我是成都文學院特邀作家,自從離開軍隊,我就為自己找到了這個身份——我終究還是一個需要身份的人,否則會有無根的漂流感。這個身份同時給我一個有益的督促,使我的自律變得有的放矢。
上世紀的最后一個夏天,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旅行來到大理;在蒼山上驀然回首的洱海,給我心里留下極深的印刻,每次想起都如在眼前。終是不舍,我把它寫進了《胭脂灰》。奇妙的是,《胭脂灰》最后一次修改時,我又是在大理,在一家民宿里。這是我第二次來大理,是一個人,感覺卻比上次兩個人來時內心從容篤定得多。蒼山洱海亦不復當年,幾乎與當年印象無一處可重疊。畢竟,二十四年過去了。但也沒什么可傷感的,畢竟,它增添了許多新的美好,正如我的生命也增添了許多色彩,那都是當年無從預料的。
我在大屯海邊等待日落時寫下這篇創作談,仿佛《胭脂灰》中站在蒼山上回眸洱海,同樣具有一種永恒感。
真水無香,真愛有痛。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去愛,不然,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呢?這也是《胭脂灰》想要告白世界的。
責任編輯/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