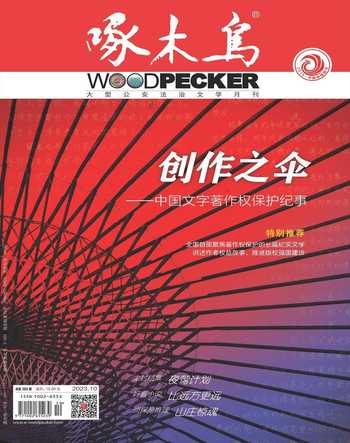比遠方更遠
米可

一
十月過半,皖北平原終于擺脫了連日陰雨,萬米之上,太陽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下面,是無盡的、被熨平的村莊、稻田和水庫,城市只是一小撮意外的凸起。
渦輪發動機發出更大的轟鳴,飛機在顛簸中不斷下降,機場跑道盡頭用黃漆涂抹的數字24清楚可見。
毫無征兆的,機身開始失重,剛一拉平,又是更為猛烈的下探,機艙內開始傳出低聲的尖叫。機艙廣播卻始終靜默,空乘藏在昏暗的布簾后面無聲無息,只有警示燈搖曳著令人作嘔的綠光。
飛機再次拉平,機翼掠過稻田水網、高速公路,以及塔臺。盤旋一圈后,再次對準了跑道。紅白色的風向袋陷入癲狂,機身在風的亂拳中劇烈震顫。機長卻似乎下定決心,在七上八下的姿態中,帶領百十來名乘客向跑道沖去。沒有人再發出任何聲音,大家都在屏息等待天、地、人交互的莊嚴時刻。
飛機幾乎是砸在了跑道上,瞬間又彈離地面,接著才緊貼地面滑行,隨著空姐如釋重負的播報,不久前的死亡恐懼變得蒼白且沒有意義。
有人笑說:“開飛機的一定是新手。”
有人回應:“不一定,也許他之前在俄羅斯開戰斗機。”
“哈哈哈哈……”
乘客們解開安全帶,查看手機信息,還有就是確認沒有把個人物品落在座椅口袋里。他們領到行李,從接機口涌出,四散而去……他們與家人親密擁抱,與甲方或乙方代表親切握手,打量熟悉或陌生的城市街道……一個兩百多斤的胖子落在了眾人身后,走走停停,舉棋不定。為了節省些力氣,他拽著行李箱踏上自動步道,出口就在另一端。行到半路,胖子蹲下身,像是在系鞋帶,幾秒鐘后,他緩緩歪倒在地,像一頭巨鯨,擱淺在步道的盡頭。
他永遠到不了家了——凡曉瀾站在原地,腦袋里先是冒出了這么個念頭,隨后又覺得有些惡心,好像腸胃還隨著飛機在半空顛簸。
離開候機廳,凡曉瀾與剛租好車的丈夫路大可、弟弟凡曉波以及弟弟的女友——一個叫作庫比卡的波蘭女孩兒會合。一行人駛離機場高速,向兩百公里外的壽縣老家繼續進發。很快,車窗外的景致便從立體的鋼筋水泥,變成了平坦無際的灰色土地。土地上沒有人,只有數以百計的麥秸卷,靜靜地棲息著,像是外星來客丟棄的小紙團。凡曉瀾有些疲倦,靠著窗發起了呆,車廂里的聒噪被她按下了靜音鍵,思緒開始盤算起未來幾天的事情。
此番回老家,是為了陪弟弟帶他的女友庫比卡見父親。如果這對跨國情侶得到父親的祝福肯定,那么他倆會到母親的墓前祭掃,然后定親,然后婚禮,然后飛到波蘭東南部一個叫作熱沃夫的邊境小城,據說有不少中國人在那里做生意……他們的未來,如同皖北平原,看似一望無際,實則籠罩在初秋逐漸彌漫起的水霧與煙塵中。除此之外,此行還有些支線任務,以及隱藏的劇情。是啊,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諸多情節與人物糾纏在一起,按照老家的說法,就像是一團理還亂的麻絲纏。
車子行駛了兩個小時,抵達了一個叫作凡郢孜的村莊。不同于大多村民聚居在郢孜里,凡曉瀾打小就和父母住在郢孜外田埂上的一個小院,緊鄰全村的泵房。早年間,郢孜里的村民大多在當地小煤窯下井,只有父親甘當農民伺候莊稼。如今,許多村民搬去了鎮上或市里,只有父親把自己活成了莊稼,越發扎根在土地上。
四人抵達時,正趕上父親坐在院子里的小桌前,邊曬太陽,邊就著臘肉咸菜啃饅頭。由于沒有提前通知,父親趕忙起身加菜,好在不管是雞鴨還是蔬果,都是就地取材。等到開飯時,已是下午三點。飯桌上,父親沒怎么說話,丈夫路大可和波蘭大妞庫比卡用她蹩腳的漢語都曾試圖活躍氛圍,但凡曉瀾習慣這種埋頭吃飯的氛圍,加之弟弟一直神經緊張,結果便是3∶2,沉默壓倒了溝通。
吃過“下午飯”,太陽已經落山,父親還要留大家接著吃晚飯,但其他三人都嚷嚷著“不用麻煩”,父親便沒有堅持。凡曉瀾倒是想多陪一陪父親,但一個突發情況已經迫在眉睫,使她不得不跟車回到鎮上的一家賓館。
四人開了兩間房,一間大床房,一間標準間。凡曉瀾和路大可入住的是標準間。進屋后,凡曉瀾便沖進了衛生間。或許是旅途奔波的疲憊,本應幾天后來串門的大姨媽竟提前到來,且因她患上了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血小板數值要低于常人很多,污血會滴滴答答流上好幾天,不僅擾亂了生活的節奏,還讓凡曉瀾產生了一種擰不緊水龍頭的無力感。
剛換上干凈的衛生用品,路大可便敲門,問凡曉瀾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給她倒一杯熱水。凡曉瀾沒有理睬。路大可又敲了幾次,大概覺得敷衍得差不多了,便轉身離開,然后打開電視,或許還會打開手機,偷偷給出軌對象發幾條微信……除醫生外,路大可是唯一知道凡曉瀾病情的人,從當初的同仇敵愾到曠日僵持,再到如今的心有旁騖,凡曉瀾并不怪他。事實上,就連她自己也需要從這該死的病中走走神兒。
凡曉瀾開始給自己卸妝,讓自己沉浸在一道道鉛華洗盡的程序中。誠然,隨著年齡增長,屋外的男人越來越油膩,而鏡中的自己也越發蒼白枯萎。生活中,凡曉瀾已經退化成一個離不開“紙尿褲”的孩子,但她的尊嚴,還有她的胡思亂想,卻隨著血液里的畸形細胞不斷增生……可不管再怎么不堪,凡曉瀾都想留在這盤殘局中,雖九死一生,仍繼續向前,而這,也是她此番回老家的隱藏任務。
該死的,說好的走神呢?
二
清早,凡曉瀾來到凡郢孜村委會的服務中心,提出要為父親補辦結婚證。辦事員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她先是查驗了凡曉瀾的身份證件,然后告訴她村部只能代為收集材料,如果想立刻補辦證件,還得去民政局婚姻登記處。凡曉瀾故作遲疑,又提出要查一查父母結婚的日期。小姑娘吃不準她是否有這個權限,便找村主任請示。
不一會兒,村主任便一口一個大才女,下樓招呼凡曉瀾,還自稱在網上看過她的職業規劃講座,希望她春節回來給村里外出打工的小年輕們上上課。村主任的熱情雖有些猝不及防,但凡曉瀾的應對也表達了尊重且不失鄉鄰的親切。寒暄完畢,凡曉瀾再次提出辦事請求,并向村主任暗示,父親一個人太孤單了,她有替父親安排晚年生活的打算。潛臺詞是,如果續弦,還是要找到原來的結婚證。
村主任撓了撓后腦勺:“老凡啊,人是老實,但要找個女人管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過得慣。”
凡曉瀾順勢把話一拉:“我倒是想把他帶進城,可他愿意跟著我嗎?”
“你啊,是大姑娘了,你有自己的事業。”村主任果真落入凡曉瀾的邏輯之中。
村主任讓辦事員查了凡曉瀾父母打結婚證的時間,1986年6月。那一年,父親三十歲出頭,母親才剛滿二十二歲,至于凡曉瀾自己,是1984年出生的。凡曉瀾看后,用開玩笑的語氣說:“小時候總聽人說,我是我爸撿回來的。”
村主任一怔,哈哈笑道:“我家兒子小的時候,我也是這么告訴他的。”
“可是您看,他倆打結婚證前,我就已經出生了。”凡曉瀾說,“難道是未婚先育?”
村主任撓了撓后腦勺:“你知道啊,那時候別說遲打結婚證,就是不打證,只是搭伙過日子,也是常有的事。”
凡曉瀾不想逼村主任太緊,怕他回頭再去找父親,便轉移話題:“我就是對過去有些好奇。您看那時候大家都住郢孜里,只有我們家跟孤魂野鬼似的,住在后郢孜的田地里,也不知道我爸咋想的。”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呢?”村主任咂摸著嘴,“總之你爸的那只眼在井下崩瞎后,他就從礦上辭了工。正好村里的泵房沒人管,就雇他把全村用水灌溉的事情管了起來。因為泵房建在田里,村里為了他工作和生活方便,就在泵房邊上給你家批了塊宅基地。”
“所以說,我爸原來也是住在郢孜里?”
“差不多吧。”
離開村部,凡曉瀾來到郢孜東南角的工房區。這些工房毗鄰已經關停的小煤窯,一共四排,每排十二戶,紅磚黑瓦漆木門,工工整整,門楣上還釘著藍色鐵質門牌。工房的外墻上,大腿粗的供氣管道曾將井下抽出的瓦斯輸送到每家每戶。
凡曉瀾不記得聽誰說過,自己和父親也曾住在這片工房里。她能記得的是上初一那年,從奧運會的電視轉播中,迷上了平衡木這項體操項目,更準確地說,是迷上了在上面跳舞的女孩兒。一天晚上,凡曉瀾偷偷穿上母親銀白色的健美褲,跑到這片工房,跳上瓦斯管道,先是保持平衡,然后向前,倒退,轉身,再加上手部動作、腰部動作。那一夜的月光格外皎潔,銀白色的健美褲也跟著熠熠生輝。
凡曉瀾屏住呼吸,余光掃過臺下唯一的觀眾。接著,她先是一招白鶴亮翅,再接金雞獨立,然后蓄力、騰空,雙臂環胸旋轉360°,就差一個完美的落地。只是不知哪里出了差錯,她一只腳刮到了一截突出的生鐵,腳踝被劃出一道長長的血口子。凡曉瀾第一時間沒有感到痛,但當她發現母親健美褲的褲腳也被撕破時,才意識到自己演砸了。
臺下唯一的觀眾,也是一直暗戀凡曉瀾的凡春喜被嚇壞了。還是凡曉瀾給他下達命令,將她送去了村衛生所。衛生所關著門,凡春喜又背著她敲響了村醫家的門。
事發后,凡曉瀾以為母親會像往常一樣暴揍自己一頓,但往后幾天,母親沒有和凡曉瀾說一句話。至于那條破了的健美褲,也不知何時被母親撕成了無數布條,扔進了化糞池里。父親呢,除了做飯時給凡曉瀾多夾魚肉外,也沒再提起此事。至于凡春喜,則因為沒有制止凡曉瀾犯傻,被他爸揍了一頓。
論輩分,凡春喜該喊凡曉瀾一聲表姑。凡曉瀾挺看不上這個同齡的表侄,特別是在他面前演砸出丑,讓她心里窩著火。不過,凡春喜對自己的那份暗戀,又能滿足凡曉瀾小小的虛榮心,加上每天攙扶著她上下學,凡春喜的溫暖漸漸令她留戀。終于,在一個月后的某個傍晚,當凡春喜將她送到田野里的小院時,凡曉瀾飛快地在表侄的臉頰上留下了一個吻。
凡曉瀾猜想,此番她回老家,凡春喜大概是知道的。這么多年來,從電話到QQ再到微信,兩人一直在彼此的通訊錄中,但最多僅限于點贊之交。凡春喜經營的超市就在村口,是不是要去打個招呼,凡曉瀾有些猶豫,有些心癢,又有些厭惡自己這樣的念頭。
三
臨近中午,凡曉瀾本想在鎮上簡單解決午飯,但想到昨天一大桌的剩菜,便又回到了后郢孜的小院。
今天早些時候,凡曉波帶著庫比卡去市里逛街。至于路大可,則找了個魚塘釣魚去了。這些都是父親告訴她的。若不是必須,凡曉瀾和路大可一天都不會給對方發一條信息。
對付完殘羹剩菜后,父親將那只瞎眼對著凡曉瀾,問她怎么看弟弟和庫比卡的婚事。
“我覺得挺好的。”凡曉瀾說。
“真的嗎?”
凡曉瀾猶豫片刻,如實答道:“我不知道。”
“你弟弟太老實,波蘭又太遠,他們要去的那個熱什么夫,距離烏克蘭邊境只有幾十公里啊,一發炮彈就打過來了。”
“阿爸,你還知道這個呀?”
“我上村部問的。”
“阿弟總是要出去闖一闖的,如果過不下去了,就再回來唄。再說了,我覺得庫比卡這個女孩兒不錯,人單純,性子也直。”
“和你一樣。”
凡曉瀾握住父親的手:“你是說我的性格像庫比卡,還是說弟弟像我一樣,非要到外面闖蕩啊?”
父親沒有回答,他扭過頭去,那只瞎眼也沉入了陰影中。凡曉瀾有些難過,但這份難過被手機的振動打斷,是閨蜜發來的郵件,標題是“一號機密”。
凡曉瀾起身要離開。父親像是在自言自語:“你也該要個孩子了。”
“也不是說要就能要的。”凡曉瀾說。
父親張了張嘴。
“老話說兒孫自有兒孫福,您就別操心了。”
凡曉瀾出了屋,打開這份“一號機密”,郵件是關于路大可出軌對象的資料: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手機和微信號碼,部分消費記錄以及一張女孩兒的個人照片。
一個月前,閨蜜偶然看見路大可和一個年輕女孩兒逛商場,兩人甚是親密,離別時還互相擁抱。閨蜜立刻向凡曉瀾舉報了路大可。但出乎閨蜜的意料,凡曉瀾竟然問女孩兒相貌如何,長得好不好看。閨蜜雖然很酸,但還是承認女孩兒樣貌標致,有胸有屁股的,像個小網紅,關鍵是還很年輕,至少比凡曉瀾小十歲。
凡曉瀾與其說是憤怒,倒不如說感到好奇。就連閨蜜也跟著納悶,憑路大可平平無奇的長相,不太討巧的口才,居然能夠泡到這樣的妹子,不可思議。如果說路大可有什么優點的話,那就是事業上還算上進,收入也屬于中等水平。但他的收入大多花在凡曉瀾服用的那些進口藥上了,剩下的錢想包小三難度還是挺大的。
總之,不管是出于打抱不平,還是八卦心理,閨蜜自告奮勇要幫凡曉瀾調查女孩兒的身份。憑借她在商場當客戶經理的便利,從拷貝商戶視頻監控,再到調取女孩兒消費充值的料理店、奶茶店的會員信息,便形成了這么一份機密報告。
凡曉瀾點開女孩兒的照片,甜美可人,如沐春風。那么,她和路大可究竟是什么關系呢,難道是真愛?想到此,凡曉瀾產生一種“萬一成真”的危機感。畢竟自從患病后,她已經在經濟上完全依附于路大可了。
為了買藥續命,凡曉瀾決定要認真對待這一段婚外情。
回屋后,父親不見了蹤影,隔壁的泵房開始發出昏昏欲睡的機器轟鳴。凡曉瀾有些困,她回到二樓自己的房間。房間依舊保持著二十年前的布置,只不過少了許多少女時的凌亂。顯然,在自己離開的日子里,父親還會定期清掃。
一年又一年,父親在宅基地的范圍內,疊火柴盒般不斷擴建房屋。在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曠野中,這些互相支撐的墻,抵御了初夏的梅雨和冬日的濕冷,壓低了那些狂風吹起的呼哨。父親以為他在努力保護著一家人的溫暖與安全,可外面的風雨與風景一樣有著強大的號召力,先是母親一次次逃離這個村莊,再到自己和弟弟相繼離開,出走,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命運使然,父親自知無法阻擋,便只能在沉默中等待著至親們的短暫歸來。
凡曉瀾剛吃過治療慢粒的靶向藥,身子有些出冷汗,她裹在被褥中,用雙臂環抱著自己,想著父親,想著那些困守一地的人們,想著那個拖著沉重行李,倒在機場的陌生旅人——
機場是那般明亮啊,一萬道玻璃幕墻反射著一萬道光芒,身處其中的人仿佛都在奔向各自光明的未來。起初,胖子也是步履匆匆地在人群中穿梭,他先是來到1號登機口,那里既沒有檢票的工作人員,也沒有出口,不知是不是當年施工者忘了在玻璃幕墻上開一道門。與此同時,機翼的尖尖滑過夕陽的金黃,機場廣播也在催促凡曉瀾抓緊時間登機。凡曉瀾趕忙來到2號登機口,接著是3號、4號,一直到最遠端的登機口,都沒有找到一道門。
凡曉瀾這才明白,這是一座看似光明實則毫無出路的機場。而那些無知的旅人啊,卻還在奔波著。凡曉瀾傷心地攔住一名旅客,試圖告訴他事實真相,但旅客根本不想搭理凡曉瀾。凡曉瀾還想呼叫,卻兩眼一黑,世界被拉上了拉鏈,凡曉瀾被塞進了行李箱。現在,她只能聽到轱轆壓過路面的聲音,聽到胖子失去節律的心跳,聽到人們的呼救聲。就在凡曉瀾覺得自己就要死去時,所有聲響變成火車沉重的喘息,哐哐當當、搖搖晃晃,遠方幾乎觸手可達。
四
村主任對于凡曉瀾問題的解答當然不足全信,至少不能解釋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就算當年父親工傷瞎了一只眼,他也可以做地面的工作,至少不用放棄連排的煤礦工房,搬進荒郊野外的泵房去當農民。這其中一定有著什么變故。
由于凡春喜經營的超市(就是他爸原先經營的小賣部)一直是村里流言蜚語和小道消息的匯集地,凡曉瀾決定還是要見一見這位初戀男友。
再見時,凡春喜正套著藍色的粗布褂在貨架邊理貨。凡春喜第一眼沒認出凡曉瀾,直到凡曉瀾低聲叫了一聲表侄,凡春喜才驚喜著,又小聲地說:“是你啊,瘦了好多。”
凡曉瀾一聽凡春喜的音調,心里暗罵了一句,也低聲回道:“柜臺和人拉呱的是你媳婦吧?”
凡春喜點頭。
“喜歡吃醋嗎?”
凡春喜笑了笑。
“明白了。”凡曉瀾說,“還記得礦上修的那片工房嗎,過會兒你到那里見我,我有些事要請你幫忙。”
半小時后,兩人在工房相見。不同于剛才的工裝,凡春喜換上了一套彪馬牌運動套裝,頭發也是新梳過的。在這片充滿荒草與鐵銹的區域,凡春喜的打扮雖有些不倫不類,但凡曉瀾還是夸贊道:“看起來很年輕嘛。”
凡春喜臉一紅:“偶爾跑跑步。”
凡曉瀾已經很少看到臉紅的男人了,她決定逗一逗這個少時的戀人:“你應該知道我回來了吧?”
凡春喜點點頭:“看到你朋友圈了。”
“那你為什么不給我打電話,好歹我還是你表姑呢。”
凡春喜的臉更紅了。
凡曉瀾的心里又可笑又心疼,她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出了請求幫忙的內容:找村里的老人打聽一下當年凡曉瀾父親辭工的原因,以及父親和母親當年是怎么認識和結婚的。
凡春喜有些困惑:“你可以直接問你爸啊?”
凡曉瀾耐著性子解釋:“我就是想知道,是我還是我媽先到的這個家。”
凡春喜更加困惑了:“不是先有你媽,再有的你嗎?”
凡曉瀾忍不住打了一下凡春喜的后腦勺:“你沒聽說我是被我爸抱養的嗎?”
凡春喜的眼睛開始瞪大。
“我從村部查的,我出生時我爸媽還沒打結婚證呢。”
“啊?”
“還有,小時候我媽打我比打我弟兇多了,所以……”
“所以?”
“所以她很可能就不是我親媽。”
凡春喜低頭想了半天,才囁嚅道:“小時候我爸媽一直說你是我的表姑,所以我不能和你談對象。”
凡曉瀾又氣又笑地說:“現在記得我是你表姑了?”接著,凡曉瀾又叮囑道,“你家超市門口聊閑話的人多,沒準兒就能探聽到真相,有消息一定要聯系我。”
凡春喜點點頭。
“對了,下次見面時,別穿得這么年輕,會顯得我老。”雖是揶揄,但想必凡春喜會把它當作夸贊吧。凡曉瀾這么想。
與凡春喜暫別后,凡曉瀾又與弟弟和庫比卡會合,帶他倆拜訪村里的長輩。一方面,這么一個金發碧眼的女孩兒早已引起了村里的廣泛輿論;另一方面,這樣的拜訪也間接說明他倆的關系得到了父親的默認。的確,如果沒有站得住的理由,父親即便反對也是毫無意義的。
打心底里,凡曉瀾并不想弟弟重復自己的老路,畢竟當年無知無畏的奔赴,只換來了今天的滿身傷痛。彼時路大可的大城市戶口,以及父母給他的一套老舊住房,已經充分奠定了凡曉瀾逃離故鄉的現實基礎。只是她不知道,在生活深不可測的洪流中,人能做的微乎其微。她可以選擇跳入哪條河流,卻無法改變流水的方向。
前夜,賓館的標準間內,當路大可在另一張床上背過身,手機發出的微光照亮他油膩碩大的鼻尖時,凡曉瀾偷偷在微信添加好友欄中輸入了路大可出軌對象的手機號。點擊發送,彈出了一個驗證框,要凡曉瀾再輸入一串邀請碼。吃了閉門羹后,凡曉瀾又試著在抖音里輸入這串手機號,成功轉入視頻主頁,她看到了正在直播間里跳舞的女孩兒。
年輕、可愛、有活力,像是一個乖乖女,但再細看下去,對方臉上的妝容和身上的裝扮,又讓凡曉瀾產生一種齁甜的煩膩。凡曉瀾戴上耳機,聽到女孩兒一邊喊著親愛的家人們,一邊邀請大家給她刷禮物,加入她的粉絲群。凡曉瀾毫不猶豫地刷了價值兩百元的火箭,然后從私信里收到一串邀請碼。
凡曉瀾退回到微信界面,修改了微信名和頭像,然后在添加好友的驗證框中輸入了邀請碼。對方很快通過了申請,并將凡曉瀾拉入一個名為“相親相愛一家人”的微信群內。進群后,凡曉瀾立即打開近五百人的群友列表。列表內男姓占大多數,其中就有路大可。凡曉瀾有點兒惱火,為了這么一個小妮子,居然這么多人花兩百元的門票錢,不知道抽了哪門子的瘋。接著,凡曉瀾潛在群里看大家聊天,從明星八卦到日系動漫,再到為“女神”挑選下次粉絲見面會的穿搭。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類似養成系的粉絲群,相較于抖音直播間,群主和粉絲的互動也更加真誠。其間,路大可除了偶爾發一發贊美愛慕的表情外,幾乎沒有說話。顯然,這些少女的話題,快四十歲的路大可不怎么搭得上。
凡曉瀾打了個哈欠,覺得路大可只是一時間的鬼迷心竅。可就在她閉眼準備睡覺時,又一個問題冒了出來:為什么在這個五百人的大群內,偏偏是路大可陪女孩兒逛街喝咖啡,還在離別時彼此擁抱?
五
凡春喜并沒有打探出凡曉瀾想要的情報,他的理由很充分。第一,在超市充當信息交流員的是他媳婦,他不能也不敢使喚媳婦幫他打聽前女友的事情;第二,那些打探的對象都牙豁舌長,口風不緊,難保不將風言風語捅到凡曉瀾的父親那里。
雖然沒能執行凡曉瀾的計劃,但凡春喜提供了另一條捷徑,他找到了派出所的戶籍警,論輩分,凡春喜該喊該戶籍警一聲三大爺,請他幫忙查一查當年的戶籍底冊,里面應該有早年凡曉瀾一家人的戶籍信息。為了答謝戶籍警,凡春喜還在派出所附近的火鍋店擺了一桌酒。
戶籍警如約赴宴,在火鍋湯水沸騰前,他講述了一段遠超凡曉瀾想象的往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凡曉瀾父親還不姓凡,而是姓趙,是一名到凡郢孜小煤窯打工的外地人。下班后,小趙就住在礦上建成的工房里,隔壁還住著另一個姓王的工友。不同于小趙的老實敦厚,小王是一個渾不吝,不僅經常吆五喝六地帶朋友到家里喝酒跳舞,就連女朋友都是隔三岔五地換,還因為打架斗毆被派出所處理過幾次。1983年的夏天,小王在一場酒后沖突中打死了人,并在警察上門抓他前就跑沒了影。這事本來和小趙沒有關系,但幾天后,警察發現小趙的家里多了一個女嬰,幾番盤問才知道,小王跑路時,把這個女嬰丟在了家里。女嬰的大聲哭鬧,攥住了小趙的心,他便將她抱到自己屋里,笨手笨腳地用米湯喂養。女嬰此后竟然一聲都不哭了,每天沖著小趙咿咿呀呀地“說話”。
戶籍警指著凡曉瀾說:“沒錯,那個女嬰就是你。”
戶籍警接著說:“小趙越是照顧就越是喜歡這個女嬰,不舍得福利院把她接走。但一個單身漢將一個來路不明的女嬰帶在身邊,不僅招來很多閑言碎語,還很分心井下的工作。他一個不注意,就在炸藥爆破時崩瞎了一只眼。小趙拿了一筆補償后,就從礦上辭了工,替村里管起了泵房。后來派出所給女嬰入戶口時,就女嬰姓趙還是姓王有了分歧,商議的結果是,小趙索性把自己的姓也改成了凡,還把戶口遷到了凡郢孜,徹底成了一個農民,村里也就勢批了他一片宅基地,并給他包了幾畝地種。
“所以說,我的親生父親是住在隔壁的姓王的殺人犯?”
戶籍警點點頭。
“他現在在哪兒?”
“還在逃,跑了幾十年了,肯定是改名換姓了。”戶籍警說,“后來有了DNA技術,派出所也找過你爸,提出想采集你的血樣,看能不能幫助追逃,但被老凡拒絕了。他肯定不想重提舊事,從而讓你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
“我的親生母親是誰?”
戶籍警搖搖頭:“我剛說過,你的親生父親當年是一個浪蕩子,結交了不少女朋友。應該是某個女朋友產下了你,卻不想養,就丟給了小王。小王逃跑后,老凡就又把你接了過去。”
“那么,”凡曉瀾一邊斟酌著措詞,一邊想起兒時母親常對自己的冷落與心不在焉,“那么,老凡的老婆,肯定不是我的親媽?”
戶籍警點點頭:“若是論起先后來,你比她要早兩年來到老凡身邊。等到你們爺兒倆安定下來后,老凡才娶的老婆,后來又有了你弟弟。”
戶籍警喝了口茶接著說:“雖說我和春喜是親戚,但這頓飯我不能吃,工作紀律。我今天來見你們,也是為了公事。當年老凡作為監護人,拒絕了我們采集你的血樣。但案子沒破,我們還是希望你能配合一下,讓我們采下血,或許就能比對上呢。”
“好的,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派出所。”
戶籍警走后,凡曉瀾凝望著火鍋蒸發的水汽,久久沒有作聲。凡春喜在邊上也沉默地坐著。半晌,凡曉瀾才說:“吃飯吧。”
凡春喜點點頭。
凡曉瀾又說:“我不能喝酒,你多喝幾杯吧,我給你倒酒。”
接下來,曉瀾一杯又一杯地倒,春喜一杯又一杯地喝。直到凡春喜緊握住凡曉瀾的手,她才發現酒瓶已經空了大半。凡曉瀾稍做掙扎,可凡春喜沒有放手,于是凡曉瀾便任由他握著。凡春喜受到了鼓舞,說起他倆曾經的山盟海誓,說起了那場虎頭蛇尾的私奔,說起了他聽從父母灌輸的近親不能結婚,才不得不對凡曉瀾放手。
凡春喜一邊哭訴,一邊不停飲下瓶里剩余的烈酒,直到酒精麻痹了深埋的痛苦,令凡春喜倒在桌上昏睡過去,凡曉瀾才捋了捋凡春喜的頭發,接管了他留下的回憶。
凡曉瀾說自己在流血,一直在流血。在所有的血流光前,她必須為自己移植造血干細胞。她曾以免費做基因篩查為由,索要了弟弟的血樣進行檢測,卻被告知他倆的基因樣本天差地別,完全無法配型。由此,她想到自己被領養的傳言。這次,她借弟弟帶女友見父親為由,回到故鄉,一番追索,卻得知自己是一個在逃殺人犯的女兒,而她的親生母親更是淹沒在往事的塵埃中無從考證……
凡曉瀾停了停,想一想接下來還要說些什么。是啊,還有什么可以說的呢?世界報以她一頓老拳,她卻不能還擊。凡曉瀾委屈極了。
就在凡曉瀾赴這場火鍋飯局前,她的另一場突圍有了進展。路大可的出軌對象給她打來了電話——女孩兒稱她是在一場粉絲見面會上遇見的路大可。當她將簽名照遞給路大可時,路大可哭了。見面會后,女孩兒找到路大可,問他為什么哭。路大可說當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下班后,他專程到商場的烘焙店訂了一個生日蛋糕。等待制作蛋糕的工夫,路大可順便旁觀了這么一場粉絲見面會。路大可坦言,當他看到臺上活力四射的女孩兒時,突然想到自己這輩子大概是不會有孩子了,才因此潸然淚下。女孩兒又問他為什么不會有孩子。路大可說出了妻子患病的事情。女孩兒既感動又同情,正好她還有一個粉絲回饋日的活動,便與路大可約定時間,假扮女兒陪他一上午。
女孩兒還說,路大可發現凡曉瀾化名入群后,知道產生了誤會,便委托她這個當事人來澄清這場誤會。收線前,女孩兒鼓勵凡曉瀾要勇敢面對病魔,畢竟這個世界充滿著愛。
是啊,充滿愛的世界,為何還會有那么多的憂傷與無奈。凡曉瀾繃不住了,她松開凡春喜的頭發,無聲地哭了。
六
離開凡郢孜的前一天,凡曉瀾一個人去派出所采集了DNA樣本。隨后,才與父親、弟弟和庫比卡會合,一同前往母親的墓前祭奠。
母親的墳位于一個小山包的半山腰上,可以俯瞰郢孜的小巷田埂,小煤窯廢棄的井架,以及通往更遠處的火車軌道。這條軌道叫作水張線,兼具著拉煤貨運和支線客運的功能。母親三十七歲那年,以慣常的“到城里轉轉”為由,再次搭上了水張線每天唯一一班的客運火車。她這一走,就是一個多月。
母親離開的那段時間,父親有時會帶著弟弟到火車站去守那班客運火車,凡曉瀾卻不愿意跟著。憑什么就她能一次又一次地出走,去城里面瀟灑,自己卻不行。
不過,和之前數次來去不同,這次母親回村時,已是非常虛弱。父親要帶她去醫院檢查,母親不讓,稱自己已在城里看過醫生,沒有救了。又過了一個月,母親就病故了。至于病因,她從未透露。
墓前,父親只做了開場白,便將掃墓、清理雜草、燒紙放炮和磕頭跪拜等全部事宜交給了弟弟和庫比卡,大概是考慮到他們以后很難返鄉,讓他們借此機會多盡盡孝。
鞭炮炸響時,父親問凡曉瀾:“你去找村主任了?”
凡曉瀾看著父親,點了點頭,等待父親接著問話。
父親看著呼呼燃燒的火,嘆口氣:“你媽還是愛你的。”
頓了頓,他又說:“活著的時候,她對你是不太好。但打心底里,她是愛你的,她只是不想你走她的老路罷了。”
“什么老路?”凡曉瀾咬著嘴唇問。
父親沒有回答,他只是揉了揉眼眶,嘆口氣道:“畢竟,你是從她肚子里掉下來的一塊肉啊。”
鞭炮炸完了,父親也不再說話了。
祭奠完畢,一行人下山。凡曉瀾落在后面,她盯著父親的背影,思量他剛才說的幾句話。天色陰沉,大風掃過山包,發出蔑視的呼哨,撥動了凡曉瀾的心弦。她突然明白:那條銀月色的健美褲對于母親意味著怎樣不可實現的美好;明白當年她和凡春喜私奔,為何會招致母親發了瘋地狠揍;明白母親那沒有說出口的病因,如今以另一種方式流淌在她的血液中。最終,凡曉瀾明白,母親當年偷偷潛入曠野的泵房,原只打算看一眼她丟棄的女兒,卻自此被牽絆詛咒,在失望、憎惡與愛中,困守一地,終其一生。
凡曉瀾仰望母親的墓碑,母親也在沉默中俯瞰自己。山下,父親開始呼喚凡曉瀾的名字,凡曉瀾哎了一聲,加快腳步跑了下去。
在凡郢孜的最后一晚,凡曉瀾勸大家退掉了鎮上的賓館,住回父親的小院。夜深了,風還在呼嘯。凡曉瀾鉆進了路大可的被窩,摟住他的腰。路大可痙攣似的,放下了手機。凡曉瀾說:“咱們飛機降落那天,有一個胖男人,好像是突發心臟病,死在了機場。”
“哦,我也從抖音上看到了。”路大可說,“他人沒死,被醫生搶救回來了。”
“我還以為他死了。”凡曉瀾舒了一口氣,路大可跟著打了一個哈欠。
凡曉瀾說:“這幾天,趁你釣魚的時候,我去見我的初戀男友了。”
“啊,哈……”
“你知道嗎,我和初戀男友還私奔過。”
“私奔?”
“我也記不清因為什么事情,把我媽惹著了,被她一頓暴打。我又氣又恨,就拽著初戀男友私奔。你知道嗎,論輩分,他還得喊我一聲姑呢。”凡曉瀾不禁笑了,“正好那會兒電視臺播《神雕俠侶》,我倆就當自己是楊過和小龍女,我還非逼他背了一根板凳腿兒,想象那就是楊過的巨劍。喂,你在聽嗎?”
“聽著吶,小龍女。”
“總之,我們沿著水張線的鐵路軌道一直向著城里的方向走,一邊走,我還一邊在鐵軌上跳著舞。我們從中午走到傍晚,又從傍晚走到夜里。天開始下雨,鐵軌濕滑,我那個初戀勸我不要跳了,老實趕路。我非要跳,結果又演砸了,崴了腳。他見狀說要回村里,私奔的事情下次再說。我不肯,但他力氣大,一把就將我扛在了肩上。我爭不過他,就求他把心愿瓶埋枕木下面。那個瓶子里除了一張寫著心愿的小紙條外,還塞滿了我疊的千紙鶴。”
“你的愿望是什么?”路大可像是在夢囈。
“那不是關鍵,小時候誰都有心愿。”凡曉瀾接著說,“我們把心愿瓶埋在了枕木下面,然后就由他背著我往回走。一邊走,我一邊數走過的枕木,一直數到出發的火車站。”
凡曉瀾伸出手指,摸了摸床邊墻上的刻痕:23989。那是她第一次出走時,所抵達的最遠的那一塊枕木。
“你許的什么愿望?”路大可翻過身,和凡曉瀾臉對著臉。
“我的愿望是生一大群孩子。”
“和誰?”
凡曉瀾笑了,她撫摸著路大可的臉:“和你,如果你愿意的話。”
責任編輯/張璟瑜
插圖/子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