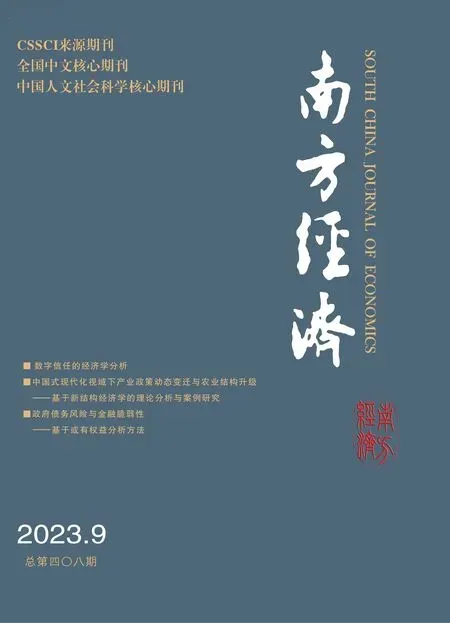政府債務風險與金融脆弱性
——基于或有權益分析方法
邵學峰 李昕達 王瓏淇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是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而且還造成生產力驟降、失業率激增、全球供應鏈中斷等嚴重經濟影響(Pak et al.,2020)。同時,俄烏沖突等全球局勢變化帶來的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也將全球通貨膨脹推升至幾十年內的最高點①數據來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October 2022,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為了應對突發性事件帶來的嚴峻負面沖擊,各國不遺余力地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大規模量化寬松,使全球公共債務經歷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幅度上漲②數據來源:IMF,IMF Annual Report 2022,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22/downloads/imf-annual-report-2022-english.pdf。,中國也不例外。雖然規模仍低于國際警戒線標準,但是我國財政同樣面臨著收入下滑、支出加大與前期債務償還壓力較大三大問題,財政可持續性得到質疑(劉尚希等,2021)。中國分稅制改革重塑的“財權上收、權責下放”格局,形成了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財政縱向失衡(李興文等,2021),又引發市場對地方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中國存在的財政與金融混合現象(鐘輝勇、陸銘,2017),是否會導致政府債務風險在金融網絡敞口間傳染與放大,推升金融脆弱性①依據明斯基理論,狹義的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機構及金融市場內在不穩定的特點,廣義金融脆弱性則是金融領域的風險積聚致使其處于對外部沖擊敏感而易于發生危機的脆弱性狀態。本文所指的總體金融系統內部脆弱性更強調在系統性沖擊下,通過各個經濟部門間錯綜復雜的金融網絡出現放大與傳染效應,最終導致整個經濟體的不穩定。,導致潛在系統性風險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十四五”規劃將債務風險識別上升為國家戰略②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強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強化金融穩定③資料來源: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因此,本文使用資產負債表法進行存量分析,將用于微觀的Black-Scholes-Merton 期權定價模型(Black and Scholes,1973;Merton,1974)拓展至或有權益分析方法(Gray et al.,2007;宮曉琳,2012a;宮曉琳,2012b),結合灰色系統理論對政府債務風險進行預測,并且考察風險在宏觀金融體系內部的傳染與放大機制(Castrén and Kavonius,2009)。這不僅有利于豐富政府債務風險的研究內容,而且對當下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有著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1)運用微觀金融學方法探討宏觀問題,將基于期權定價理論的或有權益分析方法應用于政府債務風險的測算。與使用會計流量指標作為代理變量的研究方法相比(牛霖琳等,2016;沈沛龍、樊歡,2012),基于風險調整的資產負債表法更能夠有效揭示政府部門資產與負債對外部沖擊的敏感性,更準確評估財政的可持續性。(2)與已有研究通過構建DSGE 模型模擬政府債務風險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觸發機制相比(毛銳等,2018;熊琛、金昊,2018),CCA模型構建國家資產負債表互動性分析框架,更能夠有效揭示金融網絡的復雜性與政府債務風險在敞口間的非線性放大機制。(3)與使用宏觀杠桿率對政府債務風險進行度量的文章相比(張啟迪,2020;馬建堂等,2016),本文對政府債務風險進行解構,考慮到債務的投向與資本產出比④本文參照劉曉光、劉元春(2018)的研究,定義政府資本產出比為政府資產撬動經濟增長的能力,資本產出比越高政府資產的經濟效益越低(資本產出比=資產/GDP)。,提出政府債務關鍵風險點在于經濟沖擊之下的資產價格波動。并且結論能夠反映劉曉光、劉元春(2018)和紀敏等(2017)所強調的宏觀債務率上升主要源于上行的資本產出比,而非資產負債率的增加。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后“財政疲勞”現象才得以重視(Ghosh et al.,2013;Checherita-Westphal and ??árek,2017),學者們注意到各國為了防止經濟下滑而發行超過“債務限額”的政府債務規模,直接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并且通過金融網絡的傳播,演變為更加廣泛的國際金融危機(Dungey et al.,2019;Sensoy et al.,2019;Perego,2020)。盡管找到一個能夠平衡財政可持續與經濟增長的政府負債率是一個復雜的問題,1992 年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將政府負債上限定義在60%仍然是得到普遍承認的重要標準。與發達國家相比,2022年初中國約47.2%的政府宏觀杠桿率似乎并不令人擔憂①數據來源: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宏觀杠桿率數據庫,http://114.115.232.154:8080。,中國政府債務負擔總體可控(李丹等,2017)。然而,近年來受國際嚴峻經濟形勢與國內疫情超出預期的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為應對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減弱三重壓力,政府采取了包括減稅降費、擴大投資與增加醫療衛生支出在內的積極財政政策(Wu and Luo,2022)。伴隨而來的財政收入增長放緩、支出需求加大與債務迅速擴張,自然引起了學者們對廣義政府債務風險的普遍擔憂(吳盼文等,2013;叢樹海、黃維盛,2022)。
中國分稅制改革以來,呈現出財政分權-金融顯性集權隱性分權的權利結構(何德旭、苗文龍,2016),重塑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義務和責任。其結果是,地方政府在資源收入與責任支出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財政缺口,形成了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財政縱向失衡(李興文等,2021)。從政治晉升機制來看,以GDP 增長為核心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又促使地方政府出現競爭性支出行為,形成了地方政府預算內資金與投資需求資金之間的競爭性財政缺口(杜彤偉等,2019)。在此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地方政府積壓了巨大規模的存量債務,面臨著前期債務償還壓力。陳寶東、鄧曉蘭(2018)就曾指出個別省份的財政已經面臨不可持續的狀態,債務違約風險較高(洪源、胡爭榮,2018)。再加上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這個不定時“炸彈”(何德旭、王學凱,2020),地方政府負債率將遠高于已公開數據。根據沈坤榮、施宇(2022)的測算,若是將隱性債務包含在內,2020年地方政府總負債率已然達到140%~203%之間,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不容小覷。
研究債務問題不能就債務而談債務,伴隨著宏觀杠桿率②本文所指的宏觀杠桿率為負債規模占比GDP。快速上漲的同樣還有資產價格(劉哲希、陳彥斌,2021)。因此,同時需要結合資產價格對資產端進行分析。近年來,政府部門資產金融化程度不斷加深(李揚等,2020)。20年間政府金融資產增加了將近20倍,達到134.2萬億元③數據來源:李揚、張曉晶等,《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P97。。雖然從政府償債能力的角度加以考慮,金融資產高占比能夠提升政府部門的可變現能力,但是金融資產價格泡沫化也會導致微觀杠桿率④本文所指的微觀杠桿率為負債規模占比金融資產規模。發生偏移,隱藏真實債務風險(蔡真、欒稀,2017)。一旦受到經濟沖擊,資產價格波動將會導致真實債務風險迅速攀升。
根據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說一:受經濟下行壓力影響,近年來政府債務違約風險將有所上升。
我國“財政金融混合”的特點使金融承擔部分政府融資的功能,財政金融關系失衡導致政府債務風險與金融風險“如影隨形”(李建強等,2020)。以銀行占主導的金融體系中,政府債務潛藏于銀行資產負債表主要基于兩方面原因:一是銀行主動持有被監管機構賦予零風險權重的政府債務(Brunnermeier et al.,2017);二是政府通過直接(持股)或間接手段(財政補貼、高管任免等)迫使商業銀行被動持有政府隱性債務(張甜、曹廷求,2022;伏潤民等,2017;張平,2017),形成政府與金融體系的預算軟約束機制。當然也有相關研究側重土地財政視角,提出地方政府對土地抵押融資與土地出讓收入償債模式的依賴是銀行資金向地方政府傾斜的主要原因(馬樹才等,2020;張璇等,2022;李玉龍,2019;秦鳳鳴等,2016)。政府債務由金融部門大量持有就致使政府債務風險通過資產負債表渠道在金融體系內“惡性循環”(Capponi et al.,2022),金融困境與財政困境螺旋式上升(Chari et al.,2020)。
金融部門自身高負債經營的特點又使其時刻處于對外部沖擊敏感而易于發生危機的脆弱性狀態,任何單個沖擊事件都極有可能在金融網絡當中迅速傳播,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導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經濟機制主要包括資產負債表放大機制、逐日盯市計價原則和市場信心的崩潰三方面(張曉樸,2010)。首先由于盯市制度與金融部門本身高負債經營特點,金融機構對資產價格的波動異常敏感(Adrian and Shin,2008)。一旦資產價格開始下跌,金融機構會迅速拋售相應資產以達到調整資產負債表的目的。此時,使用資產償還負債的邊際效用將大于生產效用,資產負債表放大機制將作用于所有借貸關系,各部門均會選擇拋售資產變現(吳恒煜等,2013)。但是,隨著危機的爆發,市場信心崩潰所致的各部門拋售行為會導致市場資產供給過剩,流動性不足,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形成損失螺旋(Allen and Carletti,2008),或稱為資產價格下跌螺旋(Diamond and Rajan,2005)。并且,各部門將資產用于償還負債而非投入生產的行為會進一步導致經濟的不穩定與萎縮(Brunnermeier,2009)。
因此,中國的財政金融混合現象致使政府債務潛藏于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當中。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之下,政府債務風險通過資產負債關聯渠道,在宏觀部門網絡敞口間非線性傳導(Allen and Gale,1998),加劇原本就對外部沖擊敏感而易于發生危機的金融脆弱性狀態。并且依據或有權益分析方法,高負債經營的金融部門將主要承擔負向逆反饋回路帶來的非線性資產損失,面臨“明斯基時刻”(茍文均等,2016;王兆成,2021)。
根據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說二:政府債務風險會通過資產負債表關聯渠道在網絡敞口間傳染與放大,非線性加劇金融脆弱性。
三、模型與數據處理
(一)或有權益分析方法與灰色系統理論
CCA 方法認為債務違約風險的根源在于未來資產價值的不確定。本文將研究視角置于國家整體資產負債關聯矩陣中,選擇基于隨機過程的CCA模型衡量政府債務風險,展現部門間的相互聯系。參照Gray et al.(2007)的研究,假設整個經濟體包含居民、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政府和國外五部門。每個部門資產市值A等于次級債權J(通常為股權)與債務D(通常為債權)之和:
其中高端索取權D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債務的賬面價值B和違約擔保的差額P。根據期權定價理論,資產A服從幾何布朗運動:
式中At是資產在t時刻的價值;μ 是資產價值漂移率;σA是資產價值波動率;dZ 是一個標準維納過程。在實際估算過程中,考慮到μ的可得性,使用無風險利率r替代漂移率μ。
預期凈損失P被視為隱性的看跌期權:
并且次級債券J被視為資產標的物的隱性看漲期權:
其中
式中N為標準正態分布累計分布函數;t為到期時間;A0/B是部門杠桿率的倒數。d2為CCA模型中估算出的債務違約距離(DD),可以理解為經資產波動率標準化后的資產價值與債務危機臨界點之間的距離。違約距離縮短,債務違約風險相應上升。
由于資產的市場價值A與資產價值波動率σA為兩個未知數,所以引入二者之間的關系式:
借助公式(3)(4)和(7),在已知次級債權J、債務D、無風險利率r 和低端索取權價值波動率σJ的情況下,本文使用迭代法求得各部門資產價值與波動率,再代回(6)式求解各部門債務違約距離。
參數選取與數據來源如下①由于本文關注政府債務風險在經濟體內部的積累與傳染,雖然在傳染過程中將國外部門考慮在內,但是不單獨列示其風險的真實值與變化過程。:
(1)參考王兆成(2021)采用國家資產負債表中各經濟部門各項債務之和度量債務臨界點B。
(2)對發行股權的金融部門與企業部門,低端債務索取權價值J使用國家資產負債表中股票及其他股權項目進行衡量。由于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不采取股權形式融資,因此參照Castrén and Kavonius(2009),使用金融資產凈值衡量。
(3)低端索取權波動率σJ與無風險利率r 參照茍文均等(2016),根據金融市場數據獲得,具體見表1。

表1 各部門參數匯總表
國家資產負債表只公布到2019 年,但疫情等全球突發性事件對經濟的沖擊存在滯后性。因此本文結合灰色系統理論的GM(1,1)模型,在樣本容量較小的情況下對2020 年與2021 年各部門債務危機臨界點B 與低端索取權價值J 進行短期預測。對通過級比檢驗的序列直接進行灰色模型構建,對未通過序列進行“平移轉換”。如圖1所示,擬合結果各序列平均相對誤差均小于5%,證明預測結果具有精準性(劉思峰、鄧聚龍,2000)。

圖1 GM(1,1)模型擬合結果
(二)部門間資產負債關聯矩陣與風險傳染機制
債務違約風險會通過五部門間國家資產負債關聯矩陣傳染。如圖2所示,假設五部門間任意金融工具F 的具體債務和債權關系可以用一個5×5 的矩陣表示,矩陣中任意一個元素Fij代表部門i 持有部門j 發行金融工具F 的數量。于是矩陣每一行的和ai表示部門i 持有其他部門金融工具F 的總量,每一列的和lj表示部門j通過金融工具F向各部門募集資金之和。

圖2 部門間金融關系矩陣
在已知ai和lj的情況下,本文參考Mistrulli(2011)和Upper and Worms(2004)的思路,采用極大熵方法(Jaynes,1957)推導出矩陣中所有元素Fij。更具體來說,假設ai與lj是函數f(a)和f(l)的實現值,Fij則被視為它們的聯合分布f(a,l),也可以稱其為條件熵。當f(a)和f(l)相互獨立時,則存在矩陣=ai×lj。將極大熵問題轉化為其數學本質最優化問題可以得到公式(10)和(11),也就是對帶約束非線性規劃問題求解。
本文參考劉磊、張曉晶(2020)的矩陣設計,將金融工具F分為貸款①貸款項目包括:貸款、央行貸款、其他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存款②存款項目包括:通貨、存款、保險、金融機構往來和準備金、債券③債券項目包括:債券和國際儲備資產和股權④股權項目包括:股權、證券投資基金和直接投資四類,參照Bacharach(1970)使用matlab 進行RAS 算法⑤RAS算法是指在初始估計數據的基礎之上,采用迭代的算法得出唯一解,它能夠確保初始估計數據的符號不改變。,對2019 年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求解,最終得出五部門間資產負債關聯矩陣,結果如圖3所示(具體結果見附錄)。

圖3 部門間資產負債關聯網絡
風險傳導機制參照Castrén and Kavonius(2009),假設政府債務的違約會造成債務持有部門所有者權益的損失。依據假說當中的盯市原則,在不考慮時間的情況下,金融部門、企業部門和國外部門的所有者權益損失會通過股權渠道進一步累積和傳染至次級債務持有部門,直至損失被完全吸收(居民和政府部門由于不發行股權,僅僅承受損失,而不二次傳導)。根據作者測算結果,金融部門持有最多的政府債務金融工具⑥詳細結果見附錄。,首當其沖受到政府債務風險的影響,并且風險通過權益渠道不斷累積和傳染,將進一步加劇金融壓力,使金融體系向脆弱性狀態傾斜。
四、實證分析
(一)債務違約風險分析與預測
如圖4、5 所示,利用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數據和或有權益分析模型,本文結合灰色系統理論測算出2007—2021年四大經濟部門債務杠桿率、波動率與債務違約距離軌跡。總體來看,可以發現:

圖4 中國四大經濟部門杠桿率趨勢(2007-2021)
(1)金融部門作為高負債經營的中介部門,杠桿率明顯高于企業、政府與居民部門,債務違約距離也明顯偏低。依據前文理論,金融部門自身特點使其時刻處于對外部沖擊敏感而易于發生危機的脆弱性狀態,資產價格波動將主要影響金融部門。
(2)本文測算的政府微觀杠桿率(債務/金融資產)呈現下行趨勢,與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①資料來源:李揚、張曉晶等,《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P103,圖4-5。、宮曉琳(2012b)和鄭立君、黃友逵(2020)等研究結果相似。相比之下,政府部門資產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金融資產價值增幅明顯大于金融負債(李揚等,2020),債務擴張對應著投資與資產的增加正是政府微觀杠桿率下行的主要原因。

表2 情景1模擬沖擊量化分析(單位:億元)
細究發現,當前政府部門宏觀杠桿率(債務/GDP)呈現相反的上行趨勢。本文認為宏微觀杠桿率背離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觀杠桿率忽視了債務投向與資本產出比,缺乏對償債能力相關的資產端進行分析。單純以債務規模上升作為債務風險本質存在學理與實踐的局限性。從公式分解來看,微觀杠桿率=宏觀杠桿率/(資產/GDP)=宏觀杠桿率/資本產出比(劉曉光、劉元春,2018)。根據國家資產負債表測算結果②資料來源:李揚、張曉晶等,《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P103,圖4-5。,樣本區間內政府部門資本產出比呈現明顯的上行趨勢,政府資產的經濟效益不足。即使政府債務擴張對應著投資與資產的增加,宏觀杠桿率也會隨著資本產出比持續上升。由此結果也能夠反映劉曉光、劉元春(2018)和紀敏等(2017)所強調的資本產出比的上行是政府宏微觀杠桿率背離的主要原因。因此,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的本質不是債務規模的增長。相較于債務總量的上升,經濟沖擊帶來的資產價值波動才是基于償債能力的政府債務主要風險點。
(3)2015 年之后,政府部門杠桿率階段性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新《預算法》的實施將通過城投平臺為政府籌措資金的隱性債務計入企業部門,而不是政府部門。因此,2015 年開始企業部門杠桿率攀升,企業部門中存在大量的政府隱性債務③平臺發行標準化城投債余額從2007 年的3 億元飆升至2019 年底的8.9 萬億元,占非金融企業債的38%,更有通過銀行貸款、金融租賃、債券型基金等非標準化渠道發行存在重大隱患的非標準化債務并未被估計在內。。本文提出,在進行風險傳染模擬時,不僅要從政府部門出發,而且要分析歸于企業部門的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擴散與放大機制。
(4)目前政府債務違約距離偏高,危機相對較低,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是從時域變化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3年“錢荒”與2015年“股災”幾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受到資產價值波動的影響,債務違約距離波動幅度較大。證明在重大突發事件沖擊下,政府部門的償債能力極易受到資產價值波動的負向影響,資產價值波動是政府債務的主要風險點。而含有隱性債務的企業部門自身違約距離偏低,危機相對較高,已然存在潛在債務風險。
(5)根據GM(1,1)模型的預測結果,從2019 年開始,受到疫情等突發事件的影響,經濟形勢總體下滑,政府部門債務違約距離明顯下降,債務風險大幅度攀升。2021年債務風險有所回落,但含有政府隱性債務的企業部門風險值得擔憂。金融部門受到2017 年“去杠桿”帶來的資產波動影響,違約距離短暫下降,即使在后疫情時代小幅度回升,但并未恢復原本金融穩定水平,金融體系脆弱性仍然值得警惕。
(二)政府債務風險傳染效應分析
如前文所示,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之下,政府部門債務迅速擴張與資產價格波動導致政府債務風險成為宏觀金融的重要風險點。不僅如此,考慮到政府的公共主體身份,財政是社會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劉尚希,2005)。無論是金融機構①中國金融企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即使是民營金融機構,政府也會出于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而進行救助。、國有企事業單位還是地方政府,風險層層傳遞,急劇放大,最終不斷向中央財政集中(劉尚希,2003)。該模擬結果恰恰能夠點明債務風險的累積與傳導途徑,并且強調金融網絡的存在會使債務風險在部門風險敞口間溢出,放大原本資產損失規模。不僅政府部門將承受更多債務壓力,而且會抬升金融脆弱性,存在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為了詳細描述風險傳染途徑,本文主要針對廣義政府部門債務與潛藏于企業部門的隱性債務兩類情景進行模擬分析。
情景1:10%的廣義政府部門債務①廣義政府部門債務中包括債券和貸款兩種金融工具。發生違約,市場波動性保持不變。
如表2 所示,在政府債務違約10%的情況下,債務持有部門在第一輪會根據持有比例承受相應損失。依據盯市原則,本文假設損失會直接體現在所有者權益中。因此第二輪沖擊以金融、企業與國外部門為源頭,依據其他部門股權持有比例承受相應損失。從結果可以看出居民部門、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在第二輪傳導受到的資產損失明顯高于第一輪沖擊,證明了債務風險傳導過程中由資產價格下跌螺旋導致的風險放大機制,呈現出“小沖擊,大波動”現象。
如表3 所示,在三輪傳導過后,債務違約風險通過資產負債表向關聯經濟部門傳導。各部門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居民部門、金融部門、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自身債務違約距離分別變動0.27%、0.52%、0.024%與0.23%。其中尤其以高負債經營的金融部門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風險提升最高。

表3 情景1各部門債務違約距離變動
情景2a:非金融企業債券違約10%,市場波動性保持不變。
情景2b:非金融企業債券與廣義政府債務違約規模相同,市場波動性保持不變。
正如前文分析,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實際更加龐大,但是由于統計困難,國家資產負債表編制過程中僅將歸于企業部門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納入其中。平臺發行標準化城投債余額更是占非金融企業債的38%。因此,本文首先假設歸于企業部門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券違約10%,如表4 所示,此時依然是金融部門受到最大沖擊,債務違約距離在三輪沖擊下累積下跌0.36%。
由于違約規模不同,隱性債務違約距離的下降幅度小于廣義政府債務造成的損失。但是,一方面從債券類金融工具資產負債關聯矩陣中可以看出,金融部門作為中介持有90%以上企業債券,超過廣義政府部門債務持有比例。另一方面,除融資平臺以外的主體(地方政府部門與國有企事業單位)發行的隱性債務未被納入國家資產負債表統計當中,更具規模的隱性債務風險潛藏于金融體系內。因此,本文假設以城投債為代表的隱性債務與廣義政府債務違約規模相同,如表5所示,在三輪沖擊下金融部門債務違約距離累積下跌0.58%。與情景1 相比,政府與金融部門在風險傳染過程中承受了更多的損失,隱性債務風險一旦爆發將更多的在金融體系內積聚,推升金融脆弱性。

表5 情景2b各部門債務違約距離變動
情景3a:廣義政府部門債務①廣義政府部門債務包括債券和貸款兩種金融工具。違約10%,市場波動性每一輪上升5%。
情景3b:非金融企業債券違約10%,市場波動性每一輪上升5%。
當經濟體系受到沖擊,市場主體通常會改變自身經濟行為,市場波動率會隨之發生變化。依據或有權益分析方法,一方面波動率與債務風險存在非線性負相關關系,另一方面波動率與杠桿率相互作用同樣會帶來違約距離的大幅度下降(茍文均等,2016)。如表6、7 所示,波動率的提升會明顯放大政府債務風險對經濟部門的沖擊。

表6 情景3a各部門債務違約距離變動

表7 情景3b各部門債務違約距離變動
(三)進一步討論
如上所述,隱性債務風險一旦爆發將更多地在金融體系內積聚。而債務置換計劃作為及時性的權宜措施,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政府償債壓力(刁偉濤,2015),避免隱性債務風險的集中性爆發。根據IMF的統計,2019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代表的隱性債務存量為6.7萬億①資料來源:IMF,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20 Article IV Consultation-Press Release;Staff Report;and Statement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21/01/06/Peoples-Republic-of-China-2020-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and-49992,P66。。為了驗證債務置換能否重置部門間風險敞口,本文假設政府部門發行6 萬億政府債券置換現有6 萬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存量。結果如表8 所示,置換后非金融企業部門的違約風險降低。此外,如表9 所示,部門間網絡風險敞口重置降低了金融部門政府債務持有量②具體與附錄當中的表10相比。,政府債務風險在資產負債網絡間重新配置。

表8 債務置換后違約距離的改變

表9 債務置換后五部門間資產負債關聯矩陣(單位:億元)

表11 基于股權的資產負債表關聯矩陣(單位:億元)

表12 基于債券的資產負債表關聯矩陣(單位:億元)

表13 基于存款的資產負債表關聯矩陣(單位:億元)

表14 基于貸款的資產負債表關聯矩陣(單位:億元)
五、結論與建議
在疫情影響下,中國財政可持續性受到質疑。財政縱向失衡現象與隱性債務風險又引發學者們對地方政府償債能力的普遍擔憂。因此,本文首先結合或有權益分析方法與灰色系統理論對政府債務風險進行預測,并且通過資產負債關聯矩陣,探究政府債務風險在部門風險敞口間的傳染與放大機制。研究結果表明,近年政府部門債務違約距離大幅下降,解構后發現資產價格波動是政府債務的主要風險點。并且由于金融系統自身的脆弱性與金融網絡的存在,風險在敞口間呈現非線性擴散,金融部門承擔最大資產損失。另外,依據實證結果,隱性債務風險積聚在金融體系內,一旦經濟沖擊帶來資產價格波動,金融體系將面臨“明斯基時刻”。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啟示:第一,持續推進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能夠將歸結于企業部門與資產負債表之外的債務風險顯化,重置部門間風險敞口,使積聚在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在部門間重新配置;第二,加強對財政資金管理的審計力度,有效推動地方政府收入機制改革與債務限額管理,改善地方政府對于隱性債務的依賴,提升財政透明度,從根本上杜絕債務違約風險的產生;第三,重塑金融監管體系,進一步加強監管,抑制金融體系的風險擴散作用。尤其是針對金融抑制現象的存在,需要政府提升監管能力,“精準拆彈”,防范債務風險通過影子銀行渠道傳導擴散,阻斷局部沖擊帶來的市場大規模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