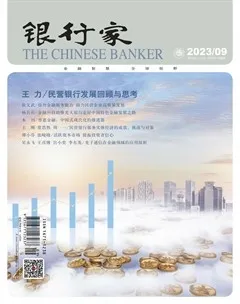“銀行”探源
文根第

Origin of “Bank”
對于“銀行”這一概念的溯源,為數不多的文獻中存在著“見仁見智”的爭議,需要引入一種新的史學研究范式——“概念史”來闡釋。概念史發端于德國,代表人物為科塞雷克,代表作為《歷史基本概念》,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其建構于語言學、語義學、翻譯學、傳播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但僅僅將這些理論聚合為一種分析工具。概念史最重要的任務是探究歷史的選擇機制,或者說重新思考在歷史的進程中,特別是在某些重要的轉折時刻,人們為什么會選擇與接受概念的某種含義,并使其變為主導性的唯一可接受的概念。
“銀行”一詞古已有之
據《淳熙三山志》(取自《宋元方志叢刊》第八冊)卷三十九記載,“嘉祐二年十月,鄉老于翰等,請紀密學蔡公(按:北宋四大家之一的蔡襄,在第二次擔任福州知府之前被授予樞密院直學士,時人稱其為密學蔡公)教民十六事,立碑于虎節門下……五、市行現行銅錢,如有夾雜砂蠟新錢,許人告。六、銀行輒造次銀出賣,許人捉。”這是中國目前現存史料中“銀行”一詞出現的最早時間,嘉祐是北宋時宋仁宗的年號,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
部分學者據此將“銀行”在中國的出現追溯至1057年。筆者認為這樣的追溯過于草率。概念史方法論在應用上首先要區分詞語與概念的差別。“銀行”的概念內涵該如何把握呢?民國時期,經濟學家?李權時在《交易論》(1929年)里認為“現在一般人之所謂的銀行,并不是保管金錢的行家,實在是制造和介紹信用的機關。”這就簡明扼要地揭示了銀行的概念內涵。既然要制造和介紹信用,首要的前提是經手的必須是貨幣。但是在宋朝,社會公認的貨幣是銅錢。這一點從蔡襄《教民十六事》的第五點——“五、市行現行銅錢,如有夾雜砂蠟新錢,許人告。”也可清晰看出。因此,1057年出現的“銀行”與“制造和介紹信用”無關,而只是作為一個詞語,表征的是制造或出售銀器的店鋪。
《宋元方志叢刊》第二冊中的《景定建康志》卷第十六記載:“今銀行、花行、雞行,鎮淮橋、新橋、笪橋、清化市,皆市也。”《景定建康志》成書于景定二年(南宋時宋理宗的年號,即公元1261年),也就是說直到南宋時期,“銀行”一詞在使用上仍然與花行和雞行并列。這也印證了宋代的“銀行”是作為兩個單字結合使用的詞語,還未凝固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復合詞,更談不上成為一個新概念。
“歷史的慣性——浩浩蕩蕩”和“習慣的力量——潛移默化”都足以使“銀行”僅作為詞語在后續朝代的社會生活中延續。兩宋之后的例子比比皆是,僅以明朝晚期成書的《金瓶梅》為例。在《金瓶梅》(崇禎本)的第九十回中有記載,“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可以看出,即使在白銀已經貨幣化了的明朝晚期,銀行仍然是作為兩個單字結合的詞語被使用的,并且可以與銀鋪通用。
“銀行”一詞的新概念
究竟是什么樣的契機使“銀行”一詞能對抗歷史的慣性和習慣的力量,開始凝固成復合詞繼而發展成為概念的呢?
王爾敏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提到,“自1840至1900的六十年間,是醞釀近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獨特的思潮發展段落。這里包括全部新概念之吸收、融會、萌芽、蛻變的過程。”梁啟超1901年在《過渡時代論》說“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王國維1905年在《論新學語之輸入》說“況西洋之學術骎骎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清末民初這個歷史階段,中國社會遭遇的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大的外力擾動因素是“西學東漸”。
今天只要一提到“銀行”就能想到英文翻譯是“Bank”,一看到“Bank”就能想到中文對應的是“銀行”,就好像“Bank”和“銀行”是天生的一對,但在歷史長河中它們找到彼此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根據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英漢歷》中的記載,第一家進入中國的“Bank”是1845年在香港、廣州建立分支機構的英國的Oriental Bank。而“Bank”進入中國時,既有音譯的也有對譯的。清末被譽為“中國西學第一人”的嚴復在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嚴復譯本名為《原富》)時,“Bank”被翻譯成“版克”。但即使聲名如此顯赫的西學大家,他的這一翻譯很快就被淹沒在歷史長河中未起任何波瀾,音譯方式在當時社會未得到普遍的認同和響應。
自唐朝的柜坊出現算起,中國的各類民間信用機關就一直存在。至清末,“制造和介紹信用的機關”的存在形式主要集中于票號、錢莊和銀號。票號是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同時經營存放款的信用機構,而據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記載,“清初另一種信用機關出現,叫做銀號……由于銀號和錢莊業務差不多,一般人對兩種機關不大加以區別,有人把規模較大的稱為銀號。”可見在當時的民間認知層面,銀號是比錢莊更具資金實力的信用機關。
由于本土已有票號、錢莊和銀號這三個同等概念內涵的事物,將三者進行比較,選取最為貼切的一個來對譯“Bank”就成為可能。票號是以匯兌為主,強調的是“匯通天下”(“天下”指全國),而英國的Bank是鴉片戰爭之后基于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實行五口通商)進入中國的,業務范圍在初期僅限于香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六個地方。因此,票號在三者之中與“Bank”對譯的貼切度最低。按照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中闡述的銀號與錢莊的區別,民間認知層面上銀號更具資金實力,與“Bank”最具貼切度。
但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強大的外部沖擊與幾千年燦爛文明深度交織,使得近代中國進入了一種“半自信”的狀態。在這種背景下,中西結合的創造性重構成為了概念吸收的主流方式。本土的“銀號”與西式商業機構“洋行”合并重構出“銀行”一詞,成為“Bank”的譯法。
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香港出版的《英華字典》中Bank詞條下,第一個譯語就是銀行。也就是在同一年,英國Oriental Bank發行的鈔票中,中文名為東藩匯理銀行(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這是“銀行”對譯“Bank”第一次出現在辭典中的記錄。
1896年,恭親王奕在奏折中說:“銀行之名昉于西俗,蓋合中國票號錢莊而變通盡利者也……博考西俗銀行之例,詳稽中國票號之法,近察日本折閱復興之故,遠征歐美顛撲不破之章,參互考證,融會貫通,擬定中國銀行辦法。”(參見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清政府統治時期〔1840—1911〕》)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在頒布《大清銀行則例》的同時,又頒布了《銀行通行則例》,規定銀行的九項業務,即票據貼現、短期拆款、存款、放款、買賣生金銀、兌換、代收票據、發行票據、發行銀錢票。凡是經營這九種業務的店鋪,都稱之為銀行。
至此,“銀行”完成了復合詞的凝結,成為習以為常、無需贅言的固有概念,一直延續至今。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
(作者單位:江蘇銀行北京分行)
責任編輯:楊生恒
ysh19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