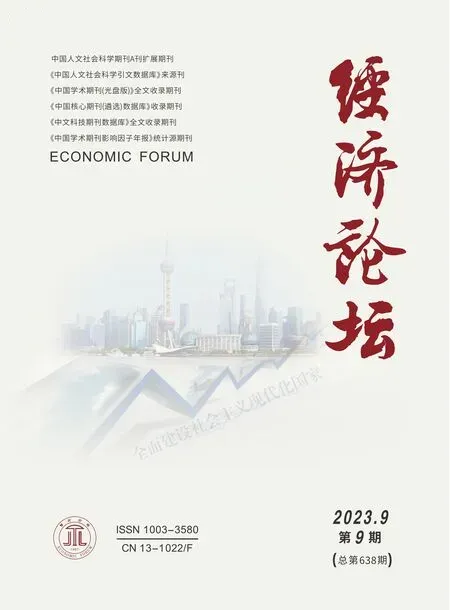數字無酬勞動的生產性分析
曹雷,曾天祺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桂林 541004)
目前,生產數據的無酬勞動是否屬于數字勞動,以及數字勞動、數字無酬勞動的生產性問題在國內外學界都存在很大爭議,這恰恰說明了正確認識數字勞動、數字無酬勞動的生產性是具有極大意義的。本文認為,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我們完全可以廓清數字勞動的內涵及其本質,并從數字勞動中區分出數字無酬勞動,進而揭示數字無酬勞動的剩余價值何以生產,從而確認數字無酬勞動的生產性。正確認識數字無酬勞動的生產性,可以使數字無酬勞動取得合理合法的勞動形式,讓數字無酬勞動在數字資本的專治下獲得適度解放,促進生產力發展,確定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數字經濟生產正義的規范導向,讓全社會共享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紅利,在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中走出實現共同富裕的新路徑。
一、數字無酬勞動的界定
數字勞動的生產性問題在國內外學界都存在很大爭議,普遍觀點都認同數字勞動中的有酬勞動,即職業的、受雇用的數字勞動者(程序員及數字平臺運營工作人員等)的勞動具有生產性,對有酬勞動的原理性分析基本上可以通過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來進行。但是對于數字無酬勞動,如“受眾勞動”“玩勞動”等,不通過雇傭的形式、不具有勞動報酬的這一類行為,是否屬于勞動,是否具有生產性,在學界仍未有定論。
(一)數字勞動的特殊性
數字勞動的概念很廣泛,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中,他為了對數字勞動進行最廣泛、最深刻的批判,將所有與數字產業相關的勞動統稱為數字勞動,在實體生產中從上游的晶體研發與生產,到下游的挖礦工人,在賽博空間中從前端的互聯網產品設計研發,到終端的互聯網應用使用者,只要是與數字相關的任何產業中的行為,在他看來都是屬于數字勞動的范疇[1]。這是廣義上的數字勞動,從對數字勞動的批判性以及對人的數字異化以及數字拜物教的反思和抗爭來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學界還有許多學者對數字勞動下了定義,黃再勝(2020)認為,用戶生成內容的過程就是一種典型的數字勞動[2];藍江(2019)認為,數字勞動的意義已經逐漸延伸到所有數字產品的使用者身上,在電腦上和手機上進行購物、玩游戲等活動實際上就是一種數字勞動[3];方莉(2020)認為,數字勞動是人類利用身體、思想、行為進行的生產勞動,是通過組織自然、資源、文化和人類經驗來生產數字商品、創造數字資源的活動[4];喬曉楠和郗艷萍(2019)認為,數字勞動是人類在互聯網及其終端上體力、腦力以及時間的耗費,最終形成系統化的知識、信息、情緒、經驗及社會關系等內容,從而給資本帶來利潤的免費勞動[5];朱陽和黃再勝(2019)認為,數字勞動是用戶利用數字技術在網絡及相關領域中開展的勞動[6]。
綜上,本文給出一個狹義的數字勞動定義,即一切生產“一般數據”的勞動,都是數字勞動。首先,數字勞動與我們傳統認知上的勞動不同。馬克思對一般性勞動曾進行概括,“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7]60。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勞動顯然符合馬克思主義勞動的概念。數字勞動身上難以達成共識的特殊性在于,數字勞動本身是一個極其廣泛且復雜的概念,既具有物質性又具有非物質性,既包含雇傭勞動又包含無酬免費勞動。數字勞動通過雇傭與非雇傭兩種形式來進行剩余價值生產,其生產的產品既包含內容、經驗、情感等精神產品,又生產了“一般數據”作為物質存在于服務器之中。數字勞動表面上是虛擬的,勞動生產出來的數字產品也是虛擬的,但是實際上并不是,一切數字勞動都會產生“一般數據”并且這個數據會儲存在服務器之中,而這個服務器是物質的,硬盤是物質的,所以數字勞動并非純粹的虛擬實踐。其次,數字時代勞動生產的遮蔽性特征更加深化,無論是生產勞動本身的價值還是勞動產品的價值,都被愈來愈復雜的技術手段所遮蔽。普羅大眾長期在資本邏輯下生存,已然覺察不出勞動異化的存在,遑論數字異化的發生。在傳統的商品生產中,勞動的價值已經具有很強的遮蔽性,馬克思對商品中具體勞動的價值分析道,“如果我們說商品——在它的交換價值意義上——是勞動的化身,那僅僅是指商品的一個想象的即純粹社會的存在形式,這種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體實在性毫無關系。商品代表一定量的社會勞動或貨幣。使商品產生出來的那種具體勞動,在商品上可能不留任何痕跡。”[8]在數據商品中,勞動的痕跡更加難以發現,甚至這種勞動都不能被認為是勞動行為,許多學者對數字勞動以及數字無酬勞動生產性問題都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再次,因數字勞動形成的數字產品具有無限性、可復制性,所以數字勞動與傳統的生產勞動形成巨大的差別,這就導致數字勞動的價值并不像傳統的勞動一樣凝結在商品的實體之中,而是可以無限制地被復制、被交換,這就對數字勞動的價值形成了第二層遮蔽。數字勞動的價值判斷到底是應當從前往后由傳統勞動價值論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還是從后往前由商品的交換價值來表現,這同樣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在數字勞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國外逐漸形成了兩種理論思路,一個是以“非物質勞動”下的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的觀點,一個是以從麥爾茲“受眾商品理論”得到啟發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福克斯物質性勞動觀點,這無疑增添了數字勞動的認識復雜性。這一理論來源既不能從意大利自治主義來,也不能從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來,而是同樣要回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從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重新廓清數字勞動的內涵及其本質。
(二)區分數字無酬勞動的必要性
數字勞動中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的區分是否有必要?目前為止,學界對此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王少光(2021)認為,“無酬勞動的出場,意味著勞動關系產生重大變化,其超出了傳統雇傭勞動的范疇,體現出數字勞動與傳統勞動的根本差異。”[9]余斌(2021)在《“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文中指出,數字勞動中有酬勞動與無酬勞動的區分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有酬勞動主要包括了互聯網公司對技術員、程序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的雇傭而進行的勞動,屬于傳統的雇傭勞動范疇,只是因為與數字產業相關而被稱為數字勞動而已[10]。除了數字無酬勞動,而對于其他勞動基本上屬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出的廣義數字勞動范疇之內,目前爭議就在于無酬勞動是否屬于數字勞動,無酬勞動是否是生產性勞動。藍江(2019)在《數字異化與一般數據——數字資本主義批判序曲》等文中提出“一般數據”的概念,“一般數據”來源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機器論片段”中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一般數據并不是具體的某種數據,它代表著所有數據的抽象層面。數字化時代或者數字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是將一切都數字化,轉化為一個可以進入云計算界面的數據,而這種數據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數據。”[11]簡而言之,“一般數據”就是指數字用戶在互聯網進行交互行為產生的一切數據的抽象。那么,對數字勞動的界定應當是:一切生產“一般數據”的行為,都屬于數字勞動;而一切生產了“一般數據”從而產生剩余價值,卻被數字資本家全部無償占有的行為,都是數字無酬勞動——這就是本文提出的“數字無酬勞動”的概念。
明確數字無酬勞動概念,是解決數字勞動內涵復雜、外延寬泛問題的一個最佳方案。無論是互聯網用戶的“產銷合一”行為、“受眾勞動”或是“玩勞動”,或者其他任何生產了“一般數據”而產出的剩余價值,被數字資本家全部無償占有的勞動行為,都可以在這個概念下進行研究。而數字勞動這一更廣泛的概念則可以與數字經濟的發展相關聯,其發展的理論能更好地適應當前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實踐需要,服務于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產業的蓬勃發展。
(三)“受眾商品理論”的批判之上
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中,數字無酬勞動的理論來源是達拉斯·史麥茲提出的受眾勞動和受眾商品化概念及相關理論。誠然受眾商品理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數字勞動進行批判的起點,它曾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起到奠基作用。但是對于數字勞動在當今的理論發展來說,正如同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數字勞動的理論應當建立在對受眾商品理論的批判之上。受眾勞動理論是在廣播電視傳媒時代發展的,受眾作為一般的、普遍的客體并不對傳媒廣告進行選擇和反饋,是被動的,消極的。在這一點上,余斌(2021)同樣認為,“受眾商品理論只不過是外部效應的一種反映”[10],人們在正常而普遍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外部效應通常都使一部分人從中獲利,但當事人卻與這些收益毫無關系。因此,部分對數字勞動的反駁實質上是對受眾勞動的反駁,數字勞動理論的發展應當且必須建立在對“受眾商品理論”的批判之上。
在數字時代,用戶作為互聯網的主體,不僅能對傳媒廣告進行選擇、反饋,還參與互聯網空間的搭建,并且在承擔“受眾”職能的同時也在生產“一般數據”,將用戶的互聯網虛體符號化、具體化,形成特殊的、個性的“受眾”。所以此時的受眾商品理論不免解釋乏力,僅僅能在定向廣告的價值分析領域發揮作用,而對于數字勞動,特別是數字無酬勞動科學概念的確立則應當要建立在對受眾勞動理論進行最深刻的批判之上。雖然在歷史上,數字勞動這一概念因其而生,但是在理論發展中,只有對其進行批判和揚棄才能使之具有生命力。而可惜的是目前國內外有關數字勞動的成果大都屬于直接建立在受眾商品理論之上,包括“數字勞動”理論影響最深遠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部分理論基礎也是來源于此,他認為媒體出售給廣告商的是媒體受眾的注意力,注意力被受眾生產為商品。而在社交媒體中,用戶是數據價值的生產者,這些數據作為商品被谷歌、百度等互聯網公司出售給他們的目標廣告客戶,數據被用戶生產成為商品[12]。順理成章地,基于福克斯的理論,許多學者都自然地將受眾商品理論當作數字勞動的理論基礎之一。
實際上,在政治經濟學中注意力是不能作為剩余價值來源的,剩余價值的唯一來源是勞動,不存在注意力勞動,勞動是人腦力或體力的耗費,而注意力是人腦力或體力的轉移而非耗費。從這方面上來說,數字勞動卻是符合的,數字勞動本質上是實踐,是生產“一般數據”的行為。所以,在研究數字勞動的時候,要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為理論根基,在對受眾商品理論的批判之上,充實和完善這一理論基礎。
二、數字無酬勞動的剩余價值何以生產
數字無酬勞動是生產性勞動,這類勞動是在所有互聯網用戶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進行的,并且并未取得傳統生產性勞動的形式,即以勞動力換取工資,因此,數字無酬勞動的所有勞動時間都是剩余勞動時間,所生產的所有價值都是剩余價值。“要實現判斷資本主義發展走向的研究目標,必須立足于剩余價值攫取和積累過程、形式的研究”[13],否則難以把握資本主義最新變化的本質,難以科學地總結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處于歷史形成過程中的發展模式。對復雜的數字無酬勞動的生產性分析,從資本剩余價值攫取和積累的方式來入手,能夠撥開云霧見月明。如果“一般數據”的價值是能夠被肯定的,那么其全部價值必定來源于數字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而在數字無酬勞動中,所有勞動都是剩余勞動,那么“一般數據”的價值,就都是剩余價值,這是數字資本對“數字勞工”百分之一百的剝奪。
(一)“一般數據”——理解數字勞動的密碼
在現在這個復雜的資本主義世界,社會生產已經不再像以前簡單的商品生產那樣能夠清晰地分辨出勞動者在生產中產生的價值。早在工業資本發達的時候就已經是如此,霍吉斯金在《保護勞動反對資本的要求》中就指出,“當分工發達的時候,幾乎每個人的勞動都是整體的一部分,它本身沒有任何價值或用處。因此工人不能指任何東西說:這是我的產品,我要留給我自己。”[8]200-201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中,數字勞動更是如此,數據的價值并不能得到普遍的認可,以余斌(2021)為代表的觀點質疑道,“這些數據有一定的使用價值,但是并不具有價值,這些數據進入生產過程后能夠帶來價值,那也是在生產過程中施加到這些數據上的勞動創造的。”[14]
事實上,數字勞動的價值需要更抽象地分析,“單個人的勞動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為被揚棄的個別勞動,即成為社會勞動。”[8]201每個用戶在互聯網生產“一般數據”的行為,對個體而言只是一串代碼,一些雜亂的痕跡,但是在大量累積之后成為數字資本積累的源泉,構成了極具遮蔽性卻又最赤裸的剝削形式——對數字無酬勞動的全部剩余價值剝奪。因此,要從具體的勞動中分析數字無酬勞動的生產性是相當具有難度的,此時“一般數據”就成為了理解數字勞動的密碼。
“一般數據”并不是某種具體的數據,它如同“一般勞動”,代表著所有數據的抽象層面。“一般數據”是每一個用戶數字勞動的產物,“它首先是一種產品,一種在數字化活動中被生產出來的產品。”[15]這是藍江(2018)在本體論意義上為數字資本主義研究發展需要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他提出:“我們確立的概念必須符合數字資本時代的新特性,而這種新特征恰恰是一種客觀性的力量,即由數據和云計算形成的龐大的關聯體系,我們可以稱之為一般數據。”[16]“一般數據”的提出能夠為數字資本主義的研究確立一個全新的對象——數據,它既是數字勞動的勞動產品,又是數字資本進行再生產的來源。如果要在看上去虛幻的數字無酬勞動之中找到一個剩余價值的載體,那只能是“一般數據”。在今天這個數字時代,每一個個體都不可避免地被一般數據所中介,無論是人還是物,所有的要素在一般數據的坐標系上才成為了對象性的存在。
“一般數據”具有二重性,他既是由勞動產出的可以在市場中被售賣的商品,也是數字資本進行資本積累和再生產的生產資料,是商品和生產資料的統一。斯爾尼塞克(2018)認為,“數據是一種被提取、被精煉并以各種方式被使用的物質”[17],應當將其看作如石油一樣的原材料,而用戶在平臺上的活動就是這些原料的來源。我們同樣可以把數字平臺看作一個數字工廠的大機器,平臺的程序員就如同這一大機器的設計師以及維修工人來保證機器的正常運轉。這一數字大機器“脫胎于海量數據的人工訓練,數字機器的生產、運轉和性能提升,需要源源不斷的數據‘喂養’才能得以實現。”[18]這個時候數字平臺就表現為固定資本,變成傳統產業資本體系中“自動的機器體系”[8]184,平臺中所有用戶的活動(活勞動)就自動被這一“煉油”大機器吸納,生產出大量的“一般數據”儲存在平臺資本所占有的服務器之中,即“活勞動”被對象化勞動占有了。由此,數字無酬勞動剩余價值的來源就得以被我們發現。
(二)對“活勞動”的實質吸納——自由時間成為剩余勞動時間
數字無酬勞動的過程就是數字資本對“活勞動”的實質吸納過程,這種吸納表現為對用戶自由時間的占有,用戶在平臺上的自由時間成為數字無酬勞動的剩余勞動時間。馬克思在批評重農學派時提出,把價值歸結為勞動的使用價值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而應當歸結為勞動時間、歸結為沒有質的差別的社會勞動[8]214。事實上,剩余價值的分析不僅可以歸結于沒有質的差別的社會勞動,即抽象勞動,也可以歸結為勞動時間,但在抽象意義上,抽象勞動比勞動時間更能說明勞動產品的價值。這是因為傳統的物質生產中,由于分工不同,所有工人耗費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不同,在不同的勞動強度下,勞動時間無法再成為計算價值的單位量。但在數字無酬勞動生產中,卻完全發生了變化。在互聯網空間中,每一個用戶都是獨立、平等的虛體,在所有虛體進行數字無酬勞動時所生產的價值都是等值的,甚至一個真實的用戶可以通過多個設備登錄多個賬戶,來操控數個虛體,比如在抖音極速版應用軟件上,用戶通過點擊瀏覽視頻來為推廣的視頻增加流量,由此可以完成其中的任務來換取獎勵金(實質就是特殊的數字勞動),不論是兒童還是老人,不論是一人操控一個虛體還是多個虛體,這一勞動都是以單位虛體來進行生產,也是以單位虛體來換取平臺的獎勵金。這類靠現金獎勵來吸引用戶參與數字勞動的現象,就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數字無酬勞動生產的價值在單位勞動時間下是等值的,此時勞動時間就能夠成為“一般數據”價值的最普遍的計量單位。
在馬克思主義機器論中,從資本對勞動的形式吸納到實質吸納經歷了在勞動時間之內對工人“活勞動”的占有到“資本就開始把工人的生命時間全部變為勞動時間,工作時間和閑暇時間的區分于是被打破了。”[19]在數字資本主義的今天,數字資本通過手機等移動終端形成了對社會全體的實質吸納,不僅工作時間和閑暇時間的區分被打破了,甚至在自由時間之下,人們的休閑娛樂也都在進行著數字無酬勞動生產,自由時間越來越多地成為剩余勞動時間。平臺資本“通過運用網絡技術實現對勞動者閑暇時間的誘導式利用與工作日的延長,此時資本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相較于以往而言更為隱蔽,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也拓展到了日常生活之中。”[20]勞動時間不僅再次成為資本家侵占的對象,并且突破了傳統的勞逸界限。數字資本比金融資本更加赤裸,它僅用對平臺建設的投入以及少量雇傭勞動就可以幾乎于無窮大地剝削用戶的自由時間。
(三)有價格的個體——平均時間構成用戶的一般價值
在數字資本主義下,流量成為資本的財富密碼。“流量變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價值是不可能憑空創造的,在流量的背后一定有支撐它的價值載體存在——一般數據。在市場上,流量儼然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基礎價格,這一價格隨著不同的平臺以及市場的變化而浮動。價格雖然不是價值卻可以反映價值。在一些大型互聯網公司——數字資本的占有者,由他們自身擁有的數據在市場經驗和大數據算法的加持下,流量的價格已經被資本掌握而不再神秘,比如Facebook 的資本積累模式就是立足于定向廣告,這就意味著出賣流量商品(占有數字無酬勞動剩余價值)的生意已經十分成熟了。
馬克思認為,生產勞動就是生產商品、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商品、物質產品的生產需要耗費一定量的勞動或勞動時間[8]234。“從資本主義觀點來看,只有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并且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生產條件所有者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只有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土地所有者創造‘純產品’的勞動,才是生產的。因為剩余價值或剩余勞動時間是對象化在剩余產品或‘純產品’中的。”[8]214-215這說明生產性勞動具備兩個關鍵性要素:一是要花費一定量的勞動或勞動時間;二就是要為資本創造剩余價值。我們將數字生產的過程簡化,如圖1所示。

圖1 數字勞動生產過程
數字無酬勞動之所以是生產性勞動,就是因為用戶將他們的剩余勞動時間全部對象化在一般數據之中,一般數據就是他們生產的剩余產品。這些一般數據進入到平臺之后被平臺的算法——一臺巨大的紡織機,把所有數據加工成用戶喜歡的款式再推送回來供他們消費,從而“實現”其交換價值。事實上,用戶在平臺上耗費的所有時間,都成為剩余勞動時間,其對象化的產品便是“一般數據”。
馬克思在手稿中談到,“使資本家對商品感興趣的僅僅是:商品具有的交換價值大于資本家為商品支付的交換價值。因此,勞動的使用價值在他看來就是他收回的勞動時間量大于他以工資形式支付的勞動時間量。”[8]218對平臺而言,一般用戶會形成一個使用平臺的平均時間,在平均時間內創造的價值用于支付或抵償平臺服務器運營費用,這相當于工人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創造的價值用于補償工資,而超出平均時間以外的時間則都是剩余勞動時間,此時平臺不僅從用戶身上收回預付的成本而且開始對其生產的剩余價值進行攫取。因此,在數字資本主義的邏輯中,剩余價值的生產可以不再通過傳統的“G—W—G”,而是從勞動時間直接到時間的消費,在這個過程中完成其剩余價值的攫取和實現。平臺運行的資本邏輯則是:用戶在平臺耗費的時間越長,其為平臺創造的剩余價值則越多;平臺的用戶越多,其具有的“生產力”就越大,就越能在資本市場獲得更高的估值。資本家從來不會是慈善家,也就是說,在用戶享受平臺帶來的免費服務的時候,用戶通過無酬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遠遠大于平臺提供服務所負擔的成本,用戶在平臺上耗費的時間不同程度上被數字資本家轉化成為無酬勞動時間。可以說,每一個用戶在數字資本的眼里都是有價格的個體,用戶耗費在平臺的時間構成他自身的價值,用戶在平臺耗費的平均時間構成用戶一般價值。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平臺通常都愿意為邀請新用戶支出高額的獎勵,這些新用戶加入除了本身提供了一般的交換價值,后續作為無酬勞工還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剩余價值。這種事實上所具有的交換價值以及生產能力,造成平臺與其將資金花費在優化和提高平臺效率上,不如花費在擴展用戶量上能更快攫取剩余價值。當用戶成為具有價格的個體,無不體現著“人格”在數字化以后真正變為了純粹的數字。
三、理路啟示:分配正義還是生產正義
對數字無酬勞動進行區分和生產性分析的目的是確立數字無酬勞動具有生產性,并且作為一種廣泛的勞動形式存在。一旦這種勞動形式得以確立,以數字無酬勞動理論為基礎便可以對數字勞動、數字資本的理論進行深入發展。以往我們分析資本,大體建立在雇傭勞動的基礎上才能確定資本的范疇,而數字資本作為全新的資本形式,并沒有按照傳統的雇傭勞動剝削的道路發展,而是以隱蔽的方式,全新的面貌發揮著資本的作用。在數字無酬勞動這一特殊的勞動形式中,我們似乎找到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勞動一般”作量化討論的最佳模型,“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于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里,勞動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8]28時間成為剩余價值的計量單位,這意味著在抽象意義上,一般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為這種勞動僅僅是最簡單的體力耗費,不必要包含智力或者其他的耗費。在這一理論基礎上,我們甚至可以通過市場中各個互聯網公司的數據精確計算出單位時間勞動的價值,并呼吁推動建立健全新的分配機制,精確地將用戶的勞動報酬返還到各個賬戶之中。
但事實上,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分配,而是在于生產。簡單的分配并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也不能改變數字資本即將在賽博空間、人的精神世界、物質世界形成三重空間的統攝專治的趨勢。正如我們對數字無酬勞動的分析,人以最一般的勞動形式為數字資本進行生產,數字資本也在生產著一般的人。數字資本在努力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同時也在最大限度地發展著資本主義及其矛盾,即在數字推送下引導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和政治傾向,把每個人都變成數字拜物教徒。數字無酬勞動理論的意義并不在于能為數字異化的現狀提出幾條具體的建議來規避,而是在于把對資本研究的視野從物質空間和精神空間擴展到一個尚在進行“圈地運動”的野蠻的賽博空間之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平臺經濟自身帶有的資本化及其私有色彩作為公有化趨勢的矛盾對立面,在數字生產力水平足以克服數字技術私有與公有的界限之前將長期與公有化趨勢共存共生。”[21]因此,真正的克服不在于如何分配個人的利益,真正的克服在于讓國家控制和掌握數字資本的重器,實現賽博空間的資本治理,在全面實現社會數據公有化之前,要讓數據真正為社會主義生產服務,引導平臺資本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揮積極作用,協助政府有效調節供給側和需求側,實現資源的精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