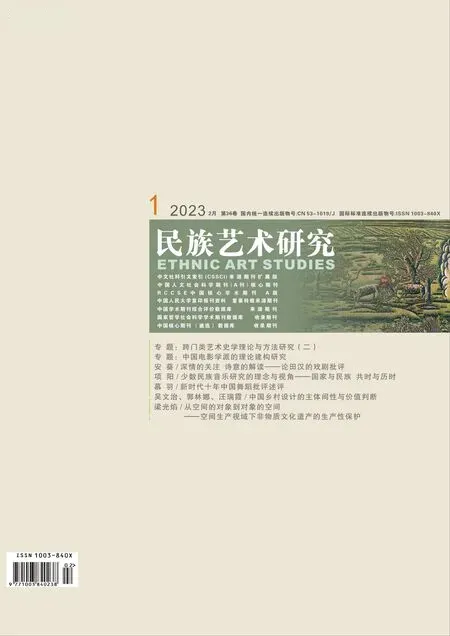中國電影理論的“體用”之學(xué)
李 洋
在電影學(xué)界倡導(dǎo)“中國學(xué)派”之時,從事西方電影研究的學(xué)者,能從什么角度參與其“中國特色”的建設(shè)?中國學(xué)者圍繞西方電影理論進行的學(xué)術(shù)生產(chǎn),從哪個角度可以納入“中國電影學(xué)派”的內(nèi)容?進行這樣的追問是為了建構(gòu)一種開放、多元、富有當代性的中國電影學(xué)術(shù)體制。如果這樣的體制想要健全、進步、有引領(lǐng)性和充滿魅力——歸根到底必須是包容的,而不是對抗的;這個體制必然是多元的,而不是單邊的。中國電影學(xué)派的建設(shè)不能源于單一的文化,不能僅存在封閉的語言,更不能只適用于中國的電影世界,它應(yīng)該可以為世界電影研究提供獨特而普遍有效的理論和方法,一種深沉有力的聲音和一種與西方學(xué)術(shù)話語有著差異性的學(xué)術(shù)見解。
當我們探討“什么是中國電影的本質(zhì)”“什么是中國電影理論固有的、其他民族所不具備的特色”,以及“與西方電影理論相比,中國電影的創(chuàng)作有哪些不可替代、難以復(fù)制的美學(xué)特質(zhì)”等問題時,這些追問都可以歸于電影理論的“中國性”問題,而關(guān)于“電影理論的中國性”的爭論,實際上可被納入中國思想史上反復(fù)出現(xiàn)的“體用之爭”。我們今天可以嘗試從“體用之爭”的角度來重新定位電影理論的中國性方向和價值。當然,今天我們重提“體用”,必須澄清其含義與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解讀是不同的。“體用之辨”源于中國古代哲學(xué)。從魏晉時期作為獨立的范疇被思想家們并置討論,到宋明理學(xué)發(fā)展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思想的本體論,再到清末民初延伸為面對外來文化而選擇的救世道路,“體用”概念的提出和發(fā)展經(jīng)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思想史上不同時期“體”“用”的含義,已不完全適用于今天的語境。
一、從“體用之辨”到“中體西用”
“體”與“用”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就被提出來了。《論語》中就提到了“本”“用”的概念。①春秋時期,“體用”是以“本”和“用”的概念被提出的。《論語·八佾第三》有“林放問禮之本”的句子,《論語·學(xué)而第一》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的表述。早在東漢時期,魏伯陽在《周易參同契》中就有“內(nèi)體”和“外用”對舉、以“用”為外學(xué)、以“體”治心、以“用”治事的學(xué)說。到西漢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已經(jīng)“體”“用”并論,如:“其術(shù)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①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M].韓兆琦,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7646.魏晉時期,“體用之學(xué)”逐漸在玄學(xué)和佛學(xué)中清晰起來,湯用彤曾認為,“魏晉以訖南北朝,中華學(xué)術(shù)界異說繁興,爭論雜出,其表面上雖非常復(fù)雜,但其所爭論實不離體用觀念。而玄學(xué)、佛學(xué)同主貴無賤有。以無為本,以萬有為末。本末即謂體用……”②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3:236.湯先生所謂“本末即為體用”,足以說明這個時期的“體用之學(xué)”已經(jīng)成為重要的哲學(xué)概念,各家理論都把“體用”之間的關(guān)系理解為本體與表象之間的關(guān)系。
“體用之學(xué)”在宋明理學(xué)中發(fā)展成為一種關(guān)于世界本體的系統(tǒng)學(xué)問,許多哲學(xué)家如程頤、朱熹等人,他們用“體用”的理論闡述本末、微顯等關(guān)系,關(guān)于“體用”的探討便進入了中國思想的核心。最早提出“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是程頤的《易傳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朱熹承接了程頤的觀念,繼續(xù)強調(diào)“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③朱熹.朱子全書[M].朱杰人,等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840.的理念,他經(jīng)常用“體”“用”的概念展開思想論述,讓“體用之學(xué)”日益豐富起來。朱熹把“體用”理解為宇宙運行規(guī)律的兩種表達,因此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本末”的等級關(guān)系,而是同源的。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他用“體用說”來解釋“仁”,提出——仁為性,是未發(fā),是“體”;而愛是已發(fā),是“用”: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于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fā)于用。性者指其未發(fā),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fā),故曰“愛者仁之用”。④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6:464.
朱熹以“體用”關(guān)系闡述仁和愛表達的不同過程和階段,強調(diào)“體用一源”即二者有著共同的源頭,而且二者不可分割,意即“體用”不可分開討論。但他不強調(diào)“體用說”的適用范圍;也不強調(diào)“體用之學(xué)”的思考對象是來自中原還是西域;也不追問“體用之思”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何為“體”?何為“用”?朱熹將其闡釋為一整套認識世界和宇宙萬物基本規(guī)律的學(xué)問,一種關(guān)于世界根本運行規(guī)律、基本特征的學(xué)說。在朱熹這里,“體”“用”是兩種形態(tài)或兩個過程,并不存在其中一個決定另一個的關(guān)系。但到了清代,對“體”“用”的闡釋就發(fā)生了根本變化。
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用“體用之學(xué)”來評估“中西之爭”的,就是清末洋務(wù)派的“中體西用”說。鴉片戰(zhàn)爭之后,洋務(wù)派成為應(yīng)對外來文化沖擊和異域文化沖撞的思想流派,洋務(wù)派在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上都提出了改良主張。在洋務(wù)派的主張中,開始用“體用關(guān)系”來分析“中國”與“西方”的對立,即用一種源于中國古代的思想方法應(yīng)對中國社會面臨的外來文化沖擊。
在洋務(wù)運動時期,“體用”與“中西”的關(guān)系并不統(tǒng)一。最早提出“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并非大家熟知的張之洞的《勸學(xué)篇》和《兩湖經(jīng)心書院改照學(xué)堂辦法片》,而幾乎在同一時期,許多洋務(wù)派人士都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一說是翻譯家和新聞人沈毓桂(1807—1907年),最早在1895年4月的《萬國公報》上發(fā)表《救時策》,提出,“夫中西學(xué)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沈毓桂曾翻譯過培根的《新工具》,他雖然主張“中體西用”,但認為中西之間沒有高低之分,因此求得真理不必區(qū)分中西。另一位代表人物孫家鼐(1827—1909年)1896年討論京師大學(xué)堂的辦學(xué)宗旨時,說道:“今中國創(chuàng)立京師大學(xué)堂,自應(yīng)以中學(xué)為主,西學(xué)為輔;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議復(fù)開辦京師大學(xué)堂摺》)孫家鼐的“體用”與“中西”的劃分,顯然是在一種關(guān)于教育和知識區(qū)分背景下進行的。因此,洋務(wù)派早期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是多數(shù)知識分子從教育和知識分類的角度,上升到評估中西方思想的模式,而最初的“西”是指西方的先進科學(xué)和技術(shù),而“中”是儒家傳統(tǒng)的社會組織形式。
我想強調(diào),在洋務(wù)派提出“中體西用”時,同時也有鄭觀應(yīng)提出了“西體中用”的概念。教育家鄭觀應(yīng)(1842—1921年)最早提出與“中體西用”相反的“西體中用”的觀點,他于1884年在《南游日記》中表達了這種思想,他說,“余平日歷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zhèn)洹S庞跁海撜谧h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此其體;練兵、制器械、鐵路、電線等事,此其用。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扦格,難臻富強。”
馮桂芬、張之洞等人提出“中體西用”的觀點時,主要是將“體用”關(guān)系作為闡述不同類型知識的模型,主要用于所謂的“新學(xué)”,因此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所謂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是為了捍衛(wèi)封建的政治體制,主張以西方的科學(xué)技術(shù)為“用”,發(fā)展清朝舊有政治體制的“體”,這與孫家鼐等人的主張不同。
在洋務(wù)運動時期,基本上“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占了上風(fēng),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沒有不同的聲音,比如張樹聲(1824—1884年)等人提出了“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的主張。這一派的知識分子認為,必須采用西方的政體、教體,之后再采用西方的科學(xué)方能真有其“用”,而不能只是采用西方的科技和先進知識,這么做無法改變中國的面貌。這種“西體中用”的觀念在當時基本上是被批評和否定的。在這一派人中,還隱藏著所謂“西學(xué)中源”說,即認為西方的科學(xué)實際上源于中國,這種認識當然是荒誕的。
二、李澤厚重提“西體中用”
洋務(wù)派關(guān)于“體用之辨”的討論沒有切入今天我們討論電影理論中國性的語境,直到李澤厚提出“西體中用”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期圍繞他的觀點產(chǎn)生了“中西體用之爭”,我們才真正進入這個語境。
1986年,李澤厚發(fā)表了《“西體中用”簡釋》,嘗試修正洋務(wù)派“體用”的定義。隨后,他于1987年在《孔子研究》上發(fā)表了兩萬字的長文《漫說“西體中用”》。在這兩篇文章中,他明確提出了“西體中用”的學(xué)說,這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指出了新的思想路徑,在思想界引起了許多爭論。張岱年、方克立、傅偉勛、周策縱等人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根據(jù)李澤厚的個人回憶,當時批評他的文章有60多篇①李澤厚.再說“西體中用”[M]//說西體中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47.。1995年,李澤厚在批評聲中沉寂多年后,在中山大學(xué)和香港中文大學(xué)做了《再說“西體中用”》的演講,回應(yīng)各家批評,并總結(jié)自己的觀點。這幾篇文章加上他在其他著述中對相關(guān)問題的表達,共同構(gòu)成了李澤厚“西體中用”的理論圖景。
李澤厚談到,洋務(wù)派形成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體用”與“中西”關(guān)系的認識上出現(xiàn)了三派。第一派是以張之洞為代表的“中體西用”派,強調(diào)鞏固中國的傳統(tǒng)體制,但要采納西人的科學(xué)與技術(shù);第二派是以譚嗣同為代表的“全盤西化”派,認為把中國的政治和宗教體制全部改為西方的模式,才能真正有效地運用西方的技術(shù)和科學(xué);第三派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所謂“超西化”社會理想(李澤厚語)派,但康有為始終畏首畏尾、不敢公開出版表達政治思想的《大同書》。李澤厚本人是贊同康有為觀點的,他想在當時知識界的“中體西用”(保守主義)和“全盤西化”(激進主義)的道路之間,提出一套新的方案,這是他提出“西體中用”的真正動機。他延續(xù)了洋務(wù)派站在中西文化差異的基礎(chǔ)上討論“體用”關(guān)系的做法,但他的出發(fā)點是中國學(xué)人強調(diào)保護的中國思想和方法不應(yīng)該屬于必須捍衛(wèi)的“體”,而應(yīng)該重新定位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系統(tǒng)在中西與體用關(guān)系中的位置。實際上,賀麟很早就把“體用”關(guān)系與文化問題的分析結(jié)合在一起了。賀麟曾說,“體是本質(zhì),用是表現(xiàn),體是規(guī)范,用是材料”,因此,他強調(diào)“體用”關(guān)系不可顛倒,也不能分離,“沒有無用之體,亦沒有無體之用。”①賀麟.文化的體與用[M]//賀麟.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47:33.李澤厚的觀點盡管在思想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但在中國思想界并非首創(chuàng)和孤例。
李澤厚像洋務(wù)運動時期的張樹聲等人那樣提出了“西體中用”的觀點,容易讓人產(chǎn)生誤解,其文章發(fā)表后,學(xué)術(shù)界的諸多爭論缺乏李澤厚強調(diào)的新的共識,這個共識就是李澤厚對“體用”含義的解釋,與張樹聲等人的“西體中用”已有著根本不同。張樹聲及其同僚們所謂“西體”,是主張換成“西方之體”,主張中國采用西方的政治體制,比如采用上議院和下議院的議會體制,同時還應(yīng)采納西方的宗教體制,這樣才能讓西方的先進科技對中國發(fā)揮作用。因此,清末的“西體中用”是指如果中國沒有體制的革新,就無法進行對西方科學(xué)技術(shù)的借鑒。這條改良主義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xué)術(shù)上,都沒有得到支持和采納。李澤厚的“西體中用”則完全不同,他認為我們要重新理解“體”“用”的含義與關(guān)系。
科學(xué)技術(sh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學(xué)技術(shù)是社會本體存在的基石。因為由它導(dǎo)致的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確實是整個社會存在和日常生活發(fā)生變化的最根本的動力和因素。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來規(guī)定這個“體”。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們屬于“體”的范疇。②李澤厚.漫談“西體中用”[M]//說西體中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31.
李澤厚認為——洋務(wù)派張之洞等人的主張之所以行不通,在于他們對“體用”含義的理解是錯誤的;而他強調(diào)他對“體”與“用”的理解,恰恰與張之洞是對立的。當時很多人對李澤厚有誤解或曲解,但李澤厚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中國古代思想之所以發(fā)達,恰恰在于儒家思想本身并不排斥外來文化,“中國儒家的實用理性能不懷情感偏執(zhí),樂于也易于接受外來的甚至異己的事物。”③李澤厚.漫談“西體中用”[M]//說西體中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17.因此,盲目地將中西對立,恰恰是與中國古代智慧相背離的。李澤厚認為,“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之學(xué)”的問題上持有兩極觀點——康有為、嚴復(fù)、胡適和陳獨秀,強調(diào)的是“學(xué)”的普遍性;而從章太炎到梁漱溟,則強調(diào)“學(xué)”的特殊性。前者追求“全盤西化”,后者強調(diào)“中體西用”。“只有去掉兩者各自的片面性,真理才能顯露,這也就是‘西體中用’。”④李澤厚.漫談“西體中用”[M]//說西體中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43.
我們可以通過馮友蘭用以對李澤厚表示支持的對聯(lián),來理解李澤厚的核心觀點。李澤厚北京的家中懸掛著一副對聯(lián),這是在他提出“西體中用”觀點引發(fā)諸多批評之后,當時90多歲高齡且雙目失明的馮友蘭專門為李澤厚題寫的對聯(lián),以示對他的支持。這副對聯(lián)的內(nèi)容是:“西學(xué)為體,中學(xué)為用;剛?cè)兆x經(jīng),柔日讀史。”在這副對聯(lián)中,馮友蘭不僅支持李澤厚的“西體中用”觀點,而且倡導(dǎo)反向理解“經(jīng)史”的關(guān)系。其實,馮友蘭早在40年前的《新事論》中就提出與李澤厚相似的觀點,他當時寫道:
從學(xué)術(shù)的觀點說,純粹科學(xué)等是體,實用科學(xué)、技藝等是用。但自社會改革之觀點說,則用機器、興實業(yè)等是體,社會之別方面底改革是用。⑤方克立.評“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J].哲學(xué)研究,1987(9):31.
李澤厚引發(fā)的這次爭論是在洋務(wù)派之后最集中地關(guān)于“體用之辨”的思想史爭論。他結(jié)合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古代所謂“體”的觀念進行了改造,認為科學(xué)、技術(shù)和經(jīng)濟等社會存在是“體”,即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產(chǎn)方式。洋務(wù)派強調(diào)“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主張采用西方的先進科技,改造中國的體制、工業(yè)和教育,而李澤厚倡導(dǎo)中國要先讓社會與生產(chǎn)方式完成基本的現(xiàn)代化,而非效仿“西方之體”來改變中國,這是以客觀的社會存在為體、包含了一部分唯物主義的基本認識,對洋務(wù)派賦予“體”的含義進行了修正。
當然,李澤厚重提“西體中用”是有具體思想史背景的,他想強調(diào)走中國現(xiàn)代化的路徑。他說,“光引進西方的科技、工藝和興辦實業(yè),是不能成功的;光經(jīng)濟改革是難以奏效的;必須有政治體制(上層建筑)和觀念文化(意識形態(tài))上的改革并行來相輔相成,現(xiàn)代化才有可能。”①李澤厚.漫談“西體中用”[M]//說西體中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36.我們今天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社會現(xiàn)實和歷史語境都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已經(jīng)成為政治大國和經(jīng)濟強國。但是,馮友蘭與李澤厚的理論訴求,對我們倡導(dǎo)“中國電影學(xué)派”是有啟迪的。馮李二人都認為,中國的理論、文化與思想并非洋務(wù)派所捍衛(wèi)的“體”,而是“用”,而科技和經(jīng)濟改革等過去被理解為“用”的,才是社會存在之“體”。李澤厚反復(fù)強調(diào),所謂“學(xué)”(思想、意識形態(tài))不可能是“體”。盡管李澤厚被批評比較多,但馮李二人轉(zhuǎn)換“體用”含義的觀點,對于我們思考中國電影學(xué)派的建設(shè)依然是有價值的。
三、中國電影學(xué)派何以“西體中用”
或許在許多人看來,“體用之辨”這種僵化的二元思維已經(jīng)陳腐過時,但許多人可能忽視了,漫長的“體用”爭論歷史與當前學(xué)界倡導(dǎo)“講好中國故事”“發(fā)展中國學(xué)派”“建設(shè)中國特色知識體系”之間的聯(lián)系有著內(nèi)在的必要性。我們在“中國電影學(xué)派”建設(shè)的呼聲中重提“西學(xué)為體、中學(xué)為用”,已不是在所謂“強國”和“現(xiàn)代化”的語境里,而是對中國思想和中國理論之價值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確認。如果中國學(xué)術(shù)界所推崇的“學(xué)”(中國思想、方法、智慧)不能成為“體”,而只能是“用”,那么在中國電影學(xué)派研究的背景下——“體”恰恰是電影作品與電影史事實(社會存在);如果是“西體”,就是西方電影史與電影作品。而學(xué)術(shù)界始終闡揚與捍衛(wèi)的中國思想、中國文化與中國理論,恰恰是“用”。但我們必須強調(diào),將中國理論作為“用”的目的,不是為了捍衛(wèi)“西方電影之體”,“體用”之間相輔相成——采用中國理論一方面重新發(fā)現(xiàn)西方電影的本體,重新定義西方電影的價值;另一方面,經(jīng)由“體用”之途,讓中國理論成為一種普適的電影理論和電影創(chuàng)作研究的方法。中國理論是否具有普適性?中國思想能否重構(gòu)西方作品“體”的意義與等級?這是本文提出“西體中用”觀點的根本原因。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電影學(xué)界歷經(jīng)三四代人,迫切而謙遜地學(xué)習(xí)和求取西方理論,以分析中國電影、書寫中國電影史、闡述中國電影的美學(xué)和特征。②圍繞中國電影學(xué)界面對西學(xué)方法的歷史回顧。胡克,鐘大豐,李洋.時代場域中的中國電影理論建構(gòu)(長篇對談)[J].當代電影,2022(1):4-19.當然,我們不斷發(fā)現(xiàn)西方理論的有限性,西方理論作為一種思想之“用”,與中國電影之“體”保持著不對位性,甚至被有些學(xué)者稱之為“強制闡釋”。③詳見張江等學(xué)者從2015年起提出的關(guān)于西方文藝理論方法在中國有效性展開的一系列“強制闡釋”的思想爭鳴,這場討論盡管未涉及電影,但其問題意識和思想旨歸與中國電影學(xué)派理論的提出非常接近。這些爭鳴讓我們反思,如果所謂的中國理論只適用于中國電影,只適用于本土的現(xiàn)實與電影文化闡釋,而不能闡釋電影世界廣泛社會存在的“體”,也就無法將其稱為一種真正的理論。如果中國的概念與方法是有限的,只能應(yīng)用于中國;如果西方電影理論是有限的,僅能解釋西方的電影作品和電影現(xiàn)實。因此,所謂“西體中用”,即讓中國的電影理論、概念、方法和價值系統(tǒng),作為理論工具以重新解釋和發(fā)現(xiàn)西方的電影創(chuàng)作,從而打破西方理論的壟斷與權(quán)威性。
四、海外電影研究的兩種嘗試
可喜的是,就在筆者近幾年不斷思考這些問題時,已有兩位海外學(xué)者在這一領(lǐng)域進行了重要的嘗試。新加坡學(xué)者張建德(Stephen Teo)2019年出版了《東方方法下的西方電影》(Eastern Approaches to Western Film:Asian Reception and Aesthetics in Cinema),運用中國哲學(xué)理論解釋西方的經(jīng)典電影名作,其中包括運用東方神話理論分析《星球大戰(zhàn)》(Star War),通過對色彩、窗戶布景等涉及中國文化的符號細節(jié)等的探討重新分析了希區(qū)柯克的名作《迷魂記》(Vertigo)。張建德在導(dǎo)論中就開門見山地指出這本書的寫作目的:
本書主要目的是引入一種“東方方法”,遵從東方思想的原則進行論證,以應(yīng)用于我選擇的西方影片的敘事與內(nèi)容,這些影片都是經(jīng)典之作,由歐洲和美國精心選擇出來的作者導(dǎo)演拍攝而成。這種方法是對東方概念的同步應(yīng)用,從與西方對象的接觸開始,沿著自在的道家“逍遙”路線而進行的思想練習(xí)。①TEO Steven.Eastern approaches to western film,rsian reception and aesthetics in cinema[M].London·New York:Bloomsbury,2019:1.
盡管他的研究沒有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而是由經(jīng)典影片的解讀組成,但這種努力非常重要。張建德格外提到其他學(xué)者有意識地運用中國理論,對西方電影文化展開的研究,尤其是倫敦大學(xué)學(xué)院的范可樂(Victor Fan)2014年的著作《電影接近現(xiàn)實》(Cinema Approaching Reality:Locating Chinese Film Theory),這本書沿著西方電影理論的概念和邊界脈絡(luò),對中國早期電影理論展開創(chuàng)造性的歷史回顧,張建德對范可樂的工作大加贊賞,但他也格外強調(diào),他所嘗試的方法——一方面不致力于建構(gòu)一種“中國式”的電影理論;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強調(diào)這些理論只適用于中國或東方的電影作品,而是從中國思想和理論的概念、文化和精神中,挖掘一種普適有效的方法論:
我的書不涉及中國電影理論的歷史研究,也不援引任何具體的亞洲電影理論(中國、日本或印度),而是廣泛地從哲學(xué)思想、白話諺語、格言或箴言中得出的東方思維,將它們應(yīng)用于西方電影,而不是暗示這些理論主要存在于亞洲或中國電影中。②TEO Steven.Eastern approaches to western film,asian reception and aesthetics in cinema[M].London·New York:Bloomsbury,2019:12.
在張建德提到的《電影接近現(xiàn)實》一書中,范可樂強調(diào)了包衛(wèi)紅、洪國鈞、王一曼、張英進、張真等海外漢學(xué)電影研究者圍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國電影“評論”展開了豐富而有益的爭論,中國本土學(xué)者有意識地致力于建立一種“中國電影理論”的經(jīng)典文本譜系和標準,但范可樂強調(diào)這些“理論”必須具有中國電影情境的適用性:
經(jīng)過近八十年的調(diào)查和梳理,電影學(xué)者們收集了很多能夠大致稱為中國電影理論的作品。然而,從概念上講,推崇電影理論而沒有把理論運用于中國電影情境中的做法是簡單的。③范可樂.電影接近現(xiàn)實——基于中國電影理論[M].朱安博,等譯.北京:首都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xué)出版社,2020:5.
2022年,范可樂出版了新作《電影圖解現(xiàn)實》(Cinema Illuminating Reality:Media Philosophy through Buddhism),這本書的立意與《東方方法下的西方電影》非常接近,但范可樂嘗試走了另外一條道路,他用東方佛教思想來建構(gòu)一種關(guān)于電影的媒介哲學(xué)。“媒介哲學(xué)”這個概念是伴隨新物質(zhì)主義方法在人文學(xué)科中的產(chǎn)生,以及哲學(xué)中的物導(dǎo)向理論的出現(xiàn),在21世紀初提出的概念,它對應(yīng)了人文學(xué)科中關(guān)于媒介本體論或者媒介考古學(xué)的興起,是一整套在西方學(xué)術(shù)話語系統(tǒng)下衍生的方法論。范可樂嘗試利用佛教的哲學(xué)重新為媒介哲學(xué)提供一套方法,并且結(jié)合電影作品來談。
我們的研究之旅可以分為五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階段: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xué)、美學(xué)和政治。在我的討論中,我也注意到辯論的歷史和跨文化背景,并討論它們的歷史性是如何影響和改變我們對特定概念的理解的。在我對美學(xué)的討論中,其歷史性問題尤其突出,因為我們所認為的“佛教美學(xué)”是一個復(fù)雜的話語,它帶有哲學(xué)同步性、語言和文化(誤)譯以及殖民干預(yù)的痕跡。④FAN Victor.Cinema illuminating reality:Media philosophy through buddhism[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2:8.
范可樂比較可貴的一點是不強求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哲學(xué)概念對英文的精確翻譯,而是保留了其概念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從佛學(xué)基本的本體論、認識論和美學(xué)角度,去回應(yīng)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等歐洲技術(shù)理論家的思想。范可樂把中日佛學(xué)學(xué)者關(guān)于技術(shù)性、科學(xué)性、運動、時間性、倫理和美學(xué)的討論,與歐美學(xué)者提出的電影媒體哲學(xué)的相關(guān)問題展開了比較。這項工作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當我們?nèi)ビ懻撐鞣礁拍顚χ袊娪敖缍ǖ挠行詴r,當我們強調(diào)中國電影經(jīng)驗的有限性時,我們應(yīng)該考慮中國是否也具有可以重新挖掘、闡釋或建構(gòu)的普適概念與哲學(xué),而這些思想反過來可以用于解決西方思想或電影創(chuàng)作面臨的當下問題。
五、品級論、溯流別與以意逆志
鑒于篇幅,本文無法詳細評述張建德與范可樂的觀點與創(chuàng)新之處,希望借用他們的工作成果,研究用中國理論書寫西方電影的可能性;易言之,運用中國理論重新對西方電影的美學(xué)價值展開全面評估,為西方電影創(chuàng)作和電影史的書寫提供完全不同的方法論。中國古典藝術(shù)理論中有許多經(jīng)典的體系性范式,但這些方法在電影誕生的時代里尚未充分發(fā)揮其作為理論對電影發(fā)展的真正作用。本文并不想研究某個古典美學(xué)范疇在電影作品中的化用,而是提出可以作為歷史方法和作品研究的系統(tǒng)性理論。本文試舉兩例,盡管不盡完備準確,但求為拓展中國電影理論的“西體中用”指出方向。
在中國古代藝術(shù)哲學(xué)的體系性著作中,“品級論”是一種歷史悠久且獨特的藝術(shù)作品品評方法。其從鐘嶸的《詩品》和謝赫的《古畫品錄》等開始出現(xiàn),在《二十四詩品》中發(fā)展完善成熟。關(guān)于《二十四詩品》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尚存爭議,①關(guān)于《二十四詩品》作者與成書年代,參見朱良志《〈二十四詩品〉講記》的《破題》和《總說》部分,其對《二十四詩品》的作者、成書年代和版本進行了詳細的說明。朱良志.破題[M]//《二十四詩品》講記.北京:中華書局,2017:3-16;朱良志.總說[M]//《二十四詩品》講記.北京:中華書局,2017:197-274.但這本著作本身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四詩品》列了二十四個品評詩歌的審美范疇,這些“品”并非簡單的分類,更為每一個“品”類的作品確立了不同的“級”。這本中國歷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體系性文藝理論著作,實際上設(shè)定了唐代之后日益發(fā)展起來的“溯流別”與“品級論”方法。章學(xué)誠在《文史通義》中曾評價《詩品》為“深從六藝溯流別也”。②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M].羅炳良,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881.即為一部作品判定具體的品,并對同一美學(xué)風(fēng)格中的優(yōu)秀作品進行推本溯源,以確定每部作品的“級”,“品級論”與“溯流別”對中國后世藝術(shù)理論的方法形成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成為諸多畫品、曲品、詞品、書品等各門藝術(shù)理論的書寫范式。
電影畢竟不是詩,但不妨以詩論電影,或許“雄渾”“沖淡”等詩品未必可以用來評價西方的電影作品,但多元范疇與推本溯源的風(fēng)格體系,無疑為西方史學(xué)單一線性的時序論述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歷史研究方法論,而這種方法何嘗不可以用來書寫西方電影史呢?中國的“品級論”與“溯流別”,與西方電影史把技術(shù)和工業(yè)動力作為基本參照的歷史敘述完全不同,純粹聚焦于作品的詩意維度和審美品格,既不追求不同品級之間的高低,也不強調(diào)品級之間的歷史因果,恰恰可以為紛繁復(fù)雜的世界電影提供非常獨特的研究視角與厘清其歷史脈絡(luò)的方法。
在對作品的分析和闡述方面,中國有著“以意逆志”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從魏晉一直延續(xù)到清末,以此在不同時期產(chǎn)生對藝術(shù)作品不同的理解與詮釋范式。以“以意逆志”論來看,電影的要義并不在于視聽語言本身,即視覺、聽覺和語言的感覺之實,而在于超越感知的意義與意象。“以意逆志”論發(fā)展到清代,強調(diào)追求“意在言外”“言近旨遠”“得意忘言”等,這與西方電影理論強調(diào)基于視聽感知的實證分析有著顯著的區(qū)別。③張伯偉.以意逆志論[M]//中國古代文學(xué)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3-101.“以意逆志”論強調(diào)作品的意義不能自動顯現(xiàn),因此必須要以批評家的“意”來理解和闡揚作品的“志”,因而作品的理解和闡釋是一項必要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不斷創(chuàng)造作品的意義和進行新的詮釋,是中國批評家的職責。
在西方電影作品的研究中,“以意逆志”論為從導(dǎo)演和電影作品出發(fā)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提供了根據(jù),影片的解讀既要“知人論世”,同時“見仁見智”,在今人之“意”與西人之“志”之間產(chǎn)生一種理論的張力。當然,清代許多知識分子對“以意逆志”的弊端也提出了質(zhì)疑,如“本事不清”“興會適然”等,但這不妨礙我們在歐美結(jié)構(gòu)主義影片分析模式之外(以雷蒙·貝盧爾、雅克·奧蒙、大衛(wèi)·波德維爾等為代表),提供一種新的詮釋范式,即追求人心的精神相通,評論家的精神沉浸于作品的“志”中,進而通過人格的內(nèi)在模仿與相互靠近,進行理解的升華。
綜上所述,通過電影研究的“西體中用”,在從事西方電影研究的過程中依然可以建設(shè)中國電影學(xué)派,而中國古典藝術(shù)理論的研究方法在與西方電影的相遇和碰撞中也可以實現(xiàn)其自身的現(xiàn)代化,中國理論也可以提供電影藝術(shù)的普適性概念、歷史研究方法和闡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