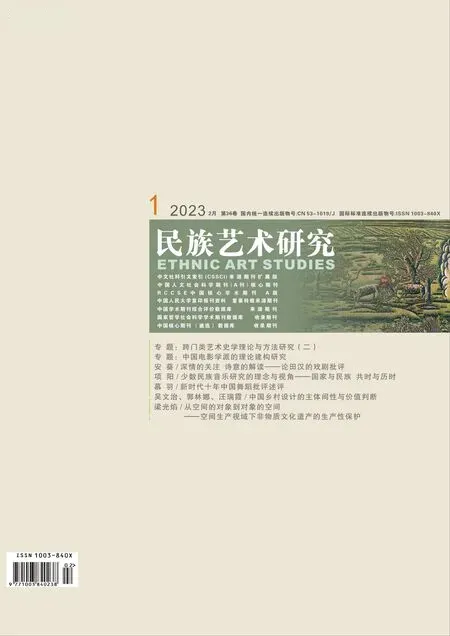人聲化的音響趣味與美感效應
——中國傳統(tǒng)音樂音色的審美取向
劉承華
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音色是音樂音響中最為直觀,也最為表象的聲音形態(tài)。音色既承擔著重要的音樂表現功能,也是音樂的重要魅力資源。在這方面,中國傳統(tǒng)音樂顯示出自身的獨特性,音色也就成為傳統(tǒng)音樂的一個極為鮮明的標識。
一、音色在傳統(tǒng)音樂中的地位
音色(musical quality)即“聲音的特色,是由發(fā)聲物體、發(fā)聲條件、發(fā)聲方法決定的。”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561.實際上,音色是聲音的感覺特性,是特定材質以特定方式在特定條件下振動所產生的聽覺效果。在音樂中,音色是與音高、音強和音長并列的基本音響要素,在構成音樂的表現性及審美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從物理學上說,音色源于不同的泛音組合。聲音由物體的振動形成,物體振動時,其整體的振動形成一個基音,這個基音決定著此聲音的基本性質;同時,在物體的各個單元和部分也發(fā)生振動,產生無數個不同頻率、不同強度的泛音。這些泛音的振動比較微弱,人的聽覺幾乎無法識別。但是,這些不同數量、不同頻率、不同強度的泛音相組合后,便形成各具特點的音色。比如不同的人用普通話念同一句詩,或用不同的樂器演奏同一首樂曲,我們都能夠明白其語義或知曉其曲名,這靠的就是基音。同時,我們又能從聲音中分辨出是什么人念出或什么樂器奏出,如男人、女人,或成人、兒童,或小提琴、二胡、長笛、曲笛,這便是由泛音及其組合形態(tài)決定的。現代聲學理論告訴我們,音色“主要由其諧音的多寡及各諧音的相對強度所決定。”①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2037.一個樂音中不同的諧音按照音高次序排列就形成諧音列。在諧音列中,“第一個諧音又稱‘基音’,其余者稱為基音的‘泛音’。每個樂音音色的異同,主要視諧音列的兩個基本因素而定:一是諧音的數量,二是每個諧音的強度。如果諧音的數量不同,音色感肯定會有差異;假如諧音數量相同,但每個諧音之間的強度關系不同,音色也會發(fā)生變化。”②韓寶強.音的歷程——現代音樂聲學導論[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60-61.一個基音加上不同頻率、不同強度、不同數量的泛音,即構成一個樂音的整體,基音決定著這個音的高低、強弱,泛音及其組合方式便決定著這個音的音色。“諧音越多,聲音越豐滿、圓潤;高頻諧音越多、能量越強,音色聽起來越明亮,反之音色則暗淡;中、低頻基音如果較突出,音色聽起來比較‘厚’,反之音色就比較‘薄’;等等。”③韓寶強.音的歷程——現代音樂聲學導論[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62-63.
由于泛音的多寡、高低、強弱基本上是由振動體的材質決定的,因此,直觀地看,音色便往往與振動體直接相關,決定音色的最直接因素便是振動的材料。正因為此,中國最早的樂器分類——“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就是以材質劃分的。這個分類至少說明兩個問題:其一,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已經認識到音色與振動材料之間的內在聯系;其二,這個行為本身亦表明,中國音樂很早就已經表現出對音色的特別重視。事實正是如此,古代樂人很早就認識到音色在音樂中的重要功能,并將音色作為比較特殊和重要的表現手段。古琴曲《流水》的第二、三段,表現涓涓泉水從山上流淌而下,輕快、跳躍、活潑,富有彈性,樂曲便以泛音演奏,其清亮、晶瑩的音色為其增添了鮮明的效果。而接下來的第四、五段,表現的是泉水流到山腳,匯集成一個小潭,潭水越積越多,終至滿溢而出,水面呈現出搖晃蕩漾之感。隨后,音樂便改用按音演奏,按音中走手音的運用,音域漸漸下行,在古琴的最低音處徘徊,強化了潭水滿溢時起伏蕩漾的感覺。《梅花三弄》中的第一主題也是用泛音演奏,古琴泛音的清亮、透明、有彈性,對于表現梅花清純、高潔的氣韻形成直接的渲染。第二主題表現梅花嚴冬中與寒風奮勇搏擊、不屈不撓的精神,音樂主要用按音演奏,古琴按音特別是手指移動時所形成的走手音,飽滿結實、富有張力,形成與泛音完全不同的表現力,對于音樂主題的推進起到關鍵作用。這里,泛音和按音兩種不同的音色本身就有著相當的表現性。再如民族管弦樂曲《春江花月夜》,其開頭部分使用琵琶輪指技法出現的三連音,是模仿敲鼓聲的,這對于音樂所要表現的夜幕降臨、游船起航、鼓樂齊鳴的夜游情景,有著真切生動的效果。笛曲《鷓鴣飛》則通過竹笛吹奏時對氣息的不同運用,形成音色的強弱變化,表現了鷓鴣在空中翻飛時漸遠漸近的動勢,形象十分鮮明。可以說,在中國傳統(tǒng)的音樂表現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著音色實現的。
與之相比,西方音樂長期以來不太重視音色的表現性。直到19世紀中期,浪漫主義音樂出現,才開始注意音色的表現作用。而真正認識到音色具有表現性并自覺加以運用的,已經是20世紀初了。這時出現的“音色音樂”,就是這方面的代表。其重要人物有勛伯格及其弟子韋伯恩。勛伯格的作品《五首管弦樂曲》之三《色彩》(1909年),就是以音色變化代替音高變化形成“旋律”創(chuàng)作出來的,應該是這方面最早的嘗試。兩年后他在其論著《和聲學》(1911年)中提出“音色旋律法”,主張“把變化音色用于一個音高層次或不同音高的作曲方式……目的是把音色確立為音樂作品中的一個結構要素。”他的學生韋伯恩在他的基礎上又發(fā)展出“點描法”和“音色序列法”,用不同的音色將旋律或和弦分割成細小的色彩點或色彩線。不同的是,韋伯恩的作品中包含著音高變化,但是突出的還是音色。代表作也是名叫《五首管弦樂曲》(1923年)的組曲。
相比之下,中國傳統(tǒng)音樂使用音色參與音樂表現,比西方音樂要早兩千多年,所以歷史悠久,傳統(tǒng)源遠流長。荀子說:“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tǒng)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鑰發(fā)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荀子·樂論》)列述鼓、鐘、磬、竽、笙等十幾種樂器,并一一指出其音色特點,有華麗,有充實,有細致,有柔和,有猛勁,有渾厚,有平和,有柔婉,這些特點無疑是音樂表現的寶貴資源。而到《樂記》,就直接講述不同音色能夠產生的不同聽賞效果了:“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歡,歡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鐘、磬是敲擊旋律樂器,鼓是敲擊節(jié)奏樂器,竹是吹奏類樂器,絲是彈弦類樂器。這些樂器各有不同的音色,參與不同的音樂表現,能夠產生不同的美感效應。所以他最后說:“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音色的真正意義不在音色本身,而在于它同所表現的內容及人生內涵有著內在聯系,亦即“有所合之”。
二、“近人聲”的樂器音色追求
中國傳統(tǒng)音樂既然重視音色的表現性,為了適應表現的需要,其音色一定是豐富多樣且富于變化的。要詳細地描述各種類型的音色,既無可能,也無必要。我們這里關注的是中國傳統(tǒng)音樂在音色方面的總體特征。這個總體特征是什么?是“近人聲”,即在音色上傾向于接近人聲。
傳統(tǒng)音樂音色的“近人聲”首先同古代“貴人聲”的傳統(tǒng)密切相關。所謂“貴人聲”,就是在音樂活動中與各種樂器的聲音相比,以人聲為貴。《禮記·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①阮元.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1446.《尚書大傳》亦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不以竽瑟之聲亂人聲。”②伏生.尚書大傳[M]//叢書集成初編:第356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34.這是通過歌唱者和奏樂者在演出時的不同位置以及歌奏時對聲音的不同要求見出的,堂上堂下的位置和對聲音的不同要求,反映了聲樂與器樂的主從關系。所以,在上古時代,“升歌下管”或“登歌下管”十分普遍,如《周禮·春官·大師》載:“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節(jié)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③阮元.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796.是歌者在上,奏者在下。《周禮·春官·小師》載:“大祭祀,登歌節(jié)拊,下管擊應鼓,徹歌。”④阮元.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797.《儀禮·燕禮》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xiāng)樂。”⑤阮元.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1025.《儀禮·張飲酒禮》亦載:“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⑥阮元.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985-986.可見,“登歌”在上,笙管在下,在先秦時十分普遍,確實體現了對人聲和器聲的不同態(tài)度。
至于“貴人聲”的緣由,古人也有表述。早在先秦時,一些記載在記事的同時,即表達了其間的差別所在。《禮記·仲尼燕語》載:“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⑦阮元.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1614.《禮記·文王世子》載:“天子視學……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⑧阮元.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1410.這是從政治道德方面做出的解釋,其間有德與事、君與臣、貴與賤、上與下等方面的區(qū)別。到東晉時,則以新的角度進行解釋,例如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的解釋是:“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曰:‘漸近自然’”,是以自然和人為論之。宋代陳旸《樂書》認為人聲“無所因”,故貴之;絲竹“有所待”,故賤之,是以直接和間接論之。清人孫希旦《禮記集解》認為,“貴人聲者,聲之出于人者精,寓于物者粗也”,①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675.則是以精粗亦即品質論之。實際上,更為貼近的解釋應該是,人聲能夠更貼切、更直接、更完滿地表達人的思想感情,再現人的風神韻致。音樂所要表達的內容是人自身,那么,其載體越是接近人本身自然就越好。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聲律》中的話應該是合理的:“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效]器者也。”②劉勰.文心雕龍[M]//中國古代樂論選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133.唐孔穎達《詩大序·疏》亦有同樣的觀點:“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讬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③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270.音樂中的音色出于對人聲的模仿,而非相反。
要說明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音色是對人聲的模仿,最直觀的是樂器。中國傳統(tǒng)樂器分敲擊樂器、彈撥樂器、吹管樂器和拉弦樂器四大類型。在這四大類型中,敲擊樂器除編鐘、編磬、方響外,其余皆為節(jié)奏樂器,離人聲最遠;即如旋律樂器編鐘編磬方響,由于以敲擊出聲,音色離人聲亦較遠。而另外三種類型的樂器則都鮮明地體現出對人聲的模仿,展示出向人聲接近的張力。
在上述三種樂器中,拉弦樂器是最后發(fā)展起來的,卻是最接近人聲的。雖然它也屬弦樂器,但由于用弓擦弦發(fā)聲,聲音可以自由延長,類似人的嗓音;又因其左手按弦更加靈敏,出音密度更高,故表現力更強。所以,以前所謂“絲不如竹”,到了宋代,便得到根本的扭轉。宋人劉敞的詩即為一證:“奚人作琴便馬上,弦以雙繭絕清壯。高堂一聽風雪寒,坐客低回為凄愴。深入洞簫抗如歌,眾音疑是此最多。可憐繁手無斷續(xù),誰道絲聲不如竹。”④洛秦.中國古代樂器藝術發(fā)展歷程[M]//薛良.音樂知識手冊:第三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80.“誰道絲聲不如竹”中的“絲聲”,就不是彈撥樂器,而是拉弦樂器了。此后,作為擦弦樂器的胡琴,又同各地的戲曲結合,充當唱腔的伴奏。伴奏中的托腔功能使得樂器的音色進一步向人聲靠近。隨著戲曲的不同聲腔,終于分化成二胡、京胡、高胡、墜胡、板胡等不同的品種。這些不同品種的胡琴,雖音色各異,但在接近各自所伴奏的人聲方面,完全一致。
吹管樂器本來是最接近人聲的,自從有了拉弦樂器,它便退居其次。吹管樂器之所以比較接近人聲,是因其發(fā)音體為管狀,空氣柱振動,其發(fā)音方式與喉嚨比較相似。但因其靠氣息發(fā)聲,氣息總是有限度,吹奏時容易弱化或中斷,加上手指按孔又不及按弦敏活,所以表現力較拉弦樂器要稍遜一籌。盡管如此,吹管樂器仍然天然地具有人聲的韻味。早在漢代,鄭玄在注《周禮》時就說:在人聲之外“特言管者,貴人氣也。”何謂“貴人氣”?唐賈公彥疏云:“以管簫皆用氣,故云‘貴人氣’。”就是說,吹奏管簫用的是口中之氣,與人聲較為接近,故亦貴之。他還將吹管樂器與人聲及鐘鼓相比較來界定其地位:“若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歌用人聲為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于用手,故在階間也。”⑤阮元.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796.“上”即堂上,“下”即堂下,亦即階間,“庭”即院子,又在階下或階外。在接近人聲方面,吹管樂器(匏竹)介于人聲與鐘鼓之間,故在堂下、階間,其地位也是以對人聲的接近程度而定。
相比之下,彈弦樂器是點狀發(fā)音,距人聲較遠,應該是不能滿足“近人聲”的品格的。但是,既然樂器之聲以“近人聲”為貴,則彈撥樂器也不能例外。于是,古代樂人通過自己的努力,終于想出使音色接近人聲的方法,那就是在彈撥樂器中普遍使用的“吟”“猱”“綽”“注”等各種滑音技法。這些技法將本是點狀的音變成了線狀,以接近人說話時語言的聲調,亦即沈洽先生所說的“音腔”。因為中國的語言屬于漢藏語系,每個字音都有升降變化。而經過升降變化后的語音,便呈現出各種不同的線狀形跡。彈撥樂器無法在聲音的連貫性上與拉弦、吹管相比,只能在微觀的音形處理上向人聲接近。也因為此,人們才說:“絲不如竹”。但盡管如此,它還是在努力克服自身的“弱點”,竭力向人聲接近的。
從最有代表性,亦最常用的三大類型樂器的音色來看,中國樂器中確實存在著以人聲為美,在音色上努力接近人聲的傾向。
中國傳統(tǒng)音樂有“近人聲”的追求。那么,西方音樂呢?應該說,西方音樂在古代也是重人聲的,如中世紀的圣詠、近代歌劇等,也屬于“貴人聲”的行列,即以人聲為主。但是,到歐洲工業(yè)文明興起,才開始表現出遠離“人聲”,而接近另外一種音色,筆者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稱之為“器聲”,并對它做過解釋:“所謂‘器’聲,則是指樂器的音響品質遠離人的嗓音,而趨向于和任何一種自然聲響都不相同,都保持相當距離的‘物’聲。因為這種物聲不屬于任何自然聲響,并且是人為制造的產物,故而稱之為‘器’聲,因為‘器’本來就是指那種人工制造的物品、工具。”①劉承華.中西樂器的音色特征及其文化內涵[J].樂器,1996(2):1-4.自然界只有“物”,沒有“器”,“器”是人為制造或加工的產物。地里生長、蔓上結出的葫蘆是“物”,將老熟的葫蘆摘下,剖開,去掉種子,做成瓢,作為舀水、盛物的工具,就是“器”。所以,“器”有兩個特點:一是人為加工的產品,而非自然物;二是因人為加工,故體現著人的意志,具有共性特征。西方樂器恰好強調人為加工,強調其非自然性,并努力消除自然物原有的個性,而著力體現某種共通的性質。西方樂器的制造遵循的就是這一原則,所以其音色趨于共性。也正是因為趨向共性,不同樂器之間才能獲得良好的融合性。西方音樂的交響化,就是建立在樂器音色的融合性上的。
其實,中、西音色上的“近人聲”和“近器聲”,不僅在器樂上得到體現,在聲樂上也有表現。中國聲樂的音色以民族唱法為代表,西洋聲樂則以美聲唱法最有代表性。恰恰在這兩種唱法上,清晰地表現出兩種音色的差異。筆者曾經對這兩種唱法下過定義,從這定義亦可清晰地見出兩者的不同。民族唱法是:“以同地方語言(語音、聲調)相結合的發(fā)聲為基礎,以風格化的吐字運腔為中心,以保持嗓音的自然狀態(tài)為樞紐,來獲得一種真實、樸實且豐富多樣、富于地方風味的、具有獨特性的音色。”而西洋唱法則是:“以發(fā)聲器官與共鳴器官的充分運用為基礎,以改變嗓音的自然狀態(tài)為樞紐,來獲得一種遠離日常人聲的、經過美化了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音色。”②劉承華.中西樂器的音色特征及其文化內涵[J].樂器,1996(2):1-4.簡而言之,中國民族唱法的音色特點是保持真實的人聲,而西方美聲唱法則是遠離真實的人聲,而趨向于共性化的“器聲”。
中西音色的這個差異有其文化上的原因,是受著雙方不同的文化意識支配的。西方文化屬于科學型的文化,重視理性是其基本特點,而在理性思維中,傾向于將世界一分為二:現象世界和本質世界,前者是感性的現實世界,后者是抽象的理念世界。現象世界是變化無常、多種多樣的,但并不真實;本質世界是穩(wěn)定的,具有同一性,故而是真實的。現象世界受著本質世界的支配和決定,本質世界才是現象世界的本原和根據。所以,我們要認知世界,就是要通過現象世界去把握本質世界,要透過變化不定的現象世界進入穩(wěn)定永恒的抽象世界,要擺脫有限的個別事物而進入普遍的共性世界。這反映在音色上,就形成努力遠離個別化的人聲而趨向共性化的器聲。相比之下,中國文化中更多運用的是具象思維。具象思維的特點是思維時始終不脫離形象,理性也不與感性分離。在中國文化觀念中,現象就是本質,本質不在現象之外,而就在現象之中。因為在現象中,所以本質并非永恒不變的抽象,而是多樣且多變的。在這個觀念指導下,我們自然就不會拋棄個別的、真實的、感性化的“人聲”,而去人為制造抽象的、共性化的、具有普適性的“器聲”。從這個角度去考察兩種音色的不同價值取向,或許能夠得到更深一層的理解。
三、“近人聲”的樂器演進軌跡
中國三大類樂器的音色表現出“近人聲”的特點,那么,在中國樂器總體發(fā)展進程中又如何?我們能否在樂器演進的過程中進一步窺見其“近人聲”的歷史張力?回答是:能。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幾個大類的樂器,除拉弦樂器出現較晚外,其他三類樂器的產生年代并無嚴格的先后之別,幾乎在先秦均已出現。敲擊樂器以鼓、鐘、磬為代表,吹管樂器以笛、簫、笙、篪為代表,彈撥樂器以琴、瑟、箏為代表,均產生于周代或更早。但是,不同種類的樂器在不同時代其地位和意義各不相同。洛秦先生在考察中國古代樂器發(fā)展史時描述過樂器演進的軌跡,認為:先秦是“敲擊樂器主宰”,漢晉是“吹管樂器成長”,隋唐為“弦管樂器并駕齊驅”,兩宋是“吹管樂器再次崛起”,明清是“拉弦樂器確立”。他還指出:“在中國古代樂器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趨向,那就是模擬人聲,不斷朝歌唱性方向完善。”①洛秦.中國古代樂器藝術發(fā)展歷程[M]//薛良.音樂知識手冊:第三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40-85.也就是說,一方面,敲擊、吹管、彈撥三類樂器雖然是同期出現,但在不同時代其地位不同,以其具有代表性的類型描述其演進軌跡,就可以反映其歷時性過程。另一方面,通過這個歷時性過程,就能夠清楚地看出,樂器發(fā)展的過程就是音色不斷“人聲化”的過程,或者說,是“人聲化”的音色要求在驅動著樂器的歷史進程。
首先,在先秦,敲擊樂器是為主體,人聲尚未在樂器中引起注意。這是很自然的,就音樂本身的歷史形成來看,最早出現的音樂元素當是節(jié)奏,旋律是稍后的事情,而音腔就更是后來的事了。就節(jié)奏而言,最適合的載體當然是敲擊樂器。因此,在先秦,敲擊樂器無疑占據樂器家族的主體位置。其功能,一是表示節(jié)奏,如《尚書》 “擊石拊石”;“投足以歌八闕”。《大雅·靈臺》“于論鼓鐘”;“鼉鼓逢逢”等。二是代表神靈,代表貴族,如《呂氏春秋》:“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韓非子》:“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鐘鼓之樂;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于瓴缶之樂。”《荀子》:“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在那個時代,最為重要的樂器就是鼓、鐘、磬,在最早的制造學著作《考工記》中,樂器方面也只是記載了鼓、鐘、磬三種的制作方法,其余皆未顧及。而湖北隨縣曾侯乙墓65枚一套編鐘的出土,其超大的規(guī)模、先進的科技、精湛的工藝及其所需的巨大人力、財力、物力,更是直觀地反映出敲擊樂器在那個時代的無與倫比的地位。同時,也正是因為此時的敲擊樂器,主天地鬼神,地位極高,人間氣反而十分稀薄,樂器中的人聲意識尚未成型,以“近人聲”為特長的樂器如吹管樂器,②當時的彈撥樂器,如琴、瑟、箏、筑等,左手技法相對簡單甚至沒有,如古琴徽位尚未出現,左手取音機會不多,故用韻相對簡單,距離人聲較遠。只能退居次要位置。
到漢晉時,吹管樂器得以成長,世俗性增強,人的主題開始覺醒。世俗文化發(fā)展,貴族文化衰落,與此相應,旋律樂器鐘磬不再輝煌,鼓只是作為節(jié)奏樂器存在,而在先秦時處于陪襯地位的吹管樂器則勃然興起,一躍而成為該時代的主體樂器。之所以會如此,原因有四:一是旋律功能得到發(fā)展,從漢代起,吹管樂器如塤、篴、篪、管均由六孔增為七孔,五聲音階發(fā)展為七聲音階,旋律功能得到大幅提高。二是樂器種類增多,除了原有的笛、簫、篪、笙、塤等進一步演進分化外,還有西域樂器大規(guī)模地傳入,如胡角、胡笳、羌笛等,形成規(guī)模龐大、種類繁多、音色豐富的吹管樂器家族。三是律制有了新的發(fā)展,晉荀勖“十二笛律”代替了“鐘律”,使定音、校律工作更方便,有力推進了音樂的標準化、規(guī)范化。四是創(chuàng)作上形成以吹歌為代表的音樂形式,鼓吹、騎吹、橫吹、相和歌、清商樂等,都是以吹奏為主。吹管樂器在這一時代頓然興盛,其音樂表現轉向世俗,人的生活情韻成為音樂表現的重要主題。其實,正是因為音樂需要完滿地表現生活情韻,故而才選擇了在當時最具人聲性的吹管樂器。
隋唐時,彈弦吹管并駕齊驅,開始既向外鋪陳,又向內求聲。此時,與西域的文化交流達到高潮,政治上南北統(tǒng)一,經濟文化全面發(fā)展,不久便形成極為壯觀的盛唐氣象。此時的社會精神氛圍是:開放、樂觀、積極、向上,宴享風氣盛行,音樂也隨之繁榮。在樂器方面則形成弦管并盛的格局,彈撥樂器和吹管樂器共同成為呈現盛唐精神風貌的載體,音色上既喜好清脆、明亮、流暢,又追求色彩的繁富密麗、網狀鋪疊,形成兩條線索互為補充、交織的格局。就吹管樂器來說,其音響效果是單向的線型伸展,笙、簫、篳篥、尺八、篪、笛等均為此時極為活躍的樂器。特別是笛,此時增加了一個膜孔,發(fā)音清脆嘹亮,使音色產生質的改變,而其人聲化的音色仍然得以保存,在音樂活動中發(fā)揮其特別的作用。而就彈撥樂器說,其音響效果則為立體的網狀鋪疊,如琴、瑟、箏、箜篌、三弦、阮、琵琶等。特別是曲項琵琶,北周時由龜茲人蘇祇婆帶入境內,唐時又不斷加以改進:形制縮小,使攜帶更方便;演奏方法由橫彈改為斜彈和豎彈,左手得到解放,手指彈奏更為自如敏活,出音密度更高,網狀鋪疊的效果更為突出。在漢晉時代、唐代盛行的生命意識和享樂心理,一方面在以琵琶為代表的彈撥樂器那繁富密麗的音色中得到激活,一方面也在以笛為代表的吹管樂器那幽婉的人聲韻味中進一步深化。
再到兩宋,吹管重新崛起,音樂轉向內心,人聲得以凸顯。宋代是文人治世,文化上追求雅致,崇尚內斂、含蓄的作風。藝術上轉向表達人的內心世界。音樂上推崇復古、提倡雅樂,其中漢魏時的鼓吹樂得以復興,形成又一個高潮。唐代音樂中開放的、張揚的彈撥樂器,或者悄悄改變了風格,或者漸漸沉息下去;而向內心開掘、以人聲韻味見長的吹管樂器,則有了新的發(fā)展。洛秦先生在考察宋朝廷用樂時發(fā)現,橫吹樂、鼓吹樂在音樂活動中占據絕對優(yōu)勢:人數多、樂器種類多、用頻高、地位突出。在宮廷樂中,簫、笛勝過箏、阮、琵琶。民間瓦肆勾欄中,簫、笙、篳篥、笛是最常用樂器;在描述伴奏時,最常用的詞是“吹”字。另據《武林舊事》記載,“乾淳教坊樂部”樂工及使用樂器的數據是:拍板7人,琵琶8人,簫8人,嵇琴11人,箏6人,笙13人,觱篥71人,笛84人,方響10人,仗鼓36人,大鼓16人。去除節(jié)奏樂器拍板、鼓和拉弦樂器嵇琴、敲擊旋律樂器方響等,僅吹管樂器即多達176人,而彈撥樂器僅14人,兩者比例是12.5∶1。吹管樂器在宋代的重新崛起,于此可見一斑。之所以會重新崛起,是因為宋代文化向內發(fā)展,音樂需要發(fā)掘人的內心,人聲化變得十分重要;加上此時戲曲曲藝開始發(fā)展起來,吹管樂器參與其中,伴奏中對人聲元素的強烈需求也促進了吹管樂器用頻的快速增長和地位的大幅提高。
最后到了明清,拉弦樂器真正確立其主要地位,借助戲曲托腔,成就其人聲特點。其實,早在宋代,一種源于唐代的拉弦樂器——嵇琴(也稱奚琴)基本成熟:圓筒,蒙皮,二弦,縛有千斤①胡琴何時有千斤,說法不一。有人據陳旸《樂書》中的奚琴圖尚無千斤,認為宋代胡琴無千斤,但最遲明代嘉靖時已有千斤,證據是此時的《麟堂秋宴圖》。但《樂書》中的奚琴圖所記應該是早期的形制,不太像“一弦嵇琴格”中的胡琴。,弓以馬尾,于二弦間擦奏出聲。沈括所謂“馬尾胡琴隨漢車”即是;而徐衍的“一弦嵇琴格”更證明其成熟。所以,在宋代,拉弦樂器在性能上已基本完備。劉敞詩云:“奚人作琴便馬上,弦以雙繭絕清壯。高堂一聽風雪寒,坐客低回為凄愴。深入洞簫抗如歌,眾音疑是此最多。可憐繁手無斷續(xù),誰道絲聲不如竹!”②洛秦.中國古代樂器藝術發(fā)展歷程[M]//薛良.音樂知識手冊:第三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80.其發(fā)聲“清壯”,音色“如歌”,感染力強。元代散曲家張養(yǎng)浩亦有散曲《折桂令·詠胡琴》:“八音中最妙唯弦。塞上新聲,字字清圓。錦樹啼鶯,朝陽鳴鳳,空谷流泉。引玉杖輕攏慢撚,賽歌喉傾倒賓筵。常記當年,青案之前,一曲春生,四海名傳。”③洛秦.中國古代樂器藝術發(fā)展歷程[M]//薛良.音樂知識手冊:第三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80.不管此時的胡琴形制是否完備,其近人聲的音色特點已經形成,并為人們所欣賞。隨著明清時戲曲的蓬勃發(fā)展,胡琴加入其中。特別是到了清代,各地地方戲(亂彈)興起之后,拉弦樂器快速發(fā)展,且種類繁多,僅清《皇朝禮器圖式》和《大清會典圖》,即記有近十種之多。更為重要的是,幾乎所有戲曲,其主要伴奏樂器均先后從吹管或彈撥改為拉弦。據《清稗類鈔》載:“昆曲必佐以竹,秦聲必間以絲。今之唱秦聲者以絲為主而間以竹,或但有絲而去其竹。”①徐珂.清稗類鈔[M].北京:中華書局,1996.這里的“絲”主要指拉弦樂器。又:“嗩吶、海笛,非吹牌不用,笛非唱昆弋腔不用。恒用者惟絲,然絲中惟胡琴必不可離。”這里的“絲”也主要是指以胡琴為代表的拉弦樂器。
戲曲伴奏之所以紛紛改用胡琴,是因為表現力強,又接近人聲,有利托腔。洛秦先生總結過拉弦樂器胡琴的特點有四條:“(1)千斤活動不固定形成了音域靈活、調高自由,非常容易‘隨腔行調’;(2)沒有指板、一弦多音,因此音律可變,宮調旋轉極自由;(3)拉弦樂器的揉弦顫音手段是模擬人聲歌喉顫音最接近和直接的表現方法;(4)蒙皮琴筒的發(fā)音音色接近人聲。”他接著總結道:“與吹管樂器相比,除了在音律固定問題上各有所長,其他的表現功能在模擬人聲上,拉弦樂器者勝于吹管樂器一大籌。”②洛秦.中國古代樂器藝術發(fā)展歷程[M]//薛良.音樂知識手冊:第三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80.胡琴的這個優(yōu)勢,我們可以從清代琴師梅雨田身上見其一二。梅雨田“初以笛名,能吹昆曲三百余套。以昆曲不盛于世,乃改習胡琴。……梅體肥而膚潤,故發(fā)音為天下第一。……胡琴……自梅弄之,凡喉所能至,弦亦能至。柔之令細則如蠅,放之令洪則如虎,連之令密則如雨,斷之令散則如風。”戲曲唱腔中樂器伴奏的主要功能是托腔,由于各地戲曲唱腔的不同,作為伴奏樂器的胡琴自然隨之變化,逐漸分化成二胡(南胡)、粵胡(高胡)、墜胡、京胡、板胡等不同的類型,以各自獨特的音色活躍于大江南北,豐富了拉弦樂器的表現力。
從先秦時樂器中人聲的尚未覺醒,到漢晉時人聲意識的萌發(fā),經過隋唐時對繁富密麗和幽婉情韻的雙軌運行,到宋元時對人聲的再次開發(fā),最后在明清時隨著戲曲伴奏而鋪開,演化成各具特色的人聲化胡琴,確乎展現出古代樂器音色不斷向人聲接近的歷史過程。洛秦先生說:“樂器發(fā)展實際上是一種音樂聽覺意識變化、發(fā)展不斷物態(tài)化活動的過程。”這說得很對,還可以加上一句:從聽覺意識到物態(tài)樂器之間的轉化有一個中介環(huán)節(jié)在起作用,那就是音色。
四、審美上的質感效果
中國傳統(tǒng)音樂如此重視音色的表現,又如此明確地追求其接近人聲,并在音樂創(chuàng)作和表演中大量使用音色,是為了使演奏或演唱的聲音獲得鮮明的質感效果。
在現實生活中,“質感”是指物體在人的感官中形成的關于該物的材料、品質或外觀、形式方面的感覺,是由物體材料本身的特點作用于人后直接產生的感知效果。質感是生理感覺和心理知覺的綜合反應,并受所在文化語境的影響。
能夠形成質感的感官有多種,但主要體現在視覺、觸覺和聽覺方面。③此外如味覺、嗅覺也能產生質感體驗。視覺上的質感是指:當眼睛看到某物體時,由于其材質或形式顯示出某種特點,使得心理上產生對于該物體品質的感知。如我們只要憑眼睛就能夠輕易地分辨出面前的物品是棉布還是絲綢,是金屬還是塑料,是松木還是紅木。觸覺上的質感是指:我們無須眼睛觀看,只憑手或其他身體部位接觸、撫摸物體,就能產生對該物體材質或形式的感知。如我們只要摸一摸面前的布料,就能夠判斷其是棉的還是絲的;只要摸一摸面前的杯子,就能判斷出是玻璃杯還是塑料杯,是陶瓷杯還是金屬杯。當然,在現實生活中,更多的時候還是多種感官相配合來產生質感,完成對物體材質和形式的判斷。如當眼睛無法斷定這塊布料是棉的還是絲的時,用手摸一摸,可以幫助你作出更為準確的判斷。同樣,聽覺上的質感,也是通過聲音對聲源所作的感知。如果我們對音樂有一定的知識和聽覺經驗,那么在聽一曲弦樂獨奏的音響時,就能夠根據聲音判斷出是小提琴還是二胡,是吉他還是琵琶;聽到敲鼓聲時,也能夠分辨出是腰鼓還是洋鼓,是大鼓還是小軍鼓。聽到聲音,無須眼睛觀看,就能夠產生對發(fā)聲體的意識或感知,就是聽覺上的質感。無論是視覺、觸覺還是聽覺,其質感都有一個特點,即具有指向物體的直接性和真切性,或者說是“及物性”,就是通過感官將意識直接指向對象物本身。
藝術中的質感源于生活中的質感,實際上是生活中的質感經驗向藝術媒介的轉移。造型藝術如繪畫,就是把生活中的視覺質感效應運用到繪畫當中。因為我們存在著對布料的質感經驗,所以才能夠在畫作中以特定的線條或色彩,表現出人物所穿衣服的質料:是棉的還是絲的,是粗布還是軟布。聽覺質感也是如此。因為在生活中有過林中聽鳥鳴的經驗,所以,我們一聽到劉天華的二胡曲《空山鳥語》,就能夠產生鳥語的感知以及聽賞鳥語的情境體驗。因為有觀看山中泉水流淌的經驗,所以我們一聽到古琴曲《流水》,那種由泛音演奏的輕快活潑旋律和按音演奏的沉著穩(wěn)健的音型,就能夠立刻產生泉水叮咚和潭水晃蕩的感覺。在這里,由樂聲所喚起的感覺、感知和體驗,就是質感;這些質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特定的音色產生出來的。
那么,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人聲化”音色,對于音樂表現有何意義?
首先,“人聲化”的音色容易引發(fā)聽賞者的心理感應和共鳴,產生審美活動。音樂就其表現的境域而言,應該是十分寬闊的,從人的情感、心態(tài)、活動,乃至一般事物、自然現象,幾乎無所不包。但就其普遍性來看,還是人的情感、感覺、心理才是音樂最常表現的對象。即使是自然中的事物,也往往是通過人的感知轉換后才得到音樂的表現的。傳統(tǒng)音樂中常以山水為表現題材,但其表現方式,雖然也有少量是直接描摹山水形貌,但更多的是表現山水所引起的人的心理狀態(tài)。而人的心理狀態(tài),包括情感、情緒、心態(tài)、意念,往往與語音、聲調、哭聲、笑聲、嘆息聲、哀鳴聲等相聯系,不同的人聲效果能夠立刻喚起相關情感和心理的體驗,快速形成審美活動。
其次,“人聲化”音色中,有些特殊的人聲效果能夠引起特殊的體驗,強化音樂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如二胡曲《二泉映月》,所用樂器二胡的音色本來就特別接近人的嗓音,同樂曲感嘆人生、抒發(fā)情懷十分吻合,故其音色本身就包含著一定的表現性。而阿炳使用的二胡,里弦采用更粗的老弦,聲音低沉、粗獷、蒼老,增加了音樂的低回、悲涼和滄桑,無疑是對樂曲表現情韻的深化。古琴曲《長門怨》,表現的是陳皇后被漢武帝打入冷宮后內心的悲苦、哀怨和不甘,其間還有訴說、呼喚的音調。古琴演奏時充分運用其走手技法如綽、注、撞、逗等,形成或長或短的滑音,以表現人聲呼喚、哀嘆等情態(tài)語氣的質感效果,增強了音樂的感染力。
再次,“人聲化”是樂器對人的嗓音的模仿,而人的嗓音是多種多樣的,因此,“人聲化”的音色也是多種多樣。這只要看一下胡琴家族就能明白,不同的胡琴音色各不相同,所內含的人聲也不一樣。甚至同一件樂器,在其不同的部位,如胡琴的上把位與下把位、內弦與外弦、連弓與跳弓,古琴的散音、泛音和按音,上準音、中準音和下準音等,都各有特色,都能形成自己的表現個性。音色的這種個性,能夠給人以鮮明而又深刻的印象,產生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和刻骨銘心的審美效果。
那么,生活中的質感是如何轉化為音樂中的質感的?這就涉及“聯覺”和“通感”。所謂“聯覺”,就是感官對感官刺激物與其相關現象的直接轉換,是生活中特定聯想和想象經過無數次重復所形成的快捷通道。而“通感”則指不同感官(如視覺與嗅覺、視覺與聽覺)之間的感覺轉換。換句話說,“通感”是某感官與另一感官之間的轉換,聯覺是感官與感知對象(意義)之間的轉換。在一個質感現象中,往往是通感與聯覺并用,它們在實際知覺活動中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質感過程中的聯覺和通感需要兩個條件:經驗和體驗。這是兩個互相交叉而非單相包含的范疇。經驗主要是指向外部事物的一種認知性積累,體驗則是著眼于內心反應的一種感受性積累。互相不一定構成前提或基礎。沒有深厚的經驗積累不一定不能產生豐富的心理體驗;而有豐富的經驗也不一定就能產生豐富的心理體驗。但是,要想形成質感體驗,就必須將經驗與體驗打通,讓它們自由往來,自由轉換。例如前述琴曲《流水》和《梅花三弄》,要想在聽賞過程中產生質感體驗,就必須在生活中有親臨山中泉流和寒風中觀賞梅花的經驗,沒有此經驗,這兩首樂曲的質感效果就不會出現。但是,光有此經驗還不一定能夠體驗到質感效應,還需要聽者有過對兩種情境的心理體驗,也就是說,要有將經驗轉化為體驗的過程。看到泉水流淌,要能夠體驗到它的輕快、活潑,看到梅花臨寒開放,要能夠體驗到它的圣潔與勇敢的品格,否則,即使面對樂曲中的音色表現,質感效果也無從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