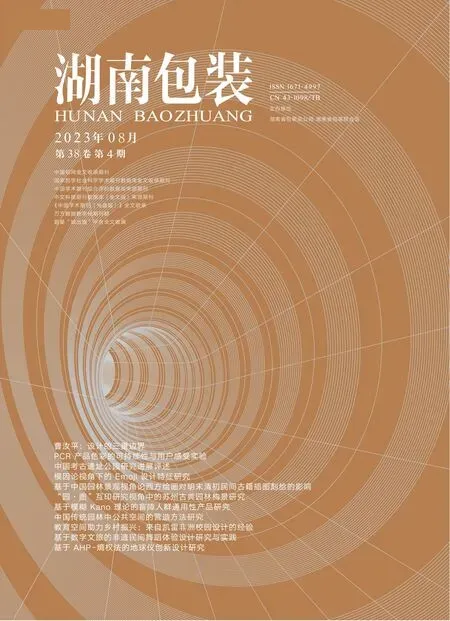甲骨文中季節文字的圖像探究
——以“夏、秋”為例
劉曉亞 王進華
(陜西師范大學,陜西 西安 710000)
漢字作為世界上僅存并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產生于早期中華民族相對獨立的特殊文化環境中,沒有受到其他文字的影響,成為了中華文化精神的載體和文化的符號。文章從視覺文化角度出發,借助索緒爾的二元論和皮爾斯的三元論以及米克·巴爾的后現代符號學理論對甲骨文進行符號化探究,選取季節性文字“夏”“秋”為例,從符號構成、符號系統、符號解讀3方面對甲骨文進行深層挖掘,結合甲骨文背后特定歷史時期的殷商文化,探究甲骨文符號化新的含義。
1 甲骨圖像與圖像時代
甲骨文是原始藝術的一種審美圖像,作為原始活動符號化的結果,它凝聚著殷商歷史時期特定的社會意識、強烈的思想情感觀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社會價值與反思。作為中華先民對于世界萬物抽象的藝術概括,它通過對事物符號化的簡化和抽象,使人們理解世界的普世價值,并概括了事物發展一般性質。商代人通過觀星,得出“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東”[1]。通過拜斗,得出“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東”,由此將一年逐漸由兩季劃分為四季[2]。四季的明顯劃分對于當時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殷商社會來說顯得尤為重要。甲骨文作為不依靠其他文字而在中華民族特殊的文化環境中孕育創生的“自源文字”,它生動地反映出中華文明之初的一系列文化信息,是華夏早期文明的發軔。
從人類表達方式的演變過程來看,圖像媒介早于文字媒介而存在,“圖像”與“文化”的碰撞歷史由來已久,這可以從早期巫術與藝術的關系中找到例證。例如圖騰,早在原始社會,出于對自然的敬畏,人們往往祈求通過巫術活動來獲得某種神秘的力量,在這種思維的驅動下,先民把圖騰繪制在器皿上,并把這種圖騰當作是氏族部落的保護神,以達到實現愿望的目的。人類作為視覺動物,“看”這一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成為人類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圖像作為一種視覺思維的表達方式,古往今來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早在原始社會,先民們通過符號,例如結繩記事、圖騰記錄等象征性行為來溝通、記錄,這剛好印證了文字與圖像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關系,使得兩者在人們表達情感的過程中一脈相通。“字之源,始為畫”,甲骨文因其具內部嚴密的書寫系統、以形表意的特征,被認為是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以形表意的甲骨文與圖像之間異質性、雙重性、互滲性、失衡性的關系,對于歷史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3]。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從本質上看來,世界圖像并非意指一幅關于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4]”圖像是人類與世界、“感性”與“理性”、“精神”與“物質”的綜合,是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產物。這其中凝聚著先祖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折射出民族的價值追求與意識形態,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它們不是對自然世界機械化的照抄照搬,而是由人類通過認知創作產生,用視覺化的符號來描述和表征他們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并反映出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狀況。
2 符號構成
甲骨文作為一種以形表意的圖像符號,其符號功能的表達能力主要體現在甲骨文以圖畫式的字形作為能指的具體形式、內容作為所指的性質以及指示二者關系的表意機制。符號能指與所指兩者之間的構成關系是索緒爾二元符號論的關鍵。索緒爾說:“我用‘符號’一語來指概念和音像的組合,用‘所指’來指概念,用‘能指’來指音像。[5]22”以漢字為例,漢字本身具有可讀性,“水”的讀音“shui”與水的圖像是能指,而我們大腦里關于“水”的心理印記以及由此聯想到“水”的概念是所指。概括來講,能指位于表層,所指位于深層,兩者之間的表意機制就是符號的內在結構,這三者之間彼此勾連、相互聯系、相輔相成。對甲骨文進行符號化解讀就涉及到符號的編碼與解碼。
從符號構成角度出發對季節性文字進行符號拆解。在甲骨文中,“夏”是一個意義相對復雜的符號,我們除了可以從季節文字角度出發來理解,也可以從深層次的社會歷史背景角度出發來解讀,這將在后續的符號解讀中進行闡述。從符號構成來看,甲骨文“夏”字由“日”和“頁“兩個符號構成(圖1)。夏天太陽高懸,人在太陽下活動,會感到非常的炎熱,于是就要坐在一邊休息,古人由此定義夏季。上面部分圓形中間加一點的符號表示“日”以示太陽實心之意。太陽位于人頭頂正上方,強烈的光照讓人無處可藏,表示烈日。下面是一個側面的人形,人呈半跪的狀態,雙手前扶在大腿上,背部直立,做虔誠嚴肅的狀態,整體的人形突出頭部和眼部,整個字就像太陽之下跪著的一個人。也有在特定的語境下來解讀“夏”字,據《齊民要術》記載,“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商代,人們會根據黍的播種來判斷季節,根據種植的相關經驗,黍一定是在夏季種植,黍種植的季節也就是語境,這也表明除了符號本身,語境也很重要,在特殊情況下具有決定意義[6]。如果符號的語境發生錯亂,符號就會被誤讀,對季節造成誤判。甲骨文的“秋”字更為復雜,從整體造型上來看它像一只蟋蟀或者是蝗蟲,整個字形由“蟲”和“火”兩個符號構成(圖2)。上方是由頭、身、足組成的完整的蟋蟀的造型,之所以這么造字,是因為特定的語境。在農耕文明的商代,蟋蟀成蟲的季節一般是秋季,同時根據書寫符號的可讀性,蟋蟀的叫聲和秋字讀音相似,也因此人們把蟋蟀當作秋天的代表。下面的“火”由三峰焰型組成,中間的主火堆成“人”型,表示農耕之后人們對土地進行焚燒播種。也有另一種語境的符號解讀,上半部分的“蟲”是蝗蟲,因為蝗蟲具有趨光性,所以下面的“火”是人們為了焚燒蝗蟲而設計,在特定的語境下,相對獨立的兩個符號之間產生聯系,具有了意義。在符號的構成中,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所謂的“指示”也就是表意,這類似于皮爾斯的解釋項。與此同時,巴爾從視覺研究的角度解釋說:再現體是可感知的符號,它另有所指,解釋項則是人腦所接受的物像,亦即對再現體的認知,是一個心理圖像。這個物像所指涉的意義,就是指稱物,即所指的事物項[5]24。解釋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人腦反應的產物。對甲骨文進行符號化的解讀,從表層能指向深層所指轉化的這一過程不是靜止孤立的,而是動態聯系的,也正是這一聯動構建了符號系統。

圖1 甲骨文:夏。

圖2 甲骨文:秋。
3 符號系統
索緒爾的二元論看重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兩方面,而皮爾斯則看重這兩者之間“解釋項”的作用,在他的“無限制”的符號轉換過程中,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多次轉化使得多個符號之間發生鏈接,這樣表層的行為能更好地揭示出深層的思維含義,因此符號系統得以構建[5]11-36。回到甲骨文來探討符號系統問題,甲骨文“夏”字由“日”和“頁”兩個符號構成。“日”的能指是太陽,圓形中間的一點強調實心之意;其所指是指位于人頭頂正上方讓人無處躲藏的強烈的光照,代表了烈日。兩者之間的表意機制是指:位于頭頂的位置好比一天之中的正午12點,此時光照最為強烈旺盛,以示夏季是萬物生長最為旺盛的時期,予以強大繁榮之意。“人”這一符號中,其表層能指是突出眼部和頭部的人的造型,其所指是指位于烈日之下辛勤從事農業勞作的人、跪著從事漁獵的人等一系列辛苦勞動的人。其深層所指從特定的歷史時期角度來看,夏字除了作為季節文字外,還可指夏朝。大禹之子啟建立夏朝。許慎《說文解字》里解到“夏,中國之人也”。作為第一個奴隸制與世襲制的王朝,夏朝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并開啟了家天下的歷史時期,也因此這里的人可以引申為“夏”人。甲骨文“秋”字由“蟲”和“火”兩個符號構成,“蟲”的能指是結構完整的昆蟲的造型,其所指是以蟋蟀或蝗蟲成蟲為代表的秋天。在這里成蟲既是一個符號,又是其他符號的語境,若無這一語境,其他符號的功能將難以發揮。蟋蟀或蝗蟲成蟲的季節是秋天,在這一語境下,它們成為秋天的代名詞,又因為蝗蟲具有趨光性,人們用火來燒作為莊稼天敵的蝗蟲,這樣可以將蟲和火聯系起來。
語境的這一功能將所有的符號以及所有的能指、所指與表意機制聯系起來,構成一個完整又聯動的符號系統。在這些季節性文字中,符號系統不僅包含了構成文字符號的各個要素,更包含了符號之間的相關性。符號相關性作用的發揮源自于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以及符號與語境之間的關系,這種聯系不是片面孤立靜止的,而是完整聯動的,是有深層次結構的,正是這樣的結構,保證了符號系統的完整運作。
4 符號解讀
符號系統內各部分之間的互動關系需要符號機制的維系,其主旨就是保障內部結構的互動,使得符號的能指能夠準確地指示所指,這一程序是雙向的,既可從編碼走向解碼,也可從解碼走向編碼。“人們在交際過程中運用符號傳達訊息,這傳達的過程就是從表達到理解的過程,也就是從編碼到解碼的過程。編碼是表達者把訊息符號化并以符號的形式呈現給理解者。而解碼是理解者把符號形式還原為訊息的過程,理解就是關于符號訊息化的解碼行為。[7]”符號的編碼與解碼在不同的符號系統內部遵循著不同的規則,這雙向的符號化機制恰好印證了編碼與解碼的相互轉化,這兩者不是孤立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為前提。對甲骨文季節性文字的符號解讀既可以從編碼角度出發,也可從解碼角度出發。其實解讀編碼的過程也是解碼的規程,正反兩方面進行解讀,打破受眾被動接受的單線思維,多維度多角度揭示出甲骨文符號創作的內在規約,提高藝術識別度,探討甲骨文背后暗含的社會、文化和思維的所指。以甲骨文“夏”字為例,在編碼的過程中,符號的表層能指和所指是指突出眼部和頭部半跪著的人與其正上方的太陽和由此引申出來的強烈光照的夏季,這些都是屬于感官所能接受的外在連接,而符號的深層能指和所指則是需要理性思考才能接受的內在連接,通過理性思考,分析甲骨文所反映出的中華民族早期審美活動的存在形式,以及審美意識的特點和規律。這里就涉及到歷史上的夏朝,夏朝是一個強大的王朝,《書經》里記載“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這里指出國家很大很發達稱之為夏[8]。春天萬物復蘇,夏天則是萬物生長,植物枝繁葉茂體格高大與大邦夏朝共通,在商朝人眼里,夏國是一個大邦,與夏天枝繁葉茂植物高大相似,兩者存在“大”的共通性。因此夏季與夏朝共用一個文字,邏輯上就說得通了。以上是從皮爾斯和索緒爾的現代主義符號學角度出發,對“夏”字進行符號解讀。
而米克·巴爾的后現代符號學理論強調能指與所指的失諧,則是以新的視角發現符號的不合之處,對符號進行新的解讀。甲骨文作為刻在龜甲獸骨上占卜記錄的卜辭,所記載的是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測。但按時間進行測算,夏朝出現在商代之前,人們不會占卜推測已經發生的事情,所以夏字里的人形符號未必是指夏人。不僅如此,南陽巨石猴的造型與甲骨文夏字人形造型很相似,其都是突出頭、手、足等結構的側面造型,在推崇圖騰崇拜的商代,“夏”字這一造型也可能是人們對于自然、對于巨石崇拜的精神符號[9]。由此,由猴造型的能指來所指“夏”朝,這兩者之間發生明顯的闡釋失諧。細節的失諧會影響到整體的符號解讀,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也正是因為這種失諧才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視角,產生了新的解讀。
在殷商先民的認知中,甲骨文字符號不僅具有認知世界的闡釋功能,還具有某種神秘的溝通天人的實踐功能,這種功能往往以占卜為媒介進行。在“殷人尊神”的時代,出于對自然的敬畏,無論事情的大小均靠占卜進行,在人為的干預下,鉆鑿火燒之后產生的自然又不規則的紋路因其走向和裂紋之間的夾角不同,貫穿刻在龜甲上作為卜辭的甲骨文字的路線不同,在特定的語境下符號的所指具有了深層的含義。對甲骨文進行符號解讀,從表層所指到深層所指,這其中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從學術上來看,圖像是客觀世界在人的主觀能動性下產生的對世界的反映,其視覺語言形成的過程就是客觀世界被符號化的過程,這意味著人們理解與看待世界的角度煥然一新[10]。
5 結語
以夏、秋為例,對甲骨文季節性文字進行探討,將甲骨文字形所蘊含的審美意蘊與其表層和深層所傳達的觀念意義牢牢聯系在一起,以此對古文字進行符號化解讀,為人們認識甲骨文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甲骨文無論是作為研究歷史發展脈絡的文字載體,還是作為視覺設計中溝通交流的文化符號,它都有著巨大的研究價值。這要求人們讓甲骨文從古籍中“活”過來,衍生出新的存在形式。從符號化的角度去重新思考甲骨文的視覺表現形式,能夠為古文字視覺表現帶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