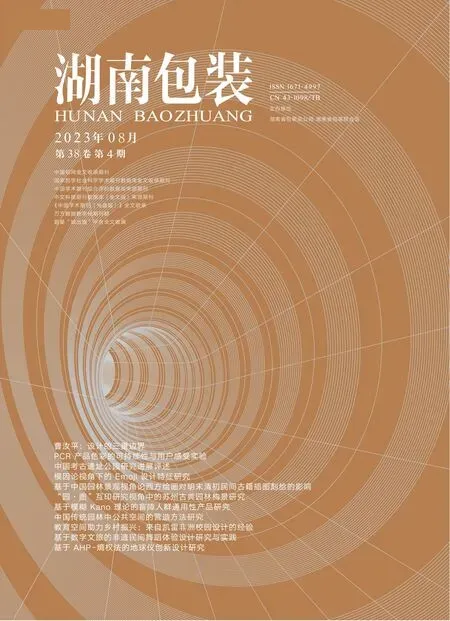中國考古遺址公園研究進展評述
唐真 管嘉敏 魏昌海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藝術設計學院,上海 201620)
1980年,西安城市總體規劃中首次明確提出“遺址公園”的概念。2006年,《“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提出建設大遺址保護展示示范園區(遺址公園)。闕維民辨析“考古遺址公園”的名稱與譯名、性質與功能、保護與規劃,至2015年還沒有發現西方學者撰寫以“考古遺址公園”為標題的文獻[1]。2015年,《塞拉萊建議》將“考古遺址公園”正式納入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官方術語并對其定義,表明這一產生于中國大遺址保護實踐的創新得到國際認可[2]。自2010年以來,國家文物局陸續公布3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并鼓勵建設省級考古遺址公園。2018年發布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發展報告》中提出新的發展格局。因此有必要對中國考古遺址公園的研究進展進行新的梳理。文章對知網數據庫中40年來中國考古遺址保護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將其研究熱點歸納為4個方面:理論發展、保護展示、規劃管理、評價研究。
1 理論發展
回顧“考古遺址公園”的發展歷程,由于中國大遺址保護在不同歷史階段提出不同的政策方針,因此在2000年前、2000—2009年、2009年至今的3個階段,由建設亂象到大遺址的整體保護與展示示范再到不同層級遺址公園的多樣格局,遺址公園在觀念與政策方面存在差別,同時又有繼承與發展(表1)。

表1 中國考古遺址公園理論發展一覽表
2 保護展示
如何既保護遺址又對遺址歷史信息正確理解與展示,真正平衡遺址公園的專業性和公眾性,是遺址公園建設的重要問題之一。目前不同學者關于展示方式分類的研究見表2。從考古專業研究到公眾考古展示的轉譯存在很大難度。考古遺址公園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遺址、遺跡、文物信息往往非常專業,但其又兼顧公眾教育、游憩等功能,因此如何跨越專業壁壘進行信息的有效傳遞?如今的公眾考古已從最初“什么是”“要不要做”的認識論階段轉向“怎樣做好”“如何推進”的實踐論階段。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三化”時代,各類互動體驗、數字技術、數字媒介極大地拓展了展示手段,譬如公眾參與性考古、文創考古盲盒、互動APP、沉浸式體驗、線上云游博物館等,然而也出現展示不足或過度的現象。
3 規劃管理
3.1 規劃建設
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建設與大遺址保護不同,要組織好遺址保護、文化展示和公園功能之間的關系。《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編制要求(試行)》涵蓋概述、資源條件與現狀分析、總體設計、專項規劃、節點設計、投資估算和規劃圖紙等要求[16]。湯倩穎[17]編制考古遺址公園可行性研究的目的、原則、基礎、主要內容和方法。劉克成等[18]系統分析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總體規劃設計。王建國[19]從歷史格局建構、城市文脈呼應、遺產價值挖掘、游覽路徑組織等方面確定大報恩寺遺址公園的空間序列與形式。張孟增[20]從愛國教育、研究保護、文化傳承、綜合管理4方面提出圓明園未來發展路徑。此外,各類技術也助力考古遺址公園規劃設計。通過 GIS 技術構建與考古遺址公園現實環境對應的三維虛擬地理信息空間,并對現實地理環境進行模擬、分析及虛擬場景飛行[21]。郭湧等[22]運用Autodesk Civil 3D和InfraWorks等軟件構建秦始皇陵園數字地面模型,探索風景園林信息模型(LIM)構建技術路徑。
公園若要滿足新時代公眾需求,就要有完善的服務設施和優美的生態環境,因此考古遺址公園的環境建設也必不可少。邱建等[23]、劉卓君等[24]針對不同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闡釋基于遺址屬性的公園植物配置及生態修復的原則與策略。李勤等[25]探討考古遺址公園中水環境建設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表現模式。考古遺址公園的植物配置及生態修復既要符合遺址本體保護要求,又要營造歷史氛圍,融合遺址文化屬性,還要滿足公眾科普、文化展示、旅游游憩需求。
3.2 管理運營
相對于規劃設計的研究,管理運營的研究略顯薄弱,涉及公眾參與、管理體制、經濟社會、旅游文化產業等方面。漢陽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采用開放式考古發掘模式,開辦各種培訓活動,讓公眾參與模擬考古發掘工作[26]。馬建昌等[27]建議大明宮考古遺址公園成立大遺址保護的非政府組織、社會資金多元化投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支持志愿服務、部分區域社會化管理運營。李昊[28]以京張遺址公園概念方案征集的微信公眾參與評選環節為例,引發如何跨越專業學術壁壘,更加通俗有效地向公眾傳遞方案,激發公眾參與到公共話題討論中的思考。李文靜[29]建議建立國家補償機制,設立殷墟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特區及管委會來統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李賓等[30]提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旅游開發中政府規制方式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優化路徑。王刃馀等[31]分析截至2017年底兩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支出結構差異的成因,并針對第二批公園支出阻滯與發展狀況提出調整建議。
4 評價研究
關于考古遺址公園定量評價的研究逐年增多,涉及客體和主體評價。客體評價指遺址本身的評價,包括遺址價值評價體系、遺址保護規劃建設實施評價(表3),此類評價仍以大遺址保護為主;主體評價包括游客和遺址保護區居民2個群體的感知評價(表4),此類評價以游客感知評價為主,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感知評價較少甚至空白。

表3 不同學者關于遺址本身(客體)評價指標

表4 不同學者關于游客/居民感知(主體)評價指標
5 研究評述與展望
自2009年以來,雖然中國考古遺址公園的遺址本體保存現狀顯著改善,學術研究百家爭鳴,公園吸引力和文化普及增強,但是還存在很大提升空間,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5.1 理論研究方面
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目前中國考古遺址公園多數為定性研究,且多集中于具體實踐案例的規劃設計、展示設計。近幾年出現保護利用、文旅融合、城市更新、考古工作等方面研究。但是考古遺址公園的理論體系、分類體系、城市更新協同發展、文化旅游產業、經濟社會、城鄉人居環境等方面的理論廣度和深度還相對薄弱或欠缺。考古遺址公園的理論研究涉及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藝術學、地理學、建筑學、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學、環境學、管理學等眾多學科,因而應探索多學科、多層次、系統化的理論研究體系,交叉協同研究,拓寬理論研究渠道,改變以歷史、文化、建筑、規劃、旅游等為理論主導的現狀。
考古遺址公園的綜合評價研究。科學評價近年逐漸增多,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2類:一類基于遺址本身的評價,集中于大遺址價值評價指標體系和大遺址保護規劃建設實施評價的研究;另一類基于游客感知的評價,主要對象是考古遺址公園游客和遺址保護區居民。考古遺址公園的功能定位、價值評價體系、綜合理論體系等研究還需不斷完善,目前學界和國家尚未有統一的評價標準。此外,科學全面的評價不僅僅依托于健全的評價體系或者先進的評價理念,必須對客體(遺址公園)、主體(游客、居民、管理者、規劃師、考古專家等)以及機制(管理機制、運營機制等)進行評價,多學科、多領域參與,創新評價方法,以期提供更為契合、準確的綜合評價體系。
5.2 展示利用方面
考古遺址公園的發展促使遺址展示技術日漸先進,展示手段日漸豐富,卻也出現展示不足與展示過度的問題。或由于資金投入不足、考古研究不足、配套設施和基礎設施不完善導致展示手段單一、可視性差、價值闡釋不到位;或由于為了吸引公眾視線,展示方式琳瑯滿目,遺址價值缺失。由此需要管理者、規劃師、建筑師、風景園林師、考古工作者、公眾共同參與,一方面,明晰遺址公園功能定位,科學論證,分層、分級、分類別,選取契合的展示技術和手段,科學、適度展示,正確處理展示信息的專業性與公眾認知的易懂性、文化科普的準確性三者之間的關系。盡管數字化技術潛力巨大,可以讓遺址公園依托文創產品、新媒體、數字技術等途徑走向“大千世界”[45],但也必須在充分理解遺址價值內涵的基礎上,利用新技術加深遺址信息的公眾理解與認同。另一方面,公眾考古實踐中也需要了解公眾興趣與需求,才能有的放矢地進行考古科普,同時還需要加強公眾考古項目的實施成效評估,包括管理運營、社會效益等方面,根據評估結果有針對性改進。
5.3 規劃管理方面
規劃建設與考古工作動態協同。考古工作具有長期性、不確定性,考古工作通常持續幾十年可能只發掘了冰山一角。目前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多數需要短期建設完成并投入使用,有的遺址公園甚至出現現代建筑、構筑物占壓考古勘探工作范圍的現象。考古工作是遺址保護展示的科學依據,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遺址公園的展示信息也會隨著遺址信息的發布而不斷更新,更加準確、完善、系統。因此,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建設是一個動態過程,需要規劃師與考古工作者密切交流,制定一個較為科學系統的分期規劃設計,為考古工作留白,同時規劃設計的編制成果也需要根據考古成果進行修編,及時更新糾偏。
規劃建設與旅游體驗、文化認同。目前有少量關于旅游體驗、游憩功能、使用后評價的研究。考古遺址公園最終要傳遞內在的歷史文化,但現存研究并不能體現出文化認同效應。規劃建設從整體格局、原真性展示、整體性保護、展示解說、活動體驗、文創產品、建筑營造、景觀營造、配套設施到生態環境等都應讓游客產生共鳴并認同其文化,產生文化自信,目前考古遺址公園與文化認同關聯的研究較少。
精準化的科學管理。目前逐漸形成覆蓋可行性研究、規劃、立項、創建、評定、開放運行、評估檢查全過程的管理體系[8];不同類型的考古遺址公園主導功能不同,精準功能定位,以便更好地指導規劃建設;學界對考古遺址公園政府規制的相關研究不足,學界也未達成共識,今后可以多層次、交叉式研究,借助大數據監控等先進科技手段探究問題根源,多方協作制定適合的管理運營機制;同時加強公眾參與度,提高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實現考古遺址公園保護利用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