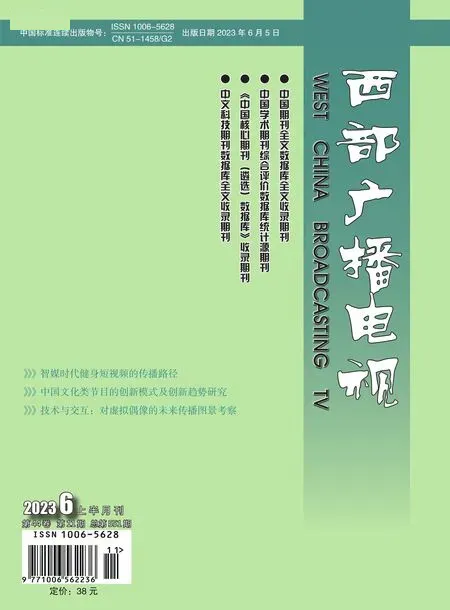《羅生門》:論經典電影之美
趙智利 張 微
(作者單位:1.貴州財經大學外語學院;2.貴州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
《羅生門》被譽為“有史以來最有價值的10部影片”之一。如今跨越大半個世紀,該作品仍是世界影視藝術中的經典之作。羅生門,原指日本古代京都的城門,后借指人間與地獄之界門,意為事實與假象之別。在影片中指事件當事人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陳述案件,所有涉案人各執一詞,使案件在真假證詞中撲朔迷離。它改編自芥川龍之介192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竹林中》,故事簡單卻富含哲理。該小說以7個人的證言,勾勒出一樁發生在竹林間的懸案。這7個人分別是承認殺害武弘的多襄丸、武弘的鬼魂、逃跑的真砂、發現武士金澤武弘尸體的樵夫、曾見過武弘與其妻子真砂的云游僧、無意中抓住大盜多襄丸的捕快、局外人乞丐。前4人分別從自己的角度陳述同一時間/地點發生的案件,致使該案件出現四個版本:其一,多襄丸:強占真砂后應真砂要求,手刃武弘。其二,真砂:丟失貞潔后羞愧不已,隨即暈厥不明丈夫死因。其三,武弘:因多襄丸的羞辱和妻子的背叛而自殺。其四,樵夫:真砂失去貞潔后,唆使武弘與多襄丸決斗,真砂趁亂逃跑。小說結局是開放式的,未揭開孰真孰假的謎團,只留給觀眾無盡遐想。乞丐,是原小說中沒有的人物,導演借該人物道盡了當事人和證人的未盡之言,讓人性的自私與邪惡暴露無遺。
自我陳述是本片的主要敘事方式。該方式是個人思想或價值觀的外在表達形式,具有明顯的主觀性。主人公們都為各自利益辯護:多襄丸認為世道不公,是女人誘使其犯罪;真砂認為多襄丸兇惡,自己無法反抗;武弘認為士可殺不可辱,自殺是因其被辱。一件簡單的搶劫殺人案,因多人趨利性的主觀陳述,逐漸掩蓋客觀事實。導演表面上展示了各人迥異的價值觀和以惡制惡的人間地獄,實際上表達了一個深層哲理:人性復雜,亙古不變,但善惡終有報,若為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終將自食惡果。
關于《羅生門》,前期研究大致如下:一是從哲學視角解讀,如《羅生門的哲學解讀》,作者邱紫華、陳欣認為羅生門的哲學與佛教哲學類似;二是從文化視角解讀,如《黑澤明電影〈羅生門〉中的“恥”文化內涵解讀》,作者沈肖燕認為人物的話語行為符合日本的恥感文化;三是從敘事視角解讀,如《情節模式、循環講述與相互說理——論電影〈羅生門〉的敘事藝術》,作者張鑫認為電影以循環講述的方式表達了導演對太平盛世的期盼與“拯救始于殘缺”的哲理。本文將區別前期研究,從電影敘事學理論與文學話語理論的角度,對電影主題、敘事方式、敘事人物、敘事空間進行審美分析,試究其經典的緣由。
1 經典主題審美
電影的真實性和紀實性是歐洲長鏡頭理論的核心觀點。該理論的倡導人巴贊認為,攝影藝術最重要的功能是再現現實,給時間涂上防腐劑,真實地還原過去某個時間人的生活,使歷史重演,歷久彌新,超過有限的時間進入永恒的真理之境[1]。區別于蘇聯的蒙太奇理論,歐洲長鏡頭理論少用特寫、近景、切割組合時空表達或創造攝影內容,而是慣用長鏡頭、全景鏡頭捕捉攝影內容,將內容的存在意義放在所指意義之前,即長鏡頭理論強調存在的表現(隨機性/偶然性),非表現的存在(刻意性/必然性)。
《羅生門》與巴贊的長鏡頭理論的核心觀念不謀而合。導演如一位理性睿智的哲人,在他的鏡頭中沒有摻雜個人情感,而是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真實地向觀眾展示觀察的內容。影片中沒有使用復雜的剪輯手法,也沒有營造夸張的故事情節,除了在當事人回憶案件經過時使用近景特寫、突出人物的情緒變化外,多用長鏡頭、全鏡頭、固定鏡頭、深焦鏡頭,客觀地展示環境氣氛、人物的動作、人物之間的關系、事件的前因后果,平實自然且極具韻味地從多個角度“還原”了一個過去的真相。這個“曾經的真相”與觀眾想象結合,衍生出超越時間的“永恒真理”:自作孽不可活,行善積德乃常理。
關于真實性和哲理性在經典電影中的重要性,國內學者周清平在將中國大片《英雄》與《羅生門》比較時指出:“亞里士多德曾經認為詩比歷史真實,因為詩能夠反映人的精神內核。中國大片沒有展示人類的精神品質,也沒有揭示生存哲理。《英雄》模仿《羅生門》的敘事方式,從四個角度進行敘事,但是真實性的缺失讓精美的畫面成為漂浮的能指,美麗卻空洞。”[2]67由此可見,《羅生門》主題的真實性與哲理性是其成為經典的原因之一。
2 敘事方式審美
《羅生門》敘事審美以電影敘事學為理論基礎。該理論是文學理論中結構主義敘事學在電影領域中的應用。周清平認為,熱內特的敘事理論中有關能指(文本)、所指(故事)、敘述(行為)、敘事距離(細節特寫與觀眾距離)、敘事人物(行為主體)、敘事視角(內、外、零視角)、敘事方式,為電影敘事,特別對經典電影敘事,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參考。把敘事理論放在電影中,敘事角度體現在三個方面,即視點、視域、視角,其中視點是人物的位置與出場,視域是景別和景深,視角是機位角度[2]12-13。
電影敘事與文本敘事相似,文本離被描寫的事件越近,細節越多,敘事方式越直接,與讀者的距離就越近,反之越遠;在電影中,鏡頭越近,特寫越多,與觀眾的觀看距離越近,觀看體驗感也會越近,反之越遠。但是,鏡頭敘事比文字敘事更形象直觀,與觀眾的距離更近一些,因為鏡頭敘事時,配合攝像機推、拉、搖、移、升、降的動態運動,可視可聽的畫面和聲音(情、景、人物、臺詞、音樂、裝容、道具),不僅可以直接為觀眾帶來視覺和聽覺上的享受,而且能夠交代故事發生的氛圍環境、人物情感表達和心理變化,這更能讓觀眾感同身受。也正是鏡頭敘事(能指)太過于具體直觀,與觀眾的距離太近,故事(所指)也變得具體單一,觀眾的想象力被極大壓縮。因此,馬爾克斯一直未同意將《百年孤獨》搬上大熒幕,他認為電影不是萬能的,在文學中讀者可以走得更遠,并且也能獲得視覺與聽覺的上享受[3]。
在《羅生門》中,導演很好地把握了與觀眾的距離,鏡頭在實虛之間自由轉換,每次從現實轉向回憶時,鏡頭會推進,從全鏡頭慢慢轉為對回憶人物的近景或特寫鏡頭,好似將觀眾帶入回憶人的想象中。從回憶轉為現實的時候,鏡頭又慢慢地從局部拉回整體,變成全鏡頭或長鏡頭,讓觀眾從故事中脫離出來,回到局外人的角色,等待后續劇情揭秘。這一距離的把握,源自導演棄用上帝視角,把自己放在與觀眾相同的位置,反復聆聽各個人物陳述,以此技巧拓展故事的可能性與想象空間,且極富哲理的主題給觀眾傳達了多視角看問題的方式:不僅需要有懷疑和批判的眼光,而且要透過現象看人性本質,真相往往不在“此處”,而在“他處”。
結構主義的敘事方式有倒敘、插敘、補敘、交錯、套層、圓周、平行、多角度、復敘、閃回、閃前等。《羅生門》則采用同主題多視角平行復敘、倒敘、插敘等敘事手法,將四個故事版本交叉剪輯安插在樵夫、云游僧和乞丐的閑談中,以此整合電影的實虛片段,增強故事的真實性和戲劇性。整個電影的敘事線可概括為,破廟閑談引出開端(現實)—公堂上多襄丸回憶版本1(想象)—破廟閑談故事轉折(現實)—公堂上武弘妻子回憶版本2(想象)—破廟閑談故事轉折(現實)—公堂上武弘鬼魂回憶版本3(想象)—破廟閑談道出版本4(現實)。整個敘事線像一個被切割成四個部分的圓,最初看不清它的形狀,而劇情的推進和每次真假參半的回憶,一點點補全了它的全貌,也慢慢地讓觀眾理順了故事的邏輯。黑灰色是整個影片的基調,表達了導演對人性的貪婪、丑惡與自私深深的絕望和對戰爭年代的混亂、惡行與不公無聲的批判。
另外,從文學角度仔細分析電影的敘事方式特點,可知它與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和狂歡話語有很大相似之處。四個版本“獨白式”回憶似復調小說結構,對同一案件,每個參與者發表各自的看法。這些看法各異的聲音像音樂里面的復調,相融交錯卻又彼此獨立。導演作為局外人,不描述、不講述主人公,亦不參與他們的對話,僅是看著他們“直抒己見”地陳情,即使在陳情過程中主人公們自我美化、弄虛作假也不介入。事實真相很自然地在他們對話中流露出來。見證人們在破廟對話中揭露事實情節又符合狂歡話語的特點,不同身份/階級聚集在一起,隨意談論公堂上的案件,在輕松平等的環境中揭露公堂上未知的實情,以此嘲諷亂世中的教條、官腔與等級,整個故事對比鮮明、反轉精彩。
3 敘事人物審美
人物是電影的核心,人物的生活、經歷、思想是電影的主題,人物的命運變化和行為動機是電影的情節,為人物的行為表現或情感表現服務的是電影的視聽語言。人物的身體話語是可見的能指,精神話語是可感的所指。人是個體人,也是社會人、歷史人和文化人。通過個體人物的表現,能微觀透視人物的性格、習慣、秉性的好壞,也能宏觀透視某個時期社會的風貌、習俗、制度、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及思維方式,甚至發現歷史的痕跡與邏輯,從而感悟社會的真理、歷史的真相和人生的真諦[2]109。
每個人物在作品中有特定作用。如巴赫金在分析古典小說中騙子、小丑和傻瓜形象時,指出這三類人物因其完全公開化的生活和毫不掩飾的話語,不僅可作為觀察者或偷窺者公開某人私人生活/秘密,而且可作為舉報人揭露社會陋習和禮教虛偽[4]322。同樣,《羅生門》中的7個有聲的主配角與兩個無聲的工具人(大眾看客與嬰兒),作為電影的核心主體,不僅推動著故事動態發展,而且通過身份、性格、外貌、行為、話語建構電影本文之外的內涵與深意,讓多襄丸見色起意強搶有夫之婦導致丈夫死亡的普通民間故事題材在偶然的共時性與異時性中成為傳奇。
傳奇故事序列中的頭一個環節不是由機遇決定的,而是主人公的性格決定的[4]310。第一當事人——多襄丸,偶遇武弘夫婦,不是故事發展的決定因素,而是多襄丸喜占他人心愛之物的欲望。從見色起意、強占順意、求愛失意、殺人轉意到回歸本意,不過是多襄丸一念之間的情緒變化,可歸之為“意念的假象”,而其貪財好色、喜占他物的本性才是真相。第二當事人——真砂,表面上堅貞不屈,溫柔善良,其實利己狠毒。她教唆多襄丸與武弘決斗,自己則趁亂先逃。真砂從溫順、反抗、接受、暴怒、挑釁、逃跑,再回到溫順可憐、訴說苦楚,這一系列的假象變化不難看出是為了掩飾欲求不滿、虛情假意的本性。第三當事人——武弘,以鬼魂的形式出場,代表日本社會上層階級的男性,但他愛妻護妻、紳士禮貌、武術高強是假象,因此他受盡侮辱、斗武死亡成為必然。而他死后變成鬼魂也要證明自己是自殺,以此保存最后的榮耀。
見證人的作用是揭露和表現私人生活的所有階級和等級[4]322。在這個故事中,第一見證人——云游僧,為傳統觀念中公正無私的見證人,不參與人物斗爭,是就事論事的局外人,其作用是揭露武弘夫妻的私人生活。他所見的是歡聲笑語的和睦夫妻,而這反而為后續夫妻反目作了鋪墊。第二見證人——樵夫,為傳統觀念中純樸誠實、遠離硝煙的局外人,其作用是揭露人性和推動劇情反轉。他目睹事情經過,順走兇器,但為不參與其中、掩飾貪欲,只遠遠地做了一個偷窺者和報案人。
聽眾一,捕快,謊稱多襄丸未受重傷,只因自己勇敢才將其擒獲。聽眾二,無所事事的乞丐,偶然聽完全過程,偵破樵夫的偷盜行為。聽眾三,世間大眾看客,好奇、猜測、議論、評判,甚至跟蹤偵查已成“事實”或“真相”的過去,讓與自己無關的他人私事變成自己的公共談資。
最后,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出現在武弘妻子曾經躲藏的地方,間接地將故事的必然性又轉向了偶然性。3個當事人,兩個見證人、3個聽眾和1個一無所知的棄嬰,涵蓋了社會各層人物。他們相遇始于偶然事件,后發生一系列事件,如真砂被搶、武弘被殺、多襄丸被抓、樵夫盜竊、乞丐揭秘、云游僧感嘆,但其實這些都是主體因其本性所致的必然事件。這些人物展示的占有欲、色欲、貪欲、私欲、偷窺欲均是佛教中的罪惡之源。為了掩蓋欲望,他們編織謊言,顧左右而言他,最終也未如愿以償。導演用放縱欲望的悲劇反向勸誡世人為仁愛善,即使身處亂世,求而不得,仍須堅守正道,懷揣光明。
4 敘事空間審美
文學作品空間分故事空間和話語空間。前者是靜態空間,是人物行為或事情發生的地方,一般用于展示人物或事物的關系,或為人物的動機、事物的發生作鋪墊;后者是動態空間,是人物行動或事情發展的地方,一般用于展示人物性格和情緒,或推動事情的發展[5]。《羅生門》按人物敘述順序出現了四個空間:揭曉真相的閑人場所——破廟(靜態空間),案件的審判地——公堂(動態空間),死亡案件的事發地——森林(動態空間),多襄丸中毒被抓的第二現場——河邊(靜態空間)。盡管整個故事具備普通懸疑劇的基本配置——原告、被告、證人、案發現場、公堂法庭,但是案件的真相并未按常理出現在公堂上,亦未出現代表正義的法官,反由破廟中的乞丐取而代之。一方面,暗示亂世的黑暗和正義的缺失;另一方面,表達了導演對和平盛世的渴望。
破廟,即代表神明或信仰隕落的地方。電影中是公共無人區、底層人民的聚集地,這里沒有權力壓迫、等級制度、信仰約束,只有民眾隨心所欲的閑談。廣場等公共空間是展示和形成人及生活的自傳式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分公共歷史性質、國家性質和私人性質[4]326。困惑善良的云游僧、貪財老實的樵夫、好奇自私的乞丐,都沒有故意夸大或縮小私人或公共自我意識,最自然的真實之我在此呈現。暴雨,既是他們偶遇的契機,又是見證人的情緒表征,也為后續的回憶增添沉重、冰冷、恐懼的色調。
公堂,權力和公正的象征。在電影中是公共權威區,是犯人、嫌疑人、受害人的聚集地。在這里,“我”不再是“我”,而是別人口中認為的“我”。公共化的自我意識顯形,為掩飾自己的罪行或博得他人的好感,“我”會不自主地展示最好的社會之我。因此,在這里,多襄丸展示武藝高強,妻子展示無辜可憐,武弘展示崇高的榮辱觀,捕快展示勇敢無畏,云游僧和樵夫展示震驚與誠實。
河邊,日常生活的公共體驗區,用于平民身份但行蹤不定、深不可測的強盜多襄丸。
森林,象征神秘奇遇,是公共隱秘區。在這里,人物行為不受社會倫理制約,不用掩藏私欲,本能之我展露無遺。
隨著故事情節發展和空間轉換,人物意識在自我、他我、本我中分裂,行為話語似真亦似假,打破同一案件的統一性和完整性。9個人物,代表9種社會/個人屬性,以及對同一件事的9種人物視角/個人意識形態,讓觀眾在求真求知的道路上越走越模糊,產生萬物皆空、唯欲是真的錯覺。
5 結語
電影主題之美在于哲理性和真實性,與倡導存在主義的長鏡頭理念不謀而合。敘事方式之美在于導演對鏡頭的良好把握。導演不參與主人公們的對話或“復調式”的獨白,而是看著他們直抒己見地發表觀點或陳情,這些自我意識的表達,相融交錯卻又彼此獨立,在實虛之間自由轉換,讓整個敘事線自然流暢又充滿懸念。敘事人物和敘事空間之美在于不同場合中真實人性本欲的表達。9個人物、9種身份、9種思想話語,在私人與公共空間中互相拉鋸,把真假難辨之美表現至極致,把人性的矛盾也表現至極致。最后,見證人在破廟“毫無保留”的狂歡式對話,揭露了公堂上未知的實情,讓人不禁感嘆亂世的黑暗,渴望盛世的正義,也是電影的點睛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