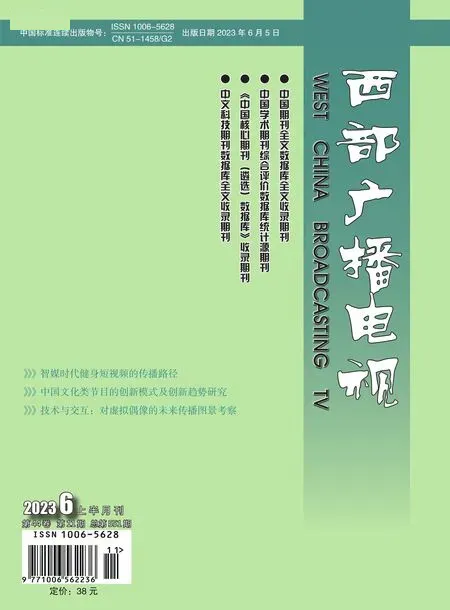德勒茲“時間-影像”視域下《藍白紅三部曲》影像敘事分析
顏 僮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享有世界級聲譽的法國電影導演耶斯洛夫斯基,其影片具有強烈的紀實風格和哲理意味,偏向于探討人性與生命的終極價值,表現了他對生活、對社會的審視。而他對鏡頭語言的精妙設計和對主題內涵的深刻表達,又使他的電影實現了紀實性與表現性的統一,被尊稱為“繼伯格曼、費里尼之后的作者電影傳人”。他的《藍白紅三部曲》中所運用的影像敘事方式,如攝影、色彩、構圖、剪切等,通常都潛藏著深刻的意蘊,令人深思。“時間-影像”的哲學理論由后現代法國電影思想家吉爾·德勒茲在其著作《電影2:時間-影像》中提出。對德勒茲而言,生命即綿延的時間,而電影的獨特價值就在于使生命或時間得以影像化。德勒茲借助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與法國新浪潮電影,將綿延時間的流逝予以視覺化,從而形成時間的直接影像,展現生命的“純粹層面”,即“時間-影像”[1],觀者在“純視聽影像”中的回憶、知覺和思維中,感悟生命的潛在意義。本文基于德勒茲的“時間-影像”理論,對《藍白紅三部曲》的影像敘事進行解讀,分析其敘事結構、視聽語言,在電影作者的筆觸里探究其體現出的哲學隱喻。
1 “時間-影像”下《藍白紅三部曲》的敘事手法
德勒茲基于“時間-影像”理論提出了純視聽影像概念。所謂純視聽模式,意味著一種作為生命體的影像,處在純聲光情境中,有生命的影像在承受著某種超越自身應對能力之極限的強悍“沖擊”,導致它無法做出任何“行動”,或者說任何“行動”都無濟于事。此時此刻,有生命的影像便是所謂純視聽影像[2]。就如同《偷自行車的人》中的主人公,面對現實的沖擊無法給予回應,最終成為一個純粹的觀看者和聽聞者。《藍白紅三部曲》雖然各自代表著不同的主題,但依舊透露著人在命運下的掙扎與面對現實的無力。《藍》中女主角朱莉自由卻悲苦,對所失去的一切極為懷念,卻也有無法擺脫的沉郁;《白》作為戲劇沖突最強烈的一部,以黑色幽默的復仇揭開人與人之間利益、情感的糾纏,一切作為都是為了求而不得的愛與平等;而《紅》雖然象征著博愛,但老法官與女主角瓦倫丁的命運交集中,依然潛藏著人對于觀念與人性的沖擊之無力感。在影像中,基耶斯洛夫斯基通過非線性的敘事結構,以及獨特的視聽語言,體現人在命運面前的茫然和掙扎。
1.1 非線性敘事結構
基耶斯洛夫斯基擅長使用非線性的敘事結構,打破“運動-影像”所遵從的邏輯因果鏈條,使得觀眾在觀看時受到阻滯,如影片《藍》中一開始看似是幾個無意義的單一鏡頭的分切,夜間車輛的光影、車后座的小女孩、車輛剎車零件滴水的特寫鏡頭、下車伸懶腰的男人及路邊玩滑板的男孩等,但都為之后的敘事埋下伏筆:車輛剎車故障引發了車禍,小女孩和男人在車禍中喪生,目睹事故的男孩后來將撿到的項鏈還給朱莉。同樣的,朱莉在公寓里發現老鼠,又偶然發現房屋中介人的臉上有貓爪印,之后朱莉抱著貓走進公寓,將貓放進有老鼠的倉庫里,這一敘事鏈條間又穿插著其他事件,導演對于事件發生順序的設計,凸顯出其并不強調事件的因果聯系,而是用細節的暗示效果來推動事件。影片《白》中也有著同樣的敘事手法,在影片開始,行李傳送帶上有一個破洞的巨大皮箱,讓人摸不著頭腦。但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卡洛躲進箱子里通過偷渡的方式回到波蘭,此時觀眾才猛然意識到影片開始的畫面意味著什么。這種非線性式的敘事方式能夠讓觀眾在觀影中得到更多的樂趣,獲得更強烈的視聽沖擊。而《紅》在整體上就采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法,影片中,女主角和年輕法官的生活一直處于平行狀態,沒有交集,直到影片最后的船難,女主角瓦倫丁才與年輕法官產生交集,而在這之中穿插了女主角與老法官的故事,年輕法官與老法官命運軌跡的極度相似,包括在年輕時遭遇戀人的背叛,在考試前偶然將書掉落,打開的那一頁就是考題,等等,這些巧合都在最后命運匯集的時刻讓人產生最深刻的思考:生命的存在問題。
德勒茲認為,剪輯手法支配著現代電影,可以借電影的一個鏡頭、一段對白達到極致。影片《紅》與另外兩部有所區別的地方就在于,其主線敘事往往由對白推動。例如,瓦倫丁第一次來到老法官家中詢問其狗被撞傷應該如何處理,而老法官的回答并不像她想象的那般溫情,甚至透露出一股漠視生命的態度,當瓦倫丁問老法官:“如果受傷的是您的女兒,您也會是這樣的態度嗎?”老法官回復她:“小姐,我沒有女兒。”這樣的對話凸顯出了瓦倫丁善良與“博愛”的品質,以及與其相對的老法官的怪異與冷酷。隨著老法官與瓦倫丁的對話次數增加,這種對立也越發明顯,老法官的深沉與尖銳不斷刺激著瓦倫丁柔和的個性,二者也在一次次交流中逐漸達到對立與統一,他們迥異的個性在不斷交融,老法官為瓦倫丁揭開了生命的冰冷法則,而瓦倫丁也使老法官產生了對人性的一絲希望。直到影片后半部分,老法官的人生故事才逐漸鋪開,其漠然的人生態度的緣由也得以揭開,導演想要表現的主題也逐漸明晰。導演通過對話與非線性敘事結構,讓觀眾在影片角色的視角中不斷確認自身的人生價值,又瓦解著他們固有的人生觀,最后又在命運的交疊中重建對人生的態度。年輕法官奧古斯特的人生經歷與老法官驚人地相似,而這也是影片的巧妙之處,兩個故事主體延伸出相同而又不同的命運鏈條,觀眾無法分清他們到底是同一個人還是命運的輪回與極度巧合,這一手法也蘊藏著電影想要表達的深刻哲理:世界上的物體,包括人類的命運,它們彼此在不同的軌跡上運行,但是卻又相互聯系。情感是不朽的,它可能在過去的人生中留下創傷,也會在未來的某一刻得以治愈。
1.2 色彩、景物與隱喻
以小津安二郎的作品為基礎,德勒茲又論及了空鏡空間、景物與靜物。德勒茲強調:小津之“靜物”影像的獨特價值就在于讓‘純粹時間’得以呈現,“所謂靜物,就是時間”,就小津的影片看,它可以表現為花瓶、自行車等,它們構成了“時間純粹而直接的影像”,即“時間-影像”,聲光符號就此延展為“時間符號”。
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筆下,藍白紅三色本身就具有其符號價值,分別象征著“自由”“平等”“博愛”,法國的自由氣質為基耶斯洛夫斯基提供了靈感,在法國大革命之后,法國人對于自由的質疑與追求從未停止。但是生命是脆弱的,自由也難以觸及。因此,在影片《藍》中,因丈夫和女兒突然離世而重獲“自由”的女主角朱莉其實在內心從未感到自由,整部影片中她都被過去所束縛,她的生活里充斥著藍色,她凝視著的藍色水晶掛飾、她飛快嚼碎咽下的女兒留下的藍色糖果、她常常投入其中的藍色泳池等。朱莉第一次從泳池上岸時,耳邊響起丈夫創作的曲調,又跌回泳池中,象征著她想要掙脫過去的束縛而不能;第二次,一位女士在岸邊擁抱水中的朱莉,身后一群孩子跳入泳池中,池水被打破,也象征著朱莉的內心正在得到撫慰,過去的束縛正在被打破;最后一次,朱莉在潛入水中許久后,嗆著水露出水面,也象征著置之死地而后生,內心的禁錮終于得以解脫,這三次經歷意味著朱麗逐漸走出心靈枷鎖的過程。
德勒茲認為,靜物自身是蘊含內容的載體。在影片《白》中,男主角卡洛從法國帶回波蘭的女性雕像象征著他對于愛情的執念。返回途中,雕像被搶劫者摔碎,隨后又被卡洛重新黏合起來,他將帶有裂痕的雕像擺在房間里,還會在夜里親吻雕像。在這些畫面中,雕像作為一個靜物雖然沒有表情和動作,但其具備表達功能,暗含著男主角卡洛對前妻隨著時間推移發生的情感變化。在德勒茲看來,自然能夠重新連接和再造人們打碎的東西,當一個角色突然擺脫自身所處的矛盾去凝視雪山時,他其實是在試圖重構當下被擾亂的秩序。例如,在影片《紅》中,女主角瓦倫丁與老法官對話時,她不認同老法官的想法,于是望向窗外的風景,鏡頭此時展示的是瓦倫丁望向的山脈。這一景物不僅連著角色之間的信息,也讓觀眾對影片中二人的對話含義進行整理與重構。在《紅》的結尾,基耶斯洛夫斯基巧妙運用了暴風雨來臨時的幾個鏡頭:暴雨中女主角拍攝的廣告被撤下;狂風吹開門,打翻了桌上的水杯……這些都為瓦倫丁在旅途中遭遇沉船事故作了鋪墊,導演通過景物影像隱喻即將發生的事件,使得整體敘事更加完整。而通過純視聽影像的理論對導演的鏡頭語言進行解讀,可以得到更豐富的體驗和更深邃的思考,也能夠意識到大師手下無閑筆,每一場對白、每一幀畫面、每一個景物都包含著哲學意涵。
2 “回憶-影像”與閃回鏡頭
德勒茲認為,作為純視聽影像的延展方式,“回憶-影像”落實到電影中,便是“閃回鏡頭”“回憶場景”和“倒敘段落”[3]。
“回憶-影像”在《藍白紅三部曲》之《白》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白》中有著三個閃回鏡頭,第一次發生在男女主角離婚的法庭上,在卡洛說不相信他與妻子之間已經沒有愛情之后,出現了女主角多明妮身穿白色婚紗,走出教堂大門驀然回首的畫面,隨后鏡頭轉回法庭上的多明妮,法官詢問她是否還愛著卡洛。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現在影片末尾,分別作為多明妮和卡洛的回憶出現,同樣是婚禮的場面,不同的是,在多明妮的回憶里她未能走出教堂,而在卡洛的回憶里他們甜蜜地親吻。在德勒茲看來,此時的影像已經步入生命的“潛在(記憶)”領域,在這種影像的潛在層面出現時,其意義就在于拓寬了影像的時間外延,深層的實質性特征不斷地涌現,從而構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豐富性。《藍》中的回憶展現并不明顯,導演通過影像的呈現,使觀眾無時無刻感受到影片主角深陷其中的回憶,從而為觀眾帶來了更深層的情感體驗,這也是“回憶-影像”的價值所在。
3 全黑與全白銀幕
德勒茲《電影2:時間-影像》提出了“影像缺席”的概念,他指出:“影像缺席”即銀幕的全黑或全白,在當代電影中具有決定意義[4]。這種全黑或全白的新價值在于兩個影像間的空隙,此處德勒茲引用了柏格森的觀點,認為大腦在刺激與反應之間存在一段空隙,一片空白電影不可能在記錄電影過程時不反射大腦過程,簡言之,全黑或全白銀幕是所有影像的外在,加大了作為非理性分切的空隙,同時又實現了一種“潛在影像”的重新連接。
這一實驗性的影像敘事手法同樣出現在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和《白》當中。《藍》中出現了三次如戲劇舞臺上常用的“暗場”,并伴有主題音樂。這種“暗場”并非為了轉場,而是營造一種情緒,在全片中能起到一種控制節奏的作用[5]。而“時間-影像”中存在著的“愣神兒”時刻,“愣神兒”意味著“有生命的影像”處于“動情”之中,此刻它必定不會有行動,也就是說,當“有生命的影像”面對某種“沖擊”,它無法做出即時的反應,此時此刻它便是一個“純視聽影像”。影片中的“暗場”意味著片中人物朱莉處于生命中的“沖擊”時刻,主人公朱莉受到情感上的沖擊,不知作何反應,此時,主角在“愣神兒”期間,觀眾可以從突然的全黑銀幕中獲取多種情緒,包括“情動”“回憶”“思考”等,帶來了比之于演員表情更豐富、更強烈的情感體驗。而在《白》中,卡洛在用死亡將多明妮騙到波蘭,影片先呈現出全黑銀幕,繼而全白,只留下多明妮的聲音,這次的全黑與全白銀幕既使主角進入生命的潛在層面,也使觀影者在“純視聽影像”中產生了諸多思索,這種巧妙的手法也能夠帶來與直觀畫面完全不同且更加深刻、豐富的觀影體驗。
4 結語
基耶斯洛夫斯基說過:“我不拍隱喻,人們只會把它們當隱喻讀。”如果僅對《藍白紅三部曲》的視聽藝術進行欣賞,不賦予其任何意義,也依然具備極高的審美價值,透過聲、光、色這些影片中的“實在”,感受其潛在的純粹生命價值,是德勒茲通過電影影像探討哲學的意義所在。在德勒茲看來,偉大的電影作者能夠準確表述他們所做的事情,他們在表述時變成了哲學家或理論家。《藍》的自由、孤獨與解脫,《白》中壓抑的情感和扭曲的平等,《紅》意味深長的“博愛”,乃至三部影片中的種種巧合,如三位主角對待往垃圾桶里扔瓶子的老人的態度,以及船難中令人驚喜的全員幸存,都讓人們感受到基耶斯洛夫斯基通過大時代下不同的人性與抉擇所展現出的人性關懷。站在德勒茲“時間-影像”的哲學角度上來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能夠從全新的角度體味其影像所表達的深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