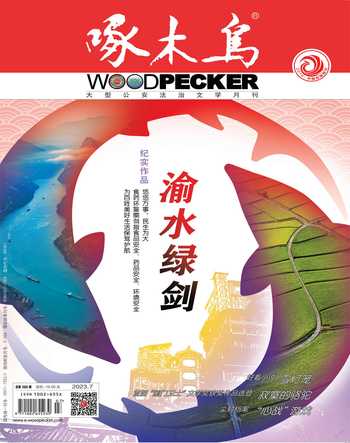雪燈籠
張軍

一
坐在拘留所木地板上,玉簪不斷回想著白天發(fā)生的事情。今兒也邪了門了,打一早開始,似乎哪兒哪兒都不對勁兒。莫非,半道撞了啥?
事情要從五天前說起——
老人羸弱的身體塌陷在扶手椅里。“媽,您是不是還覺著迷昏?”玉簪半蹲,手搭扶著母親的膝蓋不安地詢問。老人抬了下浮腫的眼皮,旋即又合上。
藥液在一次性輸液泵的塑料小壺內(nèi)露珠般生成,又露珠般滴落,懸著的藥液袋漸漸癟了下去。輸液已然到了第七天頭上。“要不,咱還是住院吧?”“不住!”老人緊著接口。玉簪抿了抿翹著白皮的嘴唇,目光踅向別處。二十三,糖瓜粘,漁陽縣醫(yī)院輸液觀察室依舊人滿為患,疾痛并不會因為春節(jié)和北京冬奧這些人間大事的來臨而踟躕自己的腳步。
此前看急診時,醫(yī)生就說這病得住院,老人當時斷然拒絕。玉簪知道,母親無非是心疼錢。醫(yī)生又說,不住也行,那就每天來醫(yī)院打點滴,至少一周。玉簪就踅出去,給家家福超市生鮮組組長莉姐打電話,問能否調(diào)換幾個晚班。這事說妥,她又打給哥哥。電話里傳來砂輪鋸咬噬鋼管發(fā)出的欻啦欻啦的聲音,哥哥的嗓門蓋過不絕于耳的噪音:“知道啦——我知道啦——你就受累吧!”
那段時間,玉簪白天跑完醫(yī)院,然后再趕到超市上晚班,直至晚上十點鐘,薩克斯曲《回家》準時在上下兩層的家家福超市悠揚地響起。玉簪最喜歡這支曲子了,倒不是她有多少文藝細胞,而是這支曲子是超市設(shè)定的下班鈴聲。
玉簪將母親托付給鄰座的一位病人家屬,對人家千恩萬謝后,離開母親去找醫(yī)生。醫(yī)生調(diào)出了老人的病歷。七年前,老人因雙側(cè)椎動脈狹窄,在北京天壇醫(yī)院放了兩個支架。現(xiàn)在CT片顯示:左側(cè)椎動脈已經(jīng)完全閉塞,右側(cè)椎動脈再度狹窄?報告上打著問號。醫(yī)生說:“小腦供血不足,所以病人走路不穩(wěn)、眩暈、嘔吐。”說完,新開了一張增強CT檢查單,向她推薦了神內(nèi)介入科的馬主任。
轉(zhuǎn)眼過了五天,也就到了年根。顧不上什么年不年的了,臘月二十八這天,玉簪緊緊挽著母親,像一個母親緊緊挽著自己的孩子,二人趕到了縣醫(yī)院。上午八點,別的診室開始叫號,唯獨神內(nèi)介入科門診不見動靜。玉簪透過鑲在專家診室門上的豎條玻璃,看到一個體格魁梧的醫(yī)生正低頭看著手機。這時,一個下巴上兜著口罩的小個子男人將診室門推開一條縫兒鉆了進去。旋即出來,向玉簪身后使勁兒招手。一個五十多歲、身穿藍色抓絨上衣的男人,和一個高顴骨的女人賊一樣鉆進了診室。
原來是個加塞的。臭不要臉!玉簪心里頓生怨氣,緊隨其身后推開半掩的門,插話道:“大夫,我們才是一號。”醫(yī)生哦了一聲,很快樓道內(nèi)響起了她母親的名字。
玉簪攙著母親進來時,加塞的還沒走,醫(yī)生的語氣已經(jīng)透出了不耐煩。按說,他們是他的關(guān)系,他對待自己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客氣些。可能這個醫(yī)生忒有本事吧,玉簪覺得,有本事的人對待別人都不耐煩。終于輪到了她們,加塞的轉(zhuǎn)由坐在一旁的醫(yī)生助理接待,那個實習女生推了下眼鏡,開始向他們介紹一款比電子血壓計大不了多少的保健儀器。玉簪照顧母親在醫(yī)生對面坐好,自己欠身坐了側(cè)座,這才與大名鼎鼎的馬主任打了照面。
“哪兒不好?”醫(yī)生接過CT片和檢查報告單。玉簪有些緊張,極力調(diào)動自己的表達能力,沒等她說完,醫(yī)生已經(jīng)將拿在手里的片子和報告單放了下來。
“嗆嗎?”他問。
“嗯?”玉簪沒聽明白。
“嗆。”石佛般的老母親開了腔。
玉簪忙補充:“嗆,嗆,吃飯嗆,喝水也嗆。”
“你們找我,想干什么呢?”
“您看,那根要堵上的血管能不能再放個支架?”她事先打聽過,支架里面再放個支架,血管就撐開了。
醫(yī)生又拿起片子看了眼:“做不了了。”
玉簪還等著他做進一步解釋,卻沒了聲音。玉簪又掏出一張光盤,小心地放在醫(yī)生面前。
“這是上次做支架手術(shù)時,天壇醫(yī)院給病人刻的資料,您再給好好看看……”她懇求。
馬主任將光盤扔還給她:“這個用不著。”
玉簪又從裝CT片的大塑料袋里掏出母親常吃的三樣藥: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倍他樂克,在桌上一字排開:“您瞧,這些藥吃得對不對?”
醫(yī)生的目光一瞟而過:“愿意吃就吃吧,吃吧,吃吧。”那敷衍的語氣給人的感覺就是:母親已經(jīng)時日不多,吃藥已屬多余。她的心忽悠往下一沉。
“真沒法兒了嗎,大夫?”
馬主任的不耐煩又浮現(xiàn)出來:“我跟你說,吃藥、放支架,做任何治療對她來說都已經(jīng)沒有效果了。”
“往后……”玉簪忐忑地看了眼母親,“往后發(fā)展,會到哪一步呢?”
“不好說,這不好說,”他右手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等血管一塌陷——也就完了。只是注意,別嗆死!”玉簪的心往下又沉了一層。她們轉(zhuǎn)身出門,玉簪將母親安頓在走廊座椅上,越咂摸醫(yī)生的話越覺得不對味兒,就返了回去。
“大夫,您是不是還有啥話跟我們家屬……”在“說”與“交代”兩個字詞之間,玉簪選擇了“說”,她覺得那個詞不吉利。
醫(yī)生翻眼看了她一眼:“沒了,都跟你說了。只是注意,別嗆死!”
“別嗆死——啥意思?”一股無名火在玉簪體內(nèi)躥騰,她說話的聲氣粗了起來。
“別嗆死就是別嗆死,還啥意思?”醫(yī)生以更粗糲的語氣回擊了她的冒犯。
那個臉盤子比一般人大一圈兒的實習女生此時停止了向病人喋喋不休地介紹和演示,茫然推了一下眼鏡,連同那兩個加塞的嚇得怔怔地望向這邊。
“你說話咋這不受聽?”不僅說話不受聽,玉簪還怨他怎么能當著病人的面說出這樣的話!他完全可以讓病人先出去,再將病人的病情向家屬交底。
他簡單粗暴地說出那句難聽的話時,玉簪緊張地盯著母親。一頂駝色軟檐帽壓著母親眉,平穩(wěn)翕動的口罩幾乎糊嚴了她的臉。雖然看不見母親的表情,可老太太明白著呢。她們抱著希望而來,可是這個不靠譜的醫(yī)生沒給她們一點兒希望。
“你會不會說話?嗯?會不會說人話!”玉簪一把拉下口罩,露出一張憤怒的臉。她跟這個知名權(quán)威拼了。
恐怕此卿從未遭受過如此無禮的質(zhì)詢,他臉色鐵青,刺啦一聲向后推開椅子站了起來,口里呼哧呼哧喘著粗氣:“醫(yī)生是人,不是神;醫(yī)生治病,不治命!你讓我治命……”他鼻子里哼哼冷笑了兩聲……
過后,玉簪在拘留所一次次回憶當時的情景,卻怎么也記不起自己在盛怒之下是如何抓住鋼木椅的椅背,如何拎舉到齊胸的高度,如何在醫(yī)生驚恐的眼神中向他丟去……
一個戴著“兩道拐”警銜的警察冷笑一聲,摸出一個小巧的優(yōu)盤擲在桌上。另一個“一杠一星”警察看著優(yōu)盤:“其實,你不交代也沒啥,那間診室有監(jiān)控錄像,它可以證明一切。”
那天,當這兩個警察夾著玉簪從凌亂的診室出來時,木然發(fā)呆的老母親臉色變得蒼白如紙,手捂著胸口從座椅上緩緩滑落……。
二
縣廣電中心編輯室。審看完樣片,縣公安局領(lǐng)導轉(zhuǎn)向在座的縣委政法委的領(lǐng)導:“王書記,是不是讓大家都說說?”
“對,大家都提提意見。”
這起案件被定性為尋釁滋事,定義為“醫(yī)鬧”。審片的陣容不凡。這檔法治類專題節(jié)目由縣委政法委牽頭,由公檢法司政法單位聯(lián)合供稿,縣廣電中心負責編輯、播出。一般的選題,審到廣電中心主管副主任這一層,只有重要選題才會有這種“三堂會審”。此事發(fā)生在疫情期間,受傷的又是為疫情做出重大犧牲奉獻的醫(yī)護人員,僅“醫(yī)鬧”就夠她喝一壺的了,再扯上這些有的沒的,此人罪莫大焉!想必領(lǐng)導重視,大抵因此。大家都避貓鼠一般不言語,冷了會兒場,局領(lǐng)導不再等:“大家都不說,我就先拋磚引玉……”
這期節(jié)目也是他向公安局通訊員烏銘直接交辦的。干宣傳這么長時間,烏銘遇到領(lǐng)導直接交辦的事情并不多見。一段時間“醫(yī)鬧”頻發(fā),社會關(guān)注度飆高。局領(lǐng)導交代任務(wù)時義憤填鷹,帶著少有的失態(tài)。
烏銘和搭檔跑辦案單位了解案情,拉采訪提綱,之后給廣電中心專題部主任葉子打電話匯報選題。葉子乍一聽不敢相信:“啥?啥?把醫(yī)院給砸了?還是個女的?太邪乎了吧!做,做,這個選題一定要做!”又說,“到醫(yī)院采訪你找王薇配合,我先給你過個話兒。”
玉簪被行政拘留十五天。節(jié)目的采編工作要在十天之內(nèi)完成,過期就掉了熱度,烏銘帶著搭檔以最快的速度將這個節(jié)目搶了出來。報審的樣片用畫外音、對目擊者的采訪和診室監(jiān)控錄像還原了事發(fā)經(jīng)過;醫(yī)院保衛(wèi)科、一名醫(yī)院副院長和隨機采訪的三名就診患者對“醫(yī)鬧”問題進行了評論;最后,主持人對案件綜合點評。
局領(lǐng)導的意見是:“為啥不讓她說話?讓她說話,向當事醫(yī)生和院方公開道歉!”
“是呀,道了歉,節(jié)目才有力度嘛!”政法委領(lǐng)導說著,看向廣電中心主任,主任看向副主任,副主任看向葉子,葉子點頭說“是的”。一干人又將目光落到烏銘身上。烏銘心里犯難,他打量那姑娘不是一般的死性,可是誰敢對領(lǐng)導的指示打駁回呢。
烏銘不得不帶著搭檔返工。
三
見玉簪第二面時,未曾開言,玉簪就顫聲問道:“我讓你們打聽的事兒咋樣了?我媽,她到底咋樣了?”
“哦,聽說她老人家在醫(yī)院輸了點兒液后,就回家了……”烏銘不敢看這個姑娘的眼睛。
作為女兒,玉簪洞悉母親的心思:只要兒女在身邊,就是死,她也不會害怕。可是——唉!此時的玉簪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她為自己的魯莽后悔不迭。
烏銘的眼神像做賊,因為他說的是實情,也不是實情——他了解到,事發(fā)當時老人情緒波動,當即引發(fā)大面積腦梗。玉簪的哥嫂聞訊趕來,要求住院治療。此次發(fā)病兇險,醫(yī)生根據(jù)病情向家屬交代:“住院行,不過也就是挨日子的事兒,你們家屬還是要早有準備。”母親氣若游絲,兒子俯耳諦聽,聽得卻是“家……走……”二字。母親的話頓時打下這漢子兩串淚來:“好!媽,咱們——家走!家走!”原來,老人以前跟兒女嘮叨過,萬萬不能死在外頭。
老人躺在屋炕上,用眼在人堆里找,哥嫂背身抹淚,他們知道母親在找誰……
第一次采訪,烏銘就對玉簪的家庭情況做了了解。
玉簪十歲那年,因為安全繩脫落,做架子工的父親從十二層樓高的腳手架上摔了下來。那年,她哥哥十二歲。別人都勸她母親趁年輕再走一步,但母親生怕孩子受委屈,這么多年,就一個人苦巴苦曳堅挺了過來。
烏銘記得,玉簪說到此處時突然大哭,好大一會兒情緒才平復下來。
“聽那大夫的意思,我媽沒得救了。是,我不過一個超市理貨員,我哥哥就一臭水暖工,我們是沒錢。但是,只要能治,砸鍋賣鐵也給我媽治!”玉簪眼神異常堅毅,“這些年,我媽為我們操勞,還沒享過一天福呢!你說,我們打小沒爸,要是再沒媽了,這日子還有啥奔頭?你說,還有啥奔頭……”她眼望墻角,哆嗦著嘴唇,兩道亮汪汪的淚線貼著鼻梁小溪般淌下,“他也是個人,他也有爹媽,他們大夫的血管和他們爹媽的血管也不是鋼澆鐵鑄的;事怕調(diào)個個兒,我要是跟他說——‘讓你媽別嗆死!他心里頭好受?”
盡管玉簪將采訪搞成了一場控訴,但這些話聽得烏銘頻頻點頭。
玉簪因此丟了眼下的工作無疑,但她更擔心的是,自此會有了前科。以后找工作,哪家單位會要一個有前科的人?小焦要是知道自己被拘留了,還會和自己交往下去嗎?小焦是玉簪離婚后正在交往的第三個男友——之前的都沒成——將自己裝扮得奧特曼一般,永遠在路上的一個外賣小哥。玉簪還擔心以后結(jié)婚生子,孩子也會受影響。這一點,烏銘向她解釋:“被行政拘留會留下違法記錄,但不是犯罪記錄,不屬于前科。”玉簪將信將疑,直到烏銘給她看百度搜索,她才略微安下心來。
“怎么樣?說說吧!”這次烏銘開門見山。
“說啥?你還讓我說啥?”
“咋說也不該動手呀。你違法了,知道嗎?”
“當時氣兒頂著。你問我為啥動手,我也不知道我為啥動手。”
“既然知錯,咱姿態(tài)低點兒,跟人家醫(yī)生、醫(yī)院道個歉,好吧?”
搭檔壓低右手,暗中給了烏銘一個OK的手勢,攝像機已經(jīng)開機。
“道歉?我要是違法你們就拘我,這不是已經(jīng)拘了嗎?要道歉,他先給我道;他給我道了,我再給他道。給他道歉?你們這是逮住蛤蟆還要攥出尿!”
“呃……”
玉簪脖子橫梗,有意不瞧這兩個警察,不瞧他們架在自己面前的攝像機,也無視杵到自己嘴邊、帶有臺標的話筒,她覺得自己正在遭受著一場侮辱。醫(yī)生無疑應(yīng)該得到尊敬,但是那個男人讓她惡心,就像清晨誤吸了一口二手煙般的惡心。
僵持了一會兒,搭檔沉不住氣,無奈關(guān)機。她的此種態(tài)度烏銘早已有所預料。
第一次去醫(yī)院采訪時,他讓王薇聯(lián)系了當事醫(yī)生馬主任,可是一見到這位名醫(yī),烏銘就打消了采訪他的念頭。馬主任五十多歲,卻是一副與年齡不相符的“潮男”打扮——打著發(fā)蠟的頭發(fā)向后背著,內(nèi)勾款男士發(fā)箍將頭發(fā)分成綹兒,亮著幅員遼闊的一面額頭,仿佛《聰明的一休》里的新佑衛(wèi)門走下了熒屏。
那天,烏銘二人拎著三腳架、背著打屁股的攝像包從門診樓下來時已是日西時分。路過醫(yī)院警務(wù)室,見警務(wù)室門楣電子屏上滾動著一條標語:嚴厲打擊“醫(yī)鬧”,堅決維護醫(yī)療秩序。想必這條標語不是沒有來由。
車上,搭檔問他:“醫(yī)生說的那個‘嗆,到底啥意思?”
烏銘摸出手機,稍后對著手機念道:“腦梗嗆咳原因通常有真性球麻痹或假性球麻痹等……”
“啥啥啥?”搭檔皺著眉頭打斷了他,“你還甭說,這些專業(yè)術(shù)語要跟那姑娘解釋是有點兒費勁。”
“那也別直給啊!”烏銘收了手機,“尤其當著病人面,還死死死的,當醫(yī)生的也沒個忌諱!”
想起那個武士形象,搭檔撲哧一下樂了:“新佑衛(wèi)門?甭說,還真挺像,這個新佑衛(wèi)門……也欠。”
烏銘將椅子往前拉了拉,又做了一番玉簪的工作,依舊做不通。看來,這位醫(yī)生給她傷得不輕。
四
玉簪一離開詢問室,搭檔就議論起來:“叫我說,要將這姑娘說明白,不容易!”烏銘承認。但是,必須讓她開口!這倒不是領(lǐng)導交辦的任務(wù)能不能完成的問題,僵下去,對她沒有任何好處——她還不知道母親在家挨日子呢。
二人重整旗鼓。稍后,玉簪再次被提到詢問室。
“玉簪,你想不想早點兒出去?”烏銘突然發(fā)問。
搭檔的眼睛不由地從攝像機的監(jiān)視器移開,吃驚地望向烏銘。
玉簪愣了。她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也沒想過還有這種可能。
“你可能還不知道,你的母親……”烏銘心一橫,將她母親的情況說了出來。
玉簪感覺四周墻壁都顫動起來:“啊!啊!啊!”母親生命垂危,可是她,這副毫不頂用的臭皮囊卻被囚在這里。她叉開十指,死命揪著自己的頭發(fā)大叫,又擼開袖子,狠狠咬著自己手腕。猛然間,她停止了瘋狂的舉動,醒悟過來,似乎明白了這個警察的意思。
“我說!我說!你們給我錄,快給我錄!咋說?咋說?你們告訴我,我咋說?說呀,說呀,告訴我,我應(yīng)該咋說?你們讓我咋說,我就咋說!快呀!開機了嗎?你摁沒摁開關(guān)?”她聲壯如牛,迫切地乞求,急切地呼喚……漸漸地,出口之音變得艱澀幽咽,氣若游絲。
態(tài)度沒了問題。可是,情緒極不穩(wěn)定的玉簪怎么也參與不進來。她一口又一口咽著唾沫,一次又一次舔舐著干巴的嘴唇,出口的每個字、每個詞都疙疙瘩瘩。她覺出了自己的不可救藥,在二人失望的眼神下央求:“再來一遍吧,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再說一遍!這次肯定能說好,肯定,肯定能說好!”可是,再次開機時,她的舌頭依舊打著結(jié)。搭檔無奈地看了眼烏銘,玉簪心中惴惴,望向那個坐在旁邊不動聲色的警察:“我真廢物,真沒用!這幾句話都說不好,真廢物!”她急得嗚嗚哭泣起來。
誰承想,猛然間她做出了一個超乎尋常的動作——離開了座椅,朝著攝像機鏡頭跪下一條腿,接著又并上另一條腿,叉開兩手手指杵住地,仰臉對著攝像機。她八成給了自己一個暗示,將它想象成那個她無意中得罪的人:“行了吧?這樣總歸可以吧?”接著,她鄭重其事地說道,“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她眼睛盯著攝像機幽藍發(fā)黑的瞳孔,“您大人不記小人過,別跟我一般見識,我向您認錯……”
烏銘徹底傻掉了。他屁股底下的座椅嘎吱嘎吱響了兩下,搭檔不失時機將鏡頭推成特寫,一張淚洗的臉充滿了畫面,因變焦過大,畫面微微顫動著。一股熱流沖擊上來,一下打濕了烏銘的眼圈,他知道這個姑娘這一跪是為誰。玉簪最后眼淚汪汪地央求:“求你們讓我出去,讓我看我媽最后一眼!求你們啦!求求你們!”搭檔已經(jīng)關(guān)了機器,這些贅語用不到節(jié)目里去的。
烏銘說:“我們盡力!會盡力的!”玉簪心里一暖,升騰起一股希望。
五
給局領(lǐng)導放玉簪跪地道歉那一段錄像時,憋在烏銘腦子里的想法一冒一冒就要跳將出來。稍后,他就為自己這個幼稚的想法感到了可笑。
局領(lǐng)導看完,只是微微頷了一下首,那動作稀疏寡淡,就像臥在他眼眶上柳蠶般的兩道棕黃色眉毛,似有似無。烏銘看他神情冷冷,心中詫異。又想,喜怒不形于色,此公可能已經(jīng)將此功錘煉到家了。
猶豫再三,烏銘將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這姑娘確實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也真誠進行了道歉。您看,能不能提前放她幾天?”
“哦?”局領(lǐng)導抬眼望向他,“有人托你?”
“那倒不是,想必您還不知,她媽因為此事突發(fā)腦梗,很重……可能就這幾天了……”烏銘從來沒有因為什么事求過領(lǐng)導,因此嘴唇黏滯,說得期期艾艾,“一個姑娘家家的……”
局領(lǐng)導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后面遙望著局促的烏銘。“沒人托你,你管她干啥?”又說,“你翻翻法條,看看行政拘留是怎么規(guī)定的。”這話猶如一道漫不過去的堤壩,將烏銘洶涌的心潮牢牢擋在堤內(nèi)。面對這道堤壩,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何等幼稚可笑。可是,常跑拘留所,有些事瞞不過他,有的人拘留日期過半,因為“特殊情況”就出去了。至于什么“特殊情況”,他倒是從未深究過。他們是如何辦到的呢?
烏銘兀自在說,卻見局領(lǐng)導在他說話時只管遙望著他,之后,又抹耷著眼,一聲兒不言語。在他們二人之間出現(xiàn)了短暫的沉默,一兩秒鐘,或許有三四秒鐘,也就是說話打個磕絆的空兒,烏銘卻感覺這段無聲的時間無比漫長。又有人敲門。春節(jié)這日子口兒,領(lǐng)導門前正是車馬簇簇的時候,烏銘識趣地站了起來。
廣電中心門前,烏銘剛從車里鉆出來就撞見了王薇。兩個人一上一下,隔著三步臺階。烏銘仰頭道謝,這次采訪,王薇給了他很大幫助。王薇駐足,笑靨如花:“那事兒還沒忙完?”又說,“這活兒,你們得好好伺候!”
“此話怎講?”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哇。”
“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算了——你不知道就算了。”
“哎哎,你這個人!怎么就算了,沒有你這樣的,話說一半,想憋死誰?以后需要公安局配合的事兒,你別找我!”
王薇這才逐級而下,壓低的聲音帶著神秘:“我告訴你,聽說——聽說啊,挨打的那個馬主任是你們局領(lǐng)導的小舅子。不知道有影兒沒影兒?”烏銘一愣,嘴里不自覺地吐出了一個臟字,扭身向剛熄火的車子噔噔走去。
“哎,你不去找葉子姐呀?”王薇手往上指,“我剛從她那兒出來,她在等你呢。”烏銘并不搭腔,三步兩步趕到車前,一只手搭著車門躊躇。臨了,扭身鉆進駕駛室。王薇見那車子心事重重地上了路。
六
天陰欲雪,冷氣襲人。
年后,如期釋放的玉簪走在回家的路上,濕潤的空氣讓她感到了一絲不易覺察的春天氣息。
春節(jié)剛過,年味兒呢?能感受到的年味兒只剩貼在各家門上的春聯(lián)、福字了。以前的年味兒濃得像一杯釅茶,現(xiàn)在的年味兒寡淡得像一杯剛倒?jié)M就涼下去的白開水。這點兒搶眼的紅色,如同一掛鞭炮炸響后的滿地碎屑,成為盛大春節(jié)僅存在早春時光里的余韻。
進村后,她扯嚴了口罩。玉簪腳步匆匆,不敢抬頭,她的目光觸到什么都會受傷,比路上的流浪狗還膽怯。
她想,此時自己要能變成個隱身人該有多好。一不小心,自己成了“程某某”。看來,人這一輩子沒有什么是確定的。受過拘留的玉簪覺得不僅丟了自個兒的臉,還丟了全村的臉。人一丟臉,就矮下三分。開始時,她覺得鄉(xiāng)鄰的目光針一樣扎在自己身上;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感覺是錯的。村里人一如既往的熱情,朝她說:“過年好啊,玉簪!”“玉簪,過年好!”玉簪跟他們每個人都是正月里第一次見面,是自己小心眼兒錯怪了鄉(xiāng)鄰!她不好意思地一一回應(yīng)。
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事嗎?不知道自己這些日子干什么去了嗎?她想,他們應(yīng)該知道。因為就在前天晚上,她在拘留所里看到了那期電視節(jié)目。作為一項法治教育,這檔節(jié)目每期拘留所都要組織在押人員觀看。
不過,也難怪啊——玉簪自己都沒認出電視里的自己。因為,畫面多是從側(cè)面或背面給的鏡頭,要不就是局部特寫。比如,她穿的“漁拘64號”橘紅色號衣;比如,戴在手腕上晃來晃去的手銬。唯一的一個正面鏡頭,是自己受審的畫面,在戴著口罩的臉上打著閃閃跳跳的碎格子。小格子在她臉上連成了片,說話的時候,她的頭向左動,小格子也向左動;她的頭向右動,小格子也向右動。有那么一陣,跳動的小格子都糊住了她的肩頭。
她姓程,程玉簪。播音員卻張冠李戴,從頭到尾叫她“程木木”。后來,她才明白,播音員略帶漁陽口音的普通話說的是“程某某”。難道一個人一違法,連名字都有了罪過,都不允許使用了嗎?
她的聲音又尖又細,像被人掐著嗓子,那絕不是她的聲音。這種奇怪的感覺,讓她覺得自己這個肇事者在旁觀發(fā)生在別人身上的事。里面有一個因為傳銷屢遭監(jiān)禁的“老炮兒”,這位大姐久闖江湖見多識廣,她說:“那打在臉上的小格子叫馬賽克,采訪的聲音叫同期聲,那個女的說話的聲音是經(jīng)過技術(shù)處理的。人家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咱的隱私。”
如此看來,也許鄉(xiāng)鄰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事。
當時“老炮兒”撇著嘴:“這姐們兒行!真魯!”直到不經(jīng)意瞟見玉簪的號衣。“姐們兒!”她號嘮一聲跳到玉簪面前,一張姜黃臉探到了玉簪鼻子底下,“這主兒不會就是你吧?你因為啥事進來的?啥事來著?”
玉簪納悶的是,為啥沒見到自己向那個大夫和醫(yī)院道歉的畫面呢?他們不是拍了嗎?那晚躺在鋪位上,她又將看過的節(jié)目在腦子里過了一遍,確信里面沒有她道歉的畫面。沒使上?不用,你們拍它干啥?
路過一個結(jié)著薄冰的水塘時,玉簪碰上了孫歪脖。這次,她主動招呼:“過年好啊!四叔。大年夕的,您也不歇兩天?”孫歪脖乜斜著眼,與玉簪擦肩而過時,瞟著路旁一叢光禿禿的楊樹窠子,口內(nèi)支吾,玉簪聽不清他在說啥,就在臉上堆起笑,看他搖搖晃晃踏上了笨重的自行車遠去。怪呀,這些鄉(xiāng)鄰沒一個人肯停下來與她攀談。
遠遠地,她望見了坎上自家那處破敗房屋的石墻,又看到了緊閉的院門。玉簪的心揪起來,她扯了口罩,眼睛抓著大門腳步疾走,繼而摟起羽絨服奔跑起來……邊跑,邊騰出一只手扯開脖上的圍巾,又將羽絨服拉鏈一拉到底。
玉簪泥偶般僵立在自家門前。
手里的圍巾被她擰成了一股繩,驚恐一絲一絲爬上臉頰——老榆木木門上沒貼門神,也沒貼福字,只在門框上貼著一副綠春聯(lián):人間皆春色,吾門獨素風。
她攥著圍巾的手越抓越緊,這個與眾不同的綠春聯(lián)讓她明白家里發(fā)生了什么。
“媽!媽呀——我的媽!您咋不等等我呀!”腿一軟,玉簪一屁股坐在地上。隨即,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玉簪蘇醒過來。
醒過來的玉簪在地上悶坐了半晌,這才注意到,腳下的土地已經(jīng)被火燒焦燒裂,地上殘存著半個沒燒透的紙錢、打碎的瓦盆碎塊和已經(jīng)變成炭灰的枕芯秕谷。從地皮泛起的灰燼味兒在院門前徘徊縈繞,竄進她的鼻腔。閉著門的小院內(nèi)雞撲棱著翅膀,綿羊咩咩叫著,有人從院子一頭走向另一頭,她聽出,那是嫂子的腳步聲。
玉簪手撐地面站立起來,拍掉手上的塵土,又撲打掉粘在身上的枯草棍,撿起地上的圍巾。她瞅了一眼院內(nèi)那棵高出門樓的棗樹梢頭,和樹梢下那對讓她傷心欲絕的綠春聯(lián),沒有進門,而是折轉(zhuǎn)身,往來時的路走去。走下了家門口那截長長的斜坡,走過了村街慘白的水泥路,又走上了通往縣城的黑灰的柏油路。
這個陰霾的早晨,撲面而來的涼風中不知何時夾進了星星雪糝。
七
玉簪來到公安局傳達室打問。小保安將玉簪打量了打量,問她要找的人是哪個部門的,叫啥。玉簪尷尬地連說了兩個“不知道”。小保安又打量她一番,就低頭繼續(xù)玩手機。玉簪走離大門,坐在對面路牙子上干等。她盯著大門進進出出的車輛和人員,尋思:甭看進出的人多,又都戴著口罩,只要那個警察從里面出來,我就能認出他。因為,自打他說出那句話,玉簪就在他身上存了心。
被風裹挾的雪糝打在臉上帶著一股冰涼堅硬的力道,麻癢,微痛。此時如果有面鏡子,玉簪就會看到,自己臉上的兩塊蘋果肌已經(jīng)凍得微紅發(fā)亮。她拱肩縮背,將羽絨服的連衣帽揪到頭上,用圍巾系住豎起的兩撇毛領(lǐng),又將兩只袖口對在胸前,雙手握在袖內(nèi)。不經(jīng)意間,觸到右手腕,玉簪一咧嘴,倒吸一口氣。那里殘留著手銬咬出的兩道淤青和自己咬下的兩排牙印。她又抖了一下肩,將煙灰色羽絨服的前擺在兩腿間夾緊。
一個又一個人從里面走出來,有三五成撥的,也有獨自一人的。三五成撥的說說笑笑,獨自一人的步履匆匆。有那么一陣兒,忽地出來一群人。玉簪緊張地站立起來,用眼睛抓住這個,撒開;抓住那個,又撒開。人走光了,她也回過味兒來:這是散了一個會。
沒人進出的時候,她就坐著想事兒。她從來沒有這么集中時間想過什么事情。腦子里一會兒浮現(xiàn)出母親的病容,一會兒又琢磨哥哥是如何安葬母親的。如今不讓土葬了,他給她買墓地了嗎?一會兒又想母親最后了是咋個樣子:熬了幾天幾宿?受沒受罪?給沒給她留話兒?
她又詛咒起該死的新冠疫情——哪兒哪兒都去不了!原本想趁母親還能動彈,等疫情好些的時候帶她到秦皇島看海鷗呢。可憐的母親一輩子沒出過遠門,也從沒見過真正的大海。一次,母女倆說閑話,母親說:“才不想去秦皇島呢,我想去張家口。”
玉簪問她:“去那兒干啥?齁冷的。”
母親說:“冬奧會就要開了,咱看不了冬奧會,還看不成那些漂亮的場館呀?”
玉簪說:“好,那咱就去張家口。”
想起這些憾事,她就怨恨起那個警察來。
自己咋這么倒霉,碰上的都是些什么人吶!不要以為姑奶奶是好欺負的!今兒個,她就要給這個警察一點兒顏色看看!無非再去蹲笆籬子,沒啥新新的!玉簪呼地吸了一口痰,舌頭一卷,呸在身后冬青樹干的綠葉叢中。
過午,又有人舉著傘陸續(xù)往里進,玉簪不錯眼珠地又忙亂了一陣。忙過之后,她聽見自己的肚子在叫。挨著公安局就有一家小吃店,招牌上寫著:手搟面、手工水餃、大餡包子。廚師將門口爐子上的籠屜揭開時,升騰的熱氣罩住了他的胳膊,他的臉,又罩住了他的半截身子。接著,煙氣蔓延,吞沒了在店前排隊的顧客,那些人在氤氳的蒸汽中只露著不安分的半截腿。雪色和熱氣包裹的小吃店成了仙氣裊裊的神仙洞府。
她收回目光,不敢離開半步,只怕錯過那個警察。找到他,就想質(zhì)問他一句:為啥騙人?她心中憤憤:騙子!警察里面也有騙子手!這個曾經(jīng)給過她無限希望,又讓她無比失望的人,讓她心中滋生了強烈的怨恨。他要是說話算數(shù),自己就能見到母親了。這么想著,又覺得鼻腔一陣發(fā)酸。
玉簪命令自己不往小吃店那邊瞧,眼睛聽話了,鼻子卻不聽使喚。從更遠的地方,一忽兒飄來麻辣燙的香味,一忽兒飄來過橋米線的味道,一忽兒又聞到了炒菜熗鍋的爆香味。地上攤著一張圍棋培訓班的小廣告,看著還算干凈,她撿起來撕成條,又揉搓皺了,卷成卷兒,塞住兩個鼻孔。她那肉透的蒜頭鼻子就長出了那么一小截。
在她忙碌的時候,那個接待過她的小保安透著蒙了一層霧氣的窗玻璃直往這邊瞧。不一會兒,掀開棉門簾走了出來。乍一出來,小保安冷得跳了兩跳。之后,冒雪走到她跟前,將淺藍色的口罩摘下一邊,掛在一只耳朵上,問她:“是不是來上訪的?”玉簪抬臉,眼睫毛上掛著一層薄霜,兩只單眼皮的眼睛快速眨巴著。她怯怯地望著小保安,對他笑了一下,她笑的時候鼻子一皺,鼻梁上聚出了幾道水波紋。她搖頭說:“不上訪,我在等個人。”搖頭的時候,插在左邊鼻孔里的紙管脫落下來,落在腳邊。她為自己的露怯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索性將另一個紙管也拔了,棄在地上。
小保安大概嫌她礙眼,請她離得遠一點兒。玉簪起身,走一步回一次頭,大概走出十多米遠,就站下不動了。再走,幾株塔形松柏就會遮掩住公安局的大門。玉簪眼神乞求著這個好似剛工作不久,還毛茸茸的小保安。小保安哈著手,瞅她兩眼,縮著肩膀跑了回去。
玉簪守著公安局大門,冥想苦等了一個上午。這個上午,她望穿了雙眼,也沒看到那個警察。雪中的玉簪身上已經(jīng)沒有了一點兒熱乎氣,她將自己攢成了一個球,又蹲過了一個陰冷的下午。這個立春過后撒著雪粒的下午,因陰冷而變得異常漫長。
天光比往日更早地黯淡下來,傳達室的保安換了班。一個歲數(shù)大些的保安接班后拿著水杯走出來,往松柏底下冬青叢里一下一下甩著茶根。甩到第三下的時候,他歪頭看到了馬路對過的女孩兒,那個女孩兒冰面上的寒鴉一般,似乎在那兒待了很久。保安大叔低頭往回走的時候,像想著什么事情,進門放下水杯又走了出來。
最終,玉簪也沒見到那個她想見到的警察。
玉簪帶著滿身碎雪隨保安大叔進到屋來,保安大叔先在門后尋到一個開關(guān)盒,按了一下,室內(nèi)頓時雪亮,驟亮的燈光將玉簪的眼睛刺成了兩道縫。接著,吧嗒一聲又按了一下。之后,拉開屋門抬頭望天,亮起的街燈已將小城夜空映成了說黑不黑說亮不亮的生鐵顏色。
保安大叔欠腳,從貼墻鐵皮柜的柜頂摸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她:“甭等了,你找的那個警察不在這兒了。”屋里暖氣打得很足,鋁合金門窗的隔音效果也很好,可能在路邊等的時間太久了,玉簪耳朵里依然響著車輪碾軋馬路的沙沙聲。
“啥?”玉簪捏著信封,她并非沒有聽清,只是想給自己一點兒反應(yīng)時間,“您說啥?”她一把扯下羽絨服帽子,露出了一頭散碎頭發(fā),帽子上的雪撲簌簌落了一地,濺濕了腳下一片花崗石地面。
保安大叔又重復了一遍。
玉簪摸不著頭腦:“為啥?”
“他們的事情咱也搞不懂,”保安大叔瞧著她,“聽說,把啥事給當官的辦砸了。給發(fā)配啦——看山去了!”
玉簪手里擺弄著信封,見上面用油性筆寫著自己的名字,她抖了抖,眼前驀然出現(xiàn)一道“彩虹”——從信封里掉出來的是一張閃耀著霓彩的光盤。“看山?”這個詞和這張炫目的光盤同樣令她費解,“看山是啥意思?”
“下基層唄,狗背嶺那邊的山區(qū)派出所,跟河北興隆搭界了,出門就是從山海關(guān)那邊爬過來的長城,一眼望不到頭。在這兒待久了,他們的規(guī)矩我曉得些,凡是這個時候的調(diào)動,都是過正月十五報到。這幾天人家肯定不來了。這是他留給你的,說你也許會來——還真來咧!”屋里飄滿了腳臭、汗臭和茉莉花茶裹在一起的味道,保安大叔放下抱在手里的茶杯,拍拍自己倚著的暖氣管壁,向她招手。玉簪一笑,領(lǐng)了大叔的好意,卻沒有動窩。
八
玉簪離開時已是傾城雪落,濃厚的暮色和雪帷將漁陽縣城緊緊包裹。出門的一瞬,她的眼睛驀然被幾盞大紅燈籠撞擊得生疼。頭頂之上,寬大的水泥挑檐之下,懸掛著四盞大紅燈籠。每盞燈籠大如栲栳,燈籠頂上覆蓋一層白雪,底部黃色流蘇迎風招展。一片火黃已將寒涼的雪夜洇透,迷蒙的夜色因此變得融融可親。
她昂著頭,微微張開嘴巴,這幾盞不期而遇的燈籠點燃了她的眸子,眸子里的光亮像爐膛里的火苗灼灼爍爍。它們有點兒像——像什么呢?噢,“雪容融”!她倚著一根粗壯的水磨石門柱,對著那幾抹彌散在夜幕中的紅光癡呆入定。
出了半日神,玉簪戴好口罩,揣著裝有光盤的信封離開公安局的大門,茫然不知何往。不知幾時,雪粒成了雪花,在路燈里像細雨紛紛揚揚,路燈將步道上還沒人踩過的薄雪鍍成了一片橘黃。騎電動車的無一例外向外耷拉下雙腳,腳底板擦著地面謹慎前行。一輛臟乎乎的道路作業(yè)車蹦著雙閃,車頭播灑出兩扇水面,慢吞吞從她身邊駛過。化了雪的馬路越發(fā)黑沉。
她一路低垂著頭,走在暮靄沉沉的街上,兩個粘著泥垢的鞋尖交替晃在眼前。一個影子總是在她到達一盞路燈時,從腳跟處生出;然后,超過她,越走越長,越走越淡,在她到達下一盞路燈時,消失得不知去向;緊接著,下一個影子又從腳跟處生出來……玉簪木然邁動雙腳,她的身影出現(xiàn)在一盞又一盞路燈昏黃的光暈之下,帶著長長拖痕的腳印在她身后不斷延長……
蠛蠓般的雪花在抵達大地的這段最后行程,暴露在路燈之下,它們在燈光里歡樂地狂舞。然后,飄然落足于汽車的頂棚,法梧的枝丫,綠化帶內(nèi)的黃楊、冬青和紫葉小檗的葉隙里。綿軟的春雪剛剛及地就撲散開來,眼見著洇開化散。濕潤又清冽的空氣滌人肺腑,嘶嘶雪聲聽起來像暗夜低沉翻卷的波濤。這個燕山腳下蕞爾小城沉入迷蒙混沌的雪色中,安靜得仿佛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哦,這是今年的第一場春雪嗎?
起風了。風搖著路旁法桐毛茸茸的雪枝微微顫動,一串又一串黑褐的干果被吹得歪斜了身子。玉簪仰臉,再次看到的不是四個,而是多得數(shù)不過來的“雪容融”。它們一路追過來似的,懸在自己頭上橐橐作響。她的心隨著它們瑟瑟顫動,覺得它們被風和日頭抽干的身體充盈而明亮起來,隨之,在自己腳下映出熒熒光亮。她一把扯下糊著自己整張臉的口罩,隨手一揚,任其在夜空中飄飛。清冽馨香的雪花味道砸面而來,那一瞬間,眼淚奪目而出。
那個找不見的警察為啥留給自己一張光盤?這張光盤里會是啥?她想得頭疼了也想不明白。雖然已經(jīng)三十四歲了,但這個紛繁的世界總有讓她不明白的事情。
她不會想到,母親在生命里的最后一天突然來了精神;更不會想到,那個警察跟拍了母親彌留在世的最后時光,用她母親的音容笑貌抹掉了第二次在拘留所攝錄的全部內(nèi)容,將之鐫刻在這張光盤里。
責任編輯/吳賀佳
插圖/紀振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