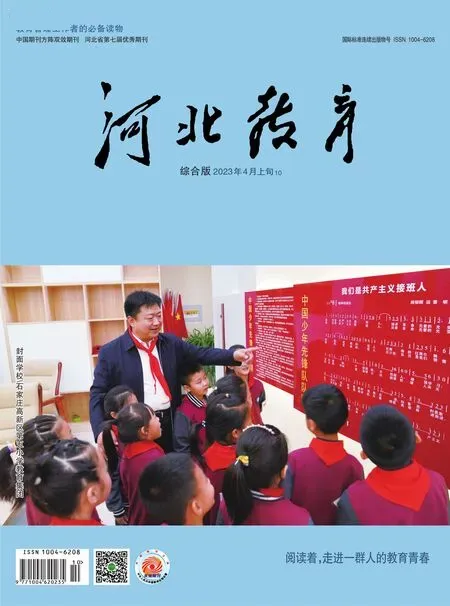向著書,向著閱讀,向著尊貴的生命
■許麗芬
20 年前,第一次去省會(福州),第一次在省會的書店里看到《夏洛的網》時,欣喜讓我有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眩暈感。是感動,更是匱乏的日常帶來的巨大滿足感。很多人可能難以想象,為什么遇到一本童書會有這樣異于常人的感受。實際上,背后的真相非常簡單,20 年前,我太窮了,工資不夠買飯;小城閉塞,連《夏洛的網》這本被全世界孩子喜愛了多少年的書,我都是在雜志上依靠“驚鴻一瞥”而得知的。我已經忘記這本書是什么深深地吸引了我。但這么多年,都沒有“成篇”地為它寫下什么。或者,我在等待那個從“深深愛著”中走出來的自己。
我的孩子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發現他是ADHD,識字認字也存在很大的困難,經常一個字教了無數遍還是不會,在上一行剛剛讀過,下一行,他就又不認識了,“這”字從一歲多我每天朗讀給他聽的故事里到一年級他的課本,出現頻率該有上千次了吧,可是,他仍然不認識啊,無論怎么教,下一次遇到,依然“是全新的陌生世界”。孩子的這個問題,帶給我極大的沖擊,無限的擔憂與難以克制的焦慮、痛苦糾纏著我。我被這個“缺陷”牢牢地控制了,以致一時都忘記了孩子還有什么優勢足以應對長長的一生。為了幫助孩子識字認字,我開始每天晚上陪他朗讀,從20 個字左右的兒歌開始,像爬過高山穿越沼澤一樣,慢慢地慢慢地孩子走出了識字認字的困境,盡管依然有很多字頑固地不認識,但總算是能囫圇吞棗地自主閱讀了。他有多愛閱讀啊,他自豪地自述為“爭分奪秒地閱讀”。我們開始一起朗讀更長的文章,讀了E.B.懷特的《夏洛的網》,接著讀《精靈鼠小弟》,然后讀《吹小號的天鵝》。為了降低難度,保持朗讀的樂趣,我和孩子一人一段,一人一章,有時感覺太精彩了也互相搶著讀而忘記了哪段該誰讀。
陪伴,讓我走出了《夏洛的網》的閱讀“戀愛腦”。在陪伴孩子朗讀的同時,我也讀ADHD 和讀寫障礙方面的專業書籍。這種閱讀,給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E.B.懷特在他的書里只在講“愛”“親情友情”“信任”嗎?
威爾伯、路易斯、斯圖爾特,不止是弱者,同時還是殘缺者。威爾伯是落腳豬,路易斯天生嗓子不能發聲,斯圖爾特則是連侏儒都稱不上的特小號袖珍鼠。假如從缺陷的角度去看,他們都太令人絕望了。威爾伯無論如何無法改變他作為落腳豬的“真相”和即將上演的悲慘命運;路易斯再怎么努力練習也永遠無法像能發聲的天鵝那樣叫出一聲“咯——嗬”;斯圖爾特出生則意味著生命結束,幾乎沒有一對父母會把這樣的一個孩子留下來,甚至連醫生也都會立即勸“別救了”,最多也就是做醫學研究凍體了。我們的日常太現實,太粗鄙了,以致見到與大家不太一樣的就價值崩塌,或許,這崩塌背后本身就沒有價值支持可言,因為它看到的始終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你必須是、唯有是“和大家一樣”的一種人。
然而,E.B.懷特堅持不懈地給出了另一種可能:我就是殘缺,我就是天生地與你不同,但我仍然尊貴,沒有任何一種殘缺可以定義我!除了和你一樣,我還可以做什么而超越“都一樣的大家”。他讓落腳豬威爾伯擁有超越死亡的愛與友情,讓路易斯像演奏家一樣吹小號,讓斯圖爾特因為極小而做很多“大人”無法做到的事情,E.B.懷特讓所有生命的尊貴一絲一毫都沒有受到缺陷的損害。如此,我便知道自己為何深深地愛著他的書了。在20 年間的反復回味中,E.B.懷特像他所寫的故事那樣不知不覺地成為我的人生導師,在我深陷困頓的時候,及時地把我和孩子從“缺陷”的深淵中打撈出來,以朗讀,以故事,以快樂地享受兒童文學的方式,溫暖地懷抱我們于每個閱讀的晚上。
放下對殘缺的恐懼,回到孩子面前,回到每一個尊貴的生命面前,我們可以做什么?
仍然是愛,無可替代的愛,仍然是幫助,義無反顧的幫助。可是,又是如此不同的愛與幫助。你再也不能用“坐端正”去要求一個多動的孩子了,再也不能用“努力”去要求一個讀困的孩子堅持視覺閱讀了,再也不能用“乖乖聽話”去訓練一個亞斯伯格綜合征的孩子了……所有的愛與幫助,都要回到這個具體的孩子面前: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像斯圖爾特,他需要的硬幣是和螳螂的眼睛一般大小的,爸爸就照著他的需求用心地裁剪制作。如果你非給他一個和你一樣需求的硬幣,是會成為斯圖爾特的災難的。事實上,所有的缺陷更準確地說,都是具體生命的一種特質,它是弱點的同時,也一定帶來了強大的優勢。只有在理解他的具體特質時,愛才能成為他的心靈之光;只有在高度契合具體特質的優勢發展時,幫助才能成為有價值的力量支持。
在當下的環境里,盡管具體指向的愛與幫助對于大班教學里的學困兒童而言仍然匱乏到令人心痛,但它仍然不能阻止我們向著書,向著閱讀,向著尊貴的生命,去尋找到足以引領我們的精神力量,并實現自我的救贖與超越,在殘缺的生命真相里活出屬于自己的廣闊天地。
如此,我要祝福每一個與好書相遇相伴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