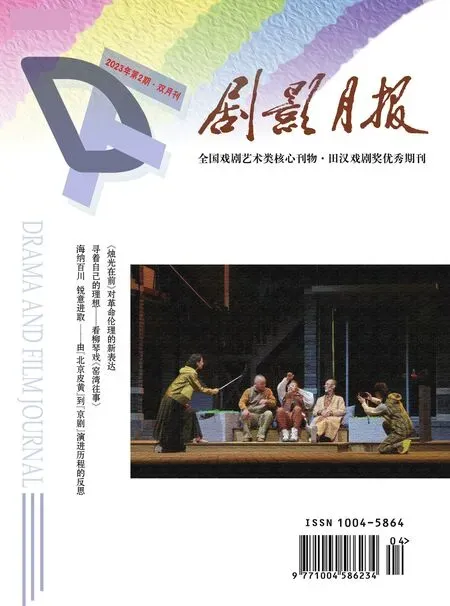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lè)閑人
——淺析唐代《西涼樂(lè)》的舞蹈美學(xué)
■申璇
唐代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鏡映了中國(guó)古代藝術(shù)博大精深的民族風(fēng)格——開(kāi)放性。唐代樂(lè)舞空前絕后的輝煌引來(lái)無(wú)數(shù)文人墨客的美嘆,是中國(guó)古代舞蹈史上第三個(gè)集大成的時(shí)代。寬泛、包容的社會(huì)風(fēng)貌給予了唐代樂(lè)舞狂草般的勃勃生機(jī)。豐富繁多的名目中,盛名顯著的《西涼樂(lè)》獨(dú)具一格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是兼具西北風(fēng)情與中原傳統(tǒng)樂(lè)舞的新創(chuàng)產(chǎn)物。既有西域樂(lè)舞的俏麗矯健,又有中原樂(lè)舞輕盈婉轉(zhuǎn)的美學(xué)特征,融入大量的龜茲樂(lè)舞文化,強(qiáng)調(diào)手眼、步伐、身段的千姿百態(tài),形成了舞蹈語(yǔ)言繁多的獨(dú)特藝術(shù)風(fēng)格。杜牧《河湟》詩(shī)云:“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lè)閑人。”可知《西涼樂(lè)》盛極一時(shí),風(fēng)靡于中原,王公貴族皆沉溺于此。
蘇聯(lián)學(xué)者卡岡指出:“‘風(fēng)格’意味著一種整頓就緒的、固定的、趨于僵化的傾向。”[1]舞蹈是一種形式感很強(qiáng)的藝術(shù),舞蹈評(píng)論家于平也曾在其著作中提出:“舞蹈創(chuàng)作意識(shí)的轉(zhuǎn)化趨向是舞蹈的社會(huì)接受心理高于歷史文化沉積,換而言之,歷史舞蹈文化沉積的‘風(fēng)格化原則’將服從于社會(huì)舞蹈接受心理的‘生命化原則’”。[2]《西涼樂(lè)》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不僅展現(xiàn)著當(dāng)時(shí)民族大融合的社會(huì)背景、其文化環(huán)境的開(kāi)放性,也說(shuō)明了社會(huì)各階層對(duì)其的認(rèn)可與心理接受度。它打破了中原樂(lè)舞和西域樂(lè)舞的固有框架,實(shí)現(xiàn)了風(fēng)格上跨越式的突破;它的出現(xiàn),打破了傳統(tǒng)中原樂(lè)舞趨向僵化的“禮樂(lè)”審美以及西域樂(lè)舞民族色彩強(qiáng)烈的定式,集中外樂(lè)舞的審美風(fēng)格于一體,為唐代樂(lè)舞的風(fēng)格性新創(chuàng)提供了兼收并蓄的先河。《西涼樂(lè)》——“變龜茲聲為之”,亦稱《西涼伎》。被列為隋宮廷《九部樂(lè)》,唐宮廷《九部樂(lè)》《十部樂(lè)》之一。[3]歷史上的音樂(lè)歌舞之鄉(xiāng)——涼州,也是多民族混雜居住之地。盛名顯著的《西涼樂(lè)》既是古代涼州當(dāng)?shù)孛耖g樂(lè)舞,又是各族人民將其同漢族樂(lè)舞、西域樂(lè)舞和印度音樂(lè)交流融合,共同創(chuàng)作的舞蹈藝術(shù)。《西涼樂(lè)》發(fā)源地處河西走廊之咽喉——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是內(nèi)通中原外達(dá)西域的交通重鎮(zhèn)。東晉時(shí)期,前秦大將呂光受苻堅(jiān)之命西伐,擊降西域諸國(guó),攻龜茲,后偕鳩摩羅什并攜帶一批龜茲歌舞伎人東還,趁中原大亂之際,割據(jù)涼州建立后涼政權(quán)。由此西域文化進(jìn)入中原,我國(guó)歷史上的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最重要的交融由此開(kāi)始。《龜茲樂(lè)》傳入此地風(fēng)靡一時(shí),人們爭(zhēng)相學(xué)習(xí)。在此背景下,差異化的樂(lè)舞種類融會(huì)了中原樂(lè)舞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樂(lè)舞而逐漸發(fā)展成為當(dāng)時(shí)一種新穎別致、具有獨(dú)特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西涼樂(lè)》。
一、美學(xué)特征
(一)舞蹈中的民族性
民族性是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性格、心理、精神風(fēng)貌,由此產(chǎn)生的審美差異。《西涼樂(lè)》是繼承中國(guó)傳統(tǒng)審美“禮樂(lè)”的中原樂(lè)舞,融合西域樂(lè)舞的奇異風(fēng)格、大膽融合新創(chuàng)的產(chǎn)物。在民族大融合的社會(huì)背景下,傳入中原的各族及域外樂(lè)舞仍保留著原有的地方特色與民族藝術(shù)風(fēng)格。《西涼樂(lè)》是以其地名為樂(lè)部名稱;美化后的民族服裝是其舞蹈服飾,與《龜茲樂(lè)》類似;所用樂(lè)器為鳳首、箜篌、五弦、琵琶、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鈸、貝等九種,由此可見(jiàn)其中西結(jié)合的風(fēng)貌。腳下著“錦履”,追求“依歌移弱步”“垂手忽迢迢”的美感,是上肢和身體的運(yùn)動(dòng)為主的漢民族舞蹈的特點(diǎn)。而《西涼樂(lè)》的腳蹬皮靴,是西域樂(lè)舞的舞蹈步伐動(dòng)作形式。他們穿皮靴的習(xí)慣是因?yàn)槲鞅鄙贁?shù)民族的地域環(huán)境和游牧生活養(yǎng)成的,皮靴擊打的聲音具有別樣的節(jié)奏,西域舞蹈繁雜豐富的腳下動(dòng)作由此而來(lái),“雙靴柔弱滿燈前”是其寫照。西涼樂(lè)舞,雖腳踏著西域風(fēng)格的皮靴,可其濃厚的中原色彩仍占據(jù)總體基調(diào)。“西涼樂(lè)”常配以宣揚(yáng)文德的《慶善樂(lè)》以及以幽靜婉約為特色的中原“清商樂(lè)”,可說(shuō)明其幽靜、典雅之格接近中原傳統(tǒng)美學(xué)。此間記載鮮明地展示了唐代民族民間樂(lè)舞被宮廷燕樂(lè)吸收并進(jìn)行編創(chuàng)的歷史事實(shí)。
(二)舞蹈中的文學(xué)性
文人雅士的助推有益于舞蹈的流傳和發(fā)展。詩(shī)歌中體現(xiàn)了舞蹈的美學(xué)價(jià)值,詩(shī)與舞相互契合、相互促進(jìn)。唐代舞蹈是以詩(shī)境取勝,富有詩(shī)意的浪漫舞蹈,輕盈、飄逸、秀美、向上是唐代樂(lè)舞其豐富繁多的名目共同的舞蹈美學(xué)思想。經(jīng)史料與文物印證,大部分的唐代舞蹈都具有明快、灑脫之美,不但給予人美的享受,其舞蹈的風(fēng)格韻律也十分鮮明。唐詩(shī)中的美學(xué)詩(shī)意濃郁。唐代詩(shī)文中描寫西涼樂(lè)舞者甚多。王建《行宮詞》曰“開(kāi)元歌舞古草頭,梁州樂(lè)人世嫌舊”;杜牧《河湟》詩(shī)云“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lè)閑人”。再如元稹的《西涼伎》,更是對(duì)西涼劍舞、弄丸、獅子舞等舞蹈的形式和內(nèi)容做出了生動(dòng)的描繪。詩(shī)人們膾炙人口的詩(shī)句,不僅使我們窺探到了西涼樂(lè)舞精美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特色,而且為研究西域文化藝術(shù)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在古代樂(lè)舞文化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唐代的社會(huì)風(fēng)況不斷進(jìn)行演變,舞蹈是社會(huì)變遷的佐證,詩(shī)歌是社會(huì)流變的紀(jì)實(shí)。詩(shī)與舞相互交融,唐詩(shī)不僅載錄了唐代樂(lè)舞的風(fēng)神,還寶藏了其美學(xué)價(jià)值,客觀推動(dòng)了唐代樂(lè)舞的流傳與發(fā)展。
(三)舞蹈的舞臺(tái)美術(shù)
《西涼樂(lè)》中的舞蹈叫“方舞”。從史料中得知,其舞蹈裝束就是一種中西結(jié)合美化后的民族服飾,體現(xiàn)其中外民族樂(lè)舞元素的融會(huì)審美。中原的《清商樂(lè)》以及西域的《龜茲樂(lè)》《安國(guó)樂(lè)》的舞蹈裝束與“方舞”的服飾類似。“‘方舞’的頭飾為假髻,玉支釵,下裝著白大口褲,烏皮靴”。
從舞蹈服飾亦可推測(cè)其樂(lè)舞風(fēng)格,《慶善舞》是唐代宮廷樂(lè)舞燕樂(lè)中的一部,屬文舞、配以《西涼樂(lè)》,多用于皇帝享宴時(shí)、顯示國(guó)力的強(qiáng)盛歌頌唐朝興盛。促數(shù)以管弦伴舞,舞者四人。舞者服飾為“假發(fā)、紫綾袍、大袖、絲步袴、玉支釵、白大口褲、烏皮靴。”由此可見(jiàn),舞姿抒情飄逸、服飾富貴華麗的《西涼樂(lè)》是種嫻雅、華美、雍容的舞蹈,其舞蹈審美的主體建立于中原樂(lè)舞的傳統(tǒng)“禮樂(lè)”華美典雅的美學(xué)。同時(shí),極富感染力的《西涼樂(lè)》較之“清商”更符合唐代上升興旺的時(shí)代特征,其滲透著西域民族開(kāi)朗、豪放情性的藝術(shù)精神,由此證實(shí)了《西涼樂(lè)》自成新風(fēng)的魅力。
二、審美文化
(一)社會(huì)演變的歷時(shí)性
唐代是封建社會(huì)歷史上一個(gè)強(qiáng)盛的大一統(tǒng)朝代,疆域廣闊、國(guó)家強(qiáng)盛、經(jīng)濟(jì)繁榮,俗稱大唐盛世;其兼容并蓄的社會(huì)風(fēng)氣、開(kāi)放寬泛的文化氛圍以及朝氣蓬勃的市井貿(mào)易促進(jìn)了民間樂(lè)舞藝術(shù)的發(fā)展。唐代樂(lè)舞的鼎盛,狂草生命于南北朝時(shí)期各族樂(lè)舞大融合的基礎(chǔ)之上;唐代欣欣向榮、頗具活力的社會(huì)風(fēng)貌,則體現(xiàn)在百花爭(zhēng)艷的舞蹈活動(dòng)上,自天南海北流入的各族樂(lè)舞與中原漢族的傳統(tǒng)樂(lè)舞生長(zhǎng)成一株枝繁葉茂的藝術(shù)之樹(shù)。得益于“廣納百川、容納異己”的氣魄與藝術(shù)情懷,唐代樂(lè)舞享譽(yù)世界。在欣欣向榮的盛唐,舞蹈是人們富足生活之余一種休閑娛樂(lè)的形式,是其宣泄熱烈情感的方式,表達(dá)了唐人對(duì)美的精致追求。由此促成了唐代樂(lè)舞盛行的社會(huì)潮流,尤其是隨著域外文化的傳入,以開(kāi)放性著稱的唐代樂(lè)舞博采眾長(zhǎng),其舞蹈動(dòng)作與形式都發(fā)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西域各族樂(lè)舞在長(zhǎng)期的流傳又不斷結(jié)合中原人民的審美及欣賞習(xí)慣加以改編創(chuàng)作。經(jīng)史料與文物(壁畫)的印證,大部分的唐代舞蹈都具有明快、灑脫之美,不但給予人美的享受,其舞蹈的風(fēng)格韻律也十分鮮明。唐代舞蹈昂揚(yáng)、爛漫、俏麗、爽朗的風(fēng)情源于昌隆的國(guó)勢(shì)、社會(huì)風(fēng)氣的開(kāi)放灑脫以及創(chuàng)作表演方式的博采眾長(zhǎng)。
(二)階級(jí)分層的共時(shí)性
舞蹈活動(dòng)是唐代社會(hu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上自達(dá)官貴族,下至樂(lè)舞伎人,各階層人士皆“珍舞”“善舞”。舞蹈活動(dòng)展示了大唐盛世欣欣向榮的社會(huì)風(fēng)貌及開(kāi)放性品格,各民族“自舞成風(fēng)”的社會(huì)風(fēng)氣是舞蹈活動(dòng)的深度及廣度的體現(xiàn),得益于此,盛唐的樂(lè)舞之花得以綻放。盛唐之際,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鼓勵(lì)多樣性,除個(gè)別當(dāng)政者外,其意識(shí)形態(tài)均奉行儒、釋、道三教并行政策,以強(qiáng)盛國(guó)力為依托,心濟(jì)天下的情懷。在這種大背景下,唐代樂(lè)舞人才輩出,帝王將相興致勃勃,用蓬勃而出的激情澆灌唐代的宮廷樂(lè)舞之花。王朝統(tǒng)治者“功成作樂(lè)”,唐代歷朝天子權(quán)貴視“燕樂(lè)”等宮廷樂(lè)舞為權(quán)力的外部象征與人欲的內(nèi)在需求,唐代宮廷樂(lè)舞除享宴外,用以顯聲威、歌頌君主功德,表率“帥萬(wàn)邦朝長(zhǎng)安”的大國(guó)風(fēng)范和民族氣魄,亦服務(wù)于禮儀祭祀。特意設(shè)立梨園、教坊、太常寺等宮廷專門樂(lè)舞機(jī)構(gòu),培育專業(yè)的樂(lè)舞伎人;“自舞成風(fēng)”的現(xiàn)象在皇族中也屢見(jiàn)不鮮,還常常親自創(chuàng)作、改編樂(lè)舞,唐太宗李世民的《破陣樂(lè)圖》用于歌頌君主德、彰顯國(guó)威;玄宗的《霓裳羽衣舞》,特點(diǎn)是“其音清而近雅”,表現(xiàn)仙女優(yōu)美形象,有一定宗教色彩。大唐宮廷“燕樂(lè)”及其樂(lè)舞文化享譽(yù)世界、傳播深遠(yuǎn)。其中將相貴族能歌善舞,高官安祿山——官至節(jié)度使,體型肥胖卻極擅《胡旋舞》;有“唐代三絕”之一美譽(yù)的裴旻將軍擅劍舞,有記載稱:“裴將軍滿堂勢(shì)。”民間歌舞藝人活躍于全國(guó)各地,有著“四方散樂(lè)”齊聚演出的美談。樂(lè)舞百戲藝人在民眾中成長(zhǎng),扎根于民間創(chuàng)作、表演,為盛唐藝術(shù)的輝煌添磚加瓦。廣場(chǎng)、街頭、酒肆皆是展示其藝術(shù)風(fēng)尚的“舞臺(tái)”,風(fēng)格各異卻又體現(xiàn)出相似時(shí)代特征與審美意識(shí)的唐代樂(lè)舞作品不僅是統(tǒng)治階級(jí)追求高水平藝術(shù)享受和有效進(jìn)行政治宣傳的產(chǎn)物,也是藝術(shù)家們廣泛吸收多種樂(lè)舞因素新創(chuàng)的成功之作,反映了大唐帝國(guó)的恢宏氣度。
(三)民族差異性
唐代社會(huì)民族融合的潮流十分興盛,這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淵源息息相關(guān)。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不斷與域外民族及各國(guó)的異質(zhì)文化發(fā)生沖突、交融的歷史。唐代樂(lè)舞的美學(xué)思想體現(xiàn)出的社會(huì)風(fēng)貌是思想上對(duì)待異域文化的包容性與開(kāi)放性,以及各民族樂(lè)舞的特性與民族性格受地域環(huán)境、文化淵源所產(chǎn)生的差異。崇尚行事果敢民族生存之道的西域民族,擁有豪放開(kāi)朗的民族性格,喜愛(ài)樂(lè)舞卻因生存環(huán)境惡劣,不能沉溺于輕松悠閑的享樂(lè)情緒。因此,西域樂(lè)舞擁有豪放的文化色彩,以矯健有力的鮮明舞蹈動(dòng)作著稱。舞蹈抒發(fā)情感的方式與西域民族果敢的性格相像,與中原傳統(tǒng)文化有巨大的差異。性格內(nèi)斂的中原民族,更多是婉轉(zhuǎn)含蓄的情緒表達(dá)。隨著大唐盛世的到來(lái),兩者差異性巨大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物質(zhì)豐盈的唐人更傾向追求一個(gè)豪放抒發(fā)與宣泄情感的良好渠道。
三、結(jié)語(yǔ)
《西涼樂(lè)》產(chǎn)生于一個(gè)認(rèn)識(shí)、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它是各民族民間樂(lè)舞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平衡并提取西域樂(lè)舞精華與中原樂(lè)舞特性的結(jié)果。中原樂(lè)舞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在其身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展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水平,對(duì)本民族樂(lè)舞文化的誨熟于心,對(duì)外來(lái)樂(lè)舞文化的接受程度,并將其融會(huì)貫通。同時(shí),彰顯其“俗世狂歡”的藝術(shù)精神,中原樂(lè)舞文化以自身的美學(xué)魅力與歷史沉淀,兼收并蓄,取各族民間樂(lè)舞文化之精華,這種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樂(lè)舞難以被輕易侵蝕。《西涼樂(lè)》雜糅著嫵媚典雅的傳統(tǒng)舞蹈與明媚俏麗的西域風(fēng)情,同時(shí)交織著中原清商的婉轉(zhuǎn)清麗與印度佛曲的宗教色彩,是唐代政治文化歷史進(jìn)程的真實(shí)寫照,蘊(yùn)含著一個(gè)朝代的瑰麗底蘊(yùn),是中國(guó)古代舞蹈史的藝術(shù)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