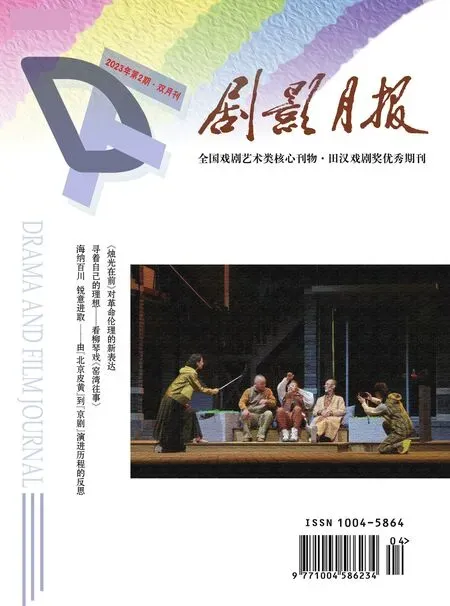鄉愁的戲劇性表達
——論普契尼歌劇《西部女郎》中的懷舊主義
■黃璇
渴望失去的愛情和過去的幸福是西方文學中一個古老的主題,它塑造了許多意大利歌劇的敘事,從最早的奧菲斯傳說到威爾第的作品,包括《茶花女》和《奧泰羅》中都能看到懷舊主義的影子。懷舊、思鄉的主題在19 世紀變得越來越突出,用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的話說,這種情感在整個歐洲大陸變成了“浪漫民族主義的核心修辭”。另外,文藝作品中懷舊主義的興起與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正如歌劇《西部女郎》中遠離家鄉的礦工們所面臨的情況,科技的進步使遠距離的遷移成為可能,人們也更容易去到離家更遠的地方謀生。《西部女郎》1910 年在紐約首演時,礦工們的鄉愁打動了許多現場觀眾的心。在普契尼的許多歌劇中,地理、空間分隔帶來的鄉愁常常與哀悼時間逝去的懷舊混用在一起,用以表達劇中人物對過去美好時光的渴望以及對愛人、親人的深深依戀。
一、“鄉愁”概念和“懷舊主題”
歌劇《西部女郎》以19 世紀中期加利福尼亞淘金熱期間內華達山脈的一個采礦地為故事背景展開。第一幕在“波爾卡”酒吧開場,礦工們在那里度過工作后的夜晚時光。一個名叫杰克·華萊士的“吟游詩人”進入酒吧,向其他礦工演唱了一首凄美的歌曲:“Che faranno i vecchi miei”(家鄉的長輩怎么辦)。華萊士的歌聲打斷了歡快的氣氛,勾起了礦工們對家鄉和家人的回憶,他們與華萊士合唱起來。在集體表演結束后,其中一名礦工拉肯斯突然淚流滿面,懇求他的朋友帶他回家。礦工們被他突然流露出的脆弱情感震驚了,他們為他籌得了一筆錢以支付他回家的旅費。當拉肯斯意識到有可能返回家鄉時,他的心情頓時輕松起來,在感謝他的同事們后離開了舞臺。然而華萊士演唱的那首思鄉民謠旋律卻在作品的結尾處再次出現,是反復出現的音樂主題之一,被稱為“懷舊主題”。對比歌劇《西部女郎》與貝拉斯科的原劇本《金色西部的女郎》在敘事、音樂和場景方面對鄉愁這一概念的處理,能發現普契尼在歌劇的開始部分就有意地、自覺地喚起了角色的鄉愁,并將其呈現為一種急性思鄉病的形式。華萊士的演唱喚起了拉肯斯的鄉愁,并使其戲劇性地爆發出來,這也為后續故事情節的展開鋪墊了一層懷舊的底色。
看似普遍和永恒的思鄉和懷舊,實際上相對較晚時間才出現在西方的語言體系中。約翰尼斯·霍費爾(Johannes Hofer)在其1688年的論文中首次根據希臘語詞根“nostos”(故土)和“algos”(傷痛)合成了“nostalgia”(鄉愁)一詞,其原始含義是一種由于思鄉情緒所導致的急性且可能致命的疾病。此后,在長達近百年的歷史中,醫生、科學家和哲學家們將鄉愁定義為不同的心身疾病,主要是心理疾病,沒有直接的生理影響,但其引起的絕望情緒也會導致生理不適。盡管鄉愁在此之前一直與醫學和疾病聯系在一起,但從19 世紀開始,詩人和作家們越來越多地探索關于鄉愁的其他存在方式,將其視為一個普遍和永恒的詩歌主題,并將其含義擴大到包括對過去的渴望,不僅是對自己的故土,也包括對過去的物品、情感和經歷的渴望。這種懷舊之情其實指向兩個不同時空的對照,即一個不充分的現在和一個理想化的過去,這也是文藝作品中關于鄉愁的重要表現形式。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中指出,懷舊是一種既在現在又在過去的心理學和社會學現象,也是流浪作家和藝術家使用的一種文學手段。鄉愁不僅為流浪在外的人提供身份認同感和類似于心靈港灣的安全感,而且也是一種創造性的藝術力量。此外,懷舊也可以發揮移情作用,通過共同的經歷,彌合分隔不同背景的個人之間的鴻溝。
《西部女郎》中普契尼首次將“nostalgia”一詞納入歌劇劇本,并明確將其作為歌劇的中心主題之一。1910年首演之后,這部歌劇被置于20世紀初意大利大規模移民的歷史語境中探討,華萊士的歌謠以及鄉愁概念在整個歌劇主題中的突出地位得到了廣泛的討論。普契尼在第一幕的開始,就期望通過華萊士和礦工們的合唱以及拉肯斯思鄉病的爆發這一情節將情緒推向一個小高潮。在普契尼創作歌劇的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鄉愁具有多種內涵,它既是一種具有特征性癥狀和嚴重生理后果的可治療的疾病,又是一種對失去的空間和時間無法治愈的情感狀態。盡管將思鄉和懷舊的情緒概念化為一種嚴重的思鄉病的做法似乎已經過時,但無疑還是能夠引起觀眾的深刻情感共鳴。普契尼在其中實踐了博伊姆所說的“懷舊”的倫理層面,即它能夠引起那些沒有直接受到懷舊之苦的人的同情。在歌劇的結尾處,女主人公明妮同樣通過懷舊情結喚起了礦工們的回憶和情感,并說服他們釋放約翰遜,明妮由此贏得了她的愛侶約翰遜的自由,并與他一起離開了采礦地。
二、《西部女郎》中的“懷舊”修辭
在普契尼歌劇中,“懷舊”既是一種人類普遍的心理感受的概念化呈現,也是一種喚起情感的修辭結構,兩者是相互關聯的。在普契尼的歌劇中,這種對懷舊的雙重處理方式,不僅使我們能夠欣賞到作曲家在其職業生涯中戲劇技巧的發展,而且使我們對其中探索的不同色調的懷舊情感有了更多的了解。普契尼構建被稱為“懷舊”修辭的手段是使用大規模重復的文本、音樂動機和戲劇性的動作與情節,通過邀請觀眾感知音樂材料的原始陳述和重復之間的差異,這種時間變化上的“距離感”變得清晰可聞。這些手段借鑒了奧托克托意大利情節劇中回憶主題的做法,瓦格納的動機技術,以及19 世紀末法國歌劇中的傳統,即對音樂材料的精心重復。
在《西部女郎》第一幕華萊士的民謠中,華萊士大聲問道,他的長輩們在家鄉做什么,并想象他們因為他不會回來而哭泣。當礦工們加入與他一起合唱時,他們的想象擴大到他們母親的情緒,甚至是他們的寵物狗是否會想念他們。這一歌劇開場的主要目標不一定是推動劇情發展,而是將各種圖像、聲音和情感印在觀眾的腦海中,以便在歌劇結束時回憶,引起他們的懷舊反應。在離開現場后,華萊士和拉肯斯這兩個角色就再也沒有在歌劇中出現過了。然而,華萊士歌曲中的一個短句在第一幕后的圣經課場景中短暫出現,在歌劇快要結束時,被稱為“懷舊主題”的華萊士的歌聲再次出現,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促使觀眾與舞臺上的人物再次情感交流的聲音載體。
《西部女郎》的最后一幕發生在“加州大森林”的空地上。這一幕中迎來了這部歌劇最關鍵的戲劇性高潮——明妮能否說服礦工們釋放他們的囚犯約翰遜。“波爾卡”酒館的女老板明妮是一個熱情果敢的女性角色,與礦工們之間的情誼頗深。她愛上了初來乍到的約翰遜,后來卻得知他是盜賊集團的首領,憤怒于約翰遜的隱瞞,卻也通過與蘭斯的賭局為約翰遜贏得了生的希望。警官蘭斯的任務是抓住約翰遜,同時他也嫉妒約翰遜得到了明妮的愛。在最后一幕中,約翰遜還是被蘭斯和礦工們抓獲,他們商量要將他處以死刑。歌劇發展到這里,所有的戲劇沖突都匯聚到了這個時刻。明妮騎著馬戲劇性地登場,走到約翰遜面前,與蘭斯和礦工們對峙。她揮舞著手槍,讓礦工們不敢靠近。當威脅不起作用時,她把武器轉向了約翰遜和她自己。當人群逐漸散開時,明妮責備礦工們試圖傷害她的愛人,并宣稱約翰遜是她來自天堂的禮物。明妮用歌聲與礦工們交談起來,連續不斷的旋律織成了一張厚厚的音樂回憶之網。明妮沒有直接懇求礦工們釋放約翰遜,而是回顧了她與個別礦工共同經歷的種種往事。明妮首先走近喬,說,你不就是那個給我提供鄉間荒野上的那些花的人嗎?然后她轉過身來,撫摸著哈利的手,回憶起他奄奄一息時她護理他的許多個夜晚,他在神志不清時把她誤認為他心愛的妹妹莫德。此時,索諾拉再也忍不住幫助明妮的沖動,開始勸說其他礦工釋放約翰遜,提醒他們虧欠她太多。與此同時,明妮轉向特立尼達,提醒在他猶豫不決時,是她引導他向家鄉圣多明哥寄出了第一封信。
事實上,在明妮對她為喬、哈利和特立尼達所做事情的回憶中,他們三人都表現出了醫學上的懷舊或思鄉的癥狀。喬在鄉間徘徊,收集鮮花,表面上是為了給明妮留下好印象,但也是因為鮮花讓他想起了自己的故鄉。最后明妮回憶起她曾經教特立尼達寫信,也是為了讓他能與他可能在圣多明哥的家人取得聯系。明妮訴諸懷舊的修辭,以激起一心要懲罰約翰遜的礦工們心中的懷舊情感和同情心,從而救贖約翰遜。明妮理解懷舊產生共鳴的力量,她把她對約翰遜的愛情與礦工們對家園的思念之情相類比,以說服他們放下,理解她對約翰遜的感情。被明妮的懇求所感動,礦工們同意釋放約翰遜。明妮和約翰遜向礦工們告別,走下舞臺,當礦工們看到他們依戀著的明妮離開礦營時,痛苦情緒彌漫,華萊士“懷舊主題”的民謠再次響起,大幕緩緩落下。在這首歌曲的再現中,對與明妮共度美好時光的懷念以及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也再次交織在一起,礦工們切身體驗到了第一幕中拉肯斯所遭受的絕望痛苦的離愁別緒。通過這段對話中對關鍵音樂動機的精心回憶,普契尼讓歌劇的觀眾感受到了懷舊的壓倒性力量,使他們在情感上與女主人公站在了一起。
三、通過懷舊主義喚起情感共鳴
在這部歌劇中,懷舊從一開始就被標記為一種移情的練習,在歌劇的結尾部分尤其如此。普契尼通過明妮這一角色展現了他非凡的“懷舊”修辭能力,在歌劇的結尾將懷舊的特殊力量戲劇化,喚起礦工們的共鳴,同時也喚起了現場觀眾的情感共鳴。因為普契尼經常依靠“懷舊”的修辭結構來引導觀眾沉浸于舞臺上所展現的懷舊體驗,以期在觀眾心中引起最大限度的情緒共振。《西部女郎》中,除了精心制作以人物對逝去的時光和過往的情感的懷念為特征的敘事外,還以這樣的方式設計歌詞和樂譜,使文本、音樂和舞臺動作都能協同工作,使舞臺上的人物所經歷的懷舊之情引發觀眾共鳴。
懷舊主義在普契尼部分歌劇的戲劇性表演和接受中都扮演了關鍵角色。普契尼的許多歌劇中的人物都對過去的事件和情感進行了美好的回憶,特別是他們曾經享受過的但現在已經遠離他們的激情浪漫和幸福。在他早期的歌劇《維利》和《曼儂·萊斯科》,以及他的成熟作品《波希米亞人》和《蝴蝶夫人》中都可以看到他對懷舊的關注。在這些歌劇中,普契尼刻畫了懷舊的人物角色,并探討了與懷舊有關的各種心理狀態。在這些例子中,對空間分離或回歸的預期和實現引發了人物的懷舊思考。在《維利》和《波希米亞人》的結尾二重唱中,普契尼在人物在各自浪漫的原地重逢但意識到現在和過去之間不可逆轉的時間距離的確切時刻,加入主題回憶。盡管即使是普契尼音樂的一些擁護者也以一種尷尬的態度看待他對頻繁大規模音樂重復的依賴,但這種對關鍵音樂特征的重復對懷舊的修辭結構至關重要。在另一個層面上,以略微改變的方式重復以前聽過的音樂,讓觀眾評估它與原始形式之間的差異。這種心理活動,對兩個時間平面的同時感知,模擬了與懷舊有關的心理體驗,并邀請觀眾分享舞臺上人物的情感體驗。換句話說,通過使用大規模的文本、音樂和戲劇性的回顧的懷舊修辭,普契尼模糊了模擬的懷舊和實際的懷舊體驗之間的界限。在普契尼的歌劇中,這種看似多余的時刻被證明是深深感動觀眾的。
懷舊在當代文化中無處不在,由于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對時間的目的論和單向流動性的瓦解,在20世紀已經開始改變人們對時間的想法。音樂是一種線性向前的時間性話語,如同時間和經歷一樣不可逆轉,但是又與它們不同,因為音樂作品是可重復的。這種特點使音樂既存在于時間中,但同時又超越了時間,即可以多次重溫,這正是它成為懷舊者喜愛的載體之所在。普契尼的作曲生涯與革命性媒體技術的發明和傳播相重疊,他改編和完善了現有的音樂戲劇裝置,加強了一種特殊的敘事邏輯,扭轉了時間進展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現在的事件以這樣的方式展開,作為未來的回憶對觀眾產生最大的情感影響。普契尼歌劇中的懷舊主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精心策劃的戲劇性效果的結果。在普契尼的許多歌劇中,鄉愁的戲劇性表現被設計成通過巧妙地操縱關鍵的文本、音樂和場景成分,邀請觀眾參與到他們所描繪的懷舊體驗中。事實上,引起觀眾強烈的情緒反應對普契尼來說似乎是最重要的,他曾向他的合作者解釋說,他寫歌劇的主要目標是感動人們,或者更生動地說,是“讓人們哭泣”。
四、結語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許多學者和批評家的研究中,懷舊作為一種心理和社會現象出現,對個人和集體身份的形成至關重要,是一個有意義的分析概念。分析普契尼的歌劇《西部女郎》時,能看到普契尼將懷舊作為一種經驗的概念化和一種修辭結構運用在作品的情感敘事之中,使歌劇中人物所經歷的情感更能打動觀眾的心。現代錄音和廣播方面的技術進步,唱片和網絡的廣泛普及,促使人們以新的方式來消費和聆聽普契尼的歌劇,其中體驗歌劇的行為本身已成為懷舊回憶的來源。盡管普契尼在其生命的最后階段對懷舊主義持懷疑態度,但懷舊主義仍在蓬勃發展,為其歌劇的持久流行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