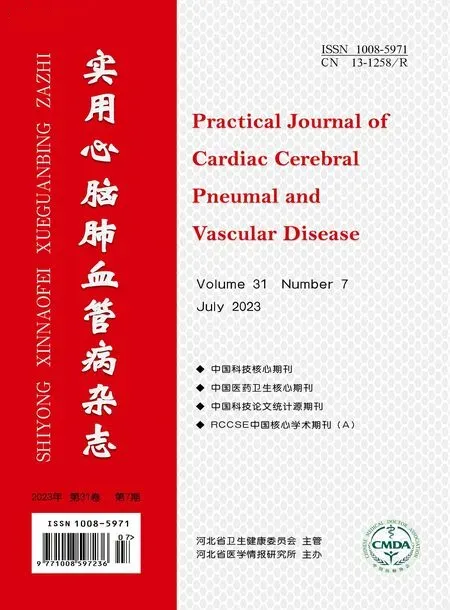低氧性肺動脈高壓中缺氧誘導因子1α調節機制的研究進展
郭暢,丁超偉,袁雅冬
低氧性肺動脈高壓(hypox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H P H)包括低氧性肺血管收縮(hypoxic pulmonary vasoconstriction,HPV)和低氧性肺血管重塑兩個階段[1],其中HPV是肺血管系統的穩態調節機制,肺泡缺氧后,機體通過收縮肺內動脈而將血液轉運至氧合更好的肺段,從而優化該肺段通氣/血流灌注比例,增加肺的氧合功能[2]。研究表明,在缺氧狀態下,激活毛細血管前肺動脈平滑肌細胞(pulmonary artery smooth muscle cells,PASMCs)的信號傳導機制對HPV至關重要,而血管細胞主要通過缺氧誘導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的氧依賴性轉錄因子活性而適應慢性缺氧情況[3]。研究表明,HIF-1α的翻譯后修飾如泛素化/去泛素化、羥基化、乙酰化、磷酸化、小泛素相關修飾物(small ubiquitin-related modifier,SUMO)化可影響其穩定性及活性,細胞增殖相關通路如PI3K/AKT/mTOR信號通路和Hippo信號通路具有調控HIF-1α的作用[4]。有證據表明,干預HIF-1α上游調控因子活性或HIF-1α特異性抑制劑是一種有吸引力的腫瘤治療策略[5]。本文主要綜述了HPH中HIF-1α的調節機制(HIF-1α的翻譯后修飾)及其相關調控通路,以期為HPH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1 HIF簡介
研究表明,HIF介導的信號傳導可維持氧穩態,其可在轉錄水平調控多個缺氧反應基因的表達[6]。HIF有HIF-1、HIF-2、HIF-3共3個家族成員,其中HIF-1β表達不受缺氧影響,HIF-1α主要受氧濃度調控[7]。在缺氧條件下,HIF-1α被轉運至細胞核并與HIF-1β形成二聚化,從而激活下游靶基因如內皮素1、葡萄糖轉運蛋白1、Bcl-2/腺病毒E1B 19kD相互作用蛋白3、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的表達[3],而這些下游靶基因蛋白可調控肺血管細胞代謝和增殖、血管張力和血管生成等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hypertension,PH)發生的關鍵過程。
2 HPH中HIF-1α的翻譯后修飾
2.1 羥基化 脯氨酰羥基化及天冬酰胺殘基羥基化是調節細胞內HIF-1α穩定性和轉錄活性的關鍵步驟。脯氨酰羥化酶(prolyl hydroxylase domain-containing enzymes,PHD)包含PHD1、PHD2、PHD3 3個家族成員,其中PHD2起主要作用[8],其能羥基化HIF-1α的氧依賴性降解結構域(oxygendependent degradation domain,ODDD)中的2個脯氨酸殘基(Pro402和Pro564),使其更易被泛素化,這個過程決定了細胞內HIF-1α的穩定性[9]。
缺氧誘導因子抑制因子1(factor inhibiting HIF-1,FIH-1)是調控HIF-1α轉錄活性的另一個關鍵蛋白,正常氧濃度下,FIH-1可催化HIF-1α天冬酰胺殘基羥基化,進而抑制HIF-1α的轉錄活性[10]。研究表明,由于FIH-1較PHD對氧氣的米氏常數低,故輕度下調氧氣濃度即可使PHD失去活性,而明顯下調氧氣濃度后才能降低FIH-1活性,因此FIH-1較PHD對HIF-1α的調控作用更精細[11]。
HIF-1α的翻譯羥基化修飾可參與HPH的發生發展過程,如ELAMAA等[12]研究發現,PHD/HIF-1α途徑可參與PH的形成,人類肺組織內皮細胞和動脈平滑肌細胞中PHD2表達缺失可增加肺動脈收縮壓,進而導致右心室壓力升高;低氧條件下,miRNA-17/miRNA-20a表達上調,而靶向抑制PHD2可增加HIF-1α的穩定性,從而促進HPH肺血管重構[13]。此外,PHD2/HIF-1α也在內皮細胞中作用于糖酵解酶6-磷酸果糖-2-激酶/果糖-2,6-雙磷酸酶3,從而增強右心室在缺氧狀態下的適應性[14]。
綜上,激活PHD2并抑制內皮細胞中HIF-1α的表達可成為HPH的潛在治療方法。
2.2 泛素化/去泛素化 泛素-蛋白酶體途徑是分解HIF-1α最重要的一種手段,其中泛素存在于大部分真核細胞中,且以單體或肽鏈形式附著在目標蛋白上,進而發揮生物學作用。泛素化過程需要三種酶,即泛素激活酶(E1酶)、泛素結合酶(E2酶)、泛素蛋白連接酶(E3酶),其中泛素分子經過E1酶、E2酶的激活和轉移后,被E3酶結合至底物蛋白的賴氨酸殘基上,進而使底物蛋白被26S蛋白酶體識別并降解[15]。泛素化過程可以被去泛素化酶(deubiquitinases,DUB)所逆轉,其機制主要為:DUB主要通過水解泛素羧基末端的酯鍵、肽鍵或異肽鍵而將泛素分子特異性地從底物蛋白上水解下來[16]。研究表明,在PH發展過程中,機體存在多種泛素-蛋白酶體系相關蛋白功能紊亂[17],其中包括調控細胞內HIF-1α穩態的泛素/去泛素蛋白功能異常,而靶向HIF-1α蛋白代謝是HPH治療的新方向。
2.2.1 VHL蛋白 VHL蛋白是一種經典的具有抑癌作用的E3酶,其與elongins B、elongins C、cullin2及Rbx-1構成elongin B/C-cullin2-VHL E3酶復合體,進而靶向識別、介導底物蛋白降解。VHL蛋白是HIF-1α最重要的E3酶,VHL蛋白途徑是HIF-1α最主要的泛素降解途徑。在常氧狀態下,VHL蛋白可快速識別并結合被PHD羥基化的HIF-1α,進而使HIF-1α維持在較低水平[18]。而在缺氧肺動脈內皮細胞(pulmonary arterial endothelial cells,PAECs)和PASMCs中,HIF-1α的羥基化和VHL蛋白途徑受到抑制,HIF-1α的t1/2明顯延長,作為核心轉錄因子,其可調控下游蛋白表達,進而使細胞轉向增殖表型。目前,針對VHL綜合征的HIF-2α抑制劑——Belzutifan已用于腎癌患者的治療中[19],而HIF-1α作為VHL明確的下游靶點,干預VHL/HIF-1α途徑可促進HIF-1α降解,進而可能成為HPH的治療靶點。
2.2.2 Siah Siah是一類高度保守的RING家族E3酶,人類基因組包含Siah1、Siah2、Siah3 3個基因[20]。研究表明,細胞中PHD的穩定性和豐度由Siah1/Siah2調節,缺氧狀態下Siah活性增加,導致PHD的泛素化水平降低和HIF-1α羥基化減弱,使HIF-1α逃脫VHL蛋白的識別和降解[21]。目前研究表明,HPH患者肺小動脈壁中Siah1/Siah2表達增高,PHD水平下降,Siah可能通過降低PHD穩定性而抑制HIF-α的羥基化,進而參與PH相關HIF通路的調節[22]。筆者推測,抑制Siah表達可能間接調控HIF-1α,進而逆轉HPH中的肺血管重塑。
2.2.3 Hsc70相互作用蛋白(carboxyl terminus of Hsc70-interacting protein,CHIP) CHIP是一種與分子伴侶蛋白功能密切相關的E3酶,其主要包含3個功能結構域:一個TPR結構域位于氨基端,負責與熱休克蛋白Hsp90和熱休克結合蛋白Hsc70結合;一個U-box結構域位于碳末端,主要負責與降解底物結合,從而維持E3酶的功能;中間的二聚體結構域含有入核信號,可能主要負責CHIP的細胞內定位。研究表明,在短期極度缺氧條件下,CHIP可以與HIF-1α直接結合,使HIF-1α發生泛素化修飾,從而被蛋白酶體識別并降解[23];而在人臍帶血間充質干細胞中過度表達miRNA-21可以通過靶向CHIP、增強HIF-1α活性而促進嚴重缺血肢體的新生血管形成[24]。有研究者在HPH模型大鼠的PASMCs中發現,CHIP表達升高,而使用小干擾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敲低CHIP后,PASMCs中的鈣離子濃度降低,缺氧誘導的PASMCs過度增殖被逆轉[25]。但CHIP作為E3酶,維持細胞正常功能時需要依賴熱休克蛋白來完成對錯誤折疊蛋白質的泛素化降解。而CHIP在HPH中能否成為低氧條件下HIF-1α新的降解機制值得進一步研究。
2.2.4 USP28 USP28是去泛素化水解酶家族中最新的抗腫瘤分子靶標,其通過控制細胞內癌蛋白MYC和促癌蛋白LSD1的穩定性而在癌癥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26]。在惡性腫瘤血管生成過程中,USP28可以拮抗糖原合酶激酶3和腫瘤抑制因子FBW7通過VHL非依賴途降解HIF-1α[27]。研究發現,USP28在低氧PASMCs中呈過表達,miRNA-92b-3p與USP28的3'-UTR結合可減緩低氧誘導的PASMCs過度增殖[28]。此外,USP28過表達還可以升高HIF-1α水平及控制HIF-1α的轉錄活性,而靶向抑制USP28表達可避免干擾HIF-1α降解,對HPH起到治療作用。
2.2.5 USP7 USP7是去泛素化酶USP家族成員,其泛素酶活性可調節多種靶蛋白表達,進而參與細胞有絲分裂、細胞凋亡、細胞周期、DNA復制、神經元發育和表觀遺傳調控過程[29]。研究表明,在多種腫瘤細胞系(如肺癌H1299、前列腺癌PC3、頭頸癌SAS、腎臟腫瘤293T、乳腺癌MDA-MB-231細胞)中USP7表達上調,而去泛素化HIF-1α可導致HIF-1α靶基因啟動子上CBP介導的組蛋白3賴氨酸56乙酰化,進而促進癌細胞增殖及轉移[30]。在經血小板源生長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處理的PASMCs中,USP7表達上調,其通過去泛素化鼠雙微粒體蛋白2、促進叉頭框蛋白O4泛素化降解、增加細胞周期蛋白D1的表達而介導PDGF誘導的PASMCs增殖,而轉染siRNA抑制USP7表達可逆轉PASMCs的過度增殖[31],提示USP7可能是參與PASMCs異常增殖的潛在因子,或可成為HPH的治療靶點。
2.3 乙酰化 乙酰化過程主要是賴氨酸乙酰轉移酶(lysine acetyl transferase,KATs)將乙酰基從乙酰輔酶A轉移到賴氨酸的ε-氨基側鏈,該過程是可逆的,而乙酰化動態平衡可參與調控蛋白質-蛋白質或蛋白質/DNA的相互作用。目前,絕大部分KATs歸為GCN5、p300和MYST19家族。
研究發現,乙酰化的HIF-1α易被VHL蛋白泛素化降解,而乙酰轉移酶可對HIF-1α的ODDD中的第532位賴氨酸進行乙酰化,與VHL蛋白緊密結合,進而使HIF-1α泛素化降解;而當HIF-1α的ODDD中的第532位賴氨酸突變為精氨酸時,HIF-1α不易經上述途徑進行泛素化降解[32]。在PH中,蛋白乙酰化可參與多種致病基因的轉錄翻譯調節,且與肺血管重構過程中的細胞增殖、炎癥密切相關。有PH動物模型和PASMCs體外實驗證實,在PH中Ⅰ類和Ⅱ類Zn2+依賴性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表達上調、活性增強,而Ⅲ類HDACs表達降低、活性減弱[33]。上述異常表達的去乙酰化酶參與了PH肺血管中PASMCs、PAECs、成纖維細胞的異常增殖及細胞基質異常沉積、上皮-間質轉化、炎癥反應等,進而使肺血管重塑,引發PH。在腫瘤研究領域,去乙酰化酶抑制劑是一種新的化療藥物,其可增加組蛋白乙酰化,保證HIF-1α乙酰化后使VHL蛋白對HIF-1α具有更好的敏感性,進而加快HIF-1α的降解[34]。
綜上,PH與腫瘤的主要病理生理機制相同,故這種調控HIF-1α的機制可以成為治療HPH的新思路。
2.4 磷酸化 磷酸化是一種常見且被充分研究的翻譯后修飾途徑。蛋白質磷酸化是由蛋白質激酶將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的磷酸基轉移到底物蛋白質氨基酸殘基的過程,或在信號作用下結合三磷酸鳥苷;而去磷酸化過程則與其相反,去除蛋白質相應的磷酸基[35]。
LEI等[36]研究發現,PH患者肺組織中ERK1/2水平升高,肺組織中磷酸化HIF-1α水平較對照者升高1.46倍,分析原因可能如下:ERK磷酸化HIF-1α后,破壞了HIF-1α兩個具有轉錄功能的結構域之間的抑制區,使HIF-1α具有更強的轉錄活性,進而加重肺血管重構。此外,M2型丙酮酸激酶、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磷酸化均與PH的發病機制有關[37-38]。因此,干預HIF-1α磷酸化過程可能作為HPH的治療方法。
2.5 SUMO化 SUMO化是繼泛素-蛋白酶體修飾途徑后的又一HIF-1α的翻譯修飾途徑,類似泛素化。SUMO蛋白屬于泛素樣蛋白,由SUMO1、SUMO2、SUMO3、SUMO4和SUMO5組成,其中SUMO2和SUMO3具有高度同源性(約97%),常被統稱為SUMO2/3,二者無法通過特異性抗體進行區分;SUMO1、SUMO2、SUMO3在組織中普遍表達,SUMO4、SUMO5通常在特異性組織中表達[39-40]。
SUMO化是SUMO蛋白與靶蛋白賴氨酸殘基的共價連接。在高等真核細胞中,至少存在3種SUMO蛋白(SUMO1、SUMO2、SUMO3)和6種SUMO特異性蛋白酶(SUMO-specific proteases,SENP)(SENP1、SENP2、SENP3、SENP5、SENP6、SENP7)。SUMO化修飾需要3步酶聯反應:第一步,無活性的SUMO前體經SENP作用后變成熟,在ATP參與下與E1酶連接;第二步,進行轉酯反應并與E2酶(Ubc9)相連,結合至目標蛋白,盡管Ubc9能夠識別并與靶蛋白結合,但在某些情況下需要E3酶識別底物;第三步,在E3酶的幫助下,結合到底物。同泛素化類似,SUMO化也是動態可逆的,去SUMO化酶可以使SUMO分子與底物蛋白分離,然后重新進入SUMO化循環。目前,HIF-1α亞基被確認是SUMO-1的底物,低氧使SUMO-1的mRNA和蛋白質表達增加,SUMO-1和HIF-1α共同定位于細胞核內,SUMO化修飾后的HIF-1α的穩定性和轉錄活性增加,SENP1在缺氧期間可調節HIF-1α的穩定性,且不通過脯氨酸羥基化促進HIF-1α與泛素連接酶VHL蛋白的結合,導致其泛素化和降解;此外,SUMO化也可以作為泛素依賴性降解的直接信號[41]。ZHOU等[42]研究發現,SENP-1通過啟動HIF-1α的去SUMO化并增加其下游VEGF的表達,進而增強PASMCs的增殖能力。JIANG等[43]研究發現,大鼠HPH模型經缺氧刺激后,其SUMO-1 mRNA轉錄水平和蛋白質表達水平均升高,且該研究通過免疫共沉淀試驗證明了SUMO-1和HIF-1α之間存在直接和特異性的相互作用,SUMO-1在HPH中可以通過SUMO化而上調HIF-1α的表達。
綜上,低表達SENP-1或去SUMO化誘導HIF-1α降解可能是HPH的治療方法。
2.6 其他 蛋白激酶C受體1(receptor for activated C kinase 1,RACK1)是WD40重復蛋白家族成員,其與G蛋白的β亞基具有高度同源性。RACK1具有7葉螺旋槳結構,可結合來自不同轉導通路的信號分子,進而發揮多功能的接頭蛋白作用,包括病毒感染、神經系統發育、細胞遷移、血管生成等[44],是O2/PHD/VHL非依賴性HIF-1α調控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期研究發現,RACK1過表達可抑制PASMCs增殖,而siRNA干擾可促進PASMCs明顯增殖,RACK1可通過與熱休克蛋白HSP90競爭和Elongin-C/B泛素連接酶復合物的募集來調節HIF-1α的穩定性[45]。提示Hsp90可保護HIF-1α的穩定性,Hsp70會增強CHIP對HIF-1α的修飾作用,加速HIF-1α降解。
綜上,RACK1可間接導致HIF-1α降解增多,其是PASMCs增殖的新負調節因子,但其他熱休克蛋白(如Hsp70)是否調控HIF-1α有待進一步探究。
3 調控HIF-1α影響HPH的相關通路
3.1 PI3K/Akt/mTOR信號通路 PI3K/Akt/mTOR是細胞內的重要信號通路,其中PI3K是由調節亞基p85和催化亞基p110構成的二聚體,其在質膜上生成第二信使后可活化絲氨酸/蘇氨酸激酶Akt,然后激活其下游的mTOR[46],進而誘導細胞增殖及內皮細胞分化,抑制細胞凋亡[47],誘導新生血管形成[48]。PI3K/AKT/mTOR信號通路通過增加HIF-1α蛋白合成或抑制HIF-1α降解而促進HIF-1α的表達及穩定,而抑制PI3K/Akt/mTOR信號通路可抑制HIF-1α表達和HIF-1α靶基因的轉錄[49]。
PI3K/Akt/mTOR信號通路可通過多種途徑參與HPH的發展,包括肺動脈血管壁內皮細胞、平滑肌細胞、成纖維細胞及各細胞組分間的相互作用[50-51]。其中PI3K/AKT/mTOR/HIF-1α信號通路對PH的影響可通過沃伯格效應促進PASMCs增殖[52],影響PH進展。而PI3K/Akt/mTOR/HIF-1α信號通路抑制劑(如PI3K抑制劑Wortmannin 和LY294002,mTORC1抑制劑坦西莫斯、依維莫司和雷帕霉素等)可能為HPH提供新的治療思路。
3.2 Hippo信號通路 Hippo信號通路最先在果蠅體內被發現,其是一條抑制細胞生長的信號通路,在哺乳動物中具有高度保守性[53]。Hippo信號通路先由哺乳動物STE20樣激酶1/2和接頭蛋白支架蛋白Salvador同源物1形成一種可磷酸化和激活大型腫瘤抑制因子1/2(large tumor suppressor kinase,LATS1/2)的復合體。研究表明,LATS1/2激酶磷酸化可激活Hippo信號通路的兩個主要下游效應分子YAP和TAZ,進而調控細胞生長、增殖、存活、遷移、分化等[54]。
Hippo信號通路可參與HPH的多個發展環節,如參與調控細胞外基質的硬度變化、維持PAECs和PASMCs的增殖和遷移[55-56];而過表達下游因子YAP或TAZ可有效降低環氧化酶2和前列腺素水平,進而影響肺血管重塑[57-58];YAP可以通過增強HIF-1α的穩定性而維持HIF-1α功能,從而觸發細胞增殖等活動[59]。內皮細胞過表達YAP可與HIF-1α結合并升高其轉錄活性,促進小鼠下肢缺血后動脈細胞增殖[60]。綜上,Hippo信號通路可作為HPH的治療靶點。
4 小結與展望
目前,臨床尚未發現治療HPH的有效方法,而通過抑制肺血管增殖和激活抗增殖機制而抑制肺血管重塑可能是HPH的治療重點。多項研究發現,在HPH動物模型中給予HIF-1α多途徑抑制劑可逆轉HPH[7],如拓撲替康阻斷HIF-1α的翻譯[61],而塞拉霉素A、2-甲氧基雌二醇和地高辛減少HIF-1α蛋白質合成[62-65]。此外,芹黃素和抗CD146單克隆抗體AA98改變了HIF-1α調節通路中的特定信號分子[66-67]。HIF-1α可通過多種途徑參與HPH的調控,故干擾HIF-1α表達可成為治療HPH的新思路。
作者貢獻:郭暢、丁超偉、袁雅冬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郭暢進行文章可行性分析,撰寫、修訂論文;郭暢、丁超偉進行文獻資料收集和整理;袁雅冬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并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