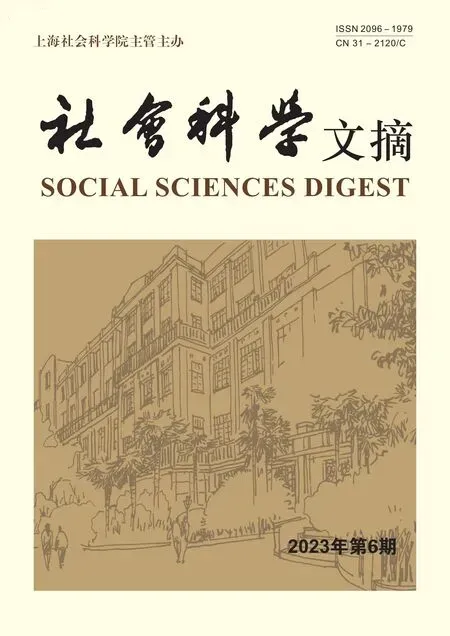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
文/張明楷
集體法益的含義
近年來,我國刑法理論開始使用集體法益的概念,并將集體法益等同國家法益與社會法益之和,或者將集體法益等同社會法益。在本文看來,倘若集體法益就是歷來所說的超個人法益、公共法益、社會法益,便只是徒增了一個概念,沒有什么意義,尤其不利于解決相關爭議問題。
集體法益中的“集體”不是法益主體,而是指法益的集合性特點。換言之,集體法益只是公共法益中被累積犯所侵犯的法益。集體法益具有三個明顯特點:第一,集體法益是所有個人都能平等地、沒有沖突地享受的利益;第二,集體法益具有不可分配性或者不可拆分性,亦即,不可能將集體法益及其部分分配給社會的特定成員;第三,集體法益雖然不可能因為個別人或者少數人的不法行為而喪失,但如果多數人實施不法行為,則會導致集體法益喪失(受到侵害)。反過來說,侵犯集體法益的犯罪便是累積犯。所謂累積犯,是指個別的構成要件行為不足以對法益造成實害與具體危險,只有同類行為大量累積之后才會造成實害與具體危險。
由于集體法益表現為非物質性法益,也不能認定累積犯直接對法益造成了實害與具體危險,于是,刑法規定這種犯罪的正當性就受到質疑。反過來說,集體法益能否由刑法來保護就需要特別論證。
就具體犯罪而言,哪些犯罪的保護法益是集體法益,需要根據集體法益的特點以及本國刑法的具體規定來確定。
第一,一般來說,侵害集體法益的犯罪是抽象危險犯,如果刑法分則將某個犯罪規定為實害犯或者具體危險犯,其保護法益就不是集體法益。據此,我國刑法第338條和第339條規定的犯罪都不是累積犯,在此意義上說,不宜一概將環境法益歸入集體法益。
第二,公共危險犯所侵犯的法益(公共安全)雖然屬于公共法益,但卻不屬于集體法益。因為侵犯集體法益的犯罪不會直接侵害某些具體個人的法益,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等)會直接侵害某些具體個人的法益,而且放火、爆炸罪對不同的個人造成的損害可能完全不同,因而能夠直接拆解成多數個人法益的集合(不具備集體法益的第二個特征);一次放火、爆炸行為就足以或者已經造成實害(不具備集體法益的第三個特征)。
第三,社會秩序或者公共秩序并不都是集體法益。雖然社會秩序是公共法益,也可以說所有個人都能平等地、沒有沖突地享受的利益,因而具有不可分配性,但并不是累積犯所侵犯的法益,因為一個犯罪就可能使個人法益遭受侵害。例如,尋釁滋事罪所侵犯的法益,不符合集體法益的后兩個特征。
第四,經濟秩序也不都是集體法益。例如,刑法分則第三章規定的金融詐騙罪以及侵犯知識產權罪,所侵犯的其實是個人法益。即使認為其侵犯的是公共法益,但該公共法益也不具有集體法益的第二、三個特征。
第五,瀆職罪的保護法益并不都是集體法益。例如,濫用職權罪一般會使特定的個人法益遭受實害,所以,本罪的保護法益不符合集體法益的第二個特征。不過,泄露國家秘密罪則大體屬于對集體法益的犯罪。
集體法益的保護必要性
(一)關于個人法益與集體法益的關系
有學者認為,個人法益與集體法益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據此,保護集體法益就減損了個人法益。但本文難以贊成這種觀點。
集體法益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沒有沖突地享受的利益。保護集體法益,是在保護了可以拆分的個人法益與社會法益(如放火、爆炸等罪)的前提下,又保護了不能拆分的個人利益。既然如此,集體法益與個人法益就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關系。
從事實上來說,刑法規定偽造貨幣罪,當然是“長”了集體法益,但不能認為由此“消”了個人法益。相反,刑法規定這種侵犯集體法益的犯罪,使罪犯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能受益(如避免接收假幣而遭受財產損失),而不是減少了個人法益。
至于值得刑法保護的集體法益,是否應當僅限于能夠“還原”為個人法益的集體法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理解“還原”的含義。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都會贊成:集體法益只能在滿足“它能夠促成人的利益”這個范圍內得到承認。所以,即使使用“還原”這一概念,也只需要采取目的還原論。從立法論上來說,保護集體法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護個人法益。從解釋論上來說,對于集體法益應當朝著被賦予個人法益的方向去理解。從事實認定來說,對一個行為是否侵犯集體法益的最佳判斷路徑,是該行為最終是否侵犯個人法益,如果得出否定結論,就不能認為侵犯了集體法益。
(二)關于個人自由與集體法益的關系
有學者認為,“集體法益以限制個人自由來維護秩序”,“對集體法益的保護不能對個人自由造成傷害,不能壓縮公民的自由空間”。但在本文看來,這樣的說法可能存在疑問。
倘若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享有自然自由,那么,法律禁止任何犯罪(殺人、搶劫、強奸),都可謂侵犯了個人自由。然而,自然狀態下的自然自由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自然狀態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交戰的狀況,違反了人謀求保全自己的天然需求,因而必須擺脫每個人充分享有自然自由的狀態。在根據社會契約每一個人讓與部分自由形成基本的法秩序之后,每個人都沒有為所欲為的自由。
從抽象層面來說,刑法設置某些犯罪,確實限制了個人自由。要求對集體法益的保護不壓縮公民個人的自然自由,是完全不可能的。問題只是在于,某種集體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護,對該集體法益的保護是否保護和擴大了除犯罪人以外的絕大多數人的自由。
其實,從刑事立法上說,個人自由與集體法益的關系,同個人自由與個人法益(以及超個人法益)的關系,并沒有什么不同。倘若認為,刑法規定放火罪、破壞交通設備罪,以及刑法規定偽造貨幣罪、內幕交易罪等,就限制了公民在法律狀態下的自由,那么,刑法規定殺人、傷害罪同樣限制了法律狀態下的自由。既然如此,上述從個人自由與集體法益關系的角度提出的反對理由就難以成立。
(三)關于集體法益的精神化、空洞化
不少學者認為,集體法益具有“精神化”“空洞化”的一面,或者認為,集體法益具有抽象性與模糊性。
首先,法益不同于行為對象,要求集體法益像行為對象一樣具有實體性是不合適的。只要集體法益具有經驗的實在性,就可以從經驗上判斷法益是否受到侵犯,就可能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
其次,不能否認集體法益具有經驗的實在性。例如,集體法益的重要部分是制度性法益, “制度雖然不是物質性的,但如果其穩定到人人都無疑可以共同利用的程度,則成為經驗的實在”。同樣,“自由的生存秩序絕不是抽象的規范秩序,其能為其成員提供具體真實的、昭然于世的自由”。
再次,刑法理論應當區分:究竟是某種集體法益本身不值得刑法保護,還是對集體法益內容的表述存在缺陷。不能因為一個集體法益可能不值得刑法保護,就宣稱所有的集體法益都不值得刑法保護。反之亦然,不能因為許多集體法益值得保護,就宣稱所有的集體法益都值得刑法保護。
最后,就真正的集體法益而言,刑法分則原本就不應規定實害結果(可以規定作為既遂標志的結果),否則就不屬于侵犯集體法益的犯罪。正是因為刑法分則的少數法條從字面上對侵犯集體法益的犯罪規定了“實害結果”,導致人們認為集體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存在判斷上的困難。
(四)關于抽象危險犯
不少學者從抽象危險犯的角度展開批判,亦即,大量增設抽象危險犯,是現代刑法中集體法益擴張的表現,處罰累積危險行為成為刑法擴張的極端形式。但這一角度的批判不一定能成立。
首先,不能因為侵犯集體法益的犯罪一般是抽象危險犯,就一概否認抽象危險犯的處罰根據。抽象危險犯存在不同類型,對任何抽象危險犯都持否定態度,明顯不當。例如,我國刑法第141條規定的生產、銷售、提供假藥罪,第246條規定的侮辱、誹謗罪都是抽象危險犯,但難以認為缺乏處罰根據。其次,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不排除各國刑法中存在過度前置化的規定,但也只能就具體犯罪提出異議,而不能一概否定抽象危險犯。最后,當刑法分則將某種犯罪規定為實害犯時,不能基于國外學說將其歸入抽象危險犯,就認為該罪的保護法益是集體法益。例如,不能因為德國將污染水體罪視為侵犯集體法益的累積犯,就認定我國的污染環境罪也是侵犯集體法益的累積犯。
(五)關于累積犯
有的學者從累積犯的角度展開了批判。一方面,累積犯導致存在沒有侵犯法益的犯罪。另一方面,處罰侵犯集體法益的累積犯,實際上是將行為人當作預防他人犯罪的工具。
首先要說明的是,累積犯與抽象危險犯不是等同概念,本文不贊成累積犯對集體法益不存在抽象危險的判斷結論,而認為累積犯至少是抽象危險犯。事實上,有的犯罪如偽造貨幣罪雖然被德國學者認為是累積犯,但如果認為其保護法益是貨幣的公共信用,則其抽象危險一目了然。其次要承認的是,如果一個行為連抽象的危險也不存在,就不得作為累積犯處罰。德國的污染水體罪之所以受到部分學者的非議,是因為該罪的成立即使就局部環境的部分要素而言,也不需要有抽象危險。德國污染水體罪所形成的問題,在我國的環境刑法中原本就不存在。最后,“在累積犯的情形下,每個人都只對自身的不法負責”。累積犯的特點是,法益最終受侵害,正是由各個人的行為造成的。刑法將這種行為規定為犯罪,只是意味著行為人要對自己實施的個別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而不是為他人承擔刑事責任。
集體法益的保護范圍
從立法論上來說,既要為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提供具體標準,也要為累積犯的成立提出判斷標準。
(一)集體法益的保護標準
總的來說,要以個人法益為核心進行選擇;具體而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一定全面),都是值得刑法保護的集體法益:
第一,當集體法益不僅是所有人可能利用,而且事實上需要利用時,這種法益就值得刑法保護。雖然事實上利用的人并不是所有人,但禁止性規定并沒有侵犯理性個體享有的自由時,該集體法益也值得保護。此外,如果某種行為嚴重妨害了他人對集體法益的平等利用,也是對集體法益的嚴重侵犯,具有實質的處罰根據。如果只是部分人才可能利用的狀態或者條件,就不可能通過限制多數人的行動自由來保護這種狀態或條件。
第二,當集體法益表現為由部分組成的形態,對集體法益的侵犯已經使集體法益的局部或者部分受到侵害或者存在具體危險,應當保護該集體法益。例如,即使退一步從全國范圍的所有環境要素的角度認為污染環境罪屬于抽象危險犯,所保護的是集體法益,但全國范圍的環境是由各地的環境所組成,所有生態要素由各個具體的要素組成,所以,只要行為對局部環境的部分環境要素產生了實害或者形成了具體危險,就可以作為犯罪處理。
第三,當集體法益實際上是許多犯罪背后隱藏的法益,即背后層法益,對集體法益的侵犯,表現為對顯在法益或者阻擋層法益的實害或者具體危險時,刑法應當保護該集體法益。例如,并非任何一個具體的偽證罪就會使整個刑事訴訟司法活動處于混亂狀態,就刑事訴訟的正常司法活動而言,偽證罪只能產生抽象的危險。而且,如果所有的證人都作偽證,必然導致刑事訴訟活動難以進行。在此意義上說,偽證罪保護的法益是集體法益。但是,如果將刑事訴訟中的證明過程的客觀真實性(純潔性)作為阻擋層的保護法益,偽證罪就成為實害犯。只有保護了證明過程的客觀真實性,才能保證刑事訴訟的正常活動。
第四,侵犯集體法益的行為同時會直接或間接對個人的其他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具體危險時,刑法應當保護該集體法益。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對集體法益的保護幾乎等于對個人其他法益的保護,而且個人法益值得刑法保護,只不過個人法益與集體法益的內容不同。例如,使用假幣罪雖然侵犯的是貨幣的公共信用,但同時直接侵害了個人(不知情接收者)的財產法益。
第五,當集體法益是個人法益的重要保障或者必要條件時,刑法應當保護該集體法益。“首先可以想到的具有集體性形態的必要條件,就是國家的存在及其功能性運作。”刑法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罪與危害國防利益罪,就是完全必要的。其次可以想到的具有集體性形態的必要條件,是國家的重要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及其功能性運轉。國家的重要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及其功能性運轉,是國民平等地享受、獲取相關利益的必要條件。
(二)累積犯的成立標準
從累積犯的角度來說,問題主要在于三點:(1)累積犯本身是否具有抽象危險?(2)如果不禁止該行為,較多的人是否會實施該行為?(3)如果較多的人實施該行為,是否會對集體法益造成實害或具體危險?
關于第1點,只能將具有抽象危險的行為規定為累積犯,而不能將所謂抽象危險之前的危險作為累積犯的處罰根據。累積犯并不是多數行為的累積才形成抽象危險,而是多數抽象危險的累積會對法益造成實害或具體危險。
對于第2點,要從實施行為的獲利(滿足)概率以及獲利多少(行為的獲利性),實施行為的成本大小、難易程度(行為的容易性)等方面,判斷他人效仿的可能性大小(行為的蔓延性),進而作出判斷。
對于第3點,需要從因果性的角度進行判斷。即使某項法益是重要的,但如果這種法益絕對不可能受到侵害,則不需要由刑法進行保護。所以,在確定了哪些集體法益值得刑法保護之后,還必須判斷集體法益最終究竟能否受到侵害,刑法能否對集體法益進行有效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