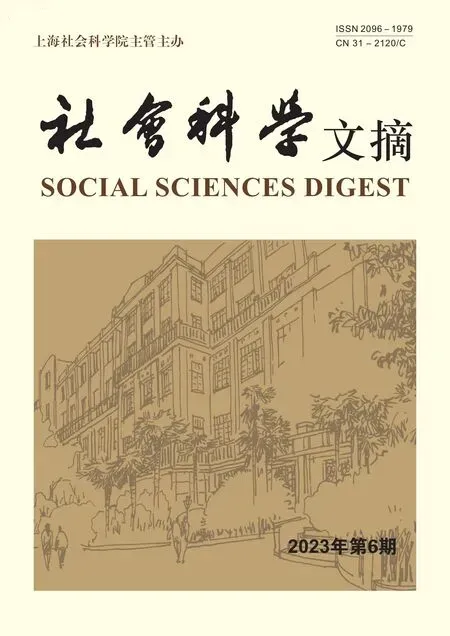中國多民族“語言—文學”譜系與比較研究的拓展
文/劉大先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為自在的歷史事實源遠流長,但作為自覺的文學生產和學術分科,則要晚至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不是由某種超越于歷史實踐的純粹個人趣味所決定,其正當性和學理性,建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本土文化實踐:一方面致力于多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另一方面著眼于新興文化的創造與發展。既有的相關研究中,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母語、多語和雜語現象,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同其他語種文學的翻譯與傳播,往往缺乏具體細致的資料梳理。本文嘗試從中國多民族文學的語言譜系入手,勾勒其文學地理的版圖演進,在此基礎性之上討論比較研究的推進。
重識“中文”
由于語言文字的豐富性且不斷地演變,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權威機構或組織能夠精準確認現存的中國各民族語言有多少種。大致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目前有130多種語言,其中少數民族語言分屬漢藏、阿爾泰、南亞、南島、印歐五個語系,地理分布復雜。它們的使用有如下四個特點:
(一)使用人口數量相差很大,壯語使用人口最多,超過千萬,而赫哲語使用者不足百人。(二)阿爾泰語系和印歐語系的語言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區,其他幾個語系的語言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區。(三)語言與民族交叉。有的民族使用一種以上語言,也有不同民族使用相同語言。如瑤族使用勉、布努、拉珈三種語言,裕固族使用東部裕固語、西部裕固語兩種語言。使用多語言的,相互間差異比其中的一種與另一民族語言相互差異還大。如景頗族使用景頗語、載瓦語等不同語言,兩者差異很大,分屬不同語支,而載瓦語與阿昌語接近,同屬緬語支。(四)語言內部差異不同。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等語言方言差別較小,彝語、哈尼語、苗語等語言方言差別大,互相甚至不能通話。另外,從結構特點來說,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具有典型的綜合—黏著型語言的特征;漢藏語系的侗傣語、苗瑤語具有比較典型的分析—融合型語言的特征,藏緬語族的一部分語言(藏、羌語支語言)保持綜合—黏著型語言的特征,一部分語言(彝、緬語支語言)有分析化的傾向;南亞語基本屬于分析型語言;南島語屬于黏著型語言。迥異的語音、構詞法和語句構造,直接體現在中國多民族文學表述上,在節奏、韻律、抒情方式和表意方式等方面呈現出萬象共生的景象。
這種情形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思“中文”的意涵。根據現有法律條款規定,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是中國推廣使用的語言文字,國家機關以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為公務用語用字,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國家機關,依據其自治條例,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幾種語言文字。“中文”作為統稱,既包含了國家通用語文(普通話、漢語文),也包含了各種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中文”是“漢語”“漢文”加上其他多民族語言文字。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中文”同“華文”及“華語”的區別。在“華文文學”的表述中,往往突出作為主干的漢語,忽略同樣作為中文構成的其他各民族語言。“華語語系”話語也同樣如此,即便意識到漢藏語系的內部復雜性,但阿爾泰、南亞、南島和印歐語系中的語言則不被視為中國語言,至少在關于“華語語系”的討論中是被擱置的。后殖民主義式的思維慣性,會將漢語同少數民族語言類比為歐洲宗主國語言與殖民地語言的關系,這是對當代中國語言格局與權力的無視。在解構“離散”的視角中,易于將漢語/中文同少數民族語言進行二元對立式的假設,無形中則在解構近現代以來艱難建構起來的“中華民族”認同,至少未能從語言持有者的內部眼光來看待相關問題。
中國文學的多元整體譜系
現代漢語(國家通用語)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不斷吸納了各民族的語言成分,由現代文學確立起典范的使用規則,經過了現代語法的改造,已經不同于古漢語漢文,本身就是一個包容了各民族元素的語言,并且在新的語言文學創造中不斷更新。同時,為中國少數民族使用的多民族語言文字,很多也為其他國家、民族、人群所使用,它們也在歷史進程中演進與變化。基于對多民族語言歷史與現實的考察,本文認為“中文”的內涵與外延需要擴大為一種以漢語文為主體、多民族語言共生的理論自覺。這是一種“大中文”,只有認識并理解這個前提,對于中國文學的多元整體性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把握。
人類學家博厄斯在考察不同地區和種族的人群之后,條分縷析地論述過語言是最自發的人類行為,在某種層面來說,“文化決定語言”,但“除了語言形式將受文化形態的改造——而不是某種文化形態受語言形式特征的制約——之外,一個部族的文化與他們的語言并無直接關系”。博厄斯的文化相對主義,對薩丕爾影響甚大。薩丕爾認為“言語似乎是通向思維的唯一途徑”;沃爾夫則更推進一步,認為“思維的問題是語言的問題”。也即,不同語言在結構、意義、詞匯和使用等方面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使用者的思維方式,這便是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是一種語言相對論,從人類學、語言學輻射到哲學和文學,被廣為接受,特別是在美學和文藝理論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幾乎成為一種毋庸置疑的前提。對于文學而言,它則成了一種語言決定論,決定了文學主體的思維方式、情感結構,進而影響到美學趣味和表達樣式。這是假說,卻并非真理。在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的推進中,語言之于文學的影響及其限度需要詳加辨析。
需要指出:(一)語言與民族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族群、文化、語言并不一定具有同樣的演變經歷,“一個民族可以保持同一類型(解剖特征——引者按)和語言而改變其文化;也可以保持同一類型而改變其語言;或者,還可以保持同一語言而改變其類型和文化……某一特定民族在其整個歷史上定然一直是這一語言的傳輸者的假設;以及這一民族必定一貫具有某種文化的假設,都完全是主觀武斷的假定”。(二)語言本身也一直在不斷吐故納新地演變中。在人口與信息交流不太發達的前現代“超穩定”社會,語言、文學傳播與變遷速度緩慢,而伴隨著工業革命后的近現代政治、經濟、貿易、技術的發展,傳播與變遷的速度加快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之間的關聯,需要在長時段中進行考察。
中國多民族共同創造了文學的豐富圖譜,漢語言文學是其中的主干,而各少數民族則是其枝葉。主干與枝葉之間是彼此共生的關系,僅就不同少數民族以各自語言創作的口頭與書面詩歌而言,貫穿于從先秦到當代的始終。某些少數族群口頭文學,經由漢文記錄、修飾和翻譯,已經成為中華文化與文學主流敘事的組成部分,無論從美學趣味,還是所表達的觀念來說,都是在中央帝國意識形態正史系統里以華夏為中心的表述。亦有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解讀的古代族群語言作品。它們屬于在主流語言中未歸化的存在,當這些散佚在史籍中的少數民族文學史料在歷史敘述中被爬梳剔抉出來,作為主流文學之外補苴罅漏的存在,就會同主流漢語文學的文學觀念和形式的規定性形成參差的對照。
與歐美多族群國家中的“少數族裔”不同,中國少數民族成員除了在人數上較少,在公民權包括語言權利上同漢族并無區別,甚至在特殊情況下有相關的優惠政策:少數民族口頭文學與書面典籍得到整理、傳播、發揚,保留了大量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遺產;無文字的少數民族得到幫扶,制訂出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出版、刊物的創辦,少數民族文學獎項(國家級的駿馬獎及其他各類地方性和刊物獎項)的設置,少數民族作家的培養,等等。
在民族平等的政策語境中,語言與文學的多樣性,使得中華文化內部具有彼此輸血、相互促進的活力。因而,中國文學的多元整體性體現在書面文學與口頭文學并重、漢語文學與少數民族母語文學共生的局面。多民族的母語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多元構成,至少在兩個層面上具有補充、充實、創造的功能。其一,它們各自以其具有地方性、族群性的內容,保存了不同文化、習俗、精神遺產的傳統。它們的多元性存在打開了漢語言文學之外廣闊的文學空間。其二,掌握母語同時又掌握第二、第三種書寫語言的作家,會將母語思維帶入書寫語言之中,讓傳統的母語書寫文學、民間口頭文學滋養著當代作家作品。后一點尤為重要,從縱向歷史發展來看,是對于傳統母語文化的承傳創變,革故鼎新;從橫向的現代進程來看,為現代漢語的發展起到了促進和變革的作用,帶來了新質,豐富了現代中文寫作的內容和形式。中國的多民族以其語言傳統和新興的母語文學創作在中國文學內部構成了本土話語的張力,讓中國文學的話語模式和思維空間不再局限于主干漢語文學,同時也具備了超越西方式民族國家文學的意味。
多民族語言文學之于世界文學的意義
中國語言—文學譜系的多元性,尤其是多民族文學以一種“不同而和”的獨特構成,在保持各自差異性(不同)的同時,追求和諧的交融共生(和)。從中國文學內部來說,多民族、多語種所帶來的是從形式到觀念的“多文學”風貌,從而使其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當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的差異性在同主流漢語文學進行互譯、傳播、影響、交流、接受時,固然有著翻譯的權力與政治問題,但通過差異互補、差異中介和差異促生,無疑共同造就了今日作為“效果歷史”的中國文學風貌,進而形成了中國形象、中國故事的多樣表述。置諸世界文學領域,中國文學的“不同而和”映照出“和而不同”的總體生態。
中國境內約有30個跨國/境/界民族(分別在兩個或多個現代國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包括朝鮮、鄂溫克、赫哲、蒙古、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烏孜別克、俄羅斯、塔塔爾、維吾爾、回、藏、門巴、傣、彝、哈尼、景頗、傈僳、拉祜、佤、德昂、怒、布朗、獨龍、壯、布依、瑤、京、苗等。“中國”與“世界”早已彼此涵納。“中國文學”內含著的跨語言、跨民族、跨文明的特質,本身便充滿了“世界文學”因素。這個世界文學因素,有著漫長時間的東亞與東南亞、中亞、西亞文化交流融合的歷程,在近現代以來更是加入了由歐洲殖民現代性傳播而來的西方現代文學滋養。
語言連帶著文化,從語言的角度切入,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研究會成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增量,體現在文類體裁、經典和經典化、世界觀與宇宙論、性別意識、生態觀念等諸多方面。面對中國文學的多樣性現實,大多數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有意突破歐美比較文學的模式,贊成在一國之內的多民族文學比較也屬于比較文學范疇。這種具有“中國學派”意味的比較,至少可以分為三個維度:
一是主流的漢語文學同少數民族語文學的譯介與變異。在不同歷史時期中,中國少數民族使用并創造過多種文字,那些古民族語文記錄的古籍文獻,也成為中國文學的寶貴遺產。無文字的民族則留下了許多口碑文獻。 許多口頭文學類型,如史詩、傳說故事、抒情歌謠等,至今仍然口耳相傳,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機組成部分。漢語言文學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互譯,體現了中國文學內部的動態生機。在譯介到漢文中時的選擇與潤飾,隱含著語言—文化的權力關系,從中既可以看到少數民族原生的觀念,也可以看到漢文尤其儒家文化的潛移默化。
二是少數民族文學同他國、他民族文學之間的比較。其中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同一語言和民族的本土與離散文學書寫,將國內外散居的少數民族母語文學作比較,可以對主體、認同、歷史、傳統等全球性共通話題有更深刻的認識;另一種情形則是不同語言和民族之間的文學比較,涉及文類、體裁、美學觀念等諸多方面。正如語言從來都生生不息、變遷不已,文學也并非靜止、凝滯、僵化的存在,將少數民族文學同域外少數族裔作家作品進行比較,會發現關于文化記憶、離散經驗、代際沖突等人類共通主題,也可以窺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域外少數族裔文學在政治和觀念上的差異。
三是少數民族文學彼此之間的比較。如“三大史詩”的比較研究,維吾爾族古代經典同漢儒經典的比較等。另外,由于很多少數民族沒有文字,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創制的拼音文字也大多使用率不高,所以在很多少數民族書面文學采用國家通用語文之外,口頭文學依然是少數民族文學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中國多民族文學還呈現出口頭文學、書面文學與新興的多媒體電子文學并行的狀態。少數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因此生發出相應的學術命題,如口頭文學向書面文學的轉化、民族民間文化的影響、媒介融合時代的多民族文學傳承等議題。
凡此種種,從中國多民族“語言—文學”的視角切入比較文學研究,顯示了以中國話語理解、改造與界定自我與世界的實踐,從而打開了重新認識“世界文學”格局。少數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同近現代世界觀和認識論轉型互為表里。在文化傳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由少數民族所帶來的視角轉換,激活了一度沉寂的中國多民族文學遺產,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學地理,讓“世界”的圖景更加完整,也成為建構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一種有效途徑。“世界文學”的新視野,對于重新認識中國文學,理解其同亞非拉文學之間的淵源,重建亞洲與歐美文學的結構性關系,進而構造一個超越性的文學理想,想象一個更美好的文學未來生態,都有著莫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