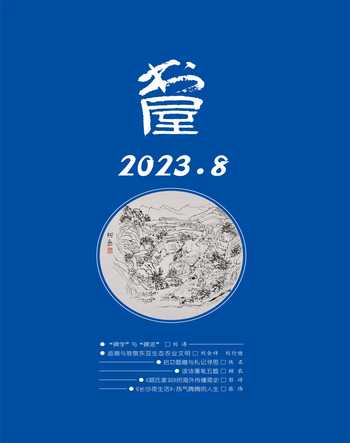《長沙夜生活》:熱氣騰騰的人生
張偉
從電影院出來,我眼圈濕潤,有點不好意思。跟同來的一位姐姐一交流,她竟哭濕了一包紙巾。我們倆都趕緊自我解嘲,年紀大了,笑點低,哭點也低。不過哭濕一包紙巾也太夸張了,像我,頂多哭濕了手背。因為我以為這是喜劇片,壓根兒沒準備紙巾啊。
要說為什么哭了,笑了,我也說不上來。可能就是那里面人與人之間的熱氣騰騰的情感,讓我瞬間代入進去了。
可能是景為為跟何西西在書店里邂逅,彼此討論小板凳與自由時,讓我想起大學三年級遇到的那個男孩子,他送給我一本厚厚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回贈給他一本葉芝的詩集。那時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每天激烈地討論莫名其妙的哲學、文學、人生問題。所以當我看到景為為和何西西的前幾句對話時,一身雞皮疙瘩都要下來了。果然是年輕人,現在我們再也不討論這些話題了,天天只聊買菜接娃。可是,看著他們倆在深夜里走來走去,從彼此提防到卸下防備,從互相安慰到彼此扶持,以及天明時何西西決定留下來的那一剎那,我看到了希望。成長是帶著傷痕的過程,也是自愈的過程。跟自己和解,跟父母和解,跟愛人和解,最后,才能讓傷口愈合,真正堅強,否則,執拗地守著過去的痛,只會讓自己深陷其中。
可能是看著從小生活在重組家庭里的何岸那么用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卻不被認可,不被父母看好,不被同行理解的樣子,我想到了自己曾經度過的那些人生至暗時刻。當爸爸跟他說“對不起”,說“你是我的兒子”時,我的眼淚瞬間流滿了臉頰。我曾經也得到過這些道歉,可我真的能像何岸那樣,對過去瞬間釋然,帶著爸爸去媽媽店里吃夜宵嗎?我捫心自問,也許不能,我做不到。感情被傷過了,想要修復,好難。可是看到麗姐為前夫、前夫的孩子、自己的孩子還有客人在深夜廚房里忙碌,煮出一碗碗熱氣騰騰的粉,坦白說,我是有些被治愈的。幾十年了,該恨的,都恨過了,麗姐有了旭哥,孩子也懂事了,她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再看到那個當年恨之入骨的人,罵一句,也就算了。吃碗粉,一切坎兒都會過去,一切會好起來的。
可能是看到那兩個分別來自西北、東北的孩子鉆在摩天輪的轎廂里互相傾訴、彼此安慰的時候,讓我想起當年做家教,在湘江大橋回望河西大學城,默默希望在這個城市里有一個小小房子的自己。我想告訴這倆孩子,堅持你的夢,你會實現的。盡管現在的我總相信生活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遇到了挫折輕輕笑一笑就過去,可別笑話孩子們。他們的夢,是支持他們走下去的勇氣。他們能走多遠,不在于現實能給他們多少,而在于他們能把自己的夢在現實生活中延長多少,直到有一天,發現夢已經實現時,他們該多開心啊!
大排檔里有那么多小人物,每個人都在生活中找得到原型。合伙的,吵著要分;畢業的,唱著“長亭外,古道邊”,淚流滿面;分手的,又哭又笑;喪偶的,孤獨地吃著老伴兒生前最愛吃的米粉……這些,不都是咱們生活里遇得到的張三李四王五嗎?很可能,就是我們自己。只是我們自己的故事,沒福氣被搬上銀幕去。
網上有人評論, 《長沙夜生活》不該叫這個名字,原來的名字《群星閃耀的夜晚》多好。但我其實蠻喜歡現在這個名字。群星閃耀,那是屬于另一種生活,那生活離我們有點遠了。在長沙,你晚上能看到多少星星?抬頭看星空,能看到十幾顆就不錯了。這是一個霓虹燈照亮的城市,注定沒法兒群星閃耀。它是一座煙火氣十足的城市,生活著像你我一樣的普通人,有著和故事里的人一樣熱氣騰騰的情感,累過、傷過,也愛著、被愛著。有人說《長沙夜生活》讓人聯想起城市文化宣傳片,一下就掉了檔次,既不商業,也不文藝。我不這么認為。城市文化不能宣傳嗎?不該宣傳嗎?這么好的城、這么好的人,宣傳一下,是長沙人的驕傲(雖然我不是長沙本地人),也是國人的驕傲。世界是多元的,北上廣值得宣傳,縣城隆回值得宣傳,難道拍部片子宣傳一下長沙,就得藏著掖著?
昨晚躺在床上,我想起《清明上河圖》。宋代那么多畫種,張擇端怎么就選擇畫這么一幅畫呢?它不是花鳥、不是祥瑞、不是山水,只是一群市民,一個熱熱鬧鬧的街市。你看他,把每個幌子都畫得清清楚楚的,把每個人的表情、動作、神態都畫得那么細致入微。雖然宋代有工筆畫的傳統,但這樣去畫老百姓的群像,恕我孤陋寡聞,至少現存的,這是唯一的吧?我私下揣摩,那時候沒有電影,沒有手機,要不然,張擇端會選擇去當個導演,當個攝影家。他的初衷,就是想給這活色生香的百姓生活留一個念想吧?讓千年之后的我們,打開這幅卷軸就知道那個時代里的那些人是怎樣活著的。假如他穿越到現在,會是個好導演的,我相信。
張冀,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