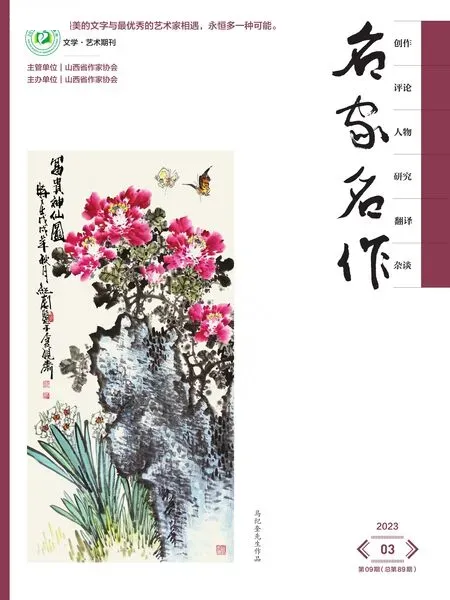約書亞·里夫金談巴赫① 譯者注:這篇采訪是由Uri Golomb 所寫、Michael Robert Williams 拍攝,于2000 年12 月1 日發表在Goldberg 雜志(已停刊)上。
宋 鴿
在“早期音樂”學界,不乏知識淵博的學者型演奏家,但像約書亞·里夫金②譯者注: Joshua Rifkin,美國著名的音樂學者、指揮家、鋼琴家和作曲家,1944 年出生于紐約市。Rifkin 是巴赫音樂的專家,他的研究重點是巴赫的鍵盤音樂和聲樂作品,特別是清唱劇。作為指揮家,Rifkin 主要以指揮巴赫的音樂而聞名,他曾領導了許多巴赫合唱團和管弦樂團的演出,尤其是指揮小型合唱團和室內樂團演繹巴赫的音樂,這一演出方式在巴赫音樂演出中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應用。除了指揮和學術研究,Rifkin 還是一位杰出的鋼琴家和作曲家。他的創作涵蓋了許多不同的音樂風格,包括流行音樂、爵士樂和古典音樂。他還是一位多產的錄音制作人,推動了很多音樂作品的錄制和發行。這樣在兩個領域都取得了同等成就的音樂家則為數不多。作為一位指揮家、古鋼琴和鋼琴演奏家,他的常規曲目涵蓋了自文藝復興開始的聲樂音樂,從巴赫、亨德爾,到喬普林、斯特拉文斯基和Revueltas③譯者注:Silvestre Revueltas(1899—1940)是墨西哥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指揮家和小提琴手。,等等。里夫金制作的音樂具有驚人的清晰度和音樂性,不僅注重細節,同時又具有非凡的流暢性——能夠讓音樂自然而優美地流淌。作為一名音樂學家,他經常打破傳統假設,憑借著歷史證據的基礎,對音樂進行深入分析;將已知事實、合理推斷和未被證實的假設區分開來;基于此種周密的思考,源源不斷地進行著開創性的研究。
在許多人心中,里夫金是一位單一領域的音樂家。他是第一位聲稱巴赫的合唱音樂大部分是為一組獨唱者而寫的學者,并且也是第一位相應地演奏該類作品的指揮。他的這一理論在20 世紀80 年代引發的爭議至今仍然存在,盡管近年來里夫金的研究結果越來越受到學界的認可,但對他來說,這種持續的爭議是有點惱人的。他說:“20 年過去了,人們對這件事情過于重視了。早就該讓它消逝于塵埃,而去追求由音樂發展而來的更有趣的問題。對于像 Parrott、McCreesh 和Kuijken 這樣的人來說,這幾乎不值一提。這就像是在問:“嘿,伽利略先生,您怎么看待那些仍在爭論太陽是否繞地球旋轉的人們?”一點意義也沒有!音樂的創作涉及很多其他的東西。
這次采訪主要基于我與里夫金的一次對話,當時我正在撰寫關于巴赫《B 小調彌撒》錄音的論文,始終聚焦在巴赫的音樂和他音樂中演奏的力量。隨著里夫金最近出版了新版本的《B 小調彌撒》,這個話題依然相關;不過,我試圖將這個話題放在里夫金更廣泛的成就、興趣和哲學的背景下來探討。
Uri Golomb:作為演繹巴赫宗教音樂作品的藝術家,您并不與巴赫有宗教信仰的共鳴,這是否對您的演繹有所影響呢?您認為了解巴赫的神學對演繹者來說重要嗎?為什么?
約書亞·里夫金:很顯然,如果我認為與巴赫宗教信仰的共鳴是以演繹他的宗教音樂作為先決條件,那么我就要非常徹底地改變我的生活:要么成為一名18 世紀的德國路德教教徒——這是真正的“歷史演奏實踐”;要么就放棄演奏巴赫。當然,了解巴赫的宗教信仰并不會有什么壞處——就像了解德語(甚至可能更重要),或者,略微改變領域,如果你指揮《巴比倫王納布科》的話,了解意大利復興時期的政治是必要的。實際上,我已經吸收了不少18 世紀路德教的文化。我了解贊美詩,了解德語的《圣經》甚至好過英語的《圣經》等。但是,在音樂中要理解的是蘊含在音符之間的語言——事實上,正是這種音符內部的語言,而不是宗教,吸引著幾乎所有人對巴赫的熱愛。
不可否認,對于這種用音符譜寫的語言,某些文化背景的人會比其他人更容易理解一些;維也納人聽著圓舞曲長大,憑直覺地比我們更能“搖擺”它的節奏。但是這些差異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把它們作為原則只會讓你陷入有害的身份政治領域。我的意思是,難道只有奧地利和波西米亞猶太人才能演奏馬勒嗎?只有非裔美國人才能演奏爵士樂嗎?只有德國反猶主義者才能演奏瓦格納嗎?
另外,“共享巴赫的宗教信仰”實際上指的是什么?對上帝的信仰?對耶穌的信仰?還是對路德在18 世紀的神學思想的信仰?我不認識任何人規定這是演奏巴赫音樂的先決條件;那么我們應該從哪里劃線呢?任何音樂家都具有某種形式的靈性;就讓我們在此結束吧。
Uri Golomb:您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鍵盤演奏家,同時也是指揮家。您與一個小型室內樂團演奏巴赫的音樂,這種音樂可以在沒有指揮的情況下演奏,不過您仍然登臺指揮。您如何回應那些認為指揮的存在在這些曲目里本就是過時的人?
約書亞·里夫金:我認為這種說法充其量是一種過分簡化。現代管弦樂的指揮家指的是——掌握著全方位的控制和解釋權威的概念——這在18 世紀是不存在的。但指揮本身是存在的,解釋權威也是存在的。當一個意志堅定的作曲家,比如巴赫,在指揮自己的音樂時,怎么可能不是解釋權威呢?無論如何,歷史演奏的主要關注點不在于演奏條件——我們不是在試圖回到沒有暖氣的托馬斯教堂,在寒冬的清晨演奏,雖然那樣可能也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有用的見解,但我們最主要的興趣在于探尋聲音和風格方面的問題。
當然,不同的曲目需要不同的演奏方法: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需要比巴赫的任何曲目都花更多的時間打拍子;馬勒的音樂似乎以某種方式預設了強有力的指引,而這些可能是早期音樂所不需要的;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或瓦格納的《女武神》不會簡單地從一個群體潛意識中產生。此外,我實際上并不指揮我們演奏的小型作品。但無論力度強弱與否,許多潛在問題——尤其是一個指揮應當有多大的控制權力,下達命令與合作激勵之間的確切關系等——在各個方面仍然存在。
Uri Golomb:有些人批評您,還有大多數使用“一人一聲部”的合唱團成員,認為你們不夠進取,即“堅持”使用女高音和男高音,而不是像巴赫那樣使用男孩童聲。
約書亞·里夫金:首先,這種批評假設執行“一人一聲部”這一決定基本上是一種考古學決策,更多地受到重現過去的愿望驅使,而不是為任何可能的音樂考慮。真是胡說八道!話雖如此,如果我們擁有像巴赫那個時代最好的男童高音歌唱家,我想我本人也會使用他們的。但是,由于訓練方法的變化,更不用說男孩們變聲年齡的提前,我認為18 世紀的男童高音已不再存在,就如另一種廣為人知的18 世紀男高音的處境一樣。此外,我認為男孩唱的童聲女高音在合唱音樂會中并沒有扮演重要角色。
無論如何,有證據強烈表明,巴赫和其他人之所以使用男孩,是制度原因而并非音樂,并且只要其他任何類型能夠勝任女高音他都樂于使用。對于巴赫來說,男孩的童聲女高音、閹人歌手和假聲男高音之間的區別,其重要程度可能只是與P rschmann、Eichentopf 和Denner制作的雙簧管之間的差別一樣重要。
Uri Golomb:無論如何,您似乎并不在所有的演出中都追求歷史演奏的真實性(無論如何定義)。以一個極端的例子為例——您曾經在英格蘭的三教區音樂節上①譯者注:三教區音樂節(The Three Choirs Festival)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音樂節,它由英格蘭的三個教區合唱團共同主辦,這三個教區分別是威爾士的格洛斯特教區、英格蘭的赫里福德教區和英格蘭的韋爾斯教區。該音樂節每年輪流在這三個教區的大教堂舉行,始于1715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音樂節之一。用英語上演了《馬太受難曲》,并且使用了全編制合唱團——這或許是您有意違背作曲家意圖的情況之一。是什么激勵了您進行這場演出呢?
約書亞·里夫金:三教區音樂節邀請我演出《馬太受難曲》是在我和巴赫室內樂團參加BBC 晚會兩年后的事情。很明顯的是,他們希望實現更具巴洛克風格的表演,但我認為,與其試圖用不適合的編制開展一種“啟蒙性的”“巴洛克式的”表演,不如更有趣地參與這個音樂節悠久、高尚和迷人的傳統。Ivor Atkins②譯者注: Ivor Algernon Atkins(1869—1953),英國作曲家、合唱指揮和風琴家。和 Edward Elgar③譯者注:Edward Elgar(1857—1934),英國作曲家,被譽為“英國音樂的國父”。曾為音樂節準備了一份《馬太受難曲》的英文版本,這個版本在英國已經成為英文標準版的《馬太受難曲》。 Novello④譯者注:英國著名音樂出版商和劇院公司,由W.W. Novello 在19 世紀初創立。如今提供了現代制作版的 Elgar/Atkins 版本,對這個版本我曾試圖追溯其來源。大教堂檔案館的人給了我訪問他們所有材料的權限:舊的節目單、詳細而豐富的新聞評論、一個年輕的合唱團成員在音樂節前跟隨 Atkins 學習《馬太受難曲》時留下的筆記,記錄了他們討論的一切。 Novello 為我們弄到了一套舊的分譜。我指揮的合唱團可能還不夠大,但我們有鋼琴演奏的持續低音,我們還保留了原始的片段,用英語演唱,以及盡可能多地獲取他們當時的速度,等等。一旦我們獲得了這些信息,我們就有能力自己研究。我不是試圖重建古老的表演,但是像歷史演出一樣,我試圖“插入”某個過去的點,越過之間發生的許多事情。
那是一次美妙的經歷,我非常喜愛它。顯而易見的是,其結果是一場后現代主義的、后歷史主義的表演。20 世紀和19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巴赫演奏的詮釋都是基于對巴赫所謂愿望的追求;即使是支持用鋼琴而不是大鍵琴演奏鍵盤作品的論據也是以巴赫“真正”想要什么為框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現在已經從中解放出來了。正是適當的“歷史性”表演的成功使我們得以自由地做其他的一切——只要我們沒有自欺欺人。
Uri Golomb :在《巴赫的合唱理想》①譯者注:原著Bach’s Choral Ideal,中文版《巴赫的合唱理想》于2002 年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您寫道:“對于合唱的規模和配置的考慮,遠遠不只是涉及如何實現的問題,它們直接關系到巴赫音樂構思的核心。”換句話說,這不僅僅影響了音樂的聲音,還影響了它的意義。您能詳細說明一下嗎?
約書亞·里夫金:在我們使用傳統的“合唱”力來演奏巴赫的作品時,我們在許多方面都不知道這些作品的真正內涵。現在我們正在揭示這一點。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自大,但我會堅持這一觀點:即通過對原始樂譜的研究,我們獲得了自己對音樂的解讀,這是自巴赫時代以來一直被掩蓋的。
對我和我合作的音樂家而言,從合唱到“一人一聲部”這樣一種過渡,引發我們重新審視音樂演奏的所有方面。你不能僅僅減少歌唱家的人數而不改變其他任何東西,并期待從中得出任何可行的結果。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演唱方式,比如線條的塑造、文本的表達以及音響平衡等。這種改變也影響了速度、聲樂/器樂的平衡、器樂樂器的分句和發音等方面。然后我們必須將所有這些細節重新整合成一個連貫的整體。最終,這些作品的身份認同對我們而言也發生了改變。
現在,我無法以各種方式量化這一點,但我可以舉個例子。以《馬太受難曲》的開頭樂章為例,該曲主要由兩個不同的聲樂組組成,每個聲樂組由四名歌手組成。起初,兩個聲樂組以對話方式進行,但并不一起演唱。然后,在第73~75 小節,他們合并為一個合唱:整個音響突然從一人一聲部變成了兩人的雙聲部,這就創造出了一個美妙的戲劇高潮。而當每個合唱都已經由雙聲部組成時,兩個合唱團分開唱和一起唱的區別其實根本看不出來——這樣的話戲劇效果也就沒有了。
當然,這只是在使用巴赫所想的配器時得到的某種關于彈性演繹的一個例子。與其說是一個獨唱者或一個完整的合唱團,不如說你獲得了一個巨大的可能性范圍,從而產生了更豐富的音響、權衡和表現手法。對我來說,舊的演奏方式會導致音樂的貧乏。
Uri Golomb:您曾經說過,您預計室內樂合唱團/古樂器組合將像巴赫琴弓一樣消失因為它是一種被標榜為歷史重建的創新,一旦被證明是沒有歷史根據的,就幾乎消失了。您真的相信或希望合唱團在將來停演巴赫的作品嗎?
約書亞·里夫金:我熱愛合唱團,它們是多么美妙的一種團體,能夠演繹出美妙的音樂。如果沒有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和貝多芬的《莊嚴彌撒》,我們會在哪里呢?(順便說一下,我的一個同事怎么可以對“我的”小合唱團在巴赫的演唱上做出諷刺的評論,然后只用40 名歌手演唱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呢?用一種一刀切的方式對待所有作曲家——40 名歌手演唱巴赫,40 名歌手演唱勃拉姆斯嗎?這是荒謬的——勃拉姆斯需要150 名歌手:我從未以這樣膽大妄為的方式對待勃拉姆斯的作品。)
合唱團習慣于考慮大范圍的音樂史——從14 世紀開始——是他們的領域。大多數這種曲目并非為他們而寫,但如果他們想演出——那也很好,只要不自欺欺人。鋼琴和大鍵琴之間的古老戰爭已不再是一場斗爭了:很少有鋼琴家會嚴肅地聲稱當他們演奏巴赫的音樂時在他們的樂器上實現了巴赫的意圖。但一旦這場戰斗結束了,人們就可以自由地說“但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整個事情”,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我在三教區音樂節上演奏《馬太受難曲》時所做的,也是我現在用現代鋼琴演奏巴赫時所做的。
如果合唱團及其支持者能夠說:“看,我們知道我們做的事情是巴赫從未想過并且可能會討厭的。但這并不重要,因為我們喜歡它。我們今天還活著,我們有這些傳統和活動,這對我們很重要。”那么這將是一個更加健康的局面。但我們大多數人仍然想說:“巴赫真正想要的是我所做的和喜歡的。”而很難說:“我才不在乎巴赫的那種方式。我非常珍視他的音樂,但我不關心他的意愿。”我們仍然不是足以擺脫這種想法的后現代主義。但是,如果人們能夠面對這一點,那么讓一百朵花綻放,讓一百種巴赫演繹流派興盛。也許在40 年后,現代合唱團與古樂器的結合將足夠歷史悠久,變得越來越有趣——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