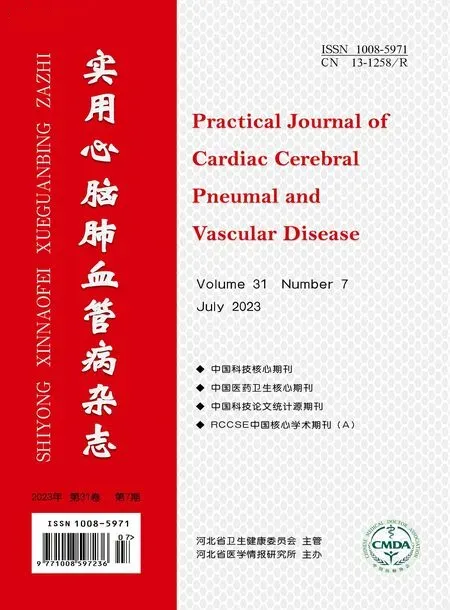炎癥指標和氧化應激指標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 后發生抑郁的預測價值研究
梁浩,金曼,谷劍,陳淑霞,呂佩源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和抑郁是兩個常見的健康問題。研究表明,AMI患者住院期間抑郁評分增高與12個月后心血管事件風險增加有關[1]。DEPACS研究[2]發現,對AMI患者進行抑郁篩查及相關因素分析可能有助于改善其心臟結局。
研究表明,WBC、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淋巴細胞比值(platelet lymphocytes ratio,PLR)、單核細胞/淋巴細胞比值(monocyte lymphocyte ratio,MLR)、全身免疫炎癥指數(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平均血小板體積(mean platelet volume,MPV)、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與抑郁有關[3]。但炎癥指標和氧化應激指標與AMI患者PCI后抑郁關系的研究少見報道。本研究旨在探討炎癥指標、氧化應激指標對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預測價值。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1年就診于河北省人民醫院心臟中心且住院期間行PCI的AMI患者282例。納入標準:(1)年齡≥18歲;(2)符合《2018第四版心肌梗死通用定義》[4]中AMI 1型診斷標準;(3)能夠配合進行漢密爾頓抑郁量表24(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HAMD-24)評估者。排除標準:(1)存在心肌炎、心肌病、心包炎、心臟瓣膜病、風濕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等其他基礎心臟疾病者;(2)有精神心理疾病史或家族史、智力低下或癡呆、認知障礙者;(3)合并活動性感染、不明原因發熱、嚴重內分泌疾病、血液系統疾病、結締組織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肝或腎功能不全(ALT>150 U/L、肌酐>265 mmol/L)等影響炎癥指標的疾病者;(4)妊娠期婦女及BMI>30 kg/m2、大量吸煙(每天超過15支)者;(5)過去2周內服用皮質類固醇或免疫抑制藥物者;(6)有嗜酒史或毒物接觸史者;(7)臨床資料嚴重缺失者。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僅采集患者住院病歷資料,難以獲取患者知情同意,且對患者沒有進行任何干預措施,在保證不泄露患者個人隱私和不影響患者后續診斷治療的前提下,本研究經河北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審批文號:2022141),知情同意豁免。
1.2 分組方法 采用PCI后HAMD-24評分評估患者是否存在抑郁。HAMD-24評分>20分者被認為存在抑郁[5],將其作為抑郁組(n=73),其余患者作為非抑郁組(n=209)。
1.3 觀察指標 所有數據從醫院醫療記錄電子數據庫中的住院病歷資料中檢索。(1)一般資料:年齡、性別、是否有固定伴侶、BMI、收縮壓、心率、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評分、住院天數、肌酐、腎小球濾過率、空腹血糖、本次使用支架數、吸煙史、受教育程度、GRACE評分危險分層(評分<100分為低危,100~149分為中危,≥150分為高危)[6]。(2)炎癥指標(WBC、NLR、PLR、MLR、SII、MPV)和氧化應激指標(SOD)。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M(QR)表示,組間比較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探討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影響因素;繪制ROC曲線以評估相關指標對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預測價值。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兩組年齡、性別、有固定伴侶者占比、BMI、心率、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評分、住院天數、肌酐、腎小球濾過率、空腹血糖、本次使用支架數、有吸煙史者占比、受教育程度、GRACE評分危險分層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抑郁組收縮壓高于非抑郁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2 炎癥指標和氧化應激指標 抑郁組WBC、NLR、PLR、MLR、SII、MPV、SOD高于非抑郁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炎癥指標和氧化應激指標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inflammatory indexes and oxidative stress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3 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以表1~2中P<0.1的變量為自變量(實測值),以AMI患者PCI后是否發生抑郁為因變量(賦值:是=1,否=0),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收縮壓升高、NLR升高、SOD升高是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3。

表3 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AMI patients after PCI
2.4 NLR和SOD對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預測價值 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NLR、SOD預測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AUC分別為0.749〔95%CI(0.673,0.825)〕、0.617〔95%CI(0.545,0.688)〕,最佳截斷值分別為4.165、141.85 U/ml,靈敏度分別為61.6%、68.5%,特異度分別為89.5%、58.9%,見圖1。

圖1 NLR和SOD預測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ROC曲線Figure 1 ROC curve of NLR and SOD in predicting depression in AMI patients after PCI
3 討論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抑郁和血管疾病可能有共同的易感基因[7]。研究發現,PCI后伴有抑郁的患者全因死亡率比未伴有抑郁的患者增加77%[8],抑郁是心臟病發病率和死亡率升高的獨立危險因素[9],早期識別并適當干預抑郁能明顯改善心臟病患者的預后[10]。
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潛在機制尚不清楚,其中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均為AMI和抑郁的病理生理基礎。近年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炎癥反應在抑郁的病理生理學機制中至關重要[11]。炎癥反應可引起四氫生物蝶呤氧化、消耗增加,繼而引發腹側紋狀體對獎賞預期的反應減弱,紋狀體多巴胺釋放減少,多巴胺合成酶降低和功能改變,導致機體呈低多巴胺能狀態,引起快感缺失、情感淡漠和情緒不良,從而導致抑郁。本研究結果顯示,抑郁組WBC、NLR、PLR、MLR、SII、MPV、SOD高于非抑郁組,與既往研究結果[12]類似,提示上述炎癥指標和氧化應激指標可能與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有關。本研究進一步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NLR升高、SOD升高是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
NLR作為易于獲得的體現機體炎癥反應的臨床標志物,與單個炎癥標志物相比,其受運動、兒茶酚胺釋放和其他混雜因素的影響較小,可作為抑郁的評價指標[13]。中性粒細胞參與了動脈粥樣硬化早期的發生、發展[14]:中性粒細胞通過直接吞噬作用去除病原體和組織碎片、分泌炎癥遞質,進而誘導細胞凋亡。在AMI的破裂斑塊中存在中性粒細胞浸潤,且其與易損斑塊的組織病理學特征有關。相反,淋巴細胞減少是AMI的早期標志之一,與患者的長期死亡率升高有關[15]。NLR是上述兩種標志物的組合。NLR升高是AMI患者急診PCI后發生慢血流的獨立危險因素[16],已被證實可預測AMI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風險[17],考慮可能與中性粒細胞對心肌和血管內皮的直接毒性作用、白細胞堵塞冠狀動脈微循環系統、血液黏度增加、高凝狀態等因素有關。AYDIN SUNBUL等[18]研究發現,與HAMD評分較低的患者相比,HAMD評分較高的患者NLR水平更高,NLR>1.57是抑郁的獨立預測因子。本研究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NLR預測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AUC為0.749〔95%CI(0.673,0.825)〕,最佳截斷值為4.165,靈敏度為61.6%,特異度為89.5%。
除炎癥反應外,氧化應激也在抑郁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SOD作為抗氧化酶可通過清除超氧陰離子阻止自由基損傷細胞。在SOD逐漸消耗的同時,氧化應激對神經組織、血管內皮的損傷逐漸減輕。既往研究顯示,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抑郁患者血清SOD活性明顯降低[19]。與此研究結果不同的是,本研究結果顯示,抑郁組SOD高于非抑郁組,這可能與疾病階段不同有關。PCI后抑郁的診斷是一個動態過程。結合本研究結果,SOD增高可能與抽血時間距離發病時間較短,其代償性增加后未充分發揮抗氧化應激作用有關;此外,AMI患者PCI前接受的抗血小板藥物、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β-受體阻滯劑、硝酸酯類、他汀類藥物等會通過特定的抗氧化機制來發揮對氧化應激的保護作用,進而導致血清SOD水平相對升高[20]。本研究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SOD預測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AUC為0.617〔95%CI(0.545,0.688)〕,最佳截斷值為141.85 U/ml,靈敏度為68.5%,特異度為58.9%。
綜上所述,NLR升高、SOD升高是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中NLR對AMI患者PCI后發生抑郁具有一定預測價值,而SOD的預測價值較低。本研究仍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一項回顧性研究,因此無法明確NLR與抑郁的因果關系;再者,遺傳特征、生活方式、營養情況和用藥情況等為不可控因素;本研究只評估了AMI患者住院期間的抑郁癥狀,未持續觀察其的心理狀態和炎癥指標、氧化應激指標的變化。未來需要大樣本量、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論。
作者貢獻:梁浩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撰寫論文、研究的實施與可行性分析;金曼、陳淑霞進行資料收集、整理,統計學處理;谷劍、呂佩源進行論文的修訂,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