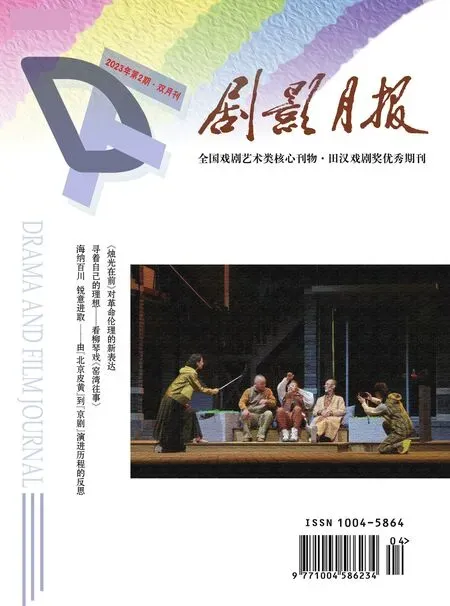《燭光在前》對革命倫理的新表達
■趙建新

“舍小家顧大家”是人們對很多英雄英模人物美德的集中概括,它經常作為一種精神感召力量,在民族危亡之際鼓舞人們舍私為公,為國家大義犧牲自我。進入現代社會后,這種傳統道德規范不但沒有因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而顯得過時,反倒在20世紀激進的社會變革中強化為一種新的革命倫理表達,反映在藝術作品中,便經常體現為英雄人物處于理性政治追求和個體情感矛盾糾葛時,其價值取向最終要以政治理想為第一標準,以階級大義超越個體情感。這種創作方式在宣傳了革命理想、頌揚了政治信仰的同時,也經常因為對個體情感的關注不夠、抒情方式的簡單直接而導致人物形象的符號化和概念化,使作品顯示出美學的貧困。其實,英雄之所以為英雄,恰恰是因為他們能夠超越凡人的個體世俗情感而獻身于信仰大義,所以無論是作品主題立意的需要還是單純的劇作法要求,都勢必讓英雄人物做出“舍小家顧大家”的戲劇行動以升華作品的主題。但問題的關鍵之處在于,如果編創者輕易否定掉個體情感欲求的價值,讓英雄人物在“公”與“私”、“家”與“國”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以“公”滅“私”或以“國”代“家”,讓英雄僅僅成為國家和群體利益的單向度代言人,就勢必會弱化個體性的世俗情感,從而導致英雄形象的失真、失信。近些年來,很多優秀的創作者都認識到了這種創作傾向的局限性,不再對個體情感的欲求予以簡單的排斥和否定,而是在承認和肯定其價值的同時,努力挖掘英雄英模人物在“家”與“國”、“公”與“私”之間的兩難處境,最終予以升華,使其不是簡單的“大公無私”,而是在守護“私情”的前提下最終仍要選擇“大公”,在“愛家”的無限溫情中仍要選擇“為國”,只有這樣方能以情動人,達到真正的審美效果。錫劇《燭光在前》在這方面做出了較為極致的探索和努力,形成了對革命倫理的新的美學表達。
在題材開掘方面,《燭光在前》濃彩重抹人倫親情,以一豆燈火“點亮”四次別離,顯得別具一格。主創用張太雷家人來寫張太雷精神,用張太雷和孩子們與陸靜華的四次別離來寫主人公的革命精神對家人的感召,四場戲各有起伏,場場精彩。第一場“剪信”,由二女兒張西蕾的離開引出張太雷的秘密;第二場“議去”,寫大女兒張西屏欲去還留;第三場“擲衣”,寫張一陽離別時同母親見與不見間的復雜情感;第四場“燭光”則尋根溯源,追述張太雷當年和陸靜華分別時在兒女私情與革命大業之間的去留撕扯。四場戲有兩場寫母女情,一場寫母子情,一場寫夫妻情,觸及的全是人間至親的人倫情感。四場戲中,每一個孩子的離去,母親既沒有斷然阻止,也沒有欣然鼓勵,而是先極力挽留,后尊重其意愿,決意讓他們去參加革命。先挽留是盡到了一個母親應盡之心,而最后送他們離開則是因為她是張太雷的妻子,而孩子是張太雷的孩子。親人的去留在“擲衣”一場里處理得最為淋漓盡致,兒子擔心母親傷心,于是躲在船艙內不露面;母親不忍兒子難過,故而假裝視而不見。母子兩人艙內艙外,咫尺天涯;欲見不見,不見卻勝似相見,輪番對唱,感人至深。主創竭力渲染描摹的是親人之間在奔赴革命之前的離愁別緒和百般不舍,與慷慨決然地奔赴革命相比,這種百轉千回的親情挽留更加動人心魄。在錫劇藝術家的精彩演繹下,那些柔腸寸斷的生離死別不但沒有成為阻礙主人公獻身革命的牽絆和拖累,反倒因為有了它們,革命者最終選擇的信仰和大義更趨深沉和厚重。


常言道,自古忠孝難兩全。“兩全”肯定不是戲,“不全”才最有戲。關鍵是如何展現這樣的“不全”。簡單地用“忠”取代“孝”,認為代表革命大義的“忠”比代表世俗人倫的“孝”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未免簡單粗暴。人倫親情和革命理想同是人類都應珍視的美好情感,英雄英模之所以能最終選擇后者而放棄前者,不是因為前者的道德價值低于后者,而是因為英雄英模在做這樣的選擇時已經超越了世俗價值的標準而進入信仰層面。只有精神信仰才能讓人不計功利得失,才能舍生取義。在《燭光在前》中,第二場“議去”是最特殊的一場。在這場戲中,張太雷的大女兒張西屏最終放棄了革命,在“姆媽的路”和“爹爹的路”之間,她最終選擇了“姆媽的路”。“姆媽的路”自然不是超凡脫俗的革命,而是成家、生子和盡孝,是默默地“熬”和“忍”,這和以張西蕾與張一陽為代表的“爹爹的路”截然相反。但是,觀眾對張西屏的這一選擇在情感上不但沒有產生任何拒斥和反感,反倒寄予了可能比張西蕾和張一陽兩人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因為或許只有這樣的張西屏才代表了最大多數的普通人的選擇。在滾滾的革命洪流中,時代自然需要英雄英模挺立潮頭一呼百應,而無數默默付出的平凡人也同樣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來源。于是,在這樣一出以弘揚革命先烈犧牲精神的紅色戲曲劇目中,那些并不具有革命色彩的“熬”和“忍”也被主創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贊頌。是的,這樣的“熬”和“忍”雖然看上去、聽上去不那么“革命”,但其本身蘊含的犧牲和奉獻卻絲毫不遜色于真正的革命本身,甚至可以說,沒有革命者身前背后的這些普通人的“熬”和“忍”,革命者的勝利甚至都無從談起。這些看上去并沒有閃耀著革命光輝的世俗人倫情感,猶如堅實深厚而寬闊無垠的大地,托舉起那些高山一樣的革命者,讓他們扎根于斯、滋養于斯。
無論是“舍小家顧大家”,還是“忠孝難兩全”,錫劇《燭光在前》都沒有做簡單的價值判斷。很多時候,人性是禁不起這種孰重孰輕之衡量的,而“戲”就是要表現這種“禁不起”,英雄的戲更是要超越這種“禁不起”。寫好了這種“禁不起”,戲便有了情感的張力。無論是“姆媽的路”還是“爹爹的路”,都是偉大的路;無論是黨性還是人性,都是至情至性。筆者認為,這便是錫劇《燭光在前》所要努力傳達給觀眾的革命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