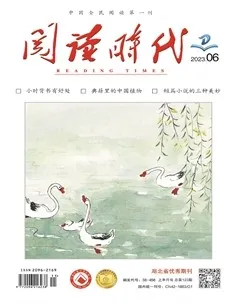病榻床頭萬卷書
申功晶
病來如山倒,且來得悄無聲息,來得毫無征兆,先是喉嚨嘶啞、聲帶充血,接著咳嗽發熱。在醫院掛完點滴,單位領導通情達理準了我半個月病假,并囑咐我好生調養身子。
記得少時,每逢臥病在床,總是習慣性在枕頭上多加一個靠墊,然后從被窩里探出一只小手,持書默讀以消遣時光。南宋大文豪陸游說:“病須書卷作良醫。”這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因為一旦捧起了書,頭腦就不再胡思亂想。等把一本書從頭頁翻到尾頁,病也將養得差不多了。
浮生偷得半月閑,我從書架上取出一本厚書,撣了撣扉頁上的塵埃。這場病,似是老天爺催我償還書債來著。對于大多數陷于職場、疲于生計的80后、90后而言,鮮少能擠出點閑余時間好好讀書。讀書,成了一件奢侈之事,似已到“書非病而不讀”的地步。學生時代,天天語數外理化生,忙著搞“題海戰”應付考試;步入職場,上有老,下有小,房貸、車貸一肩挑,硬著頭皮接受生活的捶打。
生病真好,你可以堂而皇之打著“養病”的幌子,大把大把揮霍屬于自己的時間。不必搏命職場、通宵達旦,無須敷衍人情、客套世故,更不用為瑣碎細事勞心勞神。
生病真好,只要不至于“嗚呼哀哉”,沒有大痛苦,便能如魯迅先生所言“不看正經書”“大享生病之福”。
生病真好,此間身子虛弱,兼之藥力作用,易催生一種恍若隔世之感。此刻,捧書而讀,恍惚之間,靈魂似飄然出竅,飄進了書本里。人在病中,情緒低落,更容易與書中的悲觀氛圍產生共鳴。比如,在讀到《紅樓夢》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風雨夕悶制風雨詞》,在淅淅瀝瀝的秋雨下,黛玉又犯了咳疾,她強撐著病軀,一盞孤燈,寫下了凄凄慘慘戚戚的《秋窗風雨夕》:“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已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凄涼……寒煙小院轉蕭條,疏竹虛窗時滴瀝。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此時,書中的她在窗下劇咳,書外的我倚在床頭咳嗽,書里書外,我和她已渾然一體,不分彼此。
讀到曹丕《燕歌行》“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須臾間,滋生出一番綿綿傷感之思。這位“桀逆遺丑”的腹黑君王欺母、屠弟、逼君、篡漢……頗遭后人口誅筆伐。鮮為人知的是,他自幼不為父母所喜,為一展胸中鴻鵠之志,如履薄冰,一步步從世子到新帝;為國之民生大計,他勵精圖治,不顧宗室反對,推行新政。詩為心聲,此時的我方讀懂那猙獰血腥的帝袍下實則包裹著的一顆柔軟、多愁善感的心。
人在病中,肉體孱弱,可頭腦卻尤為清明。在平日看來,那些晦澀難懂的詩文道理,此刻讀來,宛如電石火花,更似醍醐灌頂,須臾之間,明心見性,徹悟通達,頗有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讀書三境界之第三境“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意味。
我至今仍清晰記得,大二下學期,我得了一場大病,醫院開病假讓我休學半年。躺在病床上,盯著空蕩蕩的天花板,一陣陣空虛、焦慮感凌亂無章地朝我襲來。父親擔心我憂思過重而影響康復,于是,跑去文化市場直接搬了一大箱子書回來。拆開紙箱,里面都是我生平最喜愛的文史類書籍,有二月河的全套“帝王系列”小說,有姚雪垠的成套13本《李自成》,有武俠小說大宗師金庸先生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全套,更有古龍的陸小鳳系列、楚留香系列等。“知女莫若父”,父親將這些書像砌磚一樣從床頭堆至床尾,樂得我立馬從床上彈跳起來,愛不釋手地一本接著一本摩挲。翻開書,那一個個鋤強扶弱、快意江湖的身影活躍在眼前,看得人心潮澎湃。雖不能身至,然心向往之。于是,我便將內心所思所想付諸筆端,開始碼字、投稿,從最初刊登在報紙副刊上的小“豆腐干”發展到后來給電視臺寫故事劇本。當年,一個劇本的稿費差不多能抵我一個月的生活開銷。編輯也時常在回信中鼓勵我“想象力豐富”“頗有潛力”。這些直接影響了我后來的職業生涯規劃,我原是理工科出身,畢業后,卻轉行做起了記者、編輯、文書寫手、專欄撰稿人……
如今,我躺在病榻上,手里依舊捧著《全唐詩》,當讀到“病樹前頭萬木春”,忍不住會心一笑。很多年前,一個女孩,在這三尺寬、六尺長的床上整整臥病半年,病榻上的“萬卷書”為她開拓了一片廣闊的新天地,也開啟了她生命中的春天……
(本文系作者原創來稿)
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