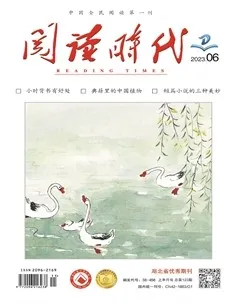“夏”字自述

我永遠記得,1942年,郭沫若先生曾在散文《石榴》里,說他在一年四季中最愛我,夸贊我所在的季節是整個宇宙的心臟,充滿著最旺盛的生命力。聽了郭先生之言,我有了幾分飄飄然,竟酒醉似的,平生第一次為自己喝彩。事情一過去,很快我就忘了。
沒有想到,2004年4月11日,蔡達斌先生又提及此事,這使得我激動萬分,自信一下子就“蹭蹭”地往上漲,差點掉下了眼淚。當時,蔡先生的妻子十月懷胎產下一子。夫妻倆像小孩般手舞足蹈,喜欲狂,愛不釋手地抱著兒子“相看兩不厭”!高興了一會兒后,妻子問蔡先生,兒子取何名為好。蔡先生便重復郭先生在《石榴》一文中對我的如此夸贊,并且還說我和“華”上古同音,本一字,相互通用,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都非常崇高,其意思是“壯美”,“華”加上我,是中國的另一個美名、雅號。說兒子本來也可以取名為“華”,譬如縣城現任公安局局長,就叫蔡華哩,但“華”在蔡氏族譜中是兒子的曾祖的輩分,因此,蔡先生只能舍棄“華”,而另揀我為兒子的名。一番“科普”后,妻子覺得這樣甚好。于是,他們倆歡然在我前面冠上“蔡”姓,便成為他們兒子的尊姓大名了。
如今,每每想起這件事,我都不禁會心地微笑起來。因了這,我可算揚眉吐氣了一回。要知道,在這之前,我那個朝代,出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暴君——桀。這讓我一直抬不起頭來,很是郁悶。當然,我那個朝代也不是沒有出過賢主明君,比如禹,就是一個好君主。為了解除水患,造福百姓,他竟“三過家門而不入”!
大學問家《說文解字》,說我是個會意字,小篆字形,從頁(人頭,讀xié),從臼(兩手,讀jù),從夂(兩足,讀suī),合起來像人形。本義是古代漢族自稱,中國之人也。可以說,這種詮釋言簡意賅,又高屋建瓴,對我的形神認識把握得十分精準、到位。不愧為大學問家吶!
近年來,隨著中文在西班牙的快速流行,漢字也被西班牙人當作時尚品使用。尤其是,不少西班牙青年人喜愛用漢字文身。有一位我這個姓的中國女孩,去西班牙遇見了一個當地小伙子。兩人情投意合,恩愛有加,在一起談起了戀愛。我真為他們高興!一天,小伙子跑到中國女孩面前,神神秘秘地說,他要給她一個最好的禮物。女孩見他兩手空空,便睜大眼睛一臉的不解。小伙兒說,他去文身了,且文的是女孩的姓,漢字的我。聽他如此說,我激動得直冒蜜汁,女孩也興奮得直流喜淚。字是文在心窩的。由此可見,小伙兒對女孩的感情有多深!當小伙兒解開衣服扣子時,女孩的神情由羞澀著的驚喜,轉眼變成了驚呆的失望。我也傻了眼,苦笑不已。原來,小伙兒竟張冠李戴,把我錯文成了“復”字。這時,我才發現,還有跟我的字形有幾分相近的字。這不得不使我對“復”字產生起敵意來:是它混淆了他的視聽,要不,怎么會有這么一出鬧劇?
更氣人的是,這西班牙小伙兒每每寫女孩的姓名時,將其姓中間的“目”字,要么多寫一橫,要么少寫一橫,令我和女孩都非常難受。好在女孩心胸寬廣,僅僅郁悶了一會兒就沒事了。因此,他們倆總的來說,相處得還算不錯。我雖耿耿于懷那小伙兒總把我寫錯,但見他們相親相愛,我也就無話可說了。畢竟是老外,應該多些寬容,多給他點學中文的時間。我衷心地祝福他們幸福久長!
實際上,我還是比較獨特的。我的相貌上面部分和“戛然而止”中的“戛”字上面部分完全相同。而下面部分,則與“復習”的“復”字下面部分一模一樣。如此一個外在簡單、明了的我,一個內在壯美、陽光的我,怎么會有人老是把我搞錯呢?
(本文系作者原創來稿)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