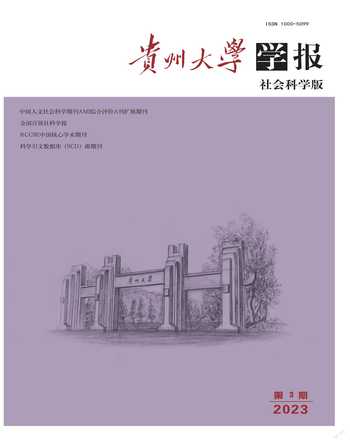個體性嵌入:基層政府結對治理實踐中的互動關系及情感邏輯
作者簡介:舒洪磊,男,貴州遵義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個體性嵌入:基層政府結對治理實踐中的互動關系及情感邏輯
摘要:隨著絕對貧困的終結,我國將邁入鞏固脫貧成果與鄉村振興發展協同推進的時期。結對治理為城鄉人才流動提供了可供參考與選擇的經驗對象,也為我們理解基層治理主體在鄉土社會的治理實踐提供了具象認知。本研究基于田野調查的經驗材料收集,以互動關系與情感邏輯的視角審視脫貧攻堅時期的結對治理實踐,研究發現結對治理在適配鄉土關系信任的基礎上增進信息全知性與互動的具象化,以個體性嵌入幫扶家庭的方式精準配置治理資源,結合技術治理邏輯下“曉之以理”與個體化聯結“動之以情”的特點,將國家的“剛性”政策目標“軟化”處理后與幫扶家庭的發展需求對接,發揮可持續的治理效能,為更好接續鄉村振興發展提供可考經驗。
關鍵詞:結對治理;互動關系;情感邏輯;個體性嵌入
中圖分類號:C913.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099(2023)03-0107-09
一、研究緣起與問題提出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其本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我國的脫貧攻堅政策實踐是依據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基本國情,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歷時八年完成了9 899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2]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一些發展薄弱地區仍然面臨返貧風險,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同時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邁進。可看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必要前提,籌劃鄉村振興的同時也應夯實前期的扶貧成果,總結前期的治理經驗與治理智慧,為鄉村持續發展提供正確的方向指引與良好的接續基礎。脫貧攻堅期間,不同地區依據地方貧困特性與發展目標制定地方性的扶貧策略,部分地區在結對制基礎上發展出“干部包幫”的結對扶貧模式,[3]即在基層干部和貧困戶之間建立結對關系,實現人才與資源的精準嵌入。結對治理體現了“中國經驗”與“中國智慧”面對西方現代化發展的本土回應,面對“同質化”與“被同質化”的現代化景觀,我國針對自身國情探索出源于自身、適合自身的治理經驗,并不斷保持更新狀態。
所謂結對,是指按照圍繞政府經濟社會決策的某個目標,經由各級行政組織資源協調,在行政組織成員與民眾個體或群體之間建立起一種在相對時間內較為穩定的聯結機制,以期達成特定目標的實現。因而“結對”意味著行政組織成員與基層鄉村民眾的特定關系,對此問題的討論關乎國家權力與個體民眾之間的關系。與以往的干部駐村幫扶模式相比,結對治理能夠長期聚焦于幫扶對象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問題,并與幫扶家庭成員建立起穩定的互動關系,將治理通過家庭這一組織單位聚焦到個人,實現治理的精準化與精細化。再者,個體性嵌入是以治理主體長期“身體在場”的方式嵌入到治理對象的生活場景(家)與具體的脫貧實踐中,獲得治理對象的信任并與其建立長期持續的情感互動,超越事本主義的治理邏輯,實現精準的資源匹配以滿足治理對象多元化的發展需求。結對治理是在國家權力以柔性細密的方式下沉及基層治理精細化的背景下產生的,利用家庭在治理中的媒介作用,將下沉的國家權力與民眾自下而上的生活需要相結合,實現“身體的物理性在場”到“身心融入治理實踐”的治理方式轉變,打通鄉村治理實踐的“最后一米”,積極回應村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時,重建村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
文章基于2018年11月至2021年9月中國西部L村的扶貧調研經驗材料,從鞏固扶貧成果和接續鄉村振興發展的視角出發,探討以下問題:結對治理模式下幫扶人員以怎樣的方式深入基層,與幫扶對象之間建立個體化聯結?建立聯結后幫扶人員與幫扶對象之間又以怎樣的方式進行信息互動?隨著扶貧的逐步深入,幫扶人員與扶貧對象之間的情感邏輯如何演變?這樣的互動關系與情感邏輯對鞏固扶貧成果與接續鄉村振興發展有無益處?探明以上問題有利于對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制度性磨合有更具象的認知,與鄉村振興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精準銜接。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選擇
在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討論中,鄉土情感治理資源常常被技術與理性治理所遮蔽。在中國處于新舊社會交替的歷史階段時,馬克斯·韋伯就認為傳統中國所面臨的艱難治理處境正是由于儒家傳統文化在治理體系中發揮強大的思想引領作用,忽略了以稅務為核心的計量技術在國家管理中的作用,[4]黃仁宇也認為正是道德治理取代技術治理才導致了中國長期處于封建狀態,難以朝著現代化國家發展。[5]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國家推動現代化治理的語境下,技術治理與理性化治理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仍占據著主導地位。隨著國家對治理體系理性化、現代化的追求,技術邏輯不斷在政府行政治理體系內部擴散,技術邏輯逐步取代了總體性支配的邏輯。[6]但情感治理在中國本土文化中仍有其存在和適應空間,中國歷來是情理法合一的社會,深具“情感國家”“感性國家”的傳統。[7]
在《心理學大辭典》中,“情感是人對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產生的態度體驗”。[8]有學者認為,情感是個人在經歷或認識事物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心理體驗[9],且情感會隨著外部刺激、情緒的波動而隨機變化[10],可知,情感治理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情感問題研究因其“主觀化”而長期被學術界邊緣化,直到20世紀中后期才被關注。霍弗在《狂熱分子:群眾運動圣經》中就認為一般而言,大多數窮人對自己的資源匱乏狀態都安之若素,能夠引發不滿情感的多是“新窮人”,他主張要特別關注新窮人的失落情感。[11]當前學界討論情感嵌入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心理學和情感社會學領域,如有研究認為人們會隨著自身社會地位的變動而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情感,特別是他們在喪失地位時,不同的喪失歸因使他們產生愧疚、不安、抑郁或是憤怒。[12]任何社會行動體都需要處理情感問題,且情感并不只是藏匿與個人的私密空間,有時也會形成正式的治理行動。易言之,情感不僅只做為個體的私人情緒,也可作為規則、規范和制度而存在的社會性行動。如王寧提出的制度合情性就認為,制度在符合了文化化、合法化的情感釋放、表達和反應方式,更能符合人們的情感期待和情感反應模式,它成為人們相互溝通和彼此接受的互動規則。[13]
自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學界多集中在政策實施的制度、技術等維度展開討論,有關扶貧主體與扶貧對象之間的情感層面以及情感治理在提高和維持扶貧績效方面的文獻仍付闕如。精神健康學認為,貧窮會給人帶來生活壓力,長期生存在生活壓力中會給人帶來負面情感。[14]負面情感會嚴重影響貧困者的脫貧意志,如果社會其他利益既得群體對貧困群體采取冷漠、孤立的態度,會加重貧困群體的負面情緒,進而出現“越幫越恨”的尷尬境況。[15]一直以來,基層政府與群眾的情感聯結方式主要還是“送溫暖”“走基層”等較為傳統的慰問活動;對此,文軍、劉雨婷認為未來的基層治理需要將文化、情感、心理層面的因素納入其中,[16]有學者從“緣情共同體”的角度解釋幫扶人員與扶貧對象之間的關系形態,[17]也有一些學者運用嵌入理論考察了剛性的“結構嵌入性”制度體制與柔性“關系嵌入性”的情感結合,增進了干部與群眾之間的聯系。[18]向德平與丁建彪等學者分析了精準扶貧戰略實施過程中駐村干部的扶貧行為與扶貧績效問題。[19-20]
嵌入理論(Embeddeclness)發源于經濟社會學,而后被引入其他學科分析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網絡等方面對人的行為和社會秩序的影響。嵌入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波蘭尼認為,個體行動者既不外在于社會環境,也不是固執地堅守其既有的、普遍的社會規則與信條,而是“嵌入”于具體的、當前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正是在這種格局中,社會個體做出符合自己目的、能實現自己愿望的選擇。[21]該理論的代表人物格蘭諾維特(M.Graonvetetr)認為,嵌入會形成結構雙方的嵌入關系,嵌入關系會使雙方逐漸增進信任與私人聯系,不僅僅靠制度與合同約束雙方行為,使雙方做出更適合彼此情境的決定,降低監督與風險成本。嵌入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會成為信息傳遞的渠道,行動主體在信息等資源的交換過程中會形成伙伴關系。[22]
嵌入理論被廣泛運用于鄉村治理研究。主要從三個視角展開:一是從文化視角出發,欠發達地區看似經濟問題,實則是深層次的文化問題。[23]駐村干部有利于彌補村干部在文化扶貧方面的短板,能夠對提升鄉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價值觀有所助益。[24]政府文化部門是開展文化精準扶貧的責任主體,高校圖書館在嵌入鄉村文化發展中扮演輔助角色。[25]有研究者運用“四象限”法選擇文化扶貧的“應扶之人”和“可扶之人”,以此確保“真扶貧”與“扶真貧”。[26]二是非科層視角。行政嵌入為超常規治理工作機制的生發提供了制度邏輯、場域邏輯和行動邏輯,可以發現駐村工作隊的運行樣態兼具并超越了國家治理中常規與動員兩種常見的治理機制的運作方式與行動特征,呈現出超常規治理的運作邏輯。[27]有利于打破傳統鄉村治理功能分割和制度僵化困局,促進鄉村治理更加人性化發展。國家權力要柔性嵌入鄉村內生規則之中,需要根據國家權力和鄉土社會對村規民約的不同定位,實現村規民約價值功能與鄉村自治效能的互動轉化,以推動形成依法立約、以約治村的良性循環格局。[28]三是關系網絡視角。駐村第一書記通過聯結關系嵌入和話語賦權,旨在不斷織密多元主體共同助推鄉村產業振興的社會關系網絡基礎。[29]但駐村干部所嵌入的關系結構,發現“碎片化”的干群關系形塑著村干部“劃水治理”的行動邏輯,“分利合作型”鄉村關系形塑著村干部“唯上”的行動邏輯,熟人社會的人情關系形塑著村干部“交換平衡”的行動邏輯。探索并改造“關系”這一傳統社會資源,挖掘“關系”的積極效用,可實現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深入推進可持續精準脫貧。[30]將嵌入理論作為本研究的分析工具,有利于分析幫扶人員與扶貧對象之間形成的制度性與非制度性互動關系,有利于審視脫貧實踐后期雙方的聯結關系與情感要素在鄉村振興發展階段的演變過程。
目前,相關研究已對國家權力如何嵌入鄉土社會問題進行了討論,但未充分考慮到作為治理實踐末梢的治理力量是如何嵌入鄉土社會治理體系的,更缺乏對治理主體間互動過程及情感邏輯演變的關注,僅注重互動結果的治理效能進行分析,這造成既有研究結論的單一化和靜態化問題。鑒于此,本研究基于脫貧攻堅政策實踐有明顯的階段化特征,根據全國脫貧實際與貧困戶具體情況呈現動態變化,在長期的脫貧政策實踐過程中,就扶貧中的結對治理機制深入田野、深入貧困對象內心分析他們對幫扶人員的情感邏輯,討論結對關系與情感邏輯在鞏固脫貧攻堅與接續鄉村振興發展中的作用。
三、結對治理的互動關系與情感嵌入實踐
結對治理重在對幫扶對象的結構性與個體性貧困因素的瞄準,政府制定的政策只是為各行動主體指明一個行動導向,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還需要幫扶人員根據幫扶對象的具體情況選擇契合的扶貧措施,扶貧措施需要與幫扶對象的困境與發展需求相統一。長期的脫貧攻堅和脫貧成果鞏固是一個動態過程,考察幫扶人員與幫扶對象之間的個體化互動也需要以階段化的視角去審視。本文的傳播視角并非依賴某一種媒介(如廣播、電視、互聯網等)而存在的對象化考察,主要以扶貧主體與客體之間建立的聯結關系作為傳播的分析路徑,考察扶貧實踐中雙方的信息互動與情感邏輯之間的關系。
1.結對治理適配鄉土信任邏輯
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是個傳統社會,依靠經驗的積累而延續,自然替人們選擇出足以依賴的傳統生活方案。[31]鄉土社會中的個體有對自身生活場域中經驗知識的信任邏輯,對熟悉場域以外的事物常保持一種觀望或不信任的態度。脫貧攻堅是一個周期性和動態化的政策實踐過程,隨著扶貧政策指向的逐步深化,扶貧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個體化聯結也需隨之深入,雙方在不同階段都需要面臨鄉土信任邏輯與技術治理邏輯的彼此融合與調適。
首先,村民信任講“關系”,建立關系要實用。信任是人類社會皆有存在的普遍現實,但又體現出鮮明的文化特征。托馬斯指出,信任是為了規避未來不確定的風險,而鄉村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面對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人們并不愿輕易付出信任。鄉土社會中的信任邏輯是基于人際交往為基礎的差序信任,有以下特征:人們的最初信任起點是由血緣關系構成的血緣關系信任,屬于先賦性關系信任,之后的信任是在先賦性關系信任關系基礎上的擴展和演化。所以鄉村的信任邏輯主要是以關系的親疏進行劃分,這種關系可以是基于血緣與地緣的情感性,也可以是基于業緣的工具性;誠然,鄉村中的個體以自己為中心所形成的“關系圈”,對內部圈層關系比外部圈層的關系更為信任,而位于不同圈層的關系可以相互轉化,充分體現了鄉土社會關系的差序性與可伸縮性。在扶貧的早期階段,為了實行貧困信息的數字化管理,政府工作人員帶隊下鄉考察貧困戶家庭的基本情況,貧困戶對這一聲勢浩大的普查行動表現出疑惑又有些抵觸,“從來沒見過這么大的陣仗,一共可能來了十幾個,有專門填表的,有專門問問題的,還有專門攝像的,家里的板凳都不夠坐,說實話有些問題我各人都不清楚,敷衍了事的就說了(笑)”。一方面他們對這樣一種聚焦式的調查和接近方式并沒有信任基礎,導致回答一些問題時云里霧里亦或敷衍了事;另一方面這樣一種注重數據留痕的統計調查方式觸及到家庭細胞的隱私部分,正如幫扶對象劉建所言:“剛開始評貧困戶的時候,經常有政府的人來問東問西,有些問題我們也聽不懂,憑什么給你講?問多了我就有點惱火(生氣)”。此時,私人生活空間與幫扶人員之間的邊界尤為突出,身體成為兩者之間交往邊界的主要呈現物。彼此對身體的陌生而產生交往關系的疏離感,使身體不自主地披上了屬于身體的“面具”,身體下的“面具”與“面具”下的身體便是陌生人之間交往的狀態,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制度環境下的“事本主義”邏輯難以適配鄉村社會的互動邏輯,雙方并沒有依托制度環境形成結對關系信任。
其次,增進信息的全知性,保持互動具象化利于構建關系信任。關系信任是幫扶雙方在結對治理實踐中因交往性關系而產生的信任,結對關系所衍生出來的信任并不同于先賦性關系的血緣信任,也不同基于制度或契約的制度性信任,它更多取決于后天在互動過程中的經驗判斷,根據幫扶雙方在互動過程中對結對關系的遠近及質量進行綜合判斷的結果,即是依據地方“人情”感性特質與后天“理性”評估的綜合體現。幫扶干部獲得信任的前提是將自身在場的行動意義與政策指向用易于幫扶對象理解與接受的方式進行轉譯,其中地方方言是幫扶干部融入幫扶對象差序關系的重要符號,促進政策信息落地的同時也有利于增進彼此信任。鄉村是一個貼近幫扶對象生活場景的“場”,身體的在場也為方言與鄉音等符號互動提供了更多的知覺經驗,社會關系就在身體的知覺經驗與語言符號互動中得以建立。抽象的制度、政策等借助具象化的實踐才會被村民接受與信任,村民的信任是指向具體的人或事物的信任。結對扶貧本就是對國家扶貧政策和扶貧目標具象化實踐的過程,幫扶人員的身體在場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物質贈予行為都是讓雙方的關系互動更加具象與實在的過程。“原來幫扶人員給我們講什么扶貧政策,扶貧目標,我也聽不太懂,離我的生活太遠了,后面只有一個扶貧干部來,一問他老家居然是隔壁村的,和我妹家挨得很近,感覺就熟悉多了”,現代化發展體系下的信任是更傾向于機構、組織等理性機制或符號系統,而鄉村中的個體更愿意將看得見、摸得著,且與自身有一定“關系”的人或物納入自己的信任范圍,所以政策過長的預期與抽象的理念對幫扶對象來說是缺乏吸引力的,幫扶對象對長期在場的幫扶人員更能表現出認可和信任。在與幫扶對象互動的過程中,長期在場互動是關系聯結最基礎的實在,一方面幫扶人員的身體在場能夠讓幫扶對象對國家的情感有具體的指涉對象,使政府與底層個體的互動從以往的形式化向溝通渠道具象化發展;另一方面,彼此身體的在場能讓治理主體關注底層個體的生產生活狀態以及內心的情感需求,這不僅凸顯治理面向從宏觀向微觀的轉變,更體現了治理與發展的終極目的——具象化的人的發展。
2.個體性嵌入適應資源精準配置
基于嵌入理論視角審視L村的扶貧實踐可知,地方政府、幫扶人員和貧困戶都結構性嵌入于他們所構建的以精準脫貧為目標,以精準扶貧為手段的網絡之中,形成了個體化聯結的結構性關系網絡。Uzzi從分析機制角度分析了績效產生的原因,他認為相對純粹的經濟聯系,嵌入性聯系通過信任,優質信息共享及共同解決問題等機制,能帶來嵌入性關系雙方行為的改變,如同心協力共同承擔風險,從而提高效率。[32]個體性嵌入構建的結對關系在感知幫扶對象發展需求的基礎上精準配置治理資源。
幫扶人員既是資源配置的載體,也是助力幫扶對象進行心理建設的推動力量。在結對治理實踐的早期階段,在幫扶對象生活空間中進行持續在場互動促進幫扶人員感知其內心真實的發展需求與日常生活困難,是個體性嵌入治理發揮治理效能的關鍵一步。不同貧困類型都有其難以言說的貧根困因,筆者訪談過程中發現,幫扶對象因長期處于“信息孤島”與發展困境中而陷入長期的迷茫狀態,這種心理層面的“困”因需要幫扶人員長期深入幫扶對象的日常生活才能感知。比如楊琳在對劉建家庭的幫扶過程中,會主動根據劉建妻子建英的病情聯系醫生診療,并對建英進行心理建設予以紓困,“那時候建英消沉得很,覺得自己的病情拖累了家庭,她悄悄給我說想一死了之,我就一直鼓勵她,那時候我下班沒事兒就去陪她聊聊天,這樣她心情好點”。楊琳作為連接多方社會資源的主體性媒介,有擴大幫扶對象社會資本的作用。社會資本的使用指的是特定行動中實際上對特定連結及其所包含的資源的調動和利用。一方面,楊琳利用專業優勢與社會資源幫助建英擺脫病痛的過程中發揮了橋接社會資本的媒介功能,使幫扶人員的扶貧行動與貧困戶的需求連結在一起;另一方面,楊琳在幫扶過程中也發現摧毀這個家庭的或許不是病痛,而是以病痛為表征之下的心理創傷,所以重建建英的積極情感成為楊琳與之互動的主要目的。
結對治理作為一種精準性、柔性化的治理方式,更能適應幫扶對象的多維發展需求。在以往的貧困治理中,鄉村的貧困是以經濟貧困為主而體現出的物質性貧困,解決物質性的絕對貧困固然重要,但容易忽視幫扶對象在脫貧實踐中的多維發展需求。在L村中有近一半是孤寡貧困戶,他們在情感層面的貧困比物質層面的困乏更甚。如陳建在幫扶張朝林的過程中就發現,老兩口是典型的溫飽有余,情感關懷缺失的孤寡戶,由于女兒在外工作繁忙,加之路途遙遠,基本保持一年回來看一次老倆口;陳建在與老人鄰居閑聊時得知,其實老倆口特別希望外孫能夠回來和他們住一段時間,但老倆口從來沒有主動向其女兒訴說這樣的要求。“2018年的暑假,我主動聯系老張的女兒,向她提了讓其兒子回來陪陪二老的要求,她答應了我的請求,讓孩子回來陪二老兩個月。”孩子回老家陪老倆口待了一個多月又回到了廣西桂林,陳建用相機幫老倆口和他們的外孫拍了一張合影,現在仍然掛在老張家泛黃的玻璃相框中間。陳建與老張的這種互動是建立在非制度性框架之上的,陳建通過更為熟識二老的鄰居獲取他們的內心需求,再與其女兒進行溝通協商,最終達成了老倆口的夙愿。陳建的扶貧實踐在此過程中與二老的內心需求形成一種互動,但互動的核心不是物質需求,而是二老的情感夙愿。像老張這樣典型的孤寡戶對發展信息的需求欲望并不強烈,他們大部分的生活費用和醫療費用都由子女承擔或政府兜底,少有人去過問這群鄉村老人的內心世界。陳建是在囑托二老鄰居幫助照顧二老時才獲取老人內心需求的信息,在這樣或直接或間接的信息互動過程中,陳建與二老建立起一種“擬親”的緊密聯結關系。
3.融入結對治理實踐的情感技術
中國歷來是情理法合一的社會,深具“情感國家”與“感性國家”的傳統。[33]中國的國家治理要根植于中國鄉土文化的傳統,以“情感”與“倫理”為本位的中國鄉土社會應重視“關系、人情”等情感元素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7]但稅費改革以來,隨著國家資源一同下沉鄉村的還有治理體系理性化、精細化的追求,理性化治理邏輯不斷在鄉村基層治理機構擴散而形成主要支配邏輯。在脫貧攻堅實踐過程中,數據留痕貫穿脫貧行動的始終,扶貧過程中各種貧困評價量表、規章制度、評估體系使扶貧行動不斷走向標準化、精細化和規范化,無不凸顯鄉村貧困治理行動中的技術治理邏輯。但筆者調研過程中發現,柔性的情感元素在結對治理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幫扶人員嵌入幫扶對象家庭的日常生活促進情感互動。“下鄉帶著真感情,何須專門去維穩”。[34]幫扶人員與幫扶對象之間的日常互動是開展扶貧工作和強弱關系轉化的前提,隨著扶貧工作的展開與深入,雙方的日常互動使得彼此的關系更符合鄉土社會關系的“熟人”邏輯,幫扶人員在與幫扶對象互動過程中收獲了幫扶對象的情感接納與信任。在扶貧實踐的早期,幫扶對象面對幫扶人員們“有文件,守規定”式的數據留痕評定方式,表現出難以適應甚至敷衍了事的態度,為了拉近與幫扶對象的心理距離,幫扶人員通過送油送米“增感情”,真幫實干“掏真心”到扶貧績效增收益的互動實踐,在扶貧工作中增進雙方的感情。扶貧工作是一個動態化的行動過程,面對不同貧根困因的幫扶對象,幫扶人員要在國家整體性的政策目標與個體化的發展需求之間找到合適的對接點,使抽象的治理目標以“柔性”的方式在脫貧實踐過程中達到具體化和在地化。在扶貧深化階段,幫扶家庭因生活變故導致脫貧阻滯等因素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進行積極情感建設,如建英在得知自己患病后成為家庭的負擔,產生愧疚自責的負面情感,楊琳通過自己在醫學知識上的優勢以“閨蜜”的身份對建英進行心理建設,建英在楊琳的開導下逐漸走出心理陰霾重建應對病情的積極情感;幫扶人員與幫扶對象在日常化的互動過程中不僅注重將正式化的治理技術進行“柔性化”處理后轉化為適合鄉土社會的超常規治理模式,也要注重利用這種“熟人”式的互動關系促進幫扶對象的積極心理建設,不僅拉近了雙方的感情,也增進了幫扶對象脫貧的信心,也就是所謂的扶貧要扶智的內在要求。
幫扶人員與扶貧對象的“擬親化”。早期中國的國家建設存在“從家到國”的發展路徑,這使得“家國同構”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底色與特性。[19]儒家文化中“推”的智慧,從推己及人說開去,有費孝通所稱的以個人為中心的差序格局,也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想。雖然歷史語境已不同,但在受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鄉土社會對這一政治理念仍有接納的空間,隨著幫扶人員與幫扶對象的聯結逐步深化,就由“熟人化”向“擬親化”的關系擴展開去,雙方的互動已逐步深入幫扶家庭的日常生活。在扶貧實踐過程中,陳建為了滿足老倆口想見外孫的愿望,與其女兒溝通,并出錢為老張家安裝了寬帶,這些在老張看來:“有時候有點事情不好意思麻煩他,實在我們不得行的還是打電話請他幫忙,他也熱情得很,進屋就問這問那的,別個和我開玩笑說我白撿了個兒子(笑),感覺自己的娃兒些有些事情他們還做不到,不過他們也是沒得法”。這種擬家人化的關系不僅是幫扶人員在脫貧過程中的情感收獲,對扶貧工作的開展大有助益,同時也預示一些幫扶對象真正的“貧”或許不是經濟的貧困,而是家庭倫理缺失的情感貧困。幫扶人員作為連接國家與幫扶對象的中介角色,在鄉土社會中以“顯性在場”的方式彰顯國家的“隱性在場”,在結對幫扶過程中幫助幫扶對象建立家國情感的心理認同。
4.結對治理融合“曉之以理”與“動之以情”的治理效能
雖然我國在絕對貧困問題上取得歷史性成就,但一些資源相對薄弱的鄉村地區仍有返貧風險,預留出鞏固脫貧成果與接續鄉村振興發展的夯實期,是實現由政府導治向自主發展轉變的基礎。幫扶人員的主要工作也從參與脫貧治理轉移到鞏固扶貧成果與接續鄉村振興的發展上來,雙方的結對關系仍在持續。在此期間,伴隨著鄉村網絡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數字技術在貧困治理過程中對個體的賦權及對治理主體的賦能使鄉村治理逐步朝著技術化路徑發展,在實現身體在場互動的同時也將線上互動融入到治理實踐中來。在此過程中,結對治理有利于兼顧技術化治理之下被遮蔽的個體化發展需求。
結對治理作為一種“曉之以理”與“動之以情”融匯實踐的治理方式,更能適應鄉村振興發展階段精細化的治理需求。韋伯認為“官僚制發展得越完備,它就越是‘非人化,在成功消除公務職責中那些不可計算的愛、憎和一切純個人的非理性情感要素方面就越是徹底”[35]。科層官僚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會排斥或消除個體的人際關系與情感要素,依此邏輯,在科層治理體系下政府利用技術與民眾建立的聯結機制也凸顯著科層理性與“非人化”的特征。結對治理作為一種超常規的治理方式,將技術的普遍服務優勢與個體化發展需求相統合,兼顧技術理性的同時也增進了與群眾間的情感互動。帕森斯認為“儒家在道德上支持的是個人對于特定個人的私人關系——在道德上強調的只是這些個人關系。為儒教倫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個中國社會結構,是一個突出的‘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36]或者按照牟宗三的表述,這種社會秩序建構方式“具有不容忽視的‘差別性‘特殊性或者‘個別性”[37],這是與西方普遍主義原則的不同之處。但中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政府主體的治理模式深受西方普遍主義的影響。數字技術作為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與政府科層治理體系相結合凸顯著普遍主義特征。而結對治理是一種特殊主義的治理模式,幫扶對象與非幫扶對象在發展過程中會體現出區別,幫扶內容也會隨著幫扶對象的發展情況而不同,這種充滿特殊主義特征的治理模式能夠適應鄉土社會發展極不均衡的特點。
就L村的脫貧實踐而言,結對治理前期高頻率的線下互動為后期個體化聯結的線上互動做好了情感鋪墊,幫扶人員脫貧后在“脫貧不脫幫扶”的政策指引下會定期主動了解幫扶對象的發展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技術治理邏輯下“壓力—回應”治理模式主動性較差的問題,幫扶人員熟悉幫扶對象的家庭實際情況與話語的表達邏輯,有利于發現和解決幫扶對象的真實需求。正如幫扶對象張召生所言:“現在沒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直接在微信上說了,我們基本上都是打視頻,感覺說話要親切點。實在有重要的事,老潘(幫扶人員)還是要下來,基本上十天半個月來一次,他來了我放下手頭的活路陪他耍,一擺就是幾個鐘頭,他和我們談話隨和得很”,結對治理模式依托移動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幫扶對象建立的聯結關系,結合信息技術普遍主義邏輯下“曉之以理”與個體化聯結“動之以情”的特點,一方面與幫扶人員建立起信任的“熟人”或“擬親”關系,良好的互動關系有利于將扶貧主體與客體的力量擰成一股繩共克貧困;另一方面通過幫扶人員與隱形在場的國家建立情感聯結關系,形成一種“過上好生活要感謝國家、感謝黨”的家國情懷。結對治理是基層治理主體結合制度環境與本土資源稟賦進行實踐探索的主動選擇,成為基層治理部門與群眾建立情感聯結貫徹群眾路線的重要方式,是兼顧科層權力下行與平等情感化互動的治理實踐形態。
四、結論與討論
隨著絕對貧困的終結,我國將邁入鞏固脫貧成果與鄉村振興發展協同推進的時代,前期的治理智慧和實踐經驗仍需加以總結和評價,有利于更好地與鄉村振興發展戰略相銜接。堅持城鄉融合發展的前提條件是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其中人才柔性的雙向流動為鄉村振興提供發展的智力資源配置,二十大報告中提到人才振興,這是因為人才是繪就鄉村振興藍圖的關鍵,是實現農村現代化的“臺柱子”。結對治理為城鄉人才流動提供了可供選擇與參考的經驗對象,也為我們理解基層治理主體在鄉土社會的治理實踐提供了具象認知。結對治理在適配鄉土關系信任的基礎上增進信息全知性與互動的具象化,以個體性嵌入幫扶家庭的方式精準配置治理資源,結合技術治理邏輯下“曉之以理”與個體化聯結“動之以情”的特點,將國家的“剛性”政策目標“軟化”處理后與幫扶家庭的發展需求對接,發揮可持續的治理效能,為更好接續鄉村振興發展提供可考經驗。
中國的鄉村治理是在一個相對分散、以小農戶為基本單位的鄉土社會中進行的,這一鄉土社會長期沁潤在傳統的地方性文化語境中,導致小農與鄉村社會都帶有很強的非現代國家印記。個體性嵌入式的結對治理更能適應鄉土社會治理問題日常化與生活化的特征,抽象化的制度與政策仍然需要具象化的人在實踐末梢發揮聯結作用。鄉村振興是在有效鞏固脫貧成果基礎上的全面振興,前期結對治理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結對關系與情感邏輯對接續后期發展仍有促進作用。首先,脫貧攻堅時期形成的信任關系仍然對鞏固發展成果有建設性作用,幫扶干部在脫貧攻堅時期已經對幫扶家庭的情況有詳實的了解,并與幫扶對象形成了長期良性的互動關系,也就意味著在后期發展階段,治理主體無需付出建立信任的成本,能夠更好地在原有基礎上鞏固脫貧成果,接續鄉村振興發展。其次,鄉村振興發展階段仍需要人才的下沉與在場。面對持續變遷的社會環境,鄉村家庭始終難以脫離社會變遷與時代浪潮的影響,外援性治理主體不僅要關注鄉村治理的制度執行層面,還要正視村民家庭日常生活中難以處理的困難與問題,治理主體嵌入鄉村家庭日常生活化的治理是鄉村治理轉型的內在要求。治理主體保持持續性在場解決幫扶家庭自身難以解決的日常生活困難,安頓幫扶家庭的生活秩序,是鄉村治理現代化難以回避的重要使命。
誠然,在認可結對治理在鄉村的實踐中發揮情感柔性化治理效能的同時,也應警惕技術下鄉導致長期在場的結對關系與情感互動脫離鄉村現實的治理場景。對此,仍需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情感異化,指的是治理主體在治理實踐過程中的情感治理技術有流于形式、表面的傾向,特別是依托移動互聯網進行線上建立和維持個體化聯結關系時,長期重視線上而忽視線下聯結易使情感工作技術化、固定化,長此以往,幫扶對象疲于應付后會采取行動規避異化的情感規訓,使結對幫扶關系失去原有的情感感召力;二是情感遮蔽,情感聯結在一定程度上是幫扶對象對幫扶干部在信息資源、人格魅力上的依賴,鄉村治理側重于“人”的治理,技術治理偏重于“事物”的治理,而幫扶干部在治理實踐中過于依賴技術化路徑會減弱聯結關系中的人格化色彩,凸顯事本主義特征。所以,在結對聯結的關系中,需要平衡技術媒介與身體媒介之間的關系,更需要平衡技術治理與個體化聯結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EB/OL].(2022-10-25)[2022-10-28].http://cpc.people.com.cn/20th/n1/2022/1017/c448334-32546752.html.
[2]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EB/OL].(2021-02-25)[2022-10-29].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69.htm.
[3]徐明強.基層政府治理中的“結對制”:個體化聯結與情感化互動[J].探索,2021(5):137-150.
[4]MAX W.“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M].Californi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212-217.
[5]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7.
[6]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學,2009(6):104-127+207.
[7]翟學偉.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情理社會中的社會交換方式[J].社會學研究,2004(5):48-57.
[8]朱智賢.心理學大詞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498.
[9]保羅·湯姆斯·揚.情感·意志·個性[M].魏慶安,譯.廈門:鷺江出版社,1988:412.
[10]孫穎,呂慧芬,張雪英.情感維度下的深度情感關聯模型[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19(5):24-30.
[11]埃里克·霍弗.狂熱瘋子:群眾運動圣經[M].梁永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53.
[12]王佳鵬.羞恥、自我與現代社會——從齊美爾到埃利亞斯、戈夫曼[J].社會學研究,2017(4):143-166+245.
[13]王寧.家庭消費行為的制度嵌入性[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187-220.
[14]張春興.現代心理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62.
[15]李鳳蘭,李飛.促進農村居民心理健康與實現精準扶貧[J].江西社會科學,2018(8):231-237.
[16]文軍,劉雨婷.40年來中國社會治理研究回顧與實踐展望[J].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27-37.
[17]王雨磊.緣情治理:扶貧送溫暖中的情感秩序[J].中國行政管理,2018(5):96-101.
[18]朱新武,譚楓,秦海波.駐村工作隊如何嵌入基層治理?——基于“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案例的分析[J].公共行政評論,2020(3):84-101.
[19]向德平,向凱.情感治理:駐村幫扶如何連接國家與社會[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6):84-93.
[20]丁建彪,張善禹.駐村工作隊在農村貧困治理中的多重功能[J].社會科學戰線,2021(8):176-183.
[21]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48-510.
[22]易法敏,文曉巍.新經濟社會學中的嵌入理論研究評述[J].經濟學動態,2009(8):130-134.
[23]胡守勇.文化扶貧的理論內涵與減貧機理[J].中州學刊,2022(8):86-93.
[24]袁立超,王三秀.非科層化運作:“干部駐村”制度的實踐邏輯——基于閩東南C村的案例研究[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131-137.
[25]羅鏗.高校圖書館文化精準扶貧中的角色定位研究[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7(5):16-19.
[26]黃輝.精準脫貧戰略下的圖書館文化扶貧精準識別、幫扶與機制創新研究[J].圖書情報知識,2017(1):49-55.
[27]鐘海.超常規治理:駐村幫扶工作機制與運作邏輯——基于陜南L村的田野調查[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64-74.
[28]孫笑非,張亞鵬.“上墻”與“落地”:國家治理視角下村規民約的現實困境與優化策略[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79-86+122.
[29]李丹陽,鐘楚原.駐村第一書記何以助推鄉村產業振興?——基于“差序嵌入—協同賦權”的分析框架[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22(5):602-609.
[30]董帥鵬.關系嵌入與精準偏離:基層扶貧治理策略及影響機制研究[J].中國農村觀察,2020(4):23-35.
[3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31.
[32]UZZI 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1):35-67.
[33]張磊,伏紹宏.結構性嵌入:下派干部扶貧的制度演進與實踐邏輯——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貧實踐為例[J].社會科學研究,2020(4):134-141.
[34]張尚初.中國多省掀新一輪干部上山下鄉運動 重拾魚水情[EB/OL].(2012-06-19)[2022-11-29].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6/19/content_25684619.htm.
[35]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2卷:上冊[M].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34.
[36]T·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M].張明德,夏遇南,彭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615-616.
[37]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2.
(責任編輯:王勤美)楊洋楊波,張婭,王勤美,蒲應秋
Abstract:The end of absolute poverty means that China is entering a period of pursing coordinated progress in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aired governance provides empirical objects for the mobility of urban and rural talents, and also concrete cognition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ubjects in local rural society. With the empirical materials from field survey, this study examines paired governance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emotional logic. It is found that paired governance enhances the informa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makes interaction more concrete if it matches the trust of local relations, and accurately allocates governance resources in the way of individual embedding in helping families; in addition, combining with the attributes of "being reasonable" in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nd "being emotionally connected" in individualized link, it turns the "rigid"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country to be "softened" and then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poor families, thus to bring into play sustainabl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 empirical experiences for further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paired governance; interaction; emotional logic; individual embedded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