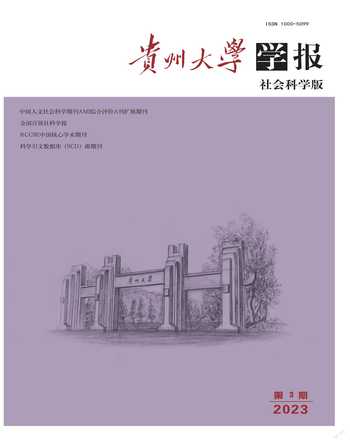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方向與路徑
作者簡介:李勇,男,安徽霍邱人,博士,南京市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東南大學反腐法治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方向與路徑
摘要:企業合規的本質是企業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的自我變革,屬于企業自治、協商治理,應當是“軟法”治理范疇。合規入法不是“條件-行為-后果”反向制裁的“硬法”立法模式,而是“合規-從寬”正向激勵法律化的模式。“軟法”意義上的法律化,既包括刑事法、行政法、公司法等正向激勵的“軟法”條款,又涉及官方指引、行業規范、協會標準等“軟法”規范,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補充,這是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基本方向。在法律化路徑上,刑事法應立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刑事訴訟法規定和完善刑事激勵措施;公司法設立法定代表人前科登記豁免等合規從寬的行政激勵措施,建立“檢察罰”制度,完善刑事激勵與行政激勵銜接與配合的機制。然而,合規有效性標準以及監管、評估機制屬于“最佳實踐”,不宜通過正式立法的方式建立,應通過官方指引、行業規范、協會標準等“軟法”規范來解決。
關鍵詞:企業合規;合規計劃;法律化;軟法
中圖分類號:DF63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099(2023)03-0060-12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這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合規是現代企業治理模式,是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必由之路。企業合規制度在我國起步較晚,大致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萌芽時期(2017-2018年)。我國最先引入企業合規的是金融領域,早在2017年中國證券業協會就出臺了《證券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合規管理辦法》《證券公司合規管理實施指引》。2018年的“中興事件”進一步激發了業界對企業合規的關注,這一年被稱為“中國企業合規元年”。同年,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人民銀行、國資委外匯局、全國工商聯出臺了《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國資委出臺了《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在國際標準ISO19600-2014《合規管理體系指南》的基礎上制定發布了GB/T 35770-2017《合規管理體系指南》。該階段企業合規主要停留在行業倡導層面。第二階段是制度試驗期(2020年)。2020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六個地方開展第一批試點。檢察機關的介入,企業合規從行業倡導轉入制度引進,面貌為之一新。檢察機關的行動表明企業合規的刑事激勵措施呼之欲出。第三階段是企業合規法律化的曙光期(2021年至今)。202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0個省級檢察院61個市級檢察院381個基層檢察院,開展更大規模的第二批試點;同年5月13日,國資委高調宣布中央企業已全部成立合規委員會;同年6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國家八部委發布《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2021年,還發生了一系列合規事件,如阿里巴巴被罰事件、滴滴公司被罰事件、美團公司被罰事件。2022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全國檢察長(擴大)會議上提出,3月份第二批試點結束后將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試點,為推動立法打好基礎[1]。2022年4月,全國檢察機關試點企業合規改革全面鋪開,由此表明企業合規的法律化已經進入快車道。
企業合規(又稱合規計劃或合規)本質上是企業自治、協商治理的模式,在法律上屬于“軟法”范疇。企業合規入法,不是一般意義上“硬法”的立法化,而是“軟法”的法律化。一般而言,立法是擁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通過嚴格的立法程序,制定法律的活動,立法過程是國家意志確認的過程,其條文的基本結構“條件-行為-后果”,以國家強制力保障法律后果實施。但是,這樣的“硬法”立法模式并不適用于合規。合規本質上是一種公司自治和協商治理模式,體現的是國家化到私人化的發展趨勢[2],是合規計劃與私人規范融入法律制度[3]。合規融入法律的過程并不是以“條件-行為-后果”反向制裁的立法模式出現的,而是“合規-從寬”的正向激勵的法律化模式。一般的立法化,是在法律中規定實施某種行為或不實施某種行為,將會引發何種法律制裁后果。但是,合規入法是企業建立和實施有效合規計劃將會獲得怎樣的激勵,并非是企業不建立合規將會引發怎樣的處罰后果。換言之,合規入法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立法化,并非將合規設定為企業的法定義務,也不是制定專門的“企業合規法”。合規入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現行法律中設定正向激勵的“軟法”條款,這不僅僅涉及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更為重要的是涉及行政法規、公司法等法律法規;二是制定出臺配套的官方規范性文件,以及行業標準、行業規范、協會標準化文件等“軟法”,這些文件雖然不是正式立法的結果,但它們屬于廣義上的法律。當今的法律體系包括“硬法”和“軟法”。它們不是以立法機關的意志為基礎,也不是國家權力的命令或者來自上層權威的強加,這是因為當法律被理解為一種有目的的活動時,它的存在取決于公民與立法、執法官員之間的有效互動與合作[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合規入法是合規的法律化,而非立法化。當前,學界討論企業合規立法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忽視了合規作為“軟法”治理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片面聚焦于刑事法的修改,而忽視行政法規、公司法等經濟法的修改,企業合規的理論研究也呈現出“刑熱行冷”的現象。企業合規的法律化是一項體系龐大的系統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更不是通過修改刑事法就畢其功于一役的。
二、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方向
當前,實踐中存在將企業合規膚淺化和庸俗化的現象,有的把合規理解為遵紀守法,有的把合規理解為“合乎法律規定”。企業合規從20世紀90年代誕生至今,被世界很多國家所采納吸收,經歷了從預防犯罪內部機制到企業治理結構變革、從注重管控到注重企業文化的發展歷史。當下,企業合規本質內涵在于企業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的自我變革,這決定了合規入法的方向是引導型、激勵型的“軟法”模式,而不是強制型、制裁型的“硬法”模式,這也是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基本方向。
1.以企業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自我變革為目標
首先,企業合規的核心在于塑造合規的企業文化[5]。傳統觀點認為,企業合規是為預防、發現犯罪行為而由企業實施的內部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措施、機制(組織體系)[6]。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樣的內涵其實是20世紀90年代企業合規在美國誕生之初的界定,可謂合規的“古典定義”。這種“古典定義”來源于美國《組織量刑指南》(1991年),該指南將企業合規界定為旨在預防、發現和舉報組織犯罪的內在機制,如果組織能夠證明曾試圖通過建立一個有效的、適當的合規計劃來阻止不當行為發生的話,為被判有罪的公司減輕刑罰處罰。《組織量刑指南》確立了有效合規計劃的七項基本要求,包括采用政策和程序來預防犯罪行為、高層人員對合規計劃的適當監督、將合規的要求傳達給所有員工,并根據需要進行監控并持續更新合規計劃等。這種古典意義上的企業合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企業為預防、發現犯罪行為避免被制裁、處罰而建立完善的內部機制。二是建立了合規計劃的企業,國家給予鼓勵回應,作為減輕甚至免除處罰的依據。這樣,企業建立合規計劃類似于“種植胡蘿卜”[7]。
這種“古典定義”的合規并沒有止步不前,而是不斷向前發展。2004年美國量刑委員會對《組織量刑指南》進行了修訂,最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引入組織文化,特別使用了“合規和道德計劃”(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的表述,強調組織文化對合規的重要性,要求企業不僅要促進“守法”,還要促進“道德行為”。這將組織文化正式作為組織量刑指南的一部分,將有效合規計劃描述為旨在“預防和發現犯罪行為”以及改善組織文化的內控機制,這種組織文化是“鼓勵符合道德的行為和承諾遵守法律”的文化[8]691-692。2010年以后,組織文化作為企業合規的內涵進一步強化。美國聯邦量刑委員會于2010年再次修訂了《組織量刑指南》,提高了設立首席道德與合規官(CECO)(或類似角色)的重要性[9]。從合規計劃到合規道德計劃,從首席合規官(CCO)到首席道德與合規官(CECO),體現企業文化(組織文化)在企業合規內涵中的地位變化。到20世紀末,組織文化在合規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可[10]942。2014年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了《合規管理體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19600)的推薦標準,后于2018年11月啟動修訂,形成了2021年《合規管理體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37301)的認證標準,其最大的特點是融入企業文化,在引言第一句就指出“為獲得長期成功的組織需要,基于相關方的需求和期望建立和維護合規文化。”
從企業合規的發生發展的歷史進程看,經歷了從強調管控(control)到重視企業文化(culture)的歷史。早期的合規計劃主要側重于通過從寬處罰來激勵企業建立管控合規風險的制度,后期以誠信為基礎的合規計劃則側重于建構組織文化。據此,現代意義企業合規的基本內涵應當為:旨在預防和發現違法犯罪行為以及改善企業文化(即“鼓勵合道德的行為和承諾遵守法律”的企業文化)的企業內控體系[8]689-692。如今,以誠信為基礎的合規計劃占主導地位,合規文化已經成為企業合規的核心所在。合規的“規”不限于刑事法,其預防的也不僅僅是犯罪,還包括違法甚至不當(不合道德)的行為。《合規管理體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37301)指出,“一個有效的、組織范圍內的合規管理系統使組織能夠證明其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要求、行業規范和組織標準,以及良好治理標準、普遍接受的最佳實踐、道德和社區期望的承諾”。美國《聯邦商業組織起訴原則》(2019年修訂版)對合規計劃的界定是“由公司管理層制定,以防止和發現不當行為,并確保公司活動按照適用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法規和規則進行。”[11]
從上述兩個代表性的文件可以看出,合規的“規”具有開放性,涵蓋了刑事、民事法律、法規,以及“軟法”意義上的規則。因此,現代意義上的企業合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預防、發現不當違法犯罪行為的內控體系;二是塑造合規的企業文化。企業建立事前合規,就是要塑造合規的企業文化;涉案企業重建合規計劃(事后合規),就是要重塑合規的企業文化。企業合規之所以重視文化建設,原因在于企業文化決定員工的行為選擇。一個行賄成風的企業文化,在企業內部形成以行賄獲得銷售業績為榮的氛圍,其員工開展銷售業務時必然傾向于選擇行賄。反之,一個廉潔的企業文化氛圍,會向每一位員工傳達廉潔行事的信號。建立中國特色的企業合規制度,應當以世界的眼光,與最新的國際標準接軌,以塑造合規的企業文化為目標。
其次,企業合規的關鍵在于改善治理結構。人們習慣于望文生義地將企業合規理解為合法經營、遵紀守法。其實,這樣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甚至會產生重大誤導。人類社會自從有法律以來,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守法律。作為一個企業,合法經營、遵守法律并不是一個新事物,也不是一個新想法。當今的企業合規,是嶄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其特別之處在于在公司內部設定一個獨立的部門或者專門人員來檢測和阻止違反法律和政策的行為,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將合規融入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改變其原有的領導層權力架構和管理模式。傳統公司治理結構主要體現為業務管理(首席執行官CEO)和財務管理(首席財務官CFO),現在增加了一個首席合規官或者首席道德與合規官(CCO或者是CECO),企業內部權力結構從原來的主要是“兩駕馬車”變革為“三駕馬車”。在這種權力框架下,通過系統的制度體系將合規融入企業管理全過程。合規是一種嶄新的公司治理模式,顛覆了傳統的公司治理理論[12]。企業內部權力架構、運行模式至此發生根本性變化。不觸及企業治理結構的合規不是真正的合規,不能改善企業治理模式的合規不是有效的合規。改善了治理結構的合規能夠阻止和預防企業違法犯罪行為,節約了國家治理企業犯罪的成本,因此,國家鼓勵企業建立合規計劃。這樣,國家其實是通過減免處罰的方式將預防企業違法犯罪行為的職責轉移給企業自身,這是一種企業自我管理、協商治理模式。
總之,企業合規關鍵在于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改善,本質目標是塑造合規的企業文化,法律的任務是給予這樣的企業以激勵措施。
2.以正向激勵“軟法”模式為基本方向
如前所述,企業合規是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變革,合規文化是其本質目標。文化需要一種合作、柔性的力量,靠強制壓力可能會適得其反。“政府關于合規文化的政策可以通過充足的‘陽光和關懷在公司內部培養親社會、守法的力量。”[10]976因此,“軟法”是合規法律化的基本方向。
一般認為,“軟法”是不運用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律規范,并不一定都是通過嚴格的立法程序,“軟法”以協商一致為法律通過的要件,而不是采取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機制。在制定程序上,從嚴格的法定程序、立法程序到簡易的磋商、談判、協調等多元化方式。與“軟法”相對應的是傳統的“硬法”,“硬法”來源于國家意志的確認,來源于議會的代表,來源于議會議事的多數票決規則,來源于嚴格的立法程序等[13]。“硬法”的立法模式是“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后果”,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其實施,而“軟法”沒有明確的行為模式,一般不規定法律后果,即使規定了法律后果,也是正向激勵的積極法律后果。“軟法”是提倡性法律規范,是激勵和引導人們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法律規范。行為人遵守這種規范能獲得相應的激勵,比如稅收優惠、政策照顧等;行為人即使違反這種倡導性的法律規范,也并不會導致承擔法律責任。“軟法”具有自律性或引導性、建議性、激勵性、協商性等特點。“硬法”強調他律,“軟法”側重自律。“軟法”的法律淵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正式立法中的“軟條款”;二是政治組織形成的規則和社會共同體形成的規則[14]。前者如《公司法》第5條第1款“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后者系指未經正規程序成立之法規范,比如政治組織的章程和規范性文件、行業協會對本行業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章程[15]。上述兩種淵源的“軟法”均屬于廣義的法律范疇。
合規和“軟法”一直是法律學者和社會學家熱議的話題[16]。如今,商業、金融和其他國際商業交易越來越多地在“軟法”規則下進行。我們正在見證傳統監管的衰落,監管體系逐漸被一套無定形且不斷演變的非正式“軟法”治理機制所取代[17]。遺憾的是,我國學界對“軟法”和合規之間關系的研究比較落后。近兩年,隨著企業合規理論的熱議,有學者已經關注到這一話題,針對《公司法》第5條第1款指出,“公司軟法重心在于激活公司自我規制和守法效應”,在公司內部建立一種長效的監督性守法約束機制,據此建議公司法通過提倡性條款,鼓勵公司通過章程規定建立科學的自我管理機制,積極培育合規守法文化[18]。此前,公司法學界主要從“軟法”角度研究該條款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化問題,尚未觸及企業合規理論,認為該條款是倡導性規定,并沒有規定法律責任或后果,以鼓勵或一般性義務的形式向企業提出要求,但法律并不能直接強制企業承擔,這種社會責任可稱之為狹義的軟法責任[19]400。
合規作為一種企業自治,是企業的自我選擇,法律的任務不是將合規規定為企業的法定義務,而是通過法律設定激勵措施來鼓勵和引導企業建立合規計劃。對于事前合規而言,企業建立并有效實施合規計劃,將來涉案時可以成為切割企業與個人責任以及獲得從寬處罰的事由;對于事后合規而言,企業可以自愿重建合規,經評估有效后,執法、司法機關將給予從寬處罰。美國《組織量刑指南》確立的合規計劃正是這個思路。除此之外,美國還有大量的“軟法”來鼓勵企業建立合規管理體系。美國學者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幾乎完全是由穩健的民間社會組織和企業本身來完成的,往往是為了響應來自投資者和消費者的市場壓力而增加非政府組織的要求。美國聯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開發了各種合作執法工具來促進企業自愿遵守監管規定,其典型例子包括20世紀90年代“重塑環境法規”倡議下推出的40多個合規項目,以及與職業健康和安全相關的類似聯邦和州的合規計劃項目[19]389。意大利作為較早從美國移植企業合規的大陸法系國家,于2001年6月8日通過首部企業合規法令《關于法人、公司、協會及非法人組織行政責任的法令》(簡稱第231號法令)。根據該法令,如果企業在犯罪后的悔改表現較好,檢察官可以建議對企業適用一系列激勵措施,例如,減少經濟處罰的數額,或者不再對有悔改表現的企業適用褫奪資格處罰等。如果企業在犯罪之前已經通過并有效地實施了適合于預防此類犯罪的組織、管理和控制模式(即合規計劃),則可以排除企業不履行監督或者管理義務的責任[20]。
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基本方向,應當堅持“軟法”治理理念。合規是企業治理理論,本質在于改善治理結構和塑造“良好企業公民”的文化,屬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企業社會責任講究自愿履行,政府采取“軟性”管制,政府應當作為參與者、組織者、促進者和引導者,采取積極的激勵措施而不是懲罰措施。一方面,合規是企業的自我選擇,不應將建立和實施合規計劃作為企業的法律義務[21],通過法律上從寬處罰的制度設計來激勵企業自主合規。這里的法律不限于刑事法,也包括行政法、公司法等。另一方面,合規也包括制定配套的官方指引、規范性文件,以及行業標準、規范、協會標準化文件等“軟法”。事實上,在我國企業合規早期興起的金融領域,已經存在大量的合規“軟法”,例如,《證券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合規管理辦法》《證券公司合規管理實施指引》《企業境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中小企業合規管理體系有效性評價》等。這些“軟法”規范的最大問題在于大多停留于口號式宣傳,缺乏實質有效的激勵措施,往往流于形式。
三、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路徑
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路徑,在刑事法領域應當立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建立刑事激勵措施,在經濟法領域建立合規從寬的行政激勵措施,這屬于在正式立法中設定“軟法”條款;同時,通過制定官方指引、行業規則、協會標準等“軟法”規范建立合規有效性標準、監管及評估等機制,兩方面相互配合、相互補充。
1.建立以認罪認罰從寬為基礎的刑事激勵機制
2018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增設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控辯協商制度,給予自愿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從寬處罰的激勵,但不會強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認罪認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選擇的一種權利,而非義務,是一種典型的激勵性“軟法”條款,也是中國特色企業合規在刑事法領域法律化的基本路徑。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試點文件也明確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企業合規試點改革的基本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開展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方案》中明確要求開展企業合規試點改革要與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結合起來。2021年6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等9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第4條規定,涉案企業開展合規的首要條件就是“涉案企業、個人認罪認罰”。筆者認為,我國刑事法在未來立法上引入企業合規的立足點仍然應當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基點。
首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我國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適用對象原本就包含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企業實施的單位犯罪理當具有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余地。
其次,自然人的認罪認罰態度通過其言行征表。作為“沒有靈魂和肉體”的企業,其認罪認罰體現在合規計劃上。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具有“企業公民”的地位,企業文化影響和塑造員工的行為,“什么樣的企業文化產生什么樣的員工”。企業作為一個組織體,企業文化類似于自然人的靈魂。一個合規的企業文化,再犯可能性降低,預防必要性降低,進而導致量刑中的預防刑降低。“如果個人刑法要求個人只在他或她的行為應受譴責的情況下才受到懲罰,那么公司刑法也應該對公司提出同樣的要求”[22]。企業因有效的合規計劃,預防犯罪的必要性隨之降低,預防刑減少,進而獲得從寬處罰。這與自然人認罪認罰導致預防刑降低而獲得從寬處罰的機理是一樣的。
最后,企業合規與認罪認罰從寬均屬于合作型司法的范疇。企業合規是一種企業違法犯罪控制和治理的合作模式,國家將治理企業違法犯罪的職責轉移給企業自身,實現企業違法犯罪治理由“對抗模式”走向“合作模式”。在美國,企業合規不起訴協議本來就是和解和辯訴交易的一部分,也是一種合作型司法模式。可見,企業合規從寬與認罪認罰從寬均屬于合作型司法的范疇。
近年來,關于企業合規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關系問題在理論界出現了一些爭議。有學者認為,合規不能單純作為量刑從寬的因素,而應當作為出罪因素;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效率為導向,強調節省資源、降低成本、快速處理案件,通過給予認罪認罰的嫌疑人、被告人較為寬大的處理,形成一種激勵效應,使得更多的嫌疑人、被告人選擇認罪認罰程序,實現刑事案件的快速辦理。相比之下,合規考察制度則強調企業合規整改的有效性,要求設置足夠長的合規考察期,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司法資源[23]。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首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企業合規在本質上都是“協商治理”模式。“協商治理”是這兩項制度的最根本特征,也是二者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是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其次,效率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價值追求之一,而非全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基本特點是實體從寬和程序從簡,程序從簡的效率目標只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特征之一,更為重要的特征是實體從寬,通過實體從寬實現犯罪治理模式從“國家-被告人”二元對立向合作型司法轉變。再次,認罪認罰從寬中的從寬既包括量刑上的從輕,也包括不起訴。事實上,不起訴本身就是一種程序出罪。從合規的實踐試點情況看,大部分案件都作了相對不起訴處理,這本身就是一種程序上的出罪。最后,企業合規與認罪認罰一樣,都是訴訟經濟原則的產物,二者在追求訴訟效率問題上具有相同的趣旨。由于企業內部結構具有高度復雜性,偵查和調查成本極其高昂,指控難度極大。企業合規通過控辯協商實現節約偵查、調查成本,降低指控難度,進而實現訴訟經濟和效率的目標。企業合規在美國誕生的重要契機之一恰恰是公司犯罪、白領犯罪,其偵查和指控成本高昂。例如,著名的西門子案件,案件事實涉及向65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行賄14億美元。西門子進行內部調查就花了5億美元的費用[24]。暫緩起訴協議(DPA)通過讓涉案企業承認犯罪事實,從而節省調查成本。至于說企業建立合規計劃之后的考察周期長、成本高,其實已經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訴訟效率問題了。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本身就是一個訴訟程序的終結,案件偵查、審查以及罪名適用等實質性的實體和程序事項均已經辦結,合規計劃的考察評估主要是檢察機關依托第三方的社會資源進行,一旦有效性評估考察通過,只是程序性地作出最終不起訴決定;評估考察不通過,則提起公訴,也無需再次審查證據。因此,與其說合規不起訴的評估考察是訴訟程序事項,毋寧說是在訴訟程序“延長線”的一個社會治理事項。
總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我國企業合規進入刑事法律之中的路徑依然是“不二選擇”,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基礎,在刑事訴訟法中建立起不捕、不訴、量刑從寬三位一體的激勵機制。對于企業犯罪來說,現有的相對不起訴面臨諸多瓶頸,對涉罪企業相對不起訴之后,缺乏監管措施進行后續監督。無論是相對不起訴之前還是之后,檢察機關都無法觸及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革,無助于改變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和企業文化,久而久之,會導致對企業犯罪“網開一面”甚至“變相放縱”。只有建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將合規計劃的建立和實施作為不起訴的附加條件,并設置足夠長的考驗期,給予涉罪企業以“考驗不合格隨時被起訴”壓力,才能真正激勵和倒逼企業治理結構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美國的DPA(暫緩起訴協議)一樣,附條件不起訴是企業合規的“標配”,需要在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增加企業附條件不起訴的條款。筆者曾建議采取修正案模式在刑事訴訟法中增設第182條之一和第182條之二,分別規定企業附條件不起訴的條件、范圍、考驗期等[25]。這是企業合規在刑事法領域法律化亟待解決的事項。
企業合規除了不起訴之外,還有量刑從寬。當前試點有一個誤區,將企業合規的“火力”集中在不起訴方面,無論是發布案例還是改革政策宣傳,都集中在不起訴。有些地方甚至提出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也可以不起訴。其實,合規從寬既包括不起訴,也包括量刑從輕、減輕處罰。在美國,對企業可以減少罰金的90%[26]。將量刑從寬作為企業合規刑事激勵措施的意義在于:一是解決企業合規適用對象的問題。如果說合規不起訴一般適用于輕罪案件,那么合規量刑從寬則適用于所有案件和罪名。這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于所有案件和罪名是一樣的。二是防止以合規之名違反罪刑法定。如果將企業合規的刑事激勵措施僅瞄準不起訴,那么對于一些重罪案件,動輒以合規為由進行不起訴,那么就可能存在違反罪刑法定的風險。從法律化的角度來說,合規量刑從寬并不需要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現行刑事訴訟法關于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規定,完全可以作為合規從寬量刑的依據。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刑法是否需要同步修改呢?筆者認為刑法無需修改。在2018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寫入刑事訴訟法的時候,有人提出刑法應當同步修改,但并沒有被立法機關采納。甚至有人認為,僅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給予從寬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片面割裂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違反刑事一體化的基本法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企業合規制度是典型的實體與程序交叉的領域,是在程序法中規定還是實體法中規定,只是一個立法技術選擇的問題,不能因為是實體與程序交叉的問題,就要求實體法和程序法必須重復規定。例如,追訴時效也是典型的實體與程序交叉的問題,有的國家把追訴時效問題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中,日本的追訴時效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250條。我國的追訴時效是規定在《刑法》第88條之中的,從立法表述上看,“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這里的立案偵查、逃避偵查或審判、被害人、控告、立案都是程序性術語,但卻規定在實體法之中。不能因為追訴時效規定在實體法之中,就否認追訴時效是一個程序問題;不能因為刑事訴訟法中沒有對此進行規定,就認為執行刑法的規定是違反程序法的。從刑事一體化的角度來說,對于實體與程序交叉的問題,立法上沒有必要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上進行重復規定。從節約立法資源的角度來說,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總則上已經規定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因此,企業合規的內容在刑事訴訟法中進行規定,在立法技術上更加科學合理。
2.建立合規從寬的行政激勵措施
對于企業來說,因違法面臨行政處罰的風險比較多見,因犯罪面臨刑事處罰的風險并不多見,且企業犯罪以行政犯為主,而行政犯具有行政從屬性,以違反前置的行政法規為前提,因此,企業合規的法律化,如果只考慮在刑事激勵措施而忽視行政激勵措施,不可能實現企業合規的治理目標,更何況企業合規的“規”原本就具有開放性。我國關于企業違法的行政處罰措施主要分布在公司法、證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環境保護法、稅法等經濟法領域《行政處罰法》與經濟法中的行政處罰條款是一般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分散在經濟法中的行政處罰條款屬于廣義上的行政處罰。同樣,“行刑銜接”不僅僅是指《行政處罰法》與刑事法的銜接,還包括經濟法領域的行政處罰條款與刑事法的銜接。。合規計劃的建立和實施,是一項高成本的事業,如果沒有充分完備的激勵措施,對于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在相關經濟法中增設合規從寬激勵的“軟法”條款,是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的基礎性工程。
首先,增設行政處罰從寬的“軟法”條款。企業合規在經濟法領域的法律化,并不是在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之中強制企業必須建立合規計劃,也不是規定不建立合規計劃給予相應處罰的“硬法”條款;而是在這些法律中設置“軟法”條款,規定事先已經建立了合規計劃的企業,在違反行政處罰條款時可以獲得從寬處罰;事先沒有建立合規計劃,在違法行為發生后自愿建立和有效實施合規計劃的可以獲得從寬處罰。行政執法機關可以與涉案企業達成行政和解協議,并要求企業建立合規計劃,經考察有效的合規計劃,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行政處罰。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隱含了企業合規的行政激勵措施,其中第25條規定,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從事不正當競爭,有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后果等法定情形的,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我國《反壟斷法》第45條、《反傾銷法》第31條、《<知識產權海關保護保護條例>的實施辦法》第27條、《證券法》第171條均規定了行政和解,遺憾的是沒有明確使用“合規”的表述。但是行政執法實踐已經走在了前面,引入了合規的因素。例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美團公司作出罰款3442億元的行政處罰決定的同時,向美團公司發出“行政指導書”,要求美團公司全面整改并連續三年向市場監管總局提交合規報告[27]。
現行法律在已有的行政和解基礎上,進一步增設合規激勵的“軟法”條款,明確將企業合規作為從寬處罰的依據,建立企業合規的附條件行政處罰制度,這是我國企業合規在經濟法領域法律化的重要路徑。如前所述,我國《公司法》第5條第1款的“社會責任”條款,屬于典型的“軟法”條款,只規定了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但是并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和后果。公司法領域的學者認為,這個條款用意不在于確定具體的義務責任,只是指出一種價值方向,沒有規定公司社會責任的權利義務內容以及違反義務的后果[28]。有學者批判認為,該條款沒有相應的法律責任作為后盾,從規范意義上講是不完整的,只有行為模式而缺乏行為后果的內容,難以起到規范主體行為的作用[29]。其實,這是對“軟法”的誤解,“軟法”的特征就是正向激勵,沒有規定違反該條款的后果并非該條款的缺陷,真正的缺陷在于沒有規定履行了該條款的責任將會獲得相應獎勵。只有配套規定激勵措施,才符合合規“軟法”治理以正向激勵為基本模式的要求,而不同于傳統“硬法”負向制裁模式。遺憾的是,《公司法》當時修改并無合規理論支撐,沒有規定相應的激勵措施,導致該法第35條第1款成為“沉睡條款”。在龐雜的經濟法、行政法之中增設合規“軟法”條款,是一項系統工程,雖然任務艱巨,但卻不得不努力推進。
其次,建立合規行刑激勵的銜接機制。行政激勵措施、刑事激勵措施的相互銜接和配合是企業合規得以良好運行的基本條件。刑法是其他法的保障法,行政犯的典型特征是以違反前置的行政法規為前提,而企業犯罪的常見類型都是行政犯。從預防犯罪的角度來說,在到達刑事違法之前,通過行政處罰予以截堵無疑是最理想的。當前,亟待解決的兩大行刑銜接問題:一是“檢察罰”制度。與美國不同的是,我國檢察機關對企業犯罪做出不起訴決定后,并無罰款權。實踐中,行政執法機關發現企業涉嫌犯罪時移交給公安、司法機關,檢察機關針對企業合規做出不起訴決定后,會給行政機關發出檢察意見書,建議行政機關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但是這種權宜之計大大影響了合規不起訴在替代刑事處罰方面的功能發揮。實踐中,還存在檢察機關頗費周折地讓企業建立并實施合規計劃,進而作出不起訴處理,努力救活企業,但行政機關沒有將合規作為行政處罰從寬的因素考慮,甚至把企業“罰死”了。為扭轉這種現象,對于那些由行政執法案件轉化過來的刑事案件,檢察機關在作出合規不起訴決定時,可以直接科處包括罰款在內的行政處罰,在立法上建立類似于“檢察罰”的制度[30],這是我國企業合規法律化值得考慮的選項。二是改革企業法人前科職業禁止制度,建立企業合規法人前科登記豁免制度。2021年4月1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12條延續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因貪污、賄賂、侵占財產、挪用財產或者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被判處刑罰,執行期滿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滿未逾5年,不得擔任企業法人。涉案企業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人如果是法定代表人,通過合規考察,被判處緩刑,按照《條例》規定,這個企業必須變更法定代表人,但是對于很多中小企業來說,銀行貸款授信、客戶合作都是基于對法定代表人的信任,一旦變更法定代表人就意味著企業倒閉。這樣,檢察機關通過企業合規試圖實現“放過企業”的目標就落空了,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倒閉了企業”。這是迄今為止企業合規研究領域尚未關注的。從企業合規的行刑銜接角度來說,應當對這樣的企業法人前科職業禁止制度進行改革,在《條例》中設立企業合規法人前科登記豁免制度。
3.建立合規有效性標準及監管、評估的“軟法”規范
企業合規始終面臨的靈魂拷問是合規計劃能夠有效地阻止和預防違法犯罪行為嗎?美國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合規計劃經過努力可以是有效的,有效的合規也是可以實現的,但是如何監管和評估合規計劃的有效實施,有效性的標準如何確定問題遠未達成共識[31]。合規計劃有效性的監管、評估問題在其發源地美國,從誕生之日起如影隨形,原因在于合規計劃的體系很容易被模仿,通過模仿而搭建合規計劃體系,并沒有真正降低不當行為的發生率,司法機關和監管機構也很難確定其有效性[32]。合規有效性標準、監管、評估配套機制的制度化、規范化是這項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合規有效性標準、監管、評估是典型的“最佳實踐”,屬于非正式政府行動的產物,但是其所發揮的作用,甚至比正式的立法更大[10]964,合規有效性標準、監管、評估等機制難以在國家正式立法中進行規范,但是專業標準領域推薦性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等“軟法”更有靈活性,效果更明顯。
首先,建立多元化的評估標準和辦法。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市場主體多元化,其中小微企業數量龐大。截至2021年10月,我國小微企業主的數量已達到了8 000多萬,它們占據了中國90%的市場主體,貢獻了80%的就業,60%以上的GDP。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平均每戶小型企業帶動8人就業[33]。小微企業在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實現科教興國、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是我國市場經濟主體中數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業群體。但是我國小微企業普遍存在家族式管理、合伙人式管理,經營管理方式粗放,人治色彩濃厚,企業與企業家合二為一、家企一體。公司戰略定位、生產、營銷及售后缺乏專業流程管控,缺乏有效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同時,還面臨經營成本壓力大、市場競爭激烈、融資困難等難題。一般而言,企業合規作為高成本的事項,適用于中大型企業。對于小微企業來說,不僅成本高昂是不可承受之重,更為重要的是其規模和結構決定了不可能建立完備的合規計劃。這種現狀決定了中國的企業合規制度,不能忽略小微企業這樣如此龐大的市場主體。小微企業涉案時,同樣不能“一訴了之”,應當給予其重建合規計劃的機會和關懷,在對其合規計劃實施的監管、評估標準和方法上應當不同于大中型企業。《合規管理體系要求及使用指南》(ISO37301)對合規計劃列舉了組織環境、領導作用、策劃、支持、運行、績效評價、改進7項要素26個子要素,并規定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組織,不論其類型、規模和性質。但是,對于一些小微企業來說,整齊劃一地全部滿足26個要素既不現實,也無必要。譬如,一個只有十幾個人的企業,成立合規委員會就不現實,至多設立合規專員,要做到“一案一企”“一企一策”。什么樣的企業需要什么樣的合規計劃,不同規模企業的合規計劃是不同的,關鍵是符合“四性”“三C”。“四性”即適應性、針對性、具體性和可操作性。適應性要求合規計劃要符合具體企業的實際情況,針對性要求合規計劃應當針對識別的風險而不能漫無邊際,具體性要求合規計劃的制度設計要融入業務流程且具體可見,可操作性要求相應的措施、政策易于實施操作。“三C”即清晰(clear)、簡潔(concise)、完整(complete)。清晰,即政策必須易于理解;簡潔,即說你需要的和需要你說的(Say what you need,and need what you say);完整,即策略和計劃全面覆蓋業務流程[34]。
其次,建立協同監管機制。在我國,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通過行政訴訟監督、行政公益訴訟、檢察建議等方式,對行政機關具有監督職能。特別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在政策上支持了檢察機關監督違法行政行為,這種特殊的監督構造,有利于檢察機關統合行政機關的力量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合規協同監管模式。企業合規是社會系統工程,檢察機關應協同地方行政機關與之形成合力。檢察機關可以牽頭工商、市場、稅務、審計、建設、司法、環保等行政機關聯合成立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管委員會,組建企業合規監管專業人員名單庫,選派第三方監督評估小組對涉案企業合規計劃實施監管。在行政違法案件中,以行政機關為主導,委托第三方監管組織,對涉及行政違法的企業合規計劃實施監管。在刑事犯罪案件中,檢察機關作為涉案企業合規的辦案機關,委托第三方監管組織監管。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八部委發布的《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確定的原則是“檢察主導、各方參與,客觀中立、強化監督”,可以說這是一種協同監管模式。協同監管模式被認為是這一種合規監管的成功模式,原因在于它創造了由資源共享、合作、信任而產生的共贏局面。
上述有效性標準以及監管、評估機制均屬于操作層面的制度建設,無需在立法層面規定,不是立法化的問題,而是作為“軟法”的法律化問題,可以通過官方規范性文件、行業規則、協會標準等“軟法”予以規范。對于事后合規,可以借鑒美國的《組織量刑指南》《企業合規計劃評估》(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的做法,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相關部門制定規范性文件;對于事前合規,可以由行業協會等制定相關推薦標準。例如,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于2022年5月23日發布了《中小企業合規管理體系有效性評價》團體標準;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于2022年10月12日發布了GB/T 35770-2022/ISO 37301:2021《合規管理體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這些都屬于“軟法”的范疇。
四、余論
當前,企業合規試點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在刑事司法領域,截至2023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企業合規案件5 150件,已有1 498家企業整改合格[35]。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發布了四批企業合規典型案例。在行政執法領域,國家工商總局針對阿里巴巴、滴滴、美團等大型公司作出行政處罰的同時,指導、督促其合規整改、提交合規報告,但是地方行政執法機關的合規行動乏善可陳。從試點的情況來看,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但也暴露諸多問題。例如,小微企業與大中型企業差異問題、放過企業還是放過責任人問題、合規計劃流于紙面問題、行刑銜接問題、監管評估標準不明確不規范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中,既有企業合規領域的共性問題,也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單純的移植國外制度、直接套用國際標準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針對中國國情,提出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構建中國特色的企業合規制度,必須全面系統建立“軟法”體系,絕非僅僅修改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就能畢其功于一役。
參考文獻:
[1]孟亞旭.最高檢: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將在全國推開[EB/OL].(2022-07-12)[2023-03-05].https://t.ynet.cn/baijia/33051271.html.
[2]托馬斯·羅什.合規與刑法:問題、內涵與展望——對所謂的“刑事合規”理論的介紹[J].李本燦,譯.刑法論叢,2016(4):357.
[3]烏爾里希·齊白.全球風險社會與信息社會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紀刑法模式的轉換[M].周遵友,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271.
[4]J.ELLIES.The King Is Dead.Long Live the King:A Reply to Matthias Goldman[J].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2(2):370-371.
[5]李勇.涉罪企業合規有效性標準研究——以A公司串通投標案為例[J].政法論壇,2021(1):137.
[6]M.GOLDSMITH,C.W.KING.Policing Corporate Crime:The Dilemma of Internal Compliance Programs[J].Vanderbilt Law Review,1997(1):9.
[7]Growing the Carrot:Encouraging Effective Corporate Compliance[J].Harvard Law Review,1996(7):1794.
[8]C.FORD,D.HESS.Can Corporate Monitor-ships Improve Corporate Compliance?[J].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2009(3).
[9]D.HESS.Ethical Infrastructure and Evidence-Based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s: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Empirical Evidence[J].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Business,2016(2):340.
[10]D.C.LANGEVOORT.Cultures of Compliance[J].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2017(4).
[11]The Department of Justic of the United Stated[EB/OL].(2023-03-01)[2023-03-05]https://www.justice.gov/jm/jm-9-28000-principles-federal-prosecution-business-organizations#9-28.010.
[12]S.J.GRIFFITH.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Compliance[J].William & Mary Law Review,2016(6):2 077.
[13]羅豪才,周強.軟法研究的多維思考[J].中國法學,2013(5):104.
[14]羅豪才.公共治理的崛起呼喚軟法之治[J].行政法論叢,2008(11):5.
[15]劉宗德.臺灣證交法強制公開收購制度之合憲性及改革論議[J].月旦法學雜志,2015(10):86.
[16]D.E.Ho.Compliance and International Soft Law:Why Do Countries Implement the Basle Accor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2(3):647.
[17]S.L.SCHWARCZ.Soft Law as Governing Law[J].Minnesota Law Review,2020(5):2 471-2 472.
[18]王蘭.公司軟法定位及其與公司法的銜接[J].中國法學,2021(5):274-275+281.
[19]V.H.HO.Beyond Regulation:A Comparative Look at State-Centr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w in China[J].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2013(2).
[20]劉霜.意大利企業合規制度的全面解讀及其啟示[J].法制與社會發展,2022(1):59-73.
[21]孫國祥.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與刑法修正[J].中國刑事法雜志,2022(3):55.
[22]C.G.DíEZ.Corporate Culpability as a Limit to the Over criminaliza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Regulation,Corporate Compliance,and Corporate Citizenship[J].New Criminal Law Review,2011(1):95-96.
[23]陳瑞華.企業合規不起訴改革的八大爭議問題[J].中國法律評論,2020(4):5.
[24]B.L.GARRET.Globalized Corporate Prosecutions[J].Virginia Law Review,2011(8):1 575.
[25]李勇.企業附條件不起訴的立法建議[J].中國刑事法雜志,2021(2):143.
[26]J.W.NUNES.Organizational Sentencing Guidelines:The Conundrum of Compliance Programs and Self-Reporting[J].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1995(3):1046.
[27]孫志成.因“二選一”壟斷被罰34.42億元,美團回應:誠懇接受,堅決落實[EB/OL].(2021-10-8)[2023-03-05]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1-10-08/1937822.html.
[28]蔣建湘.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化[J].中國法學,2010(5):129-130.
[29]周友蘇,張虹.反思與超越:公司社會責任詮釋[J].政法論壇,2009(1):58.
[30]袁雪石.整體主義、放管結合、高效便民:《行政處罰法》修改的“新原則”[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0(4):21-24.
[31]M.E.STUCKE .In Search of Effective Ethics & Compliance Programs[J].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2014(4):775.
[32]K.D.KRAEED.Cosmetic Compliance and the Failure of Negotiated Governance[J].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2003(2):492.
[33]看看新聞.中國小微企業主的數量已達到了八千多萬[EB/OL].(2021-09-15)[2023-04-0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929689677065167&wfr=spider&for=pc.
[34]K.L.SHAPIC.10 STEPS TO A BETTER DAY:The key components of compliance[J].Business Law Today,2003(1):40.
[35]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2年3月7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N].人民日報,2023-3-18(4).
(責任編輯:蒲應秋)楊洋楊波,張婭,王勤美,蒲應秋
Abstract:The essenc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is the self-chang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culture, which belongs to corporate autonomy and negotiated governance and should be the category of "soft law" governance. Compliance into the law is not a "hard law" legislative model with reverse sanction of "condition - behavior - consequence", but a positive incentive legalization model of "compliance - leniency". The legalization in the sense of "soft law" includes both "soft law"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corporate law and other positive incentives, and "soft law" norms such as official guidelines, industry norms and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the two par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i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in China. In the legalization path,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ystem of leniency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recognizing punishmen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riminal incentives; the company law should establish administrative incentives for compliance leniency such as the exemption of legal representatives from registration of previous convictions, establish the "prosecution penalty" system,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riminal incentives and administrative incentives. However, the compliance effectiveness standards,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re "best practices" and should not be established through formal legislation, but through official guidelines, industry norms,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other "soft law" norms.
Key words:corporate compliance; compliance program; legalization; soft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