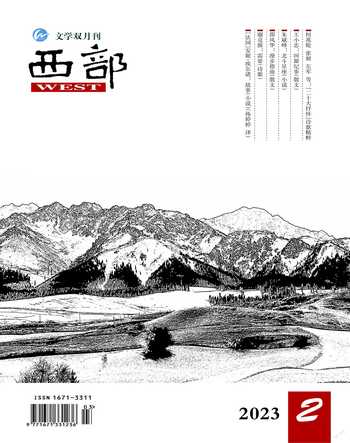對談:“寫作是一種奢侈的痛苦”
皮埃爾·路易·福爾 安妮·埃爾諾〔法國〕 孫婷婷譯
無法忽視的事實是:安妮·埃爾諾的作品正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書評、研討會、博士論文……評論界的興趣始終沒有離開這位作家的文本書寫。
然而,安妮·埃爾諾的輝煌并不局限于學術圈內。她的一些作品已經逐漸獲得“經典”的資質,成為中學生學習的對象。埃爾諾的出版商甚至決定:將《一個女人》收入專門為高中生泛讀而策劃的“伽里瑪書架叢書”。
正是在這個版本問世之際,我們得以約見安妮·埃爾諾,與她探討了其全部詩學并能從嶄新視角闡明她與寫作關系的相關問題。我們從獻給作家母親的小說《一個女人》出發,進而談到許多不同的領域,兼顧了這部具體作品的產生以及作家全部的文學創作。諸如“失卻”、對死亡的恐懼、題記的重要性、女性主義、將寫作視為“榮耀的身體”的誕生等等問題在這次訪談中匯聚,囊括了埃爾諾迄今為止發表的所有作品——從《空衣櫥》(1974)到《占有》(2002)。
皮埃爾·路易·福爾(以下簡稱皮):在您的筆下,您的母親占據了重要位置。有兩本書完全是寫她的——《一個女人》和《“我沒有走出暗夜”》。您的上一部作品《迷失》里,也能找到對您母親的大量影射。所以我想,我們最好先從專門寫她的第一本書《一個女人》以及該書的成因開始。您在《“我沒有走出暗夜”》這本書的前言中也談道:母親逝世后,“處于震驚與混亂中”的您馬上就著手《一個女人》的寫作了。
安妮·埃爾若(以下簡稱安):是的,關于這本書的“孕育”,我在《“我沒有走出暗夜”》里的講述都是真實準確的。《一個女人》絕對是出于緊迫而在服喪期內動筆的作品,遠非我父親過世許久我才擬定寫作計劃的《位置》可比——在動手準備《位置》之前,我足足等了好幾年。母親離開后,某種緊迫感明確無誤地顯現。我必須馬上寫出這本書。能和它相比的只有一部作品——哪怕看上去很是奇怪,這便是《純粹的激情》。對,也許顯得奇怪,但它們的寫作過程的確相似。也就是說,所有的一切追根溯源,都是一次離開、一種終結。對《純粹的激情》來說,是一個男人的離開,然后過程基本相同。除去一點:我是刻不容緩地投入《一個女人》的寫作中的。因為這個“項目”更名正言順。《純粹的激情》則并非如此,我幾乎是蒙著自己的眼睛把它寫完的。
《一個女人》的動筆很倉促,并沒有寫作規劃。實際上,它的開頭部分正是日記《“我沒有走出暗夜”》的結尾。我其實是把二者連接起來,有意識地從日記過渡到小說,同時,我也有一股沖動,要書寫剛剛過世的母親。
皮:就您的所有作品——具體到《一個女人》——而言,其中“元文本”的比重不小。對您來說,隨著寫作的深入,質詢寫作行為本身是必需的嗎?
安:絕對是的,我遭遇的寫作難題與文本緊密交織,尤其是在《一個女人》里。當然,有幾次我也寫過很長一段文字描述這些難題,然后便意識到“太長了”。最終我把那段文字切割成幾個部分,分別放入文本不同的地方。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多數時候,難題在我筆下出現的時機都恰到好處。例如,“讓母親再生”的想法不是心血來潮,而是醞釀了一段時間。“句子排序”的難題——我在這方面花費了很多功夫——也是如此。寫作讓我見證了一些奇跡。
皮:您說《一個女人》是“服喪期內動筆的作品”,這是否意味著您有一種要寫出它的執念?
安:是的,我始終處于對文本的執念中。只有《外部日記》和那些紀錄片斷的文本除外。而片段就其本身來說很像詩歌,只占用你把它寫出來的時間,隨后便完事大吉(此處不談偶爾會費時較長的修改潤色)。總體來說,我確實對自己的作品抱有執念。《一個女人》尤其如此。
皮:您回憶自己的母親,回憶她的去世和整個患病過程。我有種感覺,我們所處的社會正傾向于規避死亡。比如在您的書中,父親的去世發生在非常親密的氛圍里,母親的去世人們卻避而不談,二者之間的區別一目了然。
安:我想表述這種區別,在我看來這很重要。寫出太平間快速處理母親遺體的這個過程,與寫出與父親的過世——地點是在家中——相比,這個過程可怕的一面。醫院對死亡的抹除和隱匿確實讓人不安,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與塞爾吉·蓬圖瓦茲這座新城息息相關。沒有名氣的新城、故土的遠離、太平間(母親去世前我從未去過)……一切都相輔相成。反觀父親下葬后,盛大的家庭聚餐沿襲了旨在交流的古老傳統:感謝前來瞻仰和祭奠死者的親朋,感謝他們分擔了家屬的悲痛,將死亡納入變動不居的生活——通過聚餐的方式。
皮:從前有守靈的習俗。如今,多數情況下流程都在殯儀館進行——還是在有遺體告別儀式的時候。大家也不穿喪服了,不再“表露”死亡。死亡的維度被抹去了。
安:每個人服喪的方式都極為孤單。不能說“我母親去世了”,否則幾乎就是傷風敗俗。正因如此,我的《一個女人》便以這句話開頭,當時的我無法言說此事,說了會讓人尷尬。法國人不“穿”喪服已經很久了,所謂的“半喪服”——那種接替黑色喪服的深灰或紫色的喪服①——也不再穿,而喪服卻可以讓“喪親/失卻”一事表露出來,是向同樣承受“喪親”之痛的群體做正式的告知。
皮:所以有些習俗正趨于消失,尤其是那些貫穿并區分了喪葬不同階段的宗教儀式……
安:的確。因為我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摒除了所有宗教,在為我母親舉行的殯葬彌撒上,孩子們完全不知所措。有社會學家認為,沒有受過任何宗教熏陶的第一代如今已經長大成人。這是事實——我絲毫不為此感到遺憾,但它打破了慣例,迫使我們制定新的規則。
皮:在《一個女人》的結尾,您注意到母親逝世的日子比西蒙娜·德·波伏娃去世早了一個星期。翻看您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出您經常提及波伏娃。尤其是《迷失》,您在里面好幾次都談到了她。
安:是的,我得聲明是為了她才在電視上露面。不是為了我自己,也不是為了討好皮沃②,而是為了她。我討厭上電視。我覺得是出于義務,我有信心使用“義務”一詞。甚至是迫于還債,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寫作方面的債務——如某些人所說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影響了我”。比起其他作家,她對我寫作上的影響肯定要小得多。她的重要性,是讓我無論在生活還是寫作中都渴盼自由,渴盼著頂風冒雨也要堅持寫作、寫下自己想要書寫的一切。一種存在主義的債務。
皮:談到波伏娃,只消幾個字就可以把我們引向“女性主義”問題……這對您意味著什么?在這個問題面前,您是如何給自己定位的?當您寫作的時候,這個問題對您重要嗎?
安:我寫作時完全沒想過這個。但是鑒于男女之間存在統治關系的現實,我完全相信,自己在落筆時會顯露女性寫作的某些特點——哪怕不是有意為之。就算只是捕風捉影的指責——其理據可能僅限于“女人不寫這個或者不應該寫這個”,一旦被我發現,我也要強迫自己把它精準地描寫出來。毋庸置疑,我身上覆壓著一整套自己都未必意識到卻又試圖擺脫的神話。對我來說,女性主義不是一面旗幟而是一種必需,行動層面的必需、政治層面的必需。我在寫作時彰顯出女性主義,不是通過提醒自己是個女人,而是通過盡可能地深入人類的現實。這現實包含了婦女、婦女的處境以及諸如母女關系的某些特殊情況。
皮:說句實話,我是就整體而言的“性別研究”潮流提出了上述疑問。
安:我始終和這股潮流保持距離……有幾個跟我談論女性寫作的人,甚至被我比較強硬地打發走了。
需要把女性的作品獨立出來,為研究它做好“儲備”嗎?對此我不大確定。而且,我心里尤其確信一點:社會出身和社會地位比性別劃分更具決定性作用。哪怕后者也很重要,但我會把社會性放在首位。
皮:是啊,談到社會性,您在《世界報》上發表過紀念文章(《布爾迪厄,憂傷》,2002年2月6日,星期二),向皮埃爾·布爾迪厄表達了崇高的敬意,文章伊始便是您對“知識分子的介入”的一番思考。您會在什么情況下稱自己為“介入的作家”或者“介入的知識分子”呢?
安:我將知識分子與作家或者藝術家區分開來:知識分子將大部分的研究用于創立一門客觀而普遍的學問;作家的作品則首先調動了一種主觀性。我從未想過用“介入的作家”一詞來定義自己,因為非常明顯,寫作于我而言是一種旨在對世界發生效力的行為。我不想迷惑讀者,讓他們進入動蕩或者幸福的奇異世界而不能自持,而是要像在《事件》③中我對另一情況有感而發的那樣,把讀者拉入“令人驚愕的真實”。讓一直被忽視的東西暴露于人前,讓我自己在動筆之前都沒有看到,其真實的影響連我自己也沒有注意的現象顯露出來。重點有二:一是盡量多挖掘一些真實,二是要選擇——哪怕是在文學寫作中——最可靠的“方法”以達到這種真實。佩雷克④將馬克思的一句話選作《物》的題記,即“方法也是真理探求的組成部分”,我覺得正與我的觀點呼應。
皮:您在自己的大多數作品里也喜歡使用題記。被您選為題記的作者,無論是從年代還是國別來看,類型都非常多樣。您是如何篩選這句或那句引語的?為什么有些文本就沒有題記?而且我覺得,近幾年被您選中的題記有某種增多的趨勢:《羞恥》是兩句;《事件》是三句,出自兩個作家;《占有》只有一句,卻是很長的一句。這些題記的選擇對您意味著什么?它們的重要性何在?
安:寫完《空衣櫥》那本書的草稿時,我還沒有確定標題,同時也在尋找可以作為題記的名句。我想,這兩個任務當時是共存于腦海中的。我翻看了艾呂雅的一本詩集,艾呂雅是我非常喜愛和熟悉的詩人。然后,《公共的玫瑰》中的幾句詩吸引住了我的視線:
我將假珠寶收進幾個空衣櫥
無用之舟將我的童年和煩惱
以及我的游戲與疲憊相連
我馬上意識到,它們也許概括不了全書,卻可以概括讓我寫下該書的那種感覺以及這本書之于我的意義,于是標題和題記一下子都有了。我就沒再深究,也算是遵循了某種文學慣例——將自己置于某位名人的庇護之下。接下來的兩本書都沒有題記,但有獻辭,分別題獻給我的兩個兒子(即“調皮蛋們”,這是他們在家里的稱呼,取自鮑里斯·維昂⑤的《奪心記》——我在第二次懷孕期間閱讀的一本書)和我的丈夫。我不記得自己是否為這兩本書找過題記,相反,我知道寫《外界生活》的時候,我確實找過,但除了凡·高感嘆現代生活中萬物轉瞬即逝的那句話⑥,什么也沒找到。因為這句話赫然寫入了文本,我最后就沒有在題記中再次使用。
(引言式的)題記完全不適用于《“我沒有走出暗夜”》:母親生前寫下的這最后一句話是全書唯一的引語;作為標題,是“她”——我的母親——在此代表了文學的全部……
其他的題記都非常重要,幾乎和標題同樣重要。我經常在幾個選擇之間躊躇不決。比如《位置》的卷首語,同時備選的除了盧梭《愛彌兒》中的一句,還有分別來自薩特和熱內⑦作品的兩句話。三者之中我最后選定的雖然不是自己偏愛的那個作家⑧,但《新觀察家》上轉載的一篇采訪中他說的那句名言⑨還是讓我覺得,這句話給《位置》增添了某種語義——只是“言下之意”的語義:對階級的背叛。我認為這個題記比十頁紙的論證強過百倍,它揭示了寫作此書的全部意義——以“畫外音”的方式。同時,較之(題記通常具有的)擔保作用,它更傳達了某種“休戚與共”。
我給《一個女人》選擇的題記⑩出自黑格爾。找到一句適合的引語非常困難,我完全忘了自己是如何以及為何在加洛蒂關于黑格爾的一本著作11中撞上了這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買了加洛蒂的書。我知道這句話非常抽象和晦澀,但它超越了《一個女人》的具體語境,與我對世界的看法相符。摘自盧梭的《對話錄》、被我用作《外部日記》卷首語的那句——“我們真正的自我不完全存在于己身”——也是如此,還有《事件》中對雷利斯12和日本女作家津島佑子言論的引用13,《羞恥》中對保羅·奧斯特14以及《占有》中對簡·里斯15的引用16:除去表面彰顯的意思,這些引言還包含了一些我對世事、文學和語言的看法。我對它們的引用絕非無懈可擊。但是顯然,我要么對被引用的作家感到親善、與之意氣相投(比如盧梭、雷利斯和簡·里斯),要么至少對他的才能有種由衷的欽佩(比如奧斯特)。不真心喜愛的作家我不會引用。引用,永遠是編織一根連接那個作家的紐帶,向他/她伸出手去。
《純粹的激情》的題記是羅蘭·巴特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倆》雜志比薩德的作品還要色情”,這個題記產生的效果相當復雜,而且經常被人誤解——或者確切地說,經常從知識分子的共識的角度被加以理解:人們認為,我是在抨擊《我們倆》這份主要刊載言情故事、基本排除了性和色情內容的婦女通俗雜志,認為我是在恭維薩德。然而,在這句被我抽離了語境的引言中,巴特原本想說的是:看見和閱讀愛情與激情,遠比看見和閱讀“性”更讓人無措和難以忍受。巴特于1977年寫下此語,而在我發表《純粹的激情》之時,他的這番高見更是有目共睹。激情的處境正讓人心生不忍。伊麗莎白·巴丹特17在其著作《一個是另一個》中明確表示:愛情的混亂無序注定會消失,不同的性別與個體之間只會剩下平和、理性的關系。巴特的引言因此可以幫點兒小忙,讓我略過讀者的某種不無傲慢的閱讀,警告他:他要讀到的東西有傷風化,即使在二十世紀末,也比薩德的作品更讓人難以接受。這是個既失敗又成功的策略:有些讀者和評論家的確對該書冷嘲熱諷……
皮:《純粹的激情》和您迄今為止的最后一部作品《占有》,都是圍繞愛的束縛這個問題展開,都是一開始就追憶勃起的男性性器官。《占有》的結尾更是返回對男性性器官的描寫。您在《迷失》里將“性”寫入文本而使之文本化,對此您有何看法?
安:在我的作品中,性描寫占據的位置很難加以解釋。總體來說,我覺得自己一直都想“寫”性。也許因為我那些關于性的最頑固的印象來自十三四歲時候的閱讀,來自那些“信教的”所說的——比如在教義問答課上——“壞書”。我感覺得到,自己經常圍繞寫作和性之間的某種聯系轉來轉去,這種聯系可能頗具蠱惑力——十三年前第一次看到(根據原文翻譯)電影的某一幕時,我感受到的那種蠱惑力——《純粹的激情》的開頭對此有過描寫。同時也不排除在 “社會罪”(根源于社會)和性犯罪之間存在某種關系。
皮:我們再談談《占有》。《世界報》去年夏天登載的文學副刊里,《占有》的文本形式(與后來的成書)有些許的不同。您在正式出版的書中做了幾處修改,調整了若干段落,增添了一些內容并擴充了結尾。不過,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排版印刷上的變動——成書要“透氣”得多、零散得多。這種切割和在文本空間上所下的工夫從《位置》以后就出現了。請問此舉的重要性何在?
安:空白于我而言至關重要,我在今年夏天投給《世界報》的那個文本里也留有一些空白,發表時卻沒有征詢我的意見就全部刪掉了!不得不說,我非常沮喪和氣憤,立刻決定申訴,要求明年春天的刊載必須與成書里的形式相同。留白是在我自己感覺特別稠密——稠密得近乎“激烈”——的作品中打開的氣孔和出口。而且,《位置》里我第一次使用留白,是依照自己擬定的人種學寫作計劃,有意避開小說。該書原本的題目是“家族人種學資料匯編”:只是基本資料,不是脈絡連貫的語篇。正如在詩歌—尤其是現代詩歌—中一樣,空白的作用是無需添加過渡、無需闡明因果,是既可以并置又可以突出若干觀點,是彰顯某些細節的重要,是進行清查盤點……
皮:我在《占有》里再次發現了一處腳注。《一個女人》《純粹的激情》和《事件》都使用過腳注。您為什么求助這種方法?
安:如果覺得某段文字讓敘事過于撕裂——構成了外在于文本的一種思考,我就會在頁下做注。但是我心里明白,有時候看上去好像也是某種斷裂的內容還是被我納入了文本的正文,我于是安慰自己還有一種理由——它們類似在文本內部打開的幾個通往外部的大門,走不走這些大門則是讀者的自由(因為這需要付出努力,且在文學寫作中并不常見)。
皮:一般來講,外界認為您和加繆、波伏娃的作品之間存在互文性。您自己卻說受到其他作家更大的影響。您指的是哪些作家?除此之外您還欣賞哪些作家?
安:縱觀人類寫作的全部歷史,我認為薩特和他的《惡心》對我而言尤為重要。還有塞利納、普魯斯特和福樓拜——在我十六歲至三十歲之間的成長階段,之后我才正式開始寫作。我由衷地崇拜這些作家的寫作風格。我也喜歡過佩雷克、娜塔莉·薩洛特(深刻的精神上的愉悅)和雷蒙德·卡佛。在我看來,卡佛的文本絕對是卓越不凡的。我也很喜歡切薩萊·帕韋澤18,他的《同志》《美好的夏日》等作品都非常精彩。
皮:您談到了娜塔莉·薩洛特,讓人立刻想起新小說。我大概知道,新小說對您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安:千真萬確。我的第一本習作(沒有發表)就屬于新小說。非常復雜的結構,雜糅在一起的片段:夢境、想象境、童年和現在。共有四個層面,想在其中找到方向可不容易!實際上算是一首長詩。但我當時受新小說的影響太大。時任瑟伊出版社發行人的讓·凱羅樂在來信中說,我的設想很有意思,設想的落實卻未達到相應的高度。的確如此。不過,我卻第一次完整地感受到寫作的樂趣,置身于連貫的情節之中的樂趣,以及每天以此為業的樂趣。體驗另一種人生的感覺。我自此明白,寫作是另一種人生。后來,這段過往讓我很是懷念。偶爾的試筆已無法讓我滿足,我要徹底地投入寫作。然而十年過去,我才得以重新開始——這便是《空衣櫥》,盡管寫作的方式已大不相同。
皮:您在《一個女人》中說,寫作是一種“奢侈”。我們卻覺得寫作還有一個維度——痛苦。
安:對,是有痛苦。但是同時……
黑:……可以稱之為“奢侈的痛苦”嗎?
安:完全可以。要知道,不奢侈的痛苦比比皆是:有一種不奢侈的痛苦,叫作社會性的窮困和心理上的悲慘。有那么幾次,我就處于這種痛苦的邊緣……十八歲到二十歲之間的日子,我過得不好,很不好,也許挺過來的我因此成了作家……是的,我還在堅持,寫作是一種奢侈的痛苦。
皮:在《一個女人》里,您想把這種奢侈的痛苦放置到某個奇特的地方——“文學之下”。
安:“文學之下”的表述是我無意中想到的、出自契訶夫作品的一句話:“……在愛情之下”19。我還要引用契訶夫,不過這次是他關于寫作的論述:“首先要合理,其余則水到渠成。”我是后來讀到這句話的,它表述的意思非常重要,即我們不能以“咬文嚼字”為先。我還想到紀德在《論那喀索斯》中寫到的一句話:“藝術家/科學家的自戀不應該超過他想表述的真實”。有一種注重辭藻的文學形式……
皮:……追求美,唯美化的文學形式……
安:是的,以追求唯美為要務。重要之處不在于此,而是應該力求真實。當然,沒有對字詞的認真推敲也不行。“文學之下”還意味著:不要待在作為崇拜對象的文學之內,而是要走得更遠。“待在文學之下”幾乎就等于“(待在)文學之上”。走得更遠,更強而有力。這種姿態不是卑微,相反,它很是高傲。的確,《一個女人》讓我有種走出很遠的感覺——向著我母親的“榮耀的身體”。我在書里談到過“榮耀的身體”嗎?
皮:沒有,我沒有見到。
安:我接受過嚴格的基督教教育,身上還殘留著很多神話的影響。在這些神話故事里,俄耳甫斯下地獄尋找歐律狄刻的故事沒有“榮耀的身體”給我的印象深刻……盡管說到俄耳甫斯和歐律狄刻,我還做了個相關的夢……我不記得自己寫過或者刪掉的東西了……我寫過這個夢境,但是忘了寫在哪兒了……夢里,圣拉扎爾車站附近,說不清楚母親是否坐在公交車上……總之我是在等公交。汽車到了,母親出現,我想和她說話,她卻并不理我,她的身影逐漸消散,同時她示意我她無法和我說話,直至徹底消失。我失去了她。我看見了她又失去了她。就像俄耳甫斯和歐律狄刻。
還是回到“榮耀的身體”吧。它講的是什么?在基督教里,人死以后,經過最后的審判在最后一天復生,但復活的不再是我們的肉身,而是“榮耀的身體”。它確指什么?我不知道。總之不再是原來的肉體。《一個女人》的書寫讓我產生了創造出母親“榮耀的身體”的感覺。她本真的自我、她的身體通過進入他人意識和記憶的方式,變得光輝燦爛。她分解并融入人們的精神,像靈魂一樣存在(作為唯物主義者的我竟有這樣的唯靈論想法!說實話,我是唯物主義——也就是“此時此地”——內部的唯靈論者)。現在和您講起這些,我不禁想到自己在《事件》最后寫下的、關于我的存在消融在寫作之中的那段文字。
皮:對,就是全書末尾返回卡迪內甬道20之前的一段。我讀一下:“……世事紛至沓來,讓我將之錄下。我人生的真正目的,也許僅僅在于:讓我的身體、五感和思想都化為寫作,亦即化為某種易懂而普遍之物,我的存在完全融入他者的頭腦和生命。”
安:我是因為跟您講到母親才把這兩者放在一起對照的。她的復活是通過散播的方式、通過在閱讀過程中變成讀者的母親或者祖母的方式。還有一個隱喻:關于“遺失”的隱喻。我的所作所為,讓母親像我一樣遺失在作品之中。我知道自己筆下的一切極為錯綜復雜。十多年來始終知道。當一個人開始寫作,他便無法了解、他不了解自己會寫些什么。
皮:作為結語,我想讓您再談談這個關于遺失的隱喻,談談“失卻”的問題,您的作品對這個問題總是在不斷修正——直到2001年,您發表的小說題目還是《迷失》。您的文學創作是借助某種不斷“失卻”的經歷而得以進行的,可以這么說嗎?
安:不用到達“(親身)經歷”——正如對我的情況比較快速地進行一番“自我-社會性-心理分析”后,大概就可以經歷和體驗“失卻”(我的父母在我之前夭折/失去過一個女孩兒,我通過進入知識分子圈層擺脫/失去了自己的出身階層)——的地步,我想也有可能建立某些關聯:
﹡過錯、犯罪——社會的、性的、宗教的——與“迷失”的欲望或恐懼
﹡“迷失”在激情和性欲里,以相當神秘的方式(我想起1960年觀看的一部電影,奧黛麗·赫本主演的《迷失的風險》,講的是個修女的故事)
﹡“迷失”在寫作中,因為寫作是“重新贏得”一切的手段,是“榮耀的”以抽象的形式——字詞的形式——呈現的真正存在,“自在”(être)并且“使在”(faire être)21,把一切奉獻給世界而非上帝。
﹡“迷失”,也就是一直走到XX的盡頭,因為只有這樣才會抵達事物的“本質”……
談論“失卻”實在是件困難的事情:我想說的是,很難組織一段連貫流暢、因果相續的措辭。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認為“空白”是寫作——我的寫作——的理由和意義,但近一兩年來,我覺得更應該是“失卻”:它是心臟、是中堅,是抓住了文本之間所有線索的東西。
注釋:
①按照法國習俗,喪服通常為黑色,守喪半年后才可加穿白﹑灰﹑紫或淡紫色(稱半喪服)。
②當指貝納爾·皮沃(1935- ), 法國當代最有文化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法國《讀書》雜志主編、龔古爾獎評委會主席(2014-2020)、法國電視二臺讀書節目主持人。
③根據這篇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獲得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2021),電影名在國內一般譯為《正發生》。
④喬治·佩雷克(1936-1982),法國當代著名的先鋒派小說家,其作品《物》(1965)獲得了雷諾多文學獎。
⑤鮑里斯·維昂(1920-1959),法國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奪心記》(1953)是他生前所寫的最后一本小說。
⑥《外界生活》:“凡·高在一封信中說過:‘我力求表達現代生活中萬物的令人絕望的轉瞬即逝。”
⑦指讓·熱內(1910-1986),法國作家和劇作家。
⑧暗指最后選定的是讓·熱內,因為下文提到的引言出自熱內。
⑨“我斗膽解釋一下:人在背叛時寫作是最后的依仗。”
⑩“矛盾是難以理解/想象的——這種斷言是個錯誤,因為矛盾就真實存在于生者的痛苦之中。”
11當指羅杰·加洛蒂的著作《黑格爾思想研究》一書。加洛蒂(1913-2012),法國哲學家、文藝批評家。
12當指米歇爾·雷利斯(1901-1990),法國人類學家、藝術批評家和作家。
13引用的兩句話為:“我的兩個愿望是:大事都化為書面文字;書面作品都是有影響的大事。”“誰又知道,觀察事物直到它最后結束是否就等于記憶。”
14保羅·奧斯特(1947- ) ,美國作家、劇作家和電影導演。
15簡·里斯(1890-1979),英籍女作家。
16引用的兩句話是:“語言不等于真實。語言是我們在世間存在的方式。”“要知道,如果有勇氣將自己感受到的東西探究到底,我最后就會發現自己的真實情況,發現宇宙的真相,發現所有那些不斷突襲我們并給我們造成傷害的事物的真相。”
17伊麗莎白·巴丹特(1944- ),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女權主義作家。
18切薩萊·帕韋澤(1908-1950),意大利作家、文學評論家和翻譯家。
19在契訶夫的喜劇《櫻桃園》里,女主人公柳波芙·安德列夫納說:“我卻被迫處于愛情之下。”(第三幕)
20卡迪內甬道位于巴黎十七區。《事件》中的“天使制造者(做地下人流手術的江湖女醫)”就住在甬道內。
21相當于英語的be 和make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