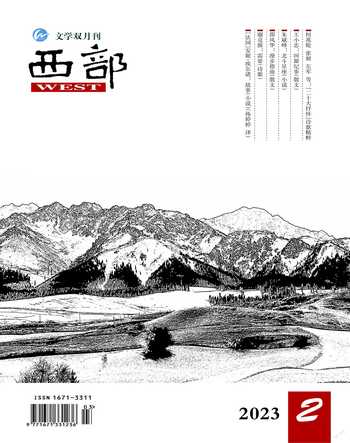老照片(散文)
安妮·埃爾諾〔法國〕 安吉拉譯
在我為數不多的家庭老照片中,有一張是我父母一九二八年舉行婚禮時的合影。照片里可以看到兩家人,“兩方”人,分成三排,第一排坐在椅子上,第二排站著,第三排大概是站在長凳上。男士和女士身影重疊交錯。兩個家庭的成員分別由佃農(我的祖父母)和工人(我的雙親,叔叔和阿姨)組成。每個人都盛裝打扮,衣著得體。女士們穿著淺色連衣裙,男士們身著深色西服,雙眼直視前方,雙唇緊閉,神情在鏡頭前很專注。坐在前排的人,雙手清晰可見,全都碩大而強壯,或放在膝蓋上,或交疊在一起,手指捏在掌心,空閑下來的雙手緊握著,對突如其來的閑暇感到無所適從。每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時,我都難以從那些手上挪開視線,不論是男士還是女士,他們的手都寬闊、有力。我來自這些人,來自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工作唯有一種形式,唯有一種意義:用雙手勞動。
我又看了看所有這些照片:干活的孩子,車間里身穿工作服的婦女,套著軛俯身于鐵鏟上的男子。這些不知名的生命,活在我尚未存在之時,卻打動著我:我認出了他們。我想說的是,他們的身軀,他們的姿態,他們的手勢,已成為我所繼承的遺產的一部分。他們寫在罷工牌子上的文字已成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這些照片喚醒的幾乎是一種物理記憶。這種記憶,深刻的勞動記憶,是博物館所有的藏品和史書上所有的記載都無法恢復的。它裝在我祖父母和父母假日餐桌的故事里,那些故事將生活勾勒為兩個空間——田野和工廠,講述他們十二歲輟學,被送到農場干活,然后進電纜廠、紡織廠,忍受工頭的咆哮和欺凌,在寒冷的建筑工地上凍得瑟瑟發抖。那是一種存在于語言中的記憶,存在于那些脫口而出的話語中——“我們沒班上了!”——將平凡的日常生活與需求交織在一起,以一己之力構建起整個世界,這記憶的分量,一個從未反復聽過那些話的人是永遠無法感受到的,他不知道“干凈活兒”“室內工作”“惡劣天氣停工”是特權,不知道“débauche”①意思是一天的活兒干完了,而“être débauché”②則表示下崗了,與“花天酒地”毫不相干。對孩子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在學校里努力學習”,對十幾歲的女孩則威脅說 “我要把你送進工廠,等著瞧吧”。這是一段在屈辱和驕傲之間搖擺沉浮的記憶。
正如其他類型的照片一樣,一張記錄個人在工作的照片,比其他照片都更容易帶給看照片的人那種轉瞬即逝的身臨其境感,他們被照片中的姿勢或環境所攫住,短暫地忘記了周圍的一切。照片并不與我們共享噪聲、氣味、節奏、工廠的哨聲,不會告訴我們薪酬多少,工作完成得好壞。然而,這類照片強過其他照片之處在于它可以反映社會的經濟結構。它體現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工業生產的秩序和紀律,即泰勒科學管理制度的基礎。該管理制度旨在給每個人在分工中一個特定的位置。就像在修道院里,世俗的跡象被驅逐,一切都必須指向上帝一樣,車間四壁之內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其他任何生活都不能有。那些精簡而又樸素的裝飾只能指向生產。相似的身影、姿勢,甚至是深深陷入工作中的視線都與排列整齊的機器微妙地一一對應。衣著強調工人對工廠的歸屬,一切都得統一起來,就像帽子,與工作服、帆布袋和午餐盒一起,都得象征著男性工人階級的地位,而不是“白領”的地位。如果在照片中,在一種凝固的瞬時狀態中看不到時間,那么在這種空間組織中,在這種對稱性中,可以感受到無限的重復與缺乏未來,似乎永遠把每一個人都釘在了他們的織布機或其他機器上。矛盾的是,生產場所的封閉,那種對工人們的限制則更加明顯,著實令人不安,為了拍照,男人們和女人們中斷任務,暫停動作,轉向鏡頭,或驚訝,或微笑。在這個短暫而殘酷的空虛中,他們不再是表演的主體,而是成了被看的客體,觀看的人則來自另一個世界,公司以外的世界。
最讓我感到心酸的是那些操弄機器日久的孩子,他們近乎成了那些機器的一部分,臉上有著與稚嫩的線條相沖突的滄桑和古板,與此同時,生于巴黎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們正在盧森堡花園中嬉笑打鬧,過著普魯斯特和薩特筆下所描繪的、被文學潤飾過的生活,享受著那黃金般的孩提時代。對于那些聽完校長的哨子再到工廠聽哨聲的學生來說,嬉戲的時間早早結束了,就像今天臺灣八歲的小孩在為西方世界的孩子們加工T恤衫那樣。諸如“父母養不起吃白飯的”和“我在你這個年紀時已經工作了”之類的話語至今在我的耳畔盤旋,這些話全部都在強調進廠打工的必要性。毫無疑問,沒人起來反抗,因為在制造業中使用的秩序和紀律原則,已經被灌輸到完美的第三共和國公民的圣經《愛國二童子傳》一書中。這本書的每一頁都處心積慮地隱去了“罷工”一詞,強調工作的價值所在,鼓吹人有貧富之分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確保所有人都各就各位:“當你路過城市的郊區時,有沒有看見那些挺拔、簡陋的房屋?有沒有聽見活躍的商販的聲音?那就是不計其數的工人生活的地方。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居所或車間,往往在五六樓,也有人蝸居在地下室里,他們成天勞作,讓梭子在絲線中往來。那些閃閃發亮、圖案精妙、色彩鮮艷的織物,就是從這些毫不起眼的住所輸送到世界各地的。”格塔爾先生——一個精明的商人,也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對未來的勞模小朱利安如是說。
這是攝影的扭曲效應,它的底片同時印上了我們的神話和現實。一群聚集在密閉的廠房中的工人們,他們看起來像一群囚徒或是身處地獄的殉難者,這點我們無法否認,但同樣令我們無法反駁的是,在田野中辛勞的收割者看起來就像圣經中所描繪的詩意景象,烘焙房中的面點師挪動的身姿看起來更加優雅,至少他們在干一件比在流水線上的工人更有創造力的工作。從某一方面來講,工作的意義在于防止社會失范。機械重復的工作帶來的疲乏抹去了混亂發生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忘記這個世紀伊始,很多人,至少是我們這些人,心中會泛起離開地球的漣漪,渴望逃離晴雨風雪的循環。我們不能忘記,在廠房和車間的庇護下工作,每天有固定的時間表,工人們摩肩接踵,聽從工頭的安排,這一度代表著進步。
我們尤其不能忘記工廠和車間在女孩和婦女們被逼維持生計時扮演的解放者角色。就算這個空間將她們禁錮,相較于她們作為“家庭傭人”的那個家、那個家庭,她們自己的家或別人的家,這個逼仄的空間已然是她們的“外部世界”了。當女人的天職還被定義為相夫教子時,當優秀小說還在描寫年輕女孩出門時一定得帶個監護人時,一個能將頭發散下、自由走動的女工已經體會不到孤獨和足不出戶的滋味了。她在男女混雜的地方收獲了同志情誼,在斗爭的生活中和同伴團結在一起。對工廠女工形象的污名羞辱(米什勒說:“ouvrière(工廠女工),一個褻瀆上帝的詞!”)與 grisette(輕浮女子) 或 midinette(輕佻少女)這樣的詞匯不同,它還沒有被文學概念化,這點就足以證明它的存在及其作用是觸犯社會準則的。往前幾個世紀,尋常人家,如佃戶的女兒,無疑都要工作;但直到二十世紀,女性才開始從事有報償的工作,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涉足某個領域里的職業,開始攻入此前專屬于男性的領域。1908年,第一位海報懸掛女工已被載入史冊,因為她打破了弱柳扶風、嫻靜溫柔等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她在靜默中堅定地向前挪動,桶和梯子穩穩當當地被她扛在肩上。你可以在腦海中這樣描繪她的形象:坐在梯子的橫木上,屏息凝神地把最新的節目廣告貼在墻上,對腳下的奚落聲不屑一顧。她就像一名點燈人——她在城市中對應的身份,擁有這整個城市。她有權占有它,她不像那些買東西或閑逛的婦女,或是那些如同妓女一樣出賣自己身體的婦女,只把它當作一個通道,相反,她是把這座城市視為一個作業空間。到二十世紀末,女公交車司機也將以同樣安靜的方式行駛在城市的道路上。
然而,這些征服的畫面并不能掩蓋勞動性別分工現象的持續存在。雖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在各行各業都頂替了原本屬于男性的位置,但當和平到來時,她們又被請回到她們的“自然”地方——家庭。在巴黎較大的咖啡館里,她們的圍裙和托盤被男人一并“回收”,因為咖啡館以“僅擁有男性服務生”為特點往往能收獲更高的聲望。我們見過女人制作礦工燈、開飛機,可我們幾乎從未見過男人熨燙衣服,很少有男人在縫紉機前俯身,后來在打字機前俯身的就更少了。計算機發明出來后,這類工具的使用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性別平等,但在利用它進行開發的任務方面并沒有多大變化。女性往往迫于經濟壓力而滲入男性的工作領域,可男性從不與女性分擔那些分配給女性的工作。因此,毫不奇怪,我在對二十世紀的工作進行審視的過程中注意到,有些重要的東西遺漏了,那些沒有報酬的、看不見的工作,融入社會背景的工作,仍然保留著、延續著,這些工作主要是由女性完成的,包括烹飪、打掃衛生和照顧孩子。
這些私人領域中的分工做法已悄悄轉移到了制造業的世界,一切都照此發生。男人與木材、金屬打交道,女人與織物為伴。相比起男人,女人總以一副低眉順眼的樣子出現在照片里,她們坐在桌子旁,眼睛低垂,專注于手頭的工作。她們靈巧翻飛的手指與被迫一動不動的身軀形成鮮明的對比。女性被暗地里要求去表現她們作為女人的天性,以匹配她們的活動和那個軟弱易碎、奉獻甚至自我否定的形象。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女性大量進軍教育和服務行業,以迎合保持女性氣質、擁有“適當的女性工作”的需求。可是,這些所謂的女性形象,被照片捕捉到的健壯軀體所展示出的現實給粉碎了,我們從而得到警醒:在農民和工人的世界中,女性的力量和耐力都十分被看重,“健康狀況不佳”這樣的詞則聽起來像是一個詛咒。(如今,在扎伊爾,被稱為“代孕母親”的女人們背上背負的重量可達五十到八十公斤)。罷工游行中不乏大量女性臉龐,她們以法律而不是自己胴體所產生的誘惑為武器,展現出與男性并無二致的、混雜著莊嚴、堅定和驕傲的面貌。
用“雙手”勞作實際上是一個不恰當的表述,或者說過于片面。我們應該說:我們用軀體勞作,身上每一塊肌肉帶著骨頭一起律動,我們的思維也不例外(事實上,認為腦力工作脫離了身體的看法是不正確的)。這些照片華麗地展示了工作中的身體抑或作為工作一部分的身體。今天,當愉悅的或被迫愉悅的身體、富有運動天賦的身體,還有那些有趣的、自我參照的身體,當它們都成了頭號話題時,展示并感受身體在世上發揮作用,就大有裨益。雙臂壓低,雙手確保抓握,雙腿邁開,身體保持平衡、準備提起袋子,雙肩扛起壓彎一個男人脊背的重負:所有這些努力、平衡、緊張的姿勢,都被所謂的體力勞動者用來與物質搏斗(沒有修辭來引導它,沒有隱喻來轉換它),因而變得更加明顯、引人注目。相機在本世紀初捕捉到的這些與物質世界展開的肉搏,漸漸讓位于工作中呈現出的優美姿態,讓位于這些姿態不同尋常的象征性特點。攝影大師杜瓦諾的作品《畫家》有力地佐證了這一點。那位畫家一只手畫畫,另一只手勉強支撐住自己,就像一只飛翔在天地間的小鳥,他的形象同時也體現了人類境況:具有帕斯卡式的思想、自負、脆弱。
隨著體力工作難度降低,體力勞動者數量減少,這種美化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體力勞動者這個類別已然從語言中消失了,好像取代本土勞動力、從事臟活累活的移民勞工不值得謳歌似的。技術繁榮、工作稀缺,以低廉成本將體力工作轉移至第三世界,所有這一切都助長我們去掩蓋人類活動中產生的利害關系與其意義,并最終從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中將其抹除。經濟和市場變成了主導價值,它們擺脫了與勞動的關系,從此我們的腦海中不再存有工人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清潔員”“安保人員”或“客服人員”。孤立和焦慮,與著了魔般的否認相伴相隨,共同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
今夜,超市收銀臺十分擁擠。收銀員會微笑著跟顧客打招呼,用右手推開分隔每個顧客物品的橫桿,同時用腳踩動傳送帶,然后拿起包裝盒,在掃描儀前揮動一下,緊接著敏捷地把它從右手遞到左手,再從旁邊成堆的購物袋里抽出一個塑料袋,猛地向下甩,讓空氣沖開緊閉的塑料袋口,再把包裝盒塞進去。當塑料袋裝滿時,她把它從支架上取下來推到顧客面前,然后打開另一個袋子。如果商品的條形碼沒有觸發掃描儀發出嘟嘟聲,她會用兩只手托住那件商品,將其慢慢揮動幾次。如果這樣仍然不行,她只好一個字一個字地輸入條形碼上所有的數字。最后,她會按下收銀機上的一個按鈕,再根據顧客的支付方式按下另一個按鈕。支票支付的流程最繁瑣,收銀員首先需要把它插入收銀機上的插槽,然后給顧客看一眼,在支票的背面記下顧客的身份證號碼,最后把它取出,存放在掃描儀下面的抽屜里。她道完再見后,又跟下一位顧客打招呼,推開分隔橫桿。
在我心目中,我可以在我父母的結婚照里看見無數雙屬于我祖先的手。我突然意識到,不管是最遙遠的過去還是當下,工作作為主線以不同的形式貫穿了幾代人的生活。而勞動作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我們應當再次肯定其價值。
注釋:
①être aux intempéries,在法語中“意為在天氣惡劣到無法工作的日子里仍然能得到薪酬”。
②débauche,在法語中意為“驕奢淫逸,花天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