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簡”與中國古代小說批評
趙秒秒
(山東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山東 濟(jì)南 250100)
“繁簡”乃重要的為文之道,詩文理論中多有探討,小說批評中也多有運(yùn)用。以往研究,或多關(guān)注“繁簡”思維[1]73,或多關(guān)注“繁簡”辯證關(guān)系,且主要以詩文理論為研究對象[2]319。本文擬基于“繁簡”意涵的類釋和“辨體”中的“繁簡”規(guī)定,以中國古代小說文本批評為依據(jù),探討其“繁簡”之辨及其組合原理,以服務(wù)于中國特色的文藝?yán)碚摻ㄔO(shè)。
一、文法與格調(diào):“繁簡”論發(fā)展歷程探析
從“繁簡”理論的發(fā)展脈絡(luò)來看,經(jīng)書作為不刊之正典,當(dāng)為“繁簡合度”的創(chuàng)作典范,《左傳》成公十四年曰:“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3]4154杜預(yù)《春秋左氏傳序》對這五例作出了進(jìn)一步解釋,認(rèn)為:“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3]3702杜預(yù)又從總體上強(qiáng)調(diào)《春秋》具有“言高則旨遠(yuǎn),辭約則義微”[3]3707的創(chuàng)作特色。可見,經(jīng)學(xué)闡釋是繁簡論得以發(fā)生的根基。
在文學(xué)批評中,劉勰《文心雕龍》依經(jīng)立義,以經(jīng)書作為“繁簡”理論資源①,從審美格調(diào)和行文運(yùn)筆方式兩大層面構(gòu)建了較為系統(tǒng)的“繁簡”批評體系。
在審美格調(diào)層面,“繁簡”包含不同文體簡約與繁復(fù)的體要之辨以及作者與作品繁縟與精約的體性之辨。首先,劉勰在文體論批評中,以“體要”作為核心概念,提出了“銘”“箴”“章”“表”等不同文體的繁簡要求。關(guān)于“體要”,《序志》篇曰:“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xùn),惡乎異端。辭訓(xùn)之異,宜體于要。”[4]1913劉勰以《尚書》為引,針對“文體訛濫”的現(xiàn)象,提出辭宜“體于要”,“體要”于此為“精約”之意。《征圣》篇曰:“《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美。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4]47-49此時(shí),劉勰雖依然引用《尚書》,但認(rèn)為“體要”成為與“言辭”互為表里的文體概念,注重“體要”是為了“成辭”,那么所成之辭可以有“繁縟”和“精約”等多種標(biāo)準(zhǔn),此時(shí),“繁與簡均可稱之為體要。”“體要的體從原來‘體于要’的動詞轉(zhuǎn)化為文之大體的名詞之‘體’,要則從‘要約’轉(zhuǎn)化為得體與關(guān)鍵之意。”[5]121在《詮賦》中,劉勰認(rèn)為“麗辭雅義,符采相勝”為“立賦之大體”,而自宋以來,作賦者卻“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4]307,此“體要”即賦之“大體”,指與不同文體相適配或不同作家所展現(xiàn)出來的語言、敘述方式、體式樣貌等文學(xué)形式相統(tǒng)一的指稱,“繁簡”是“體要”的具體形式表現(xiàn)之一。在具體批評中,劉勰論述了不同文體的“繁簡”體要要求,《銘箴》篇指出:“箴全御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4]420又在“總贊”中強(qiáng)調(diào):“義典則弘,文約為美。”[4]425可見,“銘”之體貴簡約。又《章表》篇言:“繁約得正,華實(shí)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4]844指出“章表”的體要要求之一是需要“繁約得正”,由此才能合律。
其次,劉勰還將“繁簡”與作者的創(chuàng)作性情聯(lián)系在一起,他在《體性》篇中指出根據(jù)作者“才、氣、學(xué)、習(xí)”的不同,劃分出八種體貌類型,即“典雅”“遠(yuǎn)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其中,“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繁縟者,博喻醲采,煒燁枝派者也。”[4]1014對不同作者之“繁縟”與“精約”的體性風(fēng)格進(jìn)行了辨析。《镕裁》篇指出:“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4]1190“分”即作者之個性,根據(jù)作者個性之不同,呈現(xiàn)“繁”與“略”之風(fēng)格差異。在劉勰的觀念中,陸機(jī)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較為繁縟,他在《才略》篇認(rèn)為:“才欲窺深,辭務(wù)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4]1813賈誼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較為峻潔,“是以賈生俊發(fā),故文潔而體清。”[4]1024總之,劉勰指出由于作者情性之差異,作者之體性風(fēng)格會具有“繁縟”和“精約”之差異。
在行文運(yùn)筆方式層面,《镕裁》篇從意與言兩大角度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镕意裁辭”,認(rèn)為:“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shí)無方,辭或繁雜。”[4]1177因此,通過“規(guī)范本體”之镕和“剪截浮詞”之裁,以實(shí)現(xiàn)文章之“綱領(lǐng)昭暢”和“蕪穢不生”,否則,文章便會出現(xiàn)“一意兩出,義之駢枝”和“同辭重句,文之肬贅”的弊病。[4]1180因此,劉勰認(rèn)為“镕裁”之針對對象在于“情理”和“文采”,“镕裁”之具體操作方式為“標(biāo)三準(zhǔn)”以镕意,善“刪敷”以裁辭,“镕裁”之目標(biāo)在于“情周而不繁”、“辭運(yùn)而不濫”[4]1206。
《文心雕龍》搭建了“繁簡”批評體系的基本框架,之后,唐代劉知幾《史通》推崇《尚書》與《春秋》之“簡”②,將“繁簡”引入史書批評,從史書敘事與史書載事兩個層面論述“繁簡”③。史書敘事側(cè)重于“敘”,即行文用筆方式,史書載事側(cè)重于“事”,即內(nèi)容組成要素。《敘事》篇指出:“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6]156劉知幾于“繁簡”之態(tài)度偏于一端,強(qiáng)調(diào)史書尚簡。又言:“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6]158引用《春秋》《左傳》等書來論證“省句”與“省字”的必要性。他在《煩省》篇從“載事”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衡量史書“繁簡”的標(biāo)準(zhǔn)不在于篇幅多少,事件多少,而在于敘事時(shí)不能出現(xiàn)“事重”和“事闕”的弊病。他認(rèn)為:“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dāng)要其事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闕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6]246“事有妄載”為“煩”,“言有闕書”為“省”。總之,史書敘事尚簡的目標(biāo)為“文約而事豐”。
劉知幾在行文運(yùn)筆方式層面繼承劉勰的“繁簡”批評框架④,對史書敘事尚簡之“敘”的方式作了進(jìn)一步說明。但與劉勰不同的是,劉知幾認(rèn)為史書以“載事”為主,因此行文運(yùn)筆的針對對象為“言”與“事”,而劉勰認(rèn)為是“言”與“意”,“意”包含情理。這一內(nèi)容要素的區(qū)分大致代表了“敘事”與“抒情”“議論”文體的分途。
宋元明時(shí)期,文章學(xué)在文法論層面對“繁簡”做出進(jìn)一步拓展,呂祖謙、謝枋得等人提出行文有“省文法”,呂祖謙《古文關(guān)鍵》在評點(diǎn)東坡《晁錯論》時(shí),曾言:“須看省文法,前既說景帝時(shí)事了,到此輕舉過去。”[7]33指當(dāng)提及前文已經(jīng)論述過的內(nèi)容時(shí),后文可用省文法略敘。謝枋得《崇古文訣》在評點(diǎn)柳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錢公輔《義田記》等文時(shí),都曾提到“省文法”,使用語境和含義與呂祖謙相同。在時(shí)文相關(guān)理論著作中,魏天應(yīng)《論學(xué)繩尺》在《諸前輩論行文法》中引馮厚齋之言曰:“小講中且要斟酌詳略,恐是實(shí)事,題便要入題,最忌前后重復(fù),或前面已詳,則入題處便得省文法,或未詳,則入題處卻不可略。”[8]74d對時(shí)文體式的繁簡筆法做出了規(guī)定。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將“繁簡”納入篇法體系之中,強(qiáng)調(diào):“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yáng)頓挫,長短節(jié)奏,各極其致,句法也。”[9]963可見,文章學(xué)已明確將“繁簡”納入文法創(chuàng)作體系之中,在古文和時(shí)文評點(diǎn)時(shí)都突出行文時(shí)繁簡筆法的運(yùn)用。
總之,《文心雕龍》從言與意的關(guān)系出發(fā)分析“繁簡”,其“镕意裁辭”說和“繁縟”與“精約”的“體要”說奠定了“繁簡”文法論和格調(diào)論的兩大批評體系。唐代劉知幾《史通》將“繁簡”論引入史學(xué)理論中,從言與事的關(guān)系出發(fā)突出史書對裁“事”的重視,側(cè)重于分析史書利用繁簡筆法組織事件的方式。宋元明時(shí)期,文章學(xué)明確將“繁簡”納入文法創(chuàng)作體系之中,在古文篇法以及時(shí)文體式層面論述繁簡筆法的運(yùn)用情況。
與詩文和史學(xué)中的“繁簡”理論相比,以金圣嘆、脂硯齋、馮鎮(zhèn)巒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家在繼承劉勰、劉知幾等人的基礎(chǔ)上,又在文法層面上對形成小說繁簡風(fēng)格的種種筆法進(jìn)行細(xì)化,提出“極省法”“極不省法”“加倍省”“加倍增”等各種文法,在程度上加深了“繁簡”的創(chuàng)作指向,這種差異與小說本身的功能屬性相關(guān),羅燁《醉翁談錄》曾言:“講論處不滯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guī)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shù);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10]5指說話人為了迎合聽眾的趣味,講到枯燥和冷淡處,簡單地用三言二語輕輕帶過,而在情節(jié)精彩和熱鬧處,對聽眾感興趣的情節(jié)極力鋪敘和敷演。小說出于娛人的目的,熱鬧處用墨如潑,冷淡處惜墨如金,這種觀念影響到了小說文法思想。
二、明清小說的各種“繁簡”技法論
中國古代小說評點(diǎn)家繼承史書“镕事裁辭”的理論,主要從字法和句法的形式層面以及人與事為主體的內(nèi)容層面,分析作者如何利用“極省法”“極不省法”“避繁法”等與繁簡有關(guān)的筆法構(gòu)筑小說文本意義以及架構(gòu)小說的敘事結(jié)構(gòu)。
在形式層面,評點(diǎn)家指出作者善于利用字法和句法的變化以實(shí)現(xiàn)敘事的繁簡合度。就字法而言,脂硯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許多省力處。不得此竅者,便在窗下百般扭捏。”[11]153在具體行文過程中,作者大概使用以下幾類字詞進(jìn)行敘事:一是運(yùn)用含有重復(fù)性頻度意義指向的時(shí)頻副詞省略敘事。芥子園刊本曾評價(jià)《水滸傳》用字“盡詳略伸縮錯綜之妙”[12]329,他認(rèn)為作者為宋江作傳時(shí):“但有、無有、不、便留、終日、盡力、每每、只是、如常,皆著意寫兩個好字。”[12]329“每每”“如常”“終日”這類字詞表示相同的事情多次發(fā)生,暗含出現(xiàn)頻率兩次及以上。脂硯齋在評批寶釵說自己得了“那種病”時(shí)認(rèn)為:“‘那種病’。‘那’字與前二玉‘不知因何’二‘又’字,皆得天成地設(shè)之體;且省卻多少閑文,所謂‘惜墨如金’是也。”[11]153可見,“每每”“如常”“又”這類時(shí)頻副詞表示動作、事件等變化是經(jīng)常性和多次性的,用這類字詞可以省略已經(jīng)敘述過的情節(jié),避免重復(fù)。
二是運(yùn)用具有概括性意義指向的疑問代詞以省略敘事。如《水滸傳》第三十一回寫武松從頭備細(xì)地向宋江講述兩人從柴進(jìn)府上分別后的經(jīng)歷,“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jiān)一十五口。”芥子園刊本眉批認(rèn)為此段話中“怎生、怎地、如何,數(shù)落得妙,三兩行卻像有千百句言語在內(nèi)。”[12]596因武松的經(jīng)歷在前文中已經(jīng)鋪敘而出,此時(shí)向別人講述時(shí),若再次細(xì)細(xì)描畫,則難免累贅,因此用幾個疑問代詞以概括性地?cái)⑹觯梢怨?jié)省行文筆墨,又包含無數(shù)情事。之后,脂硯齋在《紅樓夢》“賈元春才選鳳藻宮”中認(rèn)為作者不寫元春晉封等熱鬧情事,只敘述寶玉擔(dān)心秦鐘生病的情節(jié),因此對“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等事都不關(guān)心,對此,甲戌本脂硯齋評曰:“大奇至妙之文,卻用寶玉一人,連用五‘如何’,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種寫到,其死板拮據(jù)、瑣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卻多少閑文,卻有無限煙波。”[11]270作者以寶玉作金針,連用五個“如何”便省略一番熱鬧瑣碎的文字,在省卻閑文的時(shí)候也留下無限煙波。
三是運(yùn)用自主性動詞以傳達(dá)敘事和寫人神理,評點(diǎn)家將之稱為煉字之法。如《水滸傳》第三回寫“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金圣嘆認(rèn)為:“省文也,卻用一‘?dāng)嚒郑撼鏊奈鍌€月中情事。”[12]107作者只用一個動詞便寫出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情事。又如《紅樓夢》第五十一回寫“寶玉命把煎藥的銀盄子找了出來。”脂硯齋指出:“‘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11]611一“找”字寫盡敘事情理。另外,作者也會運(yùn)用表示情態(tài)的動詞以寫活人物。貫華堂本《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評、改一體,金圣嘆不僅作為鑒賞者,而且作為創(chuàng)作者參與其中,對比其與容與堂本的差異,可以考察作者的創(chuàng)作旨趣。如容與堂本第四十六回寫石秀當(dāng)著楊雄之面與潘巧云對峙:“石秀睜著眼來道:‘嫂嫂,你怎么說這般閑話,正要哥哥面前說個明白。’”“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諍,教你看個證見。’”而貫華堂本刪改為:“石秀睜著眼道:‘嫂嫂,你怎么說?’”“石秀道:‘嫂嫂,嘻!’”金圣嘆于此批曰:“上只四字,此只一字,而石秀一片精細(xì),滿面狠毒,都活畫出來。俗本妄改許多閑話,失之萬里。”[12]858對比可知,金圣嘆刪改后,只用一個字便活畫出石秀精細(xì)、狠毒的性情,簡潔又準(zhǔn)確。
就句法而言,作者善于使用“縮句法”、“不完句法”等用筆策略在實(shí)現(xiàn)敘事內(nèi)容空白的基礎(chǔ)上增強(qiáng)畫面感,富有傳神之妙。《水滸傳》第五回寫幾個老和尚正在吃粥,但因魯智深來得聲勢,于是作者于“正在那里——”突然收住,金圣嘆認(rèn)為:“正在那里下,還有如何若何許多光景,卻被魯達(dá)忿忿出來,都嚇住了。用筆至此,豈但文中有畫,竟謂此四字虛歇處,突然有魯達(dá)跳出可也。”[12]147作者使用縮句法可以增強(qiáng)敘事的畫面感,讓讀者想見正是因?yàn)橛腥送蝗欢觯庞写思笨s句。歷代評論家對《紅樓夢》中的“縮句法”也多有贊賞,如第十六回寫趙嬤嬤正在敘述接駕的聲勢,在“說起來……”處被鳳姐“忙接道”而打斷,脂硯齋甲戌本夾批曰:“又截得好。‘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完,粗心看去則說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11]280此處截?cái)嗖粌H能避免繁復(fù),還能給予讀者巨大的想象空間,是文字傳神之處。清代王雪香在《紅樓夢總評》也贊嘆道:“書中多有說話沖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咽住不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筆。”[13]46縮句法能原汁原味地還原敘事場景,不僅能更好地描畫人物情態(tài),還能增強(qiáng)敘事的動態(tài)畫面感。
作者不僅善于利用“煉字法”“不完句法”之簡實(shí)現(xiàn)辭約事豐的意蘊(yùn)傳達(dá),還運(yùn)用“重疊”之繁使得作品生色。貫華堂本第四十四回寫石秀撞見潘巧云和裴如海調(diào)情時(shí),金圣嘆增添了五個“連忙”凸顯裴如海的反應(yīng),“那賊禿連忙放茶”“那賊禿虛心冷氣,連忙問道”“賊禿連忙道”“連忙出門去了”“那賊禿連忙走”,而容與堂本無這五個“連忙”⑤,金圣嘆于此贊嘆曰:“寫賊禿正要迎奸賣俏,陡然看見石秀氣色,便連忙放茶,連忙動問,連忙不敢,連忙出門,連忙走,更不應(yīng),真活現(xiàn)一個賊禿也。”[12]834金圣嘆增添的這五個“連忙”顯然更能活畫出和尚的心虛和石秀凜然的膽色。
在內(nèi)容層面,評點(diǎn)家們認(rèn)為小說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shí),面對紛紜復(fù)雜、頭緒眾多的人和事,會通過調(diào)整繁簡的用筆策略來組織和結(jié)構(gòu)文本。與戲曲理論中強(qiáng)調(diào)頭緒忌繁不同,小說理論側(cè)重于從文法層面分析作者如何利用繁簡筆法組織以人、事為主體的繁雜頭緒。
在組織結(jié)構(gòu)文本時(shí),作者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內(nèi)安排組織多個以人、事為主體的情節(jié)線索,評點(diǎn)家認(rèn)為作者善于利用避實(shí)擊虛之法使不同情節(jié)線索在小說人物的對話和耳目見聞中詳略并出、次序井然。如《水滸傳》第一百十二回寫柴進(jìn)向宋江備說盧俊義攻打宣州一事,對此袁無涯本眉批曰:“盧俊義事皆以言見,以虛為實(shí),得省文法。”[12]1400作者并未花費(fèi)大量筆墨對盧俊義破宣州的情節(jié)實(shí)寫,而是通過他人之口進(jìn)行轉(zhuǎn)述,節(jié)省行文筆墨。之后,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又進(jìn)一步指出:“《三國》一書,有近山濃抹、遠(yuǎn)樹輕描之妙。畫家之法,于山與樹之近者,則濃之重之;于山與樹之遠(yuǎn)者,則輕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遙,峰嵐層疊,豈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詳繪之乎?作文亦猶是已。如皇甫嵩破黃巾,只在朱雋一邊打聽得來;袁紹殺公孫瓚,只在曹操一邊打聽得來;趙云襲南郡,關(guān)、張襲兩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來;昭烈殺楊奉、韓暹,只在昭烈口中敘來;張飛奪古城在關(guān)公耳中聽來;簡雍投袁紹在昭烈口中說來。至若曹丕三路伐吳而皆敗,一路用實(shí)寫,兩路用虛寫;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惟遣使入?yún)怯脤?shí)寫,其四路皆虛寫。諸如此類,又指不勝屈。只一句兩句,正不知包卻幾許事情,省卻幾許筆墨。”[14]16毛氏父子將作畫與作文相比,強(qiáng)調(diào)為了將不同情節(jié)線索交代清楚,避免重復(fù),作者利用虛實(shí)結(jié)合的方式,以繁筆描寫此處聚焦之文,借小說人物之眼、耳、口以簡筆虛敘他處之文,在節(jié)省筆墨的同時(shí),結(jié)構(gòu)不同情節(jié)線索。
作者在布局小說結(jié)構(gòu)、串聯(lián)人物情節(jié)時(shí),或以一人作線描寫活畫多人性情,或以一事作線穿插映帶多處情節(jié),即一筆作數(shù)筆之用。《水滸傳》第四十三回寫戴宗在尋公孫勝時(shí),遇見欲上梁山入伙的楊林,兩人在同行的過程中,又以楊林引出鄧飛和孟康兩人,鄧飛在敘述聚義經(jīng)歷時(shí)又引出裴宣,對此,金圣嘆評曰:“先生一人,次生出二人。卻因二人,又生出一人,真是行文省力法。”[12]819金氏認(rèn)為因?yàn)樽髡呤樟_一百八人是大難事,因此便以戴宗尋找公孫勝作線,順手串出四五人,行文筆墨較為簡潔。脂硯齋在評點(diǎn)《紅樓夢》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其“一筆作數(shù)筆”的高超結(jié)構(gòu)筆法,第七回寫薛姨媽讓周瑞給姐妹們送花,甲戌本脂硯齋眉批曰:“余問送花一回,薛姨媽云:‘寶丫頭不喜這些花兒粉兒的’,則謂是寶釵正傳,又主阿鳳惜春一段,則又知是阿鳳正傳;今又到顰兒一段,卻又將阿顰之天性從骨中一寫,方知亦系顰兒正傳。小說中一筆作兩三筆者有之,一事啟兩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數(shù)之筆也。”[11]162作者僅以送花一事作線,便將寶釵之英爽,熙鳳之不羈,顰兒之敏感活畫而出,足見作者筆法的高超。
為了使上下結(jié)構(gòu)勻稱統(tǒng)一,繁簡相宜,前文所省略的情節(jié)有時(shí)又會在下文中補(bǔ)出,即毛宗崗所說的“添絲補(bǔ)綿、移針勻繡”,他認(rèn)為:“凡敘事之法,此篇所闕者補(bǔ)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勻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無遺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14]16利用前后文的勻補(bǔ),不僅能避免前文拖沓,還能使后事增加渲染。脂硯齋又進(jìn)一步認(rèn)為這種補(bǔ)敘方式體現(xiàn)了小說行文的“省中實(shí)”,《紅樓夢》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一節(jié)中英蓮和馮淵的悲歡從葫蘆僧口中補(bǔ)敘,甲戌本脂硯齋眉批曰:“英、馮二人一段小悲歡幻景從葫蘆僧口中補(bǔ)中,省卻閑文之法也。”賈雨村聽完之后,又以“夢幻情緣”“薄命兒女”對兩人的悲歡幻景定性,對此甲戌本脂硯齋眉批曰:“使雨村一評,方補(bǔ)足上半回題目。所謂此書有繁處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虛;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實(shí)。此則省中實(shí)也。”[11]100作者并未花費(fèi)大量筆墨對英蓮和馮淵的情事進(jìn)行正面詳細(xì)地描寫,只是借他人之口虛敘補(bǔ)出,是省筆,而賈雨村對此事的感慨評論又進(jìn)一步直擊主題,因此脂硯齋認(rèn)為是“省中實(shí)”。
此外,作者在結(jié)構(gòu)組織情節(jié)線索時(shí),不僅會利用省筆結(jié)構(gòu)頭緒眾多的線索,還會花費(fèi)大量筆墨對結(jié)構(gòu)小說和突出人物性情的關(guān)鍵性情節(jié)進(jìn)行極力描寫,金圣嘆將其稱為“大落墨法”[12]20,并且舉出了以下幾個例子進(jìn)行詳細(xì)說明:第一個是“吳用說三阮”,金圣嘆認(rèn)為加亮說阮一番文字具有曲折迎送之能,而之所以對其進(jìn)行細(xì)細(xì)描寫,是因?yàn)榫汀端疂G傳》的行文結(jié)構(gòu)而言,“水滸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滸之終也,終于石碣。”[12]270石碣村阮氏三雄即為一百八人之入水滸之開始。第二個是“楊志北京斗武”,金圣嘆認(rèn)為:“梁中書之愛楊志,止為生辰綱伏線也,乃愛之而將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獨(dú)提掇。”因此才有教場斗武一番花團(tuán)錦簇的文字。第三個是“王婆說風(fēng)情”,如果沒有王婆在其中的說合,西門慶和潘金蓮也就失去了連接的紐帶。最后一個是“二打祝家莊”,這一處情節(jié)不僅是梁山大規(guī)模對外征戰(zhàn)的開始,也是晁蓋時(shí)代向宋江時(shí)代過渡的開始。可見,作者花費(fèi)大量筆墨極力渲染關(guān)鍵的情節(jié)使小說結(jié)構(gòu)環(huán)環(huán)相扣,圓合統(tǒng)一。同時(shí),作者怕文字過長,出現(xiàn)累贅,會利用“橫云斷山”等方法截?cái)唷⒉黹_文字,以避繁章法。金圣嘆仍以“二打祝家莊”等情節(jié)為例,他說:“有橫云斷山法。如兩打祝家莊后,忽插出解珍、解寶爭虎越獄事;又正打大名城時(shí),忽插出截江鬼、油里鰍謀財(cái)傾命事等是也。只為文字太長了,便恐累墜,故從半腰間暫時(shí)閃出,以間隔之。”[12]20可見,出于繁簡相宜的考慮,小說結(jié)構(gòu)在連斷中交錯并出。
最后,出于因文生事的創(chuàng)作原則,為順應(yīng)情節(jié)發(fā)展的情理邏輯,作者會隨地生波,運(yùn)用繁筆對事件發(fā)生的前因后果進(jìn)行敷衍和鋪敘,并且花費(fèi)大量筆墨蹴起波瀾,使得小說敘事波折叢生。金圣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曾對“極不省法”進(jìn)行過解釋,他認(rèn)為:“有極不省法。如要寫宋江犯罪,卻先寫招文袋金子,卻又先寫閻婆惜和張三有事,卻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卻又先寫宋江舍棺材等。”[12]21此“極不省法”指作者運(yùn)用繁筆對千曲百折的情節(jié)進(jìn)行敘述,即“夫耐庵之繁筆累紙,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成于殺婆惜者”[12]21。作者為了實(shí)現(xiàn)人物和情節(jié)邏輯持續(xù)推進(jìn),利用繁筆蹴起波瀾,使得敘事“曲曲折折,層層次次”。
總之,當(dāng)同時(shí)敘述不同的情節(jié)線索時(shí),作者對此處聚焦之文詳細(xì)敷演,利用人物之口、耳約略點(diǎn)綴他處之文;在面對頭緒繁雜的人或事時(shí),以一筆做數(shù)筆之用,串聯(lián)映帶多處情節(jié)線索以節(jié)省行文筆墨;為使上下文結(jié)構(gòu)統(tǒng)一,繁簡相宜,前文所省略的內(nèi)容會在下文補(bǔ)出。此外,對突出人物性情的關(guān)鍵性情節(jié),作者會利用繁筆敷演以使敘事曲折叢生,波瀾并起。
三、“繁簡”與古典小說文本創(chuàng)構(gòu)之適度原理
經(jīng)典性文學(xué)作品的形成需要作者之意、文本之言與文體在相互作用以及互相配合時(shí)達(dá)到恰到好處即“合度”的地步。具體而言,作者之意涉及情、理、事,文本之言涉及字、句,文體涉及詩歌、史傳、論說、小說等,這些文學(xué)要素在創(chuàng)作時(shí)需要作者經(jīng)過調(diào)和以達(dá)到恰到好處的“度”。李澤厚曾認(rèn)為“度”是人類學(xué)歷史本體論的第一范疇。[15]10又指出:“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出現(xiàn)了‘度’,即是‘立美’。”[15]11劉勰《文心雕龍·镕裁》篇指出:“夫美錦制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lǐng)袖。”[4]1205強(qiáng)調(diào)文章之镕裁如制衣,需要繁簡合度。黃侃《文心雕龍?jiān)洝酚诌M(jìn)一步引申,認(rèn)為:“尋镕裁之義,取譬于范金、制服。范金有齊,齊失則器不精良;制服有制,制謬而衣難被御。洵令多寡得宜,修短合度,酌中以立體,循實(shí)以敷文,斯镕裁之要術(shù)也。”[16]114使范金、制服、作文精良的重要因素是在實(shí)踐或創(chuàng)作時(shí)學(xué)會“合度”,掌握分寸,實(shí)現(xiàn)立美。
“繁簡合度”之“度”的把握和體現(xiàn)涉及作者創(chuàng)作和讀者鑒賞兩個層面。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shí),一方面要根據(jù)不同文體之體要特征進(jìn)行剪裁,以實(shí)現(xiàn)繁簡得體;另一方面要調(diào)和“言”與“意”之關(guān)系來實(shí)現(xiàn)繁簡合度,此“意”指作者在構(gòu)思時(shí)如何通過抒發(fā)情感、經(jīng)營位置、組織事類、取舍材料、突出主題等要素實(shí)現(xiàn)綱舉目張、彌綸有序。讀者在鑒賞時(shí),以“文約事豐”“言簡意賅”和“辭敷意顯”作為“繁簡合度”的標(biāo)準(zhǔn),此“意”與作者創(chuàng)作構(gòu)思層面的“镕意裁辭”不同,而是體現(xiàn)在作品中的“事意”“理意”“情意”。
首先,批評家們強(qiáng)調(diào)“繁簡”之度的把控要根據(jù)文體來進(jìn)行镕裁,考慮不同文體的體要和體格,作者以一種最適度的方式,即最符合文體自身體要的方式來進(jìn)行剪裁。《文鏡秘府論·定位》篇指出:“文之大者,藉引而申之;(文體大者,須依其事理,引之使長,又申明之,便成繁富也。)文之小者,在限而合之。(文體小者,亦依事理,豫定其位,促合其理,使歸約也。)申之則繁,合之則約。”[17]1489認(rèn)為文體要與事理、言辭互相配合,根據(jù)文體之大小進(jìn)行引申和歸約,一旦破體,則文體自身的繁簡之度便會被破壞。因此清代古文家嚴(yán)格遵守古文簡潔的體格特征,嚴(yán)防小說氣的侵入,李紱在《古文辭禁》中認(rèn)為:“一禁用傳奇小說。小說始于唐人,鑿空撰為新奇可喜之事,描摹刻酷,鄙瑣穢褻,無所不至,若《太平廣記》是也。宋元而下,泛濫斯極。”[18]4009可見,與古文相比,小說長于“描摹刻酷”,并且體格瑣碎。平步青《霞外攟屑》也指出:“古文寫生逼肖處,最易涉小說家數(shù),宜深避之。”[19]559強(qiáng)調(diào)古文描寫刻畫生動處容易流于小說家路數(shù)。
其次,文本中的“言”與“意”、“言”與“事”在創(chuàng)作活動中要不斷地相互協(xié)調(diào)以達(dá)到恰到好處的地步。劉勰在《文心雕龍·镕裁》篇中強(qiáng)調(diào)“镕意裁辭”,開篇即云:“情理設(shè)位,文采行乎其中。剛?cè)嵋粤⒈荆兺ㄒ在厱r(shí)。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shí)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镕裁。隱括情理,矯揉文采也。”[4]1177劉勰在這段話中透露兩個信息,一是他認(rèn)為“意”包含“情理”;二是他認(rèn)為繁簡失度的表現(xiàn)是“意或偏長”、“辭或繁雜”,因此通過“镕裁”,實(shí)現(xiàn)“隱括情理,矯揉文采”,找到令“言”與“意”相互協(xié)調(diào)之“度”,即“情周而不繁,辭運(yùn)而不濫”。到了唐代,劉知幾《史通·煩省》篇則從言與事的關(guān)系出發(fā),擴(kuò)大了作者之“意”的范圍,認(rèn)為:“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dāng)要其事有妄載,苦于榛蕪,言有闕書,傷于簡略,斯則可矣。”[6]246強(qiáng)調(diào)史傳文要注重镕事裁辭,使“言”與“事”經(jīng)過調(diào)和以合度。具體而言,在史傳文書寫中,方苞《與孫以寧書》指出:“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guī)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綴文之士以虛實(shí)詳略之權(quán)度也。”[20]136方苞認(rèn)為敘事“詳略之權(quán)度”的掌握是要根據(jù)傳主的規(guī)模來決定,不能事事皆載。劉熙載《藝概·文概》也言:“傳中敘事,或敘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敘其無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與時(shí)位,而稱量以出之。”[21]218強(qiáng)調(diào)傳記敘事需要根據(jù)人之志行與時(shí)位,稱量而作。
中國古代小說“繁簡”理論繼承史傳文镕事裁辭的基本理念,強(qiáng)調(diào)作者在立意時(shí)注重分析作者如何合理地經(jīng)營位置,如何利用恰當(dāng)?shù)难赞o處理以人和事為中心的眾多情節(jié)線索,如何利用繁簡筆法變換描摹人物性情。小說批評家認(rèn)為作者對敘事繁簡之“度”的考量和把握主要根據(jù)人物的賓主地位、事件的主次輕重差別、故事的主旨內(nèi)涵等因素來調(diào)控。小說繁簡之“度”是要從正文與閑文、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關(guān)鍵性情節(jié)與次要情節(jié)、文勢的緩急快慢、盛衰主題之演變以及描摹人物性情之隱與顯等相反相成的因素之間的比較中來把控的。
不同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shí)對繁簡之“度”的感知和把控是不同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一個需要各方面文學(xué)因素都恰到好處地相互協(xié)調(diào)的過程,這個過程具有主體性和不可重復(fù)的單一性,因此,不同作者對繁簡之“度”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規(guī)定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繁簡之“度”不能被規(guī)范化和形式化,則文學(xué)之經(jīng)典的評判和創(chuàng)作之傳承也無以為繼,因此,不同批評家致力于總結(jié)和歸納各種形成小說繁簡的技法。
讀者如何感知這種“度”呢?換言之,“繁簡合度”之“度”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敘事多、篇幅較長的小說一定為“繁”嗎?敘事少、篇幅較短的小說一定為“簡”嗎?晉張輔曾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一也。”[22]2063a劉知幾《史通·煩省》篇認(rèn)為張輔以篇幅內(nèi)容多少來評判史書煩省的標(biāo)準(zhǔn)是不合理的,史書“事有妄載”才能稱為“煩”,“言有闕書”才能稱為“省”,史書應(yīng)以“文約事豐”為工。歐陽修《進(jìn)新唐書表》曾認(rèn)為《新唐書》:“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23]6472顧炎武《日知錄》引宋代劉器之言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24]1100《新唐書》言辭太簡略,所敘之事有缺漏,因此為人詬病。具體到小說評點(diǎn)中,評點(diǎn)家贊嘆作者在敘事時(shí)善于以簡略之語描繪一個可以自由聯(lián)想并且意蘊(yùn)豐富的開放性空間。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認(rèn)為:“張二官頂補(bǔ)西門千戶之缺,而伯爵走動說娶嬌兒,儼然又一西門,其受報(bào)亦必有不可盡言者。則其不著筆墨處,又有無限煙波,直欲又藏一部大書于無筆處也。此所謂筆不到而意到者。”[25]1498在西門慶暴亡后,作者以簡略之筆描寫張二官重復(fù)西門慶賣官鬻爵、貪財(cái)好色、聚攏幫閑的種種行徑,作者雖未細(xì)細(xì)描寫張二官之后的人生軌跡,但讀者可以通過西門慶的結(jié)局透視張二官的人生走向。之后,脂硯齋又以“不寫之寫”評述《紅樓夢》的留白技巧,第三十九回寫一小廝向平兒告假,平兒埋怨道:“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著,我應(yīng)起來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脂硯齋認(rèn)為作者在這一處以一語閑言便補(bǔ)寫出賈璉處天天鬧熱、迎來送往的種種情事,事溢于文外,讀者通過作者簡略的描寫可以透視如冰山一角下蘊(yùn)含深廣的開放性空間世界。
此外,小說理論也指出作者善于在無字句處實(shí)現(xiàn)敘事和寫人的含蓄性美感蘊(yùn)含。《水滸傳》第三十七回寫李逵騙了宋江的銀子去賭博,準(zhǔn)備贏錢請宋江吃酒,卻輸個精光,大鬧賭房,宋江幫忙解決后,又請李逵和戴宗吃酒,李逵說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jià)吃。”金圣嘆贊嘆道:“李逵傳妙處,都在無字句處,要細(xì)玩。”[12]702他指出的“無字句”即李逵一方面將大鬧賭房的事情完全拋開,坐下高興吃酒;另一方面反客為主,毫無常人對請客主人的殷勤奉承。這些描寫都于含蓄處見出李逵性格的豪爽和樸實(shí)。脂硯齋也稱贊《紅樓夢》敘事的含蓄雋永,第五十七回寫紫鵑三試玉,由此引發(fā)寶玉呆病,脂硯齋在回末評曰:“寫寶玉、黛玉呼吸相關(guān),不在字里行間,全從無字句處,運(yùn)鬼斧神工之筆,攝魄追魂。”[11]626強(qiáng)調(diào)《紅樓夢》于無字句處描繪出寶黛彼此牽掛的深情厚意,是追魂攝魄之筆。
另一方面,小說敘事的“繁處愈繁”區(qū)別于簡單的“面面俱到”,作者能于常人之省處施以繁筆,能于常人之繁處用以簡筆,在行文急忙處的敷演與鋪敘不僅可以使情節(jié)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還能進(jìn)一步影響讀者的審美體驗(yàn),增強(qiáng)審美效果。《水滸傳》第二十七回寫武松脫過殺威棒后,眾囚徒、武松以及讀者都在推測后面可能會有的更重的刑罰,但作者卻細(xì)細(xì)描畫管營如何逐日管待,金圣嘆也指出作者對武松“洗浴乘涼,如此等事,無不細(xì)細(xì)開列,色色描畫”[12]525,但這種鋪敘反而使敘事的驚險(xiǎn)效果得到進(jìn)一步的增強(qiáng),金圣嘆認(rèn)為:“管營看顧后,讀者便急欲得知其故久矣。忽然接入連日看待之厚一篇,煩文瑣景,雖一往如在山陰道中,耳目應(yīng)接不暇,然心頭已極悶悶。”[12]533一系列“煩文瑣景”的鋪敘使讀者心頭悶悶,更加疑惑,急欲知下文。“繁處愈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辭敷而意顯”的審美效果。
可見,討論文章、小說、史書之“繁簡”,最重要的是辨析清楚“言”與“意”的關(guān)系,此“意”即讀者感知到的體現(xiàn)在作品中的“情意”、“事意”與“理意”,與“镕意裁辭”之“意”不同,“镕意”之“意”指在創(chuàng)作構(gòu)思階段作者組織作品之“意”。“辭約意豐”和“辭敷意顯”當(dāng)為“繁簡合度”之標(biāo)準(zhǔn)。
總之,對“繁簡”理論進(jìn)行深入探討,不僅可以進(jìn)一步從內(nèi)部把握小說文本創(chuàng)構(gòu)中的原理和邏輯,還可以從外部探討小說與其他文體互動中顯示出的文體差異和特性,對探討小說文本創(chuàng)作形態(tài)具有重要意義。
注:
①劉勰在《征圣》篇說道:“文成規(guī)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dá)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以“《春秋》一字以褒貶”的例子證明“簡言以達(dá)旨”,以“《儒行》縟說以繁辭”的例子證明“博文以該情”。劉勰認(rèn)為在創(chuàng)作時(shí)若能做到“征圣”與“宗經(jīng)”,那么文章會具有“體約而不蕪”的效果。
②《史通·敘事》言:“歷觀自古,作者權(quán)輿,《尚書》發(fā)蹤,所載務(wù)于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
③浦起龍《史通通釋》:“此篇用意,與《敘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后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法。”
④ 關(guān)于劉勰和劉知幾的繼承關(guān)系,劉知幾《史通·自敘》篇以《法言》《文心》等書自況:“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
⑤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那和尚放下茶盞”“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道”“裴如海道”“相別出門去了”“那和尚應(yīng)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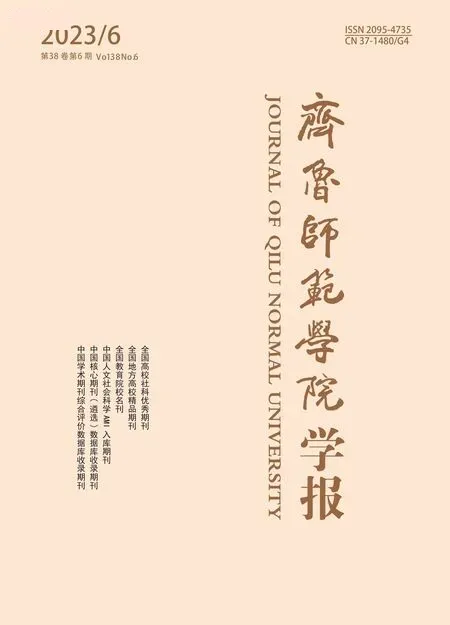 齊魯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齊魯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 齊魯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能性述補(bǔ)結(jié)構(gòu)“V 得/不了”的對稱與不對稱分析
- 效率與正義:行政訴訟審限制度實(shí)現(xiàn)的類型及其優(yōu)化路徑
- 關(guān)懷倫理與工作的未來
——基于人機(jī)關(guān)系視角的分析 - 課程思政背景下視覺傳達(dá)設(shè)計(jì)專業(yè)項(xiàng)目式教學(xué)探究
- 模擬教學(xué)法在高師教學(xué)法課程實(shí)訓(xùn)教學(xué)中的實(shí)驗(yàn)研究
——以學(xué)前兒童美術(shù)教育課程為例 - 基于OBE 理念的戰(zhàn)略管理課程混合式教學(xué)創(chuàng)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