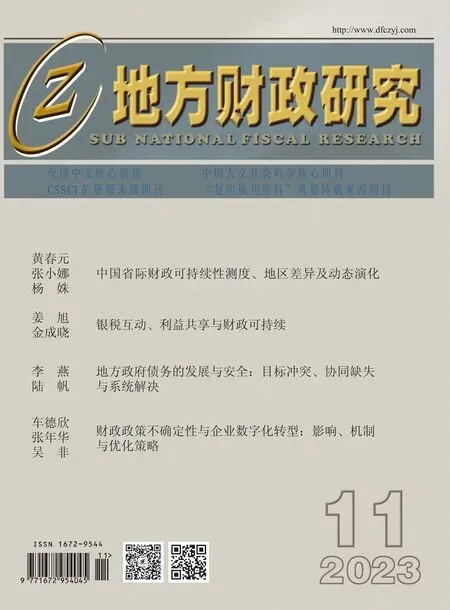減稅政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效應研究
鄧曉蘭 李 珂
(西安交通大學,陜西 710127)
內容提要:減稅短期可能造成財政減收,長期來看具有“放水養魚、反哺財政”的積極作用,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有何影響需要驗證。本文選取2008 年—2020 年全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通過財政反應函數量化測算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實證檢驗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效應。實證結果顯示:減稅背景下我國地方政府確實存在“財政疲勞”現象,但總體上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有正向作用,這種促進效應主要通過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釋放市場主體活力,推動地區經濟增長來實現;減稅造成短期財政減收也會導致地方財政自有收入能力降低,加劇其對中央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降低自身征稅努力,進而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因此,應明確減稅目標,理順地方財政收入機制,加強預算約束和稅收征管努力。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針對愈發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和市場對宏觀調控政策的敏感度,國家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發揮應有的作用;要用好政策空間,找準發力方向,精準有力實施宏觀調控。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2023 年1—11 月,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費1.34 萬億元。自2008 年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為了應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目標側重點,我國的減稅政策進行多階段的調整。從應對金融危機的需求側減稅,到新常態時期的供給側減稅,也就是結構性減稅政策,再到2018 年引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普惠性減稅政策至今,如此長時間、大規模的減稅會造成財政減收。但是,地方政府所承擔的施政功能需求并不會因財政減收而適時降低,如持續推進污染防治、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加大民生領域投入等都需要地方政府財力長期穩定的支持。另外,經濟遭受外部沖擊時,也會導致財政收入增速放緩,政府財力顯著降低。“支出難降、收入不增”使得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加大,容易引發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和信用危機,削弱財政可持續性。因此,長時間、大規模減稅政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是正向促進還是反向抑制的問題亟須深入研究。
相關的研究文獻主要圍繞短期財政減收和長期搞活經濟兩個方面展開。李萬甫和劉同洲(2020)[1]認為大規模、持續性與制度化的減稅政策會作用于地方財政收入的總量和結構,從而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減稅政策可能威脅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根本原因是減稅導致的地方財政收支不平衡(蔡昌和朱凱達,2019)。[2]減稅會對我國地方財政收支總量產生不利影響,說明“增支減收”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于樹一和楊遠旭,2019)。[3]減稅政策除影響地方財政收支總量,也對財政收入結構產生影響,一方面降低間接稅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實現稅制結構的優化,另一方面又會引起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反應,弱化財政收入的法治程度(郭慶旺,2019[4];賈俊雪,2019[5])。
雖然減稅政策在短期內可能會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造成上述的負面影響,但其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也非常明顯。減稅在中長期內釋放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推動地區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擴大規模,對國家經濟發展也有提振效果(黃健等,2018[6];范子英,2019[7];鄧力平等,2020[8];Johnson,2006[9];Pereira 和Roca,2011[10])。減稅對擴大消費規模和促進社會投資有著積極作用,最終可以有效改善財政收入規模(白彥鋒和陳珊珊,2017[11];楊默茹和楊令儀,2022[12];陳志勇等,2022[13])。減稅對地方負債率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其對地方經濟增長速度和化解存量債務的能力來發揮(劉方,2020[14];張學誕和李娜,2020[15])。減稅能夠有效地降低市場主體的稅費負擔,推動其擴大投資和助力創新來拓寬稅收基礎,彌補稅收損失,從而使地方經濟和財政形成良性循環(鄧曉蘭等,2021)。[16]
上述研究對本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但是現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個別稅收優惠政策,部分學者雖然關注到減稅的長期作用,但主要基于規范分析,未從實證角度去驗證。本文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的作用方向和機制,為我國下一步減稅政策的調整提供決策參考。本研究的邊際貢獻是:第一,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長期減稅政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效應。第二,厘清減稅政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影響的作用機制,并模擬中介效應檢驗程序,驗證減稅政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理論分析和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測度;第三部分為實證檢驗;第四部分為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和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測度
(一)理論分析與待檢驗假說
從動態的視角看,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機制有兩方面:一方面,減稅通過為市場主體減負以釋放其活力,通過促進消費行為、擴大投資規模和提升創新實力等來刺激經濟增長,實現“放水養魚、反哺財政”,有利于財政可持續性。減稅能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降低產品價格,從而刺激消費(范子英,2019)。[7]減稅對投資意愿的推動作用主要來自于成本效應和融資約束,減稅降低投資成本和緩解融資約束,增強市場主體的投資意愿(張伯超,2019)。[17]減稅對創新的激勵作用主要來自融資約束和創新回報,減稅增大市場主體的融資空間,提高凈投資回報率,激勵創新(葉顯等,2019)。[18]市場主體被激活、投資與消費增加,從而稅基擴大,稅源增加,據此,得到本文的第一個假說:
H1:減稅政策可以通過刺激消費、促進投資、加強創新等路徑正向影響財政可持續性。
減稅導致地方政府減收,而剛性支出壓力則使地方政府可能會產生一些策略性行為(馮俊誠,2022)[19],最終抑制財政可持續性。減稅帶來的財政壓力使得地方政府瞄準“自由裁量”的非稅收入來彌補剛性的財政支出,扭曲財政收入結構(谷成和潘小雨,2020)。[20]同時,減稅造成財政收支缺口的擴大使得中央政府加大“救援”力度,增加轉移支付,地方政府將其視為一種無償收入,降低地方政府征稅努力(于井遠,2021)。[21]從這一角度看,能否帶來地方政府對收入結構和征管努力的主動調整是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能否實現的關鍵。據此,得到本文的第二個假說:
H2:減稅政策可以通過扭曲財政收入結構、降低征稅努力等路徑負向影響財政可持續性。
綜上所述,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機制應從促進效應和抑制效應兩個方面分析(見圖1)。

圖1 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理
(二)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測度
財政可持續性量化是進行實證分析的重要前提,參考借鑒 Gohsh 等(2013)[22]的思路通過構建財政反應函數來求得地方政府負債率的理論上限值,進而度量地方政府財政可持續性。
1.財政反應函數的構建
本文利用跨期預算約束條件來推演、說明、檢驗和測度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模型:財政反應函數①財政反應指的是政府為應對債務風險而采取的調節盈余行為,財政反應函數則是刻畫此項政府行為的工具。財政反應函數可依據其形式劃分為線性和非線性兩種,其中,線性財政反應函數暗示政府擁有充足的意愿和無限的能力去調整政府債務狀況,而非線性財政反應函數則更為貼近現實,能夠有效刻畫政府的“財政疲勞”現象。非線性財政反應函數表明當政府負債率低于警戒值時,負債率上升,政府會積極調整財政基本盈余的狀況來彌補負債,財政可持續;而當政府負債率高于警戒值時,債務付息壓力超過政府財政調整能力,政府會放棄調整,陷入“財政疲勞”狀態。。財政基本盈余公式如下:
式中,BSit為第t 期第i 個省份的財政基本盈余(或赤字),FRit為財政收入,FEit為不含地方政府債務利息給付的財政支出。
地方政府債務公式如下:
式中:DEBTi,t-1為第t-1 期第i 個省份的債務,rit為政府債務利率。公式(2)的含義是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債務彌補財政赤字或者調節財政盈余來償還前期債務本金和利息。根據泰勒公式可得公式(3),地方政府的新增負債率主要由上期負債率、本期經濟增長率、政府債務利率和基本盈余率決定。
式中:debtit為第t 期第i 個省份的負債率,bsit為基本盈余率,git為經濟增長率。
本文應用Ostry 等(2010)[23]的非線性財政反應函數,即公式(4)。當λ>0,意味著地方政府的基本盈余可以對負債率做出正向反饋,當債務規模擴大時,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增收減支等方式來彌補債務利息,地方財政可持續。反之,當λ<0 時,地方政府則存在“財政疲勞”,存在某種剛性使地方政府無法再通過調整基本盈余來滿足債務償付,地方財政的調整能力存在著上限。
式中:Xit為其他影響地方政府基本盈余率的因素,uit為個體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理論推演可知,當債務率達到上限時,本期盈余和債務利息相等,即:
聯立公式(5)和回歸估計結果,可得計算負債率理論上限值的一元三次方程,將樣本期內變量的均值代入方程,求得最大實數根debti*。同時,本文應用壓力測試方法,利用啟動地方債務限額管理后控制變量的均值、城投債歷年平均發行利率代入模型進行驗證。地方財政可持續性fispaceit為地方政府負債率的理論上限值debti*與實際值debtit的差,計算公式為:
2.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回歸測度
(1)變量說明。參考陳寶東(2018)[24]的做法認為地方政府的基本盈余率存在著慣性,即本期基本盈余率會受到上一期的影響,因此,在公式(4)中納入上一期基本盈余bsit-1。
被解釋變量為基本盈余率。解釋變量為負債率,2015 年前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是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中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2015 年后則來自地方政府發行的公債余額,與前述口徑基本一致。個別的缺失值由來源于中國債券信息網、各地財政廳和證券公司行研報告的數據。
控制變量Xit主要選取會影響基本盈余率的因素:居民儲蓄率csit,財政支出缺口fe_gapit,以及構建開放經濟和國內環境所需的國際直接投資率fdiit和國內產業結構insit。其中,居民儲蓄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 比值;財政支出缺口是財政支出實際值偏離潛在值的程度,采用HP 濾波方法計算所得;國際直接投資率是國際直接投資額和GDP 的比值;產業結構指數則是第三產業生產值和第二產業生產值的比值。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2)財政反應函數回歸估計。表2 的系統GMM估計結果顯示:模型(1)—(3)中被解釋變量的滯后期均為正值且顯著,說明地方基本盈余率受上一期的影響,存在著慣性,將其納入財政反應函數模型是正確的。此外,還需檢驗系統GMM 估計前提{σit}非自相關,即擾動項的差分存在一階自相關和二階非自相關,AR(2)結果證實模型(1)—(3)均可滿足上述前提條件。此外,系統GMM 估計采用工具變量,需檢驗是否存在工具變量過度識別的問題,Sargan檢驗結果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接受“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假設,說明估計結果可信。模型(3)中debt-13的系數顯著為負,我國的地方政府存在“財政疲勞”現象,即我國地方政府不存在基本財政對債務的正向反應機制,既有的財政行為不可持續,需對債務規模進行控制。
(3)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水平的測度。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相對可控。以2020 年為例(見表3),排行榜位居前三位的是廣東、江蘇、上海,是我國地方經濟實力較強的東部地區,陳志勇(2014)[25]計算上述地區的財政預算調整成功率為100%,從側面印證了本文所得結論的合理性。青海、黑龍江和新疆財政可持續性表現較弱,其中,青海和新疆位于我國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黑龍江則是我國首個啟動財政重整計劃的省份,其預算調整成功率分別是36%、40%和50%,說明一旦遭受外部沖擊,極易陷入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同時,本文主要著眼于地方政府債務,若考慮隱性債務,地方政府的實際負債率應該更高,財政空間也勢必大為縮水。因此,第20 名以后的地區都應高度重視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問題。

表3 地方政府負債率的理論上限值和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水平
三、減稅政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影響的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研究設計
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間接影響路徑主要有兩條:第一,釋放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力,表現為減稅的積極效應傳導到消費規模、投資意愿和創新能力來促進地方生產擴張,經濟發展,反哺財政,提高財政可持續性。第二,轉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表現為減稅后地方政府致力于增加非稅收入規模和降低稅收征管努力來抑制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為探究上述影響機制是否顯著存在,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以投資為例):
式中:invit為中介機制變量投資規模,第t 期第i 個省份的投資規模。本文采用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26]檢驗中介效應的程序,該程序可以有效降低犯兩類錯誤的概率。
(二)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fispaceit是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代理變量,即借助財政反應函數的估計結果進行測度的2008 年—2020 年間30 個省份負債率理論上限值與實際值之間差額。
解釋變量tax_rateit為稅收收入增長率。由于減稅規模在省級層面的數據不可得,已有文獻采用稅收收入增長率來量化減稅,也有部分檢驗具體政策效應的文章通過設置虛擬變量來說明減稅。本文認為稅收收入增長率越小,說明減稅力度越大。
控制變量Xit主要選取會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因素:經濟增長率GDP_rate、貿易開放度open、財政分權fd 和財政支出剛性fis_e。其中,經濟增長率是作為經濟發展的體現,會影響地方的財政收入情況。貿易開放度是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 的比重,也是構建地方經濟環境模型中常用的指標。財政分權是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與人均中央財政收入的比值,該值越高,財政分權程度越低,則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財政自給能力越強,財政可持續性良好。財政支出剛性是地方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財政支出剛性不利于地方政府維持財政收支平衡,惡化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中介變量中,消費規模cnsmptn 是地方的消費水平,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投資意愿inv 是地方的投資規模,采用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其中,《中國統計年鑒》中固定資產投資額統計數據為2008 年—2017年,2018 年—2020 年根據各省公布的不含農戶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利用農戶增速求得農戶固定資產投資額相加整理得到。創新能力innvtn 是地方的創新水平,采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專利申請受理數、技術輸出地域合同金額、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和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創新指數。收入結構nontax_fis 是地方財政收入結構,采用《中國稅務年鑒》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的比值確定。征稅努力levy_eff是地方政府的征稅努力,采用《中國稅務稽查年鑒》中在職稽查人員數量、稽查機構數量和地方稅收收入合計數,《中國統計年鑒》中建設用地面積、其中將每公頃在職稽查人員數量、每公頃稽查機構數量以及每個機構在職稽查人員數量作為投入指標,將每個機構稅收收入額和每位人員稅收收入額作為產出指標,利用DEA-malmquist 指數模型計算得出綜合效率值衡量地方政府的征稅努力。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4。

表4 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估計
本文構建并行多重中介模型,選用2008 年—2020 年間的30 個省份(不包括西藏)的面板數據檢驗中介變量來反映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稅收增長率與財政空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呈負相關,表明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有正向效應,即β≠0,驗證作用機制的前提條件成立。
1.作用于市場主體的中介效應檢驗
估計結果如表5 所示。列(1)和(2)解釋變量稅收收入增長率和消費規模的系數都為負值,說明減稅會對消費規模和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產生正向影響,與理論分析相同。列(3)減稅和消費規模的系數都顯著,說明部分中介效應存在,占比為13.14%,減稅通過增加地方的消費規模來促進地方財政可持續性。自助法的間接效應系數在10%顯著性水平上證明了上述結論,減稅有效降低市場主體的稅收負擔,增加可支配收入,降低物價,擴大消費規模,刺激經濟增長,實現“放水養魚,反哺財政”。

表5 市場主體作用機制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列(5)中解釋變量tax 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在我國地方政府通過減稅刺激投資是可行的。列(6)中稅收增長率和投資規模的系數均顯著且γδ 和β'同號,則認為直接效應顯著并且中介效應占比為16.41%,證實假說投資規模是減稅促進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有效中介機制,這主要是因為減稅有效地緩解融資約束和降低投資成本,增強了市場主體的投資意愿。同時,比較消費和投資的中介效應占比以及間接效應系數可知,投資規模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貢獻率大于消費水平,這可能是因為政府為追求政績更傾向于見效快,力度猛的投資方式來拉動地方經濟發展。
列(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證實減稅對地區創新能力存在激勵效應,因為減稅提高創新的投資回報,同時放松創新的融資約束。但列(9)創新能力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正向作用不再顯著,因Sobel檢驗的前提條件為γδ 服從正態分布,存在不準確性,因此采用自助法檢驗,結果表明間接效應系數為負,但其并不顯著,認為間接的中介效應不存在。上述實證結果說明,減稅可以提高地區的創新能力,但創新能力和地方財政可持續性間的傳導鏈條過長,渠道有阻,因此,減稅對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動發力來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可行性低。
綜上,減稅會擴大市場主體的投資和消費規模,釋放地方經濟活力,從而提升地方財政韌性。但創新不能作為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只能通過半段檢驗,創新對財政可持續性的傳導機制不暢通。
2.作用于地方政府的中介效應檢驗
估計結果如表6 所示。列(11)財政收入結構扭曲程度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減稅會導致地方政府擴大“自由裁量”的非稅收入規模,與理論研究一致。但列(12)財政收入結構扭曲程度的系數不顯著,意味著增加非稅收入并不一定破壞地方財政可持續性,而是地方政府化解減稅政策成本的一種暫時性過渡。同時,采用自助法檢驗,結果表明間接效應系數不顯著,在統計學意義上認為中介效應不存在。

表6 地方政府作用機制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列(14)稅收增長率與征稅努力呈正相關,也就是說減稅會使得地方政府降低征稅努力,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在財權事權不匹配的情況下貫徹實施減稅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加劇其財政資金緊張程度,中央政府則會加大轉移支付來改善地方窘境。轉移支付對地方來說是一種成本為零的收入,此時,地方政府會更傾向于中央救濟。列(15)征稅努力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符合理論預期,提高征稅努力可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促進財政可持續性。列(15)中稅收增長率顯著為負且γδ 和β'異號,認為存在15.72%的遮掩效應,也就是說減稅對征稅努力的作用抑制了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綜上,減稅會轉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如提高非稅收入,降低征稅努力。但提高非稅收入與抑制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不存在顯著的必然聯系,非稅收入是地方政府緩解減收的一種過渡性機制,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不具備必然的抑制作用。征稅努力是減稅降低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作用機制,但其對減稅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正向效應是有限的。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減稅政策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效應作為研究對象,利用財政反應函數求得負債率理論上限值與實際值的差額來量化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實證分析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影響效應,借助中介效應來驗證減稅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影響的作用機制。通過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減稅背景下,我國地方政府確實存在著“財政疲勞”現象,即地方政府改善財政狀況的能力不足,通過基本盈余彌補債務的能力有限,財政可持續問題需加以關注。
第二,創新對財政可持續性的傳導機制不暢通,但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減稅來為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輸送活力,刺激經濟發展,培植財源和拓寬稅基,從而有效地提高財政可持續性。提高非稅收入影響財政可持續性的路徑不顯著,征稅努力的中介效應顯著,但是其作用有限。因此,總效應是減稅政策促進地方財政可持續性。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明確減稅目標以理順地方財政收入機制。研究結論可知,減稅促成的良好經濟運行可以彌補減稅的政策成本。經濟基礎是維持地方財政可持續性、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壓力的第一要義,因此,減稅的目標應該聚焦于推動經濟發展,拓寬地方政府的稅收基礎,發揮減稅對財政的反哺作用。一方面,加大對投資的稅收優惠支持力度,增強微觀企業的投資意愿,重視國家對“穩增長”的關切;另一方面,減免與消費相關的稅目,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的助推作用。
第二,完善財政體制,清晰界定各級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使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匹配。當前地方政府存在“財政疲勞”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遠不足以彌補其承擔責任所需的資金需求。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合理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對維持地方財政可持續性起著決定性作用。首先,應重視地方稅體系的完善,為地方政府開辟穩定持續的稅源;其次,改善地方財政支出結構,轉移部分直接支出責任,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確保用到實處,用出成效;最后,規范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增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資金,維持地方政府財政可持續性。
第三,建立綜合考評機制以加強政府預算約束和稅收征管努力。研究結論顯示地方政府因中央政府的補助收入極易出現“道德風險”問題,因此,中央政府首先應建立撥付審核機制,考核資金使用績效,從而提高補助收入的獲得成本,降低地方政府對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其次,加強預算績效考核,堅持預算法定原則,控制地方政府的赤字規模和非理性的借債行為,降低財政風險。最后,地方政府應改變工作態度,簡化工作流程,提高征稅努力,積極主動地為地區內的納稅人科普稅收優惠政策,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增強企業的獲得感,打造良好政企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