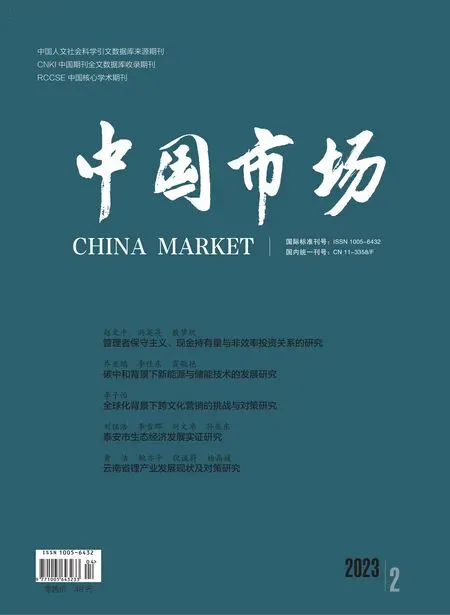政策宣傳與經濟激勵對居民快遞包裝回收意愿的影響研究
——基于計劃行為理論
靳亞鑫,游詩靈,顏 露,裴若菲
(合肥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9)
近年來,隨著電商的迅速崛起,快遞行業呈現井噴式發展,但快遞包裝的巨大浪費加大了環境壓力。因此,促進快遞包裝回收利用,提高包裝利用率,是當前城市面臨的重要課題。計劃行為理論(TPB)作為理性行為理論(TRA)的繼承者,可以用于研究人是怎樣改變自身行為模式的,其已廣泛運用于諸多領域,但用于快遞包裝回收行為的研究相對較少。
文章以合肥市為例,在TPB基本變量中加入政策宣傳和經濟激勵,提出相關研究假設,構建城市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的TPB擴展模型。針對調查問卷數據進行分析并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剖析合肥市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影響因素。最后針對回收環節中的突出主體城市居民,提出相應結論與建議。
1 文獻綜述
1.1 快遞包裝回收
快遞包裝的回收問題早已存在,來自倫敦大學Stijnvan Ewijk,Julia A.Stegemann于2020年在WasteManagement上發表的“Recognizing waste use potential toachievea circulareconomy”中對廢物循環利用提出自己的看法[1]。刁玉語、郭志達(2021)從合作激勵視角出發,描述政府、驛站、消費者相關利益問題,建立三方博弈模型,推導三者的策略選擇[2]。喬瑞良(2021)從政府立法角度出發,強調我國快遞包裝回收立法必要性及當前立法存在的問題,提出快遞包裝回收的立法保障[3]。謝蔚(2021)基于問卷調查從用戶層面研究群體行為與意愿的關系,建立基于Stackelberg理論的政府-企業博弈分析模型[4]。胡鑫(2021)比較快遞包裝的兩種回收模式,探討政府規制措施對各主體回收快遞包裝決策的影響[5]。鄭克俊等(2020)采用對比研究法,從政府的政策法規、消費者的利益感知與社會責任這三個維度構建快遞包裝回收再利用的綜合激勵體系[6]。
基于上述文獻的研讀,發現當前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回收機制、回收現狀等方面。文章將以居民參與回收作為出發點,通過問卷調查、實地走訪及模型構建研究城市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
1.2 計劃行為理論
城市居民參與快遞包裝回收的意愿受多方因素影響,文章選用TPB作為理論基礎進行因素量化分析。計劃行為理論(TPB)由美國學者Ajzen[7]提出,主要包含行為態度、主觀規范等五個要素。TPB理論認為,所有可能影響行為的因素都經由行為意向間接影響行為,而行為意向受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三項因素影響。
第一,行為態度指行為主體對實施某一行為結果的積極評價或消極評價[7]。城市居民作為回收主體,其態度決定快遞包裝回收的初始環節。當居民對包裝回收秉持積極、主動的態度時,其回收意愿更強烈,更有利于快遞包裝進行回收。
第二,主觀規范是指個體所感知到的社會壓力對某行為的支持或反對[8]。城市居民在決定是否參與快遞包裝回收活動中,會受到家人、朋友、政策制度等影響,政策對快遞包裝回收支持程度高,會對居民參與回收產生一定的引導作用。
第三,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體認為自己能夠控制并執行某種行為的容易/困難程度[8]。知覺行為控制能力越強,說明個體執行某特定行為越容易。一般而言,城市居民參與快遞包裝回收的流程越簡單,其知覺控制越強,參與回收意愿程度越高;反之,參與回收意愿程度越低。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H1a、H1b、H1c和H1d。
假設H1a:回收態度正向影響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
假設H1b:主觀規范正向影響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
假設H1c:知覺行為控制正向影響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
假設H1d:行為意愿正向影響行為。
1.3 合肥市居民快遞包裝回收意愿的其他變量與假設
1.3.1 政策宣傳對回收態度、主觀規范與行為意愿的正向影響
人類行為促進社會政策產生,同時,社會政策也在修正人類的行為,兩者相互作用,可見政策的宣傳推動對于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多數文章已將政策宣傳用于意愿研究中。Calvin Wan[9]等發現政策宣傳顯著正向影響回收行為意愿。牟雅婷[10]認為政策分別通過不同種類政策工具形式影響廢舊手機回收,政策工具對于居民廢舊手機回收具有正向影響。Schneider和Ingram[11]研究發現,政策宣傳作為重要動機影響人們的態度與行為意愿。調查發現,政策宣傳有助于普及包裝回收的必要性,使居民回收意識得到增強,可見政策宣傳對主觀規范具有正向影響。綜上所述,提出假設H2a、H2b和H2c。
假設H2a:政策宣傳正向影響回收態度。
假設H2b:政策宣傳正向影響行為意愿。
假設H2c:政策宣傳正向影響主觀規范。
1.3.2 經濟激勵對回收態度與行為意愿的正向影響
近年來,相關學者相繼提出激勵理論激勵消費者,調動消費者積極性。綜合學者觀點,文章經濟激勵具體表現為居民參與快遞包裝回收的經濟回報。藺泓濤等[12]曾基于城市居民視角研究包裝回收,發現經濟激勵能較好推動居民回收,表明經濟激勵對快遞包裝回收具有顯著正向作用。曹星[13]研究發現,快遞包裝回收中消費者行為意愿受經濟激勵的正向影響,且經濟激勵有助于提高居民包裝回收的感知收益,正向影響居民的回收態度。故提出假設H3a和H3b。
假設H3a:經濟激勵正向影響回收態度。
假設H3b:經濟激勵正向影響行為意愿。
2 研究設計
2.1 假設模型
文章以擴展TPB模型探討城市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首先,政策宣傳與經濟激勵作為外在影響因素,對居民回收行為意愿具有潛在影響。政策宣傳通過普及回收知識與必要性中介影響態度與主觀規范影響行為意愿。其次,經濟激勵由于增加居民感知利益進而中間影響居民回收態度影響行為意愿,期望擴展后TPB模型對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有更高的解釋力。
2.2 資料收集
為研究以上假設,本研究將各概念性變量進行指標化測量,采取李克特量表進行測量。政策宣傳借鑒Calvin Wan等[9]提出的5個題項進行測量,如“我了解政府部門有出臺快遞包裝回收處理政策”。經濟激勵借鑒曹星[13]提出的3個題項進行測量,如經濟激勵(如回收累計積分用于減免快遞費等)會使我更愿意參與回收。回收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愿、行為借鑒,Chen等[14]提出運用成熟量表進行測量。研究選擇合肥市城市居民作為總體樣本,正式調查前小范圍內進行預調查,回收93份有效問卷,所得結果潛變量KMO值均高于0.7的可接受標準且各潛變量因子能被很好區分,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結構,因此確定問卷設計較合理。
3 結果分析
3.1 樣本統計分析
正式問卷發放并回收,剔除填答不完整者,共收集到有效樣本371份。性別方面,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相近;年齡方面,23~35歲與36~50歲所占比例較多,分別為28.3%與29.1%;受教育程度方面,以本科生學歷居多,占47.2%,其次為大專學歷,占22.9%;職業方面,以專業人員(如醫生等)最多,占比23.2%,其次為政府/機關干部/公務員,占比20.5%;月可支配金額方面,以5001~8000元最多,占比29.6%,其次為3001~5000元;平均每月取快遞數方面,以2~5次居多,占45.0%,其次為6~9次,占19.9%。整體而言,本研究受測者以23~50歲的青壯年為主,男性與女性比例相近,受教育程度多為大學水平的專業人員以及政府/機關干部/公務員,且大多數受測試者平均每月取2~9次快遞。
3.2 數據分析
3.2.1 信效度分析
信效度分析結果顯示其整體Cronbach's α為0.934,說明其呈現出較高的信度,且各變量的Alpha值均大于0.9,表明內部一致性良好。效度檢驗結果顯示KMO統計量的值為0.812,Bartlett's球形檢驗值為2093.272,在自由度為210的條件下及0.000水平上達到顯著水平,說明快遞包裝回收問卷中各量表題項矩陣間存在顯著差異且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3.2.2 驗證性因子分析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回收態度等7個維度的組合信度均大于0.7,且各維度的平均抽取量(AVE)均大于0.5,位于0.6以上,結果顯示擬合指數較理想。綜合來看,本研究認為該驗證性因子分析模型符合適配指標。
3.3 整體模型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 28.0進行結構方程擬合度檢驗。結果如表1顯示,模型的各項參數指標大體滿足標準要求,僅IFI未達到標準結果,說明初始模型可用于檢驗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影響因素,數據擬合效果合理。

表1 修正前后測量模型擬合度指標
路徑顯著性檢驗度量模型變量間影響程度的定量關系。通常在0.05的顯著水平上,臨界比值絕對值高于1.96時,路徑影響顯著。通過初始模型研究發現,除經濟激勵→回收態度路徑系數不顯著,假設H3a未得到支持外,其他路徑系數顯著的假設支持。因此,文章進一步修正模型,刪除模型中影響關系不顯著的路徑。
修正后模型結果顯示,χ2/df為2.190,小于3.00;RMSEA值為0.036,小于0.06;且GFI為0.904,CFI為0.934,IFI為0.939,大于0.09,滿足標準,表明修正后模型適配情況較佳。修正后模型路徑關系如表2所示,當顯著性檢驗概率P<0.05時,路徑系數顯著,且C.R.絕對值大于1.96,表明模型各路徑關系通過假設檢驗,假設支持。

表2 路徑分析顯著性與標準化系數
研究模型路徑系數如圖1所示。

圖1 本研究理論模型的標準化路徑系數
4 討論
4.1 TPB擴展模型對快遞包裝回收行為的預測能力
政策宣傳與經濟激勵是快遞包裝回收意愿的重要影響因素,為此對TPB模型進行擴展。據此推論,促進政策宣傳與增加經濟激勵有助于快遞包裝回收工作的開展。此外,主觀規范對于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具有很大影響,當個體感知到的快遞包裝回收社會壓力越大,或越支持快遞包裝回收時,其回收行為意愿越強烈,進而直接增強包裝回收行為。
4.2 政策宣傳與快遞包裝回收行為的關系
結果顯示,快遞包裝回收態度與主觀規范受政策宣傳的積極影響,證實政策宣傳可直接影響快遞包裝回收意愿,亦可通過回收態度與主觀規范的中介作用影響快遞包裝回收意愿。通過政策宣傳促使居民意識快遞包裝回收的必要性,正向影響回收態度;同時,政策宣傳促使居民了解相關制度規定,對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產生約束性,增加個體感知社會壓力,對主觀規范產生積極影響。
4.3 經濟激勵與快遞包裝回收行為的關系
結果表明,經濟激勵無法通過影響回收態度影響快遞包裝回收意愿,究其原因,本次調研群體總體存在一定的分布偏差,其中政府工作人員、企業員工占比較大,群體收入水平偏高,故最終經濟激勵→回收態度影響路徑不顯著。此外,研究證實經濟激勵可直接影響行為意愿,即回收累計積分、快遞費減少有助于正向影響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強化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與曹星[13]的研究結論一致。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經研究發現,政策宣傳可對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產生一定影響,但現階段回收政策對居民的宣傳教育與約束作用較薄弱。政府可通過公益廣告及開展快遞包裝垃圾回收活動等形式,加強對快遞包裝回收的政策宣傳,幫助居民認識其重要性及個體責任,引導居民參與快遞包裝回收活動。
(2)就經濟激勵而言,本研究表明一定的經濟激勵可促使居民主動參與快遞包裝回收,這提醒相關快遞企業可實行一定的激勵措施激勵消費者,如對主動進行回收的消費者進行積分、代金券或優惠券獎勵等,對回收量較大的消費者進行小禮品獎勵等。
(3)快遞包裝回收利用須通過政府、居民、快遞企業三方協同合作。居民快遞包裝回收作為包裝回收起始性環節,需更多研究改善居民包裝回收TPB擴展模型的測量能力,調動居民回收積極性,提出快遞包裝回收循環利用的良方。
5.2 建議
本研究選取合肥市居民進行調研,研究經濟激勵與政策宣傳對合肥市居民快遞包裝回收影響情況,但因調研群體存在一定偏差,可能導致此次調研受樣本變異影響。首先,未來研究可在擴展TPB模型基礎上比較各變量對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解釋力是否存在差異,尤其是經濟激勵的影響作用。其次,回收成本多認為是居民快遞包裝回收意向的前因,可加入回收成本于擴展TPB模型中,驗證其模型預測貢獻度。最后,調查針對合肥市居民開展,僅代表合肥市居民相關看法,可進一步研究其他省市居民快遞包裝回收行為意愿,為進一步促使居民回收提出更加全面可靠的建議與意見。